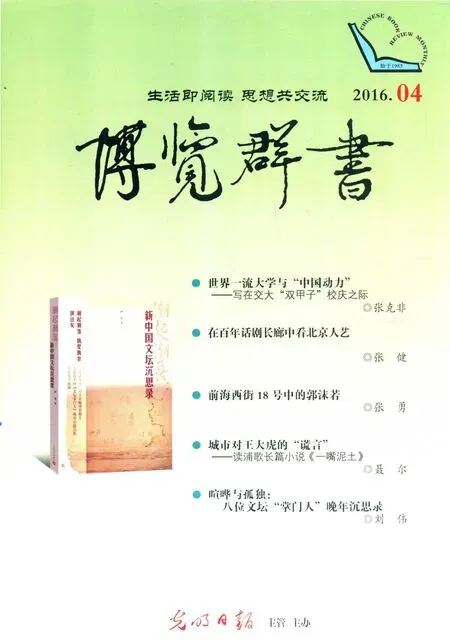流沙遗坠简 春风度玉关
张存良
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成王时期的宝器何尊,内底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一语,这是迄今“中国”一词最早在文献中的记载。但此时的“中国”,地域还非常有限,仅指东都成周(洛阳)及其周边的地区,“中国”以外谓之四夷。
壹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所谓“九州禹迹,百郡秦并”,疆域空前广大。《史记》记载说:“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根据湖南等地出土的秦简史料,秦统一后在东南地区仍有兼并扩张,加上对原有一些大郡的分割析置,秦的郡置最盛时多达四十八郡。但是黄河以西,即广义的河西地区,仍是风化未及的所谓“蛮荒”之地。
秦汉之交,活动于漠北高原的匈奴空前强大,南下牧马,侵陵“中土”。原来生活于河西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人被迫西迁,匈奴占据了河西,不断侵扰“据河为塞”的中原王朝,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汉武帝初期,国家的大政即是倾其全力解决边患问题,兴造功业,后世莫及。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通过派遣使臣,汉廷对西域诸国的山川形胜、道里远近和人口兵力(胜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经过几次大的战役之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西汉王朝“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杜度《论都赋》),在河西地区前后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一度向西延伸到了天山南北两路,于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标志着“中国”版图的空前广大,政治势力已达天山南北。
汉朝夺取河西之地以后,不仅“裂四郡,据两关”,还兴修大规模的军事防御体系即长城和交通驿站,自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直至敦煌西陲的玉门关(今小方盘城),同时沿黑河北上,修筑“居延塞”直达黑河尾闾的居延泽,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防御体系,史家谓之“汉塞”。自敦煌以西到盐泽(今罗布泊),“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从此“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文化贸易往来不绝如缕,成为海路开通之前中国与世界交流融通的重要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诗意般地称为“丝绸之路”。
贰
由于中国传统修史体例和抉择裁取的限制,有关长城防御和丝绸之路的记载非常简略,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非常匮乏,以至后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也是雾中观花,难得要领。近代以来,在“地理大发现”思潮影响下的西方探险家们,怀惴各种使命和信念,来到中亚和我国西部的新疆、甘肃、西藏等地,开展他们的各种探险和调查活动。斯文·赫定发现了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楼兰古国,斯坦因发现了沉寂在沙丘中的于阗古国,贝格曼发现了“楼兰美女”沉睡的小河墓地。一时间,中国西北探险成为国际热潮,各种探险队蜂拥而至,曾经遗落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大量遗址被粗暴地挖掘翻捡,各种文物被巧取豪夺捆载而去,西北探险史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伤心史”。
1900年前后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敦煌文书和敦煌汉简,更是近代以来学术“四大发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文书最新的统计数量是7万多件,自发现之日起,就被各国列强瓜分四散,现分藏在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文书中保存的吐火罗文、于阗文、梵文等古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献,映证了历史上中西交流的繁荣兴盛,通过释读解析这些古老的“外邦”文献,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中古时期往来于繁忙丝路上的商旅驼队和使者往来。
1907年3月,“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斯坦因来到甘肃敦煌,他在寻访敦煌文书的发现者王圆箓而不遇的情况下,试掘了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意外发现了大量汉代木简(比较完整者700馀枚,另有近2000枚削衣杮片,现均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这是敦煌汉简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发现,也是甘肃简牍的第一次集中出土。年代可考者最早为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最晚至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
甘肃简牍的第二次大发现是居延汉简的出土。1930年4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今额济纳河流域(黑河下游)首次发现汉简,随后在此流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10000余枚,是20世纪上半叶出土古代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消息传来,震惊中外。黑河下游的额济纳河流域,古称“居延”,所以习惯上称这批汉简为“居延汉简”。
1949年之后,甘肃简牍的出土和保护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所有出土简牍都收藏于甘肃本地,整理成果逐年发布,供全世界学人研究之用。因甘肃在汉代简牍的出土数量上位居全国之首,而且简牍形制之丰富、文书种类之繁多,实属宏富,堪为两汉简牍形制的渊薮、行政文书的宝库,对于研究简牍形制源流与两汉文书政治,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历史价值,从而为甘肃赢得了“简牍之乡”的美誉。1949之后比较重要的发现有以下几个批次:
武威汉简。主要包括《仪礼》简、王杖简和医药简。《仪礼》简195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共计469枚,整理者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种。其中甲本398简,有《士相见》《服传》《特牲馈食》《少牢馈食》《有司彻》《燕礼》《大射》七篇,除《士相见》一篇完整外,其馀六篇均有缺失。乙种37简,只有《服传》一篇,内容与甲种《服传》相同。丙种34简,《丧服》经一篇。“王杖十简”是1959年在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的,1981年又在該地收集到《王杖诏令册》26枚。二者互为补充,记录了两汉时期尊礼高年、优抚老人的诏令和案例。武威医药简共92简,1972年出土于旱滩坡东汉墓,包括30多个医方,100多种药物,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灸科等,是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遗产。
居延新简。1972-1974年甘肃省考古工作队在额济纳河流域的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等遗址连续发掘所获20000多枚汉简,是继上世纪30年代这一地区发现汉简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了区别,习惯上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新简内容丰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就有70多个。最早的纪年简为昭帝始元二年(前85),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前后跨越200多年,是研究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汉简。自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汉简以来,这一地区时有零星简牍发现,1949之后大规模集中出土是1979年10月的马圈湾考古发掘(敦煌西北95公里的汉代大煎都候官遗址),共出土汉简1217枚,最早纪年为元康元年(前65),最晚为王莽地皇二年(21)。这批汉简中保存的大量出入玉门关的记录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的史料,而王莽时用兵西域的公文奏疏对研究新莽政权与西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天水放马滩秦简。1986年出土于天水市北道区(今麦积区)党川乡放马滩一号秦墓,共计461枚竹简,另有木板地图7幅,时代为战国晚期。竹简内容主要分为《日书》甲乙种和《志怪故事》(《丹还阳记》)三种,其中甲种《日书》73枚,包含《月建》《建除》《亡盗》《吉凶》《禹須臾》等,乙种《日书》381枚,包含《月建》《建除》《置室门》《门忌》《方位吉时》《地支时辰吉凶》《昼夜长短》《人日》《五音日》《六甲孤虚》《六十甲子》《占候》《禹步》《星度》《纳音五行》等30多篇文献,内容极为丰富。
悬泉汉简。出土于今瓜州至敦煌间的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置是邮驿机构,负责文书传递和往来人员接待等工作。集中发掘于1990-1992年,共出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无论就其数量和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发掘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悬泉汉简都可称之为百年来西北简牍出土之最。最早纪年是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集中反映了200多年间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相关史实,对于研究两汉邮驿制度、中外关系、丝路交流、民族关系以及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和经济社会等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水泉子汉简。2008年9月出土于永昌縣境内大黄山脚下的水泉子汉墓,共计1000余枚,残损严重,内容分为《日书》和《苍颉篇》两类。《日书》是国内目前所知时代较晚的汉代日用杂占书籍,内容丰富。《苍颉篇》是在原有四言韵语的基础上增编而成的七言韵文,为国内首次发现。
叁
西北汉晋简牍的发现,是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伤心史”分不开的。罗振玉在得知斯坦因掘得汉晋简牍并运往英伦之后,禁不住发出“神物去国,恻焉疚怀”的伤叹。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居延汉简,最初入藏在北平图书馆,后转移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即北大红楼)进行整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觊觎藏在北大红楼的居延汉简,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冒着生命危险,几经辗转,从天津经海路将这批国宝运至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寄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居延汉简再经沈仲章、徐森玉以及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和驻美大使胡适等人的奔走协助,远渡重洋,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居延汉简从美国运回台湾,收藏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批汉简在收藏保护中的颠沛流离,也充满了辛酸之痛。
西北汉晋简牍的发现,同时也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转型精进是密切关联的。从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掘出第一批汉简开始,简牍研究就具有国际化色彩。法国汉学家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对这批材料进行了整理,于1913年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与此同时,应流寓日本的罗振玉之请(1911),沙畹还将简牍照片和考释手稿寄给了罗振玉,罗在王国维的协同下,撰成《流沙坠简》一书,于1914年在日本刊行。
这两部基于敦煌汉简的考释著作是近代以来简牍学的奠基之作,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尤其是《流沙坠简》,开启了分类著录和释读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其后的简牍研究具有范式意义。王国维利用这批汉简材料,结合斯坦因的考察地图和考古报告,深入系统地考证了汉代敦煌境内的长城遗址、汉代玉门关的关址、海头城的位置(海头非楼兰)和西域长史的设置等问题。这种将田野考古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是对清代以来文献考据学的一个重大突破,也将清代以来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影响深远。鲁迅曾称赞说: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沙畹的弟子马伯乐在沙畹之后继续从事斯坦因所获西北简牍的研究考释工作,他的中国助手张凤在上世纪30年代编成《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向国内及时公布了相关简牍材料。德国汉学家希姆莱和孔好古相继整理斯文·赫定在楼兰所获汉文简纸文书,于1920年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一书。
居延汉简发现之初,中国方面先后有刘半农、马衡、向达、劳榦、贺昌群、余逊等人从事释读整理,同时邀请了瑞典学者高本汉、法国学者伯希和等人参与整理,出土简牍既为传统国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居延汉简颠沛流离、客居他乡之际,从事居延汉简整理研究的人员也离散四处、居无定所。唯劳榦以一人之力,于流徙中研读不辍,草创完成并在四川南溪印行了石印本《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3)和考证之部(1944)两书,1949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铅字本《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其他学者如贺昌群、陈直、陈邦福、马衡、傅振伦、陈槃、严耕望等人,也各自结合研究所长,多有著述。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利用大陆所留资料,编辑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一书。陈梦家结合贝格曼的考古报告,全面复原出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城障的分布情况,对汉代边塞的防御组织系统、烽燧制度、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简年历以及汉代简册制度等,都有系统深入的研究。随着两岸的互通往来,居延汉简的资料得到了共享,198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汉简终于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批露。台湾马先醒等人依原编号重新排比校勘,编成《居延汉简新编》(1981),其后邢义田等人又补缀拾遗,编成《居延汉简补编》(1998),居延汉简的释读刊布才算告一段落。
自居延汉简陆续公布以来,尤其是居延新简出土公布之后,日本学术界掀起了汉简研究的热潮,先后涌现出了森鹿三、藤枝晃、永田英正、大庭脩、冨谷至、池田知久等著名学者。森鹿三在京都大学组织了汉简研读班,大庭脩在关西大学创办汉简研究会,都为日本简牍学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劳榦到了台湾之后,继续从事整理研究工作,于1957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劳榦在台湾还培养了一大批后继人才,如马先醒、吴昌廉、邢义田、廖伯源等人,在国际简牍学界都享有盛誉。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家文物局召集国内专家,在北大红楼开启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其中也包括居延新简的整理出版,于豪亮、谢桂华、朱国炤、李学勤、裘锡圭、初世宾、李均明、何双全等著名学者先后参与此项工作,确立了集中各方力量、集体讨论定稿的简牍整理方式,影响及于今日。1949年以后,特别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其他地区出土的简牍(帛)呈明显增多之势,总数已多达40多万枚。数量既多,品质也优,既有汉简,也有战国简、秦简和三国吴简,简牍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研究人员日益增多,学术影响如日中天,简牍学已然是当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新的学术增长点。甘肃既是简牍出土大省,同时也是简牍研究的重镇。为了更好地保护研究甘肃简牍,甘肃省于2012年12月成立了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继湖南长沙中国简牍博物馆之后的第二家专业博物馆,近年来已整理出版《玉门关汉简》《金关汉简》《悬泉汉简》等多部大型图版图录,为简牍学研究不断注入活力。
(作者系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档案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