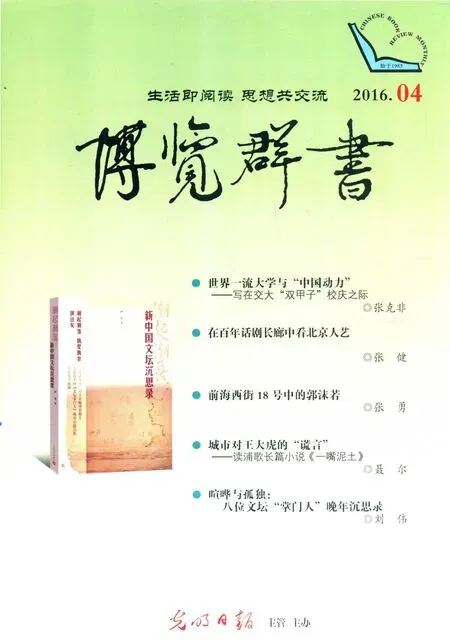没想到《银川赋》会有那么多波折
庄电一
我没想到,一篇《银川赋》会经历那么多的波折,背后会有那么多的故事,延续时间会有这么久。
2008年1月28日,光明日报配图刊登了李增林教授与我合写的《银川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也被许多媒体转载,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宁夏著名诗人韩长征看到《银川赋》后,当即赋诗一首并亲自送到我的手上,我看这首诗写得很好,就转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2月21日,这首《喜读〈银川赋〉》与《曲阜赋》在同一个版面上刊登出来。诗云:
百城吟颂相期久,
终盼华章唱银川。
览尽汉唐西夏月,
来游塞上艳阳天。
湖城广厦织锦绣,
阔道雄风振远帆。
彩凤来仪歌美赋,
稻香肥鲤胜江南。
显然,这是仔细阅读了《银川赋》的产物。
许多人也不会想到,这篇《银川赋》差一点就“流产”了,而知道它曾有过三个“版本”的人则更少。
西藏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苟天林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后,报社进一步突出了光明日报的文化特色,相继推出了《光明讲坛》《走进大家》《国学》《母校礼赞》等许多“文化味”很浓的专刊、周刊,其中2007年推出的《百城赋》,更是引起热烈的反响,全国各地文化名城和文艺界知名名家都跃跃欲试,希望在这个栏目里一展身手,报社也要求各地记者站主动联系当地宣传部门和文化名人组稿,但最初并没有明确本报记者不能写稿。很快,《西安赋》《武汉赋》等有本报记者联名的城市赋,就与读者见面了。银川虽然地处大西北,但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当然不能游离其外,我自感有责任促成其事。为此,我及时向时任银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尤艳茹通报了这个情况,请她邀请本地文化名人写《银川赋》。尤艳茹说:“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何必要另外请人写呢,庄老师,您就自己写吧!”这个回答令我感到意外:“我写?我可从没有写过这类东西啊。再说,我只是个普通记者,也没有这个能力啊!”虽然尤艳茹部长一再鼓励我,但我只答应先试一试,并一再强调这并不表明我已经作出了承诺。如果试过之后感觉不行,到时候还得另找他人。说“试一试”容易,真正写起来可就不容易了。这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基础,而且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力,还要能轻松地用文言文写作,而更为重要的,是搜集、整理、筛选素材,既要敏锐地发现所在地区的特点和“亮点”、充分反映其独有的东西,又不能主次不分、堆砌材料、杂乱无章。而对于《银川赋》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没有人向我提出要求,哪些是可以一笔带过的,哪些是不能遗漏的,哪些是要重点表现的,都要自己掌握,并没有人为我“指点迷津”,所有这些,不仅需要自己作出准确判断,而且要拿捏有度。每个提法,都要有依据;每个判断,都要经得起推敲,因为它不仅要经得起相關领导的审查,而且要经得起广大读者的检验,所以,这比写一篇通讯或散文,可要复杂得多,费劲得多。
在冥思苦想、字斟句酌了两个月之后,我于2007年4月15日完成了《银川赋》的第一稿,我在开头写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此久徘徊:分出细流润田野,婉转温柔留关爱!君不见,贺兰骏马地下生,海洋消退冰川融:展翼分身做屏障,呵护绿洲献真情。
我力图用这短短几句勾勒银川以贺兰山为父、以黄河为母的地理优势,以求先声夺人。
我将初稿发给尤艳茹部长。尤部长看后又打印出来,送给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崔波(现任自治区政协主席),没想到,崔书记对此稿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批示中说他读了以后“很感动”。
银川市这边通过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就信心十足地将稿件传到了北京。
几天后,《百城赋》的责任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基本肯定了我这一稿《银川赋》,但又说出了一个我原来不知道的情况:按报社的策划方案,《百城赋》是邀请当地文化名人来写,记者站只负责组稿、不负责审稿,本报记者也不署名,以前本报记者与人联合署名的情况,也不能再出现。不过,考虑到我已提交了稿件且稿件基础不错,编辑部决定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找一位当地文化名人合写,《银川赋》将成为最后一篇有本报记者署名的《百城赋》。
那么,与谁合作呢?我在大脑里搜索一番,很快就“锁定”了曾经担任过宁夏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首任院长、宁夏政协副主席、古典文学基础雄厚、在宁夏也颇负盛名的李增林教授,因为他完全符合“当地文化名人”的定位。在电话中,我说明了情况,老先生十分高兴,一口应允。随后,我便按他的要求,把《银川赋》的第一稿和之后的改稿以及手头的所有资料都亲自送到了他家。2007年9月,李增林教授信心满满地拿出了第二稿。看到他的“银川赋”第二稿,我有点意外,因为他这一稿几乎是“另起炉灶”,抛开了我原来的架构。虽然用了我提供的许多“泥土”和“砖块”,但他又补充了一些新材料,行文风格也与我的第一稿大相径庭。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极为认真的,也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对这样一位写了几十年格律诗、文学功底深厚的老诗人,我是十分尊重的,再说,此稿是以他为主,我就不想,也不能再改动了。
在我看来,写这个东西,对李增林教授来说是小菜一碟,因为对他充满信任,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未与他有过多的交流。出乎意料,编辑部竟然对以他为主的这一稿很不认可。责任编辑专门打来电话,提出修改意见。这让我有些为难:怎样把这个情况告诉李增林教授?如果李教授提出异议,又该怎样操作?最终,我还是原原本本地把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转告了李先生。我知道,这对满腹经纶,又为此耗费了大量心血的老教授来说,不啻当头浇下一瓢凉水,所以,我是掂量好了用语才开口的。尽管我的语气很缓和、通报的信息也有保留,但还是惹恼了老先生。他很生气,以断然的口气说:这个事,我再不参与了!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弄什么样都与我无关!我委婉地做了解释,希望他能继续参与合作,与我一起按编辑部的要求修改,但无论我怎么说都无济于事。当然,他不可能知道,报社领导是把《百城赋》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的,对每一篇都三审五审、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反复修改、不断完善也不是个别现象。
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放弃吗?难道能让前面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吗?难道能让宁夏首府银川游离于《百城赋》之外、留下令人难堪的空白吗?如果就这样前功尽弃了,我觉得无法向报社交代,也无法向银川市领导解释。但是,如果另外再找其他合作者,我又很茫然。
好为难啊。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独立自主,不靠任何人,也不求任何人:自己动笔再写一稿,走一步,看一步!
主意一定,我就拿出我的第一稿,以此为蓝本进行反复揣摩。为此,我昼思夜想,寝食难安,但一连多日也没有理出头绪。终于有一天,灵感“从天而降”:何不借鉴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写法,以虚构人物对话的形式来推进故事、铺展全篇?这个灵感,竟然让我激动不已。很快,我就虚构了江南娇、西夏叟、无是君(意为“没有这个人”)三个人物,以南方美女江南娇“乘云御风”赴大西北探奇,遇到西夏叟、无是君,并由此二人介绍银川的今昔,进而达到宣传银川的目的。
这个创意,完全是我的“灵感”“乍现”,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启发,也未与李增林教授沟通、商议,因为他已经明确表态不再参与了。
有了清晰的思路,写起来就顺手了,我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稿。
此稿与前两稿有所不同,因为里面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
丁亥之秋,有名江南娇者,乘云御风,自江南北行,做探奇之旅。渐行渐远,景物凄惶,思绪无缰。晴空鸟瞰,丘壑如肠,绿意稀缺,一片昏黄。正昏昏欲睡之时,忽见大块绿洲,似珍珠闪光。
于是:
江南娇好奇之心复萌,探奇之心顿生,乃翩然徐降。但见湖泊相连,沟渠纵横,沃野无疆,稻浪翻滚,鱼虾戏水,硕果盈枝,竟不知身在何处,顿生疑虑:“此景只我家乡有,此地如何似故乡?”
这就引出了西夏叟、無是君二人的“释疑解惑”:
西夏叟弃棋子于案,起身作答:“人说西部都缺水,独我银川水连天。湖湖相连水抱城,串串珍珠如线穿。景观水道船行稳,鱼鳖虾蟹畅游欢。湖美鱼肥夺人目,垂叟钓童频甩竿。麦浪吟出和谐曲,稻香飘出丰收年。黄河滋养乳汁甜,塞上湖城不虚传。人人都说江南好,江南焉有此景观??”
无是君接言:“农田成档,林木成网,绘就巨绒毡;沟渠如丝,阡陌似线,织出大棋盘。旱奈我何?涝有何难?灌排通畅保无虞,得天独厚数银川!”
最后,引出“江南娇陶醉其中,心向往之:‘可得久居乎?’”,从不了解银川到要长留银川,江南娇的转变,折射出银川的魅力,全篇至此也就可以“收束”了。
这一稿,我写起来一气呵成,颇有点不吐不快、酣畅淋漓的感觉。
2007年11月28日,《银川赋》的第三稿脱稿了,但它是否能够得到各方的认可,我心里没底,因为有前两稿的教训,我甚至有某种莫名的担忧。在发给报社之前,还要解决一个问题:与谁合作?跟谁联名?按编辑部要求,本报记者不能独自署名,必须与人合作,《银川赋》让我挂名,已经是格外关照了。那么,应该找谁来联名呢?我又想到了李增林教授,虽然他说不再参与了,但他此前毕竟付出了很多心血,所以,我觉得不但不能绕开他,而且还要请他把把关,如果他能锦上添花那就更好了。于是,在征求了他的意见后,我把《银川赋》的第三稿打印出来,专程送到他家,请他审定。
李教授没有拒绝,也没有耽搁,很快就把草稿退还给了我。他只改动了几个字,既没有补充新的内容,也没有删除一句,更没有写任何评语。很显然,有了第二稿的波折,他兴致锐减,不想为此再耗费精力和时间了,也许,对我这一稿他也没抱什么希望。
我对李教授的“微调”“照单全收”,也未做新的修改,就在2007年12月初直接传回编辑部。为了突出李教授的身份和成就,我特意在文末的“作者简介”栏里多写了几句:
李增林教授,著名学者,长期教授先秦两汉文学。193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宁夏文学学会会长。曾任宁夏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院长、民盟宁夏区委主委、民盟中央常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有多部专著出版。(显然,我的介绍太多了,所以,见报时编辑删去了“曾任”以后的内容。)
自然,我把李教授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在发回北京之前,我也不好意思再打扰银川市领导:既然基本内容变化不大,也没有“出格”的东西,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请他们过目了。
没想到,这一稿竟顺利地通过了。事后,有人评论说,《银川赋》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角度新、写法活,令人耳目一新。在《百城赋》中,如果这个城市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个地方也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此城“美哉”“壮哉”,彼城也“美哉”“壮哉”,岂不是“百城一面”、缺乏个性?
2008年1月28日,《银川赋》与一幅国画、一幅彩照一起,以半个版的篇幅同时见报,我如释重负。从动笔写《银川赋》第一稿,到第三稿《银川赋》见报,历时十个多月时间。其间,我耗费的精力、经受的煎熬,只有自己能够体会。
《银川赋》末尾在“西夏叟抚掌大笑:‘……尊客欲长留于此,不亦宜乎?’”之后,原稿曾有“西夏叟笑言;‘如欲在此寻觅佳偶,老叟愿作伐。’江南娇赧然,笑而不语。”之句,之所以这样写,是想加点幽默、留点悬念,结果,这个“尾巴”被编辑部“毫不留情地”挥刀砍下,我虽有遗憾也只能“徒唤奈何”。当然,砍掉自有砍掉的道理,我只是一时未能理解而已。
《银川赋》见报之后,不仅被《宁夏日报》《银川晚报》《华兴时报》《夏风》等报刊及多个网站转载,被收入《百城赋》(下册)之中,《银川地名故事》一书还把它放在了 “突出位置”,光明日报编辑部也将它评为好稿。
《银川赋》的第三稿见报了,我又“贪心不足”,因为我不想让它的第一稿“胎死腹中”。在“敝帚自珍”心理的驱使下,我以《银川之歌》为名寄了出去,结果受到了文学月刊《朔方》的“垂青”。没想到,这篇“重见天日”的东西,还在几年才进行一次的文学评选中,获得了“宁夏文学艺术奖”二等奖。对我来说,获得新闻作品奖几乎是“家常便饭”,而获得文学作品奖还真不多,所以很兴奋。
对《银川赋》的第二稿未能与读者见面,李增林教授一直感到遗憾,他很希望拿出来发表。因为他为这一稿耗费了太多的心血。在与相关负责人沟通之后,他又征询了我的意见,我自然是完全同意。于是,我便按照他的意见将第二稿改为《银川颂》(为了避开《银川赋》)转发给了相关媒体,结果,陆续被《银川晚报》《华兴时报》《宁夏日报》《中华儿女》《西部专家》等报刊刊登。此后,此篇还在宁夏的两个征文活动中都获得一等奖。这也算是为这一稿正了名,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它的价值,印证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古语。
这样,《银川赋》的三个版本——《银川赋》《银川颂》《银川之歌》,就都有多次机会与读者见面了。不仅如此,未被光明日报刊登的《银川颂》和《银川之歌》也收获了不低的社会评价。这说明,各类刊物都有各自的用稿标准,各类编辑也都有各自的选稿眼光,不能用谁来否定谁,我在这里更无意做出判断和评论。
一次写作活动,有这么“丰硕”的收获,对我来说是喜出望外、始料不及的。这也印证一句老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对《银川赋》的写作来说,则堪称“一箭三雕”“连中三元”。
《银川赋》面世后,有人在网上做出评论:
《银川赋》文笔优美,立意高远,气势雄浑,如诗如画,是对银川城市文化品位的展示和提升,也是对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既是宣传银川、展示银川、塑造银川的城市“名片”,又是大气磅礴、思想深邃、意境非凡的文学“名篇”,让广大读者领略到银川的历史沧桑和魅力风采,让银川人民增添了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也曾有人建议将它刻在奖杯、奖牌、笔筒和石碑上,还有人建议摘出其中一些句子,印在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上,让人随处可见。宁夏书法家石虎麟还将它变成了书法作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这幅书法作品“可装点商场、宾馆、学校、工矿、乡镇、社区、景区等,也可作为珍贵的收藏品赠送友人” 。
有人不僅为此向银川市有关部门提交了书面报告,而且拉我在他们写好的报告上签字,但我没有响应这个“号召”,也不想对此施加“个人影响”。我的理由是:你们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我不反对、不支持,也不参与。因为我一向认为,对自己这样的普通文字工作者来说,写出来的东西,能够发表,且能引起社会关注,那就足够了,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或褒或贬,都交给读者、交给社会。如果过分“张扬”,那就是画蛇添足了,甚至是没有自知之明,一定会让人反感。
《银川赋》发表后,曾有人讳莫如深地问过我:“《银川赋》谁执笔?谁付出的多?”对此,我从不做正面回答,总是说:“既然是两人合写,就没有必要分那么清。”
对《银川赋》,曾有不少猜疑。因为我以往对诗词歌赋很少涉足,发表的文学作品也不多,而《银川赋》又是刊登在我所属的媒体上,难免会让人产生怀疑。有人可能认为是我沾了别人的光、“揩了别人的油”,是借工作之便、分了别人“一杯羹”。殊不知,我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学写诗,此后一直爱诗、读诗、学诗,偶尔也有诗作见诸报端,自认为还是有一点“写作能力”的,而在《银川赋》的写作过程中,我“搜肠刮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所以,独立完成这样一篇质量是“马马虎虎”、内容上“平淡无奇”的《银川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觉得没有解释的必要。
2016年4月29日,我应邀参加宁夏房车文化节,饶有兴趣地欣赏了文化节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书画作品。在一幅小楷上,我惊喜地发现了熟悉的内容:这不是《银川赋》吗?这幅书法作品,出自河南省一位书法家之手。而他在抄写时,《银川赋》发表已有8年多时间了,这让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我掏出手机拍下了整幅作品。但一看落款,又有点失望:上面只有李增林教授一人的名字,并没有我的名字,整幅书法作品似乎与我毫不相干,我如此关注岂非“自作多情”?但是,我除了默认,还能做什么呢?难道去找人理论吗?
又过了几年,在宁夏一份文学刊物上,我看到了当地一位资深文艺家评论李增林教授文学成就的文章,其中不仅提到了《银川赋》,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文中只把《银川赋》当成李增林教授一个人的作品,对我的署名则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对此,我也是“沉默以对”。
我有点想不通:难道仅仅因为名字署在后面,就被认为是可有可无吗?难道仅仅因为是在自己供职的媒体上联名发稿,就一定是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吗?虽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啊!
我向来不太看重个人的名利,我采写的新闻稿件,曾不止一次被人不打招呼就毫不客气地“借用”,有时简直是被“生吞活剥”,但我都没有吭过声,也没有与人对证过,更不愿为区区小事与人“撕破脸”,所以,《银川赋》被人“忽视”、被人误解,也同样不值得我过分关注,我同样不会为此“大动肝火”“愤愤不平”,仍然一笑置之。在这里,我旧事重提,也算是“立此存照”,为自己“正个名”:我既无“借光”“揩油”之意,也无“借光”“揩油”之实,且一以贯之,从不违例。不知我的这番“辩诬”,能否或多或少地改变一些人的误解?
对我来说,《银川赋》见了报,没有降低光明日报《百城赋》的质量、没有糟蹋报社精心推出的文化品牌,那就是对得起报社的信任、对得起银川市领导的委托、对得起读者的厚爱了,“岂有他哉!”
有人为《银川赋》未能刻碑而感到遗憾,也为此做出了努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件事,但我认为最好是顺其自然,无论何时都不会施以“推力”。当然,如果真的要刻石立碑的话,我对《银川赋》还要做出必要的修改,因为银川市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写《银川赋》的前前后后,我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甚至被人猜疑、误解,但我也明显地感受到了它发挥的作用和带来的影响。首先,《银川赋》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我的信心。在“百城赋”之后,光明日报又推出了“民族大家庭”专栏,为我国的每一个民族“立传”,因为有了《银川赋》的写作经历,我信心满满地自己动手写了“回族礼赞”,没有“另请高明”,自我感觉还不错,草稿也真的一次就通过了。第二年,我写了一篇有点散文味的通讯,题为《石之奇 绿之韵 山之神——记化腐朽为神奇的宁夏石嘴山中华奇石山》,居然引出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的批示:他让我据此改写成有文采的“记”,然后将这个“记”刻在石头上,因为陈书记此前看过《银川赋》及我的许多新闻报道,便相信了我的“写作能力”。同样的,这次我也没有发怵,在两天之内就提交了让石嘴山市委满意的《中华奇石山记》。仅仅过去几天,石嘴山就将它刻在了一块120吨重的巨石之上,并立于景区入口处。
此外,也是更令人高兴的,《银川赋》的面世,不仅引起宁夏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调动起许多人写诗作赋、讴歌家乡的热情,甚至呈现一种争妍斗艳的态势。除此之外,有些人还积极主动地为宁夏的特产、为自己所在的学校、企业、单位写赋,有的“赋”写得很有水平,这说明宁夏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其间,某市还在同一时间内“冒出”了两个“赋”,弄得责任编辑难以取舍。
《银川赋》发表不久,时任灵武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威虎便请我写《灵武赋》,据称,灵武市已有2000多年建城史。他不仅提供了所有材料,而且许以不菲的报酬。因为在写《银川赋》时吃够了苦头,我并不想接下这个活,因为推辞不掉,最后只好答应先试一试。翻阅马威虎部长给我的资料,我发现此前已有二三十篇《灵武赋》了,有人还不止写了一篇,其中就有灵武市时任领导的手笔,但他们自认为都不理想,当然,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就在我开始动笔时,马威虎调到了外县,没有人再督促此事,我也就“借坡下驴”,就此罢笔。结果,《灵武赋》至今还没有问世。
余波还在荡漾。2020年12月16日,是被称作“寰球大震”的海原大地震100周年,海原县在县城兴建地震公园,需要有一篇“海原地震公园记”刻在石碑上。当地负责人在一番“搜索”“考察”之后找到了我,据说是因为看了我写的《中华奇石山记》和《银川赋》,我如约写出了《海原地震公园记》,现已刻写在一块类似古籍的石头之上。没想到,此事竟然引起连锁反应,又有人让我再写类似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
当初,硬着头皮写《银川赋》,就完全是“赶鸭子上架”,不仅让我备尝了写作的艰辛,而且让我看清了自己知识和能力的不足,所以,我也就不愿意再涉足了。但是,自《银川赋》发表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被人明显高估了,我的真实水平实际要低很多,这也给我带来一些新问题,迫使我一次又一次接受新的挑战。也正是在这些挑战中,我做出了一些过去想都没想过、现在依然不敢想的事,也让我有了新的人生感悟:人活一世,不仅要做事,而且要逼自己做一些难事,甚至要做自己都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也就是在向自己挑战、让自己为难的过程中,充分地挖掘了自己的潜力、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进而也让我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想,如果一个人专挑容易做的事來做、也总是做那些已经做过、做起来也“轻松自如”、毫不费力的事,那么,他这人生也就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了。主动迎接各种挑战,甚至做一些自己力有不逮的事,这一定会让自己付出很多,也就是在这些付出中,会发现自己从未发现的潜力,进而能得到超乎想象的丰厚回报——不知我的这点感悟,大家有无同感?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