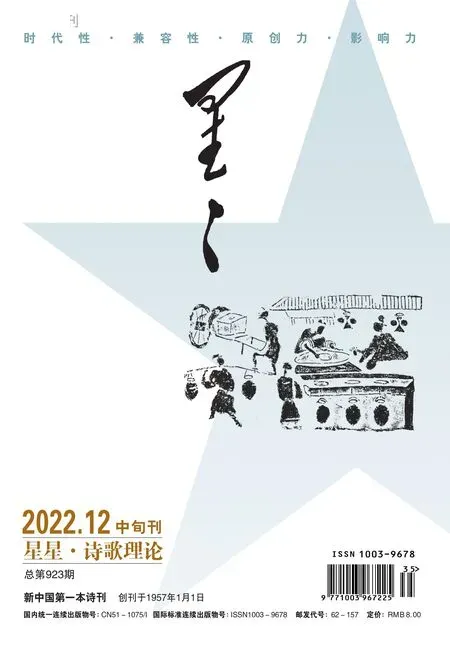诗话选(创作谈)
柏 桦
1
诗和生命的节律一样在呼吸里自然形成。当它形成某种氛围,文字就变得模糊并融入某种气息或声音。此时,诗歌企图去作一次侥幸的超越,并借此接近自然的纯粹,但连最伟大的诗歌也很难抵达这种纯粹,所以它带给我们的欢乐是有限的,遗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是不能写的,只是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动用了这种形式。
2
1990年,我在南京,以讲述诗歌中的事件为题,再次揭露了一个诗人的创作之谜:即中国古代诗学有一条广泛的写作原则——“情景交融”,字面意思是心情与风景交相混融。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其实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古人对此最有体会,也运用得十分娴熟讲究。何谓诗歌中的情景交融?其实就是讲一个故事,这故事的组成就是事件(事件等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可以是一段个人生活经历,譬如生活中一支心爱的圆珠笔由于损坏而用胶布缠起来的过程,一副新眼镜所带来的喜悦,一片风景是怎样地焕发了你良久的注目……总之,事件可以是大的,也可以是小的,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可以是情感的也可以是非情感的,甚至琐碎荒诞的。这些由事件组成的生活之流就是诗歌的情景之流。就我而言,我的许多诗就是由经历(事件)所引发的感受写成的,而这感受总是指向或必须落到一个实处(景),之后,它当然也会带来遐想或飞升(情)。这事件本可以成为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长长的故事(如果口述,或许是两个小时的故事),但情况相反,它是一首诗,一首二十或三十行的诗,更有甚者,有时竟是短短的几行。这正是事件——情景交融的张力,惊人的戏剧化。诗歌中的事件之于我,往往是在记忆中形成的。它在某个不期而遇的时刻触动我,接着推动我追忆相关的过去,并使一个或多个事件连成一片,相互印证、说明、肯定或否定,于是一首诗开始了它成长的轨迹,最终形成并显示出它的结局和命运。换句话说,这些经年累月在内心深处形成的一个一个故事,它们已各就各位,跃跃欲试。
3
每当有人问我,一首诗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就会立即想到两点(当然不止这两点):即一个诗人的感受能力和表述能力。因为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可能感受到了,但说不出来;可能说出来了,但离感受的精确度还有距离。好诗人无一不是对生活,乃至生命有着独特感受并且表述极其到位的人。话又说回来,这两种能力(感受能力和表述能力)也并非神秘莫测,只要一个人有一定的“感时伤怀”的禀赋,都可以通过训练而达到。训练从观察开始。
4
精确地说,诗歌写作中的想象力其实是一种联想能力。据我的写作经验,我无论有多么跳跃和断裂的想象,它最终必须和整体有关;只要与整体有关,我就觉得我其实运用的是联想力。或这样说,想象力只有在联想力之中才能得以落实。
只要是人(疯子和神除外),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此让我们想想哪怕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拥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想象力的诗人——都有一个边界,即总要与整体性有关,甚至解构式的碎片化也是如此,需知没有整体何来碎片?
5
不懂诗的人最爱洋洋得意地说,“你在重复自己,你应该变了。”需知,博尔赫斯一生都在重复一首诗《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继续需知,人的基因是不能改变的(江山都可改变)。因此,每个人写的诗或文只能是他的老调,最多也就是古人说的“常与变”,即“常”是一个人的基因,永恒不变(你想变也不可能,除非你能修改基因);“变”则是为了使“常”更“常”,求得一些表面的改变(或丰富)而已。
6
写诗说白了,就是学习熟练掌握词法、句法、文法,三法之中,句法最重要。回到古人的作诗法典:炼字兼炼句。回到瓦雷里的口头禅:“我写诗只思考句子,句子,句子”。
7
对于每一个我认识的死者(无论是我爱的人、恨的人或仅点头之交的人),我首先忆起并怀念的是他们的声音,而非容颜。
8
特朗斯特罗姆是真正少有的天才诗人,但不是伟大诗人。天才诗人都写得少,也写得短、精致;伟大诗人一是写作量大,二是滔滔写来,若泥沙俱下的江河,没那么精致。或者这样说更简洁:天才诗人无缺点,伟大诗人有缺点。
9
清人赵翼论诗有趣,抄几句:“不老笔不洁,不闲意不新。天予老且闲,使之作诗人”(参见《瓯北集》卷二十六)。因此,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固有的观念,即诗是青春的。一个人要成为诗人,按赵翼的说法,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成为一个老人和闲人。
10
我读到的最疯狂的饮酒歌是黄周星的《楚州酒人歌》。我最喜欢其中一句“桃花如雨八骏叫”。他在诗中称尧舜为酒帝,羲农为酒皇,淳于为酒霸,仲尼为酒王,而陶潜李白只能两边叨陪末座,亦颇有意思。
11
读一个人的诗,感觉是走着的;读另一个人的诗,感觉是站着的;读第三个人的诗,感觉是躺着的。如果读到一个人的诗,感觉是坐着的,最好。
12
诗歌是暴露加掩藏的艺术,之间的分寸(暴露多少,掩藏多少)全由作者精细掌控。坏诗人要么只知掩藏,要么一味地暴露。
13
节奏在句子里,坚定地按自己的声音节奏(句子)走。句子与句子之间要大胆留空,不要填满了。诗的妙处就在于,既有逻辑(严密性),又有跳跃(空阔性)。此说正如黄宾虹在论画中说过的,大画家作画,既要密不透风,又要疏可走马。一句话,要相信读者,好读者最怕啰嗦的写者,即一句一句根据逻辑线索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写者。
14
年轻诗人写诗都是献给自己的,难道老诗人就不是吗?其实诗人无论老小,写诗都是献给自己的。所以写诗时如能增强一些反讽,就会减少一些自恋。爱写抒情诗,又很唯美,一观便知是个自恋人。
15
精神可嘉的人,句法都无可取处,罗曼·罗兰是个典型。他的精神可嘉到什么程度?看看他的书《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世界风靡到什么程度就知道了,“我记得在1917年还有人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新一代的口令”(博尔赫斯:《罗曼·罗兰》,见《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335页)。岂止1917年。1921年,梁宗岱18岁时,曾在广州岭南的一个下午被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震撼,震撼之具体情节可参看他写的抒情文章《忆罗曼·罗兰》(梁宗岱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第208-210页)。甚至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约翰·克利斯朵夫精神仍继续生猛古怪地刺激着那时中国青年的神经。而且我注意到了一个特点:从1921年梁宗岱所受的刺激到我身处的1970年至1980年,中国的文学青年几乎都以能大段背诵《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相关内容和文字为光荣,并以此作为同道之间见面接头的暗号。
至于罗曼·罗兰行文的词法、句法、章法,就此打住。
——《复活(节选)》中的人性理想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