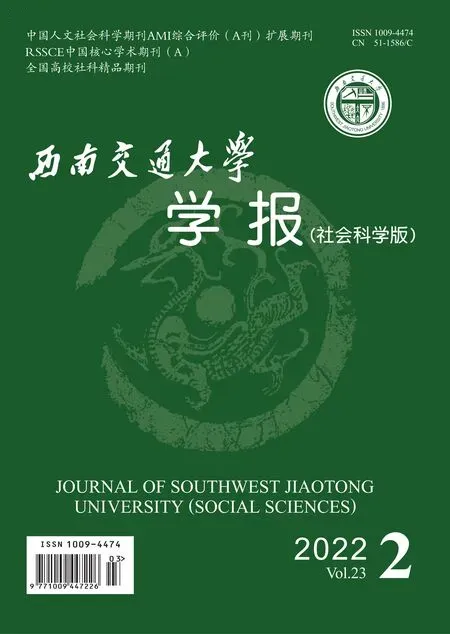在文学与历史之间
——憨山德清传记文研究
吴岳聪
中国古代传记文发展到晚明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出现了许多经典的文学形象,如袁中道笔下的回君、袁宏道笔下的醉叟、张岱笔下的五异人、归有光笔下的归氏二孝子等等。憨山德清(1546—1623),名德清,字澄印,号憨山,金陵全椒(今属安徽)人,为“万历三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以往学者主要关注德清的生平、思想和交游,特别是其儒、释、道三教兼通和改革曹溪祖庭等内容,对其文学创作关注较少,其传记文书写更是无人问津。在传记文学研究方面,学界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文人创作上,对于僧人散传的创作甚少关注,而德清具有良好的三教背景,其传记文的创作兼有文学和史学双重价值,亟待深入挖掘和探讨。
一、德清创作传记文的原因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阳明心学的兴盛都为传记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散传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传记作品不断增加。德清共创作传记文30篇,包括传文7篇、塔铭23篇,创作数目十分可观,并刻画了云栖祩宏、紫柏真可、雪浪洪恩等晚明僧人的经典形象。德清之所以创作传记文,一方面是因其颇具教界声望,所以许多僧人前来请传;一方面则是为了树立僧人典范而主动创作。
(一)交游众多,具有教界声望,应僧人请求作传
德清为安徽全椒县人,十二岁时至南京报恩寺出家,十六岁同雪浪洪恩游庐山、南康、吉安、青原等地,二十七岁时决意北游,至京师,后不断往返于京师与五台山之间。年三十八,蹈于东海崂山,年五十弘法遭难,贬谪雷州,年五十六至曹溪,晚年游历湖南、浙江等地,后住锡庐山,年七十七返回曹溪。他的行脚范围广阔,在途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妙峰福登、紫柏真可、云栖祩宏等等,虽然他们所属宗派及处事风格不尽相同,但在交往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德清还在行脚途中结识了众多士大夫,和当时的名士汪道昆、王世贞、董其昌、钱谦益等都有交往。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万历帝生母慈圣皇太后的赏识,曾被其选为诵经僧,后又主持了为万历帝祈嗣的无遮法会,慈圣皇太后甚至还成了其俗家弟子,据载:
赐衣之日,圣母命内侍传旨,欲延入宫,面请法名。师知非上意,力谢,以祖宗制,僧不入宫,乃遣内侍绘像命名以进。圣母悬像内殿,令上侍立,拜受法名。上事圣母至孝,此日未免色动。圣母法讳在谱后,法派“德大福深广”四十字中,用第二“大”字其讳字。当命名进宫时,侍者绝不得闻。但从此避忌大字一辈,法属悉从“福”字辈始。〔1〕
慈圣皇太后将德清的画像悬挂于内殿,让万历帝侍立于侧,拜受法名,可见其当时声名之盛。德清在行脚过程中,不断结识僧俗二界人士,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成为声名远播的教界大德。特别是在其晚年,与其同为“万历三高僧”的紫柏真可、云栖祩宏都已示寂,德清的教界声望达到了顶峰,僧人前来请传就在意料之中了。
(二)出于树立僧人典范的需要作传
佛教发展到晚明时期积弊丛生,出现了许多问题。德清对晚明佛教衰颓的状况十分担忧,以“末法”称之,他说道:“况兹末法奉教,例多俑人,岂禀钝根。法门所系,九鼎一丝,外患内忧,犹楚入郢,悲夫悲夫!”〔2〕直言此时佛教已到内忧外患的境地。在其著作中,德清对晚明佛教的批判也随处可见。
首先,德清批判晚明时期师资水平低,缺乏真才实悟,少有佛门正眼,如“末法弟子,去圣时遥,不蒙明眼真正知识开示,往往自恃聪明,大生邪慢”〔2〕,“惜哉末法,正眼难逢,今愈见其难也”〔2〕。其次,僧人轻慢骄横,少有真正修佛之人,如“末法学人多尚浮习,不诣真实。故于佛法教道,但执名言,不达究竟之旨”〔2〕。另外,僧人没有掌握正确的修行方法,一味浮于表面,功夫不扎实,如“大约末法修行人多,得真实受用者少;费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盖因不得直捷下手处,只在从前闻见知解言语上,以识情抟量,遏捺妄想,光影门头做工夫”〔2〕。德清认为晚明佛教衰颓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僧人自身的问题导致的,所以希望通过树立僧人典范唤起佛法正信。在耶西志若的塔铭中,德清明确表达了树立法门典型的愿望:
丁巳,予以双径因缘,过吴门,晤公于如意,睹其苍然道骨,喜法门尚有典刑也……呜呼!公秉夙慧,童真出家,即志向上事。及有发明,力穷教典,为人天师,岂非愿力然哉?生平清节自守,应世皭然,三衣之外无长物,临终脱然无挂碍。盖般若根深,人未易察识也。嗟予老朽,三十余年,慕公止一面,且末后不忘,非宿缘哉?〔2〕
耶西志若为山阴姚氏人,在雪浪洪恩开法南都时担任上首弟子。万历四十五年春,德清赴双径吊唁云栖祩宏,在途中与耶西志若有过一面之缘。德清感念其清洁自守、朴素勤俭的品质以及游戏三昧的修行境界,慨叹其可作为法门典型,供僧人效仿。德清在寓安广寄的塔铭中也写道:“我作此铭,非为公立。普告诸人,大家努力。”〔2〕寓安广寄,俗姓余,衢州开化人,礼云栖祩宏受具足戒。德清认可寓安广寄“一入法门,即尽情屏绝,精心为道,如愚若讷,居常一念,密密绵绵”〔2〕的精神,认为其真修实证的修行态度堪为后人之榜样。
对于那些声名不显的僧人,只要品行出众,德清也为之作传。《比丘性慈幢铭》就记载了两位普通僧人释性慈和释性玉的深厚友谊,二人结伴修行,后性玉患病,性慈不离不弃,如侍父母。德清赞道:“形异心同,难兄难弟。视身若己,死生不二。”〔2〕德清创作传记文秉持树立佛法正信的精神,旨在通过为晚明堪为典范的僧人立传涤浊扬清、扭转“末法”时期的不良风气。
二、德清传记文的文学价值
传记文中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者能否抓住人物特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德清善于抓住人物特点,运用各种叙述手法加以刻画,避免人物的单一性和脸谱化。他还将深沉的感情注入文字之中,改变了僧人创作传记的疏离感,因而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一)感情真挚
与僧人总传尽量隐去作者情感的书写方式不同,德清的传记文中常记录其与传主的交往过程,情感深挚。特别是在创作其先师和挚友的传文时,德清更是将深沉的感情投射其中,叙述十分动人。
在德清的成长过程中,其恩师西林永宁对其影响很大。嘉靖三十六年,德清到南京大报恩寺出家,西林永宁一见十分欣喜,青眼有加,选择了最优秀的老师来培养他,将其培养成了一位儒、释、道三教兼通的僧人。嘉靖四十三年,西林永宁八十三岁,在圆寂之前将法门事托付给德清,据载:
翁于嘉靖四十三年腊月除日,集诸子孙,叙生平行履,因属后事,乃抚某背嘱之曰:“吾年八十有三,当行矣。门庭多故,一日无老人,则支持甚难。此儿虽年少,饶有识量,我身后,汝等一门大小,凡有事,当立我像前,听此儿主张,庶几可保无虞耳。”少祖艮山厚公以下,皆唯唯受命……至十五中夜,令举众大小围绕念佛,某扶翁坐怀中,寂然而逝,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也。〔2〕
晚明时期,师徒之谊不恰的例子十分常见,湛然圆澄《慨古录》载:“是以前辈师资之间,亲于父子。今也动辄讥呵,自行不端,学者疑惮”〔3〕,“今为师徒者,一语呵及,则终身不近矣”〔3〕。而西林永宁和德清的师徒之情十分深厚,西林永宁即将示寂前,把大报恩寺托付给德清,可谓是委以重任。在西林永宁圆寂时,“某扶翁坐怀中”,深挚情谊流泻而出。
除了师徒之情,德清的传记文中还记录了他和雪浪洪恩、紫柏真可、妙峰福登等人真挚的友情。他们身上都肩负着复兴晚明佛教的神圣使命,在共同努力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与德清友情最为深厚的当属雪浪洪恩,雪浪洪恩,字三怀,俗姓黄,年十二出家。德清和雪浪洪恩一起在报恩寺成长,二人第一次见面就很投契,“公出家之明年,予十二岁,亦出家。太师翁携予参先大师,公坐戏于佛殿,一见予而色喜,若素亲狎,人视为同胞”〔2〕。二人在大报恩寺一起成长、修行,居同时,语同调,互相激励,情同手足。嘉靖四十五年,南京大报恩寺被雷火焚毁,二人决心重建该寺。考虑到复兴大报恩寺所需资金庞大,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实现,德清决志北游,以待时机。在德清出发之前,二人有如下对话:
年二十五,志将北游,别公于雪浪庵。公曰:“子色力孱弱,北地苦寒,固难堪也。无已,吾姑携子,遨游三吴,操其筋骨,而后行未晚。”予曰:“三吴乃枕席耳。自知生平软暖习气,不至无可使之地,决不能治此,固予之志也。”公曰:“若必行,俟吾少庀行李之资,以备风雨。”予笑曰:“兄视弟寿当几何?”公曰:“安可计此?”予曰:“兄即能资岁月计,安能终余日哉?”公意恋恋不已,予诒之曰:“兄如不释然,试略图之。”公冒大雪方入城,予即携一瓢长往矣。公回山不见予,不觉放声大哭,以此知公生平也。〔2〕
雪浪洪恩因北方苦寒,前路坎坷,不舍德清北行,结果德清不告而别,雪浪洪恩看到德清已走,不觉放声大哭,二人真挚的友谊跃然纸上。后德清遭难,经过故乡时再次和雪浪洪恩碰面,德清道:“事机已就,若不遭此蹶指日可成,今且奈何?予往矣,兄试相时先唱,当躬行乞于南都,以警众之耳目。予早晚天假生还,尚可计也。”〔2〕在遭难前,德清已经得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赏识和资助,有望复兴大报恩寺,而遭难后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德清自觉复兴无望,就将此重任托付给雪浪洪恩,雪浪洪恩果然不负所托,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重新修复了大报恩寺,完成了二人的夙愿。
德清和紫柏真可也相交颇深。紫柏真可,俗姓沈,讳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道人,为“万历三高僧”之一。万历十四年,德清与紫柏真可首次相遇于崂山下的即墨城中,二人相见恨晚,从此成为至交,真可有诗记载这次会面:“吾道沉冥久,谁唱齐鲁风。闲来居海上,名误孙山东。水接田横岛,云连慧炬峰。相寻不相见,踏遍法身中”〔4〕。后德清遭难,紫柏真可十分担忧,“师在匡山,闻报,许诵《法华经》百部,冀祐不死”〔2〕,后听闻德清被贬责雷州,紫柏真可就在途中等候,二人会于下关泊旅:
师执予手叹曰:“公以死荷负大法,古人为法,有程婴、公孙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濒行,师嘱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后事属公。”遂长别。〔2〕
二人都肩负复兴晚明佛教的历史重任,同样秉持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在“救法”和“救世”的过程中同样卷入了政治漩涡,相似的经历使得二人惺惺相惜。见到死里逃生的德清,紫柏真可十分动情,此时紫柏真可似乎隐隐感受到危险的气氛,所以将身后之事托付于德清,后果因“妖书案”坐化狱中。紫柏真可曾言自己有“三大负”:
法门无人矣!若坐视法幢之摧,则绍隆三宝者,当于何处用心耶?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2〕
紫柏真可列数自己的三大遗憾,其中第一负就是“老憨不归”,德清的流放成为紫柏真可人生中十分重要之事,和“矿税不止”“《传灯》未续”并列为其一生憾事,可见二人友情之深厚。
(二)展现晚明僧人的奇狂性格
阅读德清的传记文时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其传主,特别是与德清关系密切的,大多具有奇狂的性格特点。晚明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自“争国本”事件爆发后,万历帝开始了长期怠政,二十年没有上朝。晚明佛教也存在诸多问题,呈现“末法”之势。政治的黑暗和法门的衰颓激发了晚明僧人对理想的追求,纷纷承担起“救世”和“救法”的双重责任。阳明心学的兴盛使得人性论思想兴起,个体情感获得释放,从而导向了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有些僧人并不完全遵守世俗对僧人的要求,而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戒律,展现出奇狂的性格特征。
德清曾在《自赞》中这样描绘自己:“少小自爱出家,老大人教还俗。若不恒顺世缘,只道胸中有物。聊向光影门头,略露本来面目。须发苦费抓搔,形骸喜没拘束。一转楞伽一炷香,到处生涯随分足。”〔2〕他在《自赞》中自我调侃,将自己描绘成非僧非俗、不拘形骸的样态,并表明自己不“恒顺世缘”,是因为“胸中有物”。德清的一生本来就十分传奇,其传记文中也不乏性格奇狂之人,如雪浪洪恩,其出生于富室,童真入道,见解超群,十八岁即登副讲,一众悚然,据言“曾至吴、越间,士女如狂,受戒礼拜者,摩肩接踵,城郭为之罢市”〔5〕。雪浪洪恩喜着艳色袈裟,十分有个性,为文人雅士所欣赏,当时博学儒者第一的焦竑也推崇雪浪洪恩。
德清传记文中最具“奇狂”个性的应数紫柏真可。其《塔铭》载:
夫大地生死,颠瞑长夜,情关固闭,识锁难开,有能蹶起一击碎之,掉臂独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历观《传灯》诸老,咸其人哉。余今于达观禅师见之矣。〔2〕
在《塔铭》开头,德清就将紫柏真可的形象勾勒出来,塑造了一位精进不懈、果敢刚毅的雄猛丈夫形象。在出家之前,紫柏真可混迹于市井,他曾自述“屠狗雄心未易消”〔2〕,少年时即有侠气,一旦找寻到人生的奋斗方向,便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塔铭》又载:
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伟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见妇人,浴不许先。一日,姊误前就浴,师大怒。自后,至亲戚妇女,无敢近者。〔2〕
青年时期的紫柏真可性格霸道,厌恶女性,不允许其姊妹先其洗浴,以致亲戚妇女都很畏惧他。传记作品如果只记大事,而不注重描写小事、细节,也就无法给人以立体感,最终导致血肉不丰满,形象不生动〔6〕。在创作传记文的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德清对材料进行剪裁,选取典型事件使得人物性格跃然纸上。
紫柏真可个性奇狂,不遵循世俗对僧人有形的规定,而是遵循着自心之规则,将规则与人性之自由打成一片。最能体现其“奇狂”性格的当属其与释明觉师徒关系倒置之事:
年十七,方仗剑远游塞上,行至苏州阊门。游市中,天大雨,值虎邱僧明觉,相顾盻,壮其貌,因以伞蔽之,遂同归寺。具晚餐,欢甚,闻僧夜诵八十八佛名,心大快悦。侵晨,入觉室,曰:“吾两人有大宝,何以污在此中耶?”解腰缠十余金授觉,令设惊请剃发,遂礼觉为师……师于嘉禾刻藏有成议,乃返吴门,省得度师觉公。觉已还俗,以医名。闻师来,慑甚。师伪为贾人装,僵卧小舟中,请觉诊视。觉见师大惊,师涕泣曰:“尔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觉曰:“唯命是听。”师立命剃发载去,觉惭服,愿执弟子礼亲近之。师来之日,觉夕餐,饭盂忽堕地迸裂,其诚感如此。〔2〕
紫柏真可十七岁时遇到虎丘僧明觉,听《佛名经》有感便发心出家,拜明觉为师。后明觉还俗,紫柏真可十分痛心,便回到吴门化装为贾人度化明觉,明觉见到紫柏真可后羞愧难当,便重新剃度,礼拜紫柏真可为师。紫柏真可的雄猛性格连其师都畏惧,“闻师来,慑甚”“唯命是听”等心理、语言描写,都让一位“雄猛丈夫”的形象呼之欲出。禅宗一向重视师生传承,紫柏真可和释明觉师生关系倒置的做法也受到了批评。湛然圆澄就评论道:
故老人于戒定智慧曾无亏缺,独绝师承损其行耳。何则?老人受业师者,为凡心未尽,还俗娶妻。老人以方便力强之复道,返以师礼待老人矣。诸方尊宿,未有可其意者……由是而观,则老人虽有超师之作,焉忍弃其源流也。其源流一绝,使后世邪慢之辈效学其疣,而佛法不灭则几希矣。故佛祖不欲断其血脉,于此特严其报应也〔7〕。
湛然圆澄指出紫柏真可与明觉师生关系倒置、行为失当,会使后世邪慢之人效仿,损害禅宗师生相传的传统,造成不谙戒律、甚辱祖风的情况出现。紫柏真可却认为:“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2〕直言一切由心而发,与外在形式无关。
万历三十一年,“妖书案”爆发,紫柏真可被捕入狱,历经严刑拷打,只以“三大负”为对,绝无他辞,甚至还神情自若地在狱中说法。面对黑暗的现实,紫柏真可相当失望,叹道:“世法如此,久住何为?”〔2〕其弟子十分悲痛,紫柏真可怒斥:“尔侍予二十年,仍作这般去就耶?”〔2〕面对死亡他也十分坦然,游戏三昧,铁骨铮铮。德清对紫柏真可等人“奇狂”性格的刻画,也显示出其力图创新、反对模拟的进步创作观。
(三)追求个性化描写
德清传记文中的僧人形象个性鲜明,各不相同,如云栖祩宏“朴实简淡”“貌温粹,弱不胜衣”〔2〕,澹居法铠“貌粹骨刚,稜稜英气”〔2〕,瑞庵广祯“貌古神清,长松孤鹤”〔2〕,古镜义玄“体丰厚而性柔和”〔2〕,妙峰福登“貌古骨刚,具五陋,面严冷,绝情识”〔2〕。以下从僧人的出家因缘和其对待学生的态度来看德清是如何展现其鲜明个性的。
《雪浪法师中兴道法传》记载了雪浪洪恩出家时的状况:
是日设供,值讲《八识规矩》,公一闻即有当于心。倾听之,留二三日。父归唤公,公不应。父曰:“若爱出家耶?”公笑而点首。父强之,竟不归。父归数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携之。父至强之再三,公暗袖剪刀,潜至三藏塔前,自剪顶发,手提向父曰:“将此寄与母。”父痛哭,公视之而已。由是竟不归,父回告母,遂听之,公时年十二也。〔2〕
雪浪洪恩年十二来到大报恩寺,听《八识规矩颂》,当下领悟,决志出家。其父母多次阻挠,雪浪洪恩便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暗袖剪刀,自剪顶发。其父痛哭,雪浪洪恩不为所动,只是“视之而已”。德清通过描写矛盾冲突展示雪浪洪恩出家心志之坚。
而云栖祩宏出家时则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方式:
前妇张氏,生一子殇。妇亡,即不欲娶。母强之,议婚汤氏,汤贫女斋蔬。有富者,欲得师为佳婿,阴间之,师竟纳汤,然意不欲成夫妇礼。年二十七,父丧。三十一,母丧。因涕泣曰:“亲恩罔极,正吾报答时也。”至是,长往之志决矣。嘉靖乙丑除日,师命汤点茶,捧至案,盏裂。师笑曰:“因缘无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诀汤曰:“恩爱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为计。”汤亦洒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2〕
云栖祩宏年少时即归心净土,但父母不喜其出家,并强迫其娶妻。云栖祩宏并没有像雪浪洪恩一样决绝,而是听从父母之命迎娶汤氏,但不欲成夫妻之礼。后云栖祩宏父母相继过世,出家没有了阻碍,他才告别妻子剃发出家。孝亲思想在云栖祩宏的思想中占了重要地位,据载:“师以母服未阕,乃怀木主以游,每食必供,居必奉”〔2〕。这种缓和的出家方式也昭示了其温和的个性特征,与雪浪洪恩的坚毅果敢形成鲜明对比。
德清笔下僧人对待学生的态度也大相径庭。无明慧经仪表端肃,不怒而威,但对弟子十分关切,“每遇病僧,必亲调药饵,迁化则躬负薪茶毗,凡丛林巨细,必自究心”〔2〕;紫柏真可见到弟子有喝酒吃肉者,很愤怒地说:“出家儿如此,可杀也”〔2〕。“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直欲顿断命根,故亲近者希”〔2〕,紫柏真可之门庭峻绝可见一斑。云栖祩宏则对弟子非常慈爱,“十方衲子如归,师一以慈接之”〔2〕。在德清笔下,这些僧人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展现了德清“千人千面”的个性化书写追求。
德清言:“文者心之章也。学者不达心体,强以陈言逗凑,是可为文乎?须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盖天盖地。”〔2〕即言为文者,需从心而发,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故其传记文饱含对恩师、挚友的真情,并通过个性化书写突出传主的奇狂个性,体现了进步的文学观,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三、德清传记文的历史价值
德清一生肩负晚明佛教复兴重任,在其五十岁弘法遭难之前,他希望能够依靠政府的力量重建南京大报恩寺。遭难被贬谪雷州后,他在曹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禅宗祖庭获得了短暂的复兴。和德清一样,他笔下的传主也大都怀有振兴晚明佛教的历史责任感,德清用其传记文描绘了在佛教“末法”状态下法门志士用不同的方式复兴佛教的壮美图景。
(一)改革教育和修行方法

还有一批有志僧人采用匡正、改革修行方式的手段纠正晚明佛教弊端。如雪浪洪恩十八岁便登南京大报恩寺副讲,及登讲座,一改之前的说法方式,尽扫训诂,单提文本,直探佛意,德清赞道:“由是学者耳目,焕然一新。如望长空,拨云雾而见天日。法雷启蛰,群汇昭苏,闻者莫不叹未曾有”〔2〕。雪浪洪恩的说法方式卓有成效,吸引了大量僧人前来听法,可谓“自昔南北法席之盛,未有若此”〔2〕,也培养了一批法门龙象,如巢松慧浸、一雨通润、蕴璞如愚等,“海内凡称说法者,无不指归公门”〔2〕。和雪浪洪恩不同,面对晚明僧人浮躁的修行作风,云栖祩宏则主张“老实念佛”,希望以戒律为根本,匡正浮躁的作风。他著有《沙弥要略》《具戒便蒙》《梵网经疏发隐》《禅关策进》等,通过撰写著作规范弟子行为,揭示参究之诀,效果十分显著,“古今丛林,未有如今日者也。具如僧规约,及诸警语,赫如也”〔2〕。不仅如此,云栖祩宏圆寂之时还曾开目示众,叮嘱弟子老实念佛,恪守规矩,并择戒行双全者主持丛林。再如无明慧经,他是曹洞中兴的重要人物,开创寿昌派,奠定一代宗风。无明慧经提倡农禅,年过七旬仍随众耕作,可谓“生平佛法,未离镢头边也”〔2〕,将佛法完全实践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在寿昌寺期间“千指围绕”,培养出许多优秀弟子,成就了流传至今的曹洞宗寿昌派。再如瑞光法祥,其为净土宗僧人,主张虔诚念佛,他募豆四十八石,以豆为珠,净念相继,以至终身,被称为“豆儿佛”。他虽然影不出山,断绝外援,但声光日露,“十方衲子远归之,四事不思而至,丛林不作而成”〔2〕。德清赞道:“若夫清操苦节,一念终身,始终不易,如公者,可谓以身说法矣。”〔2〕
(二)复兴寺院
自明朝开国以来,政府就制定政策保护丛林,严禁买卖、盗用和私占寺田。到了晚明,佛教丛林发生重大变迁,大量寺产被侵占,而官方并没有尽保护之责。《慨古录》载:“田产为势豪所占,而官府不之究,僧为俗人所辱,而官府不之护,产罄寺废,募缘度日,将何内牒?倘有俗置新产,有田当役,有人当丁,原同百姓,何更要内牒耶?”〔3〕面对大量丛林被破坏的情况,许多有志僧人致力于恢复寺产。德清和其挚友雪浪洪恩也不断为重建大报恩寺而努力,万历二十二年,雪浪洪恩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重新恢复了大报恩寺,“公心苦极,忽呕血数升,时管木即入。在架之人,如鸟栖柔条,竟无小恙,岂非心力所致哉”〔2〕。
德清笔下有不少承担复兴丛林大任的有志僧人,其中对于建立道场着力最多的当属妙峰福登。妙峰福登,山西平阳人,俗姓续,年十二出家,年十八依蒲州城文昌阁朗公和尚。后结识山阴王朱俊栅,山阴王一见,知为法器,便不断资助他修行求法。后因其致力于修建道场,被称为“佛门鲁班”。妙峰福登营建道场、佛像,参与北方许多佛寺的修造,五台山显通寺、宝华山隆昌寺、宁化的万佛洞等都是由他主持修造的。不仅如此,妙峰福登还参与了难度更高的桥梁建设,例如陕西三元的渭河大桥、两层三十二孔的宣化大桥等等。寺庙是宣教重镇,妙峰福登修造的寺庙无一例外地成了佛教中心,对于佛教的传播有很大作用。德清赞道:“道场之盛,盖从前所未有也。”〔2〕“二百余年,其在法门建立之功行,亦唯师一人而已,岂易见哉?”〔2〕除了妙峰福登,紫柏真可也为寺院复兴贡献了许多力量。德清载:“独以荷负大法为怀,每见古剎荒废,必至恢复。始从楞严,终至归宗、云居等,重兴梵剎一十五所。”〔2〕紫柏真可一生复兴的寺院包括浙江嘉兴楞严寺、浙江径山的径山寺、北平房山的云居寺等等。他还曾多次写劝募疏文号召募捐,依靠陆光祖等士大夫和民间的力量募集善款,恢复道场。
还有一些有志僧人也承担了复兴寺院的重任,如德清的恩师西林永宁和云谷法会合力复兴了栖霞山道场,举嵩山善公为住持,德清赞叹:“善公尽复寺故业,斥豪民占据第宅,为方丈,建禅堂,开讲席,纳四来。江南丛林肇于此,师之力也”〔2〕。再如无垢性莲也曾广泛建立道场,德清称赞道:“凡足迹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皆为道场。若池阳之杉山,九华之金刚峰,观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庵,莲岭之静室,金陵之花山,余若秦头峰、婆娑垄、岑峰洞、白沙山、吉祥诸天,随地各建兰若数十所”〔2〕。又如古镜义玄,还乡广做佛事,造金像、修桥梁,四方归向,王臣敬仰,后创造普兴禅院,担任第一代住持。晚明时期居士佛教兴起,居士宰官护持佛教,对于佛教的复兴也颇有影响。德清笔下的正光居士也曾建立明因寺,重修龙泉寺、凤祥寺,复兴丛林,供养三宝。
(三)刊印《嘉兴藏》
在紫柏真可刊刻《嘉兴藏》之前,明代官刻大藏经共有《南藏》二刻、《北藏》一刻以及明中叶私刻于浙江的《武林藏》。晚明时期,宋元时期的刻板已经多有散佚,虽然有《南藏》《北藏》二藏,但《南藏》以梵夹为形式,价格昂贵,卷帙繁多,不易流通,《北藏》存于宫中,请印不易,而民间所印的《武林藏》早已不传,于是重刻方册《大藏经》就成了传播佛法、提倡经教、挽救晚明禅门疏狂风气的重要手段。
紫柏真可是刊刻《嘉兴藏》的核心人物,在士大夫冯梦祯、曾同亨、瞿汝稷等人的帮助下,紫柏真可以其弟子密藏道开为总管,于万历十七年创刻于五台山,后因五台山冰雪严寒,移往径山寂照庵。后密藏道开隐去,紫柏真可的弟子寒灰如奇、幻予本及、澹居法铠等人都参与了刊刻,德清赞叹:“若大师者,斯刻之举,不啻秦庭之哭,真有夺军拔帜之意。其恢复法界之图,远且大矣”〔2〕。紫柏真可等人刊刻方册《大藏经》,使得经藏在装帧方式上有了突破性的改变,印制费用大为降低,而以士大夫资助和民间募款的方式筹措资金,则体现了与天下人结缘、共同护持佛法、利益众生的精神。
宗教传记是一种神圣叙事,反映的是信仰的真实,而不仅仅是历史的真实〔9〕。一般来说,宗教人物传记不以纪实性为主要考量,往往更重视其神圣性的展现,甚至僧人崇高形象的确立。德清所作传记文虽然也有少量神异描写,但大多记述的是其恩师、挚友的人生经历,更为真实可信,其30篇传记文勾勒出晚明有志僧人复兴法门的壮丽图景,是研究晚明佛教不可多得的史料。
四、结语
虽然僧人所作传记具有宗教色彩,但其文学特质也非常突出,属于传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认为传记文学的作用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路”〔10〕,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德清创作的传记文将真挚的感情投射其中,注重人物特点的描写,展现了晚明僧人“奇狂”的性格特征,其创作从心而发、心光流溢,受到晚明“尚奇”“重情”思潮的影响。从佛教史的角度来看,目前学界主要将目光集中在三代《高僧传》等僧人总传上,但明清以来几部高僧传或体例驳杂,或取材不广,备受学界批评。德清所作传记文则减少了对僧人神异色彩的描写,是研究晚明佛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德清创作的传记文既重视文学性,又重视史实的记录,具有文学和历史双重价值。作为僧人书写传记文的代表,其创作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地位,值得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