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法”对于“姑苏版”产生与消亡的影响述论①
吴 震(苏州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这里首先关系到对“泰西法”的理解。光绪二十年春三月,出使日本的参赞官黄遵宪在其编撰的《日本国志·邻交志下一》中对泰西的解释为:“环地球而居,南北极有定,东西方无定,然居中国而视欧罗巴则名曰泰西。由此可见,“泰西”就是我们现在地理学概念中所指的“欧洲”,也就是过去所谓的“西洋”。“泰西法”“泰西画法”“仿泰西笔意”是指来自西方的绘画技法或具有西洋画风的绘画作品。
一、“泰西法”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地理大发现而至东西新航路通畅,伴随东西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大批耶稣会传教士受派遣来华,“泰西法”也着耶稣会东进而传入中国。对于西方绘画造型体系传入中国的途径,水天中先生认为主要有三条:即传教士在华的艺术活动;主要出口于广东的商品画(或称贸易画);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与传授。但是在18 世纪末之前,传教士在华的艺术活动无疑是“泰西法”传至中国最为显著的途径。

图1《程氏墨苑》中的《圣母》
明末,“泰西法”通过西方传教士以宣传教义的宣传品等方式在明代士大夫阶层和民间传播开来。明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达澳门,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将一幅天主像、两幅天主母像以及西方城市风景铜版画送给皇帝,使西方绘画进入了中华帝国的核心——宫廷,西画的逼真写实效果受到统治阶层的肯定和赞赏。此后,为更加有力地扩大传教活动,罗马教廷派遣了许多传教士画家来到中国为帝王们服务,为西洋风绘画在宫廷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宫廷之外,传教士们也与许多文人士大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圣保禄公学于澳门成立时,传教士便开始向中国人教授西画,使“泰西法”影响的种子在民间得以孕育。当时一些文人对西画以明暗光影塑造形体写真效果非常推崇,如明代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曾描述西洋圣母像“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蹈踊欲动”。此后,西画又通过画坊、工厂、教堂、贸易、书籍和传教士的活动等诸多途径,与民间有了广泛的接触,使西洋绘画在明末清初便“风行中国”。明万历十九年(1591 年),利玛窦将携来的宗教铜版画《宝象图》《圣母》等四幅,赠与了当时制墨大家程大约。程氏将其以木版版刻的形式收入1606 年出版的《程氏墨苑》(图1),其雕刻技法富有明暗凹凸、生动逼真的西洋铜版画风格,并附罗马字注音,这是将铜版画转刻成木版画的成功实践。从此,西方文化信息进入了中国传统绘画之中。虽然在当时,于墨块上印上西洋画也许并不是出于文人的本意,而只是为了博得更多购买者追求新奇的时尚心态,以便能够更快更多地出售,但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泰西法”在民间大规模的传播。
二、“泰西法”在苏州的传入与传播
明代的苏州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最兴盛的城市之一,“泰西画法”通过宫廷和民间的多种途径对当时苏州的艺术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对于玻璃油画这一新潮的绘画品种,出现在苏州的记载甚至早于清代最著名的贸易城市广州。清代学者毛奇龄(1623-1716)在《西河合集序》中有明代苏州画家戴鹤善绘玻璃油画的记载。可见,在明代的苏州用“泰西法”画画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现象。
明末清初,传教士在苏州地区的传教活动更加活跃,这也带动了更多的民间人士包括画家成为教友或教徒,例如,“清初六大家”之一的常熟(今苏州)画家吴历(1632-1718),早年多与传教士来往,中年时加入耶稣会,成为一名忠实的天主教徒。他的中国画作品在画面布局和设色、明暗表现等方面多有西法之痕迹,有似水彩画。又如“姑苏版”的作者丁亮先(民间画师,生卒不详)也是一名天主教徒,他所表现的建筑风景绘画更是把西法中的明暗透视之法运用得十分娴熟。当时,苏州版画采用“泰西法”成为一种时尚,在广大民间画工的创作实践中确立了特定的“仿泰西法”画风,并风行百余年。至18 世纪,“姑苏版”成为民间“仿泰西笔法”极为成功的范例,它是中国民间画家对西学中传的一次有力回应,也是研究这一时期西画东渐的民间范本。康熙中期以后的姑苏版都可见透视法的运用,而且越到后面透视越精确,“泰西法”运用越娴熟。例如,《姑苏虎丘盛胜景图》(图2),整体画面采用近大远小的透视法则构图,画面右下角房屋的绘制透视明显,从房屋比例来说达到较为精确的程度,我们甚至可以用建筑效果设计图的要求来推敲它。

图2《姑苏虎丘胜景图》康熙中后期
但 是, 许 多民间绘画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对“仿泰西笔法”运用有时显得比较粗糙。如一些作品中虽然可以看出运用了透视法,但是画面中的透视灭点却有几个,明显是几个物象的透视的混搭组合,且物象造型和比例方面也较牵强。直至雍正十三年(1735),透视学专著《视学》修订再版,焦点透视法与明暗法进一步较为广泛地扩散于民间,民间对泰西法的学习才得到了理论上的科学指导。
具体来看,康、雍、乾三朝,四大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姑苏版”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1.开放海禁是“姑苏版”产生的重要条件
清代于康熙二十三年(l684 年)开放海禁之后,进出口贸易隆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增强,西方加强了以教会为主要工具的文化渗透,进而为其经济贸易服务。清代前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本顺应了形势的发展,采取了海纳百川的态度,虽然这种态度还称不上真正的“开放”,但还是折射出康熙年间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风貌,朝廷这种对待西方经济文化的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2 在对观察组患者进行随访的基础上,同时对其进行延续性护理:1)出院后及时加患者或家属进入微信群,在其出院后,定期在微信群发布有关糖尿病知识的手册,并对其提出的疑问进行详细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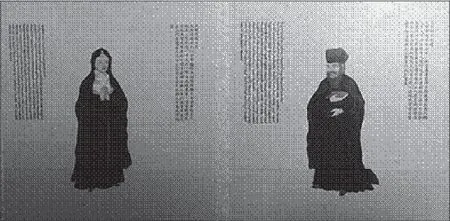
图3《职贡图》清乾隆年间大西洋国夷人僧、大西洋国女尼画册
外国文化和欧洲美术随着清政府开放海禁,随着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清代对来华职贡的传教士都有比较翔实的图像记录和文献记载(图3)。早在康熙三十四年(1715),郎世宁来华,进入宫廷效力,传授西方绘画技法。在中西画法的相互交流中,一方面,来华的传教士画家主动改变自己的画风以适应新的主人,另一方面,中国画家学习并运用西画技巧,以丰富传统的表现手段。中西美术家在互相学习和探索中前进,创造出兼采中西的新形式。当时,融合中西的画法采用自上而下的传播途径,从清宫传播、发展到民间。在此过程中,苏州地区版画受到深刻影响,并最终产生姑苏版。
另外,开放海禁,尤其是江苏海关的开通,为“姑苏版”大量销往海外提供了畅达的贸易通道。苏州地处长江、运河和长江入海口,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之地,成为清王朝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据清代康熙时人所著的《东华录》记载:“(苏州地区)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可见当时苏州对外贸易的繁盛情景。因此,开放海禁是姑苏版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2.传教士对苏州地区吸纳借鉴“泰西法”的影响
明代晚期以来,西方传教士队伍在苏州等中心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在著述的《不得已》中记有苏州堂,苏州堂“在娄门内混堂巷,今移在皇府基河西”。伽马《1663 年中国教务统计表》列苏州堂1 座,教徒500 人;徐宗泽之《1664年全国教务情形》无堂数,列教徒500 人。相对其他江南中心城市,苏州开教稍晚,1652 年何大化在苏州授洗2359 人,但未见教筑教堂的记录。费赖之书《潘国光传》也称苏州教堂建于1658 年:“1658年国光得甘第大及一武官之资助,在松江、苏州各建教堂一所。”教堂和教友的数量说明了传教士在苏州的传教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传教士把带有西洋画的宣传品在民间传播的时候,教友中间也不乏画家或画师,他们充分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洋画法,并运用到他们的绘画作品之中。于是西洋绘画的影响首先在版画中显现出来。明代天启年间的金陵版《金陵图吟》就是一例。这种影响一旦出现,便广泛地传播开来,到清代乾隆年间达到了鼎盛;而从地区上讲,受影响最大的是苏州一带。苏州版画家此时已经非常注重物象的比例和透视的科学性,这与传统绘画对物体远近关系的认知不同,应是西洋透视观念影响的结果。庞薰琹先生在《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中指出这个时期的苏州版画是“用木刻去模仿西洋铜版画的作风”,在描绘风景的作品如《三百六十行》《姑苏万年桥》等姑苏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运用:画中的房屋、街市、行人和桥梁、船只构成了近、中、远景三种层次,各个层次中物体大小比例准确,并有较一致的焦点,体现出西洋透视法之规范。在另外一些姑苏版中,如《西洋剧场图》(图4)、《泰西五马图》《西湖风景图》等,在透视法、明暗法、制版、色彩、题材等方面更是完全运用泰西法绘制的图像。

图4 《西洋剧场图》乾隆时期92.8x47.4CM 日本收藏
3.海外市场驱动逐步催生“姑苏版”画风的形成
“姑苏版”画风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借鉴融合、创新发展和成熟定型三个演变阶段。至乾隆时期,探索过程中的姑苏版,迅速催化发展并成熟定型,发展成为特定时期具有苏州地方特色和中国民族风格的重要绘画样式。
泰西笔意最为兴盛之时,正是17-18 世纪中外贸易密切交流时期,只要是中国的产品,欧洲人都争相购买或仿制。随着海外贸易的往来和欧洲“中国热”大潮席卷而来,“姑苏版”的订单也纷至沓来,苏州画铺根据海外商业订单定期、定量地创作具有“泰西笔法”风格的版画作品。这段时期苏州大型木刻版画上,往往有“仿泰西笔法”“仿泰西笔意”的题跋。画家和画商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表明自己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告知消费者其作品之新颖和时尚,以此招揽更多生意,有着一种广告宣传的目的。印制、销售这些版画的作坊、商家以“泰西法”“仿泰西”这些字眼来表明其区别于传统版画的样式,借此表明其版画是中西结合的创新作品,另一方面则是有种“唯恐世人不识君”的心态,或许也是对其未曾直接受过西洋美术训练而对其仿制西洋画法的不自信。
融汇中西艺术元素的“姑苏版”,迎合了海外市场追求“中国风”的时尚审美趣味,在为苏州画商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成为民间画铺争相模仿和销售的对象,这在当时甚至是时尚和流行之事。不仅如此,姑苏版自产生以来便形成了以画铺出版商为主体的版画“复制”生产系统,出版商根据市场需求选定题材内容、或向画家购买画稿或根据订单要求复制画稿,然后再组织进行雕刻,印刷和销售。从这个角度看,“仿泰西笔意”的民间版画作品不在其他地方形成特色,只在经济文化发达的苏州形成规模化生产和销售,从地域选择来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4.外销订制对“姑苏版”画风确立的影响
郑振铎先生认为:“像桃花坞印刷的《西洋剧场图》就完全是西洋画的木刻翻版,有阴阳向背,有远近,有明暗。”通过对海外收藏的《西洋剧场图》等姑苏版的研究,可以发现海外客户对姑苏版的订单要求的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姑苏版,使之向着更专业的“泰西法”水准发展。在姑苏版的对外贸易中,海外客户会以“来样加工”的方式订制“姑苏版”,这使得苏州年画铺有机会亲眼目睹真正的欧洲铜版画和西洋画,像《西洋剧场图》这类作品,应是海外客户将绘画样稿寄送到苏州画铺,苏州画铺继而用木刻形式翻刻了西洋铜版画,就效果来看,这类作品已无传统木刻版画的味道,反倒是像极了西洋铜版画。画面中细密的线条排列成规整的平行线,构成不同块面的阴影,出现在地面、墙壁、柱子、人物等处,这些明暗不同层次的排线在表现物象的阴暗面以及物象的灰色调的时候,起到了素描似的逼真绘画效果。其他物象的塑造也以铜版画的细密排线来表现,这些排线成块面状,有的不止一层,有的是两层垂直叠加,有的是带斜度的排线叠加。这类作品完全采用西洋绘画的明暗、透视等技法来表现西洋风景,往往根据物象体积或角度的不同进行变化,这种熟练运用泰西笔法的水平已不在欧洲铜版画效果之下。因此可以判断,《西洋剧场图》这类作品在当时就是海外客户的“高级订制”产品。现在姑苏版在国内几乎难觅踪迹,而大部分被保存在欧洲、日本,也基本可以印证姑苏版原来的销售对象就是欧洲和日本等海外市场。苏州这个时期表现都市风景的大幅木刻版画,使用排刀刻制的技法细腻而纯熟,是仿铜版画风格,在尺度、色彩、技法等方面,都与年画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为适应海外销售订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康乾时期,苏州经济发达,在世界上也属一流繁华时尚之地。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云:“顺康时,妇女妆饰,以苏州为最好,犹欧洲各国之巴黎也。”时人把苏州与巴黎做类比,可见苏州与欧洲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是平常之事。乾隆年间苏州人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有西人赁屋于余画铺之左,放利债为业,时倩余作画,因识之”,可见欧洲人在苏州民间做生意是十分寻常之事。在与欧洲客商的频繁接触过程中,苏州画师有更多的机会直接看到欧洲人带来的西洋绘画作品,得到更多的关于“泰西法”的专业指导,这些都促使姑苏版的创作者们对产品有着更加专业化的诉求。这一时期,姑苏版的画风已经完全“泰西化”了。
三、“姑苏版”衰落及消亡的原因
文化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之一,反映了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状况。清代由盛到衰的变化,在绘画和工艺美术作品中也都有一定反映。乾隆时期,艺术异常繁荣,出现新风尚,展现的是繁褥而精致的风格,这正是清初艺术作品中所缺少的。“泰西法”繁复的排线笔法正好契合了时代画风变化的诉求,助推“姑苏版”在雍正、乾隆时期达到艺术的高峰。但至嘉庆时期,在“闭关锁国”政策的持续冲击影响下,“姑苏版”已呈奄奄一息状态;到了道光时期,则已基本销声匿迹。姑苏版从产生、繁荣再到没落,恰如昙花一现般绚烂而又仓促,前后不过百余年时间。其中的原因有多种元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泰西笔法”在苏州版画运用中的消失。
1.清宫禁教和海禁促使“姑苏版”走向衰落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非一帆风顺,1715 年,当罗马教皇听说他在中国的传教士居然参加中国民俗的祭祀活动,断然下“禁约”教谕。本来就对传教士的活动不甚放心的康熙皇帝,无法容忍这般无礼,马上发布禁止传教士活动的谕令。而这一禁令又得到之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的继承和严格执行,这对中西艺术交流直接带来了阻碍。
另外,乾隆时期开始关闭江海关,“姑苏版”也正是从这时悄无声息的开始走向衰落。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制度。所谓“一口通商”是指当时清政府撤销了宁波、泉州、松江三港的海关,规定“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由于“姑苏版”的受众主要是外国人,关闭贸易口岸使进出口通商变得困难,“姑苏版”作品开始滞销。之后,清宫以及民间“参用西法”的风尚衰歇,可以说“泰西画法”是始于宫廷而止于宫廷。失去了海外市场的订单,泰西笔法的“姑苏版”就好比植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比起苏州其他的版刻品种——“画张”(晚清称为“年画”),“姑苏版”制作成本高出太多,国内市场基本没有销路,因此,“仿泰西笔法”的“姑苏版”最终还是悄然消亡。
至于嘉庆时期仍有“姑苏版”,说明了姑苏版在这一时期仍有通道远运海外,只是贸易没有乾隆时期兴盛,这可以从“姑苏版”存世作品数量,特别是作品质量等方面得以证明。越是质量高越是说明海外贸易之兴盛,画铺因为商品利润相对可观而精心制作。那么关闭江苏海关后,姑苏版这些外销商品如何还能远销海外?其一,当时走“曲线”路线,运至粤海关后再远销海外市场。其二,“一口通商肯定不如多口通商,但一些后人对此项政策的理解常有夸大失实之处。首先,当时以省命名的海关并非只有一个港口,而是下辖多个港口。其次,撤销海关机构不等于完全封港,例如,‘一口通商’期间的赴日铜商就仍走宁波。再次,贸易量与通商口岸的数量不存在线性关系,它更多的是使原来通过其他关口的进出口商品改为通过仍允许通商的关口。更重要的是,除合法贸易外,还有大量的走私贸易。”虽然江海关关闭后“姑苏版”仍有渠道运销国外,但这明显地提高了国内运输的难度和成本,极大地限制了“姑苏版”的外销发展,最终直接带来“姑苏版”的衰落。作为一种艺术商品,一旦失去了销售渠道和市场,就基本意味着其艺术生命的式微。
2.传统绘画观念积压“泰西法”生存发展空间
“泰西法”创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其透视方式是根据近代的几何原理而来,明暗关系则基于近代的光学理论,当时的中国画家一般对这些科技知识并不熟悉,所以即使想学西画,也非易事。与郎士宁同处朝中的翰林画家邹一桂(1686-1772)在《小山画谱》中这样描述西方绘画特点:“西洋人善于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馏黍(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但是,中国传统绘画讲求的是写意,抒情遣怀,与西洋人纯写实的审美观有着很大的差异。文人们虽惊异西洋艺术“与生人不殊”的精细逼真,却不太承认它是艺术品,所以,泰西笔法往往被传统文人品评为“缺乏神逸”而不屑,如邹一桂肯定西洋绘画的阴阳凸凹法“学者能参用一二,亦俱醒法。”但终究认为西洋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可见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在为宫廷服务的实践中,虽然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这只是在外表和形式上得到了认可,而于文化的内核和价值的取向上始终难以得到认同。
中西文化的不同质使得固有的传统文化与新传入的西洋画之间难以交融辉映和互学共进,而是始终横亘着一条看得见的抑或看不见的分水岭。中国传统文人在面对新传入的西洋绘画及其技术体系时保持着一种矜持和保守的心理,甚至还有一丝歧视和敌意。沈宗骞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完成的画学论著《芥舟学画编》中,如此评论西洋画:“又今人于阴阳明晦之间太为著相于是,就日光所映有光处为白,背光处为黑,遂有西洋法一派,此则泥于用墨而非吾所以为用墨之道也。”沈宗骞指出了西洋画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画面的光影和明暗效果,却片面地以中国画的标准看待西洋画,套用对烘染用墨的技法解释去理解西洋明暗法,这段评论是在西洋画传入中国达到最兴盛之时,却未见时人对西洋画有多少理解。同样,晚清画家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表示“愚谓洋法不但不必学,亦不能学,只可不学为愈。”所以,焦秉贞的作品虽然在清宫之中曾风行一时,但在当时好古的文人画家看来,却是“不入画品”的“虽工亦匠”之作而不被欣赏。《国朝画征录》中写道:“焦氏得其意而变通之,然非雅赏也,好古者不足取。”虽然在西方传教士及其作品的感染下,画面的阴阳凹凸,富于立体感的表现法曾对中国的一部分画家产生过一定的吸引力,但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使一般传统文人都无法理解西洋画技法,所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难以接受西洋画法。西洋绘画终究难以在清代融入中国传统绘画之主流。因此,从总体看,被誉为正统的中国文人绘画并没有表现出对西洋绘画视觉真实感有多大兴趣,并最终还是以传统绘画的评价标准贬低西洋画技巧。
明清时期,传统绘画观念仍统治着主流画坛,人们对外来艺术的态度总体来说比较保守,传教士画家等能在清宫发展立足也只是凭借皇帝一时的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心,以及西洋画家们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折中方式为自己的专业寻求到的生存之道。从中西结合的绘画风格的形成来看,皇帝个人和宫廷的喜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对西洋风绘画创作的干预一方面促进了其迅速繁荣,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它在笔墨气韵方面的艺术探索。很多中国宫廷画家、洋画家都对折中主义的画法并不情愿,不能尽情地施展自己的创作意趣,所以,此时宫廷趣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中体西用”的画风,并没有经受住考验。康熙后期,直到雍正、乾隆年间,教禁日益加剧,社会上作为宗教宣传的西洋画所受的打击则更大,这些都使得西洋画在清中叶以后,几乎濒于绝迹。“乾隆季叶西教被禁,钦天监中西士渐绝,于是中国画坛中糅合中西之新派,亦斩焉中绝矣。”况且,接受泰西法的国内消费者之受众远远达不到广泛和普遍的程度,大多数消费者对这一异于传统绘画形式的、另类的“仿泰西笔法”,不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姑苏版”无法立足生存于国内。
3.“姑苏版”制作成本制约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开拓
“姑苏版”由于其复杂的制作工艺成本,价格相对昂贵,要在市民阶层形成一个固定的消费群体尚有难度。从“姑苏版”创作的版材来看,版材取料通常为较硬的木料,如梨木、枣木等,为了更好地雕琢,版材的厚度要有一定标准,同时为了防止版材变形带来印制时的麻烦,“姑苏版”所用木材的厚度要达到4 厘米至6 厘米。因此,所要制作的“姑苏版”的画幅越大,其厚度要求相对要求越厚。“姑苏版”中大幅的作品比比皆是,仿泰西笔法的“姑苏版”就是以大版幅、大制作而著称于世,其单幅尺寸多为横50厘米左右,纵100 厘米左右,如雍正年间的《姑苏阊门图》尺寸是56 厘米×108.6 厘米,《三百六十行图》尺寸是55.6 厘米×108.7 厘米,乾隆年间的《全本西厢记》尺寸是43.7 厘米×98.9 厘米,《雪中送炭图》尺寸是53.6 厘米×100.6 厘米,《姑苏万年桥》(1741)的版幅达57.5 厘米×106.5 厘米,《岁朝图》尺寸是540 厘米×978 厘米。寻找横50 多厘米、纵100 多厘米的木料版材绝非易事,对于这些大版幅的作品,较常用的方法是采用拼版来降低版材的成本。但在《姑苏阊门图》等这类精彩的大幅“姑苏版”作品中,却很难找到拼版痕迹,说明当时的版画铺对此类成本不菲、售价可观的作品非常重视,因此愿意不惜成本地制作出大版子。另外,版幅越大的“姑苏版”,其刻制和印刷的难度也相应提高。刻印成本越高,不仅需要更多的木料、纸张、颜料、人工,也更容易产生次品或废品,因此,“姑苏版”的出售价格自然不菲,很难作为廉价的绘画产品来销售,这也足以印证“姑苏版”的消费群体并非是国内的平民百姓,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为满足海外订单而制作的姑苏版,每件作品都是一次性的 “精品定制”和“新鲜制作”,而不是像清末的年画版子那样可以不断地重复刷印。
四、结语
经济文化的交流互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清代中期,苏州套色版画借鉴“泰西法”催生了一种崭新艺术样式——“姑苏版”,并带来百余年的繁荣发展。后来,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近乎中断,“泰西法”的运用逐渐消失,又最终带来“姑苏版”的消亡。比之当时西方社会的“中国热”,中国社会对异邦美术总体上还是持排斥甚至鄙夷态度,所以,“仿泰西笔法”的“姑苏版”在国内的受众市场极其有限。而随着海外订单的消失,“姑苏版”最终还是走向了没落。“姑苏版”现象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研究,以便为当下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带来更多的历史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