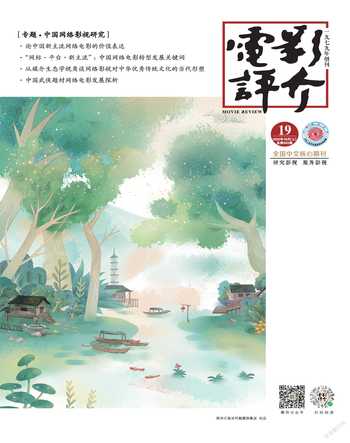从油画空间到影像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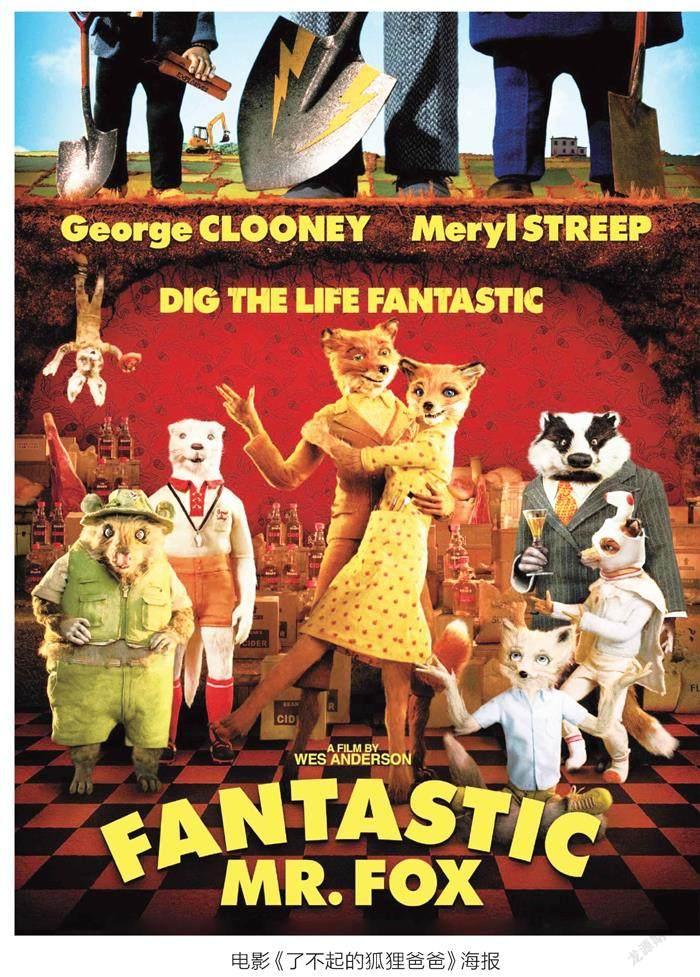

一、影像空间的前传——油画的物质审美维度
油画,是画家用油质颜料在布、木板、厚纸和墙壁上绘制而成的图画,其色彩丰富,表现力强且耐于存储,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价值和审美价值。作为一种重要的绘画形式,油画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所使用的绘画材料密切相关。首先,油画最突出的特点即以油为中间媒介来调制颜料,“用来调色用的媒剂的主要用途是化解颜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减少颜料之间的不透明,而且可以使颜料粘在绘画板上”[1];其次,油画本身即为颜料的运用与叠加,是颜料在画布上的涂抹与呈现,因此油画颜料的色彩呈现与附着度将直接影响到油画作品的美学表现;再者,画布、木板等基底也是油画审美表现的重要物质载体,是颜料附着的主要对象。故而油画语言的建构、审美性表现与色彩的运用均以物质性材料为基础,油画原料是绘制油画的必要物质基础,是构成油画的基石;油画是依赖于颜料、调色油、基底等物质材料而存在的,这也是油画物质性的主要表现。从本质上来说,油画是以油画材料的存在为前提而产生的艺术表现形式,油画原料不仅是构成油画本身的载体,也是油画语言中重要的物质呈现形式和审美表现手段,油画的美学表现必须以这种物质性为基础。因此,油画本身的主题表现与其所构建的人文性形成于矿物颜料的叠加与运用,油画材料所构建的物质二维空间是承载油画主题和美学特征的基本物质载体。
作为一种艺术品,油画中饱含着创作者的情感与思想,是对现实生活的镜像反映或想象叠加,折射出了画家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美国戏剧家艾·威尔逊曾言:“艺术并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反映……这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或对生活进行概括,或像镜子一样反映生活。”[2]从油画的主题来看,其所构建的人文性与表现出的美学观念均带有现实生活的影子。纵观油画的发展史,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迁,油画的风格与主题也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公元15世纪,欧洲处于文艺复兴之中,受到宗教批判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要求,写实主义风格盛行。“西方油画的写实体系把真实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这是由于当时社会背景的需要所决定的。教会需要艺术家在教堂的建筑中创作表现宗教历史的绘画,皇室、贵族则需要艺术家为自己画像,因此油画写实的功能应运而生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西方的审美观是从真实的造型体系中提炼出来的。”[3]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照相技术的出现使写实主义油画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印象画派应运而生。“他们反对古典主义陈旧的美学观念和法则,推崇利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如光学和色彩学)来推进油画全面的改革”[4],此时油画的色彩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户外写生的模式也随之诞生。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及频繁的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变革,在此背景下抽象画派逐渐出现。在现代主义及崇尚自由解放思想的影响下,部分画家用全新的艺术理念去肢解油画语言以重组画面,用写意性的表达来传递画面的抽象美,以表达自由与反叛精神。因此,油画所构建的人文性来源于现实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一方面,油画的人文性形成于矿物颜料的堆叠,油画使用颜料进行创作并形成了二维的物质空间;另一方面,油画的人文性取材于现实生活,是物质的二维空间与情感的三维空间叠合的结果,而颜料的二维空间堆叠与三维现实的情感交融也构成了油画物质审美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种诞生于油画之后的艺术表现形式,电影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油画的影响。油画依托矿物颜料的堆叠形成了二维的物质空间,这种物质二维空间与依托于现实形成的三维情感空间交融构成了油画作为一种物质的美学,而这一美学渊源与电影所构建的影像空间是完全相合的。首先,油画的物质审美构成了电影的物质审美基础或内在基因。正如油画材料是绘制油画的必要物质基础和载体,电影的产生与发展也离不开各种物质设备的支持。纵观世界电影的发展史,电影行业中每一次重大的变革基本都与技术及设备的发展密切相关。摄影机和放映机的出现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基础的设备支持,使得电影有了可以表现的物质载体;录音设备的出现使得电影从无声转向有声,电影也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彩色胶片则是电影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彩色电影使得电影画面从原来单调的黑白双色变成了五彩缤纷的光影世界,也因为声音和色彩的加入,使电影更加趋于自然也接近生活。从此电影艺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5]数控摄影机的出现则使得电影场景更为丰富,借助于数控摄影机的灵活拍攝与高清镜头,各种复杂的电影场景得以充分展现。同样的,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灯光、音响、服装道具等硬件设备和数字技术、视听技术等软件技术也对构建电影场景起到了重要作用,离开了这些物质设备,电影所构筑的场景意义将会消失殆尽。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电影所构建的审美空间离不开各种物质设备的支持。
其次,电影构建的人文性也取材于现实生活,电影这一艺术本质上是对生活的复写和再创作,电影是依托于现实而产生的艺术形态。从电影的主题到人物形象的建构再到电影场景和电影语言,无一不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影子。因此,电影同油画一样,均是以物质设备、材料为基础,以现实生活为创作来源,借助于物质二维空间与情感三维空间交融所建构与形成物质审美空间,即电影所构建的美学空间与油画构建的空间具有重合之处。正因如此,电影空间的美学才带有油画空间美学的美学基因,油画所构建的美学空间也就成为了电影影像空间美学的基础。
二、影像空间的诞生——电影对油画空间的复写
油画为电影影像空间的构建提供了美学基因,电影空间的建构与诞生是对油画审美空间的复写与升华。一方面,电影影像空间的诞生是将油画空间美学转译、腾挪到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另一方面电影所构筑的影像空间是对油画空间美学的创作性演绎和升华。从本质上来说,电影影像空间的美学呈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油画空间美学在电影中的还原,即影像空间对油画空间美学的复写与转译,这种还原与复写主要体现在影片的油画特色与美学表现。首先,电影的影像空间通过颜色运用及光影变化来对油画审美空间进行还原与呈现。油画中的光影变化与颜色呈现在电影的视觉效果上主要体现为“厚重感”和“高覆盖性”这两个维度;前者是指油画材料和技法,如颜料厚堆、色彩的调和与分层、视觉上的肌理特征、立体感以及光影处理等;后者则是指电影语言中展现的图像纹路、浮雕感及电影镜头的运用。在通常情况下,“油画颜料带有特殊的化学属性,不同角度呈现的光线和色泽亦可应用于不同的叙事和语境中。”[6]故而油画利用不同颜色的涂抹来实现审美空间的构造与意境的表达;而电影则利用不同的色彩搭配,通过远近镜头、特写镜头的灵活运用与转换描绘出唯美的电影画面,构筑起了独特的影像空间。一方面,电影通过镜头的运用展现出精妙的画面构图,远近镜头的灵活运用正如油画中的笔触运用,勾勒出独特的电影画面与审美空间,而特写镜头则通过对局部的放大使其更具有冲击力,体现了油画的写实性与逼真性;另一方面,电影中的色彩呈现相当于油画中的颜料,影片细腻的质感和视觉效果对比强烈的色彩组合搭配共同构成了电影中唯美的画面场景,完成了对油画画面场景的复写与转译。这不仅呈现出油画的美学特征,而且还构建起了电影的叙事空间,实现了对电影主题的烘托和渲染。在动画电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中,导演韦斯·安德森以橘黄色调为主,刻画狐狸、土地、房屋、树木、家居、乌云等形象,利用明黄、土黄、暗黄、橘黄、姜黄、棕等邻近色的搭配来展现与缩小叙事空间,以突出主体人物形象,让受众聚焦于狐狸爸爸的生存与斗争,在突出电影主题的同时也构建了油画般的唯美场景。同时,电影影片独特的色彩运用和画面美感也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器件、物品以油画般的方式呈现出来,给受众带来了独特的感官享受和巨大的视觉冲击。
此外,电影对光线的运用,光影的明暗交替使得电影画面具有油画的空间感和立体感。恰如俄罗斯动画导演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在油画绘画时所言“当光线透过颜料画面变得增加通透明亮,光线和色彩可以让油画的美感更加突出和醒目,在影片中这种效果的实现具有不可比拟的特殊效果”[7]。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影片整体呈现出油画风格的色调构图,冷暖交织的柠檬黄和青金石色调贯穿全片。导演以油画本身的基础色调为电影主色调,随着场景的切换调整不同画面场景中的灯光角度与光线的明暗程度,通过光影的对比来表现人物面部的明暗变化,以烘托人物形象,推进电影叙事主线。影片中画面的光感通常加入审美和情感因素,用光线变化造成特有的影调透视和色调透视。如葛丽叶与皮特在户外散步的场景中,春景时画面明亮接近自然光,高饱和的颜色与光线的使用让影片画面变得更加通透明亮,呈现出春日生机勃勃之景;雪景则利用地面雪花反射的大量散射光反打向上,用滤色镜加入暖黄色,充溢在整个画幅之间并且弥漫开来,形成优美柔和的暖黄色调。而少女葛利叶在地窖中休息时,导演以光线为画笔,白色侧逆光散射开来,正好打在人物的服装和侧脸上,使人物从黝黑暗沉的背景中得以凸显,就如同油画利用阴影与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电影从整体中突出局部是光线强调与突出的最高层次。故而油画借助于颜料的涂抹呈现出物质审美空间,反映现实社会;而电影则利用颜色设计与光影变化来构筑影像空间,刻画电影主题,实现对油画审美空间的复写与转译。
电影影像空间美学呈现的另一维度即为电影对油画审美空间的创造性演绎和升华,也即油画空间的电影化呈现。电影场景本身实现了对油画场面的还原,使得作为二维空间而存在的画作变为了三维空间中真实存在的场景与画面,将油画中的场景融入电影叙事中,这不仅给受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且也使画面场景变为真实的场景与环境,推动着叙事主线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影片《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电影使用复现蒙太奇手法展示时空背景,依据维米尔《德尔夫特风光》一画还原“四百年未变”的欧洲最洁净城市,并作为影片的主要背景环境;影片中出镜的维米尔家的院落,复现了同为荷兰小画派彼得·德·霍赫的《德尔夫特的院落》一画;而在影片临近结尾则使用了长达90秒的长镜头和大特写对“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银幕造型进行终极呈现,首先画面黑幕,继而从中心溶入,随着镜头的后拉,由少女珍珠耳环的局部大特写到逐渐出现整个脸部特写,再至画幅整体呈现并停格,结尾的油画画面同此前电影中的人物画面重合,实现了对油画的真实再现与复写。
三、影像空间的实现——油画影像的二元审美价值
油画是历史的油画,是在过去的历史时空中形成并展现的艺术审美形式,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是画家利用颜料在画布上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涂抹与反映。而电影技术让历史性的油画艺术在电影空间中得到再现、演绎、升华,将油畫融入电影叙事话语中,用油画影像构筑电影影像空间,借助影像空间复原油画场景,能以更符合现代人审美方式的手段来传递油画美学。电影通过影像空间再造,形成了历史的油画现代化的视觉演绎,让历史的油画与现代社会沟通与交互,同时融入电影语境,实现了电影的历史物质(油画构成的空间)到现代电影物质(现代空间物质)的融合与交互。由此,电影所构筑的影像空间就实现了油画影像的二元审美价值:一是电影中出镜的油画作品呈现出油画本身作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即油画的历史价值,使油画作品借助于电影进行了更广范围的传播;二是将油画融入电影之中,赋予油画作品以电影语言和叙事话语,利用电影还原油画场景与创作历程,将油画本身作为电影主线并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揭示油画创作与画家背后的故事,展现油画影像的现实价值。
首先,电影利用数字技术、视听技术等新技术丰富了油画的审美表现形式,实现了油画审美空间的电影化呈现,这就将油画融入了现代语境,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方式,展现了其作为作品的价值,即油画的历史价值。电影通过CGI技术及复原技术对油画进行了呈现,让静态的油画变为动态的,技术呈现油画本身的还原与影像化过程,完成了在真实素材和想象基础上的艺术再现。一方面,在技术与艺术殊途同归的审美表达之下,油画本身呈现出了一种丰富而生动的视听表现,这就使得油画本身的美学价值在电影中得以展现。影片《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就呈现了影视技术与油画艺术两者之间完美结合所构筑的宏大影像空间,导演利用动画技术手段将油画的特点表现在电影之中,不仅将主要人物以油画风的形式进行表现,而且还将梵高的画作由静态变为动态,从而令梵高神鬼莫测的笔触、出神入化的线条、绚丽斑驳的色彩都跃然于银幕之上;而另一方面,借助于电影这一更广泛的传播渠道,油画作品被更广泛地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油画所表达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也由此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其次,电影所构筑的影像空间复原了油画场景并将油画色彩与元素融入电影创作中,以油画作品为线索串联剧情主线,以油画复原的场景变化服务于叙事需要或主题表达,展现了油画的现实价值。整体而言,油画语言艺术上的表现力可以分为色彩、笔触和材料技法三方面,在电影中主要体现为强烈的视觉震撼,精致的画面构图,逼真细腻的人物形象等特点;而油画艺术特点则通过影片画面构图、色彩对比、光线运用、材质质感、镜头变换等要素进行组合搭配而呈现,适用于主题表达或影片叙事需要。《至爱梵高》利用剧情片的叙事技法,以梵高的代表性油画为叙事主线,将油画的田园风格融入电影影像空间,形成了两相契合的艺术化表达。“多洛塔导演从文森特·梵高的作品出发,以其油画为创作素材,从他的大量信件中串联叙事,独特的话语形式成就了影片视觉和思想美的统一,油画语言思想意蕴巧妙的‘影像化,实现了该片形式层面的个人特色化。”[8]为了更好地还原作品,导演将梵高的油画风格融入电影的整体创作中,根据影片叙事需要对油画素材进行处理,将梵高的生平事迹与油画作品进行情节关联,在想象的基础上串联叙事主线,将油画作品作为电影线索,通过油画作品的呈现与叙事推进展现出文森特·梵高的人物形象。创制者将油画与动画结合,借助电影形式让油画动了起来,展现出油画视觉表现效果的多样性和层次感,实现刺激观众视觉感受的目的。“通过梵高作品的艺术性俘获了观众的情绪体验,从而使其探究影片的呈现场景和梵高原作之间的关联性,激发起对梵高作品的艺术思想和风格特色的探索欲,并在对话叙事中了解梵高个人的性格特点,实现了叙事内容上的独特性。”[9]因此,油画影像的现实审美价值主要体现为电影影像空间复原油画画面,作为故事背景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油画本身作为电影叙事主线串联起了电影故事情节,彰显了电影主题。
结语
油画是来源于现实生活,依托于颜料对画布的涂抹而构筑的油画审美空间;而电影是依托于现实生活,依赖于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的运用而形成的电影影像空间。因此究其本质,电影的影像审美空间与油画审美空间的构造具有相似性,均是由二维物质空间与三维情感空间交融的结果,故而油画审美空间成了电影影像审美空间的美学基因,电影影像空间的构造实现了对油画审美空间的复写和再演绎。一方面,电影影像空间实现了对油画审美空间的符号转译与复写;另一方面,借助于数字技术与视听技术,电影为油画审美空间赋予了更多样化的审美表达,实现了对油画审美空间的再创作与现代化的视觉演绎。同时,电影的影像空间展现了油画影像的二元审美价值,即实现了油畫作品的历史价值与其作为影片的现实价值的统一,不仅展现了油画作为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而且赋予了油画作品以现实意义,将其影像化,展现出了其作为影片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江山.浅谈西方油画材料的发展历程与变迁[ J ].艺术评鉴,2018(13):38-39.
[2]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著.世界艺术与美学(第二辑)[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282.
[3][波兰]雅克·德比奇,[法]让·弗兰索瓦·法弗尔,[德]特利奇·格鲁纳瓦尔德.西方美术史[M].徐庆平,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1:177.
[4]罗璇.中西油画发展的错位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4.
[5]梁明,杨天东.中国电影类型化与电影技术发展[ J ].当代电影,2010(12):82-87.
[6]张大勇,潘宝泉.《了不起的狐狸爸爸》:韦斯·安德森油画影像漫巡[ J ].电影评介,2021(04):90-92.
[7]侯可心.动漫音乐在影片中的应用及艺术效果探究[ J ].艺术科技,2017(06):169.
[8]张大勇,潘宝泉.《至爱梵高·星空之谜》:油画影像世界之题旨解码[ J ].电影评介,2020(17):106-108.
[9]姚涛.油画与电影创构的契合——解析《至爱梵高》中的田园意象[ J ].电影评介,2018(15):101-103.
【作者简介】 周如俊,男,安徽六安人,周口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油画,民俗文化,美术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2017年度课题“周口港”[编号:2017-A-05-(147)-08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