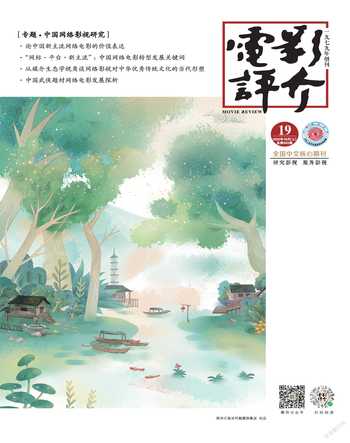从移植到创新:当代国产动画与传统戏曲艺术的互融互通
成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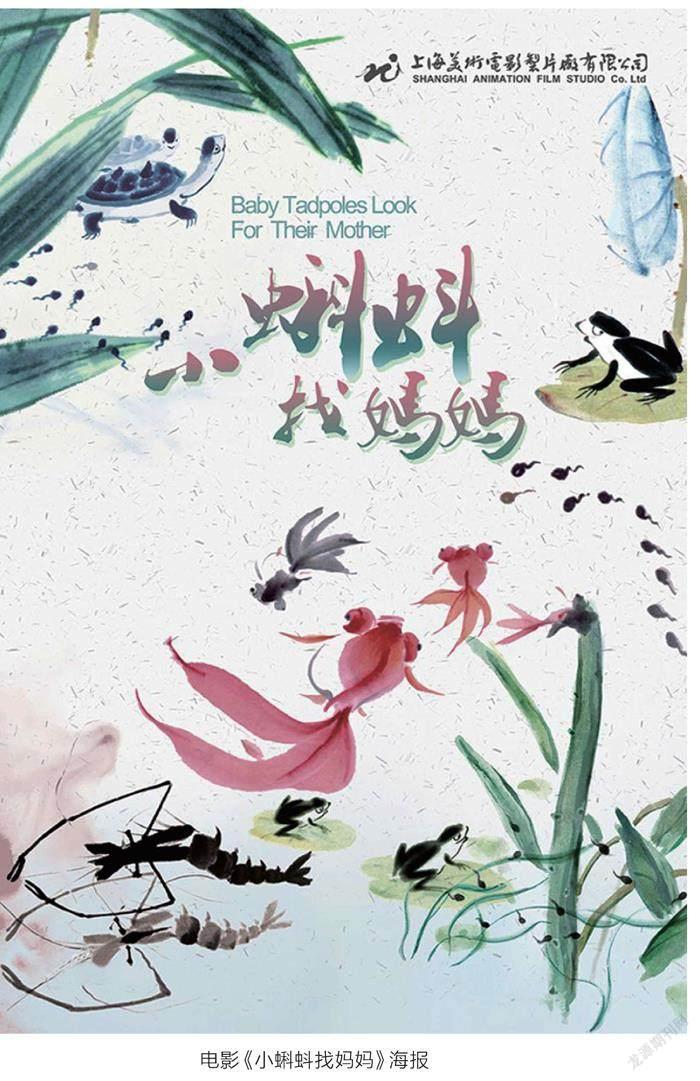

中国动画创作长期以来以多种形式探索民族化的路径,国产动画的民族化意味着动画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均需凸显中国文化特征与民族精神。戏曲是中国特有的集视觉艺术、舞台美术、文学艺术、唱腔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是集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生活意趣于一身的大成者,将戏曲元素融入当代国产动画的创作模式为探寻国产动画民族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一、传统戏曲与动画艺术融合的前提与基础
(一)同为综合艺术具有开放性
中国戏曲最早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以避邪消灾、驱魔娱神为目的的,带有巫术色彩的仪式,其诞生于“瓦舍”“勾栏”处。[1]中国戏曲发展至今,其在内容上不断吸收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内容,在表演形式和舞台美术上吸收不同类型的民间艺术、风俗仪式,最终呈现具有独特风貌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动画是一门集文学、美术、音乐、表演、影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其艺术魅力的呈现需要通过观众对动画中夸张的表演、象征性图像形式和具有想象的艺术表现力。中国戏曲艺术则正有舞台表演的假定性、程式化的动作、谱式化妆容,其开放性的戏曲舞台表演形式需要通过观众的联想、品味才能尽其语言之精妙,中国戏曲与现代动画艺术在表演种类和艺术形式的开放性上具有诸多耦合性。
(二)“形式审美”凸显假定性
假定性是美学与艺术理论中的术语,指“艺术家根据认识原则与审美原则对生活的自然形态所做的程度不同的变形和改造。艺术形象绝不是生活自然形态的机械复制,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作现实,假定性乃是所有艺术固有的本性”[2]。艺术的假定性的本质是展现艺术内容的真实性。艺术与物质现实是不等同的,需要借助假定性来创造假定的空间,以说服观众。尽管假定性是所有艺术种类的固有本性,但在戏曲艺术与动画艺术的形式审美特征中更为凸显。
戏曲舞台上含蓄的、象征的、虚拟的舞台表演手段,皆源于戏曲假定性的戏剧美学思想。“七分表演戏情,三分应付观众”[3],戏曲艺术创作与观众欣赏之间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审美超逸性,是戏曲意象创造在似与不似之间所呈现出的一种超物的天趣”[4]。中国传统戏曲将现实生活凝缩于舞台的虚拟空间中,以程式化的表演体系在人们的习惯性审美心理中唤起共鸣。例如,演员在戏曲舞台上跑一个圆场可以表示任意距离,近则几米,远至千里;摆放在桌上的数只酒杯,有时代表山珍海味,有时亦象征着粗茶淡饭。具有特定意义的舞台表演程式充分调动着观众的艺术想象力,在戏曲艺术的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形式性”审美被置于突出的位置。
“形式审美”同样是动画艺术的特征,“动画艺术从构成元素的多元性、多层次和多维性的结构形态中突出地显现出它的形式审美特征:即陌生化的符号形式、情感形式和生命形式”[5]。动画艺术中的造型是由动画家根据现实社会中的审美体验与艺术追求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是对物质现实加以童话化、神话化的改造,创造出全新的、物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非现实漫画运动影像”[6]。动画艺术中的主体造型是超现实、非现实的虚拟影像,假定性是动画艺术最根本的特征。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与动画艺术均为综合艺术,具有开放性,两种艺术皆在“形式审美”上凸显假定性,两者才能有交汇与融通。中国当代动画作品与传统戏曲有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早在1941年,由“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蟾)执导的中国第一部黑白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41)吸收了大量戏曲元素。例如,影片中的孙悟空借鉴京剧中孙悟空的“武生”形象,典型的“雷公嘴”符合京剧脸谱的设计;铁扇公主与孙悟空之间的打斗动作设计介于武术与舞蹈之间,效仿戏曲舞台上的程式化表演。作为中国动画第一人的万籁鸣曾说道:“要使中国动画事业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必须在自己民族传统土壤里生根。”[7]这一创作理念与创作取向为当代动画创作者所承继与发展。中国当代动画对戏曲元素的运用是历史与美学的选择,从移植到共融再至创新是中国动画走向民族化的路径。
二、从移植到共融:动画艺术吸纳戏曲元素的路径选择
动画艺术作为西方的“舶来品”,自进入中国后就不断吸收传统艺术元素来探索自己的民族性道路,完成自身的民族化建构。动画电影《铁扇公主》中大量借鉴了京剧的人物造型和舞台设计,传统戏曲所独具的美学体系推动中国动画开始民族性探索。1956年,伟特、李克弱导演的动画短片《骄傲的将军》是“中国学派”的开山之作,该片借鉴了大量中国传统戏曲元素。伟特先后提出“标民族之新、立民族之异”和“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的口号,这意味着中国动画正式走上“探民族形式之路”。[8]
尽管《骄傲的将军》将诸多传统戏曲元素植入动画中,但只是对戏曲符号元素进行简单移植,甚至是直接搬入,因此略显“形式化”。随着对中国动画民族形式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过猴山》(1958)、《小蝌蚪找妈妈》(1961)、《牧笛》(1963)等动画开始将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化气质与内涵融入作品,艺术手法更加成熟,逐渐显现出中国动画独有的审美特征,即程式化与意象化。1964年,由万籁鸣、唐澄执导的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1964)公映,先后获得了國内外多项荣誉。“《大闹天宫》(1961——1964年)标志着新中国动画片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动画发展史上的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9]《大闹天宫》成功地将戏曲元素与动画片共融,使戏曲美学风格成为作品中的主要艺术风格。因此,从移植到共融是动画艺术借鉴、吸纳戏曲元素的重要路径选择。
(一)动画的角色设计:借鉴戏曲脸谱与戏曲服饰
戏曲的扮相主要体现为人物脸谱图案的类型化和服装装扮的个性化。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角色行当分为“生、旦、净、丑”四种基本类型。戏曲脸谱的绘制是戏曲扮相的重要部分,戏曲脸谱的勾画严格遵照人物角色的分类,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戏曲所特有的审美趣味。
戏曲脸谱的“简洁生动的设计既是程式化的曲艺表现规律,也深藏着对文化底蕴的理解和表达”[10]。因此,将戏曲造型中脸谱设计的理念运用于动画影片的角色创作,为当代国产动画中角色形象的设计提供了直接且特色鮮明的民族化创作途径。
《骄傲的将军》在人物造型上移植京剧人物脸谱,如将军形象吸取花脸的造型,食客形象则移植丑角的造型。将军的脸部造型与花脸相对比,尽管在色彩与线条的运用中略有淡化,但能明显区分出“三块瓦”(两腮及额着色);《大闹天宫》则对传统戏曲脸谱进行明显的变通与改造,以期实现元素之间的共融,尤其体现在动画主人公孙悟空的脸部造型上。《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并没有直接移植戏曲脸谱,而是“简化京剧脸谱中猴脸上的色块,单纯的原色——红、黄、蓝、绿、白等用墨、色、线统一,形成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猴王的动画造型,创造了一个中国的、被世人认可的动画明星”[11]。动画在角色设计中借鉴戏曲脸谱,既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又有利于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动画人物。
戏曲服饰是戏曲艺术中表现人物社会地位、精神气质,是塑造舞台形象的直接手段,“宁穿破,不穿错”是梨园演员恪守的原则。当代国产动画充分撷取传统戏曲服饰的元素,并将其巧妙应用于动画角色的服饰设计,“使人们感到常见又新鲜,既有传统的东西,又有提炼加工,人物造型不但是地道的‘中国货,而且有鲜明的性格和色彩”[12]。因此,将传统戏曲的服饰特点糅合于动画创作,是塑造民族动画形象的重要环节。
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条丝腰带》于1962年上映,影片借古讽今,以寓言故事的形式讽刺人心的贪婪与永无止境的欲望。拾粪老汉最初的穿着类似于戏曲中的“素褶子”,大襟、斜大领、宽身、身长及足,在戏曲中通常为平民的服装,符合短片中拾粪老汉的身份。之后,老汉用存款买了一件缎面花团锦袍用来搭配自己拾来的珍贵丝腰带,这件新衣与戏曲中的“帔”相似。在戏曲表演中,“帔”是达官显贵所穿之便服,常绣有团花、龙凤等图案。因此,老汉换上的“帔”向观众传递了其想通过一身衣裳改变自己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影片通过对戏曲服装的借鉴与运用,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与形象。
(二)动画的动作设计:吸收戏曲程式化表演形式
王国维认为“戏剧之意义始全”,唯有“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13]。因此,成功的戏曲表演必然展现表演者娴熟的技巧与身段。程式化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中的特殊艺术语汇,即“按照形式的一定格式进行表演”[14],是中国戏曲表演的主要特征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化体现在舞台上不允许有自然形态的原貌出现,一切自然形态的戏剧素材,都须按照美的原则予以提炼、概括、夸张和变形,使之成为节奏鲜明、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15]因此,戏曲表演具有虚拟性、假定性等艺术特征。而动画作为非现实、超现实的虚拟影像,在动作设计中吸收戏曲程式化表演形式,能够为动画表演体系注入艺术性与民族性。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电影《三个和尚》(1980)以全票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并在国际上斩获多个奖项。《三个和尚》的成功在于其既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又富有时代气息,带给观众十足的新鲜感与幽默感。影片“把严肃的生活哲理通过令人发笑的人物和故事表现出来,而它取得强烈的喜剧效果的艺术表现手段,便是夸张与讽刺”[16]。夸张的人物形象与动作是喜剧趣味的载体,夸张动作的设计主要借鉴了传统戏曲中虚拟、程式化的表演手段。动画片《三个和尚》短小简洁,全片没有一句对白,故事的发生发展凭借三位和尚生动有趣的表演来推动。一条蜿蜒崎岖的小路通向高高的山顶,小和尚独自挑着水桶上山下山,影片以小和尚在同一个景别中的几次折返来体现路途的遥远。此处,小和尚的动作设计与戏曲舞台中的“打圆场”有异曲同工之处,其中“打圆场是指按规定动作以圆圈形式绕行,以表现时空的转换”[17]。动画的动作设计吸收戏曲程式化表演形式,使当代国产动画诠释出一种简单却不失精致的表达方式。
(三)动画的背景设置:利用戏曲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
传统戏曲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仅有少量的道具桌椅,观众欣赏戏曲表演主要是看动作和品唱腔。“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18]因此,戏曲背景中的“虚”往往大于“实”,借助虚拟动作创造舞台背景,以强烈的写意性为观众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当代国产动画在背景的设置中仿照戏曲艺术利用以实代虚、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使动画中的背景环境具有提示性与写意性的特征。
动画《金色的海螺》(1963)改编自同名童话诗歌,讲述了一段唯美感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中的背景虽然简单却不乏写意性的美感,如以深浅不一的蓝色色块代表山与海;以白色的连续波浪线象征起起伏伏的海浪;以红色的镂空剪纸表现海底层层叠叠的珊瑚。此外,影片中的多处景物被虚化处理,当海螺姑娘浮出海平面时,姣好的面容在浩渺烟波中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于虚实之间展现了海底世界的神秘与奇妙,同时向观众传达了海螺姑娘身份的奇特,并赋予影片唯美的特质。
三、于创新中重构:传承中国故事与文化精神的戏曲动画
中国传统动画创作中对于戏曲艺术的运用多是将戏曲内容或是戏曲唱腔、表演程式、脸谱等元素直接移植到动画中,令国内外观众耳目一新。当前中国动画作品艺术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多是以中国经典戏曲剧目为内核,或是利用戏曲中的戏曲符号,在创作形式上更多的是呈现当代动画媒体的艺术语言、动态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在艺术形式上不拘泥于戏曲,不重复于传统剧本。不论是当前各大高校中的实验动画作品创作运用了戏曲元素,还是当前以戏曲为主题的“戏曲动画”作品,均是中国动画艺术与戏曲艺术共融发展的有效方式,更是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下时代的新生发。
(一)以经典戏曲故事为内核的重组或改编
戏曲故事多为对生活事件或现象的具体描写,由剧作家从历史与现实生活中选取、集中素材并提炼加工而成。中国戏曲自诞生至今始终在演绎中国故事,塑造传统的中国式人物,弘扬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动画故事内容以经典戏曲故事为内核,因此戏曲动画的故事题材丰富多样,既讲述了一段段英雄传奇与爱情故事,又刻画了无数才子佳人与神仙鬼怪的故事。
国家大剧院推出的特色展览“舞台美术教育系列展”中展出了由中国戏曲学院的师生创作的部分优秀戏曲动画作品。其中,周星创作的《十五贯》(2005)直接采用昆曲经典剧目《十五贯》(又名《双熊梦》)作为故事内核,讲述知府况钟为了查明娄阿鼠偷走15贯钱并杀死油葫芦的案件,况钟乔装成算命先生并最终成功捉拿凶手归案的故事。短片在造型设计上借鉴中国传统陶俑的形态,同时利用昆曲小丑脸谱式的勾画方式,将昆曲这一成熟独立的戏曲艺术以与动画表演艺术契合的方式融入动画造型的再创作。除此之外,还有改编自京剧剧目的《新三岔口》(2022)、《长恨歌》(2021)、《挑华车》(2016)、《连升店》(2011)、《拾玉镯》(2020)等优秀国产动画短片。取材于戏曲剧本的戏曲动画,以经典戏曲故事为内核并在不影响其主旨意蕴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重组或改编。戏曲动画以动画艺术中的多种技法来再现戏曲舞台表演中的情感与思想,通过传达具有典型性的中国故事来展现传统文化与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
(二)数字技术使戏曲元素完成现代转换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驱动下的每一种内容媒介纷纷寻求突破叙事功能局限性的方法。当下,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动画电影不仅提高了动画制作的效率,降低了创作成本,而且使得动画的画面呈现效果更加精美,动画效果充满科技感和时代感。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当代动画中的戏曲元素、传统艺术语言和现代数字化呈现技术有机结合,使动画创作的叙事性、艺术性、功能性都取得新的突破。
在动画版白蛇传《白蛇:缘起》(2019)的人物塑造中,白素贞与小青的面部既保留了传统戏曲中脸谱的造型特征,又添加了蛇的形象特点,脸部呈倒三角形,细长的眉眼,附加白色、绿色服装的搭配,白素贞与小青的形象更为凸显。动画中人物眉宇间的一颦一蹙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清晰且生动,人物的情感、思想皆能精准地传达给观众。例如,白素贞初见许仙时泛红的脸颊配合水袖半遮面的动作,瓢泼大雨中愁眉不展的书生许仙,这是传统戏曲舞台表演无法达到的效果。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动画布景突破了舞台的空间局限性,每一帧画面都与戏曲的念白或唱词相契合,潋滟动人的西湖、烟雨朦胧的断桥皆与现实风景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此外,先进的数字技术能自如地控制人物的身形与动作。《白蛇:缘起》以技术手段精妙地呈现了白素贞与小青腾云驾雾来到人间的画面,细致地描绘了白素贞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海,导致水漫金山寺的场景,而这些画面与场景在戏曲舞台上均由于时空的限制被简化或省略。数字技术将传统经典和现代时尚紧密融合,使戏曲元素在动画中成功完成现代转换,通过动画艺术向观众传达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价值。
(三)跨文化语境下具有普适性的审美价值
优秀的民族文化具有超越地域与时空局限的普适性的审美价值,从而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无价的精神财富。动画艺术作为世界通用的传播媒介,承载着促进本民族意识形态与民俗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重任。跨文化语境下,在动画创作中融入中国戏曲元素和演绎手法是创作具有中国民族特质的动画类型,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战略中的有效途径。因此,利用中国戏曲文化在动画的创作中讲好中国故事,探究具有普适性的审美价值尤为重要。
近年来,戏曲动画在当代动画艺术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由刘娴担任导演,以传统水墨画为绘制技术的戏曲动画《牡丹亭》(2009)自播出后引发观众强烈反响,并获得第五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动画短片“美猴奖”。《牡丹亭》的成功为戏曲动画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提供了借鉴。《牡丹亭》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之间动人的爱情故事。昆剧的曲高和寡使其在现代传播中面临唱腔过于高雅、曲辞晦涩难懂等问题,然而《牡丹亭》中对自由与真挚爱情的向往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戏曲动画《牡丹亭》将昆曲剧目中的曲辞以深浅不一的笔墨、简单的线条、淡雅的色彩绘制成一幅幅生动形象的画卷。娇嫩欲滴的红牡丹含苞待放,伴着和风的杨柳丝轻轻摇曳,闻香而来的彩蝶翩翩起舞,这些令人如痴如醉的美景同时是有着暗喻功能的意象,象征着杜丽娘与柳梦梅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精致的画面取代了艰深晦涩的曲辞,在造境传情的同时给予观众无限的时空想象与审美上的愉悦。观众在对作品主题的意会、情感的领悟中早已跨越了自身的文化基因,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结语
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当代国产动画在探寻民族化道路中需要不断挖掘、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和当代动画艺术在创作形式上具有跨越世纪的高度契合之处。中国戏曲艺术中的角色脸谱形象元素、服饰形态与寓意元素、舞臺表演象征意指为中国当代动画创作提供了诸多可借鉴、可开发的创作元素。而当代动画艺术的创新发展不能止步于对戏曲元素中图形、色彩、程式化动作的形式移植,需要深层次提取戏曲艺术中脸谱造型下的性格暗示、装饰服饰下的社会关系、程式化动态下的剧情象征等戏曲艺术下的中国文化特有的语言表达。
当代动画艺术创作需要发挥其开放性和综合性的艺术特征,积极传承和运用中国经典戏曲故事剧本,以中国经典戏曲剧目为品牌演绎中国故事;和当代数字信息技术融合,突破当代国产动画的呈现途径,使其艺术性和时代形式相统一;在跨文化语境下将戏曲文化精髓融入中国当代动画作品,以戏曲动画的形式助推中国动画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演绎和传播。在中国当代动画创作中探寻与戏曲文化的融合和延伸是探寻国产动画的民族化创新途径,是推动当代国产动画走向世界的有效尝试。
参考文献:
[1]田川流.艺术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286.
[2]姜椿芳.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189.
[3]程砚秋.初拍电影的观感[C]//程永江.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354.
[4]杨非.中国戏曲学院晚霞工程丛书中国戏曲艺术方法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75-76.
[5]佟婷.动画美学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103.
[6]佟婷.动画剧作[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2.
[7]李保传.影视动画作品赏析[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7:50.
[8]李铁.1923—1976中国动画史(上)[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77.
[9]王琥.新中国设计纪事[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9:378.
[10]吴昆.脸谱艺术的植入对中国动画电影的美学启发[ J ].当代电影,2019(08):154-157.
[11]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M].北京:中國电影出版社,2005:218.
[12]杨晓林,彭俊,符攀婵.动画大师王树忱、阿达与詹同[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88.
[13][清]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56.
[14]朱立元.美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778.
[15]婧涵.中国古典戏剧艺术探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136.
[16]陈剑雨.从三句话到一部影片——评动画片《三个和尚》[ J ].电影艺术,1982(01):21-29.
[17]何林军.美学十六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13.
[18]宗白华.艺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31.
【作者简介】 成 纬,女,江西南昌人,南昌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基金项目“江西地方戏曲脸谱造型审美与活化应用研究”(编号:20YS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江西地方戏曲脸谱造型审美与活化应用研究”(编号:YS202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