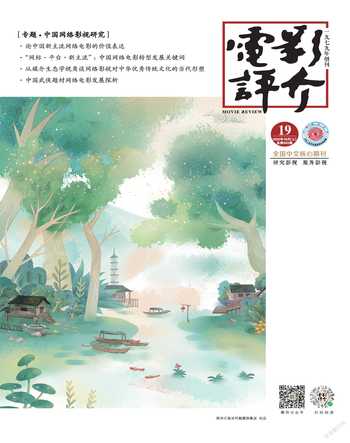城市中国:作为隐喻的地域表达
刘庆
一、象征空间:“深圳精神”的传奇式呈现
学者谭霈生在《论戏剧性》一书中提出:“剧作家在创造戏剧情境的时候,当然要重视事件的作用,并善于精心安排那种能够促使人物立即行动起来的有力的事件,从这里为剧本的戏剧性开路。”[1]电影创作者要想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展开叙事,就要为冲突的爆发和延续提供有力的前提和条件。特定的戏剧情境既可以为影片主人公的生活道路和命运走向提供社会背景,还可以激发人物之间潜在的矛盾关系,使影片呈现出“既见事,又见人”的叙事深度。与北京、上海等城市自带的传统根脉和岁月韧性相比,深圳的现代城市建设具有典型的、非传统的鲜明特质,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下催生的人口流动、信息更替、人际关系的交错与重组等现象,深圳为中国城市电影的书写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象征空间、隐喻空间和意象空间。
首先,深圳独特的发展历史和成长轨迹,使该地域具备鲜明的地缘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无论是从物理空间角度还是社会空间角度,斑驳复杂的多元性特征使深圳蕴含着丰富的戏剧性,地域空间自带被影像言说的优势,为城市电影的拍摄提供了与众不同的优越条件。
其次,作为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經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的浪潮卷走了边陲小镇的水田、山林和鱼塘。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深圳凭借着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和“鹏城”美誉,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发展最为迅速、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工商业并举的发展形态、新旧价值观念的交替与突围,在鲜明的拼图式空间里发生的多种多样的故事,让国产电影的“深圳”书写彰显出巨大的叙事张力。其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与都市群体隐匿的情感、欲望,整体的经济繁荣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孤独感和碎片化,城市空间与都市人时代记忆之间的内在关联等因素的结合与碰撞,为深圳故事的孕育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再则,对于观众来说,草根人物喜闻乐见的奋斗故事和进取情怀,与这座城市时代变革中的“拓荒牛精神”浑然一体。因此,人物传奇、民风民俗、逸闻趣事等生动的感性风貌,又为深圳的城市场所平添了丰富的故事性和电影感。“艺术作品常常通过转喻的方式来展现世界,电影就善于转喻式地通过人群来表现城市,城市市民便是电影最直接、最典型的转喻体,作为市民的生活空间,城市也相应地成为转喻空间。”[2]基于此,国产电影以移民、打工、下海经商为主题的深圳故事层出不穷,如《特区姑娘》(1985)、《特区打工妹》(1990)、《南中国1994》(1994)、《照相师》(2018)等电影,多把深圳表现为充满变革和希望的创业天堂,为敢为人先的“深圳精神”描摹出一幅幅精准的画像。
2022年春节档上映的影片《奇迹·笨小孩》,在故事背景上延续了深圳作为创业城市的文化想象,影片兼顾现实主义与传奇色彩,通过打工青年景浩的拼搏故事,将深圳城市空间本身所蕴含的精神气质充分地展示而出。众所周知,城市电影依托小人物叙事,审视城中人的自我突破与救赎,往往会比宏大叙事或者精英叙事更具现实意义,而以现实主义题材专长的导演文牧野,在影片中延续了其一以贯之的创作特色,即对底层困境的深切关照,以及为凡人英雄谱写赞歌,所以《奇迹·笨小孩》较为突出的艺术成就也是来自于对小人物的形象塑造。作为典型人物,深圳青年景浩在父亲失踪、母亲过世、妹妹患病的困境中,依靠着卓越的能力和超凡的韧性跨过重重难关,最终实现成功。从整体上看不难发现,以景浩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所表现出来的踏实肯干、敢打敢拼的精神特质,与深圳“闯”的精神、“创”的勇气、“干”的风格形成共振。创作者在影片中借用无所畏惧的创业锐气和柳暗花明的成功结局,向拼搏时代的每一位努力者致敬,以此点明了深圳四十年来的发展奇迹,是由无数个体的小奇迹汇聚而成的主题。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奇迹·笨小孩》在书写底层生存韧性的同时,还试图为景浩身上承载的“深圳精神”赋予浪漫主义色彩。文牧野曾在导演手记中提到:“我们无数次地扪心自问——‘奇迹是什么?在深圳这座‘奇迹之城背后,在这片神州热土之上,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共同组成了炽热流动的血液,促成了国家的昂扬向上。”[3]因此,创作者在影片中,一方面借助个体生命与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呈现出社会底层的困顿和挣扎;一方面为丛林法则下的人性坚持赋予温暖、浪漫的想象色彩。在手机市场竞争激烈的深圳市,由一群老弱病残组成的奇迹小分队,可以通过“笨小孩”的姿态跨越重重障碍,甚至连影片中唯一的女性形象汪春梅也是身残志坚,处处流露着大无畏的仗义精神。这样的情节设定,本身就赋予了这座南方都市以神话般的浪漫色彩。典型人物的细致刻画、叙事氛围的象征性营造,加上传奇式的浪漫色彩,体现出深圳不仅是一处简单的地域空间,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指引,承载着无限的机遇和希望,满足着奋斗群体对生命价值的渴求和想象。
二、隐喻空间:“特区使命”的现实书写
大众对一座城市风情物状的感知,一方面来源于城市街道、公共设施、地标建筑等外在形式的呈现,另一方面来源于城市自身洋溢而出的精神气质、文化底蕴和发展格局等内在特质。电影对城市文化景观和社会深层结构等需要调动感性经验才能感知到的人文情貌的塑造,往往会以符号隐喻的方式在影片中昭示而出。“透过城市风物的符号隐喻叙事,我们可以体察到人们是如何言之有‘物且‘行之有效地生活在城市之中的,进而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城市气息和人文情貌。”[4]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从“试验场”到“示范区”的目标转变,尤其是在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领域,深圳始终以强大的行业驱动力和生产力,带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为新时代的城市建设提供着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并在整体布局中担当着带动、辐射和示范的历史新使命。与该城市宣传片或者片段性的新闻影像不同的是,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能够基于现实的生活经验,在丰富的符号资源中再现、关照社会生活。同时,电影对城市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反向建构城市的地域文化和地域形象。因此,影视工作者往往会借助城市母体的风情物状,为故事言说铺陈叙事底色,在将地域文化形态进行视觉转译的同时,反向完成对城市精神的树立和强化。
区别于文牧野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行的创作理念,见证深圳成长历程的本土导演张唯,更擅长从别样的城市禀赋出发,塑造深圳改革模范和探路者的形象。在导演张唯执导的影片中,创作者往往会借用人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不断冲撞,为深圳的城市形象赋予全新的书写视角和叙事语境,打破大众对都市景观的片面观感,同时注重将城市各行各业的发展图景和生命体验,与“特区使命”这一公共议题进行连接。2014年上映的工业题材影片《打工老板》,通过朴素自然的纪实性手法,探究了中国制造行业的三十年浮沉。作品以一家民营企业的兴衰荣辱,透视着中国工业发展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的迫切与艰难,且大胆而深刻地揭露出在经济浪潮下,老板与员工、媒体与法律、外企客户与本土民营企业等主体之间矛盾的激化,同时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艰难转型提出了忧思。《打工老板》将故事的时间背景设定在2010年,在全球金融风暴余波未平之际,处于经济链条下游的达林玩具厂在恶性竞争的环境下,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最终工厂倒闭、工人四散。从事玩具生产的同行们在市场惨淡之际,纷纷向劳动力廉价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市场。怀着自主创造梦的达林玩具厂厂长林大林却坚守本土市场,与好友共同研发出原创玩偶品牌“喜禾”,但是在产品推广之际,玩具厂陷入危局,喜禾品牌未经上市便已夭折,最终只能孤寂地躺在仲裁庭上。
《打工老板》在主题上具备“接近生活渐近线”的现实性和鲜活感,丰富了大众对深圳这座城市的认知,更将“特区使命”这一公共议题带入了大众的讨论视野。与同类型的工业题材影片相比,这部电影难能可贵的是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口号,与一线工人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紧密相连,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让工人的合法权益获得保障?如何切实地帮助民营企业获得长久的健康发展,让工人群体与企业家共同铸造财富?这些看似尖锐实则现实的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民族制造业的自尊和雄心。电影上映后获誉无数,且成功入围第38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斩获最佳男演员奖,该影片至今在豆瓣平台上依然保持着8.1分的稳定成绩。①在电影中,创作者镜头下的深圳不再是充满机遇和活力的乌托邦之地,而是一处流淌着挫败和心酸的隐喻空间。导演张唯选择站在深圳发展参与者的视角,去感知城市真实的脉搏律动,同时注入了自己浓烈的社会意识。影片中的达林玩具厂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也隐喻着中国制造业的生存局面。这种充满反思意味的现实书写,可以引导观众站在理性的视角,审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代性问题。因此,深圳所承载的“拓荒牛精神”,不单指富有传奇色彩的励志故事,还有走在时代前沿、引领风气之先的价值理想和使命担当。
在2018年上映的影片《照相师》中,张唯通过“镜中之境”的形式穿越了四十年的时光长廊,将深圳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和代表性景观进行串联,并通过蔡家祖孙三代人的梦想坚守,为香港回归、股市风潮、蛇口自贸区挂牌等重大事件进行了影像留存。影片中照相行业四十年的发展变迁,也是深圳四十年春秋风劲的影像缩写,蔡家人深耕的摄影领域,有着祖辈坚守、父辈改革、子辈创新的因袭特质,这也与深圳从最初的世界工厂,到产业升级,再到创新之都的身份转变相互应和。由此可见,在张唯的作品中,深圳独特的城市禀赋和特区使命,是其区别于其他城市空间的独特所在,影片中的主人公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时代的变革之中,不管是个体勇立潮头的奋斗精神,还是企业千帆过尽的信念重燃,都为深圳城市母体的精神品格和使命担当增光添彩。
三、意象空间:外来他者的身份认同
根据法国精神分析理论家雅克·拉康对“镜像理论”的阐释,从婴儿时期开始,个体是通过形象而不是语言来感知世界,当个体借助镜像的他者建构完整的自我时,即是启动了所谓人的想象界。一般来说,婴儿在六到八个月之间,会通过镜子中“反映”回来的自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清晰的整体,在此刻作为个体与外界的关系开始转变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以镜像的实质就是“把本来想象的东西当做是真实的,把本来属于他者的属性当作是自己的,把本来属于外在的形式当做是内在的。”[5]但是当个体一旦进入人类特有的语言知识体系时,即表示进入了一个由他者设置的象征界,也标志着一种完整的、圆满的,与世界亲密结合的意识体验从此消失,个体也开始失去一种彻底的满足感,取而代之的是对想象界寻求无果后的无限失落,拉康将这种失落的对象称为“小写的他者客体”。
在书写深圳城市空间的影片中,城市的遍地机遇以及机遇带来的动力和希望,对于外来者而言即是一种“小写的他者客体”,此刻的他者主要指涉外在空间对内的虚幻映射,即现代都市的包容和魅力对外来者的吸引。因此,国产电影关于深圳外来者的书写,大都会提及繁华都市中的一处特殊的城市空间——城中村。城中村也被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在中国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极其普遍又特殊的存在。从生活条件上讲,城中村是城市地域形态的自然延伸,其工商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传统村落,同时在交通、环境和时代信息的接受上,也具有传统乡村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正是因为如此,城中村低廉的房屋租金、低消费水平和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其成为外来进城务工者的首选之地。
但是现实的落差却是这些由外来者或者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组成的社会实体,既与现代都市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又始终游离于城市管理之外。他们作为繁华都市中的他者,心里充满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推崇,身体却一直被隔绝在外。巨大的发展落差和多重身份群体的共存,也令整个城市显得斑驳复杂、混乱失衡。有学者曾经在相关的研究中指出,“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快乐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6]深圳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城中村的存在更加普遍,国产电影关于深圳城市空间的书写,只要涉及底层劳动者或者城市追梦者,都会借用“城中村”这一特殊的空间进行叙事,而身份迷失和认同危机,也永远是创作者着重书写的话题之一。
比如《奇迹·笨小孩》中深圳的喧嚣每天都是从城中村开始,奇迹小分队中的成员在这里都有各自的烟火人生。同样在《打工老板》里,工人的工作地点也是一处远离繁华都市的空旷工业区,在远景画面里,1000多名工人挤在职工宿舍楼中,逼仄的走廊里挂满了晾晒的衣物,锅碗瓢盆的碰撞和夫妻的争吵声此起彼伏,简易的行李和生活用品,时时提醒着他们“此地终归是异乡”。林大林曾在仲裁庭上陈述道“如果厂子都倒闭了,那么工人要到哪里去打工呢”,与这句话相对应的画面是玩具厂破产后,老一辈务工者扛着全部家当,拎着叮当作响的暖壶和饭盒,在泥泞的土路上渐行渐远、不知所踪;另一部由尚涛执导的剧情片《深圳在路上》,也将城中村的拆与建作为叙事原点。该片讲述了四个不同身份、不同来处的年轻人汇聚在深圳,从城中村出发开始了各自不同的道路,经过五年的打拼,有的人落地生根,有的人铩羽而归,影片最开始的相聚之地也面临着拆除。工人抡起锤子敲烂了每一面墙、每一块砖,在重型机械的作用下楼体轰然倒塌,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也像扬起的灰尘一样各自散落一方。创作者在刻画深圳这一特殊的空间时,会着重突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带给人的不安和恐惧,以及外来者被逐渐边缘化的生存状态,星罗棋布的城中村是深圳包容性的象征,那么来自五湖四海的“深漂”们如何融入城市的车水马龙,便是故事的起点。
结语
电影与城市的关系,建構着一种社会现实。电影对城市地缘文化的聚焦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国产影片在将深圳的城市魅像电影化的过程中,试图从城市母体因袭下来的城市精神、城市文化和城市禀赋等方面出发,构建出与现实生活相对照的影像世界。在这些影片中,创作者通过立体而又具体的城市生活空间、复杂多元的身份群体,塑造出深圳独特的城市气质和魂魄。现实生活与虚拟世界的互文,既能展现出城市生命主体的精神症候,也可以在时代进程中彰显出与众不同的深圳力量。
①参见:豆瓣评分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5899691/.
参考文献:
[1]谭霈生,谭霈生文集-论戏剧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146.
[2]孟君,现代性迷宫与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的空间叙事[ J ].当代文坛,2016(03):116-120.
[3]文牧野,每个平凡人的奋斗都在创造奇迹—电影《奇迹·笨小孩》导演手记[ J ].老年教育(长者家园),2022(03):51.
[4]马援,符号隐喻视角下的“城市风物”叙事[ J ].探索与争鸣,2021(05):169-180.
[5][英]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67.
[6]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2002(01):168-180.
【作者简介】 刘 庆,女,山西忻州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生,太原师范学院设计系讲师,主要从事戏剧与影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