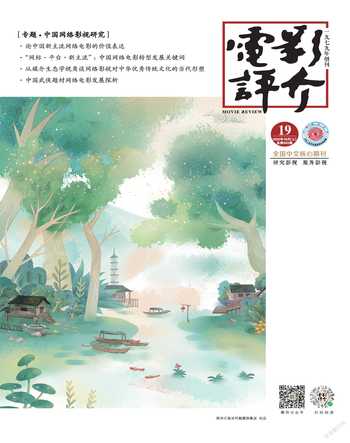纪录电影中的多元艺术性:模仿论、再现论及两者的关系
李涵
在关于电影的诸多理论探讨中,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展现现实的方式一直是电影艺术性讨论中的重点。尤其是在纪录电影的领域中,一部分学者力主纪录电影是对现实的模仿。即使不是完全对现实的复制或仿造,也是受到了现实条件限制的;另一部分则认为纪录电影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是一种与象征意义毫无关系的、再生产性的再次呈现。[1]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学者对纪录电影的表现性与再现性加以比较,将模仿性与再现性结合起来论证的意义,在于在多种意义上辨析那些让纪录电影产生的形式,例如某种事物的观念或真理等。对此,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疑问:被摄影机记录的事物如何构型自身?它是如何成型的又是如何被构型的?纪录电影的特殊能力何在?在“记录”的范畴中如何彰显艺术的多元性?本文将从模仿论与再现论的角度出发,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模仿行为的再生产体系与一体两面
与叙事电影相比,纪录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刨除了其主观叙事的意愿与目的,将所有内容压缩至了“模仿现实”的创作空间当中。模仿并非是要完全地在银幕上复制现实中的视觉与知觉,这一项努力永远不会成功——模仿现实的目的在于展现现实的理念。纪录电影展现了模仿的构思、构型与力量。所有模仿现实的形式——其拍摄、记录、构思的形式——在本质上,作为一种构型的力量是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纯粹的美。纪录片要用模仿的模式来展现这种纯粹之“美”,其实非常依赖于单纯的再生产体系。在纪录电影中,摄影机镜头的存在、或者说模仿现实这一意志的存在先于任何其他的主观决定或质性因素,当然也先于影片的存在本身。一旦人类以新的技术与理念将动物、植物或天然存在的视觉转化为人的视觉,其中就出现了“仿造”的问题。然而,模仿的东西并不是在感觉或感知上被预先给定的。“在我们准确知觉到它们的那一刻,我们就会调动起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破译其密码传达的信息。这正是艺术家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人的本性就是希望能对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出解释,能理解为什么他会看到自己看到的东西。”[2]就像生物视觉要在大脑的支配下选择其所见的主体,忽略不重要的部分一样;纪录片的模仿也要把握视知觉的基本原则,让被拍摄与感知的对象自然、生动、鲜明地呈现在画面中。在准确有效的视觉体系中,自然界的原初之美可以被模仿行为所捕捉并再次生产出来。
每次光学或数码技术进行变革、拥有了宛如自然视觉般的新技术能力之时,便也是纪录片创作者们积极以“电影眼”涉入未经探索的自然之时。以“自然纪录片巨头”英国广播公司2022年新推出的自然纪录片《绿色星球》(大卫·爱登堡,2022)为例,这部影片通过沉浸式的呈现方式聚焦植物王国中的“故事”。摄制团队前所未有地使用了7000多个机位拍摄了同一株植物的生长过程,其中大多数的摄影机都是自动地将其拍摄的植物锁定为画面主体,并自动地采用延时摄影方式进行长期“跟拍”,以模仿人类主观视觉的方式取得了植物的“第一手”影像。例如在讲述哥斯达黎加的雨林中,三种植物争夺一棵老树死去后有限的阳光与生长空间时,循序渐进地先介绍了龟背竹,它以巨大分叉的叶子来吸收阳光,在诸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接下来是一种藤蔓植物在暗中挥动卷须,卷住了龟背竹的叶面让自己尽力攀登,龟背竹也因此被“淘汰”;继而一棵年轻的轻木脱颖而出,藤蔓植物试图攀附轻木,然而轻木叶子的表面长满了尖刺般的绒毛,藤蔓根本无法攀附,最终轻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专业摄像机与4KHDR真彩加杜比音效的配合使画面的呈现拥有了类似人类的自然视觉,又在时间跨度上超越了人眼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近与深入震撼的植物世界。
BBC摄制团队在退休军事工程师克里斯·菲尔德研发的自动控制的延时设备——“三脚树(Tritree)”的基础上打造了能够承受严酷自然环境、模仿植物生长的设备。“每个伟大艺术家都会催生一个全新的宇宙,其中任何事物看上去都是全新的。这是全新的样相,而不是对旧的事物的背叛和歪曲。它们用一种扣人心弦的和新鲜的智慧方式,重新阐释了古老的真理。艺术家使用的和谐统一意象发出的简化并不是与复杂性不合拍,而且只有在掌握了大量的人类经验而不是逃向节约和贫穷中,这种简化才有价值。”[3]在《绿色星球》中的镜头运动是常速的,但是拍摄的内容却是延时摄影,这样的技术组合赋予了拍摄一种“模仿”的视野,摄影机镜头就好像在用植物的时间尺度看世界一样。
事实上,纪录电影中存在着两种模仿,或者说纪录电影中的模仿行为存在两种不同维度,它在外部与“再现”“表现”“象征”等行为相区别,在自身的内部则是一体两面的。在纪录片对客观世界的表现中,两种模式中的前者更像照相机拍摄的肖像照,而后者则更像美术家绘制的肖像画,两者的有机配合在纪录片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与现实模式的态度决定了模仿的特点:第一种模仿从属于既有的经验模式,它注定属于纯粹的、再生产式的仿造;第二种模仿则摆脱了经验性乃至与经验性相关的主体性。《绿色星球》给予我们的拍摄经验便是这样的。在一般电影乃至纪录片的认知中,植物世界总是静止沉默甚至无趣的,因为它们仅仅是利用光学原理进行拍摄,本身就是复制型的再生产。然而《绿色星球》却采用了最尖端的实时和延时摄影、移动控制与自动跟拍、超广角环拍、热成像摄影机、放大帧叠加、超高速摄影机和高端显微镜等高研发成本的拍摄技术来提升影像再生产的创意性。最终成片中的植物世界生机勃勃、植物之间合作与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人类社会,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观众对绿色植物的想象。这便是由于第二种模仿在自身的领域中制定了自身的法则,它提升了模仿行为本身的经验,且淡化了模式的规范性,它作为一种更加灵活的再造与刻板的复制有效地区别开来。在最为简单与和谐的影像中显示出和谐统一的美感。通过延时摄影、细节展现等新技术,使被忽略许久的植物世界前所未有地灵动了起来。
二、再现行为中的形式刻画与关系性构型
再现在艺术理论的许多重要内容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希腊艺术中,诗人被赋予了可以改编和润色神圣的起源神话的“特权”,这样允许对传统加以修改的方法也为视觉艺术的类似做法开辟了道路,人们从此克服了对概念性图像向心力的痴迷。“一旦想象性移情的努力变成自我理解的东西,艺术的进程便会通向人类经验的新大陆。”[4]在“表现”一词比平常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在视觉形式还是在书写形式中,它都构成了一种将自身置于与形式的约定之中的位置,一切自然事物、与生俱来的物质属性、超越人类主观情感的感情都被置于影像构型的约定之中。我们在视觉艺术中关注“形式”的概念,并经常将它与决定事物“本质”的某种基本支架或骨架的观念相联系起来,这反映了我们需要一个“图式”来掌握这个多变世界的无限多样化。对中世纪而言,图式就是图像;对中世纪以后的艺术家而言,图式就是进行矫正、调整、顺应的出发点,是探索现实、处理个体的手段。[5]如果将纪录电影对现实的“记录”理解为“再现”,那么无论采用何种矫正、调整、顺应的形式,其中被再现的对象究竟代表什么,以及如何超越自我的主觀意识、超越个体思维的封闭性与当下性展现或再现出这一对象,都是再现研究的重点。
在纪录片中,承载“美”之形式的对象一般不是人类为自己设定的孤立的存在物,因此纪录片的再现是一种在“自为”中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导演要通过人为的有意编排和引导来将自然事物自身的逻辑同人类可以理解的特质关联起来。在纪录片《王朝 第二季》(大卫·爱登堡,2022)的第一集中,刚产下四只幼崽的美洲狮“栖岩”带着四只孩子在巴塔戈尼亚的一片新领地上站创立了自己的“王朝”。导演利用画外音解说与画面的有机配合营造出悬疑感,力主让这一非“编剧编排”的作品在整体上显现出丰富的叙事性。例如,影片一开始以特写镜头展现了“栖岩”的雄性幼崽的面部特征,画外音介绍道,“这是一只雄性幼崽……”一般观众可能会以为接下来要介绍这只幼崽的其他特征,但镜头一切,远景中三只雌性幼崽正打闹在一起,画外音也随之话锋一转,介绍道:“……和三只雌性幼崽。”在漫长的冬季到来后,“栖岩”带着四只幼崽开始了艰难的求生。几组壮美的远景镜头剪辑完成了时间切换的叙事效果,伴随着最后一个远景镜头中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山川。画外音向观众介绍道:“冬季结束了,暖阳终于再次造福这片大地。带领四只幼崽撑过寒冬向来是极其艰难的……”此时画面上是中景镜头中“栖岩”带着其中一只幼崽在大地上漫步。声画对位的配合会误导观众以为其他三只幼崽已经在严冬中死去,但此时镜头又切换到远景,原来剩下的三只幼崽在“栖岩”身后不远的地方,只是在刚才的近景镜头中无法全部囊括到画框中。画外音接着介绍道:“……但是栖岩还是做到了。”这样风趣幽默又悬念十足的叙事方式在《王朝》中经常出现,并成为展现自然之惊奇与美的重要手段。《王朝》的叙事策略在于先用相对狭窄的视野给出一部分信息,再将视角拉远让观众发现镜头之外存在着大量的延伸性空间。结果对于观众来说,不仅有转折带来的趣味性,还可以非常轻松地感受到自然本身的无限性与摄影机镜头有限性之间的张力,启示观众自然王国充满着无限的惊喜与力量,还有待人类去探索与认知。
用摄影机复制物质基础很容易,但美的形式并不是可以通过单纯的复制就能够展现出来的。过于机械化的拍摄方式只会产生同一个事物的多个副本,产生两个在审美价值上极低、且在形式上等同的事物,这些副本和其原件之间依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要再现美的形式,就需要在再现的过程中辨明某一事物的银幕形象与事物本身属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其固定在既有思维模式上的关系,不如说是在创作、建构与构型意义上的形式性关系。纪录片本身的形式要求它具有复制现实的倾向,复制产生了形式的“马特西斯”——“这就是他、她、它,这种知识产生快乐;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因为其给予了我们一种关系,或者因为它让我们进入一种关系之中,它才是令人愉悦的。而这正是共同和占有的关系。”[6]从这一角度来说,BBC近些年所拍摄和出品的纪录片不仅仅是展现顶级的视觉特效,严谨的科学考证以及高级审美表现的场所,而是对自然的探索、对自然美形式的全新呈现。在结合了实拍与数字复原技术的《史前星球》(亚当·瓦德兹,安德鲁·R·琼斯,2022)中,导演力求在镜头运用和拍摄手法上极力地靠近真实的纪录片,不仅有很多震撼的长镜头,也有模拟摄影机延时拍摄的画面;导演为了还原恐龙夜晚的活动甚至还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中模拟了夜视镜头,如此注重写实的表现手法会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就把本片当成了一部实拍的纪录片。当然在丰富的镜头表现之外,强调人与恐龙之间“共处共生”的无距离感才是这部“拟像”纪录片成功的关键。其中一集表现了霸王龙求偶交配的过程,连担任画外音录制的“自然科学纪录片之父”大卫·爱登堡爵士都忍不住摘下耳机对镜头说道:“看着那些求爱过程中的霸王龙,就好像我在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它们一样。”这句话被剪辑到了成片当中。为了获得展现自然之美的恰当形式,BBC以无限接近心灵、思想、天赋、可感性的感性视角来占据这种专有的属性,最终向我们展现出这样一种将自然界的活力重新归还其身的原则或者说构型。
三、模仿与再现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模仿还是再现,无论是纯粹的美还是美的外在形式,作为类比艺术的纪录片都是一种展现业已存在的东西的技艺。纪录电影“记录”现实的方式也是它参与世界并再生产出“情动”的方式,真实的世界通过这种“情动”在影像中分辨出自己,显现、刻画并创造出自身。许多经常为人忽略而无法被人眼感知的事物通过摄影机被再现、被观看,这种关系式让事物在其外显的形象中显现出了最深刻和最隐秘的一面。摄影机镜头保存了事物本身的运动特征,与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保持一致。关于纪录片的终极问题可能是,影像中的世界如何形成自身,而纪录片又是如何被允许去记录并呈现它的运动的。
在现代,对运动方式、事物构成方式的再现关注意味着人们意识到了历史力量对事物图像呈现出巨大的影响作用。“曾经发生的事情对当下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它以其内在的持续运动影响着当代人对生活单元的理解方式。在历史力量的统御作用下,每个生活单元都以连续的整体方式出现,其本质表现在它们各自的表象中。”[7]如果说“模仿”强调的是摄影画面复制现实情景的方式,那么“再现”强调的就是摄影画面展示现实的“形式”或“图式”;如果说“模仿”要做的事是在单纯的生产体系中展现纯粹之美,那么“再现”就是要寻找一种最为恰当的、能够展现美的形式。如果有一种存在是明显且必然性地承载了“美”的话,那么应当选择何种手段(创作方式、拍摄方法、思想情感)来再现“美”的形式就是再现探求的目标。在关于诗人痖弦的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如歌的行板》(陈怀恩,2014)中,影片的叙事从老年诗人痖弦现下在温哥华的日常生活展开,在布满森林的自然环境中将诗人广结人缘的宽阔关怀、深沉浪漫的诗意生活、漫长波荡的人生况味娓娓道来。伴随着年逾九旬的痖弦先生的讲述,一代诗人与诗坛好友的回忆诗、副刊与文坛种种,摄影机镜头也随着诗人重返故乡河南,在诗人一生中的诸多住居与学校中回顾了他参军、演剧、求学、写诗、办刊的人生经历,追索诗人生命与诗意的根基。纪录电影作为传达社会观念最为重要的媒介,或者通过抽象或一般的认知将社会和国家重要事件中的重要观念传达给观众,或回到更加广袤的艺术领域、自然世界,或在日常性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中,深入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中寻找。只有在后者的领域中,摄影机镜头才能抓住“独特的、由内在力量驱动的东西”,抓住“具体且普遍和深刻的意义的东西”[8]。在《他们在岛屿写作》中,导演使用了大量的慢镜头展现出耄耋之年的诗人们,“表现”了他们缓慢的走动、念诵诗集等动作,并在“模仿”的意义生产体系中将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与壮阔波涌的文学生活展现为诗歌般的动人影像,生动而优美地铺展出痖弦的生命之诗,成就了超越“记录”的传记电影新风貌。
结语
模仿和再现都诞生于将经验归纳为方法论的欲望。人类的探索欲在现代各种技术及其相关理念的催动下空前勃发,观众也迫不及待地以纪录片为媒介参与到了世界诞生之前所展现出来的东西之中。在比“眼前所见”更为深刻的真实中,模仿欲望模仿出不可模仿的“创造”。
参考文献:
[1]聂欣如.类型电影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78.
[2][3][美]鲁道夫·艾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5.
[4][5][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M].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邵宏,译.南宗: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7,10.
[6]朱其.当代艺术理论前沿[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11.
[7][8][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吴麟绶,周新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1,129.
【作者簡介】 李 涵,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美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