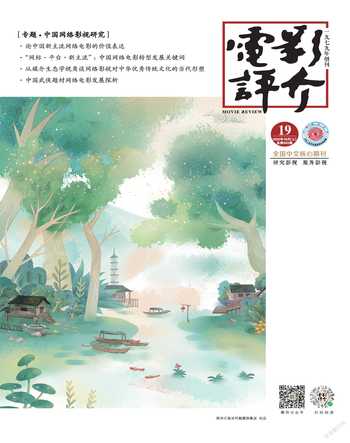迷思与归省:塔尔科夫斯基电影悲剧主题的探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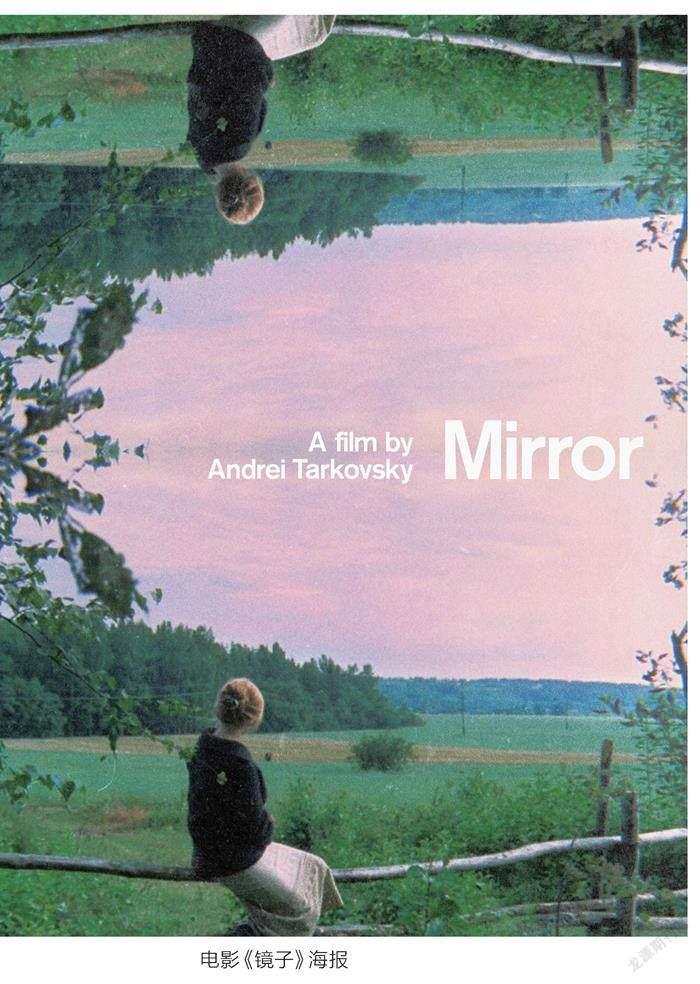
塔尔科夫斯基(Tarkovsky)是被称为继爱森斯坦(Eisenstein)之后,前苏联最杰出的导演。他自1960年起开始执导拍摄电影,一生共创作七部半影片,虽作品数量不多,但部部皆可称为精品,尤其是其处女作《压路机与小提琴》(1960)更是一鸣惊人,不仅给当时的苏联电影界带来极大的创作热情,而且在世界各国掀起了一阵“诗”电影风潮。可以说,塔尔科夫斯基的出现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革新运动注入了动力,拓展了电影“诗意美学”的表现技巧;同时作为典型个案,在文化反思及信仰归省等方面对后来的思想电影与诗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审美启示。
从塔尔科夫斯基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压路机与小提琴》(1960)到绝唱之作《牺牲》(1986),导演沉郁的悲剧意识贯穿始终。他曾在公开场合与观众分享他执导影片《压路机与小提琴》(1960)的创作理念,他认为影片虽然色调鲜艳明亮,但仍不能遮蔽影片的悲剧主题,当影片中的主人公小男孩没有如约赴会时,那么阻挡两人相见的阶级之门便得以建立,而这恰恰是悲剧的起源,更是信仰崩塌的迷惘之际。
在塔尔科夫斯基执导的七部半电影中,信仰的缺失与追寻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悲剧主题。从悲剧意蕴这一角度来看,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不仅阐释悲剧之因、悲剧之线、悲剧之果的悲剧三重奏,而且探索出信仰的最终归省,进而使世人得以形塑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正因如此,剖析塔尔科夫斯基电影悲剧主题的深度与广度,有助于世人在精神危机的时代保持对苦难的思索与生命追问的力量。
一、悲剧之因:阴郁的孤独者
在塔尔科夫斯基七部半的电影作品中,孤独是电影一直围绕的话题。这一话题不仅伴随着每一位角色人物,而且充斥在每一帧的时间雕刻上,让影片充满着强烈的悲剧性韵味。塔尔科夫斯基电影中的孤独者之所以会陷入无穷无尽的迷茫之境,根源是因为爱,并且这种爱已完全不局限于个人的小爱,而是关乎全人类的大爱。正因如此,塔尔科夫斯基电影中的每一位孤独者都被困囿在无尽的凄凉中,而这种凄楚境遇则是由内外部原因共同造成。
从内部层面来看,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悲剧之源是人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正是由于人类自我因素所形成的。在电影《压路机与小提琴》(1960)中,小男孩由于一个人孤单才会与压路机工人相遇相知。两人虽处于不同的社会阶级,但仍旧努力打破壁垒,使精神世界得以慰藉。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当小男孩与压路机工人相约去看电影《夏伯阳》(1934)时,却遭到母亲强烈的反对,两人不得不再次成为孤独者。如果说小男孩与压路机工人敢于跨越阶级鸿沟成为朋友是人物自身内部的原始冲动,那么小男孩母亲制止两人继续沟通则是社会内部的根源问题,即小男孩代表的资产阶级与压路机工人代表的工人阶级间无法打破的阶级隔阂。在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中,当卢布廖夫为挽救哑女而失手杀人后,他就陷入了自我赎罪的世界,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熟视无睹,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语者与孤独者。卢布廖夫的孤独者状态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他认为自己有罪,选择成为孤独者也是他惩罚自己的一种手段。可以说,在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中,由于内部因素成为孤独者的人物角色的孤独是与爱相伴相生的。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大爱,才会造成孤独者形象的诞生。例如,电影《压路机与小提琴》(1960)中,小男孩之所以与压路机工人成为朋友,是因为他经常遭受同龄人的欺辱,但出于对母亲的爱,他并不曾向母亲提及这种生活遭遇的不堪,而是选择与工人阶级的压路机工人成为朋友来摆脱自己的孤独境遇;小男孩的母亲恰恰也是出于爱的本意才会打破两人的友谊关系,以期让小男孩停留在社会期待下的资产阶级。由此可见,爱与孤独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中悄然滋生,不仅形塑出一个个孤独者形象,而且让孤独者形象的内部因素更加丰富充盈,使其得以立体化呈现。
从外部层面来看,塔尔科夫斯基电影中的孤独者有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孤独者形象,而是在外界的不断干扰下才逐渐沦为孤独者的。在电影《伊万的童年》(1962)中,12岁的伊万原本拥有幸福温暖的家庭生活,但残酷的战争让他在失去亲人的同时失去了童年。该电影由小说改编而成,在小说中,作家以旁观者的视点来刻画伊万的孤独形象;而在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中,导演则以伊万的主观视点来一步步呈现伊万之所以成为孤独者的悲惨历程。可以说,正是这种叙事视点的转换,才使得外部层面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入人物内心,让人物被迫接受命运的安排却没有任何反击的力量。对于孤独者伊万来说,残酷的战争让他沦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成为孤儿后的他内心深处就只有一个复仇的信念,于是在他的世界中,战争成为杀人游戏,而孤独也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在电影《乡愁》(1983)中,苏联历史学家戈尔恰科夫为了搜集资料来到异乡意大利,由于语言不通,他无法与意大利人进行沟通,于是他也成了典型的孤独者。对于戈尔恰科夫而言,他之所以成为孤独者,离不开外界环境因素。虽然他身边常伴女翻译尤金妮亚,但翻译仍旧无法解开他内心的迷惘与疑问。于是才会有他宁愿舍弃女翻译尤金妮亚,而坚持选择相信他人口中“疯子”的多米尼克。因为对于戈尔恰科夫来说,“疯子”多米尼克或许才是另一个自己——他们都囿于外界因素的影响,甘愿成为一个孤独者,以期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救世人的心灵。
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亦或外部原因,孤独者仍旧被爱所牵绊,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孤独困境,更脱离不开爱的包围。正是由于他们对親人或世人有着爱的冲动,才导致他们即使身处孤独深渊,仍旧存有反抗的勇气。或许抗争终究会被压制,但一种敢于摆脱孤独状态的精神,恰恰是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电影悲剧主题的魅力所在。无论是《压路机与小提琴》(1960)中勇于挑战社会阶级的“音乐家”小男孩,还是《伊万的童年》(1962)中被战争迫害致死的少年伊万,或是《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中只为活下去而主动铸钟的青年,他们虽然在所处的时代里是一位位孤独者,但是他们共同拥有对“爱”的执着追求,爱使他们成为孤独者,而孤独又使他们对爱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二、悲剧之线:冲突与抗争
对于悲剧而言,冲突是情节的导火索,抗争则是人物的行动线。正如马克思所言:“悲剧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1]而悲剧抗争则是明知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但仍要努力争取,从而在迷思中找到生命的真谛。在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中,孤独者拉开了电影悲剧性主题的序幕,而悲剧性的上演引线则是由冲突与抗争来点燃的。具体来说,在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中,孤独者除了要面对自我与自我的认知,还要接受自我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冲突关系,都注定离不开孤独者奋力的反抗。只有当悲剧性的冲突与抗争同时存在时,其电影中的悲剧之线才得以闭环,孤独者这一人物弧光由此更加生动。
塔尔科夫斯基电影中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孤独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电影一方面强调个人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有意突出自我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对于塔尔科夫斯基而言,他认为孤独者之所以无法得到内心的归省,是因为孤独者无法让自我与世界达到完美的融合,世界是孤独者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而正是由于孤独者的存在,世界才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换言之,在任何时代背景下,悲剧性冲突始终存在,孤独者要想在迷茫中寻觅到心灵的回归,就需要以自我的方式融入世界。只有当孤独者开始正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即自我属于世界的一瞬间时,那么孤独者才能以主观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并深知自己的薄弱与无知,进而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有更加深刻的把握与认知。例如,在电影《镜子》(1974)中,塔尔科夫斯基将自己解剖于众,将自己曾不愿提起的童年往事搬上银幕,选择正视并认识自己。影片开场是一位口吃少年诊治的画面,这位口吃少年正意指导演本人。在塔尔科夫斯基看来,彼时的自己正处于失语状态,宗教信仰也无法帮助他摆脱困境,他深知只有正视自己才能摆脱现状,于是他选择以“直播”的方式来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让自己在受众的凝视下完成自我救赎。影片中多次出现“我”照镜子的画面,每次照镜子都能让“我”看到自己真实生命的一面,还看到自己困苦的另一面人生。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Lacan)曾指出:“婴儿的镜像阶段是一次对自我认同的过程,婴儿只有顺利通过镜像阶段,那么他才能完成对自我的认同,即对自身的镜像产生认同。”[2]进一步说,人类之所以会对自我产生迷茫与困惑,其根源是无法认清自我,并一味将自我置于孤独境地。人类若能在困惑与冲突之下敢于正视自己,那么定能如影片《镜子》(1974)中的那位口吃少年一样说出一句:“我能够说话。”再如,在影片《乡愁》(1983)中,意大利人多米尼克被人讥称为“疯子”,他无法融入自己的国家,更无法融入世界。但是对于多米尼克本人来说,他有着世人不曾具有的顽强信念,他深知自己的内心,更誓死捍卫自己的使命。于是他才会在精神危机的时代下狠心将自己的妻儿囚禁在家7年之久,以使其躲避精神世界的摧残。由此可见,异类的多米尼克与世界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但这并不会使他放弃自我理想,反而激起他“圣愚”的意念,促使他在人群集聚的广场以自焚的形式来唤起坠落与迷茫的世人,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悲剧性的冲突是人物发起行动的牵引线,而矛盾冲突后的抗争才是悲剧的核心,即明知失败仍頑强抵抗的精神。塔尔科夫斯基虽然崇尚困苦磨难,但他深知苦难并不是目的,相反如何引导人类走出苦难,实现自我归省才是他提出的质问。纵观塔尔科夫斯基执导的七部半电影,他在电影中已经给人类指明了方向,即拯救与牺牲。当然,塔尔科夫斯基拯救与牺牲的抗争方式并不局限于个人自我的解脱,而是站在全世界角度的群体抗争,即使牺牲自我但仍要拯救道德日渐沦丧的人类。例如,在电影《安德烈·卢布廖夫》(1966)中,圣像画家卢布廖夫在亲眼目睹外敌侵入、同胞相杀、战火延绵、信仰崩塌、民生困苦等一系列灾难后,最终提笔作画,创作出旷世杰作《三位一体》。卢布廖夫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孤独者,还是一位苦行僧,他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甚至早已把自己献给了上帝。对他而言,在世间的唯一重任就是“拯救”,除了拯救困惑的精神,还要拯救残损的审美文化。具体来说,在悲剧的人生面前,卢布廖夫先是拯救自我,当同胞相残相杀时,卢布廖夫第一次质疑上帝,于是他开始寻找生存的意义,探寻人性之恶的源头,以期将其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卢布廖夫却发现人性之恶的源头正是人自身,也就说是,世人要想获得拯救,那么首先就要自我拯救,于是卢布廖夫开始自我漫长的拯救之旅。直到遇到铸钟少年,卢布廖夫才完成自我救赎,找到自己缺失已久的信仰。当自我得以拯救后,卢布廖夫便进入第二拯救阶段,即以美拯救世界。众所周知,美的载体是苦难,只有苦难才可以帮助人类更清楚地认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淬炼出美的含义。对于卢布廖夫而言,他除了是一位苦行僧,还是一位美的传递者,他的绘画作品《最后的审判》中不仅呈现出他对于苦难的理解,而且以这种顽强的反抗精神警示着一代又一代迷茫无助的世人。面对悲剧命运的反抗,除了有拯救的举动外,还应有甘于牺牲的精神,即牺牲自我而唤醒沉睡的世人的精神。例如,在电影《牺牲》(1986)中,当亚历山大得知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他听从邮递员奥托给予他的秘示,前去与“女巫”发生关系,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来拯救全世界的人类。换言之,在亚历山大看来,灾难之所以到来,完全是因为人类的无知与道德的沦丧,而拯救世人只有依靠上帝,于是亚历山大甘愿成为上帝的忠诚仆人,自愿放弃自己的全部,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只愿换回一个新的开始,即影片开头的一句话:“太初有道。”“道”原意为word一词,是一切的开端,于是道可以创造万物,是人类的光明更是人类的生命。因此,当亚历山大决定牺牲自我来拯救全人类的时候,道就成为一条将人类从物质危机中解救出来的路径,一条人类可以重拾希望与生命的新路。
塔尔科夫斯基认为:“世界上的苦难越多,我们就越有理由去创造美。”[3]这实质上是对抗争的赞美。对于世人来说,只有经历各种磨难后,才会对自我、他人、自然、社会及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使自我的生命得到真正拯救[4]。
三、悲剧之果:超越与归省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曾指出:“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即使是在命运的无望抗争中死去,也是一种超越的举动。”[5]可以说,超越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创造过程,其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前进的动力,而且加深了人类自我的内在认知。其实,人不单具备一定的自然属性,同时肩负一定的社会属性,于是当人类开始不满足于现存的自然生活时,那么就注定会去追逐更高的社会价值,做出相应的牺牲,以期寻觅生命的真理,完成自我内心的归省历程。虽然在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中出场的人物都是小人物,但他们却经历着棘手的生存问题,当战火已经开始蔓延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只有奋起反抗、积极应战,才能摆脱困境,进而回归平静的生活。换句话说,虽然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小人物与普通人没有区别,但当厄运来袭时,他们却可以依托自己的信仰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坚韧品质,因为对他们而言,拯救全人类的信仰理念足以使他们自愿放弃一切,努力将不可能转变为可能,从而实现悲剧的超越。可以说,在塔尔科夫斯基看来,人类只有经历无尽的苦难后,内心或许才能得到宁静与平和。当然,并不是说一个人经历苦难的数量越多其生命越有厚度,相反,只有當经历磨难而顽强抵抗不断接近目标时,其崇敬与超越才油然而生,而这恰恰是悲剧之果,即真理的超越与归省。正如尼采(Nietzsche)所言:“伟大的幸福是由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的崇高感。”[6]
悲剧的降临激发起人类抗争的欲望,形成悲剧的审美价值。在塔尔科夫斯基执导的七部半影片中,主人公在历经各种生死磨难并顽强抗争后,最终实现自我内心与家园的回归。例如,由苏联科幻小说家斯特鲁加茨基兄弟作品《路边野餐》改编的电影《潜行者》(1979),完全摒弃原小说带有的浓烈的科幻色彩,反而转向哲理层面的探讨。在影片《潜行者》(1979)中,塔尔科夫斯基第一次没有给电影人物赋予姓名,只是简单以潜行者、作家、科学家等职业名称来区别每一个人物。不难看出,塔尔科夫斯基并不想以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记录这些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反而是竭力地描写着当今社会人们迷茫困惑的生活窘境。电影中科学家与作家在杂乱无序的生活中渐渐迷失自己,为了寻找生命的真理,他们雇佣潜行者带领他们进入“禁区”,以期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真到走进“禁区”时,他们却无法直视自己的内心,于是猛然发现原来所谓的真理就是人类自身——如果世界空无一人,那么世间的一切仿佛也失去意义。影片中的潜行者就是一个最佳案例,他没有作家的文采,更没有科学家的学识,但正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却有着人类社会中最真挚的品质,即父爱。对于一个为人父的潜行者来说,他之所以不顾妻子的劝阻执意带领他人前去禁区,除了他自身的使命感之外,还有他一心想救治女儿的夙愿,正是这份纯真质朴的父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虽然,现阶段科学技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但科学技术的提升并不代表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和谐与安宁。相反,如果科学技术过快发展湮没了人类自身的话,那么人类注定将会迎来新的灾难。于是,对于潜行者而言,在他引导他人进入禁区找寻生命的意义时,他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洗涤,发现信仰的真理即是回归自我。
除了自我回归,悲剧的审美价值还应体现在家园的回归。家园是一个能为人遮风挡雨的场所,人们常说的“想家”,其实除了想念家中的人之外,还包含居住的场所。只有当人类开始正视自我时,才得以回归家园。在电影《飞向太空》(1972)中,凯文被任命到“索拉里斯”星球关闭太空站,但进入星球后,凯文却重逢了在地球上自杀的妻子哈丽。凯文深知这是自己内心深处压抑的罪恶感的外化,于是他多次试图将其摧毁,但仍无济于事。可以说,在索拉里斯星球,人类将不再受到一切道德的束缚与压制,他们被无尽的虚幻所包围,直至丧失人类的本性。于是凯文直面内心的愧疚感,开始尝试带领妻子哈丽重拾以往的美好记忆。但这对于由“中微子”组合而成的哈丽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一件事,于是哈丽在与凯文相处的过程中渐渐有了对自我的认知,她深知自己只不过是替代品,并且正是由于她的存在才导致凯文不愿接受现实,一直沉迷在过往中。于是,当哈丽拥有人类情感能力后,她选择以人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以说,哈丽人为化的举动唤醒了凯文对于自我与家园回归的渴望,让其敢于正视内心,坚定地选择回归家园,而这恰恰是塔尔科夫斯基电影悲剧主题的深层次意蕴。
生而为人,虽然会在险境中拼命求生,但结果仍旧会是向死而去。世间不存在长盛不衰,生存与毁灭更是相伴相随。对于塔尔科夫斯基而言,虽注定悲凉落幕,但仍旧追随真理,因为只有身处逆境但仍誓死反抗的灵魂才会得到真正的归省,进而获得生命的真理。
结语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体是何其脆弱与渺小。如果苦难降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并且他逆来顺受、接受苦难的话,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渺小的个体在经历各种不幸与无常后仍旧有反抗精神,才称得上自我的超越,而这就是悲剧主题的预设。塔尔科夫斯基以末世论来创作电影作品,他坚信人类将会在物质横欲的世界中迷失自我,于是他为世人建构起悲剧性的电影主题,并以自己的方式来为受众解答生命的意义,即正视自我——敢于抗争——超越真理——重获信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
[2]王平原.拉康“镜像阶段”理论探析[ J ].德州学院学报,2017(05):29-32.
[3]TRAJTELOVA J, STEINBOCK A J.Transcendence as Creativity:Vocation in Andrei Tarkovsky[M]// TRAJTELOVA J.The yearbook on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phenomenology2016.Vocations,social identities, spirituality: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2016:125-159.
[4]赵静.塔尔科夫斯基电影的悲剧意识探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1.
[5][德]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5-26.
[6]周国平.诗人哲学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28.
【作者简介】 赵 静,女,山东菏泽人,韩国清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电影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