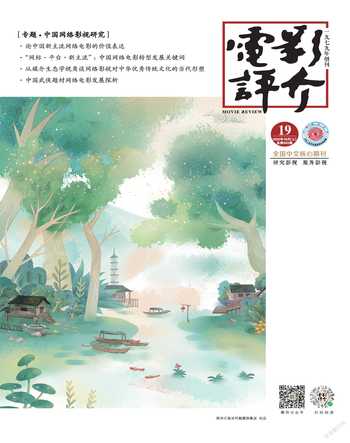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电影策略
陈娟
在影像时代,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广受追捧的畅销小说一度成为影视作品热衷改编的对象,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推理小说原是经典,改编成影视剧集之后,更是将热度持续推向高潮。1974年,瑞典演员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凭借由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西德尼·吕美特)一举夺得奥斯卡桂冠。由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改编的《无人生还》(克雷格·比贝洛斯,2015)、《尼罗河上的惨案》(约翰·古勒米,1978)更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本文通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影视化改编作品,从文学语言风格转换为视听语言、从推理小说叙事到电影叙事、从小说叙事时空到电影叙事时空的转变等三个方面探析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小说影视化的策略。
一、从文学语言到视听语言的转换
电影改编这门学问当前就遇到许多矛盾,如何处理原著与改编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首先,这里的“语言”并非口头形式上的“言语”,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人们口头语言的书写过程。在这里可以将文学语言理解为是由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用文字形成的书面表意系统。影视视听语言并不是单纯的影视的语言,而是由影视语言即对话、旁白、独白,用画面和声音共同进行叙事,用蒙太奇组接来展现情节的综合系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在影视化的过程中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与视听语言的表现形式有较大的差异。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想象与诗意的文字符号系统,电影是直观的声像符号,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相互翻译必然会碰上一系列问题。“语言”是文学和影视作品的媒介形式,文学语言与视听语言在功能、文艺创作、叙事属性、主题揭示上有较多的相似性,这为文学改编提供了可能性;但二者在欣赏地点、途径、传播方式、构成要素、修辞手法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也成为原小说和小说改编电影的差异之处。在此主要分析的是阿加莎推理小说改编电影中“语言”发生最突出的两个方面,即视听氛围的营造和推理案件细节的展示。
(一)立体化的视听氛围营造
关于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一直以来存在的最大的争议是改编到底需不需要忠于原著。库布里克(Kubrick)在提到关于改变需要遵循的原则时,明确指出了两大原则,即真实性和忠于原著。[1]在库布里克的影片中也可以看到他对真实生活场景再现的重视,对演员表演还原小说人物的重视。李玉铭先生在《改编是一门学问》一文中谈到好的改编作品应当基于原著,并对原推理小说进行合理加工[2],同时改编者应该充分发挥电影的优点和特点,尽可能调动电影的一切手段对小说进行再创作,使改编之后的电影成为上乘之作。所以,将小说改编为电影,要运用电影的媒介特性来推动情节、营造氛围,可以说,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完美营造了一个可视化、可感化的时空叙事,增强了推理小说中那些紧张刺激的氛围。比如,肯尼思·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导演于2017年上映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充分使用了电影视听特性。电影一开头,缓慢的音乐伴随着伊斯坦布尔城市大远景和中央广场远景,第1分20秒的一个长镜头开始跟随着一个提着鸡蛋篮子奔跑的叙利亚男孩快速移动,音乐节奏随着镜头运动的速率加快,变得紧张起来,当鸡蛋被送到一个八字撇胡子的“绅士”——主人公波洛面前后,快节奏的背景音乐开始随着近景和特写镜头的呈现放慢。整个片段充分发挥了视听艺术的特性,画面和音乐节奏契合,既满足了观众视听审美需求,又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完成叙事。
(二)具象化的隐喻镜头呈现
在由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的系列电影作品中,导演往往通过一些具象化的镜头来表现特定的含义,这些隐喻的镜头增加了电影文本的多重可解读性,给予了观众以充分的思考空间。比如,《无人生还》的士兵岛代表了圈禁的猎场,罪犯和受害者都无法逃脱。苏联版和2017年上映的《无人生还》则出现了海鸟的意象,海鸟的状态象征了人物当时的状态,或恐惧,或自由,或寂静。人类通过语言来有效认识世界,语言本身就具有符号功能,但认识世界并不是静态的描写过程,语言、形象和概念也并不是一一对应,简单来说,言语并不能完整表现所有概念范畴。一定的事物和思想形成一定的概念范畴,而一定的概念范畴则是由一定的语言符号体现的。[3]当要表现新的、人类过去从来没有认识到或发现的自然范畴,或者人们要通过熟悉的词语表达不熟悉的事物时,就引入了“隐喻化”(metaphorization)的概念来指代,即用常规的词语描述不常规的、隐藏于表象之下的真象和含义。而视听语言中,视觉形象及其所指形成了天然的隐喻关系。除了那些描述的直白镜头——观众不假思索就可以获得的信息,如特写镜头在展示人物的面貌、动作、着装时往往就直接指代了所表示之物。影视艺术的绝妙之处正在于此,镜头隐含着不常规的真象。在小说电影改编化的过程中,镜头语言的组成不单单是小说语言中的那些直白的“言语”,还是单个镜头,隐含着多种意味。在经典好莱坞时期西部类型片中存在三个基本图示,其中一些图像隐含了环境的特性,比如阴森的城堡、荒凉的沙漠。1945年雷内·克莱尔(René Clair)导演的《无人生还》,在开头通过黑白灰的色调,怪异的哥特式别墅营造了恐怖的氛围。当一行人登岛后,晚餐之后大家正在休息,突然从留声机里传来的人声打破宁静的场面,主人欧文指控了在场所有人的罪行,每個人神情紧张,这些都通过镜头直观展现了出来。而在2015年版的《无人生还》中,小岛总是占据画幅的二分之一,把小岛孤立无援的大环境交代了出来。
二、从推理小说叙事到电影叙事的裂变
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类型划分特征并不明显,但依然可以看到推理小说中具有的要素,比如案件的发生、罪犯、侦探、阻碍破案的众多事件,最后通过侦探或侦探与他人的合力完成案件的推理,识别嫌疑人。电影取材于小说自从电影诞生初期就开始了,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执导的《月球旅行记》(乔治·梅里爱,1902)是由凡尔纳(Verne)和威尔斯(Wells)的小说改编成的影片,大卫·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执导的《一个国家的诞生》(D·W·格里菲斯,1915)从小说中吸收灵感。最早的推理小说改编电影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步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这其中就包括了福尔摩斯系列中的《最后一案》《血字的研究》,好莱坞经典推理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则有《马耳他之鹰》(约翰·休斯顿,1941)《无人生还》等。近现代,日本以东野圭吾(Higashino Keigo)为首的一批人在亚洲掀起了一股“福尔摩斯”侦探热,东野圭吾侦探小说改编电影正如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系列改编影视剧。此外,青山刚昌(G?sh? Aoyama)动画剧集《名侦探柯南》(青山刚昌,1996)系列中柯南名字原型正是阿瑟·柯南·道尔,这一方面是作者在致敬福尔摩斯,另一方面显现了这一时期日本侦探题材漫画、动画剧集、电影、电视剧的盛行。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电影中,在叙述转换过程中变化最明显的便是情节的删减与故事内核的沿袭,不可避而谈之的应当是叙述内容。
(一)情节、情感的增减
从推理小说到悬疑电影的改编过程情节和情感有所变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已经被卡尔·谢恩克尔(Carl Schenkel)、肯尼思·布拉纳、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等翻拍过。1974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情节和情感比较符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原著小说,而肯尼思·布拉纳导演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开场前的一段则是根据电影特性对原推理小说情节的增加。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同样遵循着写作中的“龙头、猪肚、豹尾”,甚至比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更重视,而电影开头的10分钟是导演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关键。
对比分析阿加莎·克里斯蒂《东方快车谋杀案》小说文本和肯尼思·布拉纳电影文本可以看到,在写“龙头”时,原小说直接将事件发生的空间置于事件发生的地点,聚焦于冬天的列车,“叙利亚的寒冬;清晨五时。在阿勒颇车站的月台旁停着一列火车……那人的衣领一直围裹到耳朵……”[4];而这段情节出现在肯尼思·布拉纳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10分钟之后,第15分19秒主人公大侦探波洛出现在列车上,电影的前10分钟增添了波洛成功找出盗走教堂的无价之宝圣髑的情节。增添的短短10分钟用镜头语言塑造了一个声望颇高、威严、细致、近乎完美而又具有人情味的大侦探波洛形象,奠定了波洛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也饱含导演对波洛正面的情感色彩。在原推理小说中,由于其散点式的叙述方式,作者对波洛的情感往往隐藏于复杂的情节设计中,用语言篇幅表达对此人物的情感,以及人物之间的情感;而电影限于其篇幅,并不能完全展现每个角色的情感线,只能抓住影响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
(二)故事逻辑的沿袭
整体来看,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小说的改编在内容上基本没有偏离原著,反而有深化主题、加强叙事的倾向。对情节的删减和对故事内核的沿袭并不冲突,这两点是对推理小说改编电影的必然要求。前面提到,小说体量较大,电影呈现时长有限,若想在有限的时空里展现精妙的叙事,就必须紧扣故事内核和主题,这也是顺利沿袭原IP影响力的一个过程。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英国人骨子里的“绅士”,这种天然的约束使得罪犯和侦探、警察都有着合理的行动缘由,罪犯坦然接受侦探的推理并因此伏诛,而读者必须接受这一系列设定、不钻牛角尖才能完全进入跌宕起伏的推理过程。这些设定的成立使得推理小说、影视作品、漫画得以达成叙事的成功,可以说,推理小说的核心便是推理的过程,而不会过分在意有悖于现实生活的设定。
在观看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小说及其改编电影时,观众或读者必须接受以下故事逻辑设定,叙事的功能才能顺利实现:一是像波洛和玛普尔小姐这样的侦探往往是受人,比如警方或私人委托而接受案件的;二是警方并不会干涉侦探的办案,并且侦探及其助理代替了警方从事了案件侦破工作;三是即使侦探是按照逻辑的推理、细节的串联而形成的陈述,也会为罪犯及参与者所接受;四是阿加莎推理小说及其改编影视剧中存在着这样的巧合,侦探存在的现场即会发生案件,诸如此类的设定如福尔摩斯和柯南一样,侦探在哪里,哪里便会发生案件;五是存在着这样一个空间,使得罪犯、侦探和案件相关人员都被困于一个时空,也就是典型的“暴风雪山庄”模式。这些模式的设定不仅是阿加莎小说中经常善用的手法,而且在同类侦探题材中依然成立。
三、从小说空间到电影空间的差异
就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影视作品来说,其在叙事内核,特别是推理细节呈现上完美地忠实原作,保留甚至深化原作的韵味。而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由于传播介质、表现形式、傳播效应等不同,在小说影视化的过程中空间效果存在些许差异。首先必须得明确所谓的“空间”概念,恩格斯(Engels)肯定了空间之于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5]乔治·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也在其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直言:“小说的结构原则是时间,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6]可以说空间特性是电影的基本特性,空间对于电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人物处于空间并和空间产生紧密联系。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强调空间是一种读者积极参与的建构过程,他将叙事的空间看作一个整体,从纵向角度提出了叙事空间再现的三个层次:地志空间(the topographical level),时空体空间(the chronotropic level)和文本空间(the textual level)。[7]推理小说中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则充分体现了空间理论模型,以下基于这三个方面讨论阿加莎侦探小说在小说电影化改编的空间呈现的转变。小说的空间是通过读者阅读期待视野建构的,而电影中的地理空间、时空空间往往通过镜头呈现即可完成建构,空间呈现方式的转变正在于此。
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系列小说存在一个典型、封闭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即“孤岛”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说也存在于所有推理、悬疑小说中。电影《风声》(陈国富、高群书,2009)里所有人物的线索和推理都发生在孤岛上的城堡中,找出“老鬼”的鬼子和地下工作者相抗衡,这个模式就类比了侦探小说中罪犯和警察的人物关系。因此,“暴风雪山庄”模式成了判断推理小说电影化改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阿加莎·克里斯蒂创造的“暴风雪山庄模式”是在爱伦·坡(Allan Poe)开创的侦探小说之后发展出的一系列成熟的叙事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小说的叙事被局限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可能是《无人生还》的海岛,可能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火车车厢,也有可能是《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罗斯·大卫尼斯,1990)的庄园,甚至是一场聚会都可以作为案件展开的场所。此种模式下,人物背景线错综复杂,情节纷繁,不会让读者觉得单调。
首先对于地理空间的建构,小说空间和电影空间表现是有明显差异的。对于小说读者来说,小说空间是通过环境、背景描写加以头脑自主建构的产物,需要读者拥有一定的阅读期待视野及形象思维能力。而电影则依靠色彩、形状、视角、镜头运动直观呈现静态的实体地理空间;其次,时空体空间简单来说指的是一种叙述方式的呈现,是历时和共时的网交织而成,作品即使不完全按照线性的时间展开也可以。比如,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暴风雪山庄”模式充分展现这种叙事模式。受害人身中多刀,每条线索指向不同的嫌疑人,采用多线叙述的方式对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进行共时性展示,以复杂而精妙绝伦的情节推理吸引读者与观众。改编电影的时空叙述基本沿袭了原推理小说多线叙述的情节设置,并通过色调和光影将现实和推理、现实和闪回区分开来,就这一点来说,电影的时空体空间叙事比小说更有利于展示案件细节。“暴风雪山庄”模式中的叙事尽量依靠线索客观铺陈开来,避免将推理过程神秘化;最后,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文本空间,即文本所表现的空间是直接与读者的心理空间相通的,需要读者或者观众的主观想象参与才能建构成功。不同于地理空间直接描述的部分,文本空间指的是文本未详细陈述而靠观众自行填补的部分。电影主要依靠具象化的形象来隐喻,文学则主要靠间接语言表述。“暴风雪山庄”模式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叙事艺术,其在小说和电影的呈现中略显不同,这也是区别电影和小说的基本途径之一。
结语
本文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为个案研究,从叙事学视野切入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影视化改编进行探究,明确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电影改编既要保留原IP的魅力,又要充分发挥电影的特性,使得小说的内涵得以充分外延。本文主要从三个重要方面来阐述小说与电影的差异性,即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是文学语言到视听语言,从推理小说叙事到悬疑电影叙事的转换,以及处理小说与电影空间表现的差异性。优秀小说影视化改编是必然趋势。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影视化的改编过程中获得了新生,甚至比原作传播得更广。成功的小说改编电影是既能保留原著缜密的叙事逻辑,又能很好地平衡改编是否需要忠实原著这个基本的命题,但影视作品的完美呈现必定离不开原作的精彩叙事。
参考文献:
[1]唐莹.文学改编电影审美维度的转向——以《洛丽塔》为例[ J ].电影评介,2016(21):75-77.
[2]李玉铭.改编是一门学问[ J ].电影艺术,1983(08):10-13.
[3]胡壮麟.语言·认知·隐喻[ J ].现代外语,1997(04):50-57.
[4][英].阿加莎·克里斯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5.
[6][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高骏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
[7]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2.
【作者简介】 陈 娟,女,江苏邗江人,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英汉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