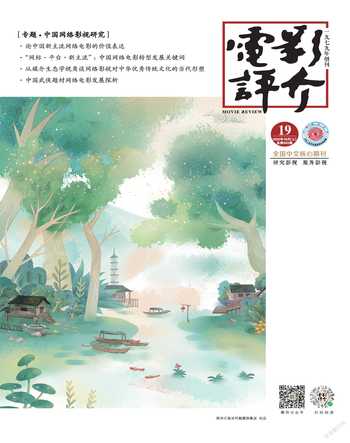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荣耀时刻》的现实主义嬗变与表述话语
常艳
在2021年中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中,一批来自中东欧国家的优秀影片陆续在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艺术院线与观众见面。其中,曾获得第69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金豹奖提名和堂吉诃德奖特别提名奖的保加利亚影片《荣耀时刻》(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佩塔尔·瓦查诺夫,2016)是一部艺术性高且兼具批判性的作品。这部电影以一只手表引发的故事展现出保加利亚不同阶层间生存状态的差异,引发了诸多关于时局、品格及道德的讨论。
一、当下全球现实主义影片的“代表”之作
《荣耀时刻》最早上映于2016年,在2021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电影领域的交流合作中,该片作为胶片盒里的“文化大使”被引入中国艺术院线,正式与中国观众见面。《荣耀时刻》承袭了东欧电影一贯的现实主义基调,以富裕普世性的人文关怀在中保两国的民众之间搭建起了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故事围绕一块前苏联生产的手表展开,讲述发生在保加利亚的铁路工人、交通部门公关与媒体之间,不同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中的观众依然能够对其中小人物的遭遇、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不同的生活境况等内容感同身受。性格木讷、独自居住的铁路工人特赞科是该片的主人公,某一天,他在检查铁轨时意外发现了一笔巨额现金,老实诚恳的特赞科将这笔“天降之财”交给了上级部门。恰逢交通部正陷落于舆论漩涡,拾金不昧的特赞科被热衷于宣传的公关部门打造为平民英雄,但女公关尤利娅却弄丢了特赞科父亲留下的“荣耀”牌手表,还一再搪塞敷衍他。特赞科在找回手表时经历了被媒体利用、被黑恶势力威胁、被迫发表道歉声明、被嫉妒他声名的同事欺负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片尾处,一直尝试人工受孕的尤利娅终于受孕成功,并偶然间找回了特赞科的表,在归还特赞科时发现他已被接踵而来的厄运折磨得面目全非;而特赞科面对尤利娅一言不发地握住了一把扳手,正片在此处戛然而止。《荣耀时刻》的剧本由两位导演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Kristina Grozeva)和佩塔尔·瓦查诺夫(Petar Valchanov)原创编写,却具有源自“真实”的力量,它在风格上让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编剧柴伐梯尼(Zavattini)与美国现实主义编剧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一系列作品,勤勤恳恳的小人物在自身无力阻止的事态中遭遇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陷入无法自拔的厄运,整体的社会处境并非完全是个人选择造成的所有事件的发生及结果。在缓慢的叙事节奏与自然的观察视角下,特赞科的生命呈现为一种被黑色幽默环绕的苦楚现实。与达到了现实主义美学顶峰的诸多经典之作相比,《荣耀时刻》无意在这一风格上作出新的突破,更多时候是以一种直白、尖锐的观察视角剖析现代社会中种种新的道德困境,从而成为一种“当下的”现实主义写照。
自路易·费雅德(LouisFeuillade)在1913年发布了一份公告,声称他创造了可以如实反映生活的电影以来,“现实主义电影”的概念已在百余年时间中经历了多次嬗变。而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产生要稍晚于路易·费雅德的公告,它最早源于有声片时代,借助有声记录电影的技术手段,在与好莱坞娱乐影片的对立面上出现,却最终形成了与表现主义电影理论相互对立、相互补充,也相辅相成的美学阵营。[1]在英国纪录片导演保罗·罗莎(Paulo Rocha)和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率先以非娱乐影片创作者自居,法国的马赛尔·莱尔比耶(Marcel LHerbier)和让·维果(Jean Vigo)以一系列自然而优美的诗意现实主义影片奠定了这一流派的美学基础;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以电影眼睛理论对抗普多夫金(Pudovkin)和爱森斯坦(Eisenstein)等形式主义者提出的理论;美国的理查德·利科克(Ricky Leacock)、唐·彭尼贝克(D.A.Pennebaker)、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和梅索斯兄弟等强调直接电影的视觉质感,认为电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本来面目与人类处境的有力工具。[2]从法国诗意现实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全球新现实主义浪潮来看,现实主义已然不再是电影创作和研究中的新鲜事物。任何一位在影片中关涉普通人现实生活、采用非戏剧性叙事,在技巧上采用自然光照明、手持摄影,在演员配置上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导演,都可以宣称他拍摄的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关键在于,在上述这些诸多极易辨识的元素之外,不断嬗变的“现实主义电影”在当下还保有哪些价值,哪些以“现实主义”自居或被称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影片存在哪些电影美学上的特质,以及探索世界未知意义的可能性。
近年来,以善良的小人物在媒体与公众的误判下陷入厄运为基本故事情节的“现实主义”影片逐渐成为各国电影创作的新选择。例如,《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2019)中,梦想成为执法者的保安理查德·朱维尔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中发现了炸弹装置,却在媒体和公众的诽谤下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号嫌疑犯;《狩猎》(托马斯·温特伯格,2012)中,托儿所工作的卢卡斯由于心地善良、个性温和饱受欢迎,却由于拒绝了早熟女孩卡拉的“示爱”遭到对方报复,蒙受侵害少女的污名而受到全镇人的排挤。这些善良、温和的普通人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推上风口浪尖,被失去自身判断能力、跟着媒体人云亦云的公众口诛笔伐,成为“平庸之恶”的受害者。在这些故事中,一切个人尝试或努力都是无力的;一切看似有效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过是人物命运向既定方向的加速。正如《荣耀时刻》中被政府部门无视的特赞科找到了媒体记者科列夫寻求帮助,科列夫却心怀叵测,他像尤利娅一样强势摆布特赞科录制了质疑交通部的电视节目,直接将特赞科推到了政府宣传的对立面上。
“现实主义由于能够认识与概括现实现象,并对现实进行社会分析而成为最完善的创作方法,借助于它,藝术能够表现本世纪的主要矛盾和冲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不但在旧的社会关系崩溃、新的社会关系形成的现代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且在与其他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比较时也显示了自己无比的优越性。”[3]在电影史的意义上,现实主义影片已经多次在不同的国家、风格、流派与美学运动中达到顶峰;但从艺术关照现实的意义而言,现实主义影片是唯一的,那就是关照影片拍摄时真正的社会环境与人物情态。在《荣耀时刻》中,导演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和佩塔尔·瓦查诺夫对于保加利亚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但该片表达的核心着眼点并非是激起民众对政府部门的愤恨,而是在细腻的情节刻画中,将一个老实人如何一步步被规则与舆论利用、裹挟的全程呈现出来。这样的故事可以超越国界与时间,令观众对这样悲剧性的平凡主人公产生共情,并由他面临的困窘境地产生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在这一意义上,《荣耀时刻》代表了现实主义电影在当前最明晰的表述方向。
二、生活素材与影像技巧中的现实呈现
电影史上诸多被冠以“现实主义”之名影片,便在真实展现社会生活的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以至于極易遭到国家机器的干扰与控制。二战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与作为“地下电影”兴起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美学运动便是如此。然而,这种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依然被限制在社会哲学与人类史的批评范围内,批评者寄希望于通过拍摄现实主义电影来揭露并改变现状,却未曾指出如何以电影的方式实现这些诉求。[4]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与询唤下,电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政治实践的工具;但在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中,电影必然先是一种反映现实的工具乃至现实本身,即使要借助它来表达具体的政治观点或主题倾向,电影也必须至少是一种媒介而非单纯的工具。优秀的现实主义影片总是在映射社会问题的同时使人们更加接近它们。以《荣耀时刻》为例,即使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特赞科面目丑陋、动作笨拙,电影中的许多场景脏乱无序,但电影的影像却是生动优美和和谐的。男主人公特赞科外形粗野却脆弱温柔,人畜无害却深陷舆论漩涡,辛勤工作却穷困潦倒。同为保加利亚导演、编剧与电影人的男演员德诺利博夫(Denolyubov)恰到好处地以凝重、孤独的表演表现出特赞科的烦恼。在急切的诉求与身体/社会的双重失语中,他在镜头中以认真的神情、过分有力的笨拙动作、大段的咕哝与结巴展现出一个非常具有层次感的小人物形象。
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的杰出大师克拉考尔(Kracauer)提出,电影是素材与技巧的综合产物;尤其是在真人实拍的传统胶片电影中,电影所展示的自始至终只有素材本身。“它也不去创造一个抽象或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而是驻反于真实的物理世界。传统艺术的目的是用特殊的方法转换世界的存在形态,而电影最深层和最本质的目的却是如实展示生活。别的艺术在创造中消解了素材,电影则如实地展示它的素材。”[5]摄影机在拍摄特赞科时,以实拍自现实世界的各种片段,在独特的处理方法中创造出一个“并非全新”的艺术世界。在《荣耀时刻》中,画面中的诸多细节都是如此真实:男人公身上松松垮垮的白色背心,他的手臂由于长期室外劳作有着明显的晒痕分界,他站在街边吃廉价汉堡时粘在嘴唇和胡子上的酱料,独自居住、狭窄凌乱的小屋,宽敞明亮、井然有序交通部办公大楼中人物的面无表情……这些细节展示了物理现实中适用于摄影机表现出来的某些方面,他们恰如其分地以现实中的状态出现在摄影机的捕捉与大银幕的放映中。“在一幅画面前,我们的认识超越了对象,而电影则使我们回到对象本身。”[6]导演以“电影眼睛”观察并记录着真实的各个方面,并引导观众在生活中重新对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加以重新体认和感知。
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整个现实都是已经被拍摄或亟待拍摄的电影素材。问题在于,如何利用电影这一揭示客观世界的科学工具,结合相关拍摄技巧将现实的特定层面挖掘出来,对于这些映射在电影中的现实又应该加以怎样的认识。创作者要将现实素材电影化,最重要的便是在影像方面用艺术化的摄影方式,使之发生形态上的改变或时空上的变形。《荣耀时刻》导演将摄影机拍摄的对象视为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而非以人类意识为转移的精神存在。对此,导演在传统的手持摄影、长镜头、景深镜头外还使用了非连贯性的剪辑手法,以镜头间的匹配不流畅唤起了人们的注意。在特赞科外,女主人公尤利娅的塑造同样非常出彩,导演在多处采用非连续性的拍摄和剪辑手法,将一个完全对立于男主人公的精明傲慢的公关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尤利娅逃避特赞科的诘问,引起丈夫的不满时,摄影机罕见地运用了越轴动作拍摄尤利娅与丈夫面对面的争吵,空间的跃动引起观众视知觉的一次震颤,观众由此感受到二人之间逐渐扩大的裂痕。在剪辑上,导演多次采用与匹配剪辑相反的跳切手法,以同一景别、同一人物两个镜头间的突兀剪辑标示着时空的变换。尤利娅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却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权术与良知的天平。在对尤利娅的刻画中,跳切造成了强烈的断裂感,时空的突兀切换可能暗示主人公的不安定状态。特赞科发表对部门不利的讲话时,她在卵泡随时可能破裂的情况下离开了手术室,头上还戴着无菌帽。此时镜头始终跟随在尤利娅的身后,以跳切的方式展现了她从出手术室到乘上计程车到交通部的全过程。等到她再次回到医院,医生通知她这种情况,卵泡可能已经完全破裂,而手术必须取消。尽管拥有财富与阶层上的优越感,尤利娅也与特赞科一样生活在迷失方向、无所归依的世界里,职业女性、利己主义者与不孕母亲的身份困境也在她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三、故事结构和叙述顺序中的主题表达
在故事结构方面,改变不同时间影像的呈现顺序以显示自身的想法,也是《荣耀时刻》切入现实的重要方法。尽管《荣耀时刻》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不是根据导演自身叙事节奏的需要,通过画面外化自身视角对现实素材加以组织,而创造出的“被编写”出的故事;而是模仿自然的形式,以记录或已有的摄影方式传达出画面本身的意义。特赞科身为一个铁路上的小职员(本身还具有生理上的缺陷),这样的一个人向整个体制展开追索与挑战,使得《荣耀时刻》的故事本身就富有深度。在围绕着特赞科展开的一系列叙述中,时间是唯一的永恒流动和变化的特质,但它不是预先设定好的框架,不可能永远为叙事结构提供抽象的或动态的支撑。在特赞科与记者在餐馆交谈的场景中,特赞科背对窗口与记者相对而坐,特赞科的面部处于阴影中,导演甚至以侧面而非正面展现他的面部表情,而对面的记者脸部则半明半暗。特赞科的面部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阴影中或背面和侧面的状态,摄影机如同尾随的班观察者一般跟随在他的背后。《荣耀时刻》中的时间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验存在或弥散在影像中的无形“框架”,它包裹一切人物、情节和影像,那些影响主人公命运的偶然事件会引起时间的变动,但永恒的时间流逝并不随外部的必然性发生改变。
在经典的叙事方式或剧作法看来,时间应该被统一于情节的安排。而情节的一波三折、起承转合构成完整的故事,在人物与环境被决定前,一个由起源到发展到高潮,再到结局的剧作结构,就已经存在于影片中了。相反,在叙事遵循现实主义的《荣耀时刻》中,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一先验性的结构,一切画面都由跟随在主人公背后的摄影机决定的。因此,画面中展现出来的事件是第一性的连续的情节,反而只是一连串事件形成的结果,事件与事件之间遵循着现实的联系:尤利娅在欧盟旗帜后偷偷换裙子,下属则在办公室把裤子脱给特赞科;尤利娅刚得知胚胎成活的喜讯,下一秒就在报纸上看到工人卧轨的噩耗;记者在强迫特赞科发表道歉声明的时候对他的遭遇没有丝毫关心,反而关注背景里出现了两个垃圾桶,不如把镜头移到一棵木槿树旁边,却因为担心特赞科穿着背心在镜头前会不好看突然把衬衣脱给了他……这样的纪实性表达既包含了人物外在的环境,更体现了人物内心的冲突。这部影片既是由导演与编剧“人为”创作出来的作品,又是影片中地域和文化本身的自然表现,它深刻批判且关注人性,充满导演的主观讽刺但属于现实本身。影片中的所有情节都没有人为创造的痕迹,而是来自现实,但恰恰是现实本身故事发生的顺序让我们感到了难以言喻的荒诞。这样的叙事方式表现了客观环境中的人性,既让我们客观了解了保加利亚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又能通过集中于小人物特赞科的遭遇让我们由衷地心生怜悯与同情。
结语
摄像机的基本记录功能是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改造现实的动力与直接记录现实的愿望发生碰撞的影片才更加有趣。《荣耀时刻》中,主观创作的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存在以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为背景发生了新的拉扯,最终产生了借助电影媒介的特征但超越媒介自身的现实主义影像。
参考文献:
[1][德]埃尔塞瑟,齐林斯基,唐宏峰等.在媒介与艺术的历史中探险——埃尔塞瑟、齐林斯基同中国学者的对话[ J ].
文艺研究,2020(05):91-99.
[2][德]托·艾尔萨埃瑟,陈梅.新电影史[ J ].世界电影,1988(02):4-15.
[3][法]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M].吴岳添,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17.
[4][德]托马斯·埃尔塞瑟,李洋,黄兆杰.媒介考源学视野下的电影——托马斯·埃尔塞瑟访谈[ J ].电影艺术,2018(03):111-117.
[5][6][美]达德利·安德鲁.经典电影理论导论[M].李伟峰,译,北京:后浪出版公司,2013:90-91.
【作者简介】 常 艳,女,湖北荆州人,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第二批教育部产学研项目“TED演讲在科技英语翻转学习中的运用研究”(编号:2018021400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