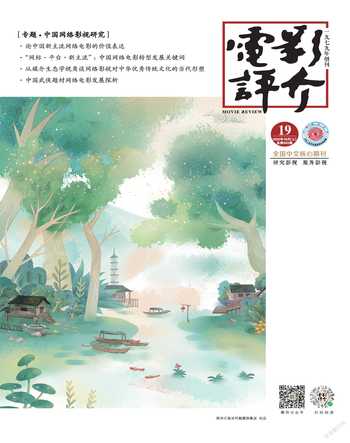当下的历史化视角:历史电影评论中的认知途径
崔颖
历史电影是一种立足当下书写历史的文本,历史电影评论则是围绕着历史与当下的文化表征再次进行书写的文本。历史电影评论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再次证明了当下话语与历史书写之间的紧密关系。[1]这一表述性的关系不仅是历史的或由当下回顾式的,而且是结构性的或在此刻书写生成的。包括电影评论在内,许多围绕历史电影产生的文本都确认了历史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被书写的现代背景。历史电影评论作为一种“当下书写的再书写”,表明了所谓“历史”从一开始就寄生于话语的结构,与一种书写、表达和认知的当下文化紧密相关,其中潜藏着重要的认知途径。
一、早期古装片与传统历史片批评中的发展历史观
现代以来的文化史观对现代话语或进步话语的过多关注掩盖了当代历史书写的许多根本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结构与社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历史性与文化书写的场域受到了质疑,这些问题由此渗透到不同的文化立场中。在对于历史电影的审视中,一种潜藏在集体意识中的进步思想成为支配评论话语的重要力量。19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一种乐观主义、强调历史向前进步的历史观在西方思想中成为主流,人类对理性的信任彻底改变了形而上学时期以来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于是便出现了强调预设目的、向前发展的历史观。中国历史电影的发展伴随着近代文明开化的思想潮流与中国社会的前进,最早一批拍摄历史电影的导演便是基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进行创作的。“现实的人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从现实的人出发,就是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现实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2]无论何种题材的电影创作,首先必须从现实的人与事物出发,基于明确或不明确的文化意识进行对历史的写作与创作。尤其是在中国历史电影的发展潮流中,这种目的性更加明显。20世纪以来,“进步”或“发展”的意识形态成为历史电影中重要的表述对象,关于进步或发展的话语也是其评论文本的重要形式。无论是古装片还是历史片,中国电影创作者都怀着“经世致用”的中国文人传统,从具体的对象、关系性世界出发,始终注视并关怀着现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3]
首先是一种并不关联中国近代历史,以泛化的封建时代历史为故事背景,但创作的潜意识中具有启蒙意识与目的性的古装片。20世纪20年代,天一公司首开先例,最早投入古装片拍摄,拍摄了《女侠李飞飞》(邵醉翁,1925)、《梁祝痛史》(邵醉翁,1926)、《义妖白蛇传》(邵醉翁,1926)、《仕林祭塔》(邵醉翁、李萍倩,1927)等改编自传统文学的电影作品,一时间古装片浪潮兴起;明星影片公司又在古装片的基础上拍摄了诸多神怪武侠片,如《火烧红莲寺》(张石川,1928)、《红侠》(文逸民,1929)等,并因为适应观众的欣赏口味而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由于过于切近商业功利意图,并未得到当时舆论的肯定。尽管在一般的主流电影评价体系中,研究者注意到了古装片尤其是武侠片的类型化特征,如多种明确的冲突主题、角色摄制吻合观众的想象、注重明星效应等,其中影片《大侠甘凤池》(林苍,1939)、《儿女英雄传》(岳枫,1938)等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曲折隐晦的方式评价生活的意味,但由于质量得不到保证,佳作较少。[4]学者钟大丰与舒晓鸣著的《中国电影史》一书中明确提出,应该看到早期电影的创作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早期电影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进行了最初的探索,“而且这些探索也是在与影系主流电影基本一致的戏剧化电影观念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他们也同样逃脱不了商业规律的制约,只能在适应观众欣赏要求的前提下,进行一点小小的尝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电影界浊流翻滚的时候,形势也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创作初衷,而被卷入投机浪潮之中”[5]。这本书的初衷在于“在将来的创作中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民族电影传统中有益的经验,推动中国电影的不断发展”[6]。
上文提到的评价与评论无论是对这批影片的批判,还是立足当时社会环境的审视,都站在了发展历史观的角度。不只是古装影片,早期中国电影作为寄托知识分子拯救中国国家和民族希望的一种大众媒介,其内容毫无疑问肩负着激发民众社会责任感的表达。
其次是有着明确“历史”书写范围与目的的历史影片。伴随着社会危机逐渐深重,中国民族电影的整体方向受到局势动荡的影响,之前以市场为主导的古装商业片在思想上轉型。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古装片的历史戏说向严肃的历史主题转型基本完成。尤其在建国后,当时的导演秉承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拍摄的一批传统历史片,在历史类型的意义上开始具备明确的年代背景。如讲述林则徐虎门销烟、对抗外侮的《林则徐》(郑君里、岑范,1959),讲述邓世昌率领“致远”号官兵与日军展开殊死大战的《甲午风云》(林农,1962)等。围绕这批最早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影片”,学者郑雪来在《现代电影观念探讨》《对现代电影美学思潮的几点看法》等文章中具体分析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电影群众、电影与其他艺术相互关系,以及电影各组成元素的关系等的发展变化后指出“时代向电影艺术提出了新任务,扩展并更新了它的形象风格,概括原则,艺术手法和手段系统”[7],并提出现代电影观念已经包含传统电影观念中的理念内核,主张电影观念既有美学含义,又有诗学含义,赞成诗学含义上的“电影观念的多样化”[8]。在20世纪80年代对历史电影的讨论中,一种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观已经从早期的意识形态向艺术形态转移,这不仅体现在电影内容的思想价值方面,而且电影的美学价值受到关注与重视。“人就是不安分,他只能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却又要为自己构建一个理想世界,要在自己所构建的理想世界的导下生活。人的活动就是要把自然世界改造为适合于人的目的的理想世界,就是不断地制造这个世界的分裂又实现着这个世界的统一。”[9]郑雪来等评论者在对所有电影史事件加以整理的基础上,以一种整体性、连贯性的眼光,凭借感性与想象力将现实材料组合为一个联贯的整体。从历史进步的关照视角审视历史题材电影,我们可以在摆脱对其意识形态工具的刻板影响之后,重新审视历史电影是怎样将个体的分散故事与历史的宏大叙事相联系,表述中华民族是如何逐渐实现民族复兴,完成一部“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的——这正是历史电影与其衍生文本重要的研究意义之所在。
二、改革开放以来全球电影批评中的多元价值观
在长久以来的历史影像书写传统中,一种部分延续着进步史观思路的宏大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电影重要的表现对象,尤其带有主旋律色彩、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的影片,都是中国历史电影类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历史电影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创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作品;历史电影评论也更加重视电影艺术的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历史影片中“历史主体”的描绘过程,从而确认历史电影的文化地位和审美价值。“主旋律电影在尽力完成其政治使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内容的重组与形式的重建,并且在努力寻找一条和主流政治合拍、和大众文化合流、和市场经济接轨的新的创作道路。”[10]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电影”对历史的刻画与日趋多元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时,历史电影评论更加成为独立于电影的存在,并关注了影像书写的不同层面。
多元价值观在历史电影评论中意味着当代文化打破了过去单一的宏大叙事,允许出现一种生动多元的历史主义。多元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空间内部的差异性。这些以时间和空间为支柱的历史差异本身就是语言与书写的产物,通过社会、文化、文明和种族的边界定义多元性和多样性。电影对历史加以具体化,以便让历史与政治上的失序变得可以管理。[11]换言之,人们应在大众文化的范围内对多样性进行管理,否则无法分析解释语言从多元化向着一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并拒绝这些实体存在的内部差异的原因。以中英意三国合拍的《末代皇帝》(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87)为例,这部在北京故宫实地拍摄并得到中国政府全力支持,由法国导演执导、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演员联袂出演主要角色、日本配乐大师担任配乐,围绕清末王朝崩解历史展开,并荣获“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影片,本身具有价值观上的多重性。多元性的历史书写在向一元化的历史书写发起挑战的同时,也承认了历史的书写可以具有不同的话语路径。
一些学者将东西方的社会与思想差异点入背景,如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1988年看过《末代皇帝》后对其大为赞赏,认为这部影片是难得的中国历史题材佳作,尤其体现在“复杂故事一氣呵成”“镜头转接得如流水行云”,以及人物塑造生动合理的方面;他以“千钧之力”“返璞归真”评价该片在艺术上的境界,并基于该片在美国、日本与中国台湾“爆棚之盛”的基础上,能得到中国大陆观众的认同,为大陆进行的改革提供经验。[12]《末代皇帝》与丰富的中国历史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是历史书写的产物。它跨越了文明与种族的边界,将多元性解构于特定的文化实体,不仅滋生了历史书写最保守的文化主张,而且转而对其施加合法化。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则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将《末代皇帝》视为未被西方文化氛围影响的东方电影。[13]
此外,多元历史书写引发的话语言说作为一种新范式的认知方法,在理解当代世界的权力格局与话语重构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电影学者对《末代皇帝》这部影片的评论中,张旭东认为其以“末代皇帝”的个人命运折射出“历史的命运”,更确切地说,一种历史冲突:“这种冲突既表现为中国历史自身内部的冲突,也表现为东西方历史观念以至两种活生生的历史之间的遭遇”[14];廖世奇同样将这部影片当作“一个意识形态的隐喻”[15]。这样的评论是对较早以宏大历史为中心的多元现代化话语的改进,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全球差异思维。多元化意味着随着世界文化格局的多极化,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正在走入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电影与文化市场生态中。尽管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不同的立场,但全球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总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多元化价值观区别于进步历史话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抛弃了发展中心的目的论,从而在历史话语的展开过程中得以容纳不同的历史轨迹。[16]日益多元化的话语表达伴随的正是中国历史电影在经历了长期的探索以后,更具包容性和创新理念的多元发展阶段。当下,中国历史电影与围绕中国历史电影的话语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对话与竞争。
三、当下的历史化:历史电影批评与日常价值的反抗
对历史电影或历史观进行的评价有很多种,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从中进行选择,究竟是什么让当下的舆论领域具有共通性,以及怎样面对关于历史、电影、历史电影及话语本身的种种表达,哪种知识是与我们所作的选择相称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决定用什么方式来解释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的……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17]脱离单一的宏大历史很简单,它对世界的描绘或者历史书写都不充分。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此类批评大多数都以再次确认关于世界的极端单一的宏大历史观念告终,而没有完成电影评价或电影批评应该完成的使命。当下电影批评的日常性十分突出,“豆瓣”式的短评论已成为大众惊醒批评的主要途径,而批评背景与消费性的电影市场、网络化的舆论环境关系空前紧密。
在消费主义的立场上,电影的观众和评论者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强调当前关于历史书写的讨论是发生在当代消费市场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一方面,电影资源与电影教育的普及使电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娱乐社会中的思想简单化倾向使人们尽量避免接触意识形态的批评。网络化的环境加剧了前述忧患。在影评可以轻松被制作为全新产品的当下,影视区Up主①选择的历史题材电影与其他题材相比可谓少之又少。以B站的影视杂谈区“近期投稿”视频作品为例,播放量最大的分别是武侠片《一个人的武林》(陈德森、2014)、体育励志片《王者之旅》(斯蒂文·泽里安,1993)与悬疑科幻片《老师不是人》(罗伯特·罗德里格兹,1998),其他热度靠前的视频也多与历史题材无关。[18]在批评成为一种日常话语建构时,人们依然需要关注多元文化主义如何组织知识,才能跨越不同文化的阶级、性别与种族中的对立问题;也需更加注意社会经济结构,它不仅制造了话语中的对立,而且对这些对立加以神秘化。“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并且鉴于未来已经丧失了可靠性,需要更加注意,我们的知识由于太执着于克服不平等的历史遗产,事实上可能反而滋生并加剧新的不平等和压迫。”[19]批评与对批评的关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日常生活中坚持批评的眼光与立场仍是我们立足当下与历史积极生存的方式。
结语
在日趋多元的话语领域,一些共通性、具有抵抗性质的真正批评主张,比起过去的任何讨论都更为融洽和有力。在历史的维度上,真正的电影不会被一时的价值观局限所掩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语境的不断变化,历史电影的艺术地位和审美价值也必将得到重视和重新确认。
①指在哔哩哔哩发布内容的自媒体。
参考文献:
[1][3][11][16]储双月.中国历史电影艺术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13,145,78,79.
[2][9]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51,129.
[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影片大典:故事片·戏曲片(1977—1994)[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315.
[5][6]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71.
[7]郑雪来.现代电影观念探讨[ J ].电影艺术,1983(10):4-14,27.
[8]郑雪来.对现代电影美学思潮的几点看法[ J ].文艺研究,1981(04):53-63.
[10]黄建国.中外电影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1:207.
[12]张五常.新浪博客-评《末代皇帝》[EB/OL].(2017-01-02)[2022-04-2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078t.html.
[13][意]貝纳尔多·贝托鲁奇,关键.关于《末代皇帝》[ J ].世界电影,1988(06):205-213.
[14]张旭东.电影叙事中的历史冲突:谈《末代皇帝》[ J ].当代电影,1988(05):38-40.
[15]廖世奇.《末代皇帝》:一个意识形态的隐喻[ J ].当代电影,1988(05):41-43.
[17][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3.
[18]Bilibili.影视杂谈[EB/OL].(2017-01-02)[2022-04-29]https://www.bilibili.com/v/cinephile/cinecism?tag=1161117.
[19][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4.
【作者简介】 崔 颖,女,黑龙江人,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电影文学,翻译文学,文化传播,媒介传播研究。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项目“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白鹿原》韩译文本研究”(编号:20JK028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