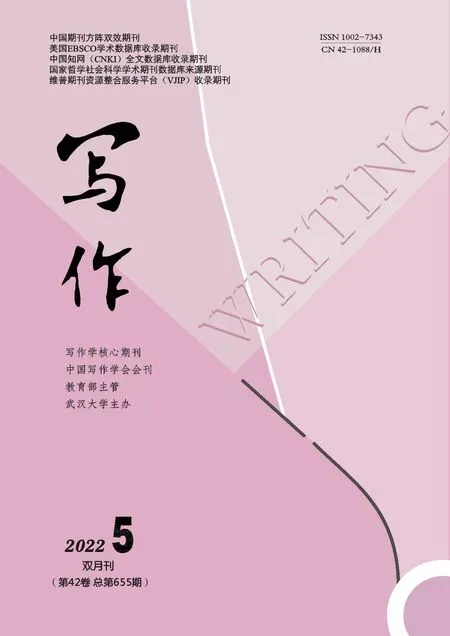废名小说的接受与回响
——以沈从文对废名的“误读”为中心
罗帅
关于废名和沈从文在创作上的关系,学界已关注多年,且大都聚焦于两人事实上的影响、艺术品位的投合以及小说作品题材和风格的接近。1935年,李健吾就曾比较两人的小说特色:废名更“内向”,接近“修士”,追求的不是“美丽”本身,而是一种境界;沈从文则“热情地崇拜美”,展现一种“美化的生活”。他敏锐地把握了两种创作的同中之异①刘西渭(李健吾):《〈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期。。经过1949—1976年废名和沈从文研究的沉寂阶段,进入新时期后,不少学者继续探究两人的文学联系。先是凌宇将废名营造山水意境和个人细微意识的文体命名为“诗体小说”,并将沈从文和萧红等人的写作也纳入其中②凌宇:《从〈桃园〉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十月》1981年第1期。。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杨义、杨联芬等,他们改用“抒情小说”或“抒情倾向”来概括废名、沈从文一脉的小说③杨义:《废名小说的田园风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抒情倾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充实了这一谱系的内涵。吴晓东借用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提出的“诗化小说”概念,梳理了包括周作人等理论家,以及废名、沈从文到汪曾祺等诸多小说家在内的文脉,认为这些作家都“追求诗意的语言、意境的营造与散淡的叙事”④吴晓东:《现代“诗化小说”探索》,《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吴晓东拓展了“抒情化”的理论边界,这也开创了此后探讨废、沈小说风格、文体以及两人创作联系的常见思路。严家炎、杨联芬等人也致力于废名和沈从文的细部比较,在将他们都归入“京派”“归隐派”的前提下,探索其创作实践的异同①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已有研究的重点几乎都放在了废名与沈从文的联系之上,而对他们彼此的质疑或者“误读”着墨较少。事实上,在沈从文对废名保持持续关注、接受和反思的多年间,不仅自己的创作在逐步成熟,废名的文学观念和实践也日渐转变,评价不可能一成不变;沈从文的文学之路始于1923年的北京,1933年后又返平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与废名不乏事实上的交往,这也会影响到他的“废名观”;作为私淑废名的小说家和批评家,沈从文对废名小说的阅读感受和艺术分析,恰是废名小说接受情况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废名小说独特价值的同时,也对当时的若干文学思潮形成了回应。
一、沈从文的“废名评论史”
沈从文对废名的评论起于1926年,终于1940年代,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26年的起始阶段,1929—1931年的发展阶段,以及1940年代的完成阶段。它呼应了废名创作的演变过程,也与自我创作和阅读体验的变化形成互动。
1926年初,初涉新文学创作的沈从文广泛涉猎了当时北京的主要新文学刊物及作家作品,综合考虑报刊连载、社团流派等因素,写下了《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逐一予以评论,其中就包括了废名及其小说集《竹林的故事》:
冯文炳的小说,最近才出了一个创作集,《竹林故事》,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东西的,不过因为穷的关系,我所见到他的几篇文章,还是《语丝》同《现代评论》登载的,不知其他怎样。他的创作写得极其细致,但并不累赘,把自己儿时所得的印象,用女人似的笔致写来,至少是我为他那篇《竹林故事》,(集中之一)已深深的感动了。在他集子上他自序他创作正是一种“悲哀的玩具”。他所见的人生,似乎就只是他创作中那类人生,使他感着亲切。这只是人生的一片,但他能把这一片人生送给我们,(虽然他说是自己的悲哀玩具。)已觉得很不少了。
我的希望,是现在的文艺园圃中,能多产生一些这类美丽文字,才能给人一点安慰。②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续)》,《文社月刊》1926年第1卷第6期。
截至该文写作的1926年1月止,废名在《语丝》及《现代评论》发表过《鹧鸪》(1925年2月14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10期)、《竹林的故事》(1925年2月16日《语丝》第14期)、《初恋》(1925年4月4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17期)、《火神庙的和尚》(1925年3月16日《语丝》第18期)、《去乡——S的遗稿》(1925年8月3日《语丝》第38期)、《花炮》(1925年10月26日《语丝》第50期)、《妓馆(花炮之四)》(1925年11月16日《语丝》第53期)等。废名“悲哀的玩具”一语,其实并不出自《竹林的故事·序》,而出自《语丝》刊登的该书广告:
这是冯文炳先生的短篇小说集,现已出版。冯先生说:“这是我的悲哀的玩具,而他又给了我不可名状的欢喜。”现在想将这欢喜分给他的读者。定价五角。③《广告·竹林的故事》,《语丝》1925年第54期。
沈从文从“悲哀玩具”谈到“一片人生”的格局、儿时的回忆,以及美丽细致的文字风格,观点与周作人都十分接近:
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按: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①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语丝》1925年第48期。岂明(周作人):《〈桃园〉跋》,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沈从文也指出了周作人的这一观点,参见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2页。
该序发表于沈从文时常阅读的《语丝》,沈从文很可能读到过并受到启发,对《竹林的故事》的喜爱,也让沈、周二人产生了共鸣。就上述小说篇目来看,两人的评论基本道出了废名早期小说的特征:以乡土记忆为题材,话题不离婚恋娶嫁、迎神赛会等家长里短和黄梅地方风致,着重叙述“我”对早夭阿妹的缕缕思念,对银姐的朦胧情愫,对三姑娘的淡淡怀恋,笔触柔软,情感细腻,弥漫着一丝淡淡的愁绪。多年后,李健吾再次谈到这部集子,仍然流连于“他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和他文笔的精练”②刘西渭(李健吾):《读〈画梦录〉》,《文季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这是废名的标志性特征,也让沈从文为之痴迷。
1930年1月,沈从文于吴淞中国公学讲授“新文艺试作”和“现代文学研究”③私立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版,第94页。。当年7月,又前往武汉大学教授同类课程④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十九年度》,1931年1月版,第8页。,从历史角度检视新文学的整体,甚至感到“头痛不过”⑤沈从文:《致王际真19300129》,《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以此为契机,沈从文撰写了若干评论,对新文学历史与现状的理性认知有了突破,其文学观念和自我定位也逐渐清晰⑥沈从文1929—1930年撰写的新文学批评篇目,屠毅力:《文学者的“政治”——对30年代京派形成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3-104页。,对废名的欣赏与质疑,也都随之走向成熟。1934年4月,沈从文出版新文学论集《沫沫集》,据已有材料看,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曾于1930年前后发表,只有《论冯文炳》《鲁迅的战斗》未曾见刊。《论冯文炳》应作于1930年7月⑦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对起始阶段的废名评价有所继承,更有所突破。
沈从文首先总结了《竹林的故事》题材方面的优点,欣赏其“农村寂静的美”和“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并将其原型追溯到作者生活的黄冈“小乡村”⑧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3-4、2页。,大体延续了《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中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沈从文致力于寻找废名乡土小说的精神脉络,将眼光对准了周作人的影响:
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无可多言。对周先生的嗜好,有所影响,成为冯文炳君的作品成立的原素,近于武断的估计或不至于十分错误的⑨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3-4、2页。。
这一判断符合周废二人的看法。废名曾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视为其小说的灵感来源之一⑩冯文炳:《序》,《竹林的故事》,北京:新潮社1925年版,第1页。,周作人也明确表示,自己“叛徒与隐逸合一”的人生态度也深得废名之心○1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语丝》1925年第48期。岂明(周作人):《〈桃园〉跋》,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沈从文也指出了周作人的这一观点,参见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2页。。沈从文的独到之处,在于试图从两人的传承关系中,梳理出一条“从周作人到废名”的文学史脉络:
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
……因为文体的美丽,最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仍然不会容易使世人忘却,而成为历史的一种原型,那是无疑的。①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8、4-7、9-10页。
沈从文将周作人的散文文体及风格影响力置于“五四”新文学发展的背景下考察,以“清淡朴讷”“原始的单纯”和“素描的美”提炼周、废共同的语言风格,从两人对乡村生活、地方风土和生活细节及自然事物的兴趣上找寻精神联系,不仅反映了沈从文敏锐的文学感受,也如同他这一时期所写的《论中国创作小说》《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等新文学批评,展露出鲜明的新文学史意识②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续)》,《文艺月刊》193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文艺月刊》1930年第1卷第5号。。
面对《竹林的故事》,沈从文不吝赞美之词,观点也基本保持前后一致,同时还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深受其影响。除去《论冯文炳》中的自白外③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8、4-7、9-10页。,一年前,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夫妇》发表于《小说月报》,结尾有一则附言:
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种,写乡下,则仿佛有与废名先生相似处。由自己说来,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但风致稍稍不同,因为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是只有废名先生才能那种经济的。这一篇即又有这痕迹,读我的文章略多而又欢喜废名先生文章的人,他必能找出其相似中稍稍不同处的。这样文章在我是有两个月不曾写过了,添此一尾记自己这时的欣喜。时七月十四日,天热,住楼上一天只是流汗。甲辰记。④沈从文:《夫妇》,《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11号。
巧合的是,在《夫妇》出刊的同日,沈从文得知中国公学可能聘请废名来替自己上三年级国文预科,显得很高兴,向胡适写信,表示“于同学及从文本人皆为幸事”⑤沈从文:《致胡适19291110》,《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对废名的钦佩溢于言表。这则附言点出废名“抒情诗”笔法的同时,似乎特别强调与废名的“稍稍不同”,且隐隐透露出一丝“欣喜”。既承认得到废名小说滋养,又有意突出自我创作的超越性,是沈从文这一时期废名批评的显著特征,这在《论冯文炳》中也有明显体现。文中谈到,废名的小说过于“宁静”,缺少“静中的动”,笔下的乡土世界不够全面,语言存在“八股式的反复”,将作品导向“病的纤细的美”⑥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8、4-7、9-10页。。相比之下,自己的《雨后》《龙朱》《我的教育》《夫妇》等作品,能以“矜慎的笔”反映“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和“一切由生产关系下产生的苦乐”,突出了乡村生活及人物的天然野性美,因而“较冯文炳为宽而且优”⑦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8、4-7、9-10页。,在审美格调和表现范围等层面皆有突破,显示了其小说写作和个人意识的成熟,并自居为“周作人—废名”乡土小说流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之后,废名走向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写作,努力营造自己所痴迷的那个梦幻“心象世界”⑧吴晓东:《意念与心象——废名小说〈桥〉的诗学研读》,《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沈从文则着力打造充满野性气息的湘西世界,彰显了各自的写作个性。至于《论冯文炳》中对废名等人“趣味化”倾向的反思,后文将详细论述,在此不赘。
1939年,沈从文因躲避抗日战火而身处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①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1940年,将“各体文习作”课程的讲义整理完善后,以“习作举例”为总题,分三部分发表,分题为《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由冰心到废名》。前两篇分别论述了徐志摩情感的“热烈”和周氏兄弟散文的“冷静”,是抒情散文的两种风格;冰心、朱自清、废名的文章则可称为“境界散文”,重点在于描绘“当前”,而非徜徉于“过去”和“回忆”,境界“沉默而羞涩”,“或透明如水”。废名“记言记行,用俭朴文字,如白描法绘画人生,一点一角的人生。笔下明丽而不纤细,温暖而不粗俗,风格独具”,保持“田园风”的“自然生趣”,同时还能做到“文情相生,略近于‘道’”,但因为笔调隐逸气太重,尽管笔下的农村确实存在,终究与读者产生了隔阂②沈从文:《习作举例三由冰心到废名》,《国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这样,对废名的喜爱与质疑都得到了保留,而所谓“隐逸气”和“文情相生”的判断,也是有意呼应了周作人的看法③岂明(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鞭策周刊》1932年第1卷第3期。。然而,连天的炮火将废名隔绝在了老家黄梅乡下,这时的他并无任何小说新作,与外界也几乎没有联系,得到的关注也骤然减少,沈从文的评论因而略显孤独。
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废名小说的接受,有一条较为明晰的发展脉络,对《竹林的故事》等早期作品,不惜溢美之词,青睐其笔触细腻、情感深挚、乡土风物、朴素文风,而对《桃园》《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则颇有微词,不满其语言的芜杂、结构的散漫和趣味的奇僻。沈从文坚持中有突破,理解中有反思,欣赏中有审视。考虑到《论冯文炳》《论中国创作小说》以及《由冰心到废名》等篇目大都是新文学习作的讲义,其观点自然会因课程性质需求而偏于印象式,但其良好的文学感觉和自觉的文学史意识,依然为废名评论增添了厚度,同时也揭示出文学史上一些关键问题,因此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论冯文炳》与沈从文的“反趣味化”批评
如上文所述,沈从文1930年7月写下了其废名评论的代表作《论冯文炳》,主要讨论周作人影响下的废名乡土小说。他认为就题材、语言等方面,废名胜过张资平等“天才”的恋爱小说,并承认自己深受影响。更需要注意的,是沈从文对废名的“扬弃”。在指出废名小说太过平静,缺乏静中之动等不足后,沈从文更对其语言的“八股的反复”和“不节制”提出批评。对于废名小说自成一体的文体和语言,其他批评者也有所留意。1929年,署名“拙亭”者发表《桃园》书评,揄扬了其“简练别致生动,且多带滑稽的意味”的小说语言④拙亭:《对于废名〈桃园〉之批评》,《开明》1929年第1卷第10号。;1932年,灌婴发表《桥》一文,从小说结构、人物形象、文化氛围和语言美学等角度评价《桥》,以其“简练”为“得”,“晦涩”为失⑤灌婴:《桥》,《新月》1932年第4卷第5期。。当《现代》杂志的书评肯定废名语言的曲折回环⑥《桥》,《现代》1932年第1卷第4期。,李健吾一针见血地将《桥》的语言形态总结为“抽象的绝句”,表现为“句与句间的空白”,尽管耐人寻味,但也“失却艺术所需的更高的谐和”⑦刘西渭(李健吾):《读〈画梦录〉》,《文季月刊》1936年第1卷第4期。,委婉地提出了批评。这与沈从文的观点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处。沈从文将其成因归结为“趣味的恶化”,这种“趣味”也和周作人的影响脱不开干系:
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等散文揉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觉得是可惜的。①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6页。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1934年第13期。
对文学“趣味”的玩味和孜孜追求,正是周作人和废名的精神契合点之一。周作人认为,“满足自己的趣味”,就足为经营“艺术与生活”的理由②岂明(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序》,《语丝》1926年第93期。,所写的正是“趣味之文”③起明(周作人):《〈泽泻集〉序》,《语丝》1927年第145期。;废名在同时期的创作论《说梦》中,也借他人观点自白道:“文艺作品总要写得intersting。这话我也首先承认。”④废名:《说梦》,《语丝》1927年第133期。到了30年代,更是津津乐道于“厌世派”文章作法之趣⑤鹤西、废名:《邮筒》,《骆驼草》1930年第3期。。周作人最欣赏废名的,也就是其从“中外文学里”所涵养出的“趣味”⑥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语丝》1925年第48期。,其小说的优点也正在其文章的“古典趣味”⑦岂明(周作人):《桃园跋》,废名:《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版。。针对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趣味化”圈子,也早有批评之声,观点与沈从文相仿。1927年,成仿吾把周作人及周边作家群描述为“以趣味为中心”的圈子⑧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1927年第3卷第25期。,李初梨响应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概括为“趣味文学”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号。;而关系较近的朱自清,也声称自己不能理解其“以趣味为主”的明代名士式追求⑩佩弦(朱自清):《燕知草序》,《语丝》1928年第4卷第36期。。周作人等及时回应,在《〈燕知草〉跋》中指出,俞平伯与明人最接近之处是“反抗”的姿态,补充了朱自清的观点。而在《〈桃园〉跋》中揄扬了废名的“古典趣味”后,周作人特意加上一句“(又是趣味)”,未必没有对这一时期蜂拥而至的“趣味化”批评的不满。废名则更直白地挑明,为“时人所病的‘趣味’二字”,正是周作人最“近乎事理”处○1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6页。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1934年第13期。。从师生的一唱一和,明显看出其对“趣味化”的默认和自喜。
沈从文口中的“趣味化”和“趣味主义”,不只用于指称周作人及弟子们的创作态度,这是他与其他批评者不同所在。在沈从文眼中,大部分新文学作品都可纳入“趣味化”的序列: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开创了对乡愁和乡村风物趣味化书写的先河,此后与周作人等人经营的“语丝体”,则形成了诙谐讽刺的趣味;郭沫若的小说语言夸张,结构松散,培养了粗率、夸大的兴味;而张资平依靠三角恋小说,迎合青年官能化的低俗口味;后起的冯文炳、许钦文、王鲁彦、蒋光慈等不同流派的作家,则在不同层面受到影响。这一经由两代作家传递后形成的新文学整体趋势,被他命名为“趣味化”:
从各方面加以仔细的检察,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实大可惊人,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把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这是文学革命稍后一点普遍的现象……过去一时代文学作品,大多数看来,皆不缺少病的纤细,前面说到的理由,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12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1931年第2卷第5、6期合刊。
沈从文在什么意义上,扩大了“趣味化”的范围,构成了与其他批评者的差别呢?这得从造成这一风气的“理由”说起。他指出,1927年前后国民革命影响下,原本集中于北京的部分新文学者赴沪,从而形成了“北京—学院”及“上海—市场”两大新文学聚居地,其连带而来的学院化、商业化和政治化,正是新文学“趣味化”风气的根源①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月刊》1931年第2卷第4号。。也正是不必靠写作谋生的学院生活,使周、废等的眼光局限于个人趣味:
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故为周作人所称道的《无题》中所记琴子故事,风度的美,较之时间略早的一些创作,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康健的病的纤细的美。②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0、8页。
这席话道出了废、沈二人的关键差异:废名身处学院内,接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大多数时间都在阅读庾信、李商隐、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波德莱尔等古今中外文学经典,他对乡村的回味和书写,大都也带着清雅脱俗的书卷气和学院风;沈从文的创作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他逃学、爬山、涉水的丰富少年生活。他的最高“学历”只有小学,15岁便当兵,辗转于湘、贵、川等地,身体和精神中都积蓄了朴野、雄强、自然之力,而这些也是他眼中真正的美③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大公报·文艺副刊》1934年第126期。。因此,当废名的小说中的隐逸气一点点上升,文体走入“奇僻生辣”④岂明(周作人):《枣和桥的序》,废名:《桥》,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4页。一路后,其整体美学风格自然就不为沈从文所肯定,两人的差异也浮上纸面。
沈从文此前并未如此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与废名的差别。1926年发表的《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中,对废名的热爱就溢于言表。《论冯文炳》则发展了这一观点,还详细阐述了自己所受到的影响,为自己的试笔阶段的工作找到了精神依据。他早期的《画家师兄》《腊八粥》《代狗》等,大都描写恬淡温馨的乡村风光和人物关系,夹杂着些微乡愁,模仿废名的痕迹确实很重。1928年后,沈从文更侧重湘西传说、爱恋故事的书写,《论冯文炳》中提到的湘西人野性、自然的一面,与废名同期的《枣》和《桥》等诗化篇章的确风格有异,其创作个性日渐成熟,隐隐有自成一派的趋势。当时拿他俩进行比较,分析两人异同的声音不在少数。毛一波起先看重废、沈二人“用那一种简练和紧凑的文字来写小说”的相似之处⑤毛一波:《新作风》,《真美善》1929年第4卷第3号。,此后又连续发表关于废名《竹林的故事》和《桃园》以及沈从文《入伍后》的评论,指出了废名和沈从文在语言和题材上的区别,前者以“精炼素朴的文章”和“滑稽的讽刺”,描摹了黄梅乡村和北京城里人的面貌⑥毛一波:《〈竹林的故事〉和〈桃园〉》,《真美善》1929年第5卷第2号。,后者则以紧凑的文笔,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活泼的军旅生活图景⑦毛一波:《〈入伍后〉》,《真美善》1929年第5卷第2号。;翻译家朱雯多年后也说,1930年前的短篇小说大都模仿废名和沈从文的文风⑧朱雯:《朱雯致沈从文》,刘衍文、艾以主编:《现代作家书信集珍》,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第893页。。这种对比沈从文一直有所耳闻⑨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0、8页。。如此看来,他的评论则有“顺水推舟”的意味,既不否认废名带来的滋养,同时前进一步,主动表白自我风格的独特之处,在皈依“周作人—废名”文学流脉的前提下,不惜以“情趣朦胧,呈露灰色”等评语夸张地强调废名的“缺陷”,通过某种程度的“误读”,凸显自己的独特所在,对废名则表现出“欣赏及不满足”的态度。1934年,沈从文由沪返平,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身份占据北方文坛要津,在这个时间点出版《沫沫集》,尤其是收入此前从未公开发表的《论冯文炳》,体现出了与前代作家对话的强烈意识,在批判中继承京派文脉。
面对诸多批评,废名不会不知道。在沈从文写完《论冯文炳》的3个月后,废名也对沈从文的《萧萧》做出了评论,称其“文章写得很好”的同时,更对小说中萧萧怀孕后族人的态度表示不满,严厉批评作品的“轻薄气息”和“下流”①法(废名):《随笔》,《骆驼草》1930年第25期。,显示了两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审美和伦理观念差异。废名当时是否读到《论冯文炳》不得而知,而4年后,收入此文的《沫沫集》正式出版,其他批评也日渐积累之时,废名也未急于正面辩解,只是一方面为“趣味”正名,另一方面则在《知堂先生》《孔门之文》《三竿两竿》《中国文章》等一系列文章中,大谈陶渊明、儒家经典及小品文,跟进、声援周作人的文章观和“趣味”观②废名:《知堂先生》,《人间世》1934年第13期。。同时,他也从六朝文、晚唐诗、塞万提斯小说、莎翁戏剧等文学资源中寻觅小说创作的依据,提炼出“玲珑多态”的“乱写”美学③废名:《三竿两竿》,《世界日报·明珠》1936年第6期。。沈从文、李健吾等人皆有微词之处,恰恰是废名津津乐道的“独门绝技”,不仅显示了不同的美学观念,还暗含了周、废等人与当时另一股乡土文学思潮的对话。
三、“乡土文学”视域下废名小说的“归类”问题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到了诸如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的小说,统称其为“乡土小说”或“侨寓文学”:“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④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6-7页。这也成了“乡土文学”概念的经典论断。同时,鲁迅将废名置于浅草社范畴内讨论,而在乡土小说部分只字未提: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了,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⑤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9、6-7页。
在此之前,就有研究者将废名的小说纳入“乡土文学”或是“田园小说”中来言说⑥灌婴的评论就有意突出了废名小说的乡土背景,见灌婴:《桥》,《新月》1932年第4卷第5期。,这一论述传统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持这一说法的,就包括沈从文。鲁迅的不同看法,正反映了双方对“乡土小说”的不同认知。
对废名小说中的乡土回忆和黄梅地方特色的讨论,贯穿了沈从文的整个“废名评论史”,在《论冯文炳》中更是通过与许钦文、王鲁彦等师从鲁迅,并为鲁迅所认可的乡土作家比较,提炼出废名乡土小说所展现的“农村寂静的美”和“地方性强”等出彩之处,进而勾勒出“周作人—废名”乡土文学脉络,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论构成了强烈的“互文”关系,显示出两种不同的乡土文学观。按鲁迅的标准,不论从“侨寓”还是“乡土”角度考虑,废名都不应被忽略。鲁迅不说,不是“不懂”,而是“不想”。《导言》中乡土小说概念似乎可以套用在任何离乡来京的作家身上,即如日后孙犁所言,“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①孙犁:《关于“乡土文学”》,《北京文学》1981年第5期。,这显然不是鲁迅的本意。其对“乡土小说家”有条件的筛选,其实在无形中规约了“乡土文学”的范围。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对鲁迅提及的彭家煌、蹇先艾、许钦文等作家的创作做了详尽分析②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31页。,及时充实了鲁迅的观点;其一年后追述的“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③蒲(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1936年第6卷第2号。,也接近鲁迅所说的“叫喊和反抗”④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郁达夫等:《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2页。,不啻为对鲁迅的补充,体现了编者之间的合作和对话。《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者团队前前后后的反复论证,表明这可能不只是鲁迅个人的意见,更是编者们针对“乡土小说”这一五四后兴起的小说类型所展开的集体建构——主调应为“暴露”,“乡愁”则应居次席。废名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冲淡”这一外衣下隐含深刻的“哀愁”,与鲁迅等人所肯定的风格大异其趣,而风格正是鲁迅遴选作品的另一层标准。
鲁迅按“内敛和外露”两种风格来大致区分五四以来的短篇小说。情绪可以有多种,如“安特莱夫式的阴冷”“炽烈”“大胆”等等,可以等而视之,但涉及表现情绪的方法、倾向,则有了“亲疏”之分,谈论风格“大胆”“外露”的作品,占用的篇幅较长,而论及风格内敛、朦胧的作家时,则几句话带过,多数还带有批评性:杨振声的《玉君》所追求的“艺术化”导致了作品“降生也就是死亡”的命运;凌叔华“谨慎”文风也只是多了一种可参照的创作方法⑤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3、11页。。而被归入“侨寓文学”的作品大都体现出“大胆”“外露”特征,那么废名“以冲淡为衣”,又过分珍惜“哀愁”的小说品格,自然很难得到鲁迅的认可。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对《竹林的故事》缺少“静中之动”,“缺少冲突”的评论,恰恰与鲁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满的都是其作品中乌托邦式的隐士风。尽管沈从文并不认同鲁迅对“乡土文学”的限定,但对待文学却和鲁迅一样严肃,反对“趣味主义”作风。
1940年沈从文再谈到废名与乡土小说关系时感叹道:“然而这种微带女性似的单调,或因所写对象,在读者生活上过于隔绝,因此正当‘乡村文学’或‘农民文学’成为一个动人口号时,废名作品,却俨然在另外一个情形下产生存在,与读者不相通。”⑥沈从文:《习作举例三由冰心到废名》,《国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他的这通发言,既有回应《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意味,同时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陆续问世,沈从文敏锐地意识到背后所蕴含的新文学经典化意义,随即撰写《读〈新文学大系〉》,高度评价其对新文学史的价值,尽管没直接提到《小说二集·导言》对“乡土文学”的界定,但对鲁迅的选文标准不以为然,指出其在编选过程中,过分抬高弥洒、沉钟、莽原社⑦炯之(沈从文):《读〈新文学大系〉》,《大公报·文艺》1935年第51期。。在《论冯文炳》中,沈从文也曾说道:“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⑧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12页。显然是将周作人、废名的路数视为“乡土文学”的正统。沈从文尽管没有直接参与过“乡土文学”“农民文学”等概念的论争,但却受到“波及”,首当其冲的正是代表作《边城》。
1934年1月起,《边城》在《国闻周报》连载,同年4月登完,并于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1935年1月,汪馥泉和王集丛发表《一年来的中国小说》,开门见山地提出“文坛无杰作”,随后一一对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等新作展开批评。具体到《边城》,汪文指出了三大“弊病”:首先,翠翠、爷爷、傩送等人物性格过于单纯,茶峒的环境过于美好,属于过去,缺乏现实性和典型性;其次,曲折的恋爱故事阻碍了思想性的呈现;再次,人物感情太节制,爆发力不够,心理、感情描写不够深刻,难以体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浓厚,不足以打动读者①汪馥泉、王集丛:《一年来的中国小说》,《读书顾问》1935年第1卷第4期。。这明显是以阶级论、典型论的左翼视角进行批判。同年8月,李健吾发表《〈边城〉与〈八骏图〉》,反对汪馥泉的批评②李维音:《李健吾年谱》,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而沈从文1936年初发表的《习作选集代序》,也隐约有回应此类批评的意味:
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结论,我知道没有人把他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引者按:指《边城》)一到了书评家手中,就有了变故。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应属于对立那一派。③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期。
正因为沈从文“不问名义”,因而他也主张,乡土书写不应该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他同年给李寒谷的信中所说:“在这些差不多的文章里,不是写农村破产,就是写天灾人祸,俱差不多。所以我偏写中国人的美德,发扬中国人的美德,如我的《边城》,也有这个意义。”④沈从文:《沈从文的来信》,转引自蒙树宏:《郭沫若、沈从文佚简六封》,《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类似的观点,废名谈到《竹林的故事》时也曾表露:“我的文章……意思是,方面不广。别方面的东西我也能够写,但写的时候自己就没有兴趣。”⑤冯文炳:《竹林的故事·赘语》,《语丝》1925年第14期。换句话说,沈从文虽然对废名朦胧的情趣、厌世的意识和奢侈僻异的文字略有微词,并在这一层面与鲁迅等人不谋而合,但就风景画的描摹、美好人性的谱写、地方风土的展现等层面而言,他仍认同周作人、废名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与李健吾等“京派”批评家达成了共识。这一问题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也延续到了1949年前后——郭沫若把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京派”重将全纳入批判范围⑥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第1辑。,冯乃超也抨击沈从文对熊希龄的揄扬之词⑦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第1辑。,文艺分歧与政治问题已经夹杂在一起,难分彼此。而1949年初,楼适夷的一篇《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终于也将废名与沈从文摆在同一平面,点名批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为“厌世主义和神秘主义”⑧适夷:《一九四八年小说创作鸟瞰》,《小说》1949年第2卷第2期。。同年开春,北平解放,废名开始阅读《新民主主义论》,提笔撰写《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这之后的长时间内,沈从文和废名都停止了小说创作,两人的复杂往来和关系也少有人问津,直到新时期以后,两人之间的精神联系才逐步得到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