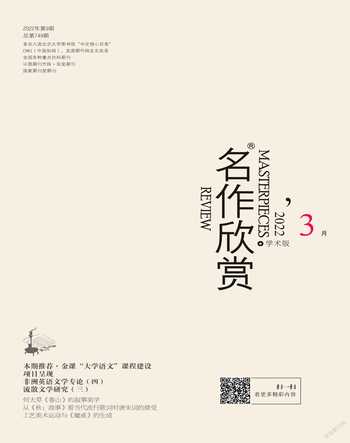从私力救济到宗教救赎
刘净娟 陈子惠
摘要:本文基于法律文学视角对普希金的小说《射击》进行文化阐释,通过分析决斗文化在19世纪早期俄国的发生发展过程,探究小说“罪与罚”叙事框架下主人公的复仇心态,以及决斗作为贵族阶级维护个人价值和尊严最有效手段的正当性及其社会制度逻辑,挖掘在畸形法律文化背景下反叛型人物西尔维奥作为复仇文学史中的精神复仇者,对私力救济手段的态度转变过程及其宗教伦理“驯化”下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法律文化普希金《射击》
复仇主题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厚重的历史感、深刻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情感色彩带给读者深刻的阅读体验。它以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复仇文化中的复杂人性和社会性因素,并积极参与法律文化建设。“法律起源于复仇”,法律文化以复仇文学为载体传承国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表达人民对法治信仰和大善大美的理想追求,体现了作者对人文关怀的终极诉求。本文拟以普希金的小说《射击》为例,从文学法律批评视角对小说的法律文化进行解读,探讨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决斗风气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罪与罚”叙事框架下的复仇心态
决斗主题以批判性的价值倾向贯入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普希金的小说《射击》在一个法律与道德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下,为读者描绘出一幅人性“冲突”的图景:个体间的冲突、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抵牾。
按照法律文化,决斗作为一种复仇形态,本质上是社会初期的私力救济手段。决斗的私力救济功能在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贵族社会贯穿着肯定的价值倾向。贵族社会普遍认同决斗是维护个人价值与尊严最有效的手段。
这与俄国决斗文化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来说,俄国的决斗史是俄国的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冲突史。有关荣誉和人格尊严的思想随着中世纪骑士决斗风俗融入彼得堡文化而发展起来,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而专制君主却希望他们继续做国家的奴隶。被贵族有意识保留的决斗权成为脱离并限制专制君主权力蔓延的标志。纵观俄国决斗史会发现,俄国贵族逐渐走上一条从主权奴隶转变为寻求自由,并准备为自己的人格尊严付出生命的“骑士”戏剧化道路。有学者认为,19世纪俄罗斯在文化思想上的复兴,恰恰蕴含着对18世纪国家主义观念的反抗。
不难发现,旧俄国贵族如同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秉持欧亚主义精神。欧亚文化的双向拉伸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极端、非理性的双重性格。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使大部分俄国贵族成为精神上的西欧人:对自己的国家无法产生文化归属感,却拥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力图改变落后社会现状却寻不到出路。在彷徨苦闷、心理失衡的状态下,“当代英雄”们以肤浅无聊的小事聊以自慰,通过血腥、暴力的决斗发泄与排解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这在当时已成为贵族青年的“时代病”。
最初,决斗普遍被视为一种扰乱公共安宁和秩序且违反当局治安管理的私刑。但到19世纪,它成为一种有效维护尊严的手段,社会对它的态度已然分化:大多数贵族将决斗视为理所当然的固有属性,是他们保持荣誉感的前提条件。决斗的嗜血性及其恶劣影响通常只受到老人与妇孺的谴责,即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决斗的人。
为遏制决斗风险增长的势头,彼得大帝时期曾严禁决斗:违者只要开枪,无论是否造成死伤皆判死刑,家产一并充公。后续补充法令将绞刑惩罚延伸至参与决斗的副手和公证人。叶卡捷琳娜二世扬言要把决斗者放逐西伯利亚,却也收效甚微。当时的人们把流放或贬职视为对决斗者的嘉奖,对勇气的变相认可,公众舆论完全倒向决斗者一方。俄国法律规定,对决斗造成死伤的处罚与普通刑事犯罪等同。19世纪初,决斗的半合法化为不良风气的滋生了提供土壤。欧洲“决斗热”几近消失时,俄国的决斗量和残酷性反而激增,令当时的人们不禁担忧起“荣誉之战”是否已然演变为“合法谋杀”的问题。
普希金通过《射击》表现这种畸形法律文化背景下俄国贵族的复仇心态。在高度尊崇个人荣誉的19世纪30年代,贵族通过代表骑士精神遗风的决斗解决个体纠纷,展示自己的英勇品格,维护个人的荣誉尊严,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决斗作为最体面也最残忍的解决分歧与争端的方式,大多是个人荣誉感、复仇情绪、舆论导向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法律文化角度来说,半合法化的决斗不是司法决斗,其动机不是法律诉讼而是个人恩怨,其目的不是判断是非而是捍卫个人荣誉。侮辱即构成“罪”,复仇则成为“罚”,决斗成为避免世仇的天然终点。
在“罪与罚”的叙事框架下,《射击》展现了高度反叛型的人物西尔维奥的三场决斗。第一场决斗源于醉鬼军官在赌局中的挑衅。在大家认为挑衅者一定会被打死时,西尔维奥却出乎意料地放弃决斗。情节突转折射出以叙述者“我”为代表的舆情态势,认为主人公对待决斗的态度是其精神品格的污点,令其在青年军官中的荣誉受损。
第二场决斗是在西尔维奥叙述视角下,展现他与新来军团的年轻军官之间的冲突。主人公因对方吊儿郎当的姿态选择中断决斗,保留放枪的权利。小说以主人公的内化视角来剖析决斗当事人西尔维奥的复仇心态,从决斗前“怀着不可理解的焦躁心情”,到决斗时“愤怒使我激动得太厉害……轮到我了。要他的命”,再到中断决斗后“从此以后没有一天我不想报仇”,小说更着重描写主人公对决斗者的精神之“罚”。西尔维奥主动选择中断决斗,意图让年轻军官感到恐惧与屈辱——不成文的决斗规则允许他这樣做。这种精神折磨比决斗中当场杀人更能刺痛他人。同样遭受精神之“罚”的还有主人公本人,他背着“懦夫”之名处心积虑隐忍六年之久。
西尔维奥身上凝聚着沙俄时代的贵族青年游戏生死、荒诞虚无的思想,他们因无足轻重的小事受辱而选择以决斗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但同其他决斗者不同的是,西尔维奥不以击倒对手为目标,而是选择在精神上彻底压垮对方,他是真正的精神复仇者。当下即刻的自卫行为因对手吊儿郎当的态度得不到疏解,西尔维奥无法平息的愤怒已然发酵,驱使着人的先天报复本能,最终催化出坚定的复仇意志,甚至让非理性的决斗具备了某种理智参与充满精密算计的可怕力量。
第三场决斗将小说情节推向高潮。西尔维奥终于找到合适的复仇时机,在已成为伯爵的军官的新婚蜜月中如死神般突然出现,欲对宿敌行使放枪权利,却在看到对手惶恐胆怯的瞬间对其精神之罚进行赦免,转而探向“罪”的起源。在亲历两场决斗的叙述者的话语中,精神复仇者心满意足的状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复仇正当性的社会制度逻辑
私力救济行为之所以能够具备“准法律”的面貌,是因其正当性以法律的不可诉性为逻辑前提。在当时的欧洲,“名誉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侮辱名誉属于口头诽谤,基本不牵涉物质利益,法律程序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无法实现履行公平正义的基本目的。因而私力救济正当性的社会制度逻辑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并非因具备天然优越的合理性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因维护了一定的社会秩序,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荣誉感高度发达的社会对荣誉的极度渴求)而被自发遵循。对于那个时代的贵族来说,荣誉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除了地位赋予他的特殊权利外,他还对国家,特别是对他的祖先负有特殊的职责。贵族必须履行与其血统相对应的道义上的义务,并且由于这一特权阶层拥有影响沙皇政府决策的力量,致使他们的言行一直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社会对其的评价至关重要。
荣誉是高贵的象征,一个人的荣誉受损不仅被视为对个人尊严的侮辱,而且也暗示着一个人的血统受到了质疑。可以说,对荣誉的侮辱是对其先祖的侮辱,这是贵族所不能容忍的。
在《射击》中,西尔维奥出于嫉妒,屡次挑衅年轻军官,却巧妙地使话语维持在“不易使当事人遭到他人羞辱、嘲笑或鄙视”的不可诉讼范围内。两人的讥讽一来一回,但都仅限于轻率行为或言语挖苦。然而在一次舞会中,西尔维奥的粗鄙话语换来了年轻军官的耳光报复,这属于引发决斗的侮辱中最严重的一类,是对个人荣誉的极端挑衅。他当场抽刀,他知道诉诸法律等待判决只能被地位较低的社会阶级评头论足,无益于维护上等人的优越自尊,唯有通过决斗才能以血洗刷侮辱,恢复荣誉。
普希金同样展示了上层阶级高度重视由荣誉导致决斗盛行的社会环境,其笔下19世纪初的沙皇军营的贵族军官们,勇敢的品质因长期远离真实战争而无法证明,他们终日无所事事,除训练之外大量的时间都用于喝酒打牌,日常以谈论和实施决斗为乐,逞凶斗恶成了英雄品质。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法律的任何一丝纰漏都能算是推波助澜。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曾说:“如果社会风气如此,任何参加决斗的人都不应该说是违法的。”如《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蔑视决斗,认为这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极其愚蠢,但当巴维尔提出挑战时,却还是被名誉和荣誉所绑架,违背初衷接受了决斗。这种社会规约的约束力主要来源于舆论压力,因而发起决斗是西尔维奥被年轻军官扇了一耳光后的第一反应。无论他是否出于复仇的本愿,所谓宽容的美德在当时只会使他蒙羞,复仇才是唯一的逻辑。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风气,西尔维奥在被挑衅后却放弃与醉酒军官的决斗被视作不勇敢的懦夫表现,但他对抗荣誉社会舆论的行为也表明了坚定的隐忍复仇之心,放弃小荣誉是为了更大的荣誉。
第二,在法律救济缺失的情况下,决斗能弥补法律空缺。诉诸法律解决纠纷的方式使当事人深陷名誉受损的困境,而在私力救济下,荣誉的恢复不依赖对决结果,决斗后敌对双方继续往来甚至建立友谊也并非反常事。虽然引发决斗的纠纷点实际上并未得到解决,但毋庸置疑的是,两人的荣誉在颇具表演性质的决斗场都得到了展现的机会。甚至正因为在决斗场上有死亡或伤残的风险,这种高代价低质量的纠纷解决机制,才会以现代人看来十分畸形的方式,赋予了决斗者们罗马角斗场时代的英雄荣光,成为他们信念和勇气的最好证明。
在荣誉文化支配下,品格成为绅士勇者们需要向世人外显的勋章,这便是决斗契合决斗者心态的原因之一。说到底,人们可能在特定情况下质疑决斗,不过是对引发决斗的无足轻重的借口、决斗过程的残酷或亵渎决斗行为的不满。无论如何,这不是批评,反而证明了人们对决斗仪式尽可能纯洁,或者说庄严如法律的渴望。
除却上述决斗心态,在《射击》中,作者更多地将决斗叙述话语指向西尔维奥的残忍个性。他极度渴望洗刷名誉的心态,使其陷入极度的“恶”,不止于在决斗场展现个人胆量,而是想要致人于死地。
第三,决斗由“半合法化”或“准法律化”转为合法化。决斗的社会规约性和悲剧性被大众普遍接受,不能完全被法律禁止,因而俄国模棱两可地将其“半合法化”或“准法律化”。这在一定上程度上将决斗推向合法化的发展态势,使其成为另类“法律”。决斗完全按照一套复杂严密的“荣誉礼法”执行,包括挑衅套语、助手的调解、决斗地点、武器、距离、规则等,都有固定程式。这将决斗与野蛮斗殴区分开来,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限制了复仇的扩大化、群体化倾向。这在《射击》中集中表现为公证人测量射击距离、抓阄决定放枪顺序等。因此在一套严格有序、被当作法律遵守的决斗礼法面前,年轻军官将“荣誉场”视作“娱乐场”,当着公证人的面不以为意吃樱桃的轻浮举动才会深深激怒西尔维奥,他欲图洗刷侮辱、重赢荣誉的心理令他升起复仇的念头。
因此,无论这一私力救济行为出于什么动机,是否违背理性、违反教义或法律,是否具有诸多弊端,是否只是贵族阶层独享的国家保护特权,都不可能被轻易取代,因为该制度已成为俄国贵族社会维护荣誉固有的特定风俗传统和共同价值理念。
還有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法律越是试图以其强制性和高惩罚力度禁止决斗,就越能刺激决斗者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荣誉的心理,反而使决斗这一复仇行为变得崇高而有价值。
英国哲人培根曾对私力救济行为做出批评。他认为:“报复是一种野道,人性越是趋之若鹜,法律就越应将其铲除。因为头一个犯罪仅仅是触犯法律,而对该罪施加报复则是取代法律。”即私力救济风气越是盛行,越是表明该时代的公共权力是多么无力,无法有效防止和制裁不道德的侵犯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复仇制度理应消亡,反过来,它理应被更加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所替代,成为捍卫个体或群体的正义利剑。
三、宗教伦理“驯化”下的自我救赎
纵观古今中外的复仇文学会发现,中国古代对复仇行为几乎是一边倒地褒扬。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对复仇行为中伦理任务实现的看重,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与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使儒家文化将忠奸善恶极端对立。这种伦理诉求寄托着人们对和谐稳定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因而无论于公还是于私的复仇,都受到封建礼教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这样的做法,模糊或忽略了复仇过程中人性的挣扎、心灵冲突和矛盾叙事,专注于描绘复仇结果大快人心起到的传颂和感化作用。
与之相反,西方复仇文学更侧重于表现个体与命运的永恒抗争,从微观叙事中选取对人性细微剖析和思考的部分,展示出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怜悯。
对于西尔维奥来说,最终的救赎方式不可能是死亡,而是宗教伦理。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灵魂的宗教体系培育出了某些根深蒂固的特性,其中有一个便是为任何信仰而忍受痛苦与牺牲的能力。教会总是对决斗持消极态度。东正教作为一种宗教,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其价值观高于世俗。在这种情况下,教会认为贵族的荣誉观绝不应该凌驾于基督教的美德之上。人的生命属于上帝,没有人有权支配生命,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的。贵族们所持荣誉观中的“荣誉”是属于世俗之人的,他们在世俗中获得的“荣誉”被看作是“异教徒的荣誉”。
对于西尔维奥这类自尊心高度膨胀的贵族青年来说,受辱后提出决斗,却因对手不珍视生命的行为而中止决斗即是痛苦。在当时的俄罗斯人意识里,排解痛苦的唯一方式是寻求宗教救赎。西尔维奥体现了东正教的受难意识,他在贫困小镇隐居六年,清苦过活,甘受肉体摧残。他的痛苦更多是在于精神折磨,为等待完美的复仇时机备受煎熬。但受难终究不是目的,西尔维奥在日复一日的兵书学习与枪法苦练中,磨炼其坚忍意志。他在最后面对仇人之时意识到这场决斗已然分不出胜负,伯爵因为有了家庭而珍惜生命,若西尔维奥此时杀了他,不断祈求宽恕的、可怜的伯爵之妻将成为这场暴力事件的无辜受害者,西尔维奥也会失去一直以来生存的动力——复仇。
东正教教义强调无差别的普世之爱,这种爱的高尚之处在于宽恕、同情和慈悲,即使对面是你的仇人。面对珍惜生命而害怕死亡的伯爵,西尔维奥在等待射击的那一刻终于明白:射击权并不赋予他杀人的权利。他的复仇只是对无法出于荣誉法则为自己辩护的人的惨烈谋杀。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丈夫也意味着摧毁年轻无辜的妻子。于是西尔维奥放下了手枪,子弹对于如今的他来说太沉了。
在西尔维奥心中,伯爵从前的无礼行径和轻视生命的态度是他认定伯爵有罪的思想基础,传统俄罗斯精神中根深蒂固的东正教原罪观使他最终认识到自己出于嫉妒的报复同样也是罪恶和反人道主义的。西尔维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已经历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但这终究是出于复仇目的的消极苦难,唯有真正的积极苦难才能使有罪的灵魂重归纯净。作为上帝和基督的虔诚信徒,他在善恶之间做出了选择。在宗教伦理的驯化下,西尔维奥的救赎是必然之路。
西尔维奥救赎之路的第一步是停止复仇。在伯爵的回忆里,西尔维奥回头对着画开了一枪,为自己六年的复仇之路做了一个形式上的终结后转身就走。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那至多是一个经历多次反转的普通复仇故事。但在故事末尾,普希金寥寥数笔,以叙述者“我”之视角,交代了西尔维奥率领希腊独立运动战士的队伍在斯库良诺战役中牺牲的结局。他意识到“复仇不过是罪恶循环”这一精神的延伸,意识到走出精神困境意味着必然走向牺牲的结果,为正义的解放战役的牺牲正是为了最终的灵魂救赎,这是西尔维奥救赎之路的第二步。
就连小说作者普希金自己也是决斗的常客,他的生命在与丹特士的决斗中陨落,成为令世界文坛扼腕叹息的憾事。作品中关于决斗的描写或多或少取材自他自己的经历,而字里行间的情节叙述透露出作者对决斗既抨击又维护的矛盾复杂态度。普希金的行为受限于时代,决斗无可避免成为维护尊严的唯一途径。但他也同样对决斗持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他意识到,在生命意义集体呈现荒诞感的时代,在“公平”、“正式”、属于优越上等人的、为了榮耀而战的光荣决斗场,所谓英雄气概是多么的脆弱肤浅,男性的骄傲自尊竟要靠对个人恩怨的斤斤计较和匹夫之勇来维系,可谓是时代的悲哀。
因而在《射击》中,普希金将这种对双方都遭受精神酷刑的复仇方式的不满寄托在西尔维奥身上,令无意义的以暴制暴的悲哀在主人公身上得以终结。此外,主人公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结尾带有悲壮意味。如若联系普希金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取向不难得知,这暗指爆发于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革命”:一群大多出生在贵族富裕家庭且在沙皇统治的政治机构里担任职务的青年们,为祖国的发展将自身置于原本阶级的对立面,毅然决然反抗沙皇封建专制和农奴制。虽然最终因阶级局限而失败,但这场革命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探索的摇篮,它所蕴含的价值也契合了东正教哲学中救世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这对于时代变革时期的俄国贵族青年,则体现为关怀国家命运且不怕为之流血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普希金无疑给予了这群血气方刚的贵族革命青年高度的评价,而西尔维奥正是青年群体精神的化身,具有叛逆的浪漫主义精神。他将冲动狂热向自由革命意志转变,最终不为无聊荒谬的决斗所绑架,而是超脱了时代的忧郁病,为宗教伦理所“驯化”,呈现出对人文乃至人类世界终极意义的关怀意识,以及为自由和国家抗争的精神。他最终也以民族英雄的形象退场,人物的民族性在此刻完满。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的忏悔不足以使他精神完整,为正义和理想的革命事业牺牲才使得他的灵魂得以升华。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A ·波斯纳.法律与文学[M].李国庆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ГординА.Я.Дуэлиидуэлянты:Панорамастоличнойжизн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ушкинскогофонда,1996.
[3] 奥兰多·费吉斯.娜塔莎之舞[M].曾小楚,郭丹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4] 汤伟丽.“欧美尼德斯”之魅[D].复旦大学,2009.
[5] 亚历山大·普希金.黑桃皇后[M].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 Van Vechten Veeder.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the Defamation[J].Columbia Law Review, Vol.4,1904.
[7] 詹姆士·包斯威尔.约翰逊传[M].罗珞珈,莫洛夫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8] 吴晗.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决斗主题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4.
[9] 朱淑丽.从荣誉决斗看法律与社会规范[D].华东政法大学,2007.
[10]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随笔[M].蒲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1]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2] 王春英.东正教与俄罗斯的道德重构[J].西伯利亚研究,2016(3).
作 者: 刘净娟,博士,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陈子惠,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本科生。
编辑:曹晓花E-mail: 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