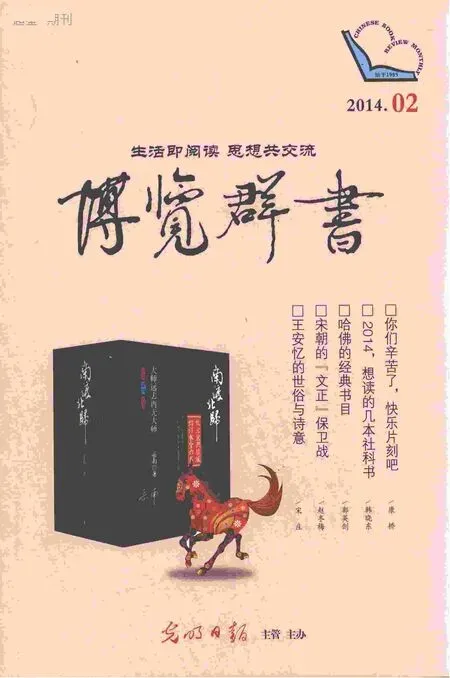骆宾王诗前为何多“序”
吴振华
据现存文献清编《全唐文》及其相关补遗的检索统计,初唐时期留存至今的“诗序”一体文章约110篇,其中,王勃创作最多,骆宾王排名第二,有“诗序”19篇。
为何他们诗前多“序”呢?究其原因,我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1.序体承继南朝骈文特色,最容易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诗化特征;2.序体轻便灵活,既无须赋颂那样精心结撰,殚精竭虑,也没有书启、碑铭那样的目的性,因而最适合个人情感、心绪的自由表达;3.序体适合宴会、群游纪行的场合,既能表达文人聚会的雅兴,又能展露文学才华,因而成为才子型文人最佳的选择文体;4.大唐初期由百废待兴渐渐走向兴旺发达的气象,文人才士游宦宴乐的频繁,促进了时代风气对序体的需求,得到名人的赠序或在著名宴会上能被推举作序均是一种很大的荣誉。最主要的还是,这些当时最负盛名的才子文人,他们命运悲惨,长期沉沦下僚,没有在朝廷获得显位,不可能在朝廷大著述的碑铭、赋颂、制诰、德音等方面获得展露才华的机会,只能在纪游、宴会、赠别、思友等方面用力,所以对赠序一体尤为偏爱。
我认为,王勃的诗序虽然留存最多,但大部分仅有序而无诗,其原因我认为王勃在刻意作序,而诗歌则成就不高,最终导致序存诗佚的状况,或许当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王勃的诗序,而不甚看重他的诗歌,即出现“序重诗轻”的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王勃诗歌的成就不如其诗序。而骆宾王则不同,他是初唐诗歌与诗序并存的重要诗人,不仅诗序可以媲美王勃,而且诗歌显然更胜一筹。如果从诗与序交融的角度来看,骆宾王应该是初唐第一人。
今存骆宾王诗序共19篇,其中宴会诗序六篇,游历诗序三篇,赠别诗序五篇,留别诗序一篇,酬赠诗序一篇,独特经历诗序二篇,表达诗歌观念诗序一篇。诗与序并存者,如《初秋于窦六郎宅宴并序》:
六郎道合采葵,啸悬鹑而契赏;诸君情谐伐木,仰登龙以缔欢。于时一叶惊寒,下陈柯而卷翠;百花凝照,澹虚牖以披红。既而俱欣得兔之情,共掩亡羊之泪。物我双致,匪石席以言兰;心口两齐,混污隆而酌桂。虽忘筌戴笠,兴交态于灵台;而搦管操觚,叶神心于胜气,盍陈六义,诗赋一言。即事凝毫,成者先唱云尔。
诗曰:
千里风云契,一朝心赏同。
意尽深交合,神灵俗累空。
草带销寒翠,花枝发夜红。
唯将澹若水,长揖古人风。
序文开头简要叙说自己与窦六郎是同道间的贫贱之交,虽然衣如悬鹑,但啸歌自乐,心志相通;与诸君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般欢情和洽,又像仰望登龙门的座主一般超凡脱俗。显然,与诗歌的前两联非常相关,诗首联强调千里契合相会,宾主之间“心赏”相同,即意趣相投,心心相印;颔联强化朋友之间的精神追求一致,且都具有超凡脱俗的情怀。唯一不同之处是:序文用典故,显得典雅庄重,而诗歌则重概括虚泛,正好形成沉稳与空灵的绝妙结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序文接着描写时下的秋景:寒秋将至,一片黄叶从翠绿的枝头飘坠;然而百花依旧绽放,其鲜红亮丽的光色映照着窗帘;再由欣赏景物而进入物我两忘、义结金兰、心口一致、举杯畅饮的精神佳境,因此借酒兴作诗抒怀,宴会只是作为一个触媒,没有作过多的描述,说明唐人写诗大多是在某一独特情景下,通过宴会的形式催生诗兴。我们再来看诗歌的后两联,颈联以“草”之“翠”和“花”之“红”相互照应,与序文描写的秋景完全一致,连颜色词都出自序文,不同的是序文骈俪对称,诗歌简洁流畅,形成序文密实与诗歌疏朗的风格差异。尾联强调君子之交淡如水,要学习古人的高古格调。序文在结尾部分稍微复杂,既用典故交代筵席觥筹交错的情景,又要表达賦诗抒怀的用意。总体上看,诗序与诗歌结构完全一致,若合符契,只存在序文典重骈俪与诗歌疏朗空灵之间的区别。结合诗歌与序文来看,可谓双美交映,互增光彩。
又如《秋日送尹大赴京并序》:
尹大官三冬道畅,指兰台而拾青;薛六郎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于时兔华东上,龙火西流。剑彩沈波,碎楚莲于秋水;金辉照岸,秀陶菊于寒堤。既切送归之情,弥轸穷途之感。重以清江带地,闻吴会于星津;白云在天,望长安于日路。人之情也,能不悲乎?虽道术相望,协神交于灵府;而风烟悬隔,贵申心于翰林。请振词锋,用开笔海,人为四韵,用慰九秋。
诗曰:
挂瓢余隐舜,负鼎尔干汤。竹叶离樽满,桃花别路长。
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素书如可嗣,幽谷伫宾行。
这篇诗序中“三冬道畅,指兰台而拾青”是对尹大的祝愿,而薛六郎是宴会的组织者,他“四海情深,飞桂尊而举白”则表达惜别的情感。此时明月东升,流火西沉,月映秋水,莲叶在水中摇晃,月照河堤,菊花在秋风中盛开。然后进行渲染,“重以清江带地,闻吴会于星津;白云在天,望长安于日路”绾结客我双方,最后是赋诗“人为四韵,用慰九秋”。从诗与序来看,有一种对应关系,序中所涉及的内容,在诗中也必须有交代,像这首诗首联概括客我双方,友人赴京“干汤”即“指兰台而拾青”,我则“隐舜”即“剑彩沈波,碎楚莲于秋水”;第二联写离别,酒杯中盛满“竹叶(青)”的美酒,桃花盛开的路途充满离情别意,是对序中描写的精练概括;第三联写景衬托气氛,银河耿耿,秋色满天,落月寒光,气氛凄然,是对序文写景部分的补充;末联与序文末尾相辉映,是对友人旅途的慰藉,说若友人的书信不断寄来,那么我一定就像兰花伫立在幽谷之中深情期待。无论序还是诗,都追求情景交融,追求凝练整饬,诗与序是对称的,或者说诗序与诗歌具有艺术结构上的同构性。
又如《秋日饯陆道士陈文林并序》:
陆道士将逰西辅,通庄指浮气之关;陈文林言返东吴,修途走落星之浦。于是维舟锦水,藉兰若以开筵;绁骑金堤,泛榴花于祖道。于时赤烟沈节,青女司晨。霜雁衔芦,举宾行而候气;寒蝉噪柳,带凉序以含情。加以山接太行,耸羊肠而飞盖;河通少海,疏马颊以开澜。豋髙切送归之情,临水感逝川之叹。既而嗟别路之难驻,惜离尊之易倾。虽漆园筌蹄,已忘言于道术;而陟阳风雨,尚抒情于咏歌。各赋一言,同为四韵,庶几别后,有畅离忧云尔。
诗曰:
青牛游华岳,赤马走吴宫。
玉柱离鸿怨,金罍浮蚁空。
日霁崤陵雨,尘起洛阳风。
唯当玄度月,千里与君同。
这是赠别陆道士和陈文林的诗序,陆“将游西辅”,而陈“言返东吴”,因此对友人旅途是对称双写,接着写宴会的地点在锦水边的一所寺庙,系马在榴花开放的路边,然后绾结于眼下统一的秋景:“赤烟沈节,青女司晨。霜雁衔芦,举宾行而候气;寒蝉噪柳,带凉序以含情。”再以太行山的羊肠小道和黄河波翻澜卷的壮阔景象作陪衬,表达登高送远、临水伤别之情,最后是安慰友人,赋诗赠别。这一完整的送别过程,在诗歌里也有表述,首联概括陆、陈二人的远路目的地,次联叙写宴会情绪,展现离别时的场面,三联用崤山函谷关及洛阳的风雨景象作陪衬,最后抒发望月相思的惜别深情。诗与序相比,更显空灵,而序则翔实,带有一种雄浑壮健的气势。显然,诗序与诗歌还是异体同构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赠别诗序与诗歌存在艺术结构的统一性,骆宾王的诗序与诗歌就是典型的样本,可以考见两种文体在初唐形成交融的关系,典故丰富的四六骈文与韵律和谐的诗歌相互映衬,既可以吟诵,又可以弦歌。
当然,由于诗歌与散文是两种文体,尽管有相通之处,但毕竟由于承载内容及表达功能方面的差异,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如《在狱咏蝉并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禀君子逹人之髙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资天纵;饮髙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徽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揺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巳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巳。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诗曰: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这篇诗序和诗歌作于高宗仪凤三年(678), 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后,遭人诬陷,以贪赃罪名下狱。序文开头叙述身陷囹圄的环境,有数株像当年殷仲文感叹的生意萧条的古槐,又像周朝召公问狱断案的甘棠,接着描述了“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的独特感受,用汉赋的铺排笔法,从洁身、蜕皮、候时、应节等方面写蝉的“声以动容,德以象贤”,表现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的高尚品质,虽然他“吟乔树之微风,韵资天纵”,但是“饮髙秋之坠露,清畏人知”,还要担心螳螂的威胁,简直就是一篇骈体《蝉赋》。然后联想到自己品行高洁却身遭徽墨囚禁,这样物我同一,于是托兴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慨,这样哀蝉即怜己,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这篇诗序与诗歌不再具备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诗歌首联只从西陆蝉声的悲鸣中,抒发这位囚徒思念家乡的悲苦心情,完全略去了序文中的背景交代。颔联运用流水对,将寒蝉与自己对写,说蝉的玄鬓影与自己的白头翁形成难堪的对比,极写自己的孤独衰老的悲惨境地。颈联忽然转向对蝉的高洁品质和不幸遭遇的描写:寒露凝重,让鸣蝉的飞起困难重重,寒风萧瑟,使鸣蝉的高唱掩盖低沉,写出秋蝉想极力表现自己却无法摆脱环境压迫的艰危情状。表面上写蝉,实际上却是借蝉喻己,蝉在凝露寒风中的遭遇不就是自己现实困境的形象表述吗?所以尾联人蝉绾合双写,序中“哀弱羽之飘零”“悯余声之寂寞”与诗中“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有相得益彰之妙。诗序的牵引作用较为明显,序详诗略是其主要特征,但序中核心句子与诗歌还是相互关联,只是没有形成完整的诗歌与序文的同构关系,诗序交代背景,写出蝉的一生遭遇,颇像一篇咏物赋,而诗歌则空灵,借蝉抒慨,运用比兴象征,颇有韵味。诗序与诗歌既可以单独欣赏,也可以相互结合考察,总体上看是非常成功的诗、序照应交融的代表作品。
骆宾王的遭遇非常曲折,带有初唐时代文士普遍的悲剧命运,因此他深沉而苍凉的人生感慨经常通过诗序向知己倾诉,与宴会群聚送别友人不同,这样的酬赠之作,带有独抒性灵的色彩,如《夏日游徳州赠髙四并序》:
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有不得尽言,言有不得盡意。仆少负不羁,长逾虚诞。读书颇存渉猎,学剑不待穷工。进不能矫翰龙云,退不能栖神豹雾。抚循诸己,深觉劳生,而太夫人在堂,义须捧檄。因仰长安而就日,赴帝乡以望云。虽文阙三冬,而书劳十上。嗟乎!入门自媚,谁相谓言?致使君门隔于九重,中堂远于千里。既而交非得兔,路是亡羊。敬止弊庐,朅来初服。遂得载披玉叶,款洽金兰,倾意气于一言,缔风期于千祀。虽交因气合,资得意以敦交;道契言忘,少寄言而筌道。是以轻投木李,以代疏麻。章句繁芜,心神媿恧。庶瞻雅韵,伫辱报章。则紫曜运星,开龙文于剑匣;素辉亏月,领骊颔于珠胎云尔。
诗曰:
日观邻全赵,星临俯旧吴。鬲津开巨浸,稽阜镇名都。
紫云浮剑匣,青山孕宝符。封疆恢霸道,问鼎竞雄图。
神光包四大,皇威震八区。风烟通地轴,星象正天枢。
天枢限南北,地轴殊乡国。辟门通舜宾,比屋封尧德。
言谢垂钩隐,来参负鼎职。天子不见知,群公讵相识。
未展从东骏,空戢图南翼。时命欲何言,抚膺长叹息。
叹息将如何,游人意气多。白雪梁山曲,寒风易水歌。
泣魏伤吴起,思赵切廉颇。凄断韩王剑,生死翟公罗。
罗悲翟公意,剑负韩王气。骄饵去易论,忌途良可畏。
夙昔怀江海,平生混泾渭。千载契风云,一言忘贱贵。
去去访林泉,空谷有遗贤。言投爵里刺,来泛野人船。
缔交君赠缟,投分我忘筌。成風郢匠斫,流水伯牙弦。
牙弦忘道术,漳滨恣闲逸。聊安张蔚庐,讵扫陈蕃室。
虚室狎招寻,敬爱混浮沉。一诺黄金信,三复白珪心。
霜松贞雅节,月桂朗冲襟。灵台万顷浚,学府九流深。
谈玄明毁璧,拾紫陋籝金。鹭涛开碧海,凤彩缀词林。
林虚星华映,水澈霞光净。霞水两分红,川源四望通。
雾卷天山静,烟销太史空。鸟声流向薄,蝶影乱芳丛。
柳阴低椠水,荷气上薰风。风月芳菲节,物华纷可悦。
将欢促席赏,遽尔又归别。积水带吴门,通波连禹穴。
赠言虽欲尽,机心庶应绝。潘岳本自闲,梁鸿不因热。
一瓢欣狎道,三月聊栖拙。栖拙隐金华,狎道访仙查。
放旷愚公谷,消散野人家。一顷南山豆,五色东陵瓜。
野衣裁薜叶,山酒酌藤花。白云离望远,青溪隐路赊。
傥忆幽岩桂,犹冀折疏麻。
这篇诗序是投赠知己朋友的,序中将自己的遭遇悉数倾吐,少负不羁,而如今“进不能矫翰龙云,退不能栖神豹雾”,进退维谷,一事无成,心中充满了压抑,因此骆宾王作了这首长篇五排,作为对友人“雅韵”的报答。这篇诗序可以看作是骆宾王的自传,而诗歌也规模宏大,纵横捭阖,风格豪迈。全诗49联,11次转韵,含有这些内容:游德州的情事,并将德州与故乡对举叙写;自己潦倒落魄的遭遇;与高四的知音交谊和对高四的赞美;自己的归隐志愿;因为“诗有不得尽言,言有不得尽意”,故赠诗抒怀。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对诗序的具体化,只不过诗歌运用大量典故抒写感慨,还运用大量的景物描写增强气势,烘托情感。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认为在骆宾王创作诗序及诗歌的时候,他有意识打通两种文体的藩篱和壁垒,具有诗文相通的观念。如果与王勃对比,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王勃文名高于诗名,尽管他写作的诗序最多,尤其著名的是《滕王阁序》,堪称千古美文,但观其序文结尾的诗歌,却与序文关系并不密切,倒是有一种疏离之感,以致很多唐文选本皆只取其序而不录其诗。这也是王勃绝大部分诗序后所附录诗歌的遭遇,尽管王勃诗歌佚失真正原因难以详考,但王勃刻意作序以炫耀文采,而勉强赋诗以应景大致是可以肯定的。骆宾王则颇有更加通脱的文体观念,写作诗序与诗歌同等用力,且诗与序紧密交融,显示了初唐时期打通诗与文艺术壁垒的努力,堪称初唐时期诗文交融尝试的第一人。
(作者系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