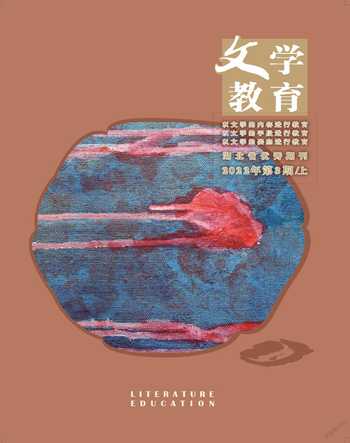从炼字的角度窥探杜甫诗歌的惊人之语
杨亚民
内容摘要: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本人和他的作品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歌创作把语言的追求与生死联系起来。这种惊人之语在他的诗歌里,一方面体现在语言的传神上,古人说“老杜炼神”,但是,这种传神,又和诗句中的关键字离不开关系。另一方面,惊人之语体现在语言传达情感感动人的巨大力量方面。
关键词:杜甫 炼字 动词 浑融
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本人和他的作品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歌创作把语言的追求与生死联系起来。这种惊人之语在他的诗歌里,一方面体现在语言的传神上,另一方面,惊人之语体现在语言传达情感感动人的巨大力量方面。从杜甫诗歌炼字的角度窥探杜甫诗歌世界,许多关键字在抒情层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古人说,老杜炼神,杜诗中的炼字因为与全诗浑融无间,有时,看起来,所用之字似乎平淡无奇,所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杜甫诗歌很少有为人津津乐道的单独的好字好句。其实,作为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从来没有忽视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正是杜诗炼字的浑融才让他的诗歌往往如行山荫道中,美不胜收,常常有惊人之语,天地独大,耐人寻味。
一.动词与诗句契合无间,浑然天成
动词往往具有诗眼、句眼的功能。诗眼、句眼作为诗歌创作和诗歌欣赏方面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是宋人在赏析唐诗时发现的。通过抓诗眼就能够找到理解诗歌的入口。诗眼在结构上具有聚焦作用,在情感上具有移情作用。担任诗眼功能的动词,因为最具活力,更能承担诗人传达内心深沉情感的任务。
杜诗的炼字往往不露痕迹,所炼之字与全诗融为一体又富于变化,增强了动词的表达效果。这些动词,能够巧妙地将诗人的主观情感转移到所写景物之中,读者借助动词进入语境,就能感受到景物之中作者丰富而幽微的心灵悸动。《江边星月二首》其二中“江月辞风缆,江星别雾船。鸡鸣还曙色,鹭浴自晴川。”开头的两句,一般认为是句式发生了变化,应是诗人解开缆绳在夜风中辞别江上的星月,乘着船行在雾气茫茫的江上。其实,这种对语序的调整弱化了“辞”与“别”二字字眼的情感力量。杜诗语序的变化,固然与平仄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移情有关。江月江星置于开头,作为辞与别动作的施动者,原来的辞别方向发生了转换,这样就把倒影在江中的星月拟人化,转变成江中星月辞别行船,意思是,虽然行人已经乘船行走,但江上的星月仍然依依不舍的跟在船边,船行江上,星月倒影相随,可爱之态顿生,难舍之意加深。这样,星月通过“辞”和“别”就承担了作者离开此地又要漂泊他乡的心理感受,比人辞别星月更能传递出内心微妙的悸动和深沉的悲哀,行路迢迢,孤舟夜月,其寂寞之情也许只有星月陪伴理解。这正是杜甫通过语序的变化突出动词的詩眼作用,如果按照单纯语序变化来理解,这两句不过是平常的别离,并无深意,而辞与别也不过是一般的动词,只承担了平常的任务,诗意减弱,读之乏味。所以,理解杜甫诗中动词的抒情作用,既要注意动词的言外之意,更要品味特殊句式的深层含义,才能体味出杜甫诗歌深厚的韵味。这正是杜诗练字与他人练字的一大区别,其他诗人练字常常一目了然,格处突出。比如有名的“僧敲月下门”“红杏枝头春意闹”,成为赏析练字常举的例句。而杜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却很少有作为练字的例句为人记诵。练字艺术的浑然天成,动词的深意又往往被人忽略。而通过动词理解杜诗可以别开生面,峰回路转。杜甫诗歌正是在这种浑融之中,蕴藉含蓄,深沉顿挫,通过对动词句眼或诗眼的细品,才能深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歌追求,也才能发现杜甫诗歌语惊人的惊人之所在。
杜诗中有些动词看似平常实则别有天地。杜诗中有些动词,看起来似乎并无深意,只表现出一般动词的意义,承担描形摹态的任务。之所以不被读者注意,是因为所用之字平常,与所写之景画面清晰,看起来一目了然。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种浑融天成正是杜诗练字的基本特点。杜诗的练字让所用动词与诗句浑然一体,契合无间,情味深长。比如《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歌是作者晚年之作。从整体看,前两联写江边秋景,第三联的“秋”字回扣前面景物的季节,悲”字又暗示前面秋景中诗人融入的情感,“悲秋“二字前扣后转,到尾联“艰难”二字既总结上一联,又向深处开掘,并在点明末句“潦倒”的原因。全诗沉郁顿挫,悲壮哀愁。从动词的巧妙运用角度来深入体味,颔联出句“下”字,对句“来”字,描写出夔州江边江上的秋景,即树叶从上面落下,江水从远处流来。从深层理解,“下〞字“来”字这两个字用的极重极有力,给人一种沉重的压迫感,把诗人晚年多病漂泊的沉重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生命意识在内心激荡搏郁着,“无边落木”,“不尽长江”通过“下”和“来”两字,给人压迫的沉重感,似有万钧力量,从高处压下来,从前面扑过来,这些动词把诗人内心的情感转移到外物上。两个动词,所蕴含的不只是秋天天地萧瑟,时序迁移之感,更有生命个体所承受的沉重的压迫与深重的苦难,诗人年老多病,漂泊无依,忧愁哀苦,时世多难,三年之后,于寒风劲烈之时,病逝于江湖扁舟之中。
二.同样色彩,别样天地
杜甫诗歌的色彩词名句与印象派绘画有点神似之处,都将色彩给人强烈刺激而引发的心理感受表现出来。杜甫1400多首诗歌中,颜色词出现1400次,用的最多的是白色、青色、黄色。色彩词在诗句中的位置灵活多样。并且开创了首字和尾字设色彩词的独特用法。杜甫诗歌中色彩词不但在绘景造境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色彩词上升到独立承担意义的地位,充分发掘出色彩词的丰富意蕴,作者的情感贴切地转移到色彩词上,增加语言表现的张力,让色彩词似乎有了活性。
色彩词在诗词中本是常用词,凡写景,常常要写景物的形声色态,以及组合的画面,绘图摹景往往需要着彩染色。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在杜甫的诗歌中,色彩词的创造性运用,让普通的色彩词有了活性,这种活性的产生不仅利用了色彩词的基本义项而拓展它的词性,而且让色彩词蕴着思想情感,激发了诗句的活力。所以,杜诗中色彩词在诗歌中有更丰富的抒情作用,将作者的情感巧妙地契合在所写景物之中,发挥了写作的移情作用。
杜甫在诗句中色彩词极为灵活多变。有句首、句中、句尾的,有单独使用色彩词,又有成对使用的,有词性为名词的,有活用为动词的。位置灵活,词性变化,运用自如,渲染白描中情味悠长。
色彩词置于句首时,词的意味也随之变化,色彩词让人感到既陌生又新鲜,意蕴丰富。句首的色彩词变成欣赏主体,显得格外突出,色彩变得可感可触,成为一个实体。比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一般认为,这是杜诗的语序变化,可以调整为“风折笋垂绿,雨肥梅绽红。”意思是风吹折了绿笋垂下来,雨足而润泽的梅子红艳喜人。意思也清楚,画面也鲜明。其实,这里杜诗将色彩词提到主语的位置上,是另有用意的,同样色彩,别样天地。沿着诗的顺序来理解,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眼前绿色强烈而鲜明,从上面垂下来,仔细一看是笋太翠绿,因风而折;那红色醒目肆意绽开,原来是因雨而肥的梅子灿烂一片。作者先写色彩给人强烈的印象,这也符合观物的一般规律,尤其是色彩极其鲜明的事物,是色彩刺激了对物的观感。因为色彩鲜明醒目,才把色彩词置于主语的位置,接着才有对物的分辨。这句诗从色彩的角度刻绘出物的生命状态。“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更能寄托作者对雨中笋梅的情感,这些情感不只是色彩词诉诸视觉,更是色彩词诉诸心理,在强烈的激发下而产生对生命的体认和人生的感悟。而“风折笋垂绿,雨肥梅绽红”则诗味顿失,平淡无奇。
杜甫诗中的色彩词的独特作用一方面缘于他对词语的敏锐体会,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学习前人,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创造功力。《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中有“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两句,仇兆鳌《杜诗详注》中认为,以前谢尚有“柳青桃复红”,梁简文帝有“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的诗句,都平淡无奇,而到杜甫手中,用“归”“入”二字写出景色之新嫩。谢尚和梁简文帝写柳与桃用青与红,只展示所写之物的直觉色彩,自己所写别人也能写出,并无新意。而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红”“青”置于主语位置上,紧承的“归”、“入”两字极具主动性,“红”“青”便具有了动态特色,后面以“嫩”“新”呼应“红”“青”,红色渐渐进入桃花,桃花朵朵绽红吐嫩,青色如有所归回到杨柳片片细叶中,叶片与昨日比较,一派新颜。将对物态的微妙变化引发的心理感受传递出来。化平淡为新鲜,化静态成动态,变化多姿。
杜诗中色彩词的词性更加多样,有名词性,形容词性,也有动词性。词性随诗句而生,诗意并没要因色彩词的词性的变化而造成理解的障碍,词性的变化反而让诗意更浓,更耐人寻味。色彩词的动词性,不仅呈现出一种色彩,而且将色彩的动感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多重呈现中更好地承担了作者的心理变化,色彩词活用的移情于物的作用也体现了作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歌追求。
《泊松滋江亭》“沙帽随鸥鸟,扁舟系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远微青。一柱全应近,高唐莫再经。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这首诗是作者漂泊途中在松滋江亭短暂停留,首句蕴藏难以言说的感慨,“江湖深更白,松竹远微青”色彩词运用巧妙,“江湖”泛着“白”色,而一“深”字与之搭配,水中之物茫然不见,唯余天光浮动,飘飘乎,茫茫然,故曰“白〞,色彩中蕴藏着对此地此身的微妙感受,一深一白,一重一轻,一沉一浮,此身若鸥之随水,扁舟浮江伴残生,尽在这一“深”一“白”之中。而远处,淡淡青色的松竹既是视觉直感,更是心中松竹之精神的写照,残生之内心浮动的渴望皆托外物之中。杜甫诗中的色彩词无论用在句首,还是句尾,都有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杜甫在色彩词的运用上敏锐地捕捉到与之相呼应的心理悸動,又有相照应的动词与之契合无间,将生命历程中的感受移于外物的描写中。杜诗对色彩词的运用出神入化,与整首诗歌形成浑融之美,而这种美只有通过对色得词的准确理解中才能发现其中蕴含的惊人之所在,如果等闲视之,很可能忽略作者对语言的独特创造之处。
三.虚词的使用凸现线索和丰富了意蕴
实词能够成就诗的情韵风神,而虚词则是诗歌的筋骨肌理,诗人很重视实词的运用,而虚词的巧妙运用也会让诗歌别开生面。杜甫在虚词的使用上开宋诗之先声,学杜者往往将诗歌写得骨力劲健。
虚词在杜诗中与诗句相互配合,增强了情感的表现力。杜诗中有时使用一两个虚词而使抒情恰到好处,有时又不惜笔墨多处使用。而多处使用的虚词既使行文思路清晰明朗,又巧妙地传达出作者情感的起伏变化。
作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虚词的使用上出神入化。多个虚词的使用形成一条情感线索,与实词的事件交相辉映,成就千古名篇。“剑外忽传出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下洛阳。”“忽、初、却、漫,须、好、即、便”连用八个虚词,加快了喜悦的节奏。将平定叛乱收复失地的惊喜融入字里行间。开头“忽”字突出喜讯的突如其来,所以“初闻”便因喜悦至极而涕泪满衣,国事好久未闻,太平期盼殷切,“却”字一转折,意在心中的喜悦当与人分享,“漫”字又回到因喜生狂的情态,“须”字突出喜后决心的坚定,而“好”字将未来行程的艰难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喜悦,这是虚写,“即”“便”两字通过设想行程之快更将喜悦外移于回乡的路上。实词完成了事件的叙述,虚词将作者的情感从全诗中凸现出来,情感脉络清晰而强烈。虚词将平定叛乱收复失地引发的心理波动承担下来,增强全诗的表现力。多个虚词的运用,让诗歌形成两个领域,两个语意流,交相辉映,熠熠生辉。
杜诗在虚词的运用中,能充盈强大的力量感,赵翼赞叹“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两句时说:“东西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尽纳入两个虚词中,此何等神力!”杜诗中虚词运用灵活,有时候,杜甫会在句眼的位置大胆使用虚词,让虚词处于动词常处的位置,而从句意来看,虚词承担起动词的功能,这种语言的创造运用,让诗歌的诗味更浓。《春远》中:“肃肃花絮晚,菲菲红素轻。日长惟鸟雀,春远独柴荆。”其中“惟”、“独”字处于动词位置,虚词承担了动词的责任,虚词成为句眼。“惟”有仅仅之意,又有唯余之意,感慨良深,“独”既是一种状态,而且又有关闭之意。两个虚词,渲染出院落冷寂荒凉的氛围,暖阳日长,花红柳绿,景色虽美,春意渐之远,柴门独闭,惟剩雀鸣,沉痛之至,“惟”字,“独”字强烈而鲜明地传达出作者流离漂泊,感时伤世之悲概。
“新诗吟罢自长改”,杜甫诗歌在语言上的创造性运用,丰富了诗歌语言,也开拓了汉字的表现空间。就杜诗而言,用词的开拓增强词的活性,让杜甫诗歌更具表现力,形成自己沉郁顿挫的风格,“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参考文献
1.谢思炜.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06.01
2.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07.01
课题: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基于学习任务群的高中语文杜甫诗歌专题教学研究》课题(课题批准号:GS[2020]GHB2819)成果。
(作者单位:甘肃省庄浪县第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