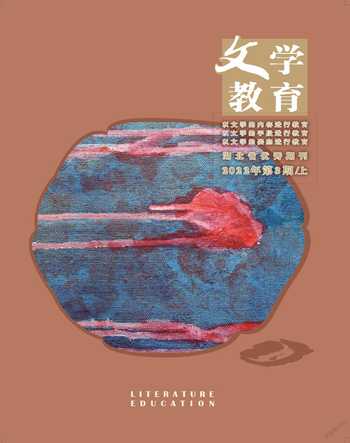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戏剧化教学”:高校课堂教学的一种新路径
内容摘要:“戏剧化教学”是将戏剧因素渗透于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教学方式。具有三个方面特征:其一,以“戏剧”元素导入教学情境。戏剧具有综合性、原创性、艺术性等多种功能,可与其他领域课程相结合,在跨学科语境中进行整体性教学,方能收获多样性、多效能的教学效果。其二,以“创意”表现作为教学理念。有赖于具有创新意识教师的教导,指引学生进行有计划、有层次、有程序的创意创作活动,从而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其三,以“健康”人格作为教学目标。将“审美”教育融入教学活动中,塑造学生超越的审美情怀以及自由高远的人生境界,培育“健康”人格形成。“戏剧化教学”模式的新探索,将成为高校课堂教学的一种新路径,使教学方式更为多元化,能够真正实现教学的预期目标。
关键词:戏剧化教学 创意发现 审美功能 艺术情境
所谓“戏剧化教学”,是指将戏剧或剧场的元素融入教学活动的一种方法,即注重运用戏剧与剧场的技巧(包括声音、行为、服装、音乐、影像、灯光等舞台空间因素),注重课堂中学生的表演与实践成分,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中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运用戏剧的表现手段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戏剧化教学”是将戏剧因素渗透于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种教学方式,它是戏剧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即运用戏剧或剧场的形式进行具有创意性的、审美化的、艺术化的教学活动。其通过“文本-表演”或“理论-实践”双向螺旋式的,自由的、自发的、创作性的实践,既包含有文本的阅读活动、理论的阐释过程,又有表演与实践等戏剧性的活动在其中,以此促进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沟通,丰富现有的课堂教学方法,有利于全面和谐发展人才的培養,从而达到戏剧与教学科目的教育目标。
“戏剧化教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反有着深厚的根基。学界对此有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研究,也有着较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美国戏剧教育学家先锋温妮弗列德·瓦德首先提出“创作性戏剧”概念,他在1930年出版《创作性的戏剧活动》一书中提出“创作性戏剧教学方法”;瓦德的创作性戏剧技术所采用的创作性教学方法具有“剧场”与“戏剧”的二元性。[1]瓦德将这种戏剧性的活动在课堂教学内容中进行了实践,包括:“戏剧性的扮演”、“故事戏剧化”、“以创作性之扮演扩展到正式的戏剧”、“运用创作性戏剧技术于正式的演出”[2]四大项目。其后,英国的芬蕾·琼森开始采用“戏剧化教学”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实践。在瓦德师生共同努力下,创作性戏剧活动对美国教育产生深远影响,许多大学或学院纷纷将其纳入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儿童教育的研究计划并培养教学师资。1959年,美国已有92所院校提供创作性戏剧活动的教学课程。2000年左右,“教育戏剧”(此名称是“创作性戏剧”的英国版本,英文Drama-In-Education,简称D-I-E,是一种重过程且以即兴创作为主的戏剧活动)在我国港、台地区发展较迅速;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出现教育戏剧相关文献;近年来与戏剧教育相关研究课题与论文逐渐丰富。台湾教育专家张晓华《创作性戏剧教学原理与实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林玫君《创造性戏剧理论与实务》(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年),林玫君、林珮如译Barbara Salisbury Wills《创作性儿童戏剧进阶——教室中的表演艺术课程》(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等著作,成为教育戏剧/戏剧化教学法推广的重要文献。一直以来,戏剧教育较多应用于儿童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中;近年来,有学者提倡将“‘戏剧教学法’运用于我国的高校课堂教学,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语言类课程教学中”,[3]以此作出探索性研究。这些都是“戏剧化教学”多元化呈现方式。但国内的戏剧教育更多还是停留在传统专业艺术教育层面,对戏剧所具有的强大艺术、教育功能重视稍嫌不足,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缺少理论性指导与研究,并且在实践层面应用较少,妨碍戏剧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旨在以自我在高校文学课程中的教学实践出发,探讨“戏剧化教学”具有的三重特征:即以“戏剧”元素导入教学情境、以“创意”表现作为教学理念、以“健康”人格作为教学目标。期待通过对此的探讨与实践研究,更多发挥戏剧教育强大功用,期待在深化素质教育与高校课程深化改革方面起到更为宽广作用。
其一,以“戏剧”元素导入教学情境。
中西戏剧戏曲经典是宝贵的精神遗存,为振奋民族精神、消解社会焦虑、净化人类心灵、提高国民素质起到重要作用。自古希腊时代欧洲戏剧艺术开始,产生诸多令人回味的经典戏剧。如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莎士比亚与人文主义戏剧,莫里哀与古典主义戏剧,伏尔泰、狄德罗与启蒙主义戏剧,雨果与浪漫主义戏剧,易卜生与现实主义戏剧,左拉与自然主义戏剧,王尔德与唯美主义戏剧,斯特林堡、奥尼尔与表现主义戏剧,梅特林克与象征主义戏剧,布莱希特与史诗戏剧,安托南·阿尔托与残酷戏剧,贝克特与荒诞派戏剧等。在中国,从关汉卿到汤显祖,从田汉、洪深到老舍、曹禺,一代代戏剧大师的天才创造,为人类留下灿烂的文化遗存。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戏剧教育一定能够发挥其独特的、难以替代的功能。戏剧作为一门综合的艺术,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在文学内部的意义上的,一个是在文学与艺术的跨学科意义上的。”[4]我们经常所谈的是作为剧本的戏剧文学,而非“融音乐、歌唱、表演、武术、舞蹈与造型艺术于一身的戏剧”。[5]我们可以与作为书页上文字的戏剧剧本邂逅,也可以到剧院去观看现场的戏剧演出,戏剧演出是几种艺术协作的产物——文本、演员、舞台布景、服装和灯光。文本可以重复,但是演出却不能——我们会在真实的时间流逝中欣赏剧场的艺术,回应它给我们带来的感官、情感和思维的多重刺激,并且下意识的将这些刺激拼接成一个整体的形象。文本可以调动我们的思维和情感,剧场里的演出则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然后再通过感官刺激到达人体的思维和情感。“戏剧化教学”意在兼顾这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让学生领悟到戏剧剧本文字的魅力,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利用戏剧或剧场的技巧,将之运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之中去,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创造力。
戏剧的功能多样化,用于教学形式的戏剧可兼具多样性。台湾学者张晓华认为,戏剧是一种“‘艺术与人文’的统整教学模式”,[6]因为“戏剧的表演就是将戏剧所含括的要素对观众的一种展演。其展演的型式是‘剧场’,其内涵则是包括了:景观的‘视觉艺术’,音韵的‘音乐’与‘舞蹈’,以及人物思想、语言、故事情节的‘人文’。可见,任何一出戏剧的展演,就是一种完整的‘艺术与人文’统整模式。”[7]恰如此言,戏剧具有综合性、原创性、艺术性等多种功能,既可作为单科戏剧门类进行教学,也可结合其他领域课程,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音乐、影视、舞蹈、心理学、教育学等,在跨学科的语境中进行整体性的教学,如此定能收获多样性、多效能的教学效果。在非戏剧类的课程教学中,可以有效利用戏剧艺术的优势,配合戏剧性的想象扮演等方式,以整体教学的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中历练、实践,以此强化学生的反应及接收能力,更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此过程中,教师可选择课程中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故事、某一个片断或某一个概念,设定一定的环境、人物、角色、道具或音乐等,让学生以角色扮演、演讲、朗诵、游戏或其他表演方式,进行即兴表现。如果在表演过程中,遇到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观点时,可以组织学生加强讨论,并鼓励学生搜集资料以及发挥此方面的创意;可以借助戏剧中的角色人物进行陈述,让学生在此表演、观看以及讨论的过程中,增强自我的表达能力,在讨论的过程中理解概念、提出问题并解决难题,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戏剧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可以以“即兴创作”的形式呈现,特别强调课堂活动中“即兴创作”的过程,参与者能够在此学习的过程中收获成长与快乐。课堂表演的地点当然更多地发生在“教室”,时间则以“上课”时间为主,使用的“道具”可以是教室随手可得的实物或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等。教师在每次课堂可以设定一个主题,并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表演、操作实践等。在这些参与者中,他们既是课堂上进行表演的学生(即表演者),同时也是制作者、策划者以及台下的观众,兼顾多样性的角色,并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中收获不同的感悟。
戏剧的魅力在于它的趣味与审美,若是将此元素渗透进课堂教学,将会其乐无穷。戏剧所蕴涵的各式各样的符号,包括人物的服装、形体、动作,以及所传达的表情、情感、意绪的多面性、复杂性等方面,都可以给予学生以超越于现实生活的审美情境,让他们的心理机能活动最大限度被调动起来,从而增强对情感和审美韵味的直觉把握能力。学生在对戏剧作品的欣赏中,通过戏剧艺术作品的情感体验,会产生精神震憾,获得审美享受,进而产生对人生的瞬间领悟,使心灵在震撼中受到陶冶、得到升华。以戏剧形式进行的教学活动,可极大地训练和提高学生的想象力与审美能力,可以通过有形式、有内容、有趣味的教学方式,来对学生的人格进行历炼。温妮弗列德·瓦德认为,采用戏剧方法教学的理由就在于:“‘趣味’就是为了它有趣!在教室的课程里,有比戏剧更有趣的吗?”[8]“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瓦德认为戏剧是一门最有具趣味的课程,那么,采用“戏剧”方式进行的教学活动,旨在一种趣味的学习过程来增进教育的效果。2015年秋季,我给全校本科生开设《西方经典戏剧赏析与表演》选修课,有一百名学生选修此课。我将学生分成十组,每一组组成一个戏剧表演团队,每一个团队表演一部经典戏剧,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麥克白》,莫里哀的《伪君子》,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建筑师》,王尔德的《莎乐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剧作。于此,将戏剧表演穿插于课堂讲授中,表演完后同学们谈各自对于剧本、表演的感想,有的同学第一次深入地接触戏剧,有的同学第一次上台进行戏剧表演,同学们的热情高涨且收获颇丰,课后每一位同学都写作有戏剧演出有感想。在这样的表演与训练的环节中,学生在扮演角色中进行艺术的构思,一方面会对戏剧的文本资料进行理性地思考与分析,一方面他们要展开想象的翅膀,赋予所扮演角色以丰富、完整、独特的灵魂。此种教学的过程,极大调动学生的心理、情感、生命活动,以及有利地发挥他们的各种潜能,并最大限度地激发创作想象力。因此,将“戏剧”元素融入教学情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其二,以“创意”表现作为教学理念。
提到“创意”一词,不得不提及“创造性戏剧(Creative Drama)”[9](也称为“创作性戏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欧美的戏剧及一般教学中。创造性戏剧“是一种即席、非表演,且以过程为主的戏剧形式。其中,由一位‘领导者’带领一群团体,运用‘假装’的游戏本能,共同去想像、体验,且反省人类的生活经验。”[10]台湾学者林玫君认为,创造性戏剧要“在自然开放的教室气氛下,透过肢体律动、五官认知、即席默剧及对话等戏剧形式,让参与者运用自己的身体与声音去传达或解决故事人物或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与情境,进而建立自信、发挥创意、综合思考且融入团体,成为一个自由创造者、问题的解决者、经验的统合者及社会的参与者。”[11]于此,创造性戏剧是一种自发性、即性式、团体性、戏剧扮演、游戏形式的活动,组成人员包含一位引导者及团体,内容包括即席的故事或意象,地点可以选择在教室或其他地方进行,观众既是参与者又是表演者。这种戏剧教学的活动,着重强调的是参与者的自信、创意、思考与自由地发挥等等,即具有只重参与过程而不重结果的特色。此“创作性戏剧”的教学活动,是一种“有结构的创意教学”,[12]而我们谈论的“戏剧化教学”之核心理念便在于此——有计划、有程序、有创意的教学活动。美国戏剧教育家安·维欧娜说:“创作性戏剧系让儿童在赋想象力教师或领导者的引导下,创造场景或戏剧,再以即兴的对话与动作表演之。”[13]此言之“创造场景或戏剧”、“即兴的对话与动作表演”,都包含有即兴“创意”的成分在其中。
如何充分发挥“戏剧化教学”之“创意”效果?首先有赖于具有“创意”意识教师的引导。引导者(即教师)须具有“创意”的意识,体现在其对教学活动的安排中,首先必须有完整的教学计划与结构,并选择适宜的课程内容主题,按程序来进行有计划、有层次、有效果的“创意”。同时,教师不可全部依赖临时的即兴表演与创作,而须按照所设计的内容,在课前激发起学习者本能的思考与创作,在课中进行逻辑的推理与发展,才不致于让正在进行中的教学活动偏离主题。作为引导者的教师而言,若能在既定的计划中进行有组织、有结构的程序性教学,就可专注于“创意”教学的应用,让学习者在创作的经验中获得更多的感悟。这就要求“戏剧化教学”活动中,教师有计划、有秩序、有创意的进行课堂教学。这样的教学活动并不是一蹴而就,需要长期摸索以及双方长时间配合,方能有效进行。如在《西方经典戏剧赏析与表演》开课伊始,充分让学生了解西方戏剧课程内容,使之产生浓厚兴趣,并将课程表演及讲授计划告知学生,让他们有充分时间认真准备课堂戏剧表演内容,这样师生才能有优秀的表现。且在戏剧表演及安排的各项问题中,教师也应引导学生间的互动合作、灵感碰撞,从发现问题、界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酝酿、灵感与执行的过程中,开创出新的形式、新的观点、新的思维,从不了解、不重视、不关心,经过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鼓励,发现新的动能、认知与自信。学生们在此戏剧表演过程中,从选择角色为自己定位,到肯定自我的表现再到开发出内在的潜能,他们经历这样一个系列的过程;对于引导者而言,不时激励学生对于未来的创造力,不论在流畅力、独创力、判断力、思考力、表现力上,他们都将会得到很大改进,并且影响他们对其他事情的处理与应对的策略。表演结束后,参与表演的同学往往都会谈谈感想,并与观众形成对话,课程结束后写成总结性论文,将课程内容作了进一步延伸并提出可资改善的建议。
于此,在课前、课中、课后一系列活动中,每一个环节都贯穿“创意”教学的理念;从引导者到参与者,都旨在激发他们内在的激情与创新力。此具有“创意”的创作性活动,带来的是活泼、生动、高尚的教学应用,使学生从内到外表现自我,并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合作,而让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形成一种良好关系,促成一种新的交流经验,从而促进双方共同成长,即学生的与教师的自我成长。“戏剧化教学”就是要将“创意”理念贯穿始终,并落实到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方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
其三,以“健康”人格作为教学目标。
教育学者张建兴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在培养受教者健全的人格。”[14]戏剧艺术教育旨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艺术素养”,“施教者与受教者相互融合、共同努力,提高广大受教者的戏剧审美能力,即对戏剧艺术的感受能力、创造能力及鉴赏能力,使受教者的人生观念、行为方式、心智能力都得到培育,从而实现对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塑造。”[15]“戏剧化教学”目标就是要“提高广大受教者的戏剧审美能力”,“实现对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塑造”,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艺术素养”。它作为教育教学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采取自我表达、感情融入、启发智能、治疗技巧、社会活动与艺术形态等方式,进行自发式、自主性的学习与交流,且注重戏剧活动的经验、团体意识的培养、学员之间的合作交流、团队个体素质的提升以及创造创新能力的实现,并且能够在相互启发、合作、讨论以及不断回馈中形成新的理念,提升新的兴趣,创造新的奇迹。于此,“戏剧化教学”对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培育,可以获得更为多样化、更为充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对于学生的个人兴趣、态度、智能、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自我意識、行为模式、感情模式等方面均有极大助益。
“戏剧化教学”蕴涵丰富能量,特别是戏剧艺术史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教育内容,对于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起着重要作用。戏剧(剧场)艺术的功用旨在“协助孩子们认识及了解自我是一个生物的个体”,“帮助孩子认识及了解自己是一个创造性个体”,“帮助孩子把自己设想为经验的整合者”,“帮助孩子把自己当成一个能够深思熟虑的个体”,“帮助孩子了解自己是社团的一份子”。[16]戏剧艺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我、整合自我,帮助个体健康成长并融入到团体之中,从而全面提升自我的素质,可见戏剧艺术对于个体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历代经典戏剧作家在其戏剧作品中表现了对人世间真、善、美的追求,如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表现的是对人与人之间真诚关系的显露,对人的美好品质的赞美,对人文理想境界的表现等。莎士比亚在最负盛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莱特》中,丹麦王子哈姆莱特赞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7]剧作家借哈姆莱特之口,把人类的力量提升到“天神”、“天使”的高度,表现出浓郁的人文主义理想。说明哈姆莱特是一个怀抱理想的人文主义者,把父亲看成圣明的君主,把母亲乔特鲁德看作贤淑的圣女,把父母的关系看作天地和谐之象征,把建立在这种和谐关系之上的世界看作是“美好的大花园”,他也一直在这样美好的幻想与现实中茁壮成长,直到其父亲被叔父克劳狄斯陷害而去世。19世纪北欧的戏剧作家易卜生在戏剧作品中所表现的,正是要建构一种高贵自由的新人格,建立一个和谐民主的新社会,建设一种繁荣昌盛的新文化。1885年6月14日,易卜生《在对特隆赫姆市工人的讲话》中提出:“一种高贵的质素必须进入我们的民族生命中,进入我们的行政管理、代表机构和新闻媒体中。”[18]他如此解释:“我这里说的‘高贵’不是出身上的高贵、财产上的富贵,也不是知识、能力和才华上的高雅,而是性格、意志和精神上的高贵。”[19]他希望,“这种高贵质素将从两种资源进入我们民族之中。这两种还没有被党派竞争的压力损害得无可挽救的资源,就是我们的妇女和我们的工人。”[20]因而,其一生最为美好愿景便是“实现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自由和高贵,就是我所希望、我所期待的未来图景;为此我一直在尽力工作,并将继续付出我整个的一生。”[21]易卜生在较早时期更多关注社会现实,以至写出众多反映社会问题剧作,如《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但是他后来越来越认识到个人的自由与高贵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因而在后期戏剧创作中更多展现人物内在灵魂的波动,更能够引起读者与观众的共鸣。易卜生众多戏剧透视人性内在生命的深刻体验,拓展人们对于自身人性结构与生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重塑人类全新的、高贵的灵魂,从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优秀的戏剧艺术作品总是能引导人们对生活采取正确的态度,并着力于净化人们的心灵,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将人类的精神引向更为高尚的境界。因此,戏剧艺术教育对于“全面和谐发展人的塑造”是相当必要的。
“戏剧化教学”的运用,能够引导人类精神走向更为崇高、更为超越、更为自由的审美情境。学者董志强认为:“对任何一种生命活动作深层的存在论考察,都必将触及审美问题;同时,也只有触及审美层面,某种生命活动的本质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澄清。”[22]更何况是与艺术教育紧密联系的教学活动呢?英国学者爱德华·戈登·克雷在《论剧场艺术》中认为,“剧场既给人以教育,又给人以娱乐。我们还看到,有时这两者同时并进;简单说吧,当剧场的演出是最高尚的和最美的时候,它既给人以教育,也给人以娱乐。”[23]于此,戈登·克雷认为剧场既能给人以教育的功能,也能给人娱乐的功能,而且它能达到艺术欣赏的目的,其最高境界便是“高尚”与“美”;人们在高雅的剧场艺术中,在愉悦身心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最崇高”与“最美”的艺术情境,此为戏剧艺术教育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学者杨恩寰如此肯定艺术教育的审美功能:“艺术教育以其自由、超越的审美快乐使人们的情欲受到规范、节制和净化,从而陶冶和塑造人们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赋予人们一种超脱精神,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24]“超越的审美情怀和自由造型的艺术技巧,是构成生活、事业审美化、艺术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而艺术教育恰是培育这两个因素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方式。”[25]诚如此言,“戏剧化教学”可以实现两个方面审美功能:一是“超越的审美情怀”,二是“自由造型的艺术技巧”。它能使学习者在戏剧的艺术活动中体验到各种色彩、图像、声音、旋律、姿态、表情、动作等的美感,由此建立起一定的审美体验、审美感悟、审美情感等,并深切认识到现实生活、艺术文化与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懂得欣赏艺术、欣赏自我、欣赏他人、欣赏自然、欣赏社会,并对艺术、创作、人类、未来等能够自由表达自我的见解,以此建立自我的价值观、世界观与审美观等。学者滕守尧认为当今社会需要培养“开放型的精英”,“就是不仅具有一技之长,而且能将各种不同的知识、观点、视点吸纳,具有通感能力,从而使自己胸怀不断开阔,使自己的感情不断丰富,使自己的思想和境界不为向完美的高峰攀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的人,也是一个具有高级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感觉的人。”[26]此处的“开放”是与“闭塞”、“狭隘”、“狭小”相对,指胸怀开阔、情感丰富、思想深隧、境界高远的人,是“具有高级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感觉的人”。文化与艺术是让人感觉美好的东西,而艺术可以通过自身的完美使人不断地趋向完美,通过良好的艺术教育可以产生趋向完美的“开放型的精英”。于此,我们的期待便是在高校课堂采取“戏剧化教学”方式,充分发挥戏剧艺术教育的功能,使学生在身体素质、心理能力、文化修养与审美趣味等方面大大提高,以此打造具有高级人文素养和审美感觉的全面发展的人,从而提升整个民族的素质。
相信“戏剧化教学”模式的新探索,必将成为高校课堂教学的一种新路径,使教学的方式更为多元化,能够真正实现教学的预期目标。其一,将“戏剧”元素导入到教学情境中,与其他学科课程相融合,在跨学科语境中进行整体性教学;其二,将“创意”概念融入教学活动中,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有计划开展创造性戏剧活动;其三,将“审美”意识融入教学理念中,塑造学生超越的审美情怀以及自由旷达的人生境界,以此培育“健康”人格。以“戏剧艺术”作为媒介手段,以“创意发现”作为教学理念,以培养健康、和谐、全面发展且具有“审美情怀”的人才作为教学目标,此三方面构成“戏剧化教学”主要特征。我们共同期待“戏剧化教学”在学校教育乃至大众教育中发挥更多、更好作用,并广泛应用于多层次、多学科的教学领域!
注 释
[1]Richard Courtney, Play Drama and Thought.4th ed.Toronto:Simon & Pierre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89,p.28.
[2]张晓华:《创作性戏剧教学原理与实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3]黄爱华:《“戏剧教学法”及其对我国高校文学语言类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意义》,《美育学刊》2014年第5期。
[4][5]《比较文学概论》编写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68页。
[6][7]张晓华:《台湾中小学表演艺术戏剧教学的解析》,《教育学报》2014年第1期,第64页。
[8]Winifred Ward,Storiesto Dramatize.New Orleans:Anchorage Press,1981,p.2.
[9]“创造性戏剧(Creative Drama)”在美国,早期有些人称它为“非正式戏剧”(Informal Drama)、“创造性表演”(Creative Play Acting)或“创造性戏剧术”(Creative Dramatics)。近年来,也有人称它为“即席创作”(Improvisation)或“过程性戏剧”(Process Drama)。在加拿大及纽西兰,“发展性戏剧”(Developmental Drama)或“教育性戏剧”(Educational Drama)是比较常用的名词。在英国,这类被应用于教育上的戏剧活动被称为“教育戏剧”;当它以剧场的形态出现时,就被称为“教育剧坊”或“教习剧场”(Theatre-In-Education,TIE)。部分内容参见林玫君:《创造性戏剧理论与实务》。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年。
[10][11]转引自林玫君:《创造性戏剧理论与实务》,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12][13]转引自张晓华:《创作性戏剧教学原理与实作》,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14]张建兴:《群育的教育》,《教育与人生》,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第21页。
[15]雒社扬、杨戈:《戏剧艺术教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16]Barbara Salisbury Wills:《创作性儿童戏剧进阶——教室中的表演艺术课程》,林玫君、林珮如译,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4页。
[17][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朱生豪等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27-128页。
[18][19][20][21][挪威]亨利克·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22]董志强:《试论艺术与审美的差异》,《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8页。
[23][英]爱德华·戈登·克雷(Craig,E.G.):《论剧场艺术》,李醒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69页。
[24][25]杨恩寰:《艺术教育丛书》“丛书总序”,雒社扬、杨戈:《戏剧艺术教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26]滕守尧:《回归生态的艺术教育》,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本文为2021年湖北高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师范类文学专业戏剧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251)、三峡大学教学研究一般项目《师范类文学专业戏剧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J2021032)、三峡大学研究生教研重点项目《地方高校文科类研究生科研能力多元协同培养的探索》(项目编号:SDYJ202104)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杜雪琴,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