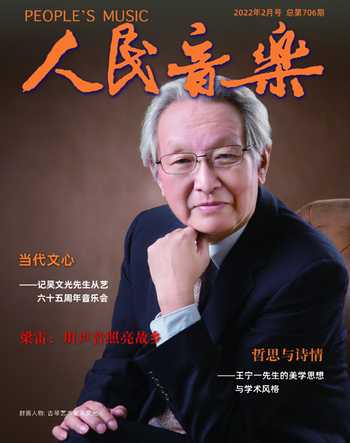论湖北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的经典性
北省歌剧舞剧院(原湖北省实验歌剧团)20世纪50年代末创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以下简称《洪》剧)已走过六十余个春秋,经过数代《洪》剧人的努力,现已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这些年兴起的经典民族歌剧复排热,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复排热”中,也出现了一些无边界改写等亟待重视的问题,其中尤以国家大剧院对《洪》剧的改编具有话题性。值得深思的是,《洪》剧等民族歌剧为什么能称为经典?经典何以形成?经典的内在要素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當代人应以怎样的姿态守护经典?理论界目前还缺乏思考。如果不从理论上反思,势必影响经典的传承,影响对这些经典的认识和理解,影响音乐历史的书写。
一、湖北《洪》剧的经典化建构
一部作品要成为经典,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淘洗,能够在历史的隧道中穿行站稳且历久弥新,达到经典的传世性,这是经典形成的历史机制。只有如此这般,被赋予“历史化”的价值内涵的作品才能被称为经典。
连绵不绝的演出和接受史是音乐经典形成的另一动态机制,传播力与影响力是衡量经典的重要依据。再伟大的作品若缺乏舞台表现,产生不了影响力也是难以成为经典的。1959年,《洪》剧由湖北省实验歌剧团创作完成,当年即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晋京演出,以其引人入胜的剧情、强烈的戏剧冲突、鲜明的角色性格和丰富且富于张力的地域特色音乐,一炮打响获得巨大成功。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评价:“‘洪湖水浪打浪’是一首难得的革命抒情歌曲。”至“文革”爆发前的六年时间,仅湖北实验歌剧团便创下了演出八百多场的记录。与此同时,包括中央歌剧院、原总政歌剧团等国家级和多个省市音乐院团等纷纷排演《洪》剧,多个地方戏曲剧团将《洪》剧移植成了京剧、豫剧、黄梅剧等,全国各地形成“处处洪湖水,人人浪打浪”的奇景。1961年,经贺龙元帅提议,歌剧被拍成同名歌剧电影,通过银幕广为传播,影响力得到巨大提升。1966年“文革”爆发,《洪》剧因“宣传贺龙”被封禁。1977年后又掀起了一波《洪》剧传播高潮。除“文革”中被禁演外,自1959年至今,仅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已上演三千多场,创下中国民族歌剧的演出记录,且当下仍然在全国各地频繁上演。如果算上其他演出团体的演出和移植,就更是不计其数。湖北省歌舞剧院已经历王玉珍、李祝华、刘丹丽、马娅琴四代韩英扮演者,夏奎斌、卢向荣、秦德松三代刘闯扮演者,从代际传承的角度看,也完成了经典的建构。
学术阐释也是塑造经典的重要力量。当年,《洪》剧晋京演出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中以作曲家王震亚先生的文章具有代表性:“由这部歌剧的音乐可以看出作曲家深入地研究了当地的民间音乐,相当熟悉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全剧的音乐稳固的建筑在一个地区的民间音乐基础之上,作曲家又根据戏的需要创造性发展了民间音乐。”“监狱一场韩英的大段独唱,显然是按照戏曲音乐中慢板与原板结合式的腔调写的,在民歌与民间小戏中很难设想有发展到如此水平的戏曲式的慢板, 作曲家用戏曲音乐的手法提高了民间音乐原有的表现。”可以看出创作者既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又大胆创造与革新的智慧。随后的岁月中,研究、评论《洪》剧的文章不断涌现,检索中国知网,达三百余篇之多,形成连绵不绝的评论、阐释史。在居其宏先生看来,自《白毛女》等掀起我国歌剧的第一次高潮以来,“《洪湖赤卫队》的创演成功无可争议地成为第二次高潮的第一座潮峰,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高度统一的创作成就,在我国歌剧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譺?訛
几十年来,《洪》剧中的《洪湖水浪打浪》《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小曲好唱口难开》《大雁南飞》《这一仗打得真漂亮》等唱段久唱不衰,《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成为音乐会和声乐比赛的常客,《洪湖水浪打浪》进入中小学音乐教材。因其卓越性,湖北《洪》剧1962年获得首届电影“百花奖”音乐奖,1993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21年入选《百部优秀剧作典藏》。如上述种种,湖北《洪》剧已满足经典形成的必要充分条件。
二、湖北《洪》剧的音乐文化信息
经典必定携带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信息。就音乐而言,湖北《洪》剧的核心文化信息就是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歌剧广泛借鉴天沔地区的楚剧、花鼓戏、民间小调等,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得作品在歌剧的总体框架中充满浓浓的洪湖味。正如作者张敬安先生(1925—2003)所说:“洪湖赤卫队的音乐创作,我们是以天沔花鼓戏曲音乐和天门、沔阳(洪湖原属沔阳县)潜江,即襄河一带的民间音乐作为主要依据的,在创作中同时也吸收黄陂、孝感乃至于外地的音乐素材。在这部歌剧里,我们具体运用了天沔花鼓戏中的高腔(又名骷髅腔)、高悲腔、沔阳渔鼓、三棒鼓、小曲和许多民歌。”
通过以下图表可以看出《洪》剧的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关系。
此外,合唱《保卫苏维埃、保卫家乡》《赤卫队歌》、彭霸天《石板栽花无根底》等都与当地的民间小调、戏曲、说唱以及当地语言的声韵、语调密切相关。地方特色是这部作品携带的最重要的音乐文化信息,也是被广为认可和赞誉的关键要素,是能够成为经典的基石。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寄予在经典所构建的世界中,湖北《洪》剧的地方性塑造了一种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其蕴含的思想倾向、价值立场、历史图景保证其始终能够维持自己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洪》剧的音乐就是一种心灵图腾,其久演不衰的历史树立了一座文化丰碑。
三、国家大剧院版《洪》剧的去地方性改写
一般来说,复排经典歌剧,在表演、舞美、布景等方面是有较为充裕的创新空间的,音乐则极少进行大动干戈的改动。遗憾的是,国家大剧院2012年以经典之名复排的这部歌剧,对原作的音乐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除韩母的《千支树丫一条根》、合唱《赤卫队歌》、老幺的《六月荷花满池香》、小红的《小曲好唱口难开》等少量唱段基本保持原貌外,大部分唱段,包括广为人知的经典唱段《洪湖水浪打浪》《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大雁南飞》等都被做了大幅改动。乐队部分更是全新的创作,原作的序曲完全不见踪影,很多统一全曲的主要腔型、重要动机都被抹掉,和声、音型、节奏、配器等几乎全部另起炉灶。如果说湖北《洪》剧以地方性取胜的话,那么国家大剧院版则朝着交响化、去地方性的方向努力,对其中蕴含的、具有基石性的文化信息给予了极大淡化,进行了朝向西方大歌剧式的改造。
笔者列举几例:
1.歌剧中刘闯是一个勇猛刚强,且有些鲁莽的基层指挥员,原作为其设计了一个刚劲有力、冲动性的刘闯动机,四、五、八度的音程大跳,富于动力性的小附点和带重音的三连音节奏,与角色的性格完美契合。
国家大剧院版中,最能显示刘闯性格的这一主题渺无踪影。在歌剧复排的历史中,将主要角色的核心动机直接删除的做法是极为罕见的。
改编者根据刘闯的独唱《狂风吹不落太阳》新创作了一个统一全剧的动机,但這个动机缺乏刘闯唱段的大气豪放,尽显抒情柔美,甚至带有一点忧郁,与角色性格格格不入。
2.《洪湖水浪打浪》是《洪》剧最具标志性的抒情歌曲,这是老一辈作曲家以江汉平原民歌《襄河谣》为素材创作的,饱含浓郁的地方韵味。国家大剧院版在第三场第三曲的女声合唱中对原作的基本旋律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以至于这个最为大众熟知,曾得到周总理高度赞誉,已进入中小学音乐教材的经典唱段被改得面目全非,原有的风味荡然无存。
3.再看《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首长大的咏叹调借鉴了天沔花鼓戏的高腔、悲腔等板腔体音乐,特别是韩母部分更是以徵调为基础的典型悲腔,以浓浓的戏曲味表现了韩母的悲愤之情。
国家大剧院版对原版的旋律、节奏均作了大幅改动,原版最具特色和基础性的徵调式不见踪影。我想改编者对这一地区的花鼓戏特别是悲腔并不了解,改编时应该也没有想过保留原曲的基本形态。改为商调式,直接导致原有的悲腔韵味荡然无存,原版激愤的戏剧张力也被大大削弱。
4.《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是新中国成立后歌剧创作中首次运用男声表演唱的典范,幽默诙谐,充满自豪与快乐,旋律依照洪湖地方语调依字行腔,特别是“他喊又不敢喊犟又不敢犟”这句活脱脱就是当地语言声调的音乐化。国家大剧院版除第三段反复基本保持原貌外,其余大部分都改成了普通话基础上的朗诵,极大动摇了原作的歌唱性,失去了原版幽默诙谐的趣味和感染力,地方韵味更是无从谈起。
5.谱例4是刘闯独唱《大雁南飞》前的女声合唱,原版的“风吹芦苇沙沙响”的“响”字和“心随波涛到远方”的“远”字,在落音上站住后,又在上方四度或三度音上做了一个三连音的润腔,再回到落音,类似于补充终止,这是典型的天沔花鼓戏的润腔,原版有很多类似处理。国家大剧院版将这段合唱进行了重大改写(见谱例5),尤为可惜的是,将上述独具特色的润腔方式抹去了,以直音的方式落句,去除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文化信息。再如“新潮翻卷恰似洪湖千里浪”中的“浪”,一个长大的具有戏曲韵味的拖腔,千回百转,绵柔不绝,使歌唱获得了更多的余味,深化了情感的表达。国家大剧院版中,这个拖腔被改成了直音,原有的戏曲味道和文化信息被抹掉了,原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被改造了,更接近一般的群众合唱。
国家大剧院版中类似的改动还有很多,其改动之大已远远超出我们对复排的想象,作为经典的《洪》剧事实上已被消解。
四、作为历史文本的经典与当下
经典,在历史的长河中应保持怎样的风貌?经典如何与当下及未来进行对话?如何保持其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张力?
有一种声音认为,对这部歌剧进行改写的正当性在于,要使其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这里隐含着这样一种态度:这部歌剧过时了!真的是这样吗?
经典作为历史文献,一定是过去的文本,它孕育在历史之中,饱含着历史的意蕴和核心文化价值,体现的是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作为经典的音乐文本已具有音乐文物的意义。然而,“过去”并不意味着“过时”。对于经典来说,保持恒久性与稳定性则是核心命意。“在一个更开放的历史空间中,释放出超越(过去)历史的意义张力。历史性价值是一种生成性力量,它从作品诞生的时代开始启动,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历史地蕴藉。”湖北《洪》剧历经六十余载,强大的穿透力使其始终保持鲜活的存在,在与当代的对话中,其意义不断生成,构成生生不息的意义张力。对于当代人,湖北《洪》剧始终具有一种新奇而又熟悉的特质,这种特质正是吸引观众走入剧场的原因之一。对于有经验的观众而言,他们仍然期待欣赏其间的文化意蕴。想当然地认为《洪》剧已经过时是一个假命题,所谓当代人的审美习惯,其实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任何时代的审美趣味一定是多元的,并不存在某种固化的、单一的审美习惯。假如真有所谓统一的当代人的口味的话,《红楼梦》《骆驼祥子》等经典文学作品的文本是否也需要做符合现代审美的改写?如果歌剧经典都需要根据想象出来的现代人的口味对音乐文本加以变动的话,更早的蒙特威尔第、莫扎特等人的歌剧岂不是更需要大动干戈的音乐改动?事实上,对于上述文学经典和歌剧经典,历代的人们都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和敬畏。所以,试图用一种想象中的高级写法去改造历史文献,也就是湖北《洪》剧注定劳而无功,理论上缺乏合法性,实践上也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
“真正伟大的经典之作,它丰富的内涵品格必然能够在每个时代进行当下性转化。所以,经典作品是不会在一个遥远的时代中被生活疏离的。”何以如此?那是因为我们本身具有历史性理解的能力,我们自会以历史的眼光观察、体悟、欣赏经典。欣赏蒙特威尔第的《奥菲欧》,会带有“这是巴洛克早期歌剧”的前见;欣赏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会带有“这是晚期浪漫派作品”的前见;聆听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里桑德》,会带有“这是印象主义作品”的前见。这种前见本身即属于历史的眼光,欣赏者的审美感受与作品的历史意义形成视域融合,作品意义的当下性转化得以形成。通常,我们不会用欣赏当代歌剧的眼光去要求历史作品。否则,听惯了瓦格纳的歌剧又如何去聆听蒙特威尔第的歌剧?难道也要把蒙特威尔第的那些相对简陋的歌剧改造成瓦格纳的样子吗?
的确,今天的创作者在写作歌剧时一般并不会向湖北《洪》剧一样追求直接而浓郁的地方戏曲韵味。六十多年了,眼界已大大扩展、创作手法愈加丰富。然而,这绝不应成为轻视这部经典的理由。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hn,1922—1996)认为艺术有历史而科学没有历史。说的是在科学研究中,新的理论范式往往意味着对旧范式的颠覆与否定。艺术的发展则是一个不断积淀的过程,德彪西说要打倒贝多芬,并不是要否定贝多芬音乐的价值,他不会将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改造成印象主义的风格却仍冠以经典的名义。德彪西要做的是另辟蹊径,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勋伯格宣告解放不协和音,也并不意味着他对传统调性价值的否定。他同样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累加在一起就构成环环相扣的艺术史。每一部经典之作都能在历史的文化坐标中找到自身的位置,都能使这些“过去”的作品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中向当代以及未来展现出特有的启示性。
经典之为经典并非因其完美无缺,包括经典中的局限本身就构成经典的有机组成部分,局限也会给后人带来启示。这种启示性在于“经典的伟大性不在于它提供唯一的真理答案,而在于它启发人类保持对真理探求的历史活力”。
作为历史文本,经典还承载着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延续历史的传承,保证当下、未来与过去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其中还包括质疑的生成性力量。“经典最为伟大的力量之一还在于它能向我们及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发出质疑;同时也能在我们产生疑问时与我们对话回答。”?讀?訛而稳定性是其承担历史传承与对话乃至质疑的重要因素。这段话说得好:“对待莎士比亚的观念和态度因时而变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没有了莎士比亚,那整个沟通交流就是无法想象的。”?讁?訛“如果没有一个历史文本作为基础,也就无所谓历史性经典之作。”?輥?輮?訛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骆驼祥子》、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等均建立在一个稳定、确定的文本基础上。湖北《洪》剧的地方风味,无论是优点还是局限,已成为歌剧的生命甚至灵魂。对待《洪》剧的态度,可以因时而变,但一个稳定、具有原作意义的文本则是必须的。当《洪》剧在创造的名义下被重大改动时,作为经典的价值意涵就被阉割了,再被冠以经典的名义自然名不副实,也就无法在历史的进程中与当下以及未来展开有效对话。
进一步,湖北《洪》剧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经典的任意改动会对音乐史的认知与书写造成巨大的混乱。仅举一例:当国家大剧院版对最具标识性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旋律进行了重大改写的时候,造成的理解混乱可想而知,特别是对原版并不熟悉的青年人,很可能会误以为国家大剧院的《洪湖水浪打浪》即是原版,长此以往,以讹传讹,该剧作为经典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尤其是,相比于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国家大剧院平台高、影响大,又有现代网络的加持,长期以经典之名演出经过重大改动的《洪》剧,可以想象的结果是:若干年后,原版《洪》剧被人逐渐遗忘,观众会认为国家大剧院版就是经典,进而造成认知的混乱。
五、湖北《洪》剧的民族性与文化自信
对《洪》剧进行交响化、去地方性的改造显然是在用西方音乐的审美观念看待这一歌剧,没有意识到原版歌剧中弥足珍贵的精髓恰恰在于其地方风味。这显然是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自信的表现。对于文化的民族化,作家韩少功说过:“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輥?輯?訛《洪》剧诞生的那个时代,追求民族化是一种普遍、自觉的观念,包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民族管弦乐《春节序曲》等均体现了这种追求。《洪》剧的地方风味更是那个时代民族化的缩影。这一点,《洪》剧的作者有着很明确的自觉意识:“民族化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目标,立足于某一地域的民间音乐,方可为祖国歌剧艺术民族化贡献出一抹艳彩。”?輥?輰?訛“在追求民族化的创作实践中,如果不立足于某一个地域,或某一个民族,而是笼而统之地希望达到一种所谓民族音调,结果难免导致缺少特色的弊病 。”?輥?輱?訛湖北《洪》剧的音乐是在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对天沔地区的戏曲及民间音乐元素进行创新性发展。创作《洪》剧之前,湖北省歌剧团已经过多年的歌剧实验,但受制于“在楚剧的基础上发展新歌剧”这一理念的束缚,时时处处以楚剧常用的调式、节奏、旋法等作为歌剧创作基础,限制了创新。经过反思,主创人员摒弃了原来的理念,不再局限于楚剧,放眼江汉平原的戏曲、说唱、民歌等更广泛的民间音乐元素,根据歌剧的要求给以创造性的发展,通过《洪》剧的创作,闯出了一条民族歌剧的新路。从编剧到作曲,从脚本的语言到音乐的风韵,这部歌剧体现了极高的智慧。时至今日,我们依旧需要从中汲取营养。
歌剧中浓郁的地方风味,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已经很陌生了。缺乏生活的根基,缺乏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刻体悟与认知,是包括青年作曲家在内的音乐学子的普遍缺陷,他们的创作常常缺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根基,这种陌生恰恰是应该补上的一课。在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湖北《洪》剧的智慧理应烛照当下,起到塑造新时代文化价值观的作用。放眼世界,肖邦、李斯特、巴托克等无不深耕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切不可对自己的文化妄自菲薄,没有必要时时处处用西方歌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经典。深入民间,体悟民间音乐,深入理解这部歌剧的深层内涵和角色的性格特征,深入理解经典唱段的结构及情感推进逻辑,是这部歌剧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跳脱功利性的态度审看湖北《洪》剧才能更有效地理解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经典即历史,正如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来随意改造历史,也没有必要随意改造经典,讓我们共同保持谦卑的姿态,尊重经典,守护经典,赓续这部红色经典的血脉,由此达成历史自觉的文化根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歌剧重大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19ZD15,发表时有删节。)
何宽钊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