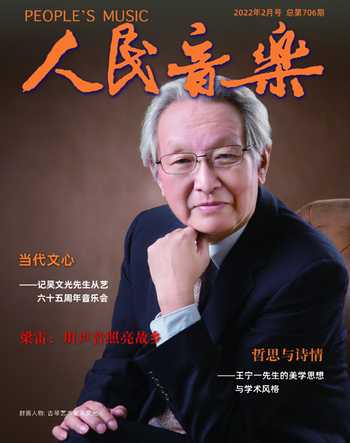古希腊“模仿论”· 荷马史诗·口头程式理论
兴创作(Improvisation)具有漫长的历史,荷马史诗就是即兴创作的产物。透过荷马史诗及20世纪关于“荷马问题”(Homeric problem)的讨论不难发现,古希腊、古罗马音乐中存在大量依赖某种固定程式进行即兴创作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前的欧洲音乐大多出自乐手和歌手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创作在那些古老的东方音乐中也普遍存在。由此可见,即兴创作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音乐生成方式,在人类早期音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类早期音乐活动中为何普遍存在即兴创作?这无疑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笔者发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荷马史诗以及20世纪围绕“荷马问题”提出的“口头程式理论”三者之间似乎存在一个解决问题的“证据链”。循着这条“证据链”,或许可以获得一些对人类早期音乐活动中即兴创作的认识。
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说起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奈特尔等人认为,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崩塌后,西方音乐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通过记忆模仿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即兴创作的方式留存下来的。①这似乎表明,古希腊音乐中存在即兴创作,并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么,两位哲人所论及的“模仿”与古希腊、古罗马音乐中的即兴创作方式有何关系呢?这里不妨对古希腊诗学理论的“模仿论”进行一番辨析。
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模仿论”,还得从“μιμησιζ”这个词说起。
柏拉图《理想国》中多次出现古希腊文“μιμησιζ”的变体形式。当代美国学者埃尔斯(Gerald F.Else)认为,在古希腊,“μιμησιζ”即“mimesis”(模仿,也作摹仿)至少有“模拟表演(Miming)”、“效仿活动(Imitation)”“复制活动(Replication)”三种含义。《理想国》第三卷中将“mimesis”用于对荷马史诗和音乐创作的描述,并将诗歌分为叙事和模仿两种形式。后来又将所有诗歌都归于模仿诗歌,并将该概念运用于绘画艺术,提出艺术起源的“模仿说”。柏拉图认为,“缪斯”作为文艺的总称是最具有模仿性的艺术,并且人们就是通过模仿将音乐的“节奏与调式”直接“浸入心灵”,在自己心中生根发芽,从而变得温文尔雅。从这个意义来讲,在柏拉图所说的“miming”并非机械模仿。这使我们意识到,柏拉图关于艺术源于由“神力凭附着”的言行——“模仿说”,有更深层的意蕴需要我们去挖掘。与柏拉图一样,在古希腊学者和戏剧家们的眼里,与“艺术创造”相关的就是“再现加表现”。
我们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学的言说中可以窥见古希腊戏剧表演中的模仿特征。柏拉图曾这样赞美史诗的表演,“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辞句,就像你自己解说荷马的那样,并非凭借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因为诗人制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他们各随所长,专做某一类诗,例如激昂的酒神歌,颂神诗,合唱歌,史诗,或短长格诗……”④显然,在柏拉图看来,诗人“解说荷马的本领”,就来自“神力的驱遣”下对神的“模仿”,尽管他极力否認这种“模仿”是“技艺”。
关于诗歌创作的来源问题,亚里士多德虽然反对柏拉图的“神附说”和“迷狂说”, 但却强调模仿艺术的合理性与积极作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模仿”作为“虚构”具有积极意义。⑤他认为模仿是人的天性,不仅使人获得“最初的知识”,还能给人以独特的快感。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drama”一词有“行动”与“扮演”之意,其中“行动”指模仿行为,而“扮演”则指模仿方式,并认为正是扮演“使戏剧在纯文本的层面外还有了舞台层面的含义,并由此发展为‘drama’”。亚里士多德的确将模仿的表现形式分为叙述(即“以本人的口吻讲述”)和扮演(即“表现行动和活动中的每一个人物”)两种,并认为悲剧的模仿方式是后者,且强调“诗人应该尽量少以自己的身份讲话”⑦。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及大部分双管箫乐、竖琴乐等,实际上都是模仿,只是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采取的对象不同,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声音、动作、语言、神态、音调都能成为模仿的对象。诗人之所以称之为诗人,是因为他们都是模仿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正如有人用色彩和形态模仿,展现许多速描形象,而另一些人则借助声音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一样,艺术都凭藉节奏、话语和音调进行模仿——或用其中的一种,或用一种以上混合。阿洛斯乐、竖琴乐以及其他具有类似潜力的器乐以用音调和节奏,而舞蹈的模仿只用节奏,不用音调。”⑧如果我们将亚里士多德这段话还原至古希腊戏剧、史诗表演语境中,即戏剧表现的是人对神的模仿,其中介或手段既包括以人声模仿神所用的方言(语言)和歌唱,也包括以乐器来模仿神的语言和歌声,如用风笛、排箫、阿夫洛斯管、竖琴来表现话语、节奏和音调,甚至弗里吉亚调式等。
但这种认识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原因正如人们所关注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没有提到与演技理论相关的只字片语”,在谈到演员的动作、言语时都说这些“不是诗艺的研究范畴”⑨。而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古典学界长期争论的“荷马问题”,恰恰是因为西方古典学界轻视表演、重视文本而造成的。今天,我们对古希腊音乐的研究也遭遇与荷马问题类似的困顿。
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不可能对古希腊音乐进行全面直观的把握,只能依据历史的碎片进行来推测。根据英国古典学家玛格利特·阿莱克斯(Margaret Alexiou)的研究可知,考古和文献描述的古希腊挽歌仪式中就有一些程式化和风格化的身体动作。这些动作不但和歌唱、哭喊、哀号结合为一体,还常常由音色尖利的阿夫洛斯管伴奏。这样的场景如舞蹈一般,时而缓慢庄严,进而狂放迷醉,?輥?輮?訛其中挽歌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定型挽歌”“即兴挽歌”“对话挽歌”。在《荷马史诗》中定型挽歌只出现过两次,而多次出现的则是根据特定歌词即兴演唱的挽歌。但相对定型挽歌,即兴挽歌的音乐性稍弱,更多的是哭喊和哀号。这就说明,古希腊音乐中存在即兴创作现象。
二、关于“模仿论”的三重内涵
有研究发现,埃斯库罗斯、品达、希罗多德、欧里庇得斯、德谟克利特和阿里斯托芬等人的文献中共有63次提到“mimesis”这个词,其中6个片段具体涉及到音乐创造和表演,即通过乐器、人声等中介,模仿、模拟、效仿或再现大自然的声音、曲调、方言等,来完成其史诗讲唱和戏剧表演。这就传递出了古希腊人对音乐、舞蹈、戏剧、绘画与雕刻等艺术形式的元认识。
其他地方有3处涉及戏剧表演,6处涉及绘画与雕刻艺术。例如,在戏剧表演中多译为“样板或榜样”“模仿”“忠实地扮演”,在绘画与雕刻中多译为“惟妙惟肖的摹本”等。这说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模仿”运用于绘画艺术,并提出艺术起源于“模仿”是有根据的。
检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前期的古希腊学者有关诗学、戏剧学、绘画学理论,“模仿论”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涵。
第一,对自然的模仿。“模仿论”中所强调的对自然的模仿,对古希腊音阶与和声构成及音乐本质作出了解释。据说,毕达哥拉斯通过铁锤敲击的声音发现了音调与简单数比率的关系,从而提出音乐源于“模仿”数的和谐统一的理论,进而提出八度、五度、四度和谐的观念。这也是古希腊四音列及调式的基础。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被后来的学者重新挖掘并融入柏拉图的理论。而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对立统一的音乐模仿自然的观点,显然也来自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统一”理论。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又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模仿论”中对自然的“模仿”不仅与中世纪教会调式和格里高利圣咏的复调和声基础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的《和声手册》(Manual of Harmonics)和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的《和声导论》(Harmonic Introduction)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本能说”和“快感说”。“本能说”和“快感说”成为“模仿论”的重要内容,表明古希腊哲学家对“模仿论”的认识已涉及到认知心理学范畴。这对于即兴音乐创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点源于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在继承毕达哥拉斯音乐模仿自然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肯定了人的主观创造。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模仿”“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这里的“快感”是指人类在大脑知觉指挥下,以“浸入心灵”为解释标准对“节奏与调式”等音乐事项进行有选择的“模仿”。可见,这里的“模仿”绝非“毫无选择”的“照搬”。这个观点已经具有鲜明认知心理学色彩。对此,英国人类学家艾伦·哈里森(Jane Alen Harrisan)也指出,“艺术不是模仿,但是,艺术,还有仪式,却往往包含着模仿的要素,在此意义上,柏拉图是正确的。” “只有用某种方式再现、模仿或者表现了那种产生了激情的思想,才能算得到艺术。”?輥?輶?訛
第三,对即兴创作的强调。“模仿论”也强调了古希腊音乐的即兴创作。以上6个片段中“mimesis”和“学说(imitate)所有人的方言”的表意,暗示古希腊史诗或戏剧表演是一种以即兴创作为特征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模仿及音调感和节奏感的产生出于我们的天性(格律文显然是节奏的部分),所以在诗的草创时期,那些在上述方面生性特别敏锐的人,通过点滴的积累,在即兴口占的基础上促成了诗的诞生”?輥?輷?訛。这里的“即兴口占”揭示了史诗源于即兴创作的本质,自然也表明古希腊史诗和戏剧表演中存在即兴音乐创作的事实。
三、“荷马问题”“口头程式理论”与早期音乐的即兴创作
“荷马问题”是18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古典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其中,荷马史诗的创作方式,诸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口头作品还是文字作品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涉及古希腊戏剧中音乐创作与表演的方式。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对古希腊史诗和戏剧中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进行一番辨析。
正如上文所引,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诗人之所以称之为诗人,是因为他们是模仿者。如此看来,“荷马”就是古希腊时期依赖“模仿”进行口头即兴创作的诗人代表(或诗人集体的代表)。20世纪30至60年代,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Bates Lord)为了回答“荷马问题”,通过大量田野调查与文献相互印证,认识到人类自古以来普遍存在一种口头编创、讲解、传播史诗的行为,从而提出著名的“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他们远赴南斯拉夫进行史诗讲唱的田野调查,将存活于当地歌手口中的史诗演唱与《荷马史诗》文本进行对照,探究史诗的创编规律。米尔曼·帕里发现,荷马史诗中“口头表演中会采用‘常备片语(stock phrases)’和‘习用的场景(conventional scenes)’来调遣词语创编他的诗作,这些循环出现的语言被看作是口头诗人创作诗歌的工具”。这个发现使困惑西方学界的所谓“荷马问题”迎刃而解。根据帕里等人的研究,史诗的口头程式表演具有三个结构性单元概念:程式、主题或典型场景、故事类型。所谓程式,就是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用来表达基本观念的词组,是一个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的词组,进而使歌手能进行现场快速表演、流利叙事,不仅能讲述简单的片语,而且还能进行大规模的情节设计。这种口头诗人在讲述故事时所遵循的这个简单而威力无比的原则,就是即兴表演原则。
口头传统研究的核心理论也对当代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学者从“口头程式理论”出发,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卡里(Robert Culley)在《圣经诗歌中的口头程式语言》中正是运用帕里-洛德的方法,揭示了《圣经》中存在着高度的程式频密度。他汇编的《口头传统与旧约全书研究》和《希伯来叙事结构之研究》着重阐述了片断式结构的构型方式可能是“旧约”最初的本源。丹麦艺术史学家本特·阿尔斯特(Bendt Alster)在《塔木兹的梦想:一则苏美尔神话中口头诗歌诸方面》中也是运用这一理论通过断篇残简重建这部诗篇。
这种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西方早期音乐研究领域。据加拿大音乐学者蒂莫西·麦基(Timothy J. Mc Gee)的研究,“中世纪的器乐演奏者之所以没有照谱演奏的习惯,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以即兴方式诠释音乐的,或者通过模仿和记忆方式学习音乐,即口传心授,因此,所缺少的乐谱资料则需要后人通过历史文献中的文字记载和少数流传下来的器乐作品来填补”
欧洲已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拟构甚至揭示欧洲早期世俗音乐的即兴表演面貌。
“口头程式理论”研究方法用于早期音乐研究的有效性,也在西方中古时期器乐即兴创作与表演的研究中得到印证。美国音乐学家劳伦斯·古希(Llawrence Gushee)运用口头理论分析萨克斯管吹奏者莱斯特·扬(Lester Young)的作品。?他发现,萨克斯管吹奏表演中存在共同结构以及程式结构问题。他指出,在即兴表演过程中,灵感是可以同时从几种不同的渠道获得的。美国音乐学家利奥·特雷特勒(Leo Treitler)也运用这一理论考察格利高利圣咏的传播问题,并阐释了口头程式和程式化系统在格列高利圣咏旋律的创作、保持和传承诸环节上是如何起作用的。解决“荷马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口头程式理论”及其对荷马史诗及对人文复兴之前許多音乐中存在的即兴创作进行解释的有效性,也进一步证明了“模仿论”在阐释人类早期音乐现象时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古希腊史学中的“模仿论”与古希腊罗马音乐的代表性文本荷马史诗之间似乎形成了相互引证。20世纪围绕“荷马问题”提出的“口头程式理论”,既证明了荷马史诗中即兴创作的存在,又证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模仿论”、荷马史诗、“口头程式理论”三者之间形成的“证据链”,不仅说明了古希腊口头文学及其音乐中的程式性创作——即兴创作,而且也说明人类早期音乐活动中即兴创作普遍存在的合理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黄河流域音乐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研究》(项目编号:2021ZD016)子课题《黄河流域戏曲与说唱音乐多元一体格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陈畅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9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