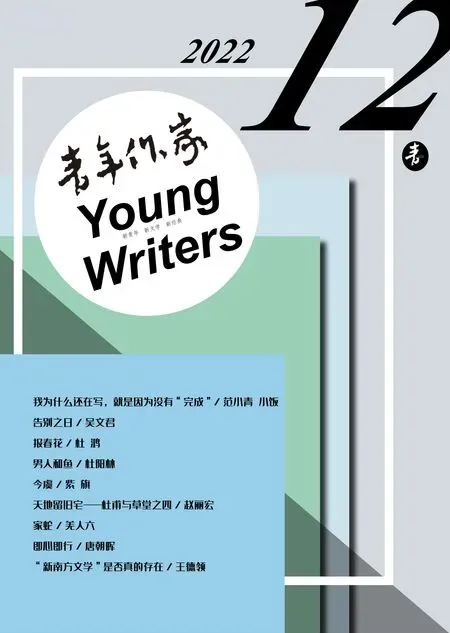“新南方文学”是否真的存在
王德领
“新南方文学”的命名
“新南方文学”的概念来自青年评论家杨庆祥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文章发表在《南方文坛》2021 年第11 期。该文界定了新南方文学的地理范围、美学风格以及代表作家。在作者看来,新南方文学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美学风格上具有“海洋性”“临界性”,具有“泛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使用“多样的南方方言语系”。
这使我想起了新时期寻根文学开端之初,韩少功的那篇宣言式文章《文学的根》。韩少功在开篇写道:“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语气的焦灼感很强烈,那是那个时代催生出的文化焦虑,充分表达了在文化发生断层之后,作家们急于从传统与民间寻找文化自信的迫切感。寻根文学产生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从理论宣言到创作实绩,寻根文学都堪称中国当代文学流派的典范。中国新文学史上,凡是成熟的文学流派,其实都根植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生长出来的。远的如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派”、创造社的“为艺术派”、京派与海派,近的如朦胧诗、寻根文学等。正是由于从时代中生长出来,所以作品也就沉稳厚重,有大气象,具有经典品质,能够经得起后人的推敲与评说。说到底,判断一个文学流派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准就是有无经典作品的产生。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新南方文学有没有坚实的现实依据呢?或者说,新南方这一地域,能否生产出一个颇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呢?新南方文学的命名依据何在?
文学作品中的“新南方”
大致盘点一下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或许能够找到是否真正存在所谓的新南方文学的答案。其实在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新南方地域,早就存在一些有特色的作品。因此,新南方文学的“新”,其实是不太确切的。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老作家许谋清,他是福建晋江人,1944 年生,2004 年出版过一部小长篇《女女过河》,写的是他家乡闽南乡村发生一起子虚乌有的强奸案。小说原来的名字叫《红地骨》,后来改为《女女过河》。“红地骨”将赤土埔这一地质特征鲜明地凸显出来,闽南是“红土地”,而不是“黄土地”。小说具有特别浓郁的“闽南”风格,不仅仅表现在地方方言的使用上,还从骨子里表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情世故,将小说主人公女女以及红圆、黑目眉三个女子与一个男子子平之间的情感纠葛写得异常微妙与繁复,尤其是表现村民面对这场子虚乌有的强奸案,闪烁其词、躲躲闪闪、似有还无,其间展现的人性的复杂,展现的村民“躲事”的劣根性,堪称入骨三分。这类故事只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舍此无他。因此可见,是否称得上地域性写作,不仅仅是方言意义上的,还有能否传达出这个地域特有的亚文化胎记。
近年来,新南方区域崭露头角的一些作家,确实有着不俗的表现。海南的作家林森,在海南岛长大,大学学的是海水养殖,这使他的《关关雎鸠》等小说,没有过分受到传统文人气的浸染。他对海边小镇风土人情的描绘,对孤悬于大陆之外的海南岛的叙述,有着陆地文学所没有的浓烈海腥气。可以说,林森是新世纪中国书写海洋的代表作家。他将海与岸连接起来,“海里”与“岸上”构成了他创作的基调。从《海里岸上》到他最新的中篇小说《唯水年轻》,写的是人与海的关系。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作为农耕民族,对土地寄予了太多深情,“土地”是一种图腾般的存在。对于“大海”,却是规避的。著名的“精卫填海”神话传说,就是表达了我们这个民族潜意识中对于海洋的恐惧与不安。在林森的作品里,大海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大海与小说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千百年来人与土地的主题,在这里置换成了人与海的主题,这是林森对中国文坛的独特贡献。
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黄锦树,在台湾读完大学和研究生,并在台湾的一所大学任教授。他的小说集《雨》在大陆出版引起了很大关注。黄锦树的《迟到的青年》写的是一个二战期间的谍战题材,亦真亦幻的叙述,疑窦丛生的时间,文本间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神秘气息,扑朔迷离又切实可感,细腻又粗犷,笔法老到圆熟,虽是短篇,情节大开大阖,现实与回忆交织,显示出作家极为出色的叙事能力。黄锦树在橡胶林长大,他的许多小说都以胶林为背景,写作本身也是还乡的过程。黄锦树的小说里有着极为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善于营造潮湿凝腻、阴鸷凄迷的氛围,在对故事的叙述基调上迥异于大陆作家。黄锦树的这种现代主义小说,是一种潮湿、凄迷而又热衷于在时空错乱中叙事的先锋文本,有点儿像20 世纪80 年代的格非、孙甘露的先锋叙事,但是格非、孙甘露的小说比黄锦树的要干燥、疏朗、粗粝,黄锦树的先锋叙事有一种热带雨林的感觉,元气充沛,植被繁茂,遮天蔽日,读者走进去很难再顺利走出来。
另一位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2021 年在大陆出版了长篇小说《流俗地》,受到了王德威和王安忆的鼎力举荐。《流俗地》以黎紫书成长的马来西亚怡保为故事的发生地,描述锡都这个华人聚集地不再耀眼的小城的日常生活。小说遵循的是严格的写实手法,写的是市井生活,塑造的是人物群像,在看似芜杂、琐碎的小人物生活中,在多元的族群中寻找华人生存的意义。小说看似写得很散淡,也没有中心事件,按照生活的流动娓娓道来,但是读完之后会有一种雕像般的充盈感,生活本身竟然是可扪可触的。有意味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古银霞是一个盲女,生来就失明。他生活在黑暗中,顽强地寻找着光亮。黎紫书曾说自己的写作理想是要“写一部有很多人、有许多声音、如同众声大合唱般的小说”。《流俗地》里的银霞所感知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虽然她无法看见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虽然她被黑暗所伤,无法确切知道夺去他贞洁的那个男人是谁,但是命运在小说末尾,还是给了她所在的族群以及她本人一个洒满阳光的未来。
90后作家陈春成,出生于福建屏南,以《音乐家》《夜晚的潜水艇》《竹峰寺》等受到文坛瞩目,尤其是在豆瓣等网络社区得到读者喜爱。陈春成对文字有着近乎洁癖的痴迷,叙述语言干净、爽利而又变幻多端。《竹峰寺》写得幽深、慵懒、神秘,散淡洒脱如汪曾祺,而又透着一种率真,在娓娓道来的叙述节奏里,蕴含着一种网络时代早已缺失的汉语的醇香之气。《夜晚的潜水艇》是向博尔赫斯致敬的短篇小说,具有梦幻般的特质,把许多不可能也不相关的事情写得栩栩如生,现实与梦幻是如此奇特如此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没有极为绚烂的想象力是完不成这类作品的,文字的魔力,在这篇小说中表露无遗。《音乐家》以上个世纪50 年代苏联对音乐审查为背景,以绚丽的想象力,冷静而又热烈的笔触,叙述了拥有通感异秉的音乐家古廖夫被政府委以音乐审查重任的传奇经历。古廖夫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自己内心那场完美的音乐会而准备的,而那竟然是一场在自己头脑里靠幻想完成的音乐会,一切都存在于幻觉中。小说叙述的沉稳、惊悚、细致、绵密,回环往复而又一唱三叹,在不动声色的寂静中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其叙述的老到、节制,想象的绚烂、丰富,意蕴的复杂与隐喻色彩,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位90 后作家之手。陈春成将天真与老练、幻想与现实糅合在一起,既飘逸又扎实,显示了纯文学的另一种路向。这是一种不同于莫言、贾平凹这些文学大家的一种路向,既带有在网络上出道的作家游戏性质,也有对现实、理想、内心的坚守,假以时日,陈春成会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大家。
林白出生于广西北流,现居北京,去年推出了长篇小说《北流》。作为上世纪90 年代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林白近十年来的写作转向令人瞩目。个人化写作往往也是藩篱,困在里面难以突围。林白是一个例外,她以坚韧的探索,从个人化写作中突围出来,建立了个人与社会的全方位通道。由《一个人的战争》专注于讨论性别的冲突,转向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呈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其实,个人化写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青春期写作,一个作家不可能沉浸在利比多的冲动里,现实生活也远远不是单纯指涉“婚姻”“爱情”等两性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作家充分意识到现实的多维性,个人化写作的弊端就会逐步显露出来。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善于反省的,会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调整。早在2012 年,林白在长篇小说《北去来辞》中就将现实复杂化,在超越个人化写作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北流》则走得更远,意味着彻底终结了《一个人的战争》的写作模式。在《北流》里,林白将诗歌与方言深深嵌入文本,以颇具个人化的方式书写宏大叙事。小说以一首长诗《植物志》开篇,而后才开始繁复的故事叙述。在正文部分采用了后现代式的麻花结构,分别由注卷、疏卷、时笺、异辞、尾章、别册等组成,还嵌入了“李跃豆词典”“西域语大词典”条目。这些碎片化的结构,使得文本变得丰富、多解,彻底颠覆了林白一贯采用的线性叙述模式。尤其是大量北流方言的引入,使得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不被标准的汉语所规约的桀骜不驯的气度。当然,与《北去来辞》一样,《北流》也是充分“林白化”的。《北流》的主人公刘跃豆,与《北去来辞》里的主人公海红一样,两人都是文艺女青年,带着鲜明的“林白式”精神痕迹,热衷于从女性自身经历出发,在从青年到中年的历史跨度中叙述个人与时代的对话、冲突与和解。
从以上几位作家来看,新南方写作以中青年作家为主。这些作家的创作,林白、黎紫书、林森的现实主义,黄锦树的现代主义,陈春成的以梦幻为基调的泛浪漫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是多元的;林白丰盈、激越、诗性,黎紫书平实、绵密,林森质朴、新异,黄锦树曲折、葳蕤、玄奥,陈春成梦幻、奇崛、幽微,在美学风格上是驳杂的,很难说有着统一的色彩。这些作家的创作作品主题也较为分散,大都是将鲜明的地域性作为一种标志凸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流派,需要有经典文本作为支撑,如《爸爸爸》《棋王》之于寻根文学,《上海的狐步舞》《梅雨之夕》之于新感觉派,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创作实绩上,虽然上述作家的作品各具特色,但是新南方文学还没有产生颇具“新南方”标识、为文坛所广泛认可的经典文本,而没有经典作品的文学流派,就会名不副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现在断言出现了“新南方文学”这个流派,还为时尚早。
方言写作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有很强的地域特征,使用方言是很常见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方言的解释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新南方文学中的方言,包括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当然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当地华人所说的汉语,又夹杂着汉语和当地语言结合之后形成的新的方言,更为复杂多样。黎紫书的《流俗地》里,就夹杂着一些当地的方言,但是基本上对阅读构不成什么障碍,可谓用得恰到好处。中国地域辽阔,方言极为复杂。即使在同一个地域,方言也不尽相同。一个方言区就是一个丰富的语言世界,它以口语的形式存在,记录成书面语时,往往找不到对应的词汇,但是这并不影响方言的存在。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形成的,而在北京,也存在着方言的差异。我在北京出版社做编辑时,在编辑稿件时经常查阅徐世荣编纂的《北京土语词典》,这本词典收录了北京市区及近郊区的地方土语10000 余条。可见地方方言的复杂性。一个成熟的作家,善于运用方言写作,以增加语言的陌生感,强化作品的地域特色。
中外作家在方言写作上可谓惊人一致。作为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威廉·福克纳就在作品中运用了不少方言口语,他在《喧哗与骚动》中用了许多方言变异来表现南方黑人的语言特点。在《村子》中,福克纳用了一些流行于当地的口语,如用bobe wire 代替常用词barbed wire(带刺的铁丝网),而这些方言词,在词典上是找不到的。方言口语的运用,使得福克纳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南方”色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我们经常把老舍的小说作为北京话写作的典范。如他的小说《骆驼祥子》、话剧《龙须沟》等作品。老舍在用北京胡同普通民众的方言写作时,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既保存了汉语特有的雅洁,又打上了深深的北京地域烙印。作家在处理方言时应该是审慎的、精挑细选的。上海作家金宇澄在写作《繁花》时,用了一些吴方言。起初用的方言数量比成稿时要多,考虑到上海以外读者的接受度,定稿时删去了许多,精心挑选有表现力的方言保留下来。例如:“亲我一记(亲我一下)、敲煞我(打死我)、橄榄屁股(坐不稳)、脚骨硬了(学会逞能了)、这只女人(这个女人)、淴浴(洗澡)、花头经(爱搞事)、老三老四(不礼貌)、轧朋友(谈恋爱)、死蟹一只(一无是处的人)、不响(不做声)。”特别是“不响”二字,小说中出现了1500 余次。“王小姐不响”“阿宝不响”“康总不响”,全书100来个人物,基本上每个都“不响”过。有关这两个字,金宇澄这样解释:“其实‘不响’是上海话中最常用的词之一,一个上海人每天都要用上那么几次,表面上意思就是不语、无语、沉默、不说话,但内涵就很复杂。比如说——我跟领导讲了半天,领导不响——那这个‘不响’意味就深长了,可能是不愿意表态,也可能不同意,还可能是很反感,或者是根本就麻木没意见,或者其他意思。上海人不习惯进一步说明,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体会。每每说到‘不响’,上海人就知道了,要靠听者自己去意会。”可见,方言用得好,就不会成为阅读障碍,是可以产生增值意义的。
对于新南方文学而言,我认为有必要明确方言写作的限度。把方言作为作品的地域特色并非灵丹妙药,要处理好一个度的问题。分寸掌握不好,方言写作就会陷入语言的牢笼。面对极为丰富的方言语汇,如何精选具有表现力的词汇,确实考验一个作家的眼力。老作家许谋清在《女女过河》里用了一些闽南乡村口语,在度的把握上,是很适当的。例如小说把夜晚叫做“暗暝”,把男人称为“打捕”,女人称为“在户”,夸一个女孩“长得水长得剔”,意思是漂亮得无可挑剔。再如作家对闽南海边村庄风物的叙述:“北方螃蟹不分,全叫螃蟹,家常吃法是蒸着吃。这个分得很细,分蟳、蛴、蟹。蟳还分仁蟳、豆蟳、红膏蟳。蟳要煎煳了才够味儿。”这里方言运用得好,是锦上添花,给小说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在用方言写作方面,林白的《北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得最远的。《北流》发表后,有评论家称赞里面的方言写作非常有特色,但是如果方言不加选择地进入文本,就会对阅读造成极大障碍。确实,借助《北流》,林白在语言上重返了自己的家乡,摆脱了普通话对自己思维的宰制,将被普通话压制、删减的无限丰盈的北流方言充分释放出来。但是,北流方言远比粤方言复杂,不要说北方方言区的读者,即使是粤方言区的读者也会有阅读障碍。为了让读者能够读懂,林白特意在一些章节前加了《李跃豆词典》,对方言词加了普通话的注释。即使如此,阅读过程还是很不顺畅。因为这些词条没有完全涵盖文本里的方言词,并且阅读时需要一遍遍去查《李跃豆词典》,对读者的阅读是一个极大考验,尤其对于北方读者而言更是一种折磨。譬如,《北流》正文《注卷:六日半》里的第三章,叙述李跃豆给弟弟米豆打电话,李跃豆说:“冇系你累了坐一下就算休息。完完整整一日都无使照顾叔叔,完全冇谂啯件事,想去歆哋就去歆哋,想去乜嘢就做乜嘢,这才是休息日。”对于这一段话,作家只对其中的“冇谂”做了注释:“冇谂:不想”。而对“冇系”“无使”“歆哋”“乜嘢”则没有注释。如果是一位来自粤方言的读者,“冇系”(不是)、“乜嘢”(什么东西)尚能理解,而“歆哋”却只能是猜着读了,因为纯粹属于北流方言。“无使”(不能)则是一个古汉语词汇,不在方言的范畴里。类似的例子,在《北流》中大量存在。可见,在小说里使用方言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如果超过了限度,方言本身就是一个累赘。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流》在方言的使用上显然过了头。这启示我们,要在作品里恰到好处地使用方言,警惕方言的滥用。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作家对方言的使用是十分谨慎的。方言自古就在,为什么历史上的那些文学家没有大量使用方言,而采用通用的汉语进行写作呢?这涉及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问题。近现代第一部方言小说是清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小说的对白部分是用吴语写成的,因为语言的关系影响了流传,幸亏张爱玲将它翻译成国语,才逐渐为读者接受。汪曾祺就对用方言写作十分慎重。倒不是不敢大胆进行尝试,而是他尊重文学史的传统。他在《小说技巧常谈》中说:“大概从明朝起,北京话就成了‘官话’。中国自有白话小说,用的就是官话。‘三言’‘二拍’的编著者,冯梦龙是苏州人,凌濛初是浙江乌程(即吴兴)人,但文中用吴语甚少。冯梦龙偶尔在对话中用一点吴语,如‘直待两脚壁立直,那时不关我事得’(《滕大尹鬼断家私》)。凌濛初的叙述语言中偶有吴语词汇,如‘不匡’(即苏州话里的‘弗壳张’,想不到的意思)。《儒林外史》里有安徽话,《西游记》里淮安土语颇多(如‘不当人子’)。但是这些小说大体都是用全国通行的官话写的。《红楼梦》是用地道的北京话写的。《红楼梦》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五四时期居京的鲁迅、胡适等许多外省作家都是以普通话也就是官话创作的,中国新文学这一百年来,正是由于用普通话书写,才保证了中国文学被现代汉语不同方言区的读者普遍接受,取得了辉煌成就。
文学的地域性及其他
讨论新南方文学,实际上是在讨论文学的地域性。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地域性讨论,是从清末开始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中,《诗经》与楚辞并称“诗骚”,二者被看做是源与流,中国文学是看作发端于一元的《诗经》传统的,这是儒家诗教的根基。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1905 年学者刘师培发表了著名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第一次从地域角度,论证了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即在《诗经》传统之外,还有一个楚辞传统。由此,中国文学的“同祖风骚”演变为“诗骚南北”,《诗经》是北方文学的发源地,楚辞是南方文学的源头,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源流的二元论。刘师培所谓的北方指黄河流域,“山国之地,地土硗脊,阻于交通”,民尚实际;所说的南方是长江流域,“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民尚虚无。南北文学的差异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由此形成了“不外记事析理二端”的北方之文,“或为抒情言志之体”的南方之文。北方之文与南方之文的差异十分鲜明。刘师培的这一论述,为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所继承。如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说:“《诗经》所选录的都是北方的诗歌,楚辞所选录的则都是南方的诗歌。”胡云翼在《中国文学概论》中说:“《诗》是以黄河为中心,代表北方民族的文学,楚辞是以长江为中心,代表南方民族的文学。”有意思的是,虽然刘师培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构了中国文学起源于《诗经》的一元论,将楚辞的地位提高到与《诗经》同等高的地位,但是同时又提出了“宗北”的主张,一再强调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地的正统性。
无论承认与否,100 余年来,刘师培这种“宗北”的主张,一直为我们所认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也是对刘师培北方之文与南方之文的地域区别的回应。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地域的不同,使得“京派”与“海派”的创作自然不同。地域不同,生活在其中的作家也有区别。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一文中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耐人寻味的是,在对比了因南北地域不同造成作家作品的差异之后,在《“京派”与“海派”》一文的末尾,鲁迅破天荒地收敛了戏谑的口吻,用少见的严肃笔墨,对“京派”寄予了厚望:“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在此,我想提醒的是,作为浙江人的鲁迅对“京派”的这个严肃表态,是不是也有自刘师培以来中国文人“宗北”的心态呢?
2012 年,苏童与葛亮进行了一个有关南北文学的对话。苏童认为,“北方是政权和权力的隐喻;南方代表着民间、野外和百姓。”在苏童与葛亮对话里,南方是依附于北方而存在的。杨庆祥认为,用北方来界定“南方”,南方是没有主体性的,南方作家解除不了“北望”的心态,“在这样的历史和文化结构里,南方的主体在哪里?它为什么需要被确认?具体到文学写作的层面,它是要依附于某种主义或者风格吗?如果南方主动拒绝这种依附性,那就需要一个新的南方主体。”需要提问的是,这个新的“主体”如何被建构起来?
100 多年来,从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始,我们一直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破除北方文学的一元地位,试图寻找并确立南方文学的主体性,但是,历史自有它的运行逻辑,文学也是。当我们不再满足于地理意义上长江以南的“南方文学”,从而提出南方以南的“新南方文学”的命名时,刘师培的论点却依然没有过时。从鲁迅到苏童,80 多年过去了,“宗北”的心态,依然缠绕着南北文学的讨论。因此,从这个文学现象出发,我认为“新南方文学”是否真的存在,远远不是一场命名所能解决的。特别是近10 年来,中国文学的语境又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新变,新时期以来所建构的文学“主体性”正在坍塌,在这样的情形下,讨论新南方文学的“主体性”,恐怕更是难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