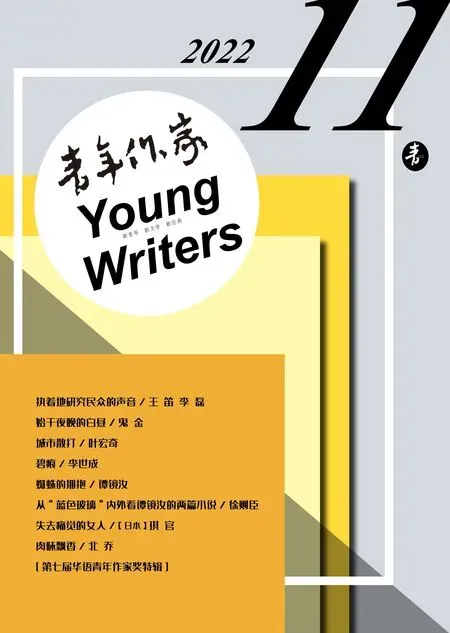碧 痕
李世成
这是一节只有两个男人的课。他们所处的空间是个只有两个男人的教室。他站在桌子上一角不停地开口,不停地说。他手里拿着小型录音机、收音机或者是教师专用的扩音器。机子显然关闭了电源。他的嘴唇在为空旷的教室效劳,为他讲述。他背对着黑板,面朝他,面朝教室的另一块黑板。他在翻阅一本厚重的书,乔伊斯或者普鲁斯特的书。他们没有任何商量,便开始了这项游戏。他不能和他说话。他只能自顾演说。他也只能看书,只好看书。就看看他们能坚持到何时。他的站姿很是自信。他阅读的姿势也显得颇为闲适。
他偷偷瞄了他一眼。他不为所动。他在看一本他已经忽略书名的书,字行愈来愈清晰,纸张愈来愈明亮。声音退到书页散发的光圈外。他到底在念些什么,无人在意。他在读些什么,无人关心。他尽可能让脖子冒出青筋,两只手前臂甩动得更自如。
他合上书本。在这间教室之外,他就不曾读过这本乔伊斯或者普鲁斯特的书。等他从这间灰黑色的教室走出,他必将忘记书页上的文字。
他明白这些。看了看桌上的他,他还在忘我地诉说。他站起身,一把将他拽下来——头、脖、肩、臂、胸、腰、胯、腿、脚——折叠好像是某只小手玩过的一只四角板,小手从书页上撕下一页纸,折成四角板,这只四角板,此刻正被他收放于外套左侧口袋中。
桌子们,带着它们苗条的四腿,坚毅地守住各自地皮。每张桌子,都是一个美人。此刻,他站在美人的右肩,他的左手轻轻托了一下腰带上的挂式扩音器。美人无动于衷。它甚至转过头去——全然不顾肩上的男人——双目对着教室后面那块水泥制作的黑板。那些远去的工人曾在由水泥和沙子框出的板块上涂黑漆。眼下,黑板抬着横放的脸孔,看着桌子美人。它们相视,不吐一字。长脸男,黑脸男,怎么叫它都好。它的额头纹,被稚嫩的四个字占领——学习园地——它怀念起那双奶香味的小手,小手剥过奶油味的瓜子,瓜子壳卷起奶油的味道成团瘫坐。不动如山,不动如小土堆。那双小手的配件,唇、舌、喉、齿,它们开口形容一堆瓜子壳。瓜子壳翻白眼。学习园地收藏了很多指纹,指纹带着汗味,在黑脸男脸上攀爬、涂抹。那些符号,权且看作声音的心情,那些嚷嚷的唇齿,哪个字写歪了,哪个字写大了,它们在刻意的表现中,将声音相互递送,最终达成共识。这些方块字,成为某个小组的荣耀,即使小手们回到家,也还在雀跃、欢呼。
那双手,它自觉作为手的表率,它有着另一双可爱的同伴。还是手。是更小的一个小女孩的双手。手们按时抓握筷子,按时给身躯赠予者汇报白天在学校经手的每一件事情。果真是一件件小事,它们会赢得大人们的赞赏。光,顺着另一双大手攀爬,顺着裸露在外的皮肤、可视的衣服攀爬,会看到大人的表情。它们安心,一副胜券在握的满足感,嘴角轻轻一动,那个女人知道晚餐该给孩子做什么了。那位晚归的男性大人,他更是不用理会日常的机轴如何转动。饭来张口,即是有女人的每个傍晚,这是称赞生活美满最恰当的词汇。作为一个男性,他幸运地拥有两个女儿,或许不只两个,也许是四个呢,此外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已在他脑子里等待降临人间的男婴。小小男孩,他如此肯定,他会随着一团雾气降落在家门口的柚子树下。
庭生柚木,亭亭如盖。他对自己的造句颇为满意。一天的劳作,无所谓辛劳与否。他与他的工友们,白天忘了机器,忘了自行车,忘了家里的门是否已经锁好。人们会忘掉哭声。那些可爱的女儿,也会忘了她们的第一声啼哭。只要愿意,会有一个女儿,记住他弟弟的哭声,哪怕她弟弟出生时,她没有在场。她会自认为自己相当懂事,是个小大人了,由于她是家里最大的女孩儿,她有权利在她母亲给她生出一个弟弟后,获准去那间被临时隔为产房的小卧室。她已经开始想象,她也是在这个房间出生的,说不准,她还是从这间房开始抛弃婴儿椅,以及严肃的门框,是她丢掉了它们。可事实真的如此么,那时候的她们,是否拥有过婴儿椅。
他作为五个孩子的父亲。全然忘了他的孩儿们如何长大。他自知出身只会是过去。而现在、将来,任何时刻,他的孩子们都不会同他一样,他是他父亲随手在地里埋下一根白薯藤结出的果实。这颗果实有过沉闷,有过渴望,有过喜悦,有过属于自己的呼噜声。孩子们是如何长大的,他已经想不起来。他站在自家院子,看着那双手在椅子上绞着。他已经不能对二十多年前的那双小手发出权威性话语,半个阻止的话声也不好丢落。他还是开口——我真不想让你出嫁——说出自己的遗憾,但更多的是欣慰。女儿长大了,女儿要嫁人。他觉得自己老了。他在女儿的婚礼上让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更忙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是个雨天。雨天的女儿婚礼。他女儿的雨天婚礼。
桌子美人摇曳生姿。他站在美人的肩膀上不停地絮叨。他在翻看一本半小时后他将遗忘的好书。此时他还没有去想那本书的书名。他会惊讶于在这空间里,读到这么好的书。除了看书,便只剩下一件事让他为之坚定,是啊,忽略这个男人,眼前的演说家。
演说家他有没有说这样的一件事呢。什么事情都可以忽略,什么人都可以遗忘。他必定不会如此将疤痕示人。他不会直接说出某句令人沉痛的话语。他宁愿让影像绕过美人之肩。杜撰黑脸男。黑脸男脸上的手。他忽略的,是一切流动的事物。同样,他企图摒弃自己成长的过程,将白薯从地里拔出,置放眼前,哈,这块头,多么喜感。多年后,他也将成为别人的父亲。
他奔赴的那场婚礼,在他若隐若现的絮叨中变得绵密起来。这和一盘月亮被乌云幕布盖住有关。他已经不能再去寻找当时的护栏,护栏上的双手、双眼、嘴唇,它们曾热烈对着那盘月亮熬夜。那双小手的主人,她抓握的粉笔,此刻正在贴上“喜”字的那间房悄然涂抹。粉笔若隐若现。那双手等候新郎家看好的时辰。她的妹妹,忙碌了两天,在另一间房短暂休息。他,和她说了些话。我的哥哥,她说,我的愿望终于达成了,我的婚礼你真的能来。这当然是,很应该啊,他话语的停顿方式足够坚定,但不符合日常用语习惯。他帮她收拾另外几个房间,以便腾出地方让客人休息。在那个摆放两张双层床的卧室,堆满了玩具动物,熊、狗、猫、兔以及别的他认不出的卡通动物。他想在众多毛茸茸的胖的瘦的堆叠的动物里找出一头猪。没能找到。她拿走了一个眼熟的布包。那是一个少数民族风格装饰的简约风格的背包,是他曾经送给她妹妹的。
那双更小一些的小小手啊。她也随着她的姐姐长大了。在她最为美好的年纪,他多次约她出来吃烧烤、吃辣子鸡、吃剔骨鸭。美好的时光随着那双温柔的小手,握着一支失踪的笔答上几张试卷,考回家乡。他们的交集随着那支中性笔的丢失而衰败。手啊。它和一双注定跟随时间奔跑的好脚密谋隐匿,她,或者他,均已失踪。
他在婚礼上再次见到她们。见到她。见到他们一家的十四只手。
他的父亲,以充实的忙碌应对失落。我,真的,不想,让你,出嫁。早上这些词,他对女儿说。说完他即和桌凳方盘碗筷桌布饮料水桶帐篷扫帚手推车互换体温。他顺利地以沉默为媒介,终于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出嫁的只是他一天的时间。只要他不停下来,他的体温触碰到物什的体温,它们会告诉他,放心好了,只是他的一个忙碌的日子出嫁了。
他和他打招呼,叔叔。他和她们的母亲打招呼,阿姨。在一场大雨中,他加入他们亲戚和邻居的队伍中。偶尔帮着递点什么东西,碗筷、桌布、饮料、盛满佳肴的碗。一只碗,下一只碗。
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会下雨。她傍晚时和他说,订婚那天,也是大雨,今天结婚也是。她的外婆对她说,下雨好。他在心内找一个词,丰沛,但没有说出来。他们在二楼过道里聊天。二楼客厅坐着三两个人,一楼是接亲的队伍正在吃饭。他想起多年前,他们还在晴隆上学,临近高三毕业的一个周末,他们八九个人一块去南山。山上杜鹃花,能站候几时?他们必将各自身躯扔向远方,或有留下复读的,但总有人最先离群。那天他躺在草地上,旁边是她,还有另一个女孩,她说在她眼里,他就是一个大哥哥。
对于结婚,他们都没有经验。先前新郎还直接把她带到楼下。正要往堂屋走去。她被长辈们喊住,还没到出亲时刻,新郎到来时,她不能离开闺房,至少是不能离开二楼。他将她送回楼上,新郎则去神龛前磕头,他的家人早已呈上部分需要放在方桌上的礼品。他将她送回闺房,此刻只有他俩了。她喊他坐着陪她说话。他站在离床边一些距离的位置。你是怕别人说闲话吗?她问。没有。他否认。说了几句,他到客厅坐着,给手机充电,她的大姐也上来了。
白天,他到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他零星帮着递一点东西,给空桌铺上桌布。她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去和她妹妹装炒米。他给每个纱制的喜糖袋里放两颗糖——那双小手——她妹妹则往袋里装炒米。糖大多是巧克力,或喜庆颜色包装的软糖。人们将会发现,这个日子的糖是最甜的。他们就那样站着给今天的日子提供炒米和糖。仿佛给她装喜糖和炒米的只能是他和她妹妹。这是她交给他们的任务。几年前的一个傍晚,他们在一家特色鹅肉火锅店里吃饭,她对他说,以后你们要是在一起,我不反对。俨然以代家长的名义悄声说出。他和她——那双小手——他们没有接话。就像今天他回答她母亲的话那般,可能太熟悉了。她母亲以为他会和她其中一个女儿走到一起。她向旁边的亲人介绍时,说他和她的孩子们一直是同学,最熟悉的朋友。如此当然说得通了。即便是个陌生人,在这样喜庆的一天里,他也会加入他们中来,即使他是重度社恐。
接亲队伍到来前。她们的父亲和邻居,雨停后更为匆忙。女儿在布置好的闺房坐着。她的妹妹们,已经在堵门的队伍里。此前,她的两个妹妹在忙碌了几天后,去换了身衣服,简单洗了脸。藏在堵门队伍中的她们,脸上显出欣喜和慌张交织的神情。她们没有多少经验。以前或曾参与过类似的堵门行动,但这次轮到在自家的楼道堵门,她们多少显现出一些慌张。姐姐出嫁,她们也将不远了。这是她们在庭院忙碌时听得最多的话。雨真切停了。楼道里摆了很多杯酒。酒和杯子起到了烘托喜庆气氛的作用,她们不会去想,接亲的人是否会一杯杯地将台阶上的酒喝完。一次性杯子盛着的啤酒,直铺到二楼廊道。
他和镇上的居民,将院内一些桌子搬走,协助旁人铲走路边遗落的桌布和饮料灌。铲子太小,他给动铲的人撑口袋,桌布浸在泥水里散开或缩成团,混乱的桌布令他们的配合不太默契,桌布挂在白色的编织袋口边,他伸出右手,抓废弃的塑料桌布放进袋内。他们的想法是,赶在接亲队伍到来前,将门前的庭院和路面清扫一番。他们的心情,只剩等着迎亲队伍的来临,那边的人已经先来电,说他们即将到路口。他没有过问他人便知迎亲队伍里会出现几个他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他看了看她家门前,还剩一堆瓜子皮及花生壳被人们忽略,他迅速找来铲子和扫帚,将它们扔到了近旁临时用砖头搭的炉灶里,一口大灶沉稳地遮在灰烬的肚腹上。
她的父亲,整夜在一楼忙着收拾。他不知道,一些东西是可以等送亲后再收拾。他只懂得用忙碌打发一个和女儿有关、和他血统有关的喜庆日子。尽管今天下过大雨,夜晚的天空还是现出明亮的圆月。他没有工夫抬头。他时不时给客人递烟,或是低头穿梭于一楼的几个房间。出嫁的女儿将于凌晨两点发亲。他和他的妻子,整夜在一楼忙着陪客人,他们站起来,到另一间房忙碌,又到另一间。这个夜晚他们夫妇将会很晚很晚才去睡。他们没有打算陪同女儿到县城,是孩子们的舅舅和舅妈陪着去。他们数了数送亲队伍,把他也算在内,说人很多了,他们就不陪着去了。他们怕难过,女儿出嫁,高兴的是他们,难过的也是他们。这复杂的情绪,为人父母都拥有过吧。他们一转身,又钻进了房间。没有人发现,他们也有些慌张。
楼上这帮老同学,熟面孔,没有谁到楼下参与喝酒。他们要赶夜路,早已蓄起充足的精神赶路。他们的汽车也时刻候着,那充满厚意的铁具,将于既定的好时辰动身。他站在廊道上看月亮。他没有去休息,比起睡眠,她家上空的月亮更为吸引他。夜晚的云层,由厚变薄,从薄变厚。他的心绪由满到空,从空到满。他想些什么,他自己也忘了。她让他去烧开水泡茶,那个器械,他不会用。生活白痴,这是她妹妹多年前赠予他的词汇,他将这词汇运用到他们家客厅旁的一个里隔中,藏身在那里等候水烧好。他看到了几年前他送给她妹妹的一罐西湖龙井,茶罐还在。他没有去触碰,而是听她的招呼,用新郎提亲那天送来的茶叶。喜茶,他说。她笑。
他们出发时,他已在一楼的人群中站着。她喊他名字,他上楼,经过二楼客厅,去摆放嫁妆的那间屋子。她指着一个红色布包着的物件,他以为是枕头,抱在手上方知里边是米袋。他抱着用红色布包着的米袋下楼梯。或许这就是枕套,枕芯已在新郎家备好,而她们家又不想让枕套空着。他将东西放在婚车后备厢。他和她弟弟坐上随行的一辆车,离开碧痕镇。夜晚的风从他们没全关上的车窗吹进来。她妹妹打来电话,问他是否上车,他说和她弟弟在一辆车上。
众人将她父母遗落身后。
第二天早上。她那内向的弟弟已经关好酒店的门离去。如果不是在她妹妹的婚礼上——如果他今后不去参加她妹妹的婚礼——他将不会再见到她弟弟了,哪怕知道他在哪个单位上班。他们没有互留联系方式。在新郎家,他和她弟弟拥有了消灭一碗米粉的共同时间。他们坐得近。从碧痕出门前,他们已经吃了一碗米饭,来新郎家,这边热忱地让他们各吃一碗粉,他们艰难地对付米粉,眼神的交流中,他知道,他们后续会多说上几句。凌晨四点左右,送亲和接亲的人被安排住在离新郎家不远的一个酒店,他和他弟弟住同一个标间。他知道她弟弟第二天要上班,先前他已请假几天回家帮忙过了,第二天他不在,他的两个姐姐也会陪刚出嫁的姐姐。她弟弟让他先去洗漱,他打算将洗澡的时间留在几个小时后的白天。
他醒来。她妹妹发来消息,说他们在新郎家。凌晨的酒店出现在白日当中。他迷路了,始终找不到新郎家。他走进了一个迷阵,迷阵里一栋栋楼的立面一模一样,无论他怎么走,始终会绕回来,停在一所幼儿园院墙外。这所幼儿园处在圆形迷阵的中央。他停在圆形围墙外,让自己停成一个竖线,这根竖线和圆的距离,如果圆也在环动,院墙任何一点他都曾靠近过,任何一个点和他的距离都曾是一致的。他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早就和圆形院墙无比亲近了,这个上午,除了他,有谁会如此绕着一圈又一圈呢。墙内飘来孩子们的嬉闹声,还有几个女老师温柔的声音,它们充满耐心地和小孩的声音混成几个圈,圈的外边是他,他依靠听觉去向他们靠近。那些小手终将长大。而其中,必定会有一双手,即便长大了,也仍然像小孩的手。他多么希望一个小孩趁老师不注意,跑到围墙这边。他或许可以和他说几句话,问他附近有没有正在结婚的人家,就在某个院子里,他找不到通往摆酒席人家的路。
他一厢情愿认为,那个逃跑出来的孩子,是个小男孩,他只是不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作为孩子们中的一员,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短暂逃离一会儿,哪怕最终会被老师喊回去,其他小朋友也终将找到他。他清楚,只要老师一声令下,让那群小孩去把逃离的小孩找回来,不用多久,他们所有人会看到离群的小孩,小孩正在和院墙外的陌生男人说话。他们在院内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他,不用他解释,他们准会以为墙外的男子,是院内小孩的家长,他不是常来接小孩的那一个男人,他是孩子的舅舅,或者亲叔叔。他们友好地在猜想中目送他离去。
他觉得自己忘了做一件什么事。比如,趁小孩的同班同学和老师没有发现他前,他们共同栽种一个什么植物。他们商量,什么东西最好存活。这差点将他难住了。最后他告诉小孩,只有白薯最好存活。可惜,他们今天谁也无法找到一截白薯,哪怕是一根白薯藤。他只好安慰小孩,不必执着于现实中栽种的举动和事实。他告诉小孩,他们完全可以在心里,将一颗白薯种下去。那颗白薯,我们希望它是什么形状,它就是什么形状。
他从两栋楼之间的缝隙穿过。在耀眼的阳光中,他的眼皮有些灼热。他认真地作出比以往持久的闭眼,他停下来,两只拇指抵住眉心,像还没学会做眼保健操的幼儿园小朋友,像还不会默哀的孩童。等他睁开眼,他已经走进一处搭着红色帐篷的空地上。酒席正在进行中。他没有看到她,没有看到新郎,没有看到她妹妹。
他经过人群中往前走,心想,也许他们在楼上,没有下来。他站在一群中老年人的桌旁,他们腾出一个位置,说加一张凳子一起吃饭。他说还不饿,一个大叔立马到近旁去拿一张塑料椅。他只好坐下,和他们一起等上菜。此时,新郎的父亲前来给桌上的人发烟,他接了一支,接完发现自己是不抽烟的。但他往自己兜里摸去,却摸到了一支打火机。他看了看他旁边不抽烟的大叔,大叔笑着对他说,没事没事,你抽你的。他手里的烟,比以往他随意点的一支烟燃得慢,那时候他仅仅只是看了一部令人难过的电影或者小说,他的沉静和难受,催促他去打开一个隐秘的抽屉,将烟盒拿出,从容地抽出一支烟。当然,他不会抽烟。
烟燃尽了,她们没有下来。新郎和新娘来他们那一桌打招呼,他发现,他并不认识新郎新娘。他和桌上的大叔们一同笑着对他们说,新婚快乐。新郎新娘笑着说,舅舅叔叔哥哥们吃好。他悲从中来。此刻她妹妹应该坐在他身边的,他们一起拥有午餐的时间。他打开手机,看她发来的消息。她说,醒了吗?我们在新郎家。他没有回复。
他甚至知道今天,他们在新郎家会帮着做些什么。男方家也准备了很多炒米,用纱质的喜袋装上。他和她,还有她妹妹,负责将炒米分发到每张桌上。每人两袋。而新娘和新郎,则在院子里和来客打招呼。新娘发消息让他去陪她的同事。他和她妹妹以及那帮老师乘电梯上楼,新娘的同事来了很多人,他们打算分成两拨乘电梯,他们即将进入电梯前,一个男子冲进来,把电梯里的男老师捞出去,说让女老师们先上去,里边的女老师问他们去哪,那个新到的男子说,带他们去他楼上的住处参观。这帮男人就这样将女老师们抛下。新娘的两个妹妹和他,陪着女老师们去新郎家稍坐一会儿。新娘太相信他了,以为他会好好陪她的同事们说话,天南地北,闲聊于他而言,应该不难。以前一块上学时,他可是时常以古怪的故事逗大家笑。一些日子将另一些日子打败,一个时段的某个人也被另一时段的自己打败。他太清楚不过了。当他坐在那帮女老师面前,没话找话时有多尴尬,他强装没让他人看出。他拖来一只塑料凳,坐在她们面前,她们甚至将他开玩笑,让他在其中几位没恋爱的女老师中相一个。他有些头晕,这类话语游戏,如同他幼年时期,因某件事而被长辈取笑那般难堪,那仅仅只是一颗纽扣没有扣在该扣的位置,或者仅仅只是他因奔跑而裤脚有一边拖得足够长,另一边被他正经地挽好了。他的母亲为了让他来年长高也还有裤子穿,故意给他买长的。屋内的空间,热浪翻滚,新郎家住在十楼,按理说外面的日光不至于侵袭到屋内。但他分明有着快要中暑的感觉。他打开一罐饮料喝了起来,暂时闭嘴,没有同眼前的女老师接话。她们叽叽喳喳,又像是一群小学生那般了。
他和她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上一次他们一块吃饭,已是三年前,她考回家乡不久。更早以前,他曾立志带她将贵阳好吃的吃遍,如今这志向,他已然要带另一个姑娘完成。这顿饭后,他将回去找他的姑娘。眼下,和她一同吃饭,也不知会是多少年里的最后一餐。他没有什么理由再喊她出来吃一顿饭了。她坐在她左边,右边是她妹妹,而她的姐姐,新娘和新郎正在远处和客人打招呼。他默默地吃饭,无比认真,这是一顿吃了便会遗忘的速餐,桌上的人,有好几个是他们以前的同学,他们偶尔说几句话,更多的时间就着篷下的喜气以沉默下饭,红色幕布透过的红光在他们的头顶上方悬着。他错觉他正在抽一支烟,故而他的这碗饭,进食得有些慢。她在旁边对他说,慢慢吃,菜不够她去添。他以为是自己吃饭的速度最慢的了,旁边的她,也没有将碗放下。以后他一定会后悔他没有看她吃饭的样子,心想她应该不是想要陪他,而是忙饿了,这几天因为她们姐姐的婚礼,她和她妹妹该准备的,没有落下每一步,一个忠实于姐妹情谊的角色和劳力,从她们所得无多的休息时间即可看出。
他昨晚就告诉她了,下午约了朋友,他们要去大灯脚吃一碗凉粉。他离开赴宴的人群,遇到新郎新娘,遇到新娘的两个妹妹。他眼里的女孩,她说送一下他。她正好可以将酒店房卡还给前台。他们走在一条极为短促且笔直的路上,不是他陷入的那个圆形迷阵,时间啊,将小孩们的玩闹声抛向他们所在的方向。他想问问她,是否听到了孩子们的欢闹声。他左边耳朵听到的是幼儿园才有的嗡嗡声,而右耳,是婚宴上人们动筷和挪动椅子等杂乱的响动。他看着她沉静的左脸,她的个子还是像中学时那般娇小,脸庞却早已是个可以抛弃记忆和时光的大人的脸庞了。他们经过那个单元楼尽头的拐角,车上坐着先前他们陪同的一个女老师,那位女士问她,你男朋友吗?她说,不是,我们是同学。
她坚定地向前面的酒店走去,他飘忽地看向她,眼前的侧脸,也将是一个可以将记忆和时光的眼目抛弃的侧脸。在他后来的日子里,偶尔想起这段路,他可能会想多加一句台词,你欠我一个拥抱。走到路口,她说,前面有一辆空车。他招了招手,快速向出租车走去。这次道别,他们没有相互挥手,没有其他致意。她娇小的身躯向酒店的方向遁去,她将会经过酒店前院、门廊、大厅、前台。她终于得以短暂地逃离了一场婚礼。
他手里拿着房卡。他坐在大厅沙发上,打开微信,她说,他们在新郎家。
前台女孩坐在柜台后发呆。他在女孩脸庞上看到一只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