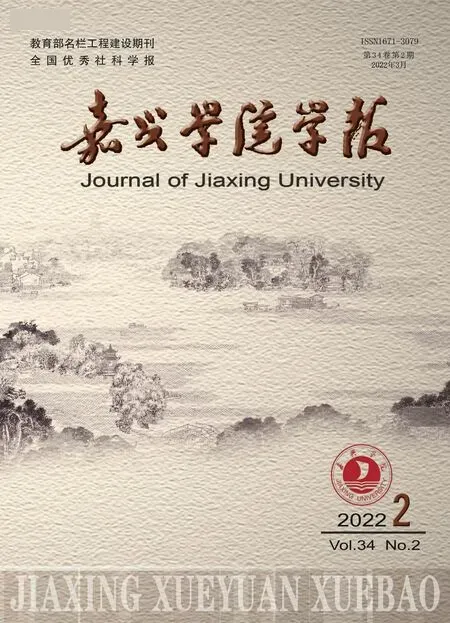楚石禅师赠来华求法僧送行诗研究
郭敏飞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一、楚石送行诗的内容与表现风格
楚石擅长诗偈,常以文字做佛事,其偈语被誉为“脱略近时窠臼,严持古宿风规,电坼霜开,金声玉振”。[2]548下他的偈语不仅流布各地丛林,日本、高丽的僧侣也都争相前来,“奔走座下,得师片言,装潢袭藏,不翅拱璧”。[3]641下凡得到楚石的一言半偈,就像玉璧一样珍藏起来。可见其诗偈在来华求法僧中极具影响。楚石赠给来华僧的诗篇,除了赞偈之外,绝大部分都是送行诗。《六会语录》中收录梵琦偈颂约300首,其中赠予日本、高丽僧侣的诗作共38首,其中有36首均是楚石为即将分离的来华僧所作,他们或是即将归国,或是离开此地继续云游他方,或是专程前来求偈而短暂相聚的僧人。这些诗作都可归结为送行诗,占其偈颂总数的十分之一。赠予日本僧人的有32首,赠予高丽僧人的有4首。这一题材成为楚石留存诗篇中重要的内容。
诗作中的来华僧,除默庵渊首座、石霜在首座、净居月长老和无极长老等有较为明确的全名和身份之外,从称谓上看,还有长老2人、上人1人、禅人3人、首座6人、藏主13人、侍者8人,而名字及称谓皆不明者1人,另有1人名“智门斯道”却不知其身份。这些来华僧中,与其往来最多的是藏主,即寺院中管理经藏的僧人,是僧团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僧人;其次是侍者,一般是指长老身边与长老关系亲密的年轻僧人,是僧团中的后起之秀;再次是首座,一般是指位居住持之下、在僧团中具有表率作用且具有一定地位的僧人。
由此可知,来楚石处求偈的来华僧人在其母国均是具有一定学识与地位,且以知识分子、年轻的后起之秀以及在寺院中作为典范表率的优秀僧人为多。可见,当时楚石是作为诗僧受到僧团中文化人的追捧,其诗词偈颂成为一种风雅之物,是禅法之修行无碍在文字上的表现。
在楚石这36首送行诗中,没有统一的格式风格,标题多以“送某某”或“送某某至某处”为题,少则8句成诗,多则28句成偈。诗中行文工整者少,形式上多新颖灵活。如赠予《无名氏》的便是送行诗中唯一一首没有“格律”“错误”的七言排律;楚石诗作中较为多见的或四言,或五言,或六七言,或交错使用,随意切换,一首诗中会出现多种字数的组合,如《送雪窦荣藏主归国》一诗中,便将这种随意性发挥到极致,摘录如下:
心地法门,匪从人得。
便与么去,天地悬隔。
师子教儿能返掷,羚羊挂角无踪迹。
以字不是八字非,觉天日月增光辉,
百尺竿头五两垂,大唐又向扶桑归。
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打破铁围山。
古今无异路,临行何待重分付。[3]634上
该诗不但打破了诗体前后句在字数上的对仗,也打破了诗体上下联对仗的关系。无论是从近体诗还是古体诗的角度考察,该诗都是不符合规格的。但从语言上而言,诗文中庄语、雅语、俗语、方言、俚语、宗教术语等无所不包,这种似口语非口语的行文,让人觉得通俗易懂,雅俗兼具,颇为耐人寻味。
楚石的这些送行诗在韵脚的处理上也颇为随心所欲,三平尾、三仄尾、失粘与用韵错误的句式常有,几乎每一首送行诗都或多或少存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韵脚问题,用韵并不严谨。即便是在句式上十分规整的几首中,也都存有用韵“错误”的问题,如《送东侍者之天平》(七言排律,押支韵)、《送志侍者》(五言排律,押先韵)等。另外,楚石的诗偈中夹杂有长句式也是常态,如《送越藏主》中便有一句“我今以百千万亿阎浮洲,拈来挂在床角头”[3]634中;又如,《送高丽顺禅人归国》中有一句“煅凡成圣,只须臾拄地撑天也奇特”。[3]633下这些虽是长句,但它们极具口语化,通俗易懂,延续了楚石送行诗中的一贯诗风。
从内容上看,楚石赠予来华求法僧的诗偈,面对不同的对象,在言语口气上是各有差异的。有的是赞叹其求法忘身之志,如《送的藏主归里》中“日本师僧皆可喜,不惮鲸波千万里。捐躯为法到南方,如此出家今有几”;[3]629中有的是劝化点拨,如《送彭禅人归里》中“大海一滴水,须弥一寸山。若将心放舍,处处是乡关”;[3]629中有的则是语气较重的警示箴言,如《送高丽蓝禅人礼補陀》中的“道人且以何为道,切忌区区外边讨。外边讨得枉劳神,只个心珠常皎皎”;[3]632下也有似老友般的心有灵犀,如《送雪窦荣藏主归国》之“古今无异路,临行何待重分付”。[3]634上这些诗作娓娓道来,更像是与来华僧的唱和对话,通俗易懂,却又处处禅机。
二、楚石送行诗的意境与风格溯源
禅宗高扬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精神,楚石作为参禅的诗人,将禅偈的写法与传统的古典诗词相结合,毫不掩饰、率直真诚地表达着自己的见解与禅悟的体验。无论是规劝告诫,还是对禅理的思索与感悟,抑或是对知音同道的赞叹,都浸染着诗人的独立风格,自我意识的色彩浓重。在这36首送行诗中,“我”“吾”等第一人称出现的频率有十余处。这种自由洒脱地抒发着自我的主观见解,既具有悲天悯人的宽阔胸怀,又具有潇洒乐观不落俗套、不拘格律、大胆创新的自觉意识,使得楚石的送行诗别具一格、真挚热情、随心无碍。
楚石送行诗亦诗亦偈,亦文亦白。所谓白话成分,是指不同于古代文言文,而接近于当时的口语表达方式的那部分。楚石的送行诗中,不管来华求法僧的身份地位如何,不因地位高而客套谄媚,亦不会因其远道而来便言语客气,该赞叹则赞叹,该训斥则训斥,该点拨则点拨,直抒胸臆,不媚流俗。与诗坛上流行的讲究格律、雕琢词藻、含蓄典雅的文人诗相比,更显出一种朴野自然之美。楚石作为一代禅师高僧,在送行诗的白话部分常夹有谈禅的话头,耐人寻味。如《送端侍者》一诗中有:
赵州文远侍者,白云清凝二师。
相与作成法社,象王狮子交驰。
灵山幸自龙钟了,左右无人话怀抱。
惭愧端僧日本来,铁牛不喫栏边草。
朝来问询,客至烧香。
上一画短,下一画长。
若更近前求指示。山僧正值接官忙。[3]640中
诗中画面感极强,从诗文中楚石似对端侍者所为略有微词,言与其他来华僧不同,以“接官忙”自喻,也点破端侍者不吃“栏边草”、似有好高骛远、忙于应付之心,劝其安住当下,并勉励其向白云清凝二师学习,得“象王狮子”之相。
在楚石的送行诗中,常常以月喻禅。以月喻禅是禅诗的一种传统,明月最具禅境的意象,也最具审美意趣。宗白华先生曾赞叹道:“月亮真是个大艺术家,转瞬之间为我们移易了世界,美的形象涌起在眼前。”[4]诗人在山林月下,对着那一尘不染的高天明月,充满了对时间与空间、瞬间与永恒、静止与运动等的思考,更是悟得纯洁空明、清净圆满的自性禅心的象征和代表。如《送净慈寿首座还日本》中的“富士山头月,祖龙溪上水。月既不来此,水亦不往彼。正当水月交辉时,万里何曾隔一丝”,[3]635中又如《送久藏主游天台雁荡》中“台岳云浮点点青,蜃江月汎茫茫白”,[3]636上再如《送中天竺吾藏主还日本》中“亦不唤作半满偏圆,亦不唤作照月权实”,[3]639上这些明“月”,既是明心见性、平常心是道的佛性自悟之“月”,亦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返真之“月”。对同处一个明月下的同道中人,在淡淡的月光下,共同体证这自静本心。
若追根溯源,楚石的诗文风格在格律和语言上的突破乃是受唐代著名诗僧寒山子的影响,其在寒山画题赞中曰:“寒山拾得两头陀,或赋新诗或唱歌。试问丰干何处去,无言无语笑呵呵。”在《楚石梵琦禅师语录》收录的诗作中有12处正面提及寒山子,言辞间充满了对寒山子的欣赏,对寒山子才华的推崇溢于言表,甚至首开赓和寒山诗之风,著有《和天台三圣诗》,在自序中对寒山诗大加赞赏:
尝读三圣(寒山、拾得、丰干三大士)诗,声韵似出寻常,意义都超格外,故愚者读之易晓,智者读之益深,三圣之诗至矣。[5]8
认为以寒山子为首的天台三圣的诗作,乃是雅俗兼具、愚智兼通,十分难得。又云:
天台三圣诗,流布人间尚矣。古今拟咏非一,而未有次其韵者。余不揆凡陋,辄撰次和之,殆类摸象耳。虽然,象之耳,亦岂外于似箕之言哉?[5]28
古之拟咏寒山诗者有之,如授予楚石法嗣的一代高僧元叟行端便曾留有《拟寒山子诗》百余篇,效仿寒山诗作。而和寒山子韵者,楚石乃是开先河之人,其认为当时人情淡薄、世道艰难更胜三圣之时,故步三圣诗韵作和诗,弘扬三圣悲悯之心,并自谦为“摸象耳”。三圣诗声韵超出寻常,义理高远,且有悯世惺世之深意,故初不敢轻和之。后人评价其赓和水平却是极高。石树道人之《和三圣诗自序》中有言曰:“余初读之,不知三圣之为楚石,楚石之为三圣。再读之,恍若三圣之参前,楚石之卓立也。”[5]9认为天台三圣诗与楚石之诗几乎无法分辨,如出一辙。有此评价者还有许宸翰,他曾在《合刻楚石石树二大师和三圣诗集序》中云:
尝诵其诗,或喜或悲,或笑或骂,究其所以然者,无非使人徵善弃恶而已也。斯后楚石、石树二公,何其人辄敢和之。亦尝诵其诗,亦喜亦悲,亦笑亦骂。虽时移事易,究其和之所以,亦无非征善弃恶而已也。其词转意宛,悉亦如之。尝错杂于三大士篇,若不可辨。[5]4-5
认为楚石之和诗嬉笑怒骂,悲喜慈心,征善弃恶,与三圣之诗作如出一辙,就连词意婉转之处也与原诗风格一致,有“不下三大士之风”,若置于一处,难以分辨。
楚石如此推崇寒山诗,其创作风格也深受寒山诗的影响。除《和三圣诗》之外,楚石的其他诗作均带有浓厚的寒山风格。上文所分析的赠来华求法僧的送行诗,亦诗亦偈,不讲究对偶与平仄,不合格律,朴实无华,浅白如口语。这正是禅家所追求的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尽显不拘声律、不假雕饰、不媚世俗的禅家本色。
三、楚石送行诗流行的原因
楚石的诗作不拘于格律,近乎口语化娓娓道来的语言,受到了当时来华求法僧的大力追捧。
其一,楚石所处的元末明初,正是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后期,每年有大批日本、高丽的僧侣前来中国求法。禅宗在日本传播的早期阶段,临济宗与曹洞宗相比一直占有绝对优势。杨曾文先生将临济宗的日本化过程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传入和早期传播时期,相当于镰仓时期(1192-1333);二是向全国深入普及时期,主要在室町时期(1336-1573);三是民族化基本完成时期,是在进入江户时期(1603-1867)以后。初期传入时是宋元赴日僧发挥了指导性作用;第二时期,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日本禅僧,此时幕府推行五山十刹制度,尊崇禅僧,促进了禅宗特别是临济宗向全国各地的普及;[6]楚石所处的时代恰好跨越了早期传播向全国深入普及两个阶段。此时临济宗在日本已有一定的传播,来华求法僧对得临济法脉的“明初第一等宗师”楚石自是多了几分崇敬。
另外,日本在镰仓末期开始推行五山十刹制度。这一制度乃是借鉴了始于中国南宋时期的五山十刹制度,径山乃是五山十刹之首,地位显赫,一直以来都是来华求法僧的参拜之处。与楚石同时,至元叟行端处参叩求法的日僧,有嵩山居中、可翁宗然、寂室元光等,有的居住3年,有的居住6年。因此,可以推测,楚石从青年时起,就与日本、高丽等来华求法僧侣开始了友好交往。鉴于此,楚石自然成为来华日僧较为熟识的僧人。日僧归国之时,必也会将其事迹与诗作带回日本。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界流传着楚石的名号,使得后来的来华僧,也竞相要去楚石那求赠诗作,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
其二,楚石诗作思想特点完全符合传入日本的临济宗思想。此时佛教所宣扬的,不再强调艰深的教义,而是呈现更为世俗化的样貌。楚石之送行诗不拒诗律,不限韵脚,雅俗兼具,随心无碍,摆脱“心意识”的束缚,断除“是凡是圣”的差别观念,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法,这与临济宗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思想完全契合。
将临济宗传入日本的僧人荣西(1141-1215)曾两次入宋求法,并在归国后大力弘扬禅宗,在集中体现其对禅宗的理解和主张的《兴禅护国论》中曾多次阐述禅宗是超越于诸宗的佛法,认为禅宗是“离文字相,离心缘相”,“不拘文字,不系心思”。[7]在荣西之后,圆尔辨圆(1202-1280)认为,禅宗乃是以“无念为宗”,不执著名相,摆脱各种精神束缚,确立自信,自修自悟。[8]这些思想特点也体现在楚石赠予来华求法僧的诗作之中。
圆尔辨圆之后,临济宗在日本迅速兴盛起来,以兰溪道隆、兀庵普宁、一山一宁为代表的宋元禅僧主张“纯禅”或“纯粹禅”,并将看话禅传入日本,认为修这种禅法未必非要打坐不可,只要在日常动静中参扣一个话头,也即禅宗公案语录中的一句话乃至一个字,专心致志、反反复复地参扣下去,便可达到解脱境界。这种禅法的兴起,使得在文字与修行上都造诣颇深的楚石禅师受到热捧,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其三,楚石的送行诗风格符合日本审美观。楚石的送行诗风格与寒山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寒山诗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远胜中国本土。
北宋时期的日本僧人成寻,已将寒山诗传入日本,这种直白朴野、不避俚俗的诗风早已被日本僧人所接受,并且备受推崇。以五山文学为代表的日本僧人在汉诗、汉文作品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寒山的记录。与楚石同时期的著名学僧义堂周信(1325-1388)是五山文学中的代表性文人,吟有“同流结约寒山子,去探林边与水涯”之句,[9]不仅在诗文中流露出对寒山子委身自然山水的向往,更以应友人请求在画上题诗为条件,交换友人所画“寒山拾得图”。[10]可见,以“寒山拾得”为主题的画作是当时文人相互赠答时常见的礼物,足见“寒山拾得”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深受寒山诗风影响的楚石,其口语化的语言贴近寒山诗的诗风,完全符合来华求法僧的审美观,自然深受来华僧侣们的偏爱。
总之,楚石送行诗诗风独特,雅俗兼具,随心无碍,不拘格套,力求新奇,是寒山诗风的一种延续,亦是那个时期来华求法僧文化交流的实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化交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