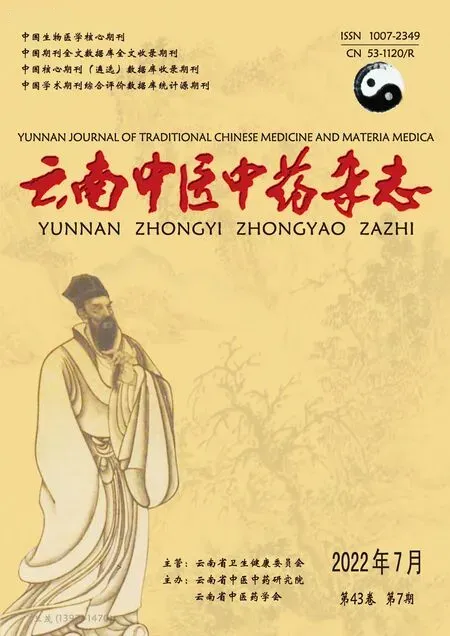郑进教授防治湿疫经验*
金 羽,李长瑾,蔡碧波,王雪梅△
(1.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湿疫之为病,乃湿毒为患,湿遏热伏,内外相合,邪伏膜原所致。郑进教授是云南省名中医在诊治湿疫的过程中,重视在病程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体化针对湿、热、寒、瘀毒邪,因势利导、祛邪外出,截断病势,扶正固本。通过中医药治疗湿疫,可有效减少并发症,降低重症率、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现将郑进教授防治湿疫经验介绍如下。
1 基本概念
疫,也称戾气、疫病或温疫,涵盖传染性和流行性较为强烈的一类疾病,突出其能相互传染导致大流行的特点,故有异于普通温病。《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温病学家吴有性亦在《杂气论》一章中提出:“为病种种,难以枚举。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认为杂气是导致疫病的主要因素,感病后传变迅速,且病情易趋危重。《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疫病划分为温、寒、燥、湿四疫。其中,湿疫作为传染性疾病中的一种,多因湿毒疫邪侵入人体而发病,现代诸多急性传染病,如甲型H1N1流感、钩端螺旋体病、手足口病、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登革热等,大部分均可以从湿疫论的角度去辨证施治[1]。此外,和湿疫密切相关的还有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 “新冠肺炎”)。
2 病因病机
2.1 毒素物质累积,湿毒为患 “毒邪”即人体因外感六淫或体内病理代谢产物堆积,导致机体产生特殊症状或体征的因素[2],其在历代各种疫病的流行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体内的毒素物质的累积便是新冠肺炎发生的重要因素。毒邪侵袭人体后之所以产生温疫、寒疫、燥疫、杂疫、湿疫等不同的表现,主要与致病之“毒”寒、热、湿、瘀的性质差异有关。其中,湿疫属于传染性较强的一种湿热类疾病,又被称为湿热疫,因湿毒为患,湿遏热伏,内外病邪相合所致[3],是瘟疫中比较常见的一型,但也属于比较顽固,且难以根治的一类瘟疫。
2.2 邪自口鼻传入,直达膜原 在人体内,邪气伏藏之内外交界之地可称之为膜原。薛生白提出“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的论断,并认为膜原是三焦之门户和关键,其位于人体半表半里,内近胃腑,外通肌表,与疾病的产生联系紧密。吴又可则在《温疫论》中对疫邪侵袭人体的途径及传变规律进行了具体阐述:“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故从病机来看,可以认为疫病的产生,乃是人体感受疫疠邪气以后,病邪自口鼻入侵机体,停留于人体半表半里之“膜原”部位而致。新冠肺炎经呼吸道飞沫传播的方式与吴又可所述“邪自口鼻而入”的特点相符,时疫邪气与当地时下流行之湿邪相合,自口鼻传入人体,直达膜原,正邪相争,终致邪盛而正衰,营卫之气受阻,阳气郁遏,邪气郁而化热,加之湿邪偏盛,湿遏热伏,以及湿性黏滞的特点,更加重气机运行不畅。湿与热伏于膜原,湿毒随热蒸腾弥漫,病情与日俱增、缠绵难愈。
3 治疗策略
由于疫病是“一气自成一病”,因此疫病在不同的时期常有其自身独特的临床表现。湿疫症早中期可因邪气困遏卫、气分,而出现恶寒、头身重疼、脘痞、纳差、舌苔厚腻等临床症状,且随着病情进展反复迁延不愈,湿聚成痰,久病致瘀,痰瘀与湿邪合而成毒,影响肺对水谷精微物质的输布,使得气血津液不能与清气合成宗气,出现胸闷和气促的表现,甚或因有形之毒邪闭阻心窍而导致神昏、谵语等危重情况的发生。故若能及早把握病情的发展走向,提出有效的治疗策略,便可有效减轻临床症状,缩短疾病病程,同时避免由轻症向重症的转化。
3.1 湿邪偏盛,芳香透邪为要 前人在治疗疾病时常以祛邪为第一要义,诸如“邪去则正安”,“邪不去则病不愈”的说法都是在强调疾病诊治过程中祛邪的重要意义,而疫病的治疗也同理。吴又可《温疫论》提出:“大凡客邪贵乎早逐。”认为疫病的治疗当乘人体气血未乱、津液未伤之时截断病势、驱邪外出,则“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所以尽早施以祛邪之法,对于疫病的诊治及病人的预后均具有积极作用。
笔者通过梳理吴又可瘟疫学说、叶天士的温病学说、络病学说以及温病学大家吴鞠通、王孟英、薛生白等的相关认识,认为“祛邪通络,恢复气机”是治疗湿疫症的最有效的治则。湿邪有内湿、外湿之别,脾失健运与湿邪停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叶天士所提出的:“湿胜则阳微,湿阻则阳郁”,湿邪可通过阻碍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从而出现头晕目眩,胸闷腹胀,大便溏薄或泄泻的临床表现。且湿无定体,随五气而化,常相兼为病,如外感湿邪多兼夹风、寒、火邪而发为风湿、寒湿、湿热、温热等证,或随不同的病因、体质、四时、环境而表现寒、热、燥的属性差异,故有“千寒易除,一湿难去”的说法。而这也导致了湿邪致病临床症状的复杂多样化和易于出现全身弥漫的情况。如湿遏肌表常以头痛身重,发热不扬,汗出不透为表现。湿滞经络,气血痹阻,表现为痹、痿、肿、木等症。面色黄胖,皮肤瘙痒多因湿郁肌肤所致。此外,湿为阴邪,易损伤阳气,影响人体气血运行,不通则痛而表现为关节重痛,甚或变形,活动受限;湿性趋下,下窍闭塞,膀胱气化不行,则尿少尿闭。加之湿性黏滞的特点,病情常常迁延难愈、缠绵反复。以藿香、佩兰、苍术为代表的芳香类药物,具有避秽化湿、醒神开窍、行气活血的特性[4],故临床治疗湿疫常以之宣畅气机、透达外邪。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报道中,以清肺排毒汤的使用频率最高,该方是第6版和第7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家诊疗方案当中的通用处方,由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加减化裁而形成,普遍适用于各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治疗。方中辛温解表与寒凉清里共施;芳香化湿和甘淡渗湿同用,针对寒、热、湿、毒等诸多邪气,发挥了宣肺止咳、清热化痰、祛湿排毒的功效。
3.2 因势利导,给邪气以出路 湿疫因“邪伏膜原”所致,主要表现为:先憎寒后发热、后但发热无憎寒、苔白或苔如积粉、脉数[5]。因病位在膜原,既非表也非里,既非经络亦非脏腑,因此在治疗上并非单纯以清热利湿、清热解毒之法可以取效。逐邪法在瘟疫中的具体应用又有辛凉清解、开达膜原、清热解毒、急急攻下等不同治法。其中,辛凉清解法主要适用于热毒邪气在表的病证,投辛凉之剂促邪从汗而解。开达膜原法即以疏利之剂祛除湿热秽浊之邪,一则鼓动正气,松动伏藏于膜原之邪气,使邪随战汗而解;二则使湿热秽浊从燥化、火化,促其速离膜原,归于胃腑,为后期攻下逐邪做准备。清热解毒、急急攻下则实为清、下两法。故笔者以为,逐邪的实质在于让邪气有出路。
“膜原”作为三焦之门户,与人体气血运行联系紧密,其居于人体半表半里,具有沟通机体内外的作用,因此当其为湿浊疫疠之气所郁滞,需使气机调达,则邪气自有出路[6]。《温疫论·行邪伏邪之别》中亦有云:“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此时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离膜原,乃观其变,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去,邪尽方愈”。故导邪速离膜原是治病的关键点,随后根据邪气的传变结果进一步辨证施治,则疾病向愈。倘若邪气聚结不散,无传变之兆,则如吴又可所言:“邪不去则病不瘳”,终致病情缠绵,迁延不愈。以新冠肺炎的治疗为例,重视在病程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湿毒停聚的关键病机个体化施以治疗,使邪气有出路。用药无论是发汗的麻黄、羌活、藿香,还是健脾燥湿的苍术、陈皮、厚朴,亦或是通利小便的茯苓、猪苓,均为因势利导、透达外邪思想的体现,旨在让湿邪从汗、尿而出,从而使内积去则气机通,邪气消则正气安。
4 防疫经验
据相关统计,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重大疫情就有557次[7]。在长期与疫病的斗争中,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防疫理论、方法体系和有效的防疫方法[8],为我们今后预防各种传染病提供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古人发现疫病具有传染性特征,故当疫病发生时会将病患定点隔离治疗。《汉书·平帝纪》中便有隔离治疗的相关记载,且早在秦代以前就已经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9]。此外,古人非常重视未病先防,在机体尚未感邪之时预防性施以艾灸、烧烟、药浴等法,使人体正气旺盛,邪不可侵。唐代大医孙思邈提出:“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扁鹊心书》里讲道:“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将艾灸用作生命垂危、极度虚弱患者的保命之法。而对于常人养生,《扁鹊心书》说:“人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艾灸功能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明清温疫学家则多提倡烧熏芳香辟秽药物,以达净化空气、驱避疫邪之效[10]。如清代的《验方新编》中便有将苍术末、红枣捣细碎焚烧,用其烟进行空气消毒防疫方法的记载。药浴即通过将处理过的药物茎叶煎汤煮沸,以外用熏蒸洗浴的方式来祛邪避秽、预防瘟疫的一种方法。据《松峰说疫》中的相关记载,通过以等量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煎水外洗,可有效预防疫病的发生、增强体质。可见,无论是医疗条件局限的古代,还是医疗技术发展的今天,中医药在疫病的防控工作中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也正因为此,许多防疫手段时至今日仍然适用。就本次新冠疫情而言,通过定点隔离和预防性内服中药调摄的方式,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传播。此外,诸如艾灸、佩戴防病香囊等以驱邪避秽为目的的防疫方法亦可用于新冠的预防[11]。
5 典型病案
汪某,女,49岁。2020年1月28日因“咳嗽5天”来诊,症见:咽痒咳嗽,无力,低热,体温36.8℃,既往有抑郁病史,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收入院治疗。初诊(2020年2月3日):中医会诊症见:咳嗽,咯黄色黏性痰,痰中夹有少量血丝,不易咯出,咽喉干痒,自觉有气上冲,大便质稀,3~4次/日,口干苦而欲饮,眠差,舌红苔黄腻。西医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断:湿毒疫;中医证型:肝强脾弱,痰湿壅肺证;治法:疏肝除风清热。处方:炒柴胡12 g,白芍药15 g,僵蚕12 g,地肤子12 g,白鲜皮12 g,桔梗15 g,前胡12 g,浙贝15 g,百部15 g,紫菀15 g,杏仁10 g,麻黄10 g,五味子10 g,炒黄芩15 g,法夏12 g,瓜蒌12 g,枳壳12 g,桑白皮15 g,白茅根12 g,枇杷叶15 g,仙鹤草30 g,甘草10 g。3剂,水煎服。
二诊(2020年2月6日):患者肺部CT提示肺部感染加重,前天晚上因受凉出现发热症状,体温39.0℃,咳嗽、咽痒较昨改善,咯痰减少,咳血消失,无胸闷,口苦较前改善,口不干,不欲饮,睡眠可,大便3次/日,质稀,查痰核酸(一)。处方:炒柴胡12 g,蝉蜕10 g,前胡12 g,五味子10 g,炒黄芩10 g,麻黄10 g,法夏12 g,白芍15 g,瓜蒌12 g,枳壳15 g,桔梗12 g,百部15 g,紫苑12 g,北沙参20 g,枇杷叶15 g,杏仁10 g,甘草10 g,仙鹤草30 g,黄芪30 g,葶苈子15 g,白茅根15 g,川贝10 g,芦根30 g,桃仁12 g,苡仁30 g,桑白皮12 g。
三诊(2020年2月10日):患者近3天发热,体温39.0℃左右,口腔溃疡,咳嗽,咽痒,痰白,无胸闷,睡眠可,大便3~4次/日,质稀,乏力较前改善,查痰核酸(一),氧饱和度94%。处方:炒柴胡15 g,白芍15 g,蝉蜕10 g,桔梗12 g,紫菀12 g,前胡12 g,川贝10 g,百部15 g,杏仁10 g,麻黄10 g,五味子10 g,炒黄芩12 g,法夏12 g,枳壳12 g,北沙参20 g,甘草10 g,芦根30 g,桃仁12 g,苡仁30 g,桑白皮12 g,生石膏20 g,茯苓20 g,白术15 g,山药20 g。
四诊(2020年2月13日):患者复查CT:病灶较前吸收。刻症见:咳嗽,少痰,痰白质稀,大便稀3~4次/日,乏力,口腔疼,低热37.4-37.6℃,潮热,汗出而多,口干苦而欲饮,纳稍差。治法:宣肺止咳,健脾祛风。处方:桔梗12 g,前胡12 g,紫菀12 g,浙贝15 g,百部15 g,杏仁10 g,麻黄10 g,五味子10 g,僵蚕12 g,蝉蜕10 g,法夏12 g,北沙参20 g,苡仁30 g,茯苓15 g,白术15 g,炒黄芩12 g,芦根20 g,枇杷叶12 g,甘草10 g,瓜蒌皮12 g,牛蒡子12 g。
五诊(2020年2月18日):患者自觉午后潮热,口干口苦,咳嗽明显减少,大便稀4次/日,眠可,口腔溃疡改善。目前肺系症状明显好转,调整处方以扶正托毒方。生黄芪30 g,玉竹15 g,白术10 g,苍术10 g,藿香15 g,青蒿15 g,秦艽10 g。
2月19日行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遂予出院。随访3周未出现症状。
按:患者为中年妇女,素体阴虚内热,又感受外邪湿毒,内外相合、伏于膜原而致病。初起湿热邪毒壅滞于肺,随着病情的进展,邪盛正衰,正气不足,湿毒向里传变,或热滞阳明,或劫灼真阴,出现湿毒、热毒、寒毒、瘀血、气阴两虚,虚实夹杂的复杂病机。因湿毒贯穿于湿疫病情的发生发展演变阶段,因此治疗首重湿毒的祛除,采用透邪解表的方法,透邪速离膜原,防止湿毒入里之势。考虑到湿毒重浊黏滞,易困阻中焦,故治以健脾利湿的茯苓、白术、薏苡仁、法夏;又因“风能胜湿”,故加入白鲜皮、地肤子、蝉蜕、枳壳,以达祛风除湿之效。针对寒毒疫疠伤阳的特点,予麻黄、百部、前胡、紫苑温表以助透邪之力,针对热毒伤阴的特点,炒黄芩、白茅根、桑白皮、枇杷叶、芦根、川贝、瓜蒌壳、青蒿、秦艽。另以藿香、苍术等芳香辟秽化浊药物宣畅气机,分散聚结于膜原的湿秽邪气。考虑到病久入络加入了桃仁活血化瘀,患者气阴亏虚,采用黄芪、玉竹、山药、北沙参等益气养阴。本案观察时间较长,治疗过程记录完整,组方用药谨守病机,随证施治,处处体现透邪外出,截断病势,扶正祛邪的思想。
6 小结
综上所述,湿疫为湿毒疫邪侵入人体后,伏藏于膜原所致的传染性疾病。治疗上,以因势利导,祛邪外出为第一要义,同时重视透达膜原、芳香辟秽,促邪溃败。然在具体使用处方治疗患者的过程中,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相关情况能守善变,谨守病机,随证施治。中医药在治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吾辈应将此种优势加以充分学习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