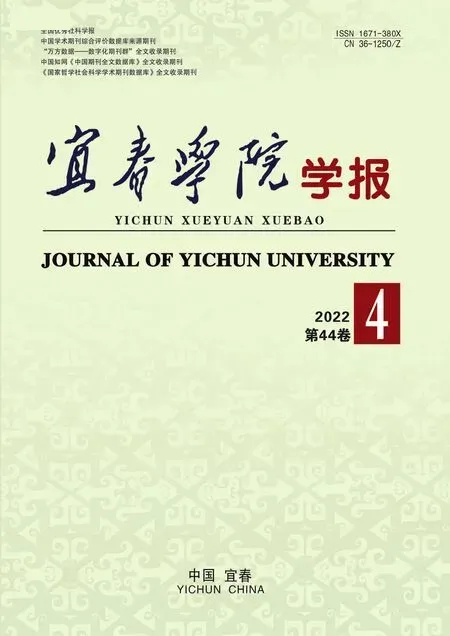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性质在我国的变异
吴未意
(宜春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我国的“旅行”中发生了一些自觉、不自觉的变异,这些变异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我国“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学界对此方面内容基本上尚未展开具体探讨,这显然不利于后学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解,也不利于全面揭示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的“旅行”。故,本文以知识学方法实证清理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的变异中之文论性质的变异,即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变异为一种批评方法与美学理论,从变异的依据、变异的现象与变异的成因三方面展开具体探讨。
一
为什么说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视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与美学理论,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性质的变异呢?首先,此二种看法早在俄国形式主义同时代就已出现,对此,艾亨鲍姆在《“形式方法”的理论》一文中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是希望根据文学材料的内在性质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学科学”,以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学科学为目的,并非确立一种方法论;俄国形式主义“并不是作为美学理论”,它“不承认哲学的前提,不承认心理学和美学的解释”,它“脱离哲学美学和艺术思想理论”“摆脱美学”“抛开诸如美的问题、艺术感的问题等许多问题”“不顾一般美学所确立的前提”“对艺术形式及其发展的理解问题又重新提出疑问”,即俄国形式主义反对学院式“运用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原则研究文学,追求“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1](P21-24)即,艾亨鲍姆明确指出俄国形式主义以建立一种文学理论为目的,并非是想确立一种方法论,也不是作为一种美学理论。众所周知,艾亨鲍姆是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形式方法”的理论》一文发表于俄国形式主义盛行十余年后,文中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主张的阐释应具有充分的权威性与可信性,即,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一种方法论、一种美学理论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性质的变异。
其次,俄国形式主义不是一种美学理论还可从其经验基础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前期吸取一般语言学,尤其是库内特尔的语言学思想,在与日常语言、散文语言相区分的基础上探讨诗歌语言的特征,将艺术界定为语言的形式、手法,将语词与实在分离,专注于语词的语音、形态层面。后期借鉴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专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的研究,将语词的语音、形态层面与语义层结合起来。即,俄国形式主义前、后期皆以语言经验为其经验基础,而非以审美主义的审美经验为其经验基础。正如余虹在其《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中所指出,俄国形式主义以“语言经验取代器具经验和审美经验成为诗学的经验基础”,开启了西方诗学的“语言的转向”。[2](P88)
再次,虽然俄国形式主义与西方审美视域下以审美经验为基础的诗学,如浪漫主义诗学等,确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皆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但俄国形式主义明确反对从美学角度研究文学,不以审美感受为艺术的目的,而以增加感觉的难度与时延为艺术的目的,这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陌生化”——的基本涵义。即,西方美学视野下的诗学以审美感受、审美愉悦为艺术的目的,以审美经验本身为艺术的本质;而俄国形式主义以感觉、经验为艺术的目的,重视感觉过程本身,与审美感受、审美愉悦之间存在差异,以陌生化手法或结构形式为艺术的本体,认为艺术即手法。可见,美学视野笼罩下的西方诗学以经验为核心词,而俄国形式主义以手法、结构为核心词,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此外,浪漫主义诗学等审美视域下的西方诗学对作者心性机能的设定是“想象”“天才”等,而这些却是俄国形式主义所反对的,俄国形式主义对作者心性机能的设定主要是“联想”。综上,从重要代表人物艾亨鲍姆的阐述、俄国形式主义的经验基础、核心概念及对作者心性机能的设定等可以见出,俄国形式主义不是一种美学理论。最后,俄国形式主义被同时代人指责为“对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普遍问题漠不关心”,[1](P21)亦可作为此一观点的佐证。
21世纪以来,我国一些研究者已开始认识到俄国形式主义并非审美主义。如2004年,曹顺庆、支宇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归为“符号性”解释,而不将其归为“审美性”解释。[3]2006年,桑农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不是审美论者,对形式主义与审美论者进行了细致区分: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是“不能预设的,只有通过对大量语言材料的分析和归纳才能得出”,而在审美论者那里,“文学性是文学的审美性,是自我认定的,不证自明地成为文学理论的导向和文学批评的原则”,“形式主义是自下而上的,审美论者是自上而下的”,“形式主义是实证的,审美论者是思辨的”等。[4]同年,刘万勇也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扬弃了审美主义。[5](P55)2009年,肖翠云指出西方语言学批评采用的方法与理论皆是语言学的,不是美学的。[6]2011年,朱涛指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提出的“诗性功能”概念是“从语言学的层面对作为‘语词’的艺术”采用二元对立方法的、面向客体的、单功能的文学功能观,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功能观才是采用辩证法,从哲学、美学层面,对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从主体出发的、多功能的文学功能观,[7]等等。
而西方更早时期已有一些研究者并不视俄国形式主义为美学理论。如厄利奇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将美学思考作为废弃的、可恶的贵族生活方式的一种奢侈品加以抛弃;[8](P20)法国让-伊夫·塔迪埃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一书中亦指出,俄国形式主义“与美学,与关于美的科学、哲学,与作品的心理的和美学的阐释相决裂”;[9](P11)佛克马、易布思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以及罗伯特·休斯的《文学结构主义》、特伦斯·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等书中亦皆未从美学角度谈论俄国形式主义,未视俄国形式主义为一种美学理论,等等。
以上对俄国形式主义并非一种美学理论的探究较多,从中亦可见出俄国形式主义流派虽然作了一些文学批评,但是为了在大量文学语言材料的分析中总结文学材料的内在性质,即俄国形式主义注重探究的是艺术的手法与结构等内容,其研究目的与实际行动皆是建立一种文学科学,而非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即,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一种批评方法,与将其视为一种美学理论皆是对其性质的变异。
二
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变异为一种批评方法、一种批评流派,称之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文评等,这种变异在我国主要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如:1983年,张隆溪介绍俄国形式主义时指出,“这派文评被称为形式主义文评”;[10]1987年,仲文、刘康、[11]宋大图、[12]小川等研究者皆在论文中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视“苏俄的形式主义”为“一个文学批评运动”,[13]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建立科学性的批评方法”;[14]1988年,徐潜等亦称之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一个“文学批评理论”,[15]同年,魏家骏也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16]1989年,钱佼汝、[17]李自修[18]亦视俄国形式主义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等等。20世纪90年代,这种变异在我国仍有少量发生,如李锐、[19]魏家骏[20]等在论文中仍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
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变异为一种美学理论的现象,在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存在。如:1986年,方珊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将文学艺术当作审美对象看待、关注语词的审美价值,在文学与美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航向,是“本世纪文学和美学研究的一股重要思潮”;[21]1987年,仲文指出俄国形式主义以“新奇”与“惊异”作为审美标准、“视美感为一种先验的存在”、“以美感价值标准为唯一的标准”,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一种美学理论;[14]1992年,陈思红将俄苏形式主义视为一种美学流派,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注重审美感受;[22]1998年,张政文、杜桂萍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第一个主动放弃典型化方法论的现代主义美学流派”,[23]等等。
21世纪以后,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变异为文学批评的现象在我国较少再发生,但将其变异为美学理论的现象却仍较广泛地存在。如:2000年,张冰称谓“俄国形式主义美学家”,[24]2009年仍称“俄国形式主义美学”,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美学范式”;[25]2006年,龚北芳也称呼“俄国形式主义美学”;[26]2012年,戴冠青亦称“俄国形式主义美学”,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美学研究”,是“20世纪最有影响、最富有活力的文艺美学流派之一”[27]等等。
与批评方法论的变异不同的是,我国部分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一种美学理论者,同时也认可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性质。如:1986年,方珊在《俄国形式主义简述》一文中既视俄国形式主义为一种美学理论,同时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是“本世纪最有影响、最富有活力的重要文学理论派别之一”;2000年,张冰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是“一种文艺理论和美学诗学体系”;[24](P2)2006年,汪正龙将俄国形式主义定位于“一个美学及文学理论派别”;[28]同年,龚北芳在称呼“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同时,也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26]等等。
当然,在我国,无论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21世纪,没有将俄国形式主义变异为一种批评方法或一种美学理论者,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如:20世纪80年代,李辉凡、[29]周宪、[30]樊锦鑫、[31]景国劲、[32]周启超[33]等皆没有变异俄国形式主义的文论性质;20世纪90年代,范方俊、[34]赖干坚、[35]乔雨、[36]陶东风、[37]李思孝、[38]崔凤琦、[39]赵志军、[40]苏宏斌、[41]张无屐、[42]范玉刚、[43]石海光、[44]苏冰、[45]温恕、[46]刘万勇、[47]刘晓文、[48]吕周聚[49]等在论文中亦皆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或俄国形式主义诗学。21世纪,研究与应用俄国形式主义的论文急遽增加,绝大部分论文中都视俄国形式主义为一种文学理论,因为数量过于庞大,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性质的两种变异基本属于不自觉变异,造成两种变异较多出现的首要原因,应归结于此时期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的接受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解、研究尚不全面、深入。当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较多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一种美学理论,还与当时将文学视为审美意识形态、重视从美学角度研究文学的观点在我国文论界较为普遍、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密切相关。在此种文论视野下,容易将一切文艺理论、批评理论,尤其是注重形式研究者视为美学理论。其次,批评方法的变异还与俄国形式主义确实进行了不少文学批评实践有关。俄国形式主义流派虽然以文学科学的建立为目的,但并不以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为目标,而注重发现文学中的一些理论原则,并通过文学批评实践检验、完善它们,因此,势必会较多地撰写文学批评,使得表征上更似一种批评方法论。
21世纪,将俄国形式主义变异为一种美学理论的现象在我国仍较多发生,这又首先与西方近代美学的特征及俄国形式主义以感觉为基础的特性有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美学思想认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艺术,所以人们一般容易将所有的文学艺术理论都视为美学理论,认为文学与艺术理论皆是从属于美学的。同时,俄国形式主义以感觉为基础,而近代美学认为美学是研究美感或审美经验的,这亦很容易让人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近代美学的一个流派。
尤为重要的是,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中确实有不少成员谈到了审美感受等美学问题。如领袖之一什克洛夫斯基就说到,“新的形式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新的内容,而是为了代替已经失去审美特点的旧形式”,[50](P35)“艺术形式是审美需要产生的”[51](P38)等;勃里克曾说,“节奏的手法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审美感”;[1](P44)托马舍夫斯基说,“情节的美学功能正是在于使读者注意到这种主旨排列”;[52](P123)艾亨鲍姆亦承认形式主义者专注的是形式“和其它没有审美的形式特点”[1](P47)的对比;雅各布森曾指出“特尼亚诺夫、什克洛夫斯基、穆卡尔若夫斯基和我”皆追求“突出美学功能的独立性”,[53](P345)并在1965年为托多洛夫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作序时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语言学与美学的成就,[54](P4)等等。虽然从整体上看,这些言论并不多,也不频繁,但是,从以上言论完全有理由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美学理论。也就是说,部分俄国形式主义者,包括重要代表人物,并没有完全摆脱近代美学思想的视野,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不由自主地存有近代美学视野下文艺思想的一些遗留,还带着“裹脚布”。从这个角度来看,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一种美学理论就并非变异了。正是俄国形式主义这些“裹脚布”式的言论导致后世研究者的混乱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是美学理论,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不是,甚至同一研究者亦可能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如厄利希一方面认为“对美和绝对理念的沉思与他们不甚相关”,却同时又称俄国形式主义为“形式主义美学”。[8](P171)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说俄国形式主义是一个美学流派,也肯定不是哲学美学流派,而是重视美感或审美经验的近代美学流派,其自下而上的实证与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艾亨鲍姆所明言的“不借助于思辨美学”[1](P24)的主张,体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科学美学性质。2007年,桑农在《不确定的“文学性”及其张力》一文中实际上是将俄国形式主义与哲学美学进行了比较,论证了俄国形式主义不是哲学美学。本尼特亦指出,“尽管形式派所提出的研究模式仍然是一种美学模式——‘文学’本身的理论——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科学美学”。[55]
再次,美学理论的变异在我国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西方学界的影响,因为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美学理论的现象在西方学界亦较广泛存在。如托多洛夫指出俄国形式主义者与美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是“拒绝接受当时支配俄国文学批评的心理学、哲学或社会学的方法”;[56](P6)韦勒克从美学、审美效果的角度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研究了各种形式以及“主题、母题和情节的审美功能”,指出什克洛夫斯基使用了“审美感受”的概念;[57](P535-P536)J.M.布洛克曼亦认为彼得堡学派的诗语研究是美学和文学理论,明确指出“俄国形式主义起初是一个文学和美学的运动”,[58](P27)等等。这些观点在我国的引入,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影响到我国学者的理解与判断。此外,我国较普遍地将俄国形式主义视为美学理论,较大程度上还与我国长期以来将日尔蒙斯基视为俄国形式主义成员有关,而日尔蒙斯基确实显然是从美学视角考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