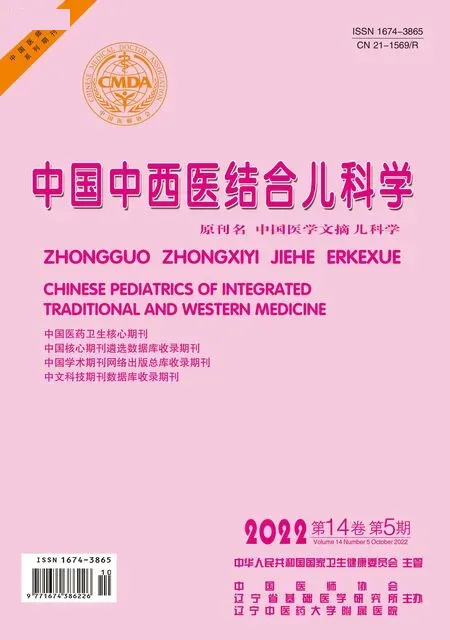王继安辨治小儿肺系疾病经验
李久杰, 田云龙, 王靖, 王爱珍, 李亚群
王继安(1919-2011),师承于江苏省姜堰儿科名医丁伯安、东台儒医潘味清,1944年悬壶桑梓,1948年由东台迁居泰州,以个体行医为生,1955年与多位泰州中医组成“五人联合诊所”,翌年并入西坝口“中心联合诊所”,1958年底进入泰州联合医院(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前身),1980年调入泰州市中医院,为泰州市中医院儿科创始人以及里下河王氏儿科创始人,曾任江苏省中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专业方面擅长小儿出疹性疾患,呼吸、消化及肾炎等疾病。
小儿肺系疾病临床最为常见,病种包括小儿感冒、咳嗽、肺炎喘嗽[1]以及温热病如麻疹肺炎、百日咳等。小儿咳嗽分为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2],急性咳嗽多为外邪犯肺所致,慢性咳嗽是指咳嗽持续4周以上不愈,咳嗽变异性哮喘、上气道综合征及呼吸道感染后咳嗽占前三位[3],部分患儿西药治疗效果欠佳,中医药在治疗小儿慢性咳嗽有其独特优势,有研究认为中药是通过抗炎机制达到治疗小儿慢性咳嗽的目的[4]。
王继安老中医有感小儿温热病发病率高,且小儿为纯阳之体,感邪之后易于热化,曾求教儒医潘味清,在行医过程中碰到麻疹肺炎患儿尤多,王老师在患儿进门之前未抬头,仅凭患儿咳声就能判断又来了个麻疹患儿,以宣透清解法治疗,收效显著,现总结王老师治疗小儿肺系疾病经验如下。
1 宣肃有别,以利肺气升降
王老师认为肺气不宣多为外感风寒初起,恶寒无汗、鼻塞多嚏,且有咳嗽不爽、胸闷、呼吸欠畅、咽痒咽痛,或有胸胁痛,一般兼见发热、咽痛、鼻流涕、头痛、颈项僵硬等,或有全身肌肉、关节酸痛、出疹不透等;而肺失肃降多见咳声响亮,往往昼轻夜甚,伴有气逆上冲或气不相接,胸胁满闷,喘促痰鸣;或呈痉咳、呛咳,进食或有烟雾刺激则咳作,痰出气顺方可得片刻缓解。临证二者不可混淆,差之毫厘,用药谬以千里,失治误治矣。
2 清温勿过,辨治及时准确
王老师认为小儿肺脏娇嫩,既恶热又恶寒。临证虽辨之为热证,但其药不宜大寒,稍过极易伤及肺气;反之,辨之为寒证,其药当忌温燥,否则易耗散肺阴。小儿脾常不足,清肺之品宜选金银花、连翘、黄芩、生石膏、知母、菊花、蒲公英、芦根等甘寒之品,不宜选用黄连、大黄、穿心莲等大寒之品。温肺之品宜选桂枝、干姜,不宜选用附子、肉桂、麻黄等辛温大热之品。
3 补泻适时,务求邪去正安
关于补法,王老师强调:小儿素体肺气偏虚或阴分不足,治疗中尤要顾护肺气或育养阴分(每于初施之方中即加入适量黄芪、白术或南沙参、玉竹)。患儿罹患肺病稍久(短则五六天,长则十余日)多有肺气受损,宜细加观察,不致疏忽,此时予党参配黄芪或太子参加百合、五味子。极少部分小儿有更严重的虚损表现,通过辨证认清脾虚肾虚等,施以相应治疗以纠其偏。
关于泻法,王老师主张治疗中清热、泻火、利气、祛痰、化湿、消积、通腑等法应用及时、大胆,不可犹豫不决。
4 剂轻程短,切记脏腑娇嫩
《景岳全书》云:“然治标之法,以精简轻锐,适当其可,及病则已,毫毋犯其正气,斯为高手。但见虚象,便不可妄行攻击,任意消耗;若见之不真,不可谓姑去其邪,谅亦无害。不知小儿以柔嫩之体,气血未坚,脏腑甚脆,略略受伤残,萎谢极易。”
王老师强调攻逐痰邪、行气宽胸、泻火通腑之品,一般应用2~5 d,且药量一、二日一调,中病即止。补虚之品用后需密切观察患儿舌苔、气息、饮食、脘腹、大便等变化,再调整处方。正如《儿科醒》云:“至于用药之法,宁勿药,无过剂,宁轻无重,毋偏寒,毋偏热,毋过散,毋过攻。……知乎此,于婴儿诊治之道,思过半矣[5]。”
5 脏腑关联,治肺不拘一脏
《难经》云:“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气也,其脉在中,……”《素问》中“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将引起咳嗽原因从单独的肺脏扩大到其他脏腑,从整体观念高度说明咳嗽虽是肺脏病理反映,但其他脏腑病变也可影响肺之宣降而咳嗽[6]。
5.1 肺与脾胃 脾为生痰之源,小儿肺系病中痰湿并不少见,宣肺肃肺理气化痰之外,往往还要健脾化湿以杜生痰之源;如果小儿素体肺脾气虚,则益气健脾、补土生金更不可少;至于胃家食滞小儿最为常见,方中宜加鸡内金、神曲等以消食导滞。汪受传教授亦认为小儿慢性咳嗽从脾胃肺论治,提出升阳益胃,补肺益气的治疗原则[7]。王雪峰教授基于《素问·咳论》:“聚于胃,关于肺”,肺胃经脉相通、五行相生、气机相辅,亦提出久咳患儿出现胃的症状时当从胃论治,采用安胃降逆止咳法[8]。
5.2 肺与肝 小儿咳嗽尤其是慢性咳嗽其本在肺[9],与肝密切相关,肝与肺在生理上相互联系,在病理上密切相关。足厥肝经沿胁肋而上并有分支与肺经相连。肺气不利,也会影响肝的功能。表现为胸胁胀痛、喘逆气促、痉咳难止、目胀目赤、肢体拘急、口苦、烦躁易怒等,主要用药如菊花、旋覆花、磁石、僵蚕等。小儿“肝常有余”,上焦邪热易于窜肝动风,故应细加观察,及时清肝泻火或柔肝解痉,主要用药如钩藤、白芍、石决明、全蝎等。
5.3 肺与大肠 生理上肺与大肠互为表里,临床上常见肺气不宣、肺热壅阻而腑气不通,亦有肺气虚而大便不畅,此时宣肺或者清热泻肺可迅速改变肠腑症状;反过来,泻热通腑可以使痰壅喘促得到改善,主要用药郁李仁、虎杖、大黄等。
5.4 肺与心 心肺同居上焦,心主行血,肺主呼吸,心肺关系即气血间的关系,肺主气之障碍,可影响心血运行。肺病也可能出现心悸心慌、胸闷、心痛以及唇舌发紫、脉象异常等。小儿心常有余,心属火,主血脉,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若心火过旺,则火旺克金,煎熬津血,致使肺失清肃之令,而致上气咳嗽[10]。在咳嗽同时兼有气急、心慌时,王老师常常喜欢在方中加当归、桃仁、郁金等以养心活血。
5.5 肺与肾 肺主气司呼吸,肾主纳气;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五行上肺和肾有母子关系,金水相生。所以肺的疾病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阶段会影响到肾的功能,出现气短不足以息的喘证、水液代谢障碍的水肿以及气虚阴虚等虚损,王老师此时用药喜加用坎脐,其性甘、咸、温,功能益肾、纳气、敛汗。
6 验案举隅
患儿,男,3岁。1979年2月12日初诊。肛温38.0 ℃,发热5 d。咳嗽。鼻流清涕。注射青霉素、复安比注射液,热势不退时抽搐,口干频饮,舌红苔薄黄,时邪外袭,肺气失宣,法以辛凉解表(耳、可见麻疹隐隐)。处方:桑叶、菊花、连翘、豆豉各8 g,桔梗4 g,苏薄荷后下、蝉衣、炒牛蒡子、苏叶各6 g。2剂。
1979年2月14日二诊。肛温37.7 ℃。服药后麻疹透露。色鲜红密布。处方:原方+金银花8 g,去豆豉。2剂。
1979年2月16日三诊。麻疹渐退,仍咳嗽,鼻流黄涕,大便两日未行,小便量少、质混,口干。处方:金银花、连翘各8 g,桔梗4 g,杏仁、苏薄荷后下、炒牛蒡子、炒黄芩、苏叶、石斛各6 g。1剂。
1979年2月17日四诊。麻疹渐退,饮食增进,大便色黄,小便转清。拟方调理。处方:银花、连翘各8 g,沙参、神曲、麦芽各10 g,枇杷叶、石斛、苏叶、炒黄芩各6 g。2剂。
按:王老师认为,麻疹的治疗以宣透清解为要,临床上麻疹以卫气同病、气营同病多见,深入血分者较少,其精髓在于针对病因透邪外出,进而调达气机,以求营分热邪有外泄之路,叶天士《外感温热论》“大凡看法……入营尚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王老师临床治疗小儿麻疹,麻邪在卫气分选用银翘散合桑菊饮加减(桑叶、菊花、桔梗、连翘、金银花、薄荷、牛蒡子、蝉衣、紫草、甘草),疹出不畅者加用升麻、葛根,表寒稍重者加用荆芥、苏叶,咽红疼痛明显加二根汤(山豆根、板蓝根),咳嗽较重者加杏仁、苏子,邪入营血者加用生地黄、赤芍、丹皮。
7 讨论
王老师认为一切肺病均为肺气宣降失调所致。风热犯肺者当清宣肺气,常用药:桑叶、菊花、薄荷、牛蒡子、蝉蜕、浮萍;风寒犯肺者当温宣肺气,常用药:麻黄、紫苏、荆芥、防风、羌活、葱白、生姜皮。
肺失肃降者王继安老师有降气肃肺、解痉肃肺、通腑肃肺、泻肺平喘四法。降气肃肺法常用于咳嗽未及他脏者,常用药:白前、前胡、桔梗、莱菔子、白芥子、旋覆花、胖大海;解痉肃肺法常用于百日咳等以刺激性痉挛性咳嗽者,王继安老师认为属肝气太过,横逆犯肺,常用药:地龙、全蝎、杏仁、苏子、款冬花、旋覆花、磁石、白芍、百部、鹅不食草,治疗百日咳经典名方“旋磁白部汤”对痉咳期疗效显著[11],已制成院内协定方,近年来百日咳有抬头趋势,类百日咳综合征临床亦较为常见,近年来工作室成员治疗类百日咳综合征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有待工作室进一步研究;通腑肃肺法常用于伴有大便秘结者,肺与大肠相表里,从肠治小儿咳喘是儿科医者临床常用之法,常用药:大黄、虎杖、郁李仁,南京中医药大学韩新民教授经验方“泻肺平喘灵”通腑平喘临床疗效显著,且实验研究显示中药能够保护肺组织,减轻肺部病变,有效阻断内毒素血症对模型大鼠组织的损伤[12-13];泻肺平喘法常用于小儿咳喘肺气壅实者,常用药:葶苈子、桑白皮。
综上所述,小儿肺系疾病总由肺气宣发肃降失常所致,无论六淫外邪还是疫疠之邪所致,关于脾胃及肝者多,用药当时时安脾胃,痉咳、久咳者可从肝胃论治,如仅从肺论治则失治误治远矣,王继安老师在治疗百日咳痉咳期的经验在今时论治类百日咳综合征仍有效,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