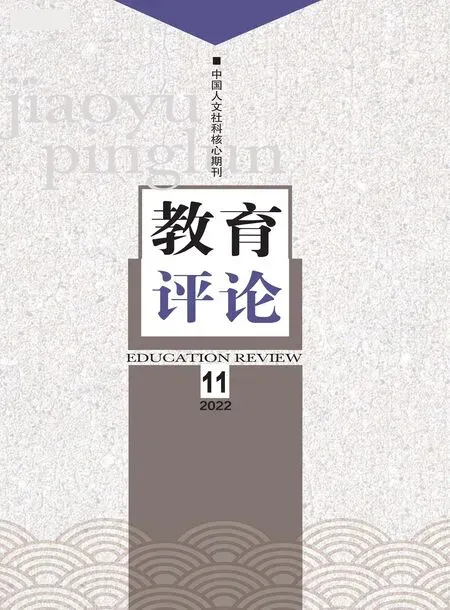财经思维与当下的本科生教学改革
——以外国文学教学为例
●王小英
2019年秋,笔者担任了内外招生合体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任务。该课程共20多名学生,除了2018级学生,还有上几届重修的,以及对分数不满意希望能刷分的学生。该门课的教学活动中,发生了让笔者从教十年来深感震撼的一件事:一名学生从上课到考试本人都未出场过,全程都在雇人上课和考试,因为上课和考试非同一人,所以最后被发现。常言道“知识改变命运”,但在这次事件中,“知识”学习竟然成了一种“负担”,学习就是为了获得学分累进至毕业,此外别无他用。学生忙于生意,无暇学习这种“琐事”,所以想到了用钱解决问题。其行为背后的逻辑是财经思维,从经济维度来衡量事情的重要性并作出应对办法,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个别事件不足以代表普遍现象,但随后笔者注意到学生选课和评教中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倾向:第一,学分和学习量的匹配度,低学分和高任务容易引起学生反感;第二,学习量和学习成绩的正相关关系要建立在与同类课程以及历来考试成绩的比较上,如果学习投入度差不多,而分数较低,就会让学生强烈不满。这些倾向比较好理解,学生需要“效益最大化”,效益的直观体现就是分数。分数影响学生的毕业、评奖、保研、找工作诸种事宜,所以学生自然渴望高分。在精力——分数——实际利益的获得度间,效益至为关键。没有实际利益的付出令人沮丧,其背后的衡量逻辑是财经思维。在这一逻辑中,文化习得和人格涵养被排挤到边缘。
在以经济发展为主的社会导向之下,当代大学生以财经思维来考量和规划学习可以理解。但当其成为主要、普遍的学生行为指导时,就需要我们深刻地反思:大学教育并非要把人都培养成生意人,但我们的教育为何会将人朝着这个方向来塑造?大学教育应该如何进行?
一、当代货币文化与主体性教育的弊病
2012年,在刘道玉教育基金会“《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就当前高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作出如此评价:“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1]钱先生此语可谓振聋发聩,高校教育出现这种状况是由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
从宏观来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货币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相关。德国哲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早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中就指出了货币经济中的生活风格:“理智力是货币经济这一特殊现象产生的心理力量,不同于一般被称为情感或情绪的那些心理力量,情感在货币经济尚未渗透进去的时期和兴趣范围中占据着主要地位。”[2]今日生活之目标需要通过无限接续、迂回曲折的方式和更长久的时间准备才可达到,一个阶段成了另外阶段的准备。货币到处被视为目的,迫使很多本身目的性的事情变成了手段,且由于货币的客观性,这些事情成了能以客观数据衡量的对象。大学生衡量自己效益的方式即是投入程度和成绩的比例,轻轻松松就能获得高分成为最便捷的阶段升级方式。
从教育领域来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我们多年来秉持的教育理念也有一定关系。放眼国内外教育,“把学生当作主体,培养学生的主体性”的主体性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3]毋庸置疑,这种理念相较于过去那种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改造对象的“塑造论”和“工具论”理念而言,有了很大提高,教育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和提高。但不管以学生为主体还是以教师为主体,其实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都是强调个体以理性的方式占有对象,而这种“占有尽可能多的对象”的理念,外在直接表现是鼓励学生去占有知识和荣誉,对学生灌输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观念,或者表面上打着尊重别人的名义,实际上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的高层次的个体主义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但这种观念塑造出来的“优秀分子”自然而然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拥有的越多越能体现主体的价值,而只有“精致”才能更“利己”,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努力立马得到回报,或者不努力也可以不错,成为现代社会主体性教育下的默认法则。客观地说,精于算计并非完全是主体性教育之过,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所塑造的主导人格即是如此。但教育对确立主体性,并建立量化了的个人价值判断标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大学教育在树立崇高人格方面并无建树,只是在培养善于以分数来证明自己的学子,那么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必然是锱铢必较、精致的个人主义者。
具体到高校来看,学生和教师间存在相互制约关系,这种制约有其非常有效的一面,学生评分高的教师得到奖励和表扬,得分低的写总结。但也有其不尽人意之处,学生的成绩不能够太低,原先85分及以上是优秀,放在今天需要至少提高到90分以上。学生对自己成绩报表的好看度要求很高,而对知识的渴求度持续走低,甚至看作是一种累赘。以笔者碰到的雇佣学习事件为例,该生用上课时间做生意,用做生意挣到的钱雇人替自己上课和考试,只要生意收入超过雇佣花费,那么其就可以实现金钱和学位的“双丰收”。至于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尤其是人文方面的知识,即便认真学了也无法立即见效,并不能转换成经济效益,显然是在浪费时间。目的成了手段,手段成了目的。从经济维度来思考学生的行为,虽然学生有冒犯学校规章制度且被发现的风险,但若不被发现,则意味着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学位问题。这的确是一种简单干脆的手法,背后追求的既是财富,也是效益。相较于踏踏实实学习获取高分,或者和教师拉关系来获得及格,其付出的只有金钱成本,高效务实。事件虽是个别事件,但学生对分数的要求越来越高是一个普遍现象。另外,两位“刷分”的学生上课时东张西望,经常在音乐世界里漫游,但每次都到,作业都交,就是在用打分规则来替自己争取更好看的分数。时间成本理应换算成更高的分数,这是学生眼中明摆的规则。
由此看来,主体性教育的弊端必须引起反思。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主体性教育虽然对纠正原先教育中存在的主体性偏失的状况有颇多好处,但“受教育者所发展的主体性只是一种外在的主体性,即主体仅具有对外部世界进行改造的能力,而缺乏对自己的内部世界进行反思和‘改造’的品质。在教育中,受教育者的学习变成了一种占有式的学习,如对知识的掌握便是以知识的数量和知识的实用为目的,而没有使知识成为智慧,没有理解知识对人格生成的作用……这样的主体性由于缺乏内在的向度,而使受教育者没有养成自我反思的品质,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狭隘、自私、封闭的心理”[4]。针对这种情况,许多教育工作者提出以“主体间性”作为教育的价值取向,以纠正以往主体性教育带来的价值偏差。
二、多维度主体间性的文学教育
“主体间性”原本是一哲学术语,由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首先提出,在认识层面上用来作为对以个人占有为中心的主体性的反驳和纠正,后经海德尔格(Martin Heidegger)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的发展,开始有了实践层面上的交往主体性的含义。而在社会生活层面,“主体间性是主体间的‘互识’与‘共识’。‘互识’是指主体之间相互认识和相互理解;‘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所达成的相互理解,所形成的主体间的共同性和共通性。通过对共同事物达成共识,主体才能达到深层的互识”[5]。不再将同为主体的他人当作外在于自己的客体,而是强调主体间的相互认识与理解,假如主体间性教育理念可以推行,对破解工具理性主义和利己主义不无好处。但问题是如何实践主体间性呢?
整个教育体系都强调师生互相交流,互相尊重和理解。但在高校系统中,实际情况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互相尊重但很少交流,他们分属于不同的体系,受到不同的制约,也被按照不同的标准所评价和衡量,各自忙碌于占有不同的荣誉、分数和客体,个体被单一的主体性观念所害,也可能用这种观念损害别人。但无论如何,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假如不能改变整个社会氛围,或许可以从小处着手,积跬步以至千里。其实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日常相处,师生之间都应是一种以达到主体间性为目标的双向交流,而不是独白和自言自语。换言之,即便是在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标的专业教学上,教师也应该与学生尽可能地互识,和学生共同思考一些问题,以便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贩售,或者说将教学当成谋生方式。
站在教师的角度看,教学的投入度和学生的认可度并不一致,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经常会被视同苛刻,学生已经不再是求知若渴的状态,令人颇感沮丧。但若从主体间性的经济维度去思考,就比较好理解。付出需要收获,没有收获的付出是浪费时间。在当今高校的体制下,本科生任课教师不同于初高中教师,也不同于研究生导师,教师和学生的接触不过一两门课程的时段,在这一时段中,任课教师和本科生很难建立情感上的强纽带关系。师生双方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维系课堂外的关系,所以从传统师道尊严和师徒相授的角度去规范学生的学习是不可行的,而从主体间性的经济维度去理解学生学习行为是比较可行的。经济虽然在今天的社会成为人之主要生存维度,但不可否认还有爱与尊重等其他维度。皮格马利翁效应依旧有效,学生喜欢喜欢自己的教师,教师喜欢喜欢自己的学生,这是一种双向的情感增长。文学向来不是经济为主的文学,而是包含着对人生和世界的广阔理解,所以也给学生从多维主体间性来理解规划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种长远目光的可能。
课堂教学是围绕特定内容的讲授展开的面对面交流,主体间性的发挥也应当围绕所传授内容来展开。在理想的教学中,教师、学生和知识能够产生互动。也即,无论是学生还是以书本形式呈现出来的知识都应被当作主体对待,都具有沟通交流的功能。这涉及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将对方当作主体来看待?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其代表作《我与你》中指出,人只能在关系中存在,因为关系方式的不同,所以出现了两种 “我”:处于“我——你”关系中的“我”和处于“我——它(他、她)”关系中的我。“‘我——你’关系与‘我——它’关系,指的是‘我’对与‘我’相关的一切事物的态度或关联方式,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对关系者的态度不同,与之打交道的方式不同,则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就不同;人生态度或生活方式不同,其人也就不同。”[6]“我——它”关系中,我将另一关系者视为探索占有、利用压榨的客体对象,“我——你”关系中,我将另一关系者视为可以对等交流,信赖沟通的另一主体。“我——你”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主体“我”对客体“它”的利用占有关系。“我——它”关系对于实践“我”的主体性,成就“我”的辉煌人生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关系,如中学教师通过严格督促学生学习的方式促使学生获得好的成绩,自己成为优秀教师,获得表彰奖励。但是假如“我——它”关系扩大为一种普遍关系,那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会出现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就会出现自我中心主义。因此,将包含有动物、植物以及她、他的关系者视为人,尊重他们的主体性和存在,以一种主体间性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主体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文学包含了人性的各种复杂性和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同时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主体间性思想,抓住文学知识中的主体间性,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讲解,对学生理解主体间性对人类之必须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如,古希腊文学中便蕴藏着丰富的主体间性思想。在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整个剧情的展开都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即“寻找导致瘟疫的罪魁祸首”,而寻找的思路和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瘟疫、洪水、地震、干旱、火灾等自然灾害,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天灾,面对天灾,我们喊出的口号是“苍天无情人有情”等。而在古希腊,忒拜人乞求他们的国王俄狄浦斯,俄狄浦斯采取的做法是:第一,向太阳神阿波罗求神谕;第二,表示自己会按照神意严惩凶手;第三,找先知判断谁是凶手。这些答案只要是对戏剧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但我们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去了解戏剧,就会发现里面包含不同于今天的天人关系理解。把瘟疫、地震、洪水等看成天谴和看成天灾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体现了人不同的姿态。将灾害看成是天谴,意味着人类开始反思自己行为的正确性,怀疑自己是否做了错事,求神示是想进一步明白自己究竟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以便知错就改。这是“我——你”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而“你”是被看成神的自然,尽管这种交流方式现在看来显得荒诞可笑,但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敬畏心理,将自然看作有灵性、能以自己的方式与人对话的神,这体现的是主体间性。其现代意义在于,重新审查作为整体的人类行为是否导致自然环境的大改变,如何减少自然灾祸的发生,实际上这也正是今日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进行的工作。
主体间性使得人们在面对灾难时,随时反思自己的行为,自觉地将人的行为本身纳入一定的伦理规范之中。将灾害看成天灾,就是将灾害看作不可理喻的偶然的自然灾难,这种灾害既与人类的过往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又毫无来由,不可解释,因此面对天灾,需要的是抗争、战斗且战胜,而非和解。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自然在这里是“它者”,“我——它”之间“我”是主体,“它者”是被征服改造的客体对象,而非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象,这里彰显的只是人颇富掠夺性的“主体性”。“我——你”间对话成功的前提是承认对话方各自的不足,然后进行调整。“我——它”间不存在对话关系,因为“它者”不在场,不能发声,只要一发声就不再是“它”,而成了“你”。“我——它”关系中只有“我”的发言权和“我”的主体性,“它”的主体性根本不存在。以“我——它”方式存在的“我”即便能够取得暂时性胜利,也必然是以牺牲“它”为代价。自然作为“它者”被牺牲掉,但自然同样是人的生存前提之一,因此牺牲了“它者”也在相当程度上等于牺牲了自己。审视古希腊的瘟疫解决方案,虽然显得不太可信,但其中人的反思品格却是今天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需要借鉴的。科技再伟大也掩饰不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主体间性的姿态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同样,《俄狄浦斯王》的最后一段,也写到应对人生作长远的判断:“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7]人生并非一个累进的过程,成绩的高低固然重要,但从长远来看,会有很多因素发挥作用,没有必要计较一时的得失。很多筹划没有办法通过计算来进行。精于算计虽然是现代社会养成的习性,但现代社会同样要遭受自然的无情鞭打,需要承受更多不确定因素,文学反复提示我们计算型人格的不可取。人生理应有多纬度的价值,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才是令人敬畏的。
文学作品中伟大的爱情也常以“我——你”的充分理解为前提,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新爱洛漪丝》中的男女主角们,正是因为尊重对方的感情,能够互识,才值得敬重。这种主体间交往因为有了尊重和理解,显得格外纯洁,同时更符合人们公认的伦理道德。假如一方通过各种手段去迎合另一方的感情进而占有他人,即便是最终能够成功,怕也只是一种孽缘。这部作品中的爱情都是没有经济维度的。就恋人交往中的主体间性问题,师生从日常生活及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许多可以谈论的话题。这样传授——接受的教学模式就转化为“我”与“你”共同对话思考的模式,双方可以在交流中促进深度互识。
三、主体间性实践:借“悬念”和“叙述方位”改写以言取效
日常语言哲学派学者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区分了三种言语行为:以言言事、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一般意义上的讲课是用语言将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陈述出来,其主导语力是以言言事,即讲述某些知识本身,讲述不是为了产生某种行为,也不是为了在讲述者身上产生某种特别的效果。这种状况在高校教学中较常见,典型表现是教师上课就一个人讲,下课就走,学生听与不听,来与不来都不关教师的事。从表面上看,这种方式给了学生极大自由,其实是将学生看作客体的一种典型表现。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在讲的时候通过悬念式言语引发思考,从而进一步激起主体间的交流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悬念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只有通俗类文艺、探索解密以及娱乐类影视节目才会频繁使用的技巧,是一种吸引受众的手段。但从话语能力而言,悬念具有的效力远不止于此,悬念可以设定注意力导向,并引发积极的思维,力求对话者对悬念本身做出完整的意义阐释。悬念的作用在于通过“留空”的方式调动人的意义阐释本能。在这种“留空”待解的过程中,作为教师的阐释者和作为学生的接收者便有了沟通交流的空间。因此,课堂教学应该借用悬念来调动学生的意义阐释欲望,促使师生之间就知识展开主体间的交往,以言取效。实际上,将学术变得通俗,这种工作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做得很成功。《百家讲坛》组织节目的常用技巧便是将所讲的知识先概括为一个大的悬念,然后再分解为几个小的悬念,整个节目在大大小小的悬念中层层推进。对于文学课来说,其中相当一部分确实适合采用悬念的方式来讲解,如戏剧和小说因为叙述性比较强,在讲解中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方式,尤其是学生们不太熟悉的作品。
意义的实现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可以分成三步:感知、接受和理解。教师将外国文学知识在课堂上呈现给学生,只能保证学生感知到了这些知识,至于这些知识能不能通过学生的“选择性接收”,进入到真正理解阶段,并进一步融入自己的既有知识体系中,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对不太熟悉的作品,如果经过一定程度的熟悉化处理后再通过悬念来引导学生,可以有效减少不必要的陌生信息的干扰,更好地实现与学生原有知识系统和经验的融合。
熟悉化的方法之一是尽量减少作品中拗口的外国名字的干扰,减少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以便更好地体会文学普遍性的一面。因此,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时,将拗口的主人公名字放在最后再说可以使学生便于接收和集中体会作品的创作规则并对之做出判断,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如,关于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戏剧作品《熙德》的讲解,可以采用如下方式:一对年轻男女相爱,两人父亲却是同朝为官的对手。女青年的父亲侮辱了男青年的父亲,男青年该怎么办?按照社会惯例,替父报仇,于是未来的老丈人被打死了。这时候女青年该如何处理,分手还是继续相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女青年决定分手。爱情故事眼看就要成了悲剧,但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什么力量促使故事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是战争和国王。这时,战争爆发了,男青年立下了战功。于是,国王命令女青年抛弃旧怨,与之结婚。最终,两人尽释前嫌,重结良缘。这对青年男女的名字分别是唐罗狄克和施曼娜。直接命令爱情悲剧改向的是“国王”,国王的洞察一切和英明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国王在这里代表理性的力量,男女之间的感性让位于大义,是当时官方钦定的剧情处理原则。这种戏剧设计本身就是古典主义规则的显现,也体现了外在政治力量对文艺创作的规训。由此,作品、教师、学生之间通过理解达成共识,比单纯地讲解规则更能使知识内化。同时,能使学生了解文学作品必须放在产生它的社会语境中去理解,戏剧作品的最终面貌通常是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文学写作需要采用一定的叙述方位,也即采用叙述者(谁说)和叙述视角(谁看)的搭配来展现故事世界。叙述方位多达9种,现代小说多采用限制性人物视角,也就是采取剧中某个人物的眼光来看周围世界,这带来的阅读效果是读者在阅读时会不由自主地跟随那个视角人物来评判世界。此种状况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尤为常见,如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的《洛丽塔》、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有意地限制了某些重要人物的话语权,使得读者的印象很难逃脱那些话语人物的意识,话语人物的主体性占据了霸权地位,给读者造成“偏听则暗”的现象。基于文学文本设计给读者带来的这种解释引导,可以通过叙述方位改写训练来换位思考。如,鼓励学生变化视角,采用罗切斯特、简的舅妈、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视角来重构故事,写出一个小短篇,然后分析其中的不同之处。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能够快速体会原著中其他非视角人物的立场和态度,更多地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理解故事世界;另一方面,有助于快速提高文学鉴赏水平和叙事学理论修养,领悟何种写作方式才是高水平的写作。并且,将学生的叙述方位改编之作通过互相交换、评析的方式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更容易激发多种主体意识的碰撞,带来文学深度体验中不同主体间的交锋,既可以促使学生在社会中互相理解,又可以以文学故事的虚构性为遮掩进行争辩,不至于伤了和气。
总之,主体性教育在培养人才上的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财经思维下对学习和知识的轻蔑现象令人警醒。主体性教育在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上功效显著,但其促使学生以个体占有多少为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负面意义明显。主体间性理念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识和共识,可以对主体性教育的偏颇起到矫正作用,鼓励人们换位思考,对世界人生有一个更长远的理解。在课堂教学方面,主体间性实践可以从文学内容的讲解入手进行,引导学生重视并学习文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也可以从形式上的引导入手,通过设置有意味的悬念,采取文学中的视角改写训练来增加对他人主体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