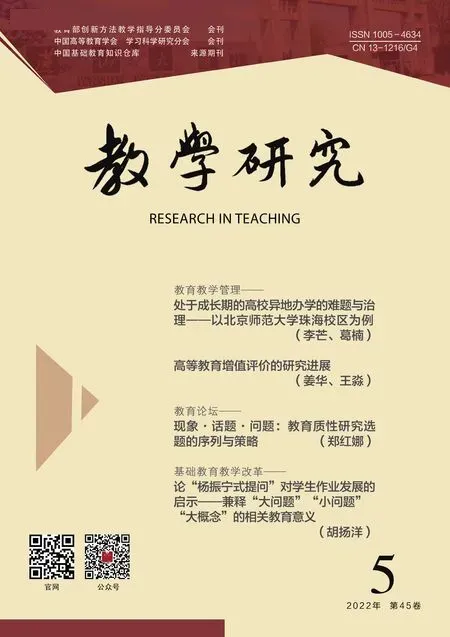我国近现代阅读实验系列研究述评
耿红卫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五四”以来,我国心理学研究开始兴起,借助课堂教学这一平台得以快速发展。艾伟、杜佐周、沈有乾、龚启昌等学者可以说不只是心理学家,更是教育家,在汉语文教育心理学实验研究方面都有着突出的建树。就阅读综合性实验研究而言,如艾伟在阅读兴趣、阅读速率、阅读理解能力等方面,龚启昌在“阅读之机能”“阅读之理解与速率”“阅读之兴趣”“阅读的方法与条件”和“阅读之教学原则”等方面,对20世纪前期国内外近20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并对汉语文阅读心理做了重点实验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研究结论[1]。就阅读专题性实验研究来说,如艾伟等学者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单项实验。实践证明,近现代阅读心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当时及日后语文教材的编写和阅读活动的开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1 阅读兴趣实验
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对儿童心理与儿童阅读兴趣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特点和状态影响着阅读兴趣的养成,同时只要阅读材料内容得当,就能刺激兴趣,诱导兴趣,育成兴趣。
1.1 艾伟的阅读兴趣实验:反复求证,力求科学
艾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注重阅读的实效性,在汉语文阅读心理方面的实验研究成果硕丰。1938年9月,艾伟以某小学五六年级上学期9名学生为实验对象,以16篇文言文为实验材料,组织实施了第一次阅读兴趣实验。他按照学习内容将文言文材料分为四大类,即儿童故事、惊人的描写和叙述、生动的描写与叙述、静的叙述。让每位学生将所学的16篇课文按照自己的兴趣大小进行等第的排列,最后将学生排列出来的文章兴趣的等第加以平均,进而观察位于不同等第文章的所属特性。此次实验的结果为:由于所阅读的文章特质不同,学生的阅读兴趣也会有很大不同,学生最感兴趣的是儿童故事类材料,比较感兴趣的是惊人的描写与叙述类材料,一般感兴趣的是生动的描写与叙述类材料,而兴趣不高的是静的叙述类材料。但是,就这个实验研究而言,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并不高,结论也比较片面,对当时教材的编写参考价值也不大。究其原因,该实验存在被测试人数过少、文言文材料偏难且数量有限、实验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也不够科学等诸多制约因素。
在汲取第一次实验教训的基础上,艾伟于1939年6月再度举行较大规模的阅读兴趣实验。该实验以四、五、六年级下学期26名小学生为测试对象,实验材料为当时通行的教材,随机从中抽取数篇文章,体裁既有白话文也有文言文等,主要采用等第的办法,对文章的兴趣的评价结果进行表达。被测试文章按照兴趣等第由高到低排列为:《刮骨医毒》、《好妹妹》(一)(二)(三)、《千里寻父》、《鸽子医生》(一)(二)(三)、《鲁宾孙漂流记》、《世界最大民族》(一)(二)、《喜雨》、《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愚公移山》、《黄天荡之役》(一)(二)、《出塞》、《最早的火车》、《书籍的故事》、《夏日的田园》、《水的旅行》(一)(二)、《交通大道》、《劝种牛痘》、《蒙古人骑马》、《报告乡村生活的一封信》、《窑居生活》。实验结果为:学生对于阅读读物兴趣相近,阅读兴趣的浓与淡和读物特质转变有紧密关联性,学生对惊异、生动、动物叙述、谈话式、幽默、情节、男性、女性、儿童等类读物最感兴趣,但是对于成人、静的叙述、知识灌输、道德暗示等类读物阅读兴趣不高。学生对于韵文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偏爱,对于文言文与家庭生活经验类的材料兴趣不高,甚至淡然,没有白话文受欢迎。究其原因,与阅读的难度关联度不大,与学生的生活经验接近的阅读兴趣会高一些。在实验研究中,他认为,作家应当熟悉儿童发展的心理,同时要多创造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唯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2]。由此可见,第二次阅读实验相比首次实验而言,在实验对象、材料、方法等方面都有所改进,增加了实验的信度和效度,无形中也提高了实验结果的科学性。
到了20世纪40年代,艾伟开始在初中进行“由背诵结果分析学生之兴趣”“学生对读物兴趣之评判”等多个阅读兴趣实验。其中最为典型的实验就是艾伟通过背诵来观察学生对阅读内容的兴趣。此次实验材料均为初中国文教材的文章,共计43篇,被试学生16人。背诵等第为1~27,实验表明:兴趣最高者为《陋室铭》,最不感兴趣者为《瓯喻》。实验的结论是:(1)初中的学生最感兴趣者为惊人或奇异的叙述,如《口技》等;(2)学生也喜欢描绘生动或者带有情感叙述的文章,比如《捕蛇者说》等;(3)容易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包括幽默、奇辟、别致的韵文,如《归去来辞》等;(4)另一个为学生所欢迎的阅读内容就是伟人故事或者儿童故事,如《岳飞之少年时代》等;(5)简短的游记与教条有时也能使学生感兴趣,如《座右铭》等;(6)学生们不感兴趣的内容则是包括《习惯说》等这些刻板的理论以及类似《瓯喻》的静态的描述;(7)就文章形式而言,初中学生喜欢文字简洁、叙述曲折、浅近易识类的,如《口技》等;而最不喜欢文字艰深、生涩、难于了解类的文章,如《战国策》各篇等[3]。实验表明:就各种读物而言,儿童的阅读兴趣不随成人的喜好而转移,成人喜欢的读物,未必就受到儿童的欢迎。因此在阅读学习中,儿童阅读不喜欢的内容,教学质量就会降低。这一实验结果备受当时学界的关注,成为语文阅读教材编写的主要参考依据。
1.2 胡士襄、江文宣等学者的阅读兴趣实验:扩大规模,力求实效
在艾伟的指导下,胡士襄、江文宣于1943~1944年间,以初小三年级上学期至高小二年级上学期685名学生为测试对象,进行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阅读兴趣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学生对不分阶级性别的儿童故事;儿童现实生活的叙述与描写类的文字材料;惊人的叙述与描写,包括冒险故事;拟人叙述的诸多动物故事;赞颂祖国的爱国故事;能够满足儿童心理需求的幽默故事以及具有儿童感兴趣的人物故事或时事报告等读物材料最为感兴趣。然而,学生对于自然、卫生、公民等常识性知识;枯燥乏味的应用文材料;成人角度写作的作品,不论是幽默、讽刺类的,还是机智、勇敢类的语言风格;含有道德驯化类的材料以及平铺直叙、内容单调等的劣质文章,均表现出反感和厌恶的情绪[2]。此次实验研究方法与前几次基本相同,其价值非常明显,在于以存在的大量样本为基础,证实了其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此研究与艾伟的同类研究结果相近,对于当时国语课程与教材改革、教学方式的变革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通过对以上学者关于阅读兴趣实验研究的梳理发现,中国的儿童对于国语、国文的阅读与美国儿童对于英语的阅读一样,尽管材料不同,但阅读兴趣趋势基本相同。就读物的特质而言,儿童对惊异、生动、动物叙述、谈话式、幽默、情节、男性、女性、儿童类的阅读材料感兴趣,而对于成人、静的叙述、知识灌输、道德暗示类的阅读材料兴趣不足。从国外的同期研究看,美国儿童对道德行为叙述类材料也最不感兴趣。可见,中外儿童的阅读兴趣点大体是相同的。研究发现,儿童读物的深浅程度、儿童文学的优美程度及读物的内容,此三者之间有密切关联,但是儿童的阅读兴趣与读物的难度则没什么关联。就文言文与白话文学习而言,与阅读兴趣关联度不大,但是文言文读物的选择要重于白话文。
2 阅读速率实验
2.1 汉字直排横排对阅读速率的影响:实验中确立汉字横排的优势
从商代甲骨文诞生之日起到近代时期,我国文字不管是甲骨文、大篆、小篆还是隶书、行书、楷书、草书,均为纵行书写与编排,一行十几字到几十字不等。阅读者的习惯是从上向下,从右到左。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晚清政府的国门,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也是中华民族屈辱史的开端,中华民族不仅遭受到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而且来自西方的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也日益加剧。同时,在这种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学习西方一些新式教育理念,外语学习一时成为时髦。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到以拉丁文字为主的外国文字的编排方法和阅读方法与国人的阅读习惯不同,即从左至右编排,且为横读。当时受到西方文字编排的影响,我国开始尝试汉字的横排实验。比如,1904年编写的《汉语字典》是第一次汉字横排的印刷品,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等也陆续采用了横排版。在民国初年,作为方块字的汉字横排与竖排印刷混杂与并存的局面十分严重,也没有统一的编排标准。这一现象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教育心理实验来对比中西文字编排方式与阅读速率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汉文而言,哪种编排方式更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更符合人们的阅读规律,依然是争执不断。
比如,1918年,张耀翔以中国留美学生为对象做了一次中英文阅读速率实验,实验结果是直排好于横排。1925年,沈有乾依然选择中国留学生作为被试对象,做了一次关于中英文阅读横排或直排材料的实验,用照相机记录被试者眼球注视的时间、字数,以秒为单位作为读取字数多少的衡量标准。研究发现:被试者在阅读中文时,眼睛运动的角度要小于英文,阅读竖版文字,眼睛停顿的次数要多于英文,就每秒阅读的字数而言,中文数量多于英文数量。最后得出了要想提高汉文阅读速度,就需要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在文字编排上就必须采用横排印刷的结论。同年,陈礼江、哈尔以两篇汉语散文为实验材料,做了汉字直排与横排哪种方式更适合阅读的研究,最终的结论是两种编排方式无优劣之分,只不过阅读速率纯粹受到个人阅读习惯和阅读训练的影响而不同罢了。赵欲仁等学者在1925年的实验证明了横排比直排更有利于阅读与写作。1929年至1930年前后,周先庚的研究结论是:影响诵读速度最关键的是汉字的格式塔和汉字的位置,而汉字的横读速度与竖读速度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异。由此可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汉字的横直排对阅读和写作速度的影响问题尚无定论,横排优于直排者有之,直排优于横排者有之,直排、横排无所谓优劣论者也有之。不过,就当时诸多实验的科学性而言,由于个别学者的研究对象是成人留学生,研究方法上过于注重主观推理以及经验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所研究的结论可靠性不高。
艾伟在1927~1928年采用速视法,通过看无意义的材料进行汉字横直排的研究,科学性比较强,现作重点阐述。艾伟的横直阅读实验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实验共有280人,其中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各100人,高中一年级80人;实验材料分为白话、文言及无意义汉字三种。第二种实验共有160人,男女生各半,均为高中一年级学生,实验材料中所有汉字纯属于无意义的,只是各组的笔画不尽相同。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艾伟借助表格数据统计方式使研究结果更加彰显,核心内容为:(1)在白话、文言以及无意义的汉字中,均为直行成绩比较优秀;(2)三种汉字形式的成绩比较,白话成绩最为优秀,文言次之,无意义者最次。这种情况在横行、直行中也如此;(3)就横行与直行比较而言,白话、文言、无意义三者之中,横行速度相对较快,但同时错误也较竖行多;(4)在不同笔画(无意义)的各组字中,其成绩速度和笔画数不一定成反比;(5)就两性差别而论,横行与直行表示的差异并不明显;(6)在不同笔画(无意义)的试验中,横行成绩远优于直行成绩;(7)通过对两组实验结果的比较,平均成绩中横行的成绩较为优秀。在系列研究中,艾伟得出低年级直行阅读较优而高年级横行阅读较优(无意义材料表现更为明显)的初步论断。为了进一步印证此观点,他在参考杜佐周、陈礼江、哈尔、沈有乾等学者研究意见的基础上,排除阅读习惯和熟悉材料的干扰,通过速视法,最终得出横行阅读速率大于直行阅读速率的结论。
以上几位学者对于汉字横排与直排(竖排)问题的研究,最终使横排成了汉文的主流,对当时各种教材及印刷物的印制有着积极的社会价值。但如何排版问题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依然争论不断。随着汉文横排在阅读中的优势愈加凸显,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逐步取代汉文直排,并得以广泛推行。1949年,新中国制定简化字拼写方案,决定使用横排印刷。目前,除了出版个别古籍以外,其他纸质文本和资料均采用了汉字横排的形式。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钱玄同、陈独秀等学者的提倡,以及艾伟、杜佐周等学者的实验研究是分不开的。
2.2 篇幅长短对诵读速率的影响:默读的速率要好于朗读
传统语文学习的经验之一就是多诵读一些经典篇章,这是学生积累知识、发展语感、学好语文的有效途径之一。如何提高诵读效率问题不能仅凭直觉和经验,还需要一定的科学方法来验证。20世纪30年代,艾伟对此做过四次分项实验研究。首先是“篇幅长短与诵读速率”的关系研究。实验材料为64字到302字的文言文若干篇,在教者讲解清楚后,让被试者诵读一篇数遍,直到会背为止,并记下每次诵读的秒数。这样的背诵课文实验,不仅可以看出学生读的遍数与费时多少的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出学生智力上的差异。其次是“文章内容在背诵与默写上的影响”的研究。实验材料为初一文章中的7篇,让学生熟读成诵,观察学生诵读次数与阅读内容深浅之间的关联。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艾伟认为:《陋室铭》一文语言比较风趣幽默,《马说》一文所述多是儿童常见的动物,了解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这两篇文章费时短,易读易记,且不容易遗忘。而《春夜宴桃李园序》字数并非最短,但费时最多,原因是文章立意玄诞,内容枯燥乏味,非学生兴趣之所在。《孔子世家书》《曾文正家书》之类的文章,多是空泛的道德说教,内容也很枯燥,所以儿童也不愿意读,即便会背也容易遗忘。再次,文章的体式研究。采用高中二年级的散文和韵文各两篇,分析其对诵读速率的影响。最后,年龄的影响研究。分别对儿童与成人、儿童与老人的诵习速率作了比较。艾伟通过整理与分析,综合四项因素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在四个因素中,文章的篇幅长短对诵读的影响最大;(2)文章内容也是影响诵读速率的因素之一,但往往与学习者的兴趣相关;(3)文章的体式,不论是散文还是韵文,都能影响诵读速率,这是学习方法及习惯造成的;(4)年龄使诵读速率有差异,但组间差小于组内差[3]。对此实验,艾伟曾评价道:“在学习心理实验班里最近八年来所作类似的研究非常之多。其所获得的材料并由此而拟定的原则,足够我们编辑一部合乎儿童学习心理的初中国文课本。”[4]
同期,有学者做了整读、段读实验,得出的结论是:篇幅小于300字的文言文,整读速率高;而篇幅在300字以上的,段读的成绩较优。还有学者通过对800名小学生的朗读行为和默读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学生年龄不同,对朗读与默读的理解和速率不同,年级越高,理解和速率就会随之增加;从理解的角度看,朗读比较适合低年级学生,而默读更适合高年级学生来理解阅读内容,从速率的角度看,朗读低于默读。通过一系列阅读速率实验表明,朗读的方式固然很好,但是通用于中小学各个年级,以小学低年级尤胜,可以多采用此学习方法。而对于高年级以上的学生,随着年龄的增加和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默读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速率,应以此类学习方式为主。因此,就教师教学而言,建议要重视儿童的默读习惯,因为默读习惯是制约默读速率的重要因素,小学低年级尤甚。国外同期的研究表明,在阅读理解方面,默读好于朗读,尤其是小学高年级表现最为明显,而默读习惯是否养成与阅读速率和理解力的高低有正关联。朗读教学也不容忽视,对于一二年级的儿童阅读兴趣的培养,显得尤为关键,因此,教师要在朗读材料、朗读技法上给予指导。近现代艾伟等学者的有关研究尽管还不太符合严格的实验程序,但他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今天看来也是比较正确的,对于语文阅读方式和模式的变革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3 阅读能力实验
3.1 默读能力:多种因素制约默读能力的高低
我国古人学习重视朗读、诵读和吟咏,但也在大量地从事着默读教学实践,但从实验研究的角度看,到了20世纪20年代默读才被学界重视起来。在众多学者的实验中,以艾伟关于默读能力的实验最为突出。1936年艾伟为了深入了解学生阅读的速度与理解程度,对其默读行为做了一系列实验,研究的结论是:第一,阅读理解力与阅读速率成正比,默读能力与智力成正比。比如,在一秒钟内读7个字或8个字的小学生,其理解力就强于能读5个字或6个字的小学生。第二,中国孩童的默读速率与理解都可以借助训练而逐步提高。认为中国的默读训练太迟,强调应从三、四年级就开始有意识地组织训练。第三,原本默读能力差的学生经训练进步较快,而原来默读能力好的学生经训练进步较慢。在这些实验中他总结出国语默读应具备迅速浏览撮取大意、精心评读记取细节、综览全章挈取纲领、玩味原文推究含义等四个方面的能力,据此编写有“中小学各级默读能力测验”(有常模)材料,并得以广泛推广和使用。通过对有关默读能力的实验研究发现,儿童在迅速浏览撮取大意、精心评读记取细节、综览全章挈取纲领、玩味原文推究含义等四个能力方面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儿童在玩味原文推究含义这一能力方面表现最为薄弱,这与此能力难以养成和不够重视有关。此外,同一年级儿童之间的能力差别大于年级之间儿童阅读能力的差异。
3.2 阅读理解能力:与知识背景、联想能力等有紧密关系
对于阅读理解能力,艾伟曾为此做过专门实验,实验在南京某女中进行,应试者为初高中六个年级72人,每个年级12人,所有应试者国文成绩均为优良。阅读材料为第二次编制的国文理解力测量量表甲,其中文言文1篇,共926个字;白话文1篇,共1 763个字,设计问题为20个。应试者共参与五次解答,对五次结果做出比较[3]。研究发现,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主要有三种:第一,理解是一种思维习惯,是一种本能的主观反应。有些人的理解力已经达到一种习惯的高度,遇到熟悉的事物就能够立刻反应。对于这种阅读理解习惯已经高度养成的人,他们在阅读经验范围内的书籍的时候,能够达到迅速联想、一看就懂的情形。第二,对于内容比较深的书籍或资料,需要慢慢阅读,长时间联系性阅读作为理解能力的有效补充,使原来本能的反应得以巩固和提高。第三,尽管阅读者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但对于阅读中遇到的新的生字词及难以深入理解的内容,需要多次反复阅读方可达到理解的效果[5]。概而言之,主要包括纯粹理解力、记忆理解力、文字连贯上的理解力,这三种理解能力其实与学生的知识背景、联想能力及阅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很显然,学生如果具备厚实的先前知识经验作为基础,具有快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么就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
3.3 文白能力:凸显文白学习的渐进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大,很多学者倡导彻底废除文言文的学习,主要学习白话文、语体文。然而,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深,很难说立即废除,更何况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弘扬和继承。20世纪20年代的文白之争,最终在“以学习白话文为主,兼学文言文”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教授文言文,学生应具备怎样的文白阅读能力,学界没有统一的看法。为此,艾伟做过三次实验,但每一次结论都有差异。1926年艾伟在上海、南京、杭州三地做第一次实验。通过实验,他认为对于儿童而言文言文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建议小学语文教材中删去文言文,在初中语文教材中遵照由易到难、文白比例(随年级的增高加大文言文学习的分量)的原则编写一些文言文让学生学习。1928年以来,艾伟在北京、天津和苏北等地进行第二次实验。几年的实验表明,学生无论在文言文阅读理解方面还是在阅读速率方面,都比白话文进步慢,因此,他建议文言文教学应从初一全面展开,只教授文言文而不教授白话文。1940年以来,艾伟在中山大学实验学校进行第三次实验。当时他主持该校的教学工作,以小学高年级学生为实验对象开展文言文阅读教学实验十分便利,实验的效果也好于往年。实验的结论是:高小是开始文言文教学的最佳时间。通过对艾伟的系列实验分析发现,小学生白话文理解程度好于文言文,文言文学习时间不宜过早,最好在高年级进行。而中学阶段,就文白程度而言,从初一到高三,学生的理解程度逐年增高,即年级越高,无论文言文或白话文,成绩均随之提高。但是文言文的进步不如白话文迅速,尤其是对于语文程度比较薄弱的学生而言,相对聪明者、语文程度好的学生,文言文的进步也比较迅速,但多不及白话文进步快,或许与学生的生活经验及语言习惯、语言环境等有密切关联。艾伟关于学生文白能力的研究、中小学文白能力的分级测量研究,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对于学界文白观念的转变以及教科书文白比例的编写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4 结语
从近现代阅读实验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心理学有密切的联系,并逐步走向人性化与科学化。关于阅读兴趣的研究,实验围绕学龄儿童展开,根据文章的特质进行兴趣等第的划分,最终发现国语教学应该根据孩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来制定更适合学生学习的内容。有关阅读速率的研究,通过“汉字直排横排队阅读速度的影响”以及“篇幅长短对诵读的影响”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实验,并通过对白话、文言以及无意义的文字进行多方比较,最终得出横排是最适合中国人阅读的排版印刷方式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应针对篇幅长短来制定不同的诵读方法,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优化。关于默读能力的研究,艾伟认为默读能力和理解力与智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归纳出了默读能力的四要素,依据此编制出广为流行的中小学默读能力测验,指出人们的阅读能力与个人经验背景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此外,还对文言和白话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随着阅读心理实验的不断深入,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更新,最终得出了文言文教学应从高小开始的结论。由此不难发现,语文教育的科学性正在深入人心。总之,受西方现代教育观念的影响,近现代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此为契机来改造中国的教育。
艾伟等学者在阅读心理方面的实验尝试,使得更多人认识到实验科学、教育测量等理念和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阅读教学改革实验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科学主义教育思潮以及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国语文教育迎来了改革的春天。阅读教学领域的改革实验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比如,钱梦龙主持的“语文导读法”改革实验,旨在以发展学生的智能为前提,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要目标,让学生通过三至六年有计划的训练,达到“不待老师讲而学生自能读书”的目标;蔡澄清的阅读教学“点拨教学法”,通过点拨,启发学生开动脑筋,引起共鸣,达到掌握知识并发展自学能力的目的。另外,曾祥芹主持的“新概念阅读教学”散发训练体系(精读、略读、快读)改革实验、顾德希承担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教法”实验研究、程汉杰主持的“快速阅读”改革实验、晏茂新主持的“四级台阶速度训练研究”[6]、窦桂梅的“主题阅读”教学改革实验、韩兴娥的“海量阅读”教学改革实验等阅读教学实验,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对当今新课程标准的制定与修订、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以及阅读教学课堂实践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