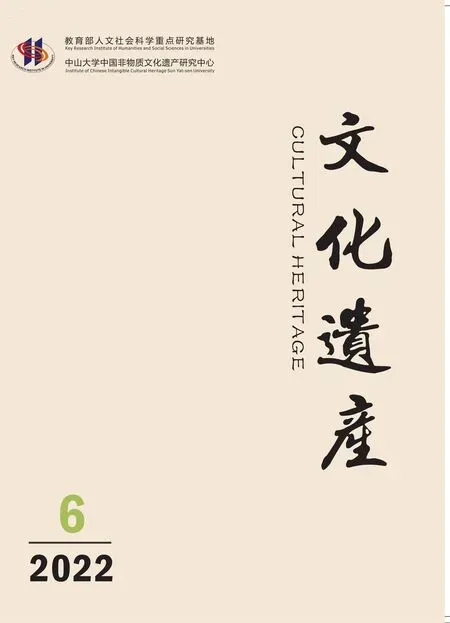何为“真”:学术史背景下顾颉刚“真”之观念的演变
周争艳
学术以求真为本职,但学者在求真的同时又不能不兼顾致用,如何在求真与致用的天平上找到一个平衡点,大概是令不少知识分子都苦恼的一个问题,在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20世纪上半叶就更是如此了。章太炎、康有为、胡适、傅斯年等都曾就学术求真与致用问题发表过见解。顾颉刚对此亦有很多想法,甚至抱持双重情怀,他既追求学术之真,又关心学术之用,颇有鱼与熊掌都想兼得之累。1928年6月25日,顾颉刚为杨成志所译《民俗学问题格》作序,曰:“大凡学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理论,一方面是应用。没有理论,应用的泉源就要干竭。没有应用,理论也不会发生实际的效果。”对于五、六年前所提倡的“到民间去”之口号,若要实行,“也应当有两部分人分工做:其一是专门做研究调查的工作的,其一是把研究调查的结果拿去设施的。前一种人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宗教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后一种人是政治家,教育家,社会运动家。”(1)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这里,顾颉刚主要将“到民间去”视为一种学术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实践,就需要理论与应用结合。
不过,顾颉刚的态度并非始终淡定如斯,对于求真与致用及它们在个人选择中动辄失衡的微妙关系,他曾有过复杂的心理斗争。近年来,关于顾颉刚求真与致用观念、求真与致用之间两难和两全的分析文章开始增多,这些文章有大体相同的研究视点,或从史学角度立意,或以国家-民族的危机为进路。本文认为,既然顾颉刚曾沉浸于歌谣、故事研究,并曾以孟姜女故事等材料为载体开展古史辨伪,那么,民间文学领域内的歌谣运动和歌谣、故事的研究成果,同样可以成为顾颉刚真之观念研究的出发点。
一、真与歌谣运动
先秦已降,求真与致用一直难以调和,甚至尖锐对立。至晚清,求真与致用之争更是“演变成了既含学派又含政术的大论战。”在这样一个“寻求政学分途而又需要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的时代”(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需要在求真与致用之间做出抉择。章太炎独尊实事求是,康梁一派力求经世致用,双方观点彼此拮抗,成为20世纪开端求真与致用之争的最典型案例。学术要不要致用?要怎么用?求真与致用之争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曾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能置若罔闻。总的来看,民间文学界对真的表述有以下几种情况:
(1)韦大列(Guido Vitale)的“真正的诗歌”说。1896年,在《北京的歌谣》前言,韦大列交代了搜集北京歌谣的三条方法与宗旨,最后一条是“读者还可悟出,真正的诗歌很可能在中国民歌中觅得源头。”(3)Baron Guido Vitale, Pekinese Rhymes(Peking: Pei-t’ang Press, 1896), vii.还说,“我们因此可以预言,中国的民族新诗歌的样式一定会在这些情真意切的民歌基础上产生出来。”(4)Guido Vitale, Pekinese Rhymes, ix-x.
(2)韦大列不会想到,他为中国歌谣记上的一笔会在歌谣运动中得到浓墨重彩的描画与渲染。1922年,周作人等(5)学界普遍认为发刊词的作者是周作人,施爱东认为这一说法未能叫人焕然无疑。详见施爱东《〈歌谣〉周刊发刊词作者辩》,《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为歌谣搜集工作找到了两顶合适的帽子:“学术的”与“文艺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热情地拥抱和推广韦大列“真正的诗歌”的说法,在“文艺的”条目下,“发刊词”的作者们这样说:
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6)《发刊词》,《歌谣》周刊,1922年第1号,12月17日。
韦大列“真正的诗歌”的说法点燃了周作人等凝固在身体里的爱好。周作人本身就非常喜欢自然实在、真情流露的文学作品,对于真他更是情有独钟,他多次称赞民歌、神话、传说的真挚与诚信。“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7)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页。周作人还认为,神话和传说也能传达民众最率真的心声,表达民族的思想和情感。
(3)《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也出现了“真”的字眼,撰写者刘半农还对真做出了附带说明:
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
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由寄稿者加以甄择。(8)刘半农:《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歌谣》周刊,1923年第26号,9月30日。
(4)胡适不仅接受韦大列“真正的诗歌”的说法,更从古代文学史中打捞民众的真之情感。他说,“但从这些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自然地产出这些活的文学……他们不能等候二十年先去学了古文再来唱歌说故事。所以他们只真率地说了他们的歌;真率地唱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切平民文学的起点。”(9)胡适:《白话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可见,在现代歌谣运动中,真不得不以两副面孔(10)崔若男认为,真包括真的语言和真的情感。对于前者,作者说:“‘真的语言’主要体现在歌谣中的口语与方言,以及口语与‘诗’的关系上。”崔若男:《韦大列〈北京的歌谣〉与中国现代歌谣运动》,《文化遗产》2020年第2期。“两面作战”。一方面,学术的追求就是真,科学客观、价值无涉是其最起码的内涵。换言之,真是一种规范的学术标准。为了研究的真实,无论是材料中夹杂的方言不合乎北京官话的用语习惯、文法构造以至于读来别扭、拗口,还是材料愚陋、迷信以至于思想陈腐,或者是内容过于浓艳、低俗以至于猥亵、淫秽,从民间搜集到的歌谣材料都不应该被冷眼看待、刻意删改或有意避讳,忠实地记录就好。正如《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明确陈述的那样,“歌辞文俗,一仍其真”“附注字音”“详注其义,以便考证”等。另一方面,真与“文艺的”追求有关,它是文学文体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情感表达的真实状态,如胡适和周作人在文学的角度强调的真的情感、真的情趣、真的哀怨等。就此而论,真就是民众或民间文学作品中情感的真实、纯粹。
学术之真与情感之真在歌谣运动中“梦幻联动”,胡适和顾颉刚是为数不多同时属意过两种真的人。顾颉刚既因任职《歌谣》周刊的编辑与周作人打过交道,也作为胡适的弟子,在学术上与胡适声气相投。然而,他很少像周作人和胡适那样,做“文艺”的入戏观众,尽心“叫卖”“文艺”,而是心折于学术之真。不过,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顾颉刚也发现了“文艺的”魅力,印证了民众的情感之真。
二、求真:顾颉刚的学术意志
顾颉刚特别注重研究方法的学习与总结,如有清一代重事实的考据、康有为西洋历史家考订古史的方法、胡适西方的实验主义及科学研究方法(演变-辨伪-伪史的背景-演变线索)(11)详见户晓辉《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等。这些科学研究方法都统摄在一个目标下面:求真。
在经历新文化运动而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中,顾颉刚是在学问求真主张中独领风骚的一位。1925年,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一文中,顾颉刚说,他希望专事空谈的人看看实做研究的难处,“我的工作,无论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为考据、思辨、博贯、综核、实事求是,我总是这一个态度。”(12)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0页。即研究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切实的工作,而非说来便来、华而不实。顾颉刚多次说明他喜欢追求学术真理,不愿做别人的应声虫和奴隶,因此特别注重学术事实和真相,喜欢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比如,他说,“我们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1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页。接着又说,既然自己的目的在于辨认东周、秦、汉间发生的伪史,那么对于此期间的时势、思想、制度,都要寻出一个真相来。还有“我们要秉着纯粹求真理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所以不容得把个人的爱憎参入其间。”(14)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9页。诸如此类。总之,实事求是、求真是顾颉刚学术研究的一个醒目的追求与特征。
所以,讨论顾颉刚的民间文学研究,不能不首先回到顾颉刚求真的学术目标上来。此间,有两份文献值得特别注意:《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和《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的求真意志、对民间文学的态度与研究的原动力都在这两份文献中体现了出来。
(一)求真与应用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写道:“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2页。学问当问真,不当问用,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在顾颉刚的学术研究中。而章太炎、康有为的学说对他这种想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1)章太炎的薄致用而重求是。1913年,顾颉刚始遇章太炎,章太炎渊博系统的古文讲述启发顾颉刚开始对学术求真问题的认真思考。顾颉刚自述道,自己日后如果能在学问上取得一些建树,“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16)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2页。不过,虽然顾颉刚一直坚守章太炎的学术观念,但他逐渐觉得,章太炎过于信古,且其求是信念屡屡动摇,并不纯粹。顾颉刚不愿意追随任何偶像,他发现古史中有不少伪史、伪书,他要辨伪,推翻伪史。
(2)康有为的古史今用。作为古史辨伪的先行者,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给了顾颉刚直接启示。他非常佩服康有为的卓识,但也不满意于今文家康有为拿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功利用法。顾颉刚批评康有为们的这种做法是“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1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8页。顾颉刚拒绝压抑自己的直觉和理性,而屈服于哪个人或哪种传统学说的命令,在他看来,学问、辨伪的任务就是求真、求事实(1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7页。,而非政策应用或取得什么利益。
顾颉刚说,“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他坚信,夹杂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赏绝不能成为真的欣赏。“我的意思,不过要借此说明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酝酿出一些成绩来,这些成绩便不是在实效的目标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86页。越不求实效越能得到料想不到的实效,顾颉刚说自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就是他在不求实效的初衷下培养出来的成绩。
在《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顾颉刚也对求真与应用之间的矛盾关系做了阐释。顾颉刚批评从前的学者,说先前的学者屈从于时代、阶级,并且“他们的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两千年余年来没有什么进步。”(20)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19页。在不少人眼中,帝王的诏谕是学术研究的史料,而妇人的弓鞋和孩子的玩具在学术研究中似乎没什么用,顾颉刚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现代研究学问的人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被事物的用途所支配。他甚至觉得,“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21)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29页。至于应用,那是做学问的意外收获,或者直接是社会改造家、政治学家们的事。
可见,在此时的顾颉刚看来,求真与致用实在是个两难问题。不过,为了学术研究,他还是选择站在求真一边,而暂时放下了自己早年对改变民族现状的赤诚与狂热。“我们原不要把学问致用,也不要在学问里寻出道德的标准来做自己立身的信条。”(22)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18-219页。并且,“彼此爱好真理之心超过了爱好金钱和地位之心,从事于努力的探求,那么,国学的进步便未始不可做他种科学兴起的先导了。”(23)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28页。
总之,在顾颉刚眼中,求真和应用虽然有时是关联着的,但总的来说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应用不是求真的标准,但凡是学问都应该以求真为初衷,而事实则是现代学术之真的一个关键根据。“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事实既诏示我们这般,我们便不能改说那般。”(24)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19页。这是说,学术研究要在材料完备、方法周密的基础上,得到真实的事实,因为即便时代和政体会变更,事实却是不会变的。
(二)求真与求平等
顾颉刚的求真也包括材料、学问和角色的平等。(1)材料平等。1925年12月,顾颉刚所在的国学门将搜集的展品对外开放。顾颉刚发现,参观的人看见考古室的鼎彝时便唏嘘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感到诏谕的尊严,但到风俗和歌谣室时,却对赌具、妇人的弓鞋、孩童的玩具表示出轻蔑的态度,顾颉刚不满意于此。他觉得,在学问上不应该有什么势利心,煌煌法典、高文典册与玩耍场的玩意儿都可以用来做学问。“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顾颉刚承认风俗物品和歌谣中有荒谬的、残忍的、秽亵的成分,但“社会上有这些事实乃是我们所不能随心否认的。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事实,我们自己愿意做的是研究。”(25)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18页。另外,顾颉刚还认为,不可用新旧的眼光去看待材料,认为历史的就是陈旧的,科学的就是时新的,这是一种功利的应用眼光。他觉得,学问不要受材料新旧这种应用眼光的羁绊,而是把“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下至今日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一律收集,作平等的研究。”(26)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21页。
(2)学问平等。材料平等带来了学问平等。顾颉刚说,“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27)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18页。他不会因为古物值钱而宝贝它,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而尊敬它,因为风俗和歌谣是民众的小玩意而轻蔑它。在顾颉刚眼中,考古、历史、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都是平等的学问。
(3)角色平等。从求真的角度出发,所有历史角色在顾颉刚眼中都是平等的,高门显贵和市井小民并没有阶级和尊卑之别。所以,虽然事与愿违,观众们多以功用和世俗的眼光做品评,但在国学门展品对外开放时,顾颉刚的初衷却是希望观众从皇帝的展品看到小民的展品时,能有一些学术平等的观念。
(三)求真与理性
求真需要对学术偶像的态度做出表决。在顾颉刚看来,一个人崇拜偶像就不会自己去寻求问题的答案,更不用说真实的见解了。顾颉刚说他的心中没有一尊学术偶像,“我用了活泼的理性做公平的裁断。”他当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这种佩服也是出于别人的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2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71页。正因为理性,顾颉刚坚守学术独立品格,不仿效任何学术偶像,不加入任何家派,并能以理性和平等的眼光对待没有势力的人、不同派别的人,不用毁誉去压抑说良心话的人。
由上,虽然顾颉刚非常注重求真,并发表了对真的理解,但什么是真呢?顾颉刚没有明确定义。或许顾颉刚认为,实在没有定义真的必要了。因为该说的他都重复多次了,即真就是真理之“真”,真伪之“真”,真实之“真”,它主要表现为某一历史事件或故事在时间上的最早形态,也即溯源性真实。
三、“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与民众的情感、想象
虽然顾颉刚试图寻求上古古史和一些故事的真相与本来面目,但古史或故事真的有终极真相吗?真的标准是什么呢?比照顾颉刚前后两年的三篇文章,即1925年的《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与1926年的两篇文章《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我们发现,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和《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顾颉刚明确表明求真态度,但在早一年的《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顾颉刚的态度却不是这样的。
(一)求真、近真与“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1925年2月3日,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顾颉刚用“近真”与“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来概括他在古史与故事研究中的求真态度。顾颉刚说,“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比较的近真,绝无圆满的解决。”(29)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12页。古史或故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一问题被顾颉刚悬置了起来。“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因为“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变化的情状,把所有的材料依着时代的次序分了先后,按部就班地看它在第一时期如何,第二时期如何……这是做得到的,而且容易近真的。”(30)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13-314页。在对待每一个故事时,顾颉刚的做法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他认为从前的人因为没有演变的眼光,所以一定要在诸多传说之中“别黑白而定一尊”:或者定最早的故事为真,驳斥种种后起的为伪;或者定最通行的一个为真,驳斥种种偶见的为伪;或者定人性最充足的一个为真,而斥含有神话意味的为伪。顾颉刚认为,这种做法把故事割裂了,且其所执定的一个故事未必为真。在顾颉刚眼中,“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31)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66页。以整体和系统的眼光将所有相关材料搜集起来,领略“故事的整个的体态”,(32)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14页。并穷其演变,才是古史与故事研究的“体”,也即新的“真”之尺度。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目标有求真、近真与“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这是否说明顾颉刚对求真的态度不坚定,甚至左右摇摆呢?毕竟从1913年左右听戏开始,顾颉刚就开始比较戏剧、小说与史书,试图从中探究某一历史或故事的本来面目,在1925年的《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顾颉刚说的却是近真与“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而在1926年的两篇文章里,顾颉刚好像又回过头来表明自己的求真志向。
其实,近真与“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并不是对求真标准的绝对颠覆,近真和“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主张的提出,主要表明历史演进法代替顾颉刚先前念兹在兹的真伪区别观念以及求历史真相的诉求,成为古史研究新的真之标准。而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与胡适的历史演进法,尤其是胡适1920年的《〈水浒传〉考证》与《井田辨》两篇文章有直接关系。
1923年,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引发了顾颉刚、钱玄同与刘掞藜、胡堇人二位先生长达九个月的论战。面对刘、胡二人事无巨细的批驳,顾颉刚并没有在禹的身份问题上完全说服刘、胡二人。1924年,双方论战结束后,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说:“这一次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双方都希望求得真相。”(33)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胡适也称赞顾颉刚“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3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80-181页。的说法,但胡适说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并且,“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35)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全集》(第2卷),第105页。也就是说,历史演进才是顾颉刚古史研究的“根本观念”和“根本方法”,而史事的真伪区分不是。这的确是胡适替在论争中深陷细枝末节而遗忘自己中心见解的顾颉刚坚定了方向——“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36)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全集》(第2卷),第105页。
顾颉刚自己在读书、看戏、歌谣搜集等经历中对古史与故事层累演进的思考,再加上导师胡适的提点与历史演进法的熏染,就逐渐搁置了上古史的真伪问题,确定了学术求真的新标准——历史演进,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提出不关注古史真相,而主张“近真”与“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重要诱因。而我们上文分析的顾颉刚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的求真主张主要是顾颉刚未将历史演进作为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之前的观念。所以,顾颉刚“真”的具体内涵发生过转变:由真伪之“真”、真相之“真”转变为材料真实之“真”、故事与传说的经历之“真”,这正说明顾颉刚对学问求真的专注,而非求真态度的不坚定。
(二)真与民众的情感和想象
不过,同样是历史演进法,胡适注重在故事或历史历时演变的线索与条理上做考量,而顾颉刚则在践行胡适历史演进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到了历史与故事演变的原因——民众的情感与想象。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中,对于伟人的神奇出生(如姜嫄履巨人迹生后稷、黑虎星下凡、文曲星降世),顾颉刚就指出,这“在事实上是必不确的,但在民众的想象里是确有这回事的:他们总以为大人物的来历与普通人不同,该有这类奇迹。”(37)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95页。也就是说,能确定的、真的就是民众的情感与想象。
顾颉刚非常看重民众的情感与想象,这在他早年看戏时已经露出端倪。顾颉刚发现,史书、小说和戏剧是层层相因,层层变化的,而变化的原因则在于编者为了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而发挥想象的缘故,但“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象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纷歧的。”(3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19页。
孟姜女故事是顾颉刚应用层累演进法或历史演进法的典型案例,正是在这一系列研究中,顾颉刚多次且大力突出民众的情感与想象,并将之定位为故事演进的一个终极原因。1925年,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一文中,顾颉刚交代了他对孟姜女故事研究持有的态度,他说,实在的孟姜女的事情,他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想知道,他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目的是“要在全部的历史之中寻出这一件故事的变化的痕迹与原因”,而不是“考定杞梁之妻的真事实。”(39)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89页。
的确,在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中,顾颉刚先是证明孟姜女故事中心的历时转变,即从战国的不受郊吊,到西汉前期的“哭之哀”“善哭”,再到西汉后期减去“却郊吊”而增添“崩城”情节,自东汉末至六朝末的四百年中,故事的中心依然是“崩城”,唐时,故事中心转变为孟姜女哭长城。同时,也关注孟姜女故事地理系统层面的问题。通过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得出了六个结论,其中之一便是:“就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上看这件故事的酝酿力。”顾颉刚指出,“与其说是这件故事中加入外来的分子,不如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上酝酿着这件故事的方式。”也即,民众的感情与想象是故事情节增减的决定力量,外界的风俗和时势只是影响故事情节增减的次级力量。不仅如此,就连孟姜女这一角色本身都是民众感情与想象的结果,“所以我们与其说孟姜女故事的本来面目为民众所讹变,不如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中建立出一个或若干个孟姜女来。”(40)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65页。顾颉刚说,孟姜女故事讲的是夫妻离别的悲哀,它与讲男女恋爱的悲哀的祝英台故事,有着相同的地位,因为民众的感情与想象中有这类故事的需求,所以它们能打破士大夫礼教传统和书面传统的束缚,凭借着民众世俗的情感与想象而日益发展。
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结果,使顾颉刚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籍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的要求的。”(41)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68页。即便传说、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感情和要求却是真实的,它是为了适应人民的需要、满足人民的希望而产生的。”(42)顾颉刚:《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自序”第17页。由此,民众的情感与想象之真和故事演变的过程与经历之真一样,都成了真之内涵。
四、求真与致用的两全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说自己一度非常想研究“中国民族是否却为衰老,抑尚在少壮?”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当时国势贫弱,这仅仅是病的状态,不是老的状态,而教育不普及,则是民族衰老的原因。同胡适一样,顾颉刚也觉得,教育是国民和民族改良的唯一路径。顾颉刚认为,手腕高超的教育家正可以从病的状态中唤醒国民健康的要求、激发国民参与政治的自觉心。只要各民族能获得相当的教育,能够自觉地努力,中国的前途终究是有希望的。顾颉刚仍然抱守着传统士大夫救国的责任感,“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唯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份子的责任。”用怎样的方法救国呢,顾颉刚的想法是:“先就史书,府县志和家谱中寻取记载的材料,再作各地的旅行,搜集风俗民情的实际的材料。”(4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79页。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顾颉刚的内心似乎不再纠结于学问求真与致用之争,而开始关注民族和民众的生存问题,致力于学术致用,求真与致用得到了两全。彼时,北大同人推选他做文字宣传工作,向民众宣传“五卅”惨案情况。怎样宣传才能使民众乐于接受呢?顾颉刚的办法是,“须用民众习用之语言和表现形式来写。”(44)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10页。他用民众语体写了两份传单:《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和《伤心歌》,其中不合北京口语的地方还经他的朋友潘家洵修改,使它们更贴近京话。这两个传单发出去后立即生效,孩子们开始传唱,刷黑的墙上也有粉笔抄录。之后,在《京报副刊》刊出的《救国特刊》专刊中撰写《〈救国特刊〉发刊词》时,顾颉刚交代了此专刊的宗旨:
一是用浅近的语言作演讲稿,可以供给演讲员的应用;二是把这次的事变寻出它的前因后果,以求不止于这一件事的解决,更进而了解多少件积案,慢慢的计划总解决的办法。
我们所希望的,是要把这次兴奋的感情变为持久的意志,要把一时的群众运动变为永久的救国运动。(45)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10页。
为此,他写了《上海的租界》《不平等条约之一——江宁条约》《我们应当继续救济失业的工人》《〈科学救国大鼓书〉序》等文章。在《〈科学救国大鼓书〉序》中,顾颉刚说:
学生们嚷的到民间去的声浪虽是常接触于我们的耳鼓,但他们毕竟只是一种漂亮话而已;实际上,他们何尝要去,亦何尝能去!这一次五卅惨案起了之后,一时的通俗传单仿佛雪片一般的飞开来,似乎智识阶级确有开通民智的勇气,但等不到两个月也就寂无声息了。(46)顾颉刚:《〈科学救国大鼓书〉序》,《京报副刊》1925年第315期。
顾颉刚认为,一般的民众不能看报,不知道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他痛觉通俗教育的缺乏,认为世界剧变,可民众接触的还是18世纪以前的智识。木兰从军、草船借箭、宝玉探病类的旧式鼓书,根本不能提供新材料、新意味,唱的人、听的人都烦了、疲乏了。顾颉刚因此感叹说,在智识不更新的情况下,“我们尽骂他们不醒,其实便是他们立志要醒也醒不了呵!”所以,他指明,写一些具有通俗艺术性、时代性和教育性的鼓书,并唱给民众听,一定可以得到他们救国的同情,使他们知道中国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顾颉刚觉得,这种行为“比了狂喊乱跳的学生们的演说的收效不知可以加增到多少倍。(学生们的演说,固然是一腔热诚,但因口音的隔膜,用语的艰深,态度的失当,使得民众听了之后感不到切身的需要,只觉得还是他们的事。)”如果将改编的大鼓书由民众素来信任的唱书人唱出,并且让民众都能听得懂,那么,“他们自然要感到救国是自己的事了。”(47)顾颉刚:《〈科学救国大鼓书〉序》。体会并唤醒民众情感成了理解和深入民间的方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顾颉刚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他创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颠沛流离远赴西北,研究边疆史和民族史,积极宣传抗日文艺,试图唤起民众的救国情感,这些举措都是学术致用主张的延续。
结 语
顾颉刚对求真、近真、“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与对民众情感和想象的强调,展露出他在寻求古史与故事演变过程中研究侧重点的转变,即从溯源性真实:古史或故事的最初真相、本来面目,转变为古史或故事的叙述性真实、民众的情感与想象的真实。顾颉刚多次表示,他想做的不是一般的史学研究,“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48)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95页。可见,顾颉刚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历史辨伪或历史演进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观念史研究,民众的情感与想象就隶属于观念史范畴。可以说,真之标准的流变、隶属于观念史范畴的民众的情感与想象,为我们回顾和反思顾颉刚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