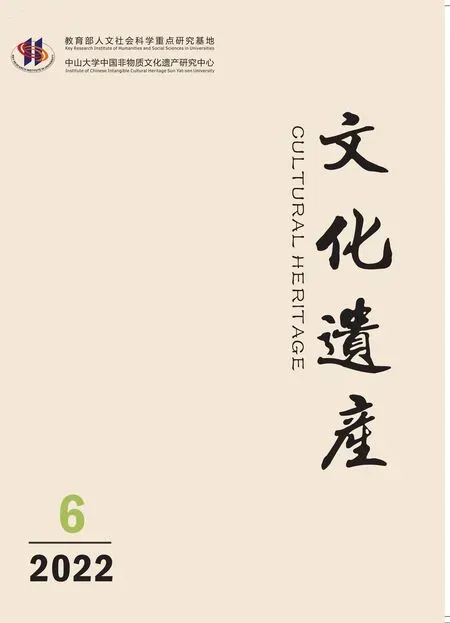从大拼盘到新生态:新文科视野中的非遗学建设*
高小康
一、非遗保护:从文化实践到学理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发生是在二十世纪后期。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届执行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布计划”条例》,正式提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概念。(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布计划’背景情况及其最新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06/0525/Document/325351/325351.htm,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2日。但只是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真正形成了比较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以及相关的保护观念、原则和实践体系,即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政治理念,以及不同政治实体之间通过交流沟通形成的促进当代世界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建设原则与实践策略。经过20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下的全球实践,非遗保护在保护的对象、原则和操作范式方面都形成了日益成熟而又多样化的形态及其成果。
然而,从非遗保护实践在全球的进展和面临的种种问题来看,不同文化共同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形态、价值、保护目的及方法等诸多问题还在不断探索中,不同国家、民族对非遗保护的理解和实践各有特色。可以说,《公约》所表达的非遗内涵、保护观念及其意义,只是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对非遗保护的理解及其实践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完整周延的逻辑与知识体系。从非遗保护的更深层次来看,非遗保护实践的学理根据研究尚不充分。一些作为世界非遗保护实践基础的知识与理念还有待深入探讨和深化发展。这些深入的学术研究,对于不同文化共同体在非遗的现代价值、保护的目的、相互理解分享的基础等问题形成深度理解的共识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非遗保护不仅是文化实践,而且需要作为指导实践理念的理论研究,即相关知识、观念及其逻辑在学理层面的探讨和交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理研究应当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中相互联系的两个层次。非遗学的理论建设所面对的是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显现的多方面问题和矛盾。我们可以从非遗保护的价值观念及其历史文化根据这样两个层次来探讨这些观念矛盾的深层文化意义及其对非遗保护实践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谈论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时指出,由于电力、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由爆炸式的外向扩张发展逆转为内爆式发展,相互联系由非部落化的发散式交往逆转为再部落化的内聚交往:“我们这个世界由于戏剧性的逆向变化而缩小了……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落。”(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页。
这就是“地球村”概念的由来。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经济贸易趋向一体化,地球村观念再度受到重视,并演化为世界贸易、政治、文化走向更加一体性联系的“全球化”概念。正是这种“全球化”趋势成为政治学家福山提出“历史终结”世界大同想象的现实政治根据。
然而20世纪的全球化并非世界大同。全球化对于不同文化实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分裂》一书中展现了近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即“全球分裂”。(3)[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迟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上册,第9-20页。具体地说就是发达国家驱动的以普世化、同质化为特征的经济、文化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共同体认同这两种政治价值之间的矛盾。冷战时代全球政治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冲突是以“第三世界”的崛起与政治对抗的激烈形态表现出来的;而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认同则表现为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立场。文化多元主义坚持每个文化实体有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有根据本族群习俗和意愿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这种多元主义价值观是对当代政治冲突和文化冲突形成的“全球分裂”危机的一种应对,体现了后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实体共享的政治正当性价值观念,即世界上不同文化实体平等共存、共同发展的理想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核心就是这种多元主义价值观。
比政治正当性更深层的文化价值在于不同文化政治观念的历史正当性问题,即文化政治价值的历史根据及其在当代语境中表现出的伦理正当性。这里存在着现代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
19世纪基于进化论和理性启蒙主义的线性历史发展观认为,历史是依据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逻辑演进发展的。按照这个历史进化逻辑,越是后出的文化形态越是高级的即更完美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4)[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页。这就是说历史不仅是按照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进化发展,而且后来的高级形态吸收了低级形态的内容。按照进化论的历史主义,作为高级文明形态的现代文化已吸纳和超越了过去的文化,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就成为历史进化的逻辑归宿。
然而在当代文化学者福柯看来,19世纪的历史主义观念并没有指向更高级更美好的文明:
如我们所知,十九世纪最令人痴迷的是历史:发展,停滞,危机和循环的主题,永恒累积的过去造成无穷死者的压力以及世界冰川化威胁的主题。热力学第二原理成为19世纪的基本神话资源。(5)Foucault,Of Other Spaces(1967), Heterotopias,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
与进化论相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对历史发展前景的预示是悲观的:世界随着不可逆的熵增而走向无序化和毁灭是必然趋势。这是一种反进化论的悲观主义历史观:人类在活动发展中所创造的一切只会使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而不是越来越完美。然而无论进化论还是毁灭论,在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两极观念的深处,都预设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超越文化差异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也就是说都属于一元论历史观。福柯认为这正是19世纪与20世纪世界观的差异所在:
今天可能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于共时化的时代:我们处于并置的时代,远近、并排、分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正处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世界体验与其说是随时间推移的生命过程,不如说是由一个个点和线束交叉的网络。或许可以说当今某些意识形态冲突激发了虔诚的时间捍卫者和坚定的空间居民之间的冲突。(6)Foucault,Of Other Spaces(1967), Heterotopias,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
福柯认为20世纪是空间的时代,时间的单向性与空间的并置性共存,这意味着历史一元论的线性发展观受到多元化空间的挑战。进入21世纪后的非遗保护观念所依据的文化多元主义与一元论历史观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挑战在今天的延伸。
文化多元主义与一元论历史观的冲突在非遗保护实践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在保护目的方面的分歧——非遗保护的伦理正当性(应当)与历史的现实性(可能)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非遗保护“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的问题。
从一元论的历史观推论,过去的历史文化现象已经随历史发展而消失或融入新的文化形态中,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是脱离语境的物化遗迹或证据,即狭义的“遗产”。从这个观念推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质是对必然消逝之物的临终关怀仪式。
而文化多元主义所依据的历史观则是福柯所说的在空间并置共生的多元网络历史观。空间是使历史摆脱一元性时间序列的三元向量。地理空间的意义不仅仅是几何投影,更重要的是在并置的地理关系中生成和累积繁衍的多样性文化内涵,即由环境、种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自然与文化诸要素整合构成的多维文化生态系统。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着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性质。这种观念转变是现代历史观从进化论到生态主义的转变:进化论历史观的核心是优胜劣汰的线性发展逻辑,根据这种逻辑,一切过去产生的东西终将被新生的东西替代而消亡;生态主义则提出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并置共生相互依存演化的多样性多维度发展逻辑。
从时空关系来看非遗保护的学理根据,从历史主义到生态主义的历史观转换,简单地说就是让过去进入当下:传统文化是时间轴上的过去,然而在当代时空并置的文化生态中,“过去”作为与“当下”不同质的共存,使文化空间具有了复杂的异质化多样生态特征。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形成了异质空间——“异托邦”(Heterotopias):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荡荡的空间里,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物体,或许也充满了幻想的空间里……我将把它们称为异托邦……这些异托邦之间,可能有一种混杂、嵌合的经验……一种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神话与现实的并立与竞争。(7)Foucault.info,Of Other Spaces(1967), Heterotopias,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 heteroTopia.en/,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2日。
异质空间或“异托邦”之“异”就在于时间与空间、记忆与现实的不同质混杂嵌合,即“过去”与“当下”的并存。20世纪中期以后兴起的人文地理学和空间记忆等方面的研究关注到空间作为凝聚个人和集体文化记忆而生成的空间化情感“恋地情结”(Topophilia)(8)Yi-fu Tuan,Topophil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xii.,以及历史记忆的空间集聚“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emoire)(9)[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发掘着历史从时间逝去后留下的证据和记录中蕴涵的活的文化内容。传统文化从“过去”的物质形态进入“当下”社会后异化为“非物质”形态,本质上是特定群体的历史作为文化记忆在当下文化环境中的重构与再生,传统的本土文化通过心灵化的活态传承而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过去文明的再生曾经被许多人类学家认为是不可能的。然而人类学家萨林斯持不同看法。他在研究新几内亚高地恩加人(Enga)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存与发展形态时,指出恩加人接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同时把这种影响转化成促进地方性传统文化发展的力量:
印加人(恩加人?)将能够变西方人的好东西为他们自身生存发展的好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的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10)[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23-124页。
萨林斯所说的“现代性的本土化”意味着一种不同于全球同质化的多元化世界文化体系:源自过去的地方性生活方式进入了当下世界的“现代性”文化体系,而当下世界的“现代性”也在被各种地方性本土文化所改造和利用。这正是非遗保护的世界性和可持续性意义——使地方性文化记忆成为全球文化生态的一部分。这种全球文化生态观念应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学术视域。
二、多学科介入:各自为战的大拼盘
从定义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很宽泛的所指,涉及的保护或研究对象中包含了许多不同形态、不同性质而且差异很大的文化活动与事项,同时在非遗保护的进展中被纳入保护对象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非遗概念的宽泛和具体保护形态的复杂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建设中形成了多学科介入和不断扩展的特征。
非遗学研究的多学科性涉及非遗保护的当下性与传统文化的多方面关系,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从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与阐释。
与非遗保护的核心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当属民俗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文版文献中的“非物质”(intangible,“无形”)一词与日本民俗学界使用的“无形文化财”概念有关,而非遗概念正式确定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述中前置于非遗的“口头”一词则与民俗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口传文学相关。自19世纪赫尔德对地方、民族古老传统及其文化精神的研究和重新认识以来,在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德国民俗学不仅仅是一种面向特殊对象的狭义学术研究,而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及其意义的重估。民俗学研究通过精英/乡土、世界/地方、固化历史/集体记忆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批判视野突破了启蒙主义时代的线性文明史观,为非遗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思想启蒙的根据。
与非遗研究相关的另一学科是文化学研究。从19世纪阿诺德的现代社会文化批判开始,20世纪文化学研究中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兴起——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后现代文化批判等,重点对殖民化、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时代世界文化演变的主流趋势及其意义进行批判性研究。而非遗保护所关注的对象是在近现代被主流文化所遮蔽的地方、民族、社群传统文化,主要是从文化多元主义视域对非主流文化进行的文化形态及其价值研究。非遗研究对多元文化价值的探索深植于全球文化政治关系的语境中,推动着不同文化主体走向相互理解、承认和尊重。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项决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11)“Ethical Principles for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UNESCO Intagble Culrural Heritage,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decisions/10.COM/15.A,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2日。巴莫曲布嫫译,《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决议中提出的伦理原则,重点是强调非遗的传统价值以及相关文化群体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不同文化之间应当通过合作、对话、协商和咨询实现互动和相互尊重。作为非遗伦理原则“应当”享有的文化权利包括了文化传承主体的独享权利和作为合作互动的主体间性互享权利。这种合作互动的相互尊重与文化分享是应对当代全球冲突的文化策略,也是21世纪文化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对于非遗形态及其文化价值的研究中,艺术学也是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学科。非遗具体形态的 “非物质”性质主要指精神性形态特征,在当今进入文化保护视野的非遗代表作中,表现特定文化群体的集体记忆、情感交流、感知意象和形式趣味的传统文学艺术最为典型。这方面的研究包括艺术史、文艺美学和体现审美传统多样性的“小型社会中的艺术”的艺术人类学研究(12)[英]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李东晔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等方面。
非遗保护的目的并非对某种遗物的保存,而是特定文化传统形态及其内涵的存续和传承,由此涉及教育与传播机制研究。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自媒体平台、虚拟空间乃至“元宇宙”(Metaverse)等传播技术与社交形态的发展应用促进着非遗教育、传播研究视野的扩展和深化。
总起来看,非遗学研究涉及的多学科介入现象显现出作为学术研究活动的非遗学在很多学术领域有了重要的发展。然而这种体现于学科领域扩展的外延式发展和不同学科从不同领域进行的并行研究也存在着学科互动性或学术相关性方面的问题。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各学科研究视域之间往往缺少逻辑和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多学科研究形成了杂多研究领域并置的大拼盘。
比如在研究生论文写作中,由于学位论文规范性要求比较严格,在非遗研究中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特性与非遗学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复杂,因而更容易形成不同学科范式、思路并置拼合的多学科拼盘研究模式。例如做一个非遗项目保护问题的研究论文,常见的研究模式是首先做田野调研以了解民俗文化背景,再进行相关史料档案的扒梳整理以确定历史线索,然后针对项目本身的形式特征进行艺术学和美学的形式与风格研究,接下来是对相关社区和传承群体现状进行社会学调研以发现传承保护的现状与问题,然后从传播学角度研究传承路径及其效果,最后从文化产业管理学视角提出整体的管理与保护规划或建议……整个研究思路通常是“调研对象——描述状况——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样一个模式。具体的研究路径大体是以保护规划为模板提出问题一、二、三;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分别对应问题一、二、三;期待效果与相对评价一、二、三……
这样一个“描述状况—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模式具有典型的面向客观成果预期的实践工作特征:在研究动机中就预设了可实现、可计量的最终成果。这种研究模式的核心是具有普适和可判定性的“保护”这一工具性目的及其路径。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所有关于非遗的研究都以“保护”为可实现或应当实现的具体目的而模糊了不同学科的汇聚点——文化多样性研究及其在保护观念中的轴心地位,因而不同学科的研究在“保护”的工具性目的引导下都成为相似的问题和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拼盘。
拼盘式研究导致的学理悖论是不同学科作为理论根据的基础观念之间的悖离与分歧。
首先是作为保护对象的客体性观念,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与“假”的问题。民俗学中关于“伪民俗”或“民俗主义”的讨论与批判就是关于现代搜集、整理、研究和传播的传统民俗是否为“真”传统的问题。从民俗学角度判断真伪的根据是事实考证,然而从人类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的角度研究非遗的真实性,就不是事实考证能够充分说明的。比如萨林斯提到爱斯基摩人“利用工业技术来实现旧石器时代的目的”(13)[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第118页。也就是他所说的“现代性的本土化”涉及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延续生存及其文化的再生产,是超出客体性限制的文化传统内在生命力存续繁衍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归为伪民俗或民俗主义的“假”概念。
与民俗学观念的特殊性类似,从史学研究的视野研究非遗的历史性,会产生关于历史内涵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问题,即“死的”与“活的”:被史料和编年记录确证保存的历史具有固化的客观性,可以说是“死的”;而流传在民间口头和习俗中的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或者说是“活的”。传统史学相信“实录”,王国维的史学考古主张二重证据,都不承认历史可以离开证据成为“活的”。但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与传统史学家观点不同。他研究的历史不是史料证据和编年,而是通过各种叙述流传的“集体记忆”。他在谈到基督教历史时区分出两种历史记忆:神秘主义与教义主义,“我们可以把神秘主义和教义主义之间的关系比作鲜活的记忆和多少变为成规的传统之间的关系。”(1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变为成规的传统”就是通过证据和系统传授固化而确定的教义传播与发展史,由被认为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专职人员的记述阐释构成;而渗透在基督教文化传承过程深处同时又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联系着的个人心灵体验则是“鲜活的记忆”。后者是无法确认的活的记忆。非遗传承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地确定是死是活,而是在已经过去的(死的)历史中重新发现与后代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心灵需要相关的“鲜活的记忆”;因而超出了传统史学的确定性观念。
从文化学视野对非遗的研究涉及的一个中心观念是对文化主体的认知——“我们”与“他者”的区分。这种主体区分对于确认相关文化资源及其权益的归属非常重要。但非遗文化的主体性既有文化传承主体,也有在文化传承发展的当代环境中不同文化合作互享的主体间性关系。这种“我们”和“他们”的二重性表现为对非遗价值的判断、认同与互享等多重关系。社会学家芮德菲尔德曾谈到,在美洲一些种植玉米为生的印第安人部落中,玉米如同宗教活动一样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也在市场上出售玉米:“种植玉米用来祭神时,玉米是传统的,神圣的,道德的。但要用来出售时,人们给它起个不同的名字。作为商品的处理方式和本土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15)Redfield Robert,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47-48.玉米种植文化因此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具有了本土和互享的二重文化内涵及其价值,也因此形成了多重主体间性关系。
上述种种传统学科观念在非遗研究中产生的矛盾或复杂性意味着非遗学研究不能仅仅靠各学科拼盘,更需要新的多学科关系,需要探讨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具体个案、特定问题与当代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总体观念之间的关系和学术逻辑。
三、走向“新文科”:从大拼盘到新的知识生态整合思维
近年来教育部在推进我国文科研究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设想中提出“新文科”建设的思路。这是个新的概念,其中包含的多重涵义有待在学科建设进程中思考、实践和拓展深化。对于非遗研究这种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创新性特征的学术研究来说,“新文科”概念尤其具有引导意义。但要真正实现这种学术创新需要首先理清楚:“新文科”所要建设的“新”意究竟在哪里?就非遗学研究而言,多学科关系如何从拼盘式多样化转向有机联系着的多元化研究领域?
从非遗学涉及多学科领域的学术特色角度上说,作为“新文科”创新探索的非遗学应当超越传统文科知识范畴而具有学术发展转型的性质。现代学术知识体系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范畴分类,即从不同角度区分研究对象的各种特质,由此构建起了传统知识的性质分类及其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体系。然而非遗研究的指向不是区分性质范畴而是整合关系,即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影响与互动。这是建构知识生态系统的创新工作。可以说“新文科”研究的方向之一就是建构文科知识系统新生态。
非遗学作为文科知识系统新生态的建构,意味着从不同知识范畴的差异性研究转向互动互补的生态关系,首先是非遗保护的实践操作与理论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
非遗保护的实践性集中体现于“保护”概念。字义上的保护(safeguarding)是个日常用语中的经验概念,主要含义可以表达为“防范危害”(protects, something that offers security from danger)也就是对被保护对象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全。然而在关于非遗保护的国际公约和各国政府文件、文化工作者的实践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对被保护对象“非物质”属性的理解和实践运用却是个不断发展演化中的概念。
基于“非物质”这一特定文化性质而形成的保护观念,从消极意义上的防范危害转向了积极意义的保护——即从保存到“活化”(或“活态传承”)观念的发生及其实践。然而怎样才算是活态传承却是有争议的。非遗的“非物质”性涉及言语、音乐、技艺、动作、仪式等多种活动形态,保证这些活动形态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活化?这是在非遗保护一开始就发生的实践问题。比如一种古老的地方性活动因社群萎缩和生活方式变迁,参与者越来越少近乎消亡了。如果靠政府投资、社会扶持来勉力维持传承活动或者干脆通过数字化技术保存三维活动档案,这算活化吗?不可否认,有些濒危项目出于特别需要不得不以生态博物馆乃至数字化档案的方式保存,但这种类似输氧甚或防腐式的保护方式显然既不可普遍应用,也不具有使遗产真正活化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算是“苟活”甚或生祭。真正的活化不是苟活,而是使文化的内在生命活力在当代世界的文化生态中获得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与可能性。
在活化保护观念形成的初期,有人提出“生产性保护”的概念。所谓“生产性”实际上是市场化的一种委婉说法,目的是将传统文化的存在发展纳入当代社会再生产机制以获得持续的生命力。之所以用“生产性”而不是市场化的说法是为了避免产生商业利益侵蚀文化内涵,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误解。然而尽管概念换了,问题其实仍然存在:一方面,“生产性保护”在实际操作中很难避免市场需求造成对保护内容的扭曲和变质;另一方面,完全保持古老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即所谓“原生态”,不仅难以进入文化消费市场,也与非遗活化进入当代文化生态的意图有悖。
面对非遗活化中变与不变的二难困境,有研究者提出“文化基因”保护的观念——认为非遗保护不是原封不动“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维持,而是从遗产中提取携带相关文化实体核心信息的特征要素,如列维-斯特劳斯在研究神话时提出的文化深层组织“板岩”结构(16)[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68页。。这种从深层结构层面的文化保护是一种涉及学术探索的深度和争议性的难题。
另外一个探索的向度是从文化生态系统的维度探索认识非遗活化的现实根据,这就是文化生态保护观念的提出——从早期封闭隔离性的“生态博物馆”,到我国自2007年开始试点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再到后来相关行政官员对文化生态保护的进一步具体描述——“见物见人见生活”(17)“项兆伦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1809/t20180911_834728.htm,访问日期:2022年6月6日。,这个文化生态保护意识的演进显示出非遗保护理念在学术层面的探索对保护实践的影响:探索传统文化进入当代文化生态环境的可能性与路径。
总之从世界非遗保护经验来看,真正的活化或活态传承不是单纯的实践问题,必须基于深度文化分析形成的认识。在实践与研究的互动过程中对“保护”观念和实践进行修正、拓展与转换生成,不断探索非遗保护的文化意义及其深层学理根据。
作为文科知识系统新生态的建构,非遗学创新意味着从不同知识范畴研究转向互动互补的生态关系,这种转向不仅是知识体系的演进,而且涉及传统学术研究的逻辑体系如何开放与创新的问题。传统学术研究的最底层逻辑在于自洽性——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及其基本逻辑关系应当具有自证和不矛盾的闭环关系。然而当各学科研究进入到相互关联乃至相互冲突的学科间性关系时,这种学科互动的特殊学术生态需要建构不同于自洽性闭环逻辑的开放性逻辑——一种类似“莫比乌斯环”那样可翻转衔接的传统学理逻辑与非遗学学理的开环互补逻辑。
这种开环互补逻辑涉及各学科基础概念从矛盾到互动的生态建构。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在谈到21世纪新都市社会学时就指出,当代都市研究的对象已形成多重对立关系的交互影响及其张力,如“个体化与社区共同化”“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以及“流动空间的草根化”(18)[西]曼纽尔·卡斯特:《21世纪的都市社会学》,刘益诚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年第5期。,就是超越了20世纪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关于社区生态学的“区位”(Position)(19)[美]罗伯特·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3页。概念的地理空间闭环,从当代多重空间结构的关系交互性及其张力视角进行的开放性生态研究。
一般来说,非遗学涉及的多学科之间的观念及其逻辑矛盾,实质上都是从传统学科的闭环自洽状态向开环互动生态拓展的契机。如从社会学和史学对传统的不同研究立场转向相互沟通,通过学术视域的开放重构集体记忆的“小传统”与历史中心的“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跨越口传历史“浮动的缺口”实现社会记忆中多种传统的整合和传承。在文化研究中关于文化主体 “我们”的独特性与人类学意义上“他者”的可比较性形成主体间性的沟通关系;从跨文化视角来看是在民族想象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层次认同的重构。从艺术学与美学学科的研究来认识小型社会“各美其美”的传统特征与当代社会“美美与共”的艺术美学互动互享生态关系,有助于使“原生态”艺术与美学的人类学研究拓展进入到当代艺术生态研究视野中,可以使“原生态”艺术的传统封闭性通过自组织而又相互联系的生态壁龛建设融入当代文化生态多样性和互生共享性环境。总之,作为新文科知识生态这种开放性、互动性的研究逻辑对于非遗学建设和新文科生态建设应当说是一种积极的创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