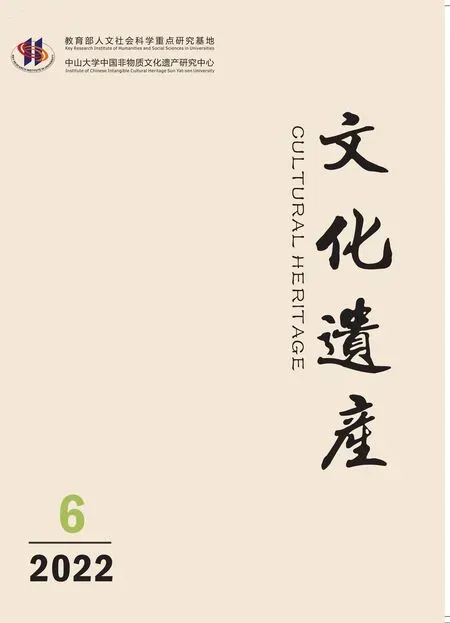困中前行:顾颉刚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汤 莹
如所周知,顾颉刚是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过往学界对此予以充分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1)较为系统的论述有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及贡献》,《文史哲》1993年第2期;吕静:《“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顾颉刚先生与中国民俗学》,《史林》1993年第3期;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06-121页;王文宝:《一代民俗学巨擘顾颉刚》,《文化学刊》2006年第2期;施爱东:《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4-202页。。不过,对于全面抗战时期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活动,现有研究成果则基本语焉不详,往往一笔带过,或提及顾颉刚在抗战时期成立过中国民俗学会,主编过《风物志集刊》与《文史杂志》的“民俗学专号”(2)参见吕静《“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顾颉刚先生与中国民俗学》;王丹、张瑜:《抗日战争时期“自觉图存”的民俗学术实践》,《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或关注到《浪口村随笔》以及该书修订本《史林杂识》中有一些与民俗学相关的文章(3)参见周励恒《西北民族考察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因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课题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考察,以期彰显顾颉刚在全面抗战时期取得的民俗学成绩,进而揭示其忧心民族前途的家国情怀。
一、以民俗学的方法重建 神话与传说中的上古史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以古史研究闻名于世。打破伪古史则是其古史研究的真正起点。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4)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1页。。此文发表之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学界基本认定,“层累说”的提出,初步推翻了三皇五帝的传统上古史系统。而民俗学的眼光则是顾颉刚建立“层累说”的主要学术思想资源之一(5)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32-36页;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94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逐渐由推翻伪古史转向重建古史(6)参见刘俐娜《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事变爆发之后,顾颉刚因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大量播传抗日思想”(7)顾颉刚:《皋兰读书记》,《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而被日人列入“欲捕者之名单”(8)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67页。,遂不得不被迫离开北平。此后不久,受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邀请,前往西北进行教育考察。直到1938年10月,顾颉刚由兰州抵达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开设了一门“中国古代史”,最后编成一部约九万言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讲义的编纂,标志着顾颉刚初步完成了中国上古史的重建。
而民俗学的方法正是顾颉刚重建上古史的一件利器。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该讲义第一章《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之中。顾颉刚在该章中讲述,在古人的想像中,天上的神过的就是人间的生活,天上的神和地下的人彼此都有交通的办法。地下的人是从地面上最高的地方——昆仑山一直往上走去。当初,人和神本都是互相往来而且是杂乱不分的,只为蚩尤造反才把这条道路截断了。但是,地面上还有很多杂居的神。上帝和鬼神的生活同凡人一样,喜欢吃东西,谈恋爱。比如,上帝丹朱与周昭王的房后生了穆王,楚怀王梦见巫山之神的女儿向他荐枕席。于是,这些神们还有了家属。比如,帝俊的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太阳,另一个妻子常羲生了十二个月亮(9)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第445-449页。。当然,这些“天”和“神”在事实上是不确的,但在“一般古人的想像中”是有这回事的。
根据该章的注释,正文内容主要依据的是《山海经》与《楚辞》。顾颉刚指出,前人都是以史实的眼光来看《山海经》,认为记载的都是“荒唐之言”,但如果改用民俗学的眼光,则可知该书中记载的奇怪故事非常接近民众的想像。与此相近,《天问》一篇就像民间的“对山歌”,其中“所举古事,为神话与传说之总汇”(10)参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山大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第27-28页。。要而言之,以民俗学的眼光来看,《山海经》与《天问》保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而这些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即是“社会情状的反映”(11)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一》,《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七),第60页。。因此,顾颉刚即主要根据《山海经》和《楚辞》的记载,讨论了“中国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重建了商周以前神话与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史。
此外,能够体现这一民俗学方法的,还有该讲义中关于商、周两个种族起源的认识。顾颉刚首先在该讲义第四章《商王国的始末》中说,商朝是有史时代的开头。据商人自己说,他们这个种族是上帝降下来的。有娀氏的国君生了两位美丽的姑娘,大的叫简狄,小的叫建疵。有一天,她们到河里洗澡,然后简狄吞了燕子下的一个五彩的卵,就怀了孕。后来,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契,就是商人的始祖(12)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第468页。。此后,顾颉刚在该讲义第五章《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中则说,据周人说:“古时有一个女子名唤姜嫄,她的德行为上帝所赏识。她诚心祭祀,祈求上帝赐给她一个儿子。有一天,她在野里走路,瞥见路上留着很大的脚印,一时高兴,踏在上面走过去,就觉得肚子里怀了孕。足月之后,很顺利地产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稷,是周人的始祖(13)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三),第477-478页。。
其实,早在1924年,顾颉刚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中就以周人的起源来谈过应用民俗学来解释古代史话的意义。比如,“《大雅·生民篇》中说姜嫄生后稷由于‘履帝武’,这原是一段神话,很可能且极平常,但自古至今终不曾给他一个适当的地位。”如果用了民俗学的眼光,“这种故事,在事实上是必不确的,但在民众的想像里是确有这回事的”。最后,顾颉刚表示,自己打算在1938年到1940年做这项工作时,“能处处顺了故事的本有的性质去研究,发见他们在当时传说中的真相”(14)顾颉刚:《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第294-295页。。由此而言,顾颉刚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对商、周两个种族起源的阐述,正是将十多年前的民俗学认识付诸到了学术实践之中。
由上所述,民俗学的方法是顾颉刚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顾颉刚编纂了旨在古史重建的《中国上古史讲义》。在该讲义中,顾颉刚不仅在开篇以民俗学的方法讨论了“一般古人想像中的天和神”,还以民俗学的方法审视了商、周两个种族的起源。于今来讲,这一民俗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还开辟了重建中国上古史的一个新方向。
二、依据民俗资料考察古书记载与西部风俗
除古史研究之外,顾颉刚的学术成就还在于古书考辨。“活”的民俗资料无疑是弄明白古书本身问题的重要参考。而要想获得“活”的民俗资料,则需要实地调查。1924年,顾颉刚发表《东岳庙的七十二司》,即是根据自己前往苏州、北京东岳庙的调查,并征引了《汉书》《日知录》的相关记载(15)顾颉刚:《东岳庙的七十二司》,《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6-480页。。1927年,顾颉刚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发表《泉州的土地神》,则是根据自己前往泉州的调查,又征引了《庄子》《后汉书》的相关记载(16)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500-508页。。要而言之,顾颉刚正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活”的民俗资料,进而弄明白了古书本身问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顾颉刚前往西北进行教育考察。此后,顾颉刚“跋涉于河、湟、洮、渭之间”(17)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8页。;直到1938年9月,离开西北。1944年,顾颉刚出版《西北考察日记》,记录了这长达一年之久的西北之行。根据此书记载,顾颉刚非常注意西北民俗的调查。1937年10月8日,在临洮观剧,“觉甘肃腔与陕西腔有异”。1938年1月30至31日,在临洮上街观新年风俗。2月7日,在当地看社火。5月14日,在临潭新城的阎家寺,“观跳神礼”,发现“仪式较北平雍和宫、黄寺等处所见者为繁重”。7月11日,在夏河观看藏女在新年中歌舞的风俗(18)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425、437-438、438、461、493页。。总之,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期间搜集了一些较为珍贵的民俗文化资料。
除了上述实地调查之外,顾颉刚还进一步考究典籍与西部当地风俗。这一作法在《浪口村随笔》中有着集中的呈现。该书虽然发行于1949年,但主体内容基本完成于全面抗战时期,并曾发表于《责善半月刊》等期刊。因此,顾颉刚本人将该书视为自己“八年乱离之纪念”(19)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263页。。而民俗学的参与是《浪口村随笔》的特色之一。
首先,卷二论制度,共计二十二则,其中与民俗学直接相关者有五则。《歌诵谱牒》以爨人的家谱风俗证《国语》《周礼》等古书记载的汉族古代笃重谱牒;《夫妇避嫌》以蒙、番之俗证《国语》《淮南子》等古书记载的“夫妇避嫌”或并不“虚诞”;《赘婿》以视赘婿为奴的“藏民风俗”证《史记》《汉书》等古书记载的“赘婿”苛待;《蒸报》以川北的“大转房”之俗证《左传》《汉书》等古书记载的“蒸报”;《一妻多夫》以“一妻畜夫四五”的西藏之俗证《后汉书》记载的西汉燕赵间尚行的“一妻多夫”现象(20)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80、86、86-89、89-91、91页。。总而言之,上述学术小品文都以西部风俗钩沉了若干“周秦之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21)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11页。。
其次,卷三考名物,共计二十二则,其中与民俗学直接相关者有五则。《中霤》以四川人家在几下左端别供“中霤之神”的风俗证《礼记》中记载的供“中霤”为家之土神的古风;《“造舟为梁”》根据西北当地的“造舟为梁”指出,《诗经》中的“造舟为梁”仅为“渡水”;《“被发左衽”》指出,蒙、番诸地的人因工作的便利,仅穿左臂,由此可知《论语》中的“被发左衽”只是“左臂穿入袖中”,“其襟固仍在右”;《饮器》以喇嘛寺中以人头盖骨作鼓的风俗证《史记》中记载的“饮器”是酒器,而非溺器;《氐羌火葬》以拉卜楞火葬的风俗证《墨子》《庄子》等古书记载的“氐羌火葬”(22)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102-104、107-108、128-129、129-130、133-134页。。要而言之,上述小品文都以当时的西部风俗证实或解释了古代的一些名物,其中不乏“创为新解者”(23)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11页。。
再次,卷四评史事,共计二十一则,其中与民俗学直接相关者有四则。《二女在台》以民俗学的眼光解释了商人的祖先传说;《徐偃王卵生》以图腾说解释了徐君卵生的传说;《〈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指出,扬雄的《华阳国志》“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尾生故事》则对绵延二千余年的尾生故事的始末进行了叙次(24)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139-141、159-160、165-166、167-172页。。总而言之,这些小品文“衍《古史辨》之绪”,对若干史事进行了洗刷工夫(25)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11页。。
最后,卷六记边疆,共计二十则,其中与民俗学直接相关者有二则。《“吹牛、拍马”》指出,“吹牛”与“拍马”,来源于西北方言,“吹牛”的本义是吹一种用牛羊皮做成的筏子,西北地区黄河两岸经营此种生计,故以此来讽刺夸口者;“拍马”的本义则是西北地区“平常牵马与人相遇,恒互拍其马股”,“表其欣赏赞叹之意”,后“流于奉承趋附之途”。《抛彩球》则指出弹词、平剧中的“抛彩球”虽然在史书中“未绝一见”,但并非“纯出想像”,而是源自西南边裔的一种风尚(26)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251-253、254-258页。。要而言之,这些学术小品文“活泼泼地叙述民风”,稽考了社会生活(27)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256页。。
由上可知,顾颉刚在全面抗战期间一方面通过实地调查搜集了一批珍贵的民俗资料,另一方面则在自己的代表作《浪口村随笔》中考究典籍与西部风俗,提出了诸多“新解”。因此,有学者强调说,顾颉刚在抗战期间写出《浪口村随笔》,“使许多本来僵死的古代记载都获得了新的生命”(28)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12页。。而这一研究路径与方法,还开创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新领域(29)参见汪宁生《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记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启迪和帮助》,《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汪宁生《论民族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三、打造大后方的民俗学园地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不仅以精深的学术研究名世,还以擅长办学术刊物、组织学术机构蜚声学界(30)王学典主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6页。。仅就与民俗学相关者而言,1920年代初,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积极参与歌谣研究会,主持编辑《歌谣周刊》;1926年,到厦门大学,发起成立风俗调查会;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之后,发起组织民俗学会,主编《民间文艺》;1929年,回北平执教于燕京大学,至1935年,发起组织风谣学会,次年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创办《民众周刊》。可以说,这些民俗学机构与民俗学刊物的有效经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与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顾颉刚并没有因学术生态的恶化而打消组织学术机构、创办学术期刊的热情。1939年9月,顾颉刚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随后,即与上海开明书店进行出版洽谈(31)张廷银、刘应梅整理:《王伯祥日记》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796、2826页。。截止到1941年1月,研究所拟出版专著汇编十种;至7月,又增加至十二种。其中,与民俗学相关的有两种,一是王兴瑞著、刘咸校的《海南岛黎人调查》,一是刘历莹的《西康旧宁属概况》(32)参见钱穆主编《齐鲁学报》1941年第1期、第2期。。不过,稍嫌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虽都已在印刷中,但因“日寇侵入上海租界,形势恶劣,书局改变出版计划”(33)王兴瑞:《海南岛黎族研究叙说》,《南方杂志(广州)》1946年第1卷第3、4期合刊。,以致当时未能出版。
除支持著作出版之外,顾颉刚还为研究所办了《责善半月刊》等学术刊物。该刊虽然不是民俗学专业期刊,但却刊发了许多与民俗学相关的文字。除了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之外,还有张政烺的《玉皇姓张考》、王树民的《陇岷日记》与《洮州日记》、杨向奎的《〈李冰与二郎神〉自序》与《杜宇开明的故事》、廖友陶的《倮苏族的火把节》、李安宅的《拉卜楞藏民年节》与《拉卜楞寺公开大会》、李鉴铭的《康俗杂记》与《康游杂记》、冯沅君的《南戏拾遗补》、岑家梧的《槃瓠传说与傜畬的图腾崇拜》与《灯影戏杂记》等。这些文字的刊发,无疑缘于主编顾颉刚对民俗学的密切关注。
1942年11月,《责善半月刊》停刊,但顾颉刚打造民俗学园地的热情没有消退。1943年12月29日,顾颉刚、娄子匡、黄芝冈、罗香林、于飞、樊縯等“同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一致认为应该筹立中国民俗学会(34)《纪在渝同仁两次的座谭》,《风物志集刊》1944年第1期。。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离不开顾颉刚与娄子匡的倡议与领导(35)王丹、张瑜:《抗日战争时期“自觉图存”的民俗学术实践》。。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座谈会受到了即时关注,《益世报》于两天后就刊出了顾颉刚等筹组民俗学会的“中央社讯”(36)《民俗学会》,《益世报(重庆版)》1943年12月31日第3版。。
1944年1月31日,由顾颉刚、娄子匡主编的《风物志集刊》正式出版。该刊共计刊发十八篇文字。顾颉刚在开篇的《序辞》中简要地回答了《风物志集刊》刊出的理由,呼吁“我们一面要欢迎全国道一风同的新风俗的实施,一面要赶紧搜罗那已经实施了千百年而现在奄奄欲绝的旧风俗而加以整理和研究”(37)顾颉刚:《〈风物志集刊〉序辞》,《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587页。。后面的文字则依次是罗香林的《制礼与作乐》、娄子匡的《岁时序的移易》、王兴瑞的《黎人的文身·结婚·丧葬》、郑师许的《中国古史上神话与传说的发展》、于飞的《重庆歌谣的研究》、李友邦的《台湾风物志》、黄灼耀与褟毓枢的《傜人的要歌堂节》、屈万里的《五月子》、樊縯的《凤皇来仪》、黄芝冈的《谭蛊》、汪祖华的《陇西南藏民风物》、孙福熙的《修编县志》、岑家梧的《黔南仲家的祭礼》、胡耐安的《谈八棑傜的“死”仪》、李禺的《伊索寓言与百喻经》以及《纪在渝同仁两次的座谭》《学林动态》(38)参见顾颉刚、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1944年第1期。。由此可知,这些学者并未因抗战而中缀“风物”的整理与研究,而是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收获。而顾颉刚、娄子匡主编的《风物志集刊》,无疑给这些学者提供了公开发表自己成果的平台。
《风物志集刊》创刊之后,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1944年3月11日,有学者发表评介文章,认为其中的文章是在“建国建礼的任务里,研究风物,创化现代的中国的新风物”(39)《读〈风物志〉评介》,《中央日报(重庆)》1944年3月11日第4版。。同年3月,还有学者发表评论,认为《风物志集刊》创刊号以王兴瑞的《黎人的文身·结婚·丧葬》与屈万里的《五月子》最为“可观”(40)《风物志(创刊号)》,《图书季刊》1944年新第5卷第1期。。同年3月25日,《联合周报》刊载《风物志集刊》出版的消息(41)《风物志》,《联合周报》1944年3月25日第4版。。直到1947年3月,还有学者对1946年再版的《风物志集刊》进行评论(42)《风物志再版》,《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1947年复刊第1号。。由此而言,由顾颉刚、娄子匡主编的《风物志集刊》可以说带动了抗战时期民俗学的风气。
除了主编《风物志集刊》之外,顾颉刚还主持了《文史杂志》。1941年6月,顾颉刚由成都飞抵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接管《文史杂志》的编辑工作。此后,顾颉刚虽然遭遇了经费、印刷、人手等诸多困难,但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学术声望与锲而不舍的工作态度,为文史杂志社赢得了较高声誉,各方来稿遂不断增多。最后,顾颉刚在史念海的建议下,“多出专号”(43)史念海:《回忆文史杂志社在北碚的旧事》,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2-276页。。其中,该刊第五卷第九、十合刊即是“民俗学专号”(44)该期出版于1945年10月,但按照期刊的运行来讲,可以视为考察顾颉刚抗战时期主编《文史杂志》的资料。。
除了“社论”“学术消息”“通讯”“编后记”之外,这期的“民俗学专号”文章共计有十三篇文字,与民俗学相关的有朱锦江的《中国古史中羽翼图腾之探究》、岑家梧的《中国民俗艺术概说》、马长寿的《中国四裔的幼子承继权》、梁钊韬的《古代的馈牲祭器及祖先崇拜》、郑德坤的《古玉通论》、任乃强的《喇嘛教民之转经生活》、于式玉的《“浪帐房”》、李承祥的《缅铃》、宋蜀青译的《龙舟节龙舟与龙》、李鉴铭的《康属见闻》等十篇文章(45)参见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1945年第5卷第9、10期合刊。。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些文章主要是由华西大学博物馆民族学研究室梁钊韬代为征集(46)王丹、张瑜:《抗日战争时期“自觉图存”的民俗学术实践》,《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但绝不能忽视的是,梁钊韬的征集与这些文章的发表主要缘于顾颉刚对民俗学的热爱。而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不仅为当时学术界所关注,还对后来的民族民间物质文化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47)徐艺乙:《中国民俗文物概论:民间物质文化的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由上可知,组织学术机构与办刊物是顾颉刚学术人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仅就全面抗战时期而言,顾颉刚先是任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责善半月刊》,刊发一系列与民俗学相关的文字;此后,又与娄子匡等人组建中国民俗学会,主编《风物志集刊》;与此同时,顾颉刚还接手文史杂志社,主编《文史杂志》,推出“民俗学专号”。这些学术机构或刊物无疑为当时的民俗学者提供了平台,进而推动着抗战时期民俗学的发展。
四、鼓励青年才俊进行民俗资料整理与研究
除了“为他人作衣裳”的办刊物、组织学术机构之外,顾颉刚的学术贡献还在于培养出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仅就全面抗战之前的民俗学而言,钟敬文、钱南扬等青年学人就在顾颉刚的支持和鼓励下,走上了民俗学的道路,并迅速成长为学有成就的民俗学家(48)参见施爱东《钟敬文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钱南扬:《我的书是颉刚老友鼓励下写出来的》,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31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顾颉刚不忘初心,不仅自己继续民俗学相关研究,还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励青年学人从事民俗学工作。兹举几例,以证其实。
最先能够证实这一判断的例子是王树民。王树民,直隶武清县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38年1月至7月,跟随顾颉刚前往西北各地进行考察。王树民晚年深情地回忆说,顾颉刚“虽为考察地方教育”,但“其目光所及与精神所注远出其外”,民间文艺即是其所重视事情之一。期间,自己“搜集了许多有关地方史的资料,和儿歌、山歌以及一种俗称倒浆水者”。后来,“写成为《洮州土司僧纲之源流与世系》《临洮的儿歌》《蓬花山的山歌》和《乾隆年间撤拉回民起义》等文,分别发表于《大学》月刊、《新西北》月刊、《风土》杂志和《西北通讯》等刊物上”。而这些“都是和(顾颉刚)先生分不开的”(49)王树民:《顾颉刚先生甘青之行的轶事》,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214页。。
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例证还有杨向奎。杨向奎,河北丰润人,是顾颉刚的知名弟子之一。1940年2月,杨向奎辞去甘肃学院的教职,前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向顾颉刚问学。就在此之前,顾颉刚正在搜集李冰治水与二郎神故事的材料,并拟专门写一本《二郎考》(50)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第339页。。但是,因自己工作繁忙,身体又不健康,遂将这份工作委托给了杨向奎(51)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第339页;杨向奎:《〈李冰与二郎神〉自序》,《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19期。。此后,杨向奎集中精力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期间,其时常与顾颉刚讨论(52)杨向奎:《〈李冰与二郎神〉自序》。。最后,杨向奎不负重托,用了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便写出了二十万字的《李冰与二郎神》。顾颉刚看到这部书稿后,非常高兴(53)杨向奎:《杨向奎自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页。;此后,还称赞该书是可以“纪念的作品”(54)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五),第291页。。而诚如杨向奎在《〈李冰与二郎神〉自序》中坦言的,“假如不是顾颉刚先生的督促和指导”,该书是难以成功的(55)杨向奎:《〈李冰与二郎神〉自序》。。时人甚至表示,“这个研究课题的完成,不但是出于颉刚先生的鼓励,而且是他们共同讨论的结果”(56)方诗铭:《记顾颉刚先生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259页。。
受顾颉刚鼓励进行民俗整理与研究的还有李文实。李文实,青海化隆人。1935年,被保送至南京蒙藏学校读高中。1937年2月1日,李文实在该校开学式上结识了顾颉刚。顾颉刚得知其是西北青年,“热情给予鼓励”,并嘱其“为民俗学会搜集有关民俗资料”(57)李得贤:《顾颉刚先生与西北》,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第228页。。是年7月,李文实毕业后回西宁从教。1941年,李文实考入齐鲁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受业于顾颉刚门下,颇得其赏识,被认为是“边疆工作可用人才”(58)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第466页。。值得关注的是,受顾颉刚的鼓励和启发,李文实撰写了《释“白教”与“吹牛拍马”》《补释“吹牛”及“嘉麻若”》《青海杂话》《青海风俗杂记》等文字。顾颉刚颇为欣赏这些文字,将其刊发在自己主编的《责善半月刊》或《文史杂志》之中。
值得一提的还有李鉴铭。李鉴铭,山东寿光人。193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1937年,参加张怡荪在成都主持的西陲文化院,从事藏事的研究。1940年,游历西康,作更进一步的研究(59)吴乃越:《“甲喇嘛”李鉴铭》,《中央日报》1947年11月21日第7版。。此后,与顾颉刚有书信来往。至西康后,李鉴铭撰写了《西康牧区之游》《康游杂记》《康俗杂记》《康属见闻》等十余篇涉及西康风俗的文字。顾颉刚收到这些文字后,亲自进行修改(60)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第404、427页。,然后将之刊发于自己主编的《责善半月刊》或《文史杂志》。而且,顾颉刚还在《浪口村随笔》中直接引用李鉴铭关于西康“赘婿”风俗的两封来信对“赘婿”进行了考察(61)顾颉刚:《浪口村随笔》,《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第88页。。要而言之,在顾颉刚的引导与支持下,李鉴铭逐渐成为了一名“边疆可用人才”(62)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第466页。。
由上所述,顾颉刚在全面抗战期间还不忘支持与培养青年俊才从事民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可以说,正是在顾颉刚的直接支持与鼓励下,王树民、杨向奎、李文实、李鉴铭等这些并不是完全以民俗学为专业的青年才俊,都撰写出了较高学术价值的民俗学文字,从而推动着全面抗战时期民俗学的发展。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民俗学在全面抗战时期的艰难发展,与顾颉刚的努力与引导紧密相关。顾颉刚不仅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以民俗学的方法重建了神话与传说中的上古史,还在《浪口村随笔》中依据民俗资料对古书记载与西部当地风俗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顾颉刚还主持或组织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中国民俗学会,主编《责善半月刊》《风物志集刊》《文史杂志》,为大后方的民俗学者提供了公开出版或发表的园地。此外,顾颉刚还鼓励与支持王树民、杨向奎、李文实、李鉴铭等青年才俊从事民俗研究工作。总之,正是在顾颉刚的示范与带领下,中国民俗学在全面抗战时期的艰难环境中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而顾颉刚在这一特殊时期对民俗学的学术热爱,还充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忧心民族前途的家国情怀。1939年,顾颉刚在《责善半月刊》发刊词中即说:“方今敌寇凶残,中原荼毒,我辈所居,离战场千里而遥,犹得度正常之生活,作文物之探讨,苟不晨昏督责,共赴至善之标,俾在将来建国之中得自献其几微之力,不独无以对我将士,亦复何颜以向先人!”(63)顾颉刚:《责善半月刊发刊词》,《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一),第9页。1944年,顾颉刚在《〈风物志集刊〉序辞》 中强调说,“风物志”是“想从搜集风俗资料,探究她(民俗)的成长、展布和存在价值,因势利导的来移风易俗,创化出现时代适应于中国的新风气”(64)顾颉刚:《〈风物志集刊〉序辞》,《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民俗论文集》(卷二),第587页。。而如上所述,顾颉刚可以说相当出色地实践了这些学术宣言。这无疑是更值得我们当下“鉴观”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