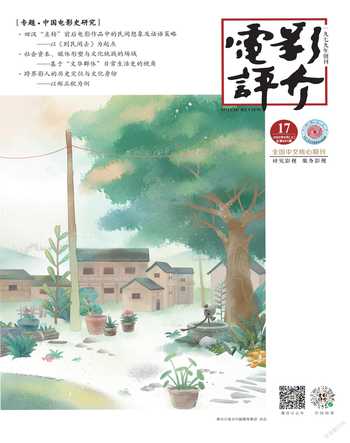曲意回环、记忆营构与地缘视域
邓静 漆尉琦
作为中国香港影坛进军内地的代表导演之一,关锦鹏先生的作品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佳作代表。从1985年的《女人心》算起,关锦鹏踏足导演领域已有近40年的时间,共执导了电影及电视剧20余部,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一般来讲,任何一位在电影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导演,往往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关锦鹏也不例外。综合分析关锦鹏导演的众多影片,可以将他的艺术风格或艺术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曲意回环、记忆营构与地缘视域。本文将结合关锦鹏执导的具体影片,详细地分析这三种艺术风格在其影片中的使用与呈现方式。
一、曲意回环:增强艺术观感
所谓曲意回环,指的是在影片的情节设计方面,能够做到曲折照应,给观众一种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的艺术观感。[1]关锦鹏的电影作品在情节设计方面特具匠心,往往能设计出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1985年上映的《女人心》是关锦鹏的导演处女作,这部影片已经展现了关锦鹏擅长制造曲意回环的故事情节的特点。影片讲述了孙子威与梁宝儿的爱情故事,两人育有一子,但孙子威婚内出轨,梁宝儿决意与之离婚,并加入其他单身女性的交际圈中,在她们看似热烈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空虚的人生;而孙子威与第三者同居后,发现前任妻子才是自己的最爱,于是在签署离婚协议书时反悔,与梁宝儿重归于好。影片情节设计较为简单,但在呈现孙子威和梁宝儿感情破裂后各自精神空虚的面貌时,已取得了明显的曲意回环的艺术效果,仿佛空中的回音,彼此照應又彼此复制。
1989年上映的《人在纽约》(又名《三个女人的故事》),在情节设计方面仍延续了曲意回环的艺术风格。影片讲述了三位分别从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三地赴美生活的女性,她们有各自的人生追求与生存状态,却在美国不期而遇。这种情节设计本身就有一种奇趣,但关锦鹏并不满足于这种回环照应的叙述方式,他为三位女主人公设定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例如从大陆移居美国的赵红深受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一直想让母亲搬到美国,与他们夫妻一起生活,这当然不是美国社会所能理解的行为,因此她的生活也充满障碍;而从中国台湾地区赴美的黄雄屏则醉心于舞台表演,一心想要在美国出人头地,可惜当时的美国对华人存在偏见,整个体制都不利于华人发展自己的事业,黄雄屏的艺术生涯遭遇了难于突破的瓶颈;与赵红和黄雄屏相比,从中国香港到美国的李凤娇虽然没有赵红、黄雄屏的苦闷,却也有另一个难以冲决的网络,虽然她在美国生活质量很好,但毕竟身处异国他乡,内心的孤寂与苦闷难以排遣。从这三位女主人公的命运轨迹来看,《人在纽约》显然体现了一种精心安排的曲意之美。而随着三位女主人公在一场婚礼中的偶然邂逅,并迅速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之后,她们互诉衷肠,利用自己的能力互相帮助对方解决各自的难题,为美国的华人生活与相处模式树立了榜样。在不断解决各自难题的过程中,影片又存在明显的回环往复之美。两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人在纽约》曲意回环的艺术风格。更为可贵的是,这种艺术风格的呈现源于精心的安排设计,但观众在观影之时却没有见到牵强凑泊的痕迹,足见关锦鹏在导演方面的匠心所在。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注重曲意回环的艺术风格,似乎是关锦鹏早期影片所着重追求的品质。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锦鹏在电影制作中的追求实现了转向,即更加追求电影内部美感的实现。换句话说,转型以后的关锦鹏更加侧重借助电影内部要素的自足来呈现美感,而不再特别追求在情节表现上出彩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关锦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拍摄的影片多数存在文学作品作为底本,另一方面也与关锦鹏对导演艺术的不断反思与总结有关。通过对关锦鹏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影片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在导演电影时出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开始更加重视向文艺电影转向,如《阮玲玉》就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转变;第二,开始对当代文学的部分代表作进行改编,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长恨歌》(具体分析详见下文)都属于文学改编的典型。
众所周知,文艺电影对于情节的要求并不太高,而改编现成的文学作品大致层面上可以保留原作的情节设计,以上两种变化都不再要求关锦鹏在情节设计方面继续创新。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关锦鹏转向电影内部要素的探讨与发掘,既属必然,也属合理。在近年的访谈中,关锦鹏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种转换,他说:“《地下情》说的是都市的人际疏离关系。如果今天来拍,我会从另一个视角切入。假如有机会重拍,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重拍,但我很有兴趣看看如今的梁朝伟,看看如今的温碧霞,如今的周润发、蔡琴、金燕玲他们会怎么样。”[2]很显然,如果今天再重拍《地下情》,关锦鹏定然不会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追求情节取胜了。事实上,这正是关锦鹏对导演艺术不断探索后的发现,代表了一个对艺术始终有追求的导演追逐艺术飞跃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二、记忆营构:锻造文化环境
所谓记忆营构,是指以营构记忆的环节为中心的导演风格。[3]从关锦鹏执导的电影来看,这是他在20世纪80—90年代之间的新尝试,于1988年上映的《胭脂扣》是最突出的代表。这部由梅艳芳、张国荣主演的影片,由于情节设计非常曲折(上文提到关锦鹏早期影片追求一种曲意回环之美,《胭脂扣》的情节设计即可作为范例),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成为整个影坛中难以忘却的经典作品。影片讲述了由梅艳芳饰演的名妓如花与张国荣饰演的纨绔子弟十二少陈振邦之间的爱情纠葛。男女主人公在50年前相知相爱,但男方家庭不满女方过往身份,遂极力反对二人婚事。无奈之下,两人以胭脂扣定情,一起吞食鸦片殉情。如花死后,因为未能在地府找到陈振邦,遂决意到阳间寻找。她在两名记者的帮助下,得知原来当年陈振邦自杀后被人救活,如今尚在人世,只是生活已十分潦倒。面对懦弱偷生的陈振邦,如花大梦初醒,归还定情信物胭脂扣,返回阴间投胎转世。影片便在陈振邦怅然若失的背影下落下帷幕。
从剧情的安排来看,《胭脂扣》在记忆营构方面极为用心。因为剧情的设计围绕两个世界进行,所以在穿越这两个世界之时,记忆的营构就变得异常重要,这是由于如果割裂记忆,两个世界之间的剧情便无法有效地开展了。在《胭脂扣》中,剧情的发展虽然将影片分割为人间和地府这两个世界,但贯穿其中的则是如花与陈振邦的人生记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在二人之间的记忆变得不朽,即使如花到了地府,也仍然能够不忘世间记忆,苦苦寻觅陈振邦,并借助这种顽强的记忆重返世间。不得不说,这确实是《胭脂扣》最动人心弦的情节。明代著名传奇《牡丹亭》的题词中,有一节脍炙人口的名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用这句题词来衡量如花对陈振邦的爱情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实现这种死而复生的能量,恰恰正是如花念念不忘的记忆。秦兰在分析《胭脂扣》时,曾提出影片的三个关键词——痴情、殉情、别情,这是非常有创见的看法。但围绕这三种不一样的“情”,如花穿越两个世界的记忆却是永恒的底色。[5]
众所周知,《胭脂扣》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小说采用的是一种“非纯情写作”的书写模式[6],而关锦鹏在将其改编为电影作品时,一改“非纯情”的风格,大胆使用纯情手法,将如花刻画为情痴的形象,其为情所困、为情所伤的遭遇,一度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而其为情而死、为情复生等环节,则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十分接近。由此可见,关锦鹏在处理如花这一人物形象时,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精神是高度接近的。
事实上,利用不朽的记忆来穿越两个世界,在中国以往的志怪小说中时常可见。最著名的就是曹丕《谈生》,这则故事也讲述了阴阳相隔的夫妻的爱情故事,最终也以悲剧收场。李碧华在创作《胭脂扣》时,脑海中未必没有谈生夫妻的影子。从志怪小说到《胭脂扣》原作,再从《胭脂扣》原作到电影《胭脂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记忆营构技术的日渐成熟,也可以清晰地发现由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再到电影作品中,记忆这一要素的发展脉络。美国汉学家柯马丁(Martin Kern)曾认为中国人自古就有浓烈的“记忆情绪”(memory emotion)。[7]在《胭脂扣》的呈现中,“记忆情绪”再次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关锦鹏在《胭脂扣》中对记忆营构技术的运用,是具备深厚的文化背景的。这也反映出一个常见的艺术原理,即一位导演的艺术风格往往与其所身处的文化环境有着深厚的联系。
三、地缘视域:延展城市想象
关锦鹏的不少作品改编自文学作品,如早年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改编自张爱玲的同题小说,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功。尹媛媛曾就此话题,进行过专门的探讨。[8]关锦鹏的另一部电影《长恨歌》也是对当代小说的改编。《长恨歌》是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是一部充满着上海情味的长篇小说。关锦鹏素来关注女性主义的话题[9],因此这部以上海女性为主角的小说自然就对关锦鹏产生了重要的吸引力。于是,将该小说翻拍为电影作品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正像上文所说,上海元素是《长恨歌》的底色,关锦鹏将这种地域文化的基调完整地保留到了影片中,展现了重视地缘视域的艺术风格。由于《红玫瑰与白玫瑰》与《长恨歌》都出自女作家之手,二者都具备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同时兼备老上海慵懒、世俗同时华艳的艺术特质,这两部电影常常被影评人或电影研究者拿来比较。需要承认的是,这两部影片有着明显的艺术风格上的差别。与《红玫瑰与白玫瑰》侧重情节不同,《长恨歌》对于地缘色彩的重视是异常突出的。甚至可以说,《长恨歌》是一部银幕版的上海旧文化的长卷。犹如喜帖街对于中国香港旧文化的映照,《长恨歌》可以视为对已经消逝的上海文化的祭奠,这在影片的色调中有着明显的呈现。一如题目显示的那样,影片讲述的是一段悠长的、无可名状的,又挥之不去的“恨”。这种“恨”,源于人物性格,源于时代背景,源于情节脉络,但它们却无一例外,都生根于上海文化,因此这种“长恨”,是上海这一片土地所特有的“长恨”。因此对《长恨歌》的分析,自然就无法将其与旧上海的文化特色脱钩。
事实上,无论是《红玫瑰与白玫瑰》还是《长恨歌》,关锦鹏都相当自觉地表现了重视地缘视域的艺术风格。《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既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女性,又带有上海女性所特有的若干特点,在艺术批评的语言中,王琦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典型化”的过程。而这种典型化的实现,可以归功于关锦鹏对地缘视域的重视,二者在此时是相得益彰的关系。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关锦鹏出生于中国香港,是深受香港文化影响的导演,而香港和上海都是旧都市文化的代表城市,因此关锦鹏对于上海旧文化的熟练呈现,与他成长的文化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有学者曾指出:“上海和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缘文化和历史渊源历来被文化界津津乐道并赋予‘双城之名。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吸引着众多香港导演如许鞍华、王家卫、关锦鹏等将其影像建构的对象选为上海。关锦鹏借上海题材、上海视角先后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阮玲玉》《长恨歌》中构筑其上海想象。”[10]这种看法恰好体现了关锦鹏电影中无比突出的地缘视域。
《阮玲玉》也是关锦鹏基于上海文化拍摄的文化影片。阮玲玉作为上海的一代名伶,本身就是旧时代上海摩登的代表,是旧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言人。关锦鹏选取这样一个人物,是有着充分的艺术考虑的。如果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和《长恨歌》塑造的是上海的平凡女性,《阮玲玉》则致力于刻画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艺术家一生的悲喜经历。在《阮玲玉》中,关锦鹏特别重视对历史的真实展现,忠实地反映了以阮玲玉为代表的旧上海影视圈的面貌,而且能够以小见大折射出上海这座文明都市的变迁史。从这个意义来分析,《阮玲玉》讲述的不仅是阮玲玉个体的荣辱浮沉,而且反映了整个上海这座旧文化之城的发展进程。这里同样折射出关锦鹏对地缘视域的重视。
由此可见,在关锦鹏一系列文化性质的电影作品中,地缘视域始终是他一以贯之,并非常重视的表现风格。观众在这些文化电影中可以看到旧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也能够对这种文化的衰歇进行独立的思考。这是关锦鹏在地缘视域中提供给观众的文化信息,很明显,这是极富文化关怀的艺术风格。
结语
关锦鹏的影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上文的论述只是提纲挈领地梳理出三种较为明显的艺术风格,并结合代表影片进行分析。需要澄清的是,本文对于关锦鹏艺术风格的分析,并不认为某部影片只能反映出一种单一的艺术风格。恰恰相反,这些影片既然都出自关锦鹏之手,就必然带有关锦鹏主体艺术风格的若干面相。只能说,在某部影片中,某种艺术风格体现得最为集中或明显,所以笔者在分析具体影片时往往就较明显的艺术风格进行论述,却并非否认影片还存在其他艺术特色。其实,任何一部影片都不可能呈现出完全单一的艺术风格,这几乎是电影制作的常识,但任何一部影片通常又能体现出某一种特别突出的艺术色彩,这也是电影制作的常识。对于关锦鹏电影艺术论的分析,必须在承认以上内容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对于关氏影片的分析就未免太简化了。
如果从关锦鹏进入电影行业的年头算起,现在他已经是拥有近40年导演生涯的导演了。在这一段经历中,他的不同佳作呈现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同时反映了他不断探索导演经验的历程。通过对他执导的影片的艺术风格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他的导演风格出现了明显的重心转移,由开始较单纯地追求情节设计方面的出彩,到后期重视发掘电影内部美感的自足,这些转变体现了他对电影艺术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深入,因此他后期的作品尤其富于文化魅力和艺术感染力。但需要揭示的是,这种源源不断的魅力和感染力,归根结底是由其影片的艺术风格传递出来的。曲意回环、记忆营构与地缘视域,这三个方面为关锦鹏的电影贴上了明晰的标签,同时为他的影片注入了最充足的养分。
【作者简介】 邓 静,女,四川成都人,四川传媒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影视文化,电影电视研究;
漆尉琦,男,四川成都人,四川传媒学院编导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跨媒介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四川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藏羌彝走廊民族音乐研究中心
2022年度课题“藏羌彝题材电影中民族音乐的叙事考索”(编号:LZY2022-D03)阶段性成果、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羌学研究中心”2022年度课题“基于短视频媒介的羌族非遗文化呈现方式与传播路径研究”(编号:2022QXYB00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安静.解读《胭脂扣》与曲意回环的交响曲[ J ].电影文学,2014(15):102-103.
[2]关锦鹏,庄君,关灿,等.“念你如昔”:从私人记忆到公共历史——关锦鹏访谈[ J ].当代导演,2021(05):88-95.
[3]王芝琳.创伤、记忆与疗愈——大林宣彦电影研究[D].北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22:2.
[4]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
[5]秦兰.痴情·殉情·别情——观影片《胭脂扣》[ J ].电影评介,2006(10):25.
[6]赵颖颖.“非纯情写作”:独特的情感书写——重评李碧华的《胭脂扣》[ J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06):23-26.
[7]MARTIN K. Memory in Early Ancient China[M].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177-198.
[8]尹媛媛.《紅玫瑰与白玫瑰》电影改编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2018(03):112-113.
[9]陈烨熙.关锦鹏电影创作中的女性情怀[ J ].视听,2017(07):73-74.
[10]陈慧茹.身份认同与城市想象——关锦鹏电影中的旧上海情结[ J ].电影评介,2013(18):63-66.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