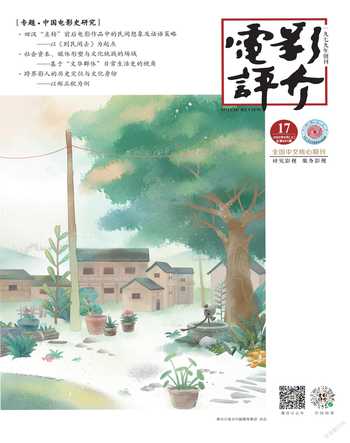城市电影的现实空间与文本想象
凯丽比努尔·色提尼牙孜 冯超
“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世界上第一部影片《工厂的大门》,于1895年首映于法国巴黎。事实正好说明,电影诞生之日,也即是城市电影问世之时。”[1]当然,城市电影并不等于以城市为背景的电影。譬如,各种风靡市场的动作片和灾难片都往往将城市作为影片的叙事场所,并通过各种拍摄技巧和特效技术赋予城市一种奇观化、刺激眼球的观感,但很显然其本身不能称之为城市电影。城市在其中只是起到表征某些想象的作用,要么是过度浪漫化的,要么是过度危机化的,真实的城市被这些表象所掩盖,成为一个满足观众幻想、可被随意篡改和替换的空壳,而“城市作为一种物质空间容器,被赋予了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的想象。”[2]
此外,当代城市和电影作为工业化的产物,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微妙的联系。一方面,电影对于城市的描述和勾勒,承载着人们对于城市景观的想象,城市正日益成为当今中国电影的核心对象;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电影逐渐走向商品化以及连锁影院在城市的兴起,观看电影便构成了人们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电影在城市之中逐渐收获了最广泛的受众,于是开始自觉地迎合受众的观影喜好,以期斩获更多的票房。同时,这一联系还包括电影从政治话语到个人话语、城市从生产空间到消费空间等一系列变迁间的相互对应。这些变迁和联系既带来了复杂的经验,也为今日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电影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本文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电影为例,探索伴随着国内城市化进程而发展的城市电影中的现实空间与文本想象。
一、城市电影的现实空间:差异与同一
城市与乡土作为一组相互对立的观念,不仅长期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还延伸至电影之内。两者的二元差异结构既是物质意义和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和时间意义上的。伴随着现代化呼声成为主流叙事,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区隔与差异被进一步放置在前现代和现代的话语之中:乡土代表着落后、封闭、愚昧,会产生种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奇观;城市代表着先进、开放、高流动性,是对传统中国的一种超越。事实上,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最早在国际上斩获声誉的便是一批以乡土为背景的电影。《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芙蓉镇》《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反映出各种时期中国乡土社会所遭遇的冲击,细致地呈现出乡土人的内心世界,并营造了一种独有的中国式的乡土景观,渗透着对故土的缅怀和对伤痕的反思。但与之相比,城市影片的发展卻略显艰难,在20世纪中后期城市影片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电影中的城市生活往往被视作是“小资产阶级”式的、堕落的,是要被批判的,这使得创作者们避之不及。同时在“十七年”时期,电影放映员的运送让偏远地区的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看到电影,建立了有别于以消费和商业为导向的都市院线电影网络的农村电影网。“新中国成立以来迅速发展农村电影网的需求促使流动放映这一模式成为主流。”[3]在这一网络中,受众被视作具有生产潜能和革命潜能的群众,而非商业语境下的能够消费的观众,乡土和城市的差异也在这种话语中被掩盖了,两者最终在劳动和生产这一叙事以及工人阶级的形象中找到了经验的通约之处,并通过影片所弘扬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产生联系。
如此一来,城市电影的创作在生产和受众这两个层面上遭遇了双重阻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加之中国城市的扩张和兴起,城市电影开始呈现出复兴态势。而城市电影的重新出现,必然伴随着对于城市空间的呈现和阐释。正如列斐伏尔所论述的那般,社会关系促成了社会空间的产生,而社会空间会使得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再生产。[4]革命话语的退却和发展经济的观念的风行,使城市身上的现代性特征越发明显。这种现代性代表的是先进,是对落后的乡土伦理和文化的改造,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意味着对空间的再塑和重新定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成为一个高流动性、潜藏着无限可能的空间,当代的、开放的、“洋气”的观念在其间同乡土的、老旧的乃至是封建的道德进行交锋。物质层面上实践的变迁,直接地影响着空间的再现,而这一影响又通过电影——大众媒介的代表勾勒出某种具备共时性的象征和秩序:城市不再仅仅是工作和劳动生产的场所,城市的生活经验中包含着对消费、对物品的肯定。例如在李少红导演的《四十不惑》(1992)中,描述了人到中年的北京摄影记者曹德培、妻子段京华和其在东北插队时的前妻留下的孩子赵小木的故事。曹德培与段京华的恋情既是浪漫的,同时也标志着一种个人话语在城市空间中的生成,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和消费主义一同携手取代集体话语。这种个体经验与曹德培在东北下乡时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影片以城市和地下室为主要表现空间,在天坛边跳交谊舞和在地下通道谋生的人群仿佛刻画着一个时代的群像。林林总总的城市景观仿佛是在宣告城市完成了一次“再现空间”的转变:城市作为消费空间受到认可。但空间意义转变的直接后果是人们的无所适从:当曹德培去福利院认领儿子,人被镶嵌在一个通风口处,城市的浩大与个体的渺小顿显。父与子透过时间看到了穿越时代的折痕,他们站在近代中国巨大的城市社会变迁的浪潮之下,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无所适从。空间意义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一次断裂。
这种无所适从同样可以在娄烨的《苏州河》(2000)中看到。在《苏州河》中,摩登都市上海的城市空间显现出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质地:不再是崭新、充满朝气的,而是饱经风霜、残破不堪、满目萧条的。苏州河两岸的城市空间被影片阐释为进程的中断之处,杂乱不堪的河道、触目可见的城市垃圾……在这个空间中,传统的依然根深蒂固,现代的却无法完全降临。都市文化形成了一个遥远坐标,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却颇具诱惑的承诺。这种传统的失落和远方的时尚共同赋予了城市空间以荒芜的气质。它被经济发展的大潮带离了原有的位置,却因为种种原因停留在了进程的中断点上,城市空间因之呈现出一种去时间化的特点。传统的话语被破除,先进、现代的话语被搁置。
显然,城市的发展应当伴随着对人的改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将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转而拥有新的性格和心理结构。但当外部条件发生转变,而个体依然滞留在原处之时,一种结构性的压迫便降临了。这种压迫不仅存在于城市的公共交往空间,也发生在家庭内部。在《万箭穿心》(2012)中,影片对变革动荡时期的家庭进行了细致地呈现,并围绕女主人公李宝莉这个角色,将现代城市的一系列症结串联起来:挣票子、分房子、老人的赡养、强行拆迁、出轨、下岗、寻短见、蹲监狱、离婚、高考、婆媳失和、母子决裂、单亲家庭、扫地出门、风水、技术革新、文化水平不同造成的隔阂等。[5]李宝莉的命运被讽刺性地归结为风水上的“万箭穿心”,但从一种社会结构的地理学上来看,这样的总结未免不失为一种合理解释:城乡差异、贫富差距、社会转型、男女倒错等诸多要素,就像万箭一般,射在了李宝莉所处的位置。在变革动荡时期,城市转变成为一个充满危机的场所,并将这种危机蔓延至家庭内部。马学武与李宝莉婚姻的悲剧,是出于对爱的误认,对自身性格的误解,但快速变动的空间环境,不曾留给他们来纠正这些错误的余地,相反地,空间的急剧变动对他们的家庭施加了源源不断的压力。武汉的城中村和汉正街街景成为城市空间的微缩隐喻,挑扁担亦将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直接地转置为肉体和视觉上的压迫。城市空间最终成为一个充满敌意、需要谨慎对待的危险场所。李宝莉被赶出马家,也是封建男权思想的又一次胜利。
当然,城市电影的空间也不总是象征着痛苦、压迫的“异托邦”。在城市电影中,对空间的建构有时还会与新自由主义下个人的成功学叙事相合谋。此时,危机被转变为机遇,个体的焦虑被改造为对成功的渴望。在《奇迹·笨小孩》(2022)中,深圳近乎成为一个创业者的神话诞生地。厂房、高楼大厦、电子产品市场,这些空间渗透着创业者的信念:要么成功,要么去死。个体与城市的关系被隐喻为蜘蛛和蛛网。城市的空间成为一个凶猛的、待征服的存在,个体既有可能像冒险家一样在其中斩获资本和名誉,取得成功,也有可能遭遇不测。
不过,在这些旨在表现伤痕、迷茫和焦虑的城市电影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城市电影。它们倾向于迎合观众(往往是都市白领和中产阶级)对于现代都市的想象,挑选特定城市的某些标志元素,围绕这些元素进行消费意义上的空间再现,从而获取观众的好感和青睐,斩获票房,从而赢得市场意义上的成功。在《火锅英雄》(2016)、《摆渡人》(2016)等影片中,重庆的山城、方言、火锅、地名、防空洞、电梯、陡峭的层次感等元素被萃取而出。对这些元素的极端强调和社交网络上对川渝文化的宣传一道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再现空间。这里的再现空间象征的是市井、令人心生向往的生活,是感官的滿足和欲望的释放。从商业角度上来说,这些城市电影构成了一种“类型片”,即强调城市特色、打造城市名片的类型影片。当然,这种“类型片”早在港台的电影工业中就已存在。对香港和台北特质的渲染和描摹,对其现代、时尚、琳琅满目的景观的叙写,被今日的内地电影工业承接过来。尽管每一座城市的特质是不同的,但这种类型片更强调的同一性,即竭力将城市空间塑造为一个激发欲望、创造需求的游乐场。城市被过度地浪漫化、美好化,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是千篇一律的内核,是对观众欲望的号召。
因此,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的现实空间呈现出差异和同一性的特点:一方面,对它的建构中既包含着对现代化的希冀与反思,又包含了对社会变迁和转型的焦虑和不安,还蕴含了对乡土的缅怀与对新道德的呼唤;另一方面,又掺杂着港台甚至西方都市示范的影响。城市空间作为一面镜子式的存在,既映照着一个理想的、时间跨度意义上的现代景观,将人们对于现代生活的幻想呈现出来,又映照着过去和当下,映照着乡土和各个现代化的断裂之处,将痛苦、失落、遗憾等情感和心绪呈现出来。虽然城市空间的气质和表象各不相同,但其象征的涵义以及城市人的情感结构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这背后是当代中国面对现代性的迷茫。
二、城市电影的文本想象:另一种生活
城市电影对于空间的建构实质上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心态的回应。而城市电影的文本想象通过对于城市生活的符号化呈现以及自身强大的影响力,成为人们认知城市、理解城市的主要资源。贾樟柯与山西、王家卫与香港、杨德昌与台北……这些导演的影片与特定的城市、地域近乎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关联。这些基于导演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构建出的影像文本具有强烈的辨识性。在王家卫的影片中,香港成为一种持续在场的事物。即便是在《春光乍泄》(1997),一个发生在南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中,香港仍然以潜在的方式进入观众视野:那与香港极度相似的灯火、小巷、酒吧,以及主角流利的粤语。香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王家卫的影片中被成功转变为一个文化概念。这个文化意义上的香港超越了黑帮火拼、豪门内斗等奇观式的浮夸想象,通过对欲望与孤独并存的都市生活的指涉,抵达观众的内心。这种从地理意义到文化意义的跃迁,在城市电影中可谓比比皆是。或者可以说,城市电影的文本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磨灭地理的概念的功能,将城市浓缩为一个文化性质的命题,继而阐明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最初诞生于某个特定的地点,但城市电影具有将它从地理空间的束缚中释放出来的能力。
同样的现象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也可以看到。《三峡好人》(2006)的叙事场所不局限于山西,但山西的影子依然无处不在。长江流域的漂泊之感与山西的气质相交汇,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呈现出混乱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在日新月异的中国突然变成了一种过去的事物,充满了怀旧气息。边缘人物的内心世界、对出人头地的渴望、对爱人的寻找,这些日常的叙事主题被淹没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之中。贾樟柯将他独有的山西经验化为一种废墟之感,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时常更新的废墟。因而影片同时还兼具了一种记录的功能:它捕捉着转瞬即逝的个体生活,挖掘曾有过的现实,并将其放置于影像文本中,形成了对于转型期社会的追问。
同时,城市电影的文本还发挥着涵化的作用。它教导着人们城市生活的方式,挖掘城市生活的某个侧面,是人们进一步了解某座城市的途径。在《甲方乙方》(1997)中,顽主式的北京青年形象以玩乐的姿态消解了首都宏伟的意义,宣告着市民生活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不过这种顽主在《老炮儿》(2015)中就成了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形象,这种历史的脉络表明了北京文化或者说生活方式在十多年内的转变。而在《钢的琴》(2010)中,历史以更加明晰的方式实现了在场。苏联老歌、机床、砖墙、下岗的大潮……这些事物烘托着辉煌的失落。沉默、狼狈的父亲与渐行渐远、走向破落的城市,向人们讲述着一段在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日被遗忘的过往。在《爱情神话》(2021)中,上海的厅房、弄堂、街巷等空间和方言、咖啡、小家碧玉的精致作风相交织,将“海派”生活阐释得淋漓尽致。尽管影片专注的是男女之间的情谊,但这种情谊却拥有了某种历史感,它穿过革命的岁月与奢华的岁月,和市民意义上的上海相挂钩,从而为人们展示了另一个上海。
不过,城市电影所表达的并非总是真诚的、触动人心的。城市电影的空间建构往往呈现出文化工业的特征:即虚假的个性和实质上的标准化。在城市电影的文本想象中,这种情况也常常出现。在这种文本当中,观众所看见的是千篇一律的内核:即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浪漫爱情以及成功至上的叙事氛围。它不留给失败者、被时代淘汰的人、孤独忧郁的都市人以表达空间,即便有,态度也总是戏谑的、轻浮的,其文本想象最终也只是沦为对于经典的团圆结局的空洞歌颂。
结语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城市电影亦同步前行。城市电影依托某座或某些特定城市,通过影像搭建出一个媒介空间,形成了一座“镜城”式的存在,表达出转型时期民众对于城市的想象。同时,城市电影还通过文本塑造着观众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乃至认同,成为人们认识当代中国的一条重要路径。
【作者简介】 凯丽比努尔·色提尼牙孜,女,新疆吐鲁番人,新疆财经大学基础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冯 超,男,河南鹤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科学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习近平文艺思想推进新疆文学发展研究”(编号:19BZW09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汤晓丹,桑弧,沈寂,等.“城市电影”大有可为——本刊编辑部召开“城市电影”研讨会[ J ].电影新作,1988(6):54-63,1.
[2]黄露.城市电影中的空间意象:以家庭、街道、都市为维度的考察[ J ].传媒观察,2021(11):89-93.
[3]周晨书.“十七年”农村电影放映再审视:放映员的身体作为媒介[ J ].当代电影,2019(10):54-59.
[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上海:商务印书馆,2021:34.
[5]罗荣.《万箭穿心》:一曲江城市井女性的命运哀歌[ J ].名作欣赏,2019(24):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