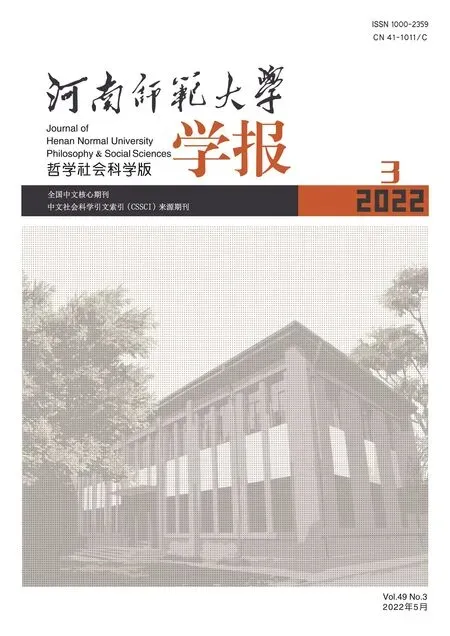清初藏书家对官修《明史》的贡献
——以康熙朝为中心的考察
李 雪,李宗辑
(1.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2.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康熙年间,清廷重开明史馆,为了以丰赡翔实的明代史料佐修《明史》,积极向藏书家征购图书,这些史籍对《明史》的最终修成功用甚大,是故总裁张廷玉强调《明史》乃“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1)张廷玉:《张廷玉全集》之《澄怀园文存》,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藏书家广泛参与《明史》修撰的整个过程,对高质量完成《明史》,功不可没。初步统计,包含监修、总裁、纂修官以及私下聘请人员在内,康熙一朝参与纂修《明史》的朝野士人约111人,其中著名藏书家达38人,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探讨清初藏书家对官修《明史》的贡献,不仅可以深化官修《明史》的史料来源和纂修过程等诸方面的研究,亦可洞悉清廷与士人间关系的微妙演化(2)关于清初官修《明史》与藏书家互动之研究,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门成果。但颇有涉及相关内容者,其中重要的论著有何冠彪《清代前期君主对官私史学的影响》,《汉学研究》,1998年第1期;王记录、刘海静《清代史馆征集资料的途径与方法》,《历史文献研究》,第26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段润秀《官修〈明史〉的幕后功臣》,人民出版社,2011年;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乔治忠《增编清朝官方史学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吴振汉《明清之际的史家与明史学》,台北“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9年;段润秀《文化认同视角下的清代〈明史〉修纂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
一、修书何据:顺、康二朝纂修《明史》的史料困局与化解
顺治、康熙两朝曾多次下令撰修《明史》,然受制于各种因素,一直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官方所藏明代史料极度匮乏。顺治二年(1645),清廷首次下诏组成《明史》纂修团队,筹备修撰胜朝史书。冯铨以总裁身份被征入朝,首奏“收前朝典籍”,请求从中央和地方各衙门以及藏书家征购图书以资修史之用(3)(乾隆)《涿州志》卷14《人物三·名臣下·冯铨》,天津图书馆编:《天春园藏善本方志选编》第6册,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就北京宫廷藏书而言,华北地区历经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明代史料存留不多。顺治年间《明史》副总裁钱谦益说:“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以至“内阁之书尽矣”。他慨叹:“自有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26《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95页。纂修官王士禛则言:“鼎革之际散轶,不可胜道。”(5)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为修史重要依据的诸朝《实录》,亦存在残缺;特别是崇祯一朝,《实录》未纂成,史料散佚严重(6)张岱:《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24页。,使晚明史事编纂缺少了重要的资料依凭,“国无藏书,事近人存,野史未出”(7)傅维鳞:《明书》卷171《叙传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0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03页。。
内府藏书大量亡佚、焚毁,使得修史无据,对《明史》编纂造成莫大困难。即使是尚存的官方《实录》,也多有记载不实或缺漏,不足取信。明人王世贞曾指出明代史职之弊:“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8)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72页。钱谦益亦称《实录》所载“不过删削邸报,而国史又多上下其手,乞哀叩头之诬……恐难以信后也”(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55页。。即便甚为推崇《实录》的万斯同,也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为国讳”“暗于大而明于小”“疏漏已甚”“随人曲笔”“是非颠倒”等诸弊病(10)许苏民:《朴学与长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邓之诚甚至认为明之《实录》与唐宋有“上下床之别”,“其乱如绳,发凡起例未见,其人褒贬无闻,徒侈篇翰”(11)邓之诚:《〈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序》,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首,燕京大学图书馆据馆藏抄本印行,1937年,第1b-2a页。。而崇祯一朝史料虽时有冯铨亲属呈送的邸报入馆,但其史料真实性饱受怀疑,“岂无意为增损者”(1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苏同炳考证崇祯十一年前明廷邸报均为手抄本,尚未雕版印刷,故易增损篡改。见苏同炳《明史偶笔》,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4页。?总裁叶方蔼也疏言仅以邸报为史料之危害:“若启祯两朝,非得确有纪载之书,而徒凭区区断简残编之邸抄以为依据,则挂漏差讹,势必不免矣。”(13)叶方蔼:《叶文敏公集》卷1《请购书籍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因官方史书和档案的缺乏,私史重要性于此时凸显。
鉴于内府藏书损失严重和《实录》之缺讹,朝廷才有“不得已采之稗史”的决策(14)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页。。黄宗羲等人强调私史对正史的补充作用:“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15)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序》,《黄宗羲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大学士刚林等奏请在揽收官方档案、史书以外,还提出对私史的征集:“野史、外传、集记等书,皆可备资纂辑,务须广询博访,汇送礼部,庶事实有据,信史可成。”(16)《清世祖实录》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癸丑,中华书局,1985年,第426页。因而,征购藏书家手中有关明代的私家著述辅助修撰《明史》显得非常必要。然顺治朝虽多次下旨征书,但内府藏书情况并未得到改观,康熙曾指斥顺治朝臣工征书不力:“至今未行察送。因循了事,不行查收。”(17)《清圣祖实录》卷16,康熙四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1986年,第239-240页。再者,顺治后期政治发生转向,导致《明史》纂修中对私史管控趋于严格,要求“不许滥收”(18)《清世祖实录》卷126,顺治十六年五月己卯,中华书局,1985年,第977页。。康熙初年重申“止采实录,严禁旁搜”(19)《清圣祖实录》卷16,康熙四年八月己巳,中华书局,1986年,第239-240页。。统治者在诸多方面对士绅采取的“压抑政策”(20)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83年,第24-28页。,使得征书工作难于展开,影响尤大者是《明史》案。
顺治十八年(1661),浙江发生庄廷鑨《明史》案,书内多“指斥昭代语”,清廷为收杀一儆百之效,波及者“以千数”(21)沈起:《查继佐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第56页。,大量江南世家巨族受到冲击。案中不仅刻书、印书、订书、送板者“一应俱斩”(22)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节庵辑:《庄氏史案本末》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5页。,连售、买者也难逃一死,“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23)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9页。。在这样的氛围下,藏书家噤若寒蝉,如文学家吴伟业担心自家藏书与所著书可能触祸,“惴惴莫保”(24)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32页。。
藏书家为求自保,藏书或自行毁弃,或秘不示人。朱彝尊亲眷将其购藏书籍内凡涉明季者,“争相焚弃”(25)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戴名世称有书人家子孙惧受牵连,藏书秘而不宣:“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26)戴名世:《戴名世集》,中华书局,2019年,第36页。故而整体情况发展为“其家后裔不知考核可存与否,悉以付火,故皆佚而不传”(27)范锴:《华笑庼杂笔》卷6《施汉三丹桂楼杂箸坿茹略文殉战事》,清道光乌程范氏刻《范声山杂著》本,第14b页。。《明史》案是清廷加强文化压制的重要事件,造成了恐怖肃杀的文化景况,使藏书家身心遭受挫伤。官方意志莫测不定使他们对待朝廷征书的态度发生转变,在随后征书行动中各种搪塞应付,乃至为规避祸患删改史书上交。诸多因素对《明史》纂修产生了不良影响,成为顺治一朝《明史》未能成书的重要因由,修书成果亦寥寥(28)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康熙四年(1665),明史馆短暂复开,朝廷鉴于顺治朝征书修史之困难,为保证纂修工作顺利进行,松解长期以来的高压政策,“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但不久修史活动再次罢停。延至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在全国的统治趋于稳固,遂再次倡修《明史》,旨言“编纂史书,关系一代政事,用垂后世,若书籍缺少,虽编纂不能成完史”,命“各省遣官购取书籍”(29)《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癸丑,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这一系列举动为康熙一朝史馆以明代私史助修《明史》提供了保障,从而确定了《明史》撰写基本标准:“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众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30)刘承幹:《明史例案》卷2《徐健庵修史条议》,徐蜀编:《〈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3页。这一政治“解禁”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藏书家戒心,使其能够且愿意在纂修过程中贡献力量。
“一代信史”之成书必依据存留史料和前人著述,叶方蔼言:“书籍者,作史之材与器也。假使一无证据,从何刊削成编?”(31)叶方蔼:《叶文敏公集》卷1《请购书籍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史料、史书除来自遣官采访、地方官府购买、官学和书院呈献等途径外,以藏书家为主要对象的民间征集也是其中一种重要途径。经历一系列动荡,私藏明代诸史籍,大有“脱于水火之灾者,或不免饱蠹鱼之口;能逭逃于悍兵剧盗荡子孤嫠之手者,或湮没于通人显官崇楼邃阁之中”(32)傅增湘:《校刻〈儒学警悟七集〉跋》,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卷末,中国书店,2010年,第229页。。故此,《明史》监修徐元文上疏提及藏书家之重要性:“藏书之家,许详计卷帙多寡,厚给赏赉;或所献多者,量行甄叙;若未刻书籍,不愿径献者,官给雇直,就其家钞录。”(33)徐元文:《含经堂集》卷18《请购〈明史〉遗书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叶方蔼亦请求朝廷在征书一事上“曲示旁求”(34)叶方蔼:《叶文敏公集》卷1《请购书籍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如此,藏书家中无论是在朝官吏,还是明遗民,或是依违于故国、新朝间之摇摆不定者,都有机会以不同方式为纂修《明史》效力。《明史》得以顺利修撰且成一代全史,藏书家之助益功不可没。进一步讲,藏书家对《明史》修撰的贡献,远不止提供藏书,他们以多种方式参与其中,贡献是多方面的。
二、“资书”史馆:藏书家为修纂《明史》提供资料
《明史》修纂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数十年时间,任职于明史馆的史官汪由敦曾赞誉当时史稿之“精审”乃“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35)汪由敦:《松泉文集》卷7《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33册,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633页。。在撰修《明史》过程中,藏书家亦以不同方式从多方面与事,从最初向清廷献、借明代史籍,参与《明史》稿本的起草,到最终审阅校定,这些都为《明史》最终之“精核”打下了坚实基础。
所谓“资书”史馆,是藏书家将藏书交付明史馆使用,分为两类:一是应清廷要求,主动或被动地将藏书提供给官方使用;一是不经过官方,把藏书私下借予纂修官参阅。
第一类,通过官方渠道提供藏书。明史馆内史料凭征书得到很大充实,汤斌即言:“史局既开,四方藏书大至。”(36)汤斌:《汤子遗书》卷4《答黄太冲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6页。提供藏书的主力军,当是藏书家。叶方蔼道:“藏书之家,或详计卷帙多寡,给直若干;或开注姓名送部,俟纂修完日,仍以原书给还;或有抄本书籍,官给雇直,遣人就其家誊写。”(37)叶方蔼:《叶文敏公集》卷1《请购书籍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依照叶氏记载并参考相关资料,可知藏书家向官方“资书”的方式主要为收购、呈送和抄录三种。
其一,收购。顺治年间,汤斌在《敬陈史法疏》中早已言明购书的重要性:“今日时代不远,故老犹存,遗书未烬,当及此时开献书之赏,下购求之令。凡先儒纪载有关史事者,择其可信,并许参考。庶几道法明而事辞备矣。”(38)汤斌:《汤子遗书》卷2《敬陈史法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顺治时曾多次下旨“购求遗书”,但效果不佳。康熙年间明史馆征书之时,受《明史》案等影响,藏书家起初并不积极,徐元文指出:“馆阁见存书籍,有关明史者甚少……而藏书之家,又恡于陈献,稽延日久;即使间有呈送,不过以寻常见闻之书,苟且充数,终无裨益。”(39)徐元文:《含经堂集》卷18《请购〈明史〉遗书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8页。“恡于陈献”道出了大部分藏书家的抵触心理,随着康熙朝文教政策改变,购入之书渐多,“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40)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与余生书》,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总体来看,购书量虽不多,亦是征书的有效途径。
其二,呈送。以此种途径献书的藏书家不少,如冯铨家人将所藏邸报呈送朝廷:“顷馆中诸君,俱以启祯二朝记志缺略,史宬本未备。而涿州相公家,以崇祯一十七年邸报全抄送馆编辑。”(41)毛奇龄:《寄张岱乞藏史书》,见张岱《张岱诗文集》附录“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31页。明遗民、藏书家李清,其家“藏书满架、缣帙烂然”,颇蓄世间罕本(42)季娴:《闺秀集》卷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330页。。当清廷征召其往京师佐修《明史》之时,他称病不出,但呈书数种,徐元文记“今皇上十八年开局纂修《明史》,余首列公名以上,亦谢病不行,朝廷于其家取数种付史馆焉”(43)徐元文:《含经堂集》卷27《李映碧先生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8页。。黄宗羲将其珍藏的部分明代史书移送史馆;朱彝尊将先祖朱国祚撰写的《孝宗大纪》“送馆”(44)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96页。;王世德之《崇祯遗录》、冯甦之《见闻随笔》、邵廷采之《西南纪事》《东南纪事》亦送史馆(45)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7《谒毛西河先生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8-309页。。另外,著名藏书家曹溶曾整理大量明代史书,如《明史事实》《续献征录》《明漕运志》和《崇祯五十宰相传》并其《年表》等。当史馆征集史籍之时,曹溶呈送了大量史书,“编辑故明事迹共七种,计六千余页,皆与史书相关,足供局中采择者”(46)曹溶撰,胡泰选辑:《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牍》,《清代名人尺牍选萃》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其中所辑《崇祯疏钞》《传谕录》等书,多“史馆所未备”,此外还进献其珍藏崇祯朝邸报“五千余册”(47)李集、李富孙辑:《鹤征录》卷3《曹溶》,《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95页。。明史馆臣称赞他“不忍藏名山,为功在石渠”(48)施闰章:《施愚山集》之《诗集》卷14《寄赠曹秋岳司农是年七十(三)》,黄山书社,1992年,第274页。。曹氏因在当朝士绅及明遗民中颇具影响力,他主动呈送图书的行为推动了清廷征书活动的顺利进行。
藏书家呈送藏书的原因各不相同,大部分呈送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有些藏书家目睹献书可得朝廷青睐,希冀以藏书换取朝廷表彰或功名利禄,如冯铨在清初饱受非议,其亲眷欲借献书邀宠于朝廷;有为婉言谢绝清廷的拉拢而曲意应承者,如李清;亦有为故国之事辩诬、力证事实者,如王世德、冯甦、邵廷采等人。
其三,抄录。由于史籍珍贵或尚为手稿等原因,藏书家不愿将书出售或外借,对于这类书籍,清廷采取派人抄录的方式获取文本。清廷曾点名将査继佐、傅维鳞等人的史著给资誊写,“该抚转行所属访取誊写,于文到之日,限四个月内速行解部,转送史馆可也”(49)傅维鳞:《明书》卷首《圣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38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5页。。其中以抄录黄宗羲书之事最为突出,叶方蔼致书海宁知县,希望其遣人往黄家抄书,“先生(黄宗羲)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书必富,《万历编年》乃其先公笔,而《史概》《国榷》等书,又皆浙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开,此间未有者,录一单奉寄,求老年台令善书胥史,就梨洲先生家尽数抄写为幸”(50)叶方蔼:《与许酉山书》,《黄宗羲全集》第21册《南雷诗文集》附录《交游尺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87页。。清廷还明旨要求黄氏配合史馆工作,“凡黄某所有著述有资《明史》者,着该地方官抄录来京,宣付史馆”(51)黄百家:《〈明文授读〉序》,黄宗羲编:《明文授读》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0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10页。。又如毛奇龄致信张岱请求抄录其相关书籍:“鲁国、隆武,始终阙然……不揣鄙陋,欲恳先生门下,慨发所著,汇付姜京兆宅抄录寄馆,以成史书。”(52)毛奇龄:《寄张岱乞藏史书》,见张岱《张岱诗文集》附录“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30-531页。黄宗羲和张岱这些当世大藏书家愿意借予抄录,堪为表率,促成了这一方式的成功。
从结果看,康熙年间这次“上谕征集海内遗书”的行动无疑是成功的,凡盐铁、兵农、礼乐、河渠、沟洫以及邑志、家乘、稗官、野记等有关史事者,“会萃”史馆(53)徐釚:《南州草堂集》卷19《〈吴江县志〉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3-364页。。据雍正年间纂修官万邦荣《答庶常刘芳草先生手札》言,史馆内明代史籍“可供修史者共贮两库,约有一千几百部,浩如烟海”(54)万六德:《〈明史列传分纂〉跋》,万邦荣:《明史列传分纂》书后,清道光十四年万六德刻本,第1b页。。这些书籍为《明史》的高质量撰稿提供了详尽且丰富的史料。
第二类,藏书家将藏书私下借予史馆纂修人员参考。需要指出,除去部分藏书家有奇货可居心理不呈进外,直接献书或借书给朝廷尚存风险,《明史》案相距不远,藏书家尚有颇多顾忌,“康熙初,为国史事,杀戮多人,自此文网渐密”(55)归庄:《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18页。。因此,较之前文提及存在风险的“资书”方式,通过馆臣之亲属、师生和友朋等私人情谊将书籍私下借阅互通更为安全。朱彝尊在明史馆期间,曾将私藏借予馆中同僚使用,如将《土官底簿》借予毛奇龄编写《土司传》,“予在史馆,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毛检讨大可是予言,撰《蛮司合志》,因以是编资其采择焉”(56)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87页。。纂修官方象瑛亦从丹徒张氏处借得“穆、神两庙《实录》”,进行有关史传之撰写(57)方象瑛:《健松斋集》卷16《纪分撰〈明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4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66页。。徐元文以私人名义购买明代史书供史馆诸人参阅,“遍征古今图籍,至稗官小史,凡有裨于纂修者无不购也”(58)钱澄之:《田间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第316页。。汤斌富有藏书,他欲阅览明朝史书,然京师“不能寻买”,乃命其子于家乡收集,除家藏外,还寻觅亲友手中“可借”者(59)汤斌:《汤子遗书》卷4《寄示诸子家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1页。。朱彝尊分撰嘉靖朝诸臣传并《文苑》《诸王》二传,叮嘱子昆田往富藏之家搜寻相关资料,“可问南门伯祖,若有数人文集,须借寄。倘坊间有鬻者,千万买来寄我……我乡若姚绶、戚元佐、项笃寿诸先辈集及所著书并瀛洲十老诗,千乞寄来”(60)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018页。,并多次致书友人请求借阅相关书籍(61)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999、1014页。。黄宗羲也曾将家藏史书提供给万斯同,“先公《大事记》,神庙逮光熹。余有《三史钞》,实录及家稗。倾筐授万子,庶为底本资”(62)黄宗羲:《全祖望选本南雷诗历》卷5《寄贞一五百字》,《黄宗羲全集》第2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08页。。这种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借书行为成为一种规避政治风险、保护自我的有效手段。
赵园指出部分清初私家史书的写作是“对抗官方政治的一种隐蔽的形式”(6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5页。。与这种“隐蔽”反抗对应的是“自我审查”,这在藏书家中不乏其人。王汎森提出,清代统治集团施行史狱或文字狱,“打压之酷与形成的‘涟漪效应’,使得人心极度恐慌,而处处形成‘自我压抑’的现象”(64)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6页。。尽管清廷表示“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但藏书家力求避祸且不触怒官府,进行严厉的“自我审查”,主要表现为删改著述。研山堂主人孙承泽在呈进《崇祯事迹》时表示“因检旧日抄存,辑成十八卷,装成七本”,其实早在顺治年间此书业已完成,谈迁云:“孙侍郎北海承泽《崇祯事迹》一袠……侍郎辑崇祯事若干卷,不轻示人。”(65)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55页。此次“辑成”工作很明显是在“自我审查”。曹溶也颇类似,他对徐元文言:“出以所纂辑末年杂事,重加参订,厘为数书,敬于仲冬恭上史馆。”(66)曹溶撰,胡泰选辑:《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牍》,《清代名人尺牍选萃》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59页。曹氏强调这些史著都已“重加参订”,且“中间绝无忌讳”(67)曹溶撰,胡泰选辑:《倦圃曹秋岳先生尺牍》,《清代名人尺牍选萃》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77页。。戴名世察觉到此举动危害了《明史》撰写的完整与客观:“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68)戴名世:《戴名世集》卷1《与余生书》,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直接后果就是纂修过程中相关史料的缺乏,如潘耒在史馆撰稿时,颇叹“家无藏书,转展借觅,此有彼无,缀残补缺”(69)潘耒:《遂初堂文集》,卷5,《上某总裁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776-777页。。这也是《明史》案的影响在藏书家献书方式以及对待史籍态度等方面的一种显性表征。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涉及清朝及其建国前史事存在大量错漏、删改,这更需要纂修官们在撰写史稿过程中凭借自身史识和自存史籍进行辨误纠正。
三、入馆修史:藏书家参与《明史》纂修
为前朝修史,对撰修者学识要求甚高:“世远年湮,事迹隐晦,而稗官野乘又皆杂出不经,非有高古今之识、擅论断之才者,不能订讹正伪,垂为信史。”(70)毛奇龄:《重修宗谱序》,《萧山长浜陈氏宗谱》,卷首,清同治十一年敬睦堂刻本,第1a-1b页。因此,参与《明史》纂修的藏书家,皆是才能出众之通才。黄宗羲在《传是楼藏书记》中说世之藏书家“至于书之为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读,即有能读之矣,或不能文章”(71)黄宗羲:《南雷诗文集》记类《传是楼藏书记》,《黄宗羲全集》第19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而参与《明史》纂写的诸藏书家,则可称兼具藏、读与文章之能,是《明史》得以成功的功勋之臣。作为藏书家的纂修者们出于各种顾虑,很多人虽不愿呈送自己的藏书,但其藏书却仍为修纂《明史》所利用,可谓一件幸事。其中一些藏书家已意识到以自己所藏史书协修《明史》的重要性,朱彝尊说他们“必能记忆所阅之书,凡可资采获者,俾各疏所有,捆载入都,储于邸舍,互相考索”(72)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89页。。加上史馆内部“虑其间定多湮灭不传之人,许任意搜讨,不拘分限题目”(73)毛奇龄:《西河合集》,《毛奇龄全集》,第21册,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301页。,营造了宽松的撰史氛围。
当时明史馆分纂《明史》之盛况,杨椿在《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略》中稍有述及:“汤文正公为《太祖本纪》,徐公嘉炎为《惠帝本纪》,朱君彝尊为《成祖本纪》,徐公乾学为《地理志》,潘君耒为《食货志》,尤君侗为《艺文志》,汪君琬为《后妃》《诸王》《开国功臣》传,毛君奇龄为《流贼》《土司》《外国》传,其余各有所分。”(74)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略》,《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页。仅此处就提及汤斌、朱彝尊、徐乾学、潘耒和毛奇龄等多位藏书家。除去主事大臣外,主要参撰的藏书家群体内大致有博学鸿儒和普通士人两类。
康熙十八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大量“博涉经籍”“沉酣经史”“淹通古今”之宿儒通学被笼络在内,部分为《明史》纂修官,其间不乏藏书家。如经学家毛奇龄,浙江萧山人,有藏书楼冰香楼、友汉居。毛氏“居屋三间,左右庋图史”,藏本中不乏宋元善本(7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32,《毛西河先生事略》,岳麓书社,1991年,第920页。。他用自己藏书《宫闱记闻》完成了《后妃传》的撰写。甫入史馆,毛氏抓阄分得《后妃传》中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但史料方面毛氏于史馆仅见明官方“册封年时,及后妃崩薨、丧葬诸礼节”。所幸藏书内有《宫闱记闻》一卷,“可谓小备,虽所阙亦无几”,参核实录和其他私史,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76)毛奇龄:《西河合集》,《毛奇龄全集》,第32册,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7-8页。。毛氏修史慎谨,为草拟初稿,除史馆当值外,“日就有书人家,怀饼就抄”;每领一传记,“必几许掇拾,几许考核,而后乃运斤削墨,侥幸成文”(77)毛奇龄:《西河合集》,《毛奇龄全集》,第22册,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他凭借丰富的藏书与见识,为《明史》初稿完成贡献颇多。再如朱彝尊,聚书数十年,藏书富于当世,自称“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康熙十八年,以博学鸿儒科一等,奉旨入明史馆,对《明史》体例多有建议。他指出作史首在制定体例,“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同时提议史书体例要因时制宜,不能因袭前代,“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78)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88页。。对于《明史》相关内容的书法,诸如建文帝“亡”“逊”问题、《明史》是否立《理学传》的问题、如何看待东林党人等,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秉持公正直书的书史标准,反对以私人好恶作史,“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79)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392页。。
普通士人代表当推万斯同。万斯同乃一介布衣,未参加博学鸿儒科,康熙十八年,为保证《明史》修纂质量,在其师黄宗羲的鼓励下,应邀入京修《明史》,“携书数十万卷”以随(80)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20页。。修《明史》期间,万斯同虽然不署衔、不受俸,但却是实际上的总纂,“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明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81)魏源:《古微堂外集》,见《魏源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97页。。因谙熟明代史事典故,万氏被徐元文等人委以审校稿本,“昆山领史局,季野为之任考索”(82)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567页。,“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万斯同)覆审”(83)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18页。。再如黄虞稷,本应参加博学鸿儒科,因“闻母丧还白下”(84)李集、李富孙辑:《鹤征录》卷3《黄虞稷》,《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3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99页,后蒙徐元文举荐,以布衣入明史馆修史(85)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6《徐立斋相国事略》,岳麓书社,1991年,第187页。。黄氏入史馆后,受命撰写《艺文志》,当时清廷藏书中尚不能满足志稿编写,黄氏以自家丰富的藏书为基础,参考已草成的《千顷堂书目》,官私互补,“益加裒集,详为注释”(86)吴骞:《愚谷文存》卷4《重校千顷堂书目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完成了《艺文志》稿本。近人姚名达评价此稿:“据所见所藏而备列之,最为征实。其分类亦多创例……书目卷数之外,更注撰人略历,较其他各志,特为详明。”(8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明史》自王鸿绪删定至武英殿刊印,《艺文志》多本于黄氏之稿。
四、勘误订谬:藏书家校订《明史》初稿
《明史》稿拟就后,馆臣为保证史稿质量,还要对其进行订补修正,馆内外学者参与《纪》《志》《表》《传》稿本的审核校订,其中有不少人就是藏书家。
馆内学者如汤斌,除了编纂大量史稿外,还陆续删改“《天文志》九卷,《历志》十二卷,列传三十五卷”,后改任职地方,将“改定志传缮写成册,付史馆备诸臣参订”(88)汤斌:《汤子遗书》卷2《题〈明史事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熊赐履为清初著名藏书家,收书“十万卷有奇”(89)孔继涵:《熊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24-525页。。熊氏后为《明史》监修,亲自着手修改史稿,自称“悉心刊订,删芜补佚,黜赝祛浮。袭陋者必择焉加详,传疑者宁存而不论”(90)熊赐履:《澡修堂集》卷2《进呈〈明史〉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0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02-503页。。总裁王鸿绪也是藏书家,其为《明史》修订贡献颇多,曾“访远近藏书家,得宋元明诸儒经解百余种”(91)张伯行:《正谊堂续集》卷7《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加七级王公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杨椿说:“王公乃取徐公旧志《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删改之,其他俱仍其旧;表则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惟《诸王表》与之同……删改徐公《本纪》,不浃旬而十六朝《本纪》悉具。”(92)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页。王氏“删繁就简,正谬定讹”,于《明史》殿本定稿多有功劳(93)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燕京学报》,1939年第25期。。
在野学者如黄宗羲和梅文鼎先后删改《历志》,黄氏在《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中讨论《历志》删改和增表问题,其云:“承寄《历志》,传监修、总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删定……某意欲将作表之法,载于志中,使推者不必见表,而自能成表,则尤为尽善也。”(94)黄宗羲:《南雷诗文集》书类《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黄宗羲全集》第19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6-187页。继黄氏之后,著名藏书家、天文学家梅文鼎亦参与《历志》的订补,他在《明史历志拟稿》中提到:“诸君子各有增定,最后以属山阴黄梨洲先生宗羲。岁己巳(1689),鼎在都门,昆山以志稿见属,谨摘讹舛五十余处,粘签俟酌……于是主一(黄百家)方受局中诸位之请,而以《授时》表缺,商之于余,余出所携《历草》《通轨》补之。”(95)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之《明史历志拟稿三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39-40页。与此同时,总裁陈廷敬等还曾延请海宁藏书家朱嘉征之子朱尔迈和藏书家许汝霖往京师勘定史稿(96)南炳文:《“迈注”之“迈”何许人也——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研究之一》,《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此外,福建文士林佶有藏书楼朴学斋,自称“购求儒先集录,毋虑数千卷”(97)林佶:《朴学斋文稿》之《上御史某公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6页。。林氏经王鸿绪聘请,与万斯同“商订编辑”,协助修订稿本(98)(乾隆)《福州府志》卷60《人物·文苑》,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154页。。
从书籍的进献、借予到个人亲身参与史稿撰写,再到稿本的讨论修订,藏书家切实参与其中。虽然这些藏书家在身份和自我定位上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均以自己的丰富藏书和精邃学问为《明史》最终成书贡献良多。
五、结语
藏书家作为身具多重身份的社会精英,自康熙朝下诏纂修《明史》伊始,参与了随后成书的整个过程,为《明史》最终面世充任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赵翼在论述历代正史之良莠时,尤为推崇《明史》:“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99)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721页。《明史》成书之完备与部分学术素养高超的藏书家之贡献是分不开的,清初藏书家多是集才、学、识于一身的优秀学者,如黄宗羲、李清、毛奇龄、徐乾学和汤斌等,不仅是闻名的藏书家,还以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能臣著称于世,是以《明史》之卓著,与藏书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从清代学术发展史看,藏书家搜罗、利用大量明代官私文献草写《明史》稿本,进而补遗和校订,正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重要一步,为乾嘉学术的最终成型做了准备。同时,《明史》正式纂修之前施行的征书方法和准则,以及通过《明史》纂修“把对明代历史的解释权收归官方”(100)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都为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时的征书、编书活动所承袭,对后者有着重大的借鉴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透过清初藏书家与官修《明史》互动的探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普通文人在这一修史过程中如何寻求保存自我、易代之际如何主动进行自我调适的景况,展现其在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而且可以进一步窥见在清初官方文化政策更迭这一大背景下,文人如何参与国家文化活动以及这一特定时期的学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