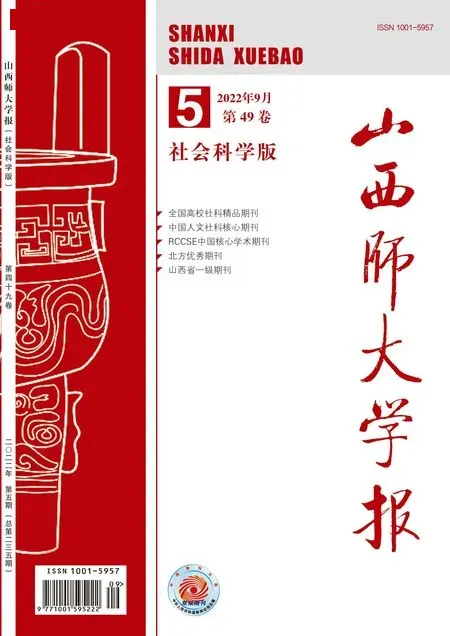文化传统与国家形构
——从《收刀入鞘:武士阶层与近世日本的缔造》谈起
李钧鹏, 王东猛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武汉 430079)
一、引言
精神气质与资本主义、文化传统和国家形构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基于理性化视角,提出“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只如此,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177页。这一著名论断后,社会学界就近现代国家的传统根源展开了持续的讨论。(2)[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日裔美籍社会学家池上英子(Eiko Ikegami)的代表作《收刀入鞘:武士阶层与近世日本的缔造》(3)中文版由王莹译出,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TheTamingoftheSamurai:HonorificIndividualismandtheMakingofModernJapan,下文简称《收刀入鞘》)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中,日本通常被当作检验以解释欧洲经验为目的的理论模型的重要个案。例如,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以现代化到来之前的农业商品化程度以及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为分析主线,展示通向民主世界的三条道路时,日本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之一。在摩尔看来,明治维新之后,前现代日本由农业转向资本主义式生产与经营,商人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农业秩序,而且成功压制并扭转了农民的不满,以此阻止了农民革命的爆发,而日本政治和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原则的适应性虽然帮助日本避免了以革命方式进入现代历史阶段,却最终陷入了法西斯主义和战败的泥沼。(4)[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34—322页。通过对日本历史的分析,摩尔检视了经过自上而下保守革命的法西斯主义道路。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关于日本德川幕府与欧洲封建主义的比较分析,不仅没有注意到德川国家统一而又地方分权的“新封建主义”国家结构的特殊性,而且几乎完全忽视了武士名誉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5)[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9—344页。在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那里,日本更是被降格为解释早期现代亚洲国家崩溃起因的例外案例,进而证明其“人口/社会结构模型”的理论解释力。(6)[美]杰克·A.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章延杰、黄立志、章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8—400页。相对于这些将日本经验置于西方理论模式的次要地位的比较历史研究,《收刀入鞘》采取了一条另类别致的分析路径。池上英子从广泛的比较视野出发,聚焦于日本这一单独案例,关注国家形成的文化维度,考察了在日本从中世封建社会转型到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过程中,武士的名誉文化与国家建设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7)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5,13.这本著作的独特贡献在于,池上英子基于名誉文化的差异、武士风格的区别、“封建主义”类型的差别以及中日儒教思想的不同影响等诸多比较维度,通过剖析日本社会变迁的本土经验,发展出独特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更加准确地理解日本经验所含有的比较意义”(8)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3.,这一比较历史分析路径超越了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日本研究,既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固化思维,又促进了比较历史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对话。正如池上英子本人所说,她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学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尝试把非西方的案例带入到社会学实践这种更为理论化的基础中来,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讨论与交流,开阔西方学者的非西方视野”;另一方面则是“公共领域、公共性以及个人主义概念的理论化”。(9)郭台辉、李钧鹏:《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93页。
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进入到一个更为多元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阶段。与之相对应,一些历史社会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中静态的、化约的结构主义思维做出批评后开始强调文化的自主性和社会科学的建构性,在研究议题和分析视角上呈现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态势。1983—1989年,就读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池上英子恰好处于这一学术思潮的风口并深受影响,而其导师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在对奴隶制性质的比较研究中将文化类型与历史深度相结合的分析路径(10)Orlando Patterson,Slavery and Social Death: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更是启发了《收刀入鞘》的创作思路。池上英子没有踯躅于结构主义分析的窠臼,而是选择深入分析日本文化的内在结构,展现了武士名誉文化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冲突与并存的相互关系,同时,她也关注社会过程、文化意义、象征符号、意识形态、意外后果、历史偶然性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如果说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是结构分析流派的代表人物(11)[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6页。,那么,池上英子基本可以归为文化分析流派。
下文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进入《收刀入鞘》文本的核心内容,分析垄断暴力的日本武士精英阶级的文化变迁;其次,在此基础上,展示“名誉型个人主义”(honorable individualism)这一区别于“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的独特概念的构建,并展开讨论不同于比较历史研究的宏观因果分析路径,《收刀入鞘》别有心裁地关注到名誉文化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将视野转向当代中国,结合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探讨基于非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的比较历史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国家建构独特性的意义。
二、武士阶级、暴力独占与名誉文化
武士阶级,以职业化的军事技能、专业战士的自我认同和独特的社会等级组织为核心特征,作为一个政治行为体,是日本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收刀入鞘》中,池上英子探讨了这个垄断暴力、崇尚名誉的精英阶级是如何发展、崛起的,在之后几个世纪的国家建构中又是如何被驯服的社会过程。同样,在西方武士宫廷化的过程中,武士阶层也逐渐丧失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地位,由武士沦为廷臣。(12)[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495—507页。但日本武士与欧洲武士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社会差异,欧洲封建时期的武士更多指的是骑士阶级,这种骑士身份与贵族特权是重叠的,因而没有动力去颠覆现存的封建贵族权力体系。而日本武士则与依附于天皇朝廷的宫廷贵族完全不同,是拥有土地的军事阶级,他们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范畴,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简而言之,武士获得政治权力可被视作一个全新社会阶级出现了,并且反过来还催生了一系列独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化以及文化的变迁。”(13)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7.另外,武士阶级的崛起与其能有效地使用军事技术和暴力能力密切相关。在日本早期农业社会,由于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并出于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创建了军事和社会组织以及结合社会经济条件变迁的背景,武士阶级得以控制农业,并能够强行从农业社会中获取利益。然而,对暴力手段的集中与独占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控制在武士手中,而是与国家形成过程密切交织。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国家的社会发生时发现,“独占机制形成的过程要区分为两个阶段:一为自由竞争的阶段,或者说淘汰阶段,其间机遇积聚在越来越少的人的手中,最后落入一人手中,这是独占形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对业已集中化和独占化的机遇的支配权趋向于从个别人手中逐渐过渡至越来越多的人的手中,最后变为作为整体的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的职能,这是一个由相对‘私人’独占走向‘公共’独占的阶段”。(14)[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361页。其中,武士阶级在第二个阶段对暴力的垄断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后期阶段任何政权独占的关键是体力暴力和军事暴力实施权的独占,这使人得以在广大地区建立牢固稳定的社会机构。”(15)[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395页。
对于武士来说,暴力不仅仅是他们扩展势力的手段,更是维持自身文化正当性的工具。随着武士独占暴力而崛起,这个阶级的名誉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风格。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历来都是学者的好奇关注点,其中影响最大的研究当属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与西方社会的“罪感文化”不同,这种文化的强制力来源于外部社会,服从于社会规范和义务。“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16)[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2页。这种强调外在的/内在的文化二分法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池上英子就认为本尼迪克特假定了罪感文化相对于耻感文化的道德优越性,可能完全忽视了日本名誉文化的多面性和内在的动态变化,以及社会化的自我意识与主观化的自我意识之间的接近性,因此,她反对文化类型区分的简化思维,提议从日本武士的名誉文化入手,来展现个体身份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资源。(17)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72—378.在池上英子看来,日本武士名誉文化的变迁过程,是更好地理解和审视日本社会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追求个性与服从规范、竞争与协作之间对立和紧张关系的关键。名誉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复合体,与社会评价和权力结构息息相关。当日本从中世转型至近世,武士也相应地经历了从半自治的军事地主到被驯服的官僚的文化再形成过程。中世的日本武士拥有土地所有权,视身体暴力和军事表现为维护名誉的核心手段;到了德川时期,武士阶级通过集体垄断暴力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却被剥夺了自治的经济基础,被整合进组织化、制度化和等级化的国家政治结构之中,这导致武士的集体认同发生了转变。武士名誉文化的特殊性质与近世日本的国家形成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其好战的传统精神气质在和平的德川体制中日益被驯化和磨平,却从未被完全抹去。“在结构上把武士阶级纳入新的国家体系,这并不会自动产生‘被驯服的武士’。武士名誉准则中新内容的产生,与其说是德川国家有意识地策划的结果,不如说是武士抗争、国家与武士之间谈判、反复协商的副产品。”(18)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2.在这段国家转型时期,武士名誉与社会秩序的部分融合在带来严重的内心冲突的同时,引发了一种矛盾的共存状态——对名誉化个性的向往与对名誉化服从的自制。需要强调的是,池上英子在把日本武士阶级的名誉文化看作国家形成的文化维度来加以考察时,关注到名誉文化、社会结构和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相互关系,这与埃利亚斯关于文明的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于“结构二重性”的阐述有异曲同工之妙。(19)[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469—485页;[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6页。
三、名誉型个人主义与国家形构的关系
武士阶级的文化变迁,带有两个主要的文化主题标志:控制和变化。诚如池上英子所言:“控制与变化,武士文化中的这两个主题,如双胞胎一般,相互共存、相互结合,是理解日本文化传统的重要钥匙。”(20)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30.其中,控制包含两种构成元素,在个人层面克制短期欲望以实现长期目标,在集体层面将个人冲动与社会目标协调一致;变化则以武士的名誉和自尊信念为基础,凸显其强烈的自我意识。联系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可以更明晰地审视武士文化转型、重组的独特轨迹。在日本中世,武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地位范畴出现,发展出一种强烈竞争的、黩武好战的、自我夸耀的名誉文化;到了战国时代,武士由松散自治的状态向等级化的、组织化的家臣体系过渡,名誉表现为军事能力方面;德川国家时期,武士阶级经过文化传统的连续、变化和重组过程,出现了文化复合体困境:既渴望竞争进取的个性化,又期待组织有序的服从性。即使是德川国家体制,也未能将武士完全规训成科层制中被动的官僚,这源于武士名誉文化的深层动力——名誉型个人主义,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个人主义模式。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内含着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预设。C. B. 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把17世纪的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和财产权理论联系起来发现,“个人主义的占有性可以在它的个人概念中找到,这种概念认为个人实质上是自己人身或能力的所有权人,为此他对社会无所亏欠。个人既不被视为一个道德整体,也不被视为更大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被视为他自己的所有人”。(21)[加]C. 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怀着这种个人主义世界观来观察日本社会,观察者很容易武断地得出现代日本缺乏一个清晰的个人主义形式的结论。类似这种戴着西方有色眼镜在日本社会寻找个人主义的方式,往往预设了某些独特的文化特质只能在西方国家土壤中生根发芽,而忽视了不同社会可以以不同方式表达个性的可能性。为解释日本武士文化的变化主题和进取精神,池上英子创造了“名誉型个人主义”的概念,这种个人主义形式为日本国家转型提供了一个变革机制。武士阶级的名誉型个人主义没有像西方个人主义那般在普世哲学的支撑下发展成一个连贯一致的思维范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风格,随着国家形构而缓慢变迁。名誉型个人主义早在中世武士社会就已出现,这与当时武士重视名誉权力的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个性联系在一起。另外,由于获取名誉的权力只有加入军事组织才能实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世武士,名誉型个人主义是一种与社会范畴共生共存的情感”(22)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55.。这种个人主义内含着变革的动力,一旦与社会组织目标有效连接,便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结构转型。虽然德川国家的家臣官僚制剥夺了武士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其个人名誉观也失去了中心地位,被驯化、降格至忠诚品格之后,但武士对体制规训的抵抗和对“一分”(23)“一分”是一种暗示了个人名誉觉醒意识的观念,表明在逆境中存在着与个人自尊和骄傲相联系的名誉情感。参见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56—357.精神的珍视始终存在,“在德川日本,名誉型个人主义以一种强烈的情感和强大的伦理推动力的形式,依旧存在于文化之中”(24)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58.。在日本近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精英阶级的名誉型个人主义也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新环境,从而持续不断地发展演变。概言之,在武士统治时期,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以往研究者在解释社会结构变迁时,或寻找造成案例差异或相似的结构性原因,或关注文化、情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或强调地理环境、重大转折性事件的重要性,这些均预设了因果关系的存在。在审视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形成与武士转型之间的关系后,池上英子发现结构变迁并没有以线性的因果关系方式自动产生一系列的文化后果,恰恰相反,武士阶级在经济、政治层面的发展与文化变迁在长时间的社会过程中紧密相连,而那些将社会的不同层面分开并试图扯上因果关系的分析应该引起怀疑。(25)Eiko Ikegami,The Taming of the Samurai: Honorif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31—332,377.不同于比较历史研究的宏观因果分析路径,《收刀入鞘》集中关注武士名誉文化与国家形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纵观日本从中世到近世国家形成的不同形态,武士阶级名誉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政治结构的变革。日益兴起的中央政权,驯服武士的政治过程,逐步改变了武士的自治传统和军事自豪感,产生了一种有利于协调个人主义精神与社会组织目标的心理倾向。然而,植根于中世武士文化的名誉型个人主义从未完全屈服于政权体制,这些文化资源构成了武士争取独立的积极动力,推动了制度变革和国家转型。池上英子在分析日本文化的矛盾性质时,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始终紧密交织在一起,没有截然分别的因和果,这种互为因果的过程分析彰显了一种独特的分析路径。
四、 面向中国的比较历史研究
历史社会学中主流的国家形成理论和比较历史研究均基于欧洲经验,亚洲国家不是被作为检验西方理论的补充案例引入比较历史分析,就是被长期视而不见。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分析路径,池上英子选择适宜的比较方法,通过对日本近世国家形构的考察和武士名誉文化变迁的探究,发展出独特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资源,提供了一个充满多样性的世界图景。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在中国学界的发展态势令人瞩目。(26)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2015年第1期;成伯清:《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江海学刊》2015年第5期;周飞舟:《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赵鼎新:《时间、时间性与智慧: 历史社会学的真谛》,《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1期;郭台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但是,在比较历史研究领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基于中国历史经验来讨论国家形构独特性的努力还是欠缺。赵鼎新的著作《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TheConfucian-LegalistState:ANewTheoryofChineseHistory,下文简称《儒法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此书甫一出版,就引起诸多关注,吸引不少国内外学者参与讨论。(27)Zhao, Dingxin,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王正绪:《古代中国大历史的社会科学解释》,《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郦菁:《历史比较视野中的国家建构——找回结构、多元性并兼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殷之光:《“大一统”格局与中国两种延续性背后的普遍主义——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赵鼎新:《哲学、历史和方法——我的回应》,《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魏海涛:《社会科学中的机制解释——兼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6期;迈克尔·曼、金世杰、约翰·霍尔、乔纳森·赫恩、理查德·拉赫曼、乔治·劳森、威廉·H·休厄尔、王国斌:《再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巨桐、孙金、韩坤、张帆、刘伟、周盼译,《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赵鼎新:《〈儒法国家〉与基于理想类型集的理论构建》,巨桐译,《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通过修正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即IEMP权力模型)理论框架(28)[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从开端到1760年的权力史》,刘北城、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赵鼎新宏观考察了自周已降约三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回答了中国何以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这一关键问题。对于中国政治的大一统传统,赵鼎新认为其形成的关键时期在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后期,也就是“全民战争时代”。出于战争驱动型的军事竞争和汲取资源需要,秦王吸收了法家思想,打败了竞争对手,实现对整个中国的控制。到了西汉,统治者出于建立道德合法性来巩固统治的目的,开始将儒家的道德伦理与国家的政权结构相结合,自此中国的“儒法国家”(confucian-legalist state)政治体制基本成型。儒法国家,“即一种将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融为一体、军事力量受到严格控制、经济力量被边缘化的统治体系”,在之后的历史变迁中,“这种体制具有强大的弹性和适应性,以至于历经无数挑战它仍能顽强地存续下去,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29)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4页。即使儒法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经在革命浪潮中覆灭,儒教的政治社会功能也近乎消失殆尽,但儒法思想的文化传统和“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based legitimacy)的政治传统在今日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依然有迹可循。(30)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1页。通过引入“例证性比较”(illustrative comparisons)的研究方法,并采纳“宏观结构观照下以机制为基础的研究”(macrostrcuture informed,mechanism-based study)的分析策略,赵鼎新重新检视了帝制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结构的发展过程,由此提出新的历史变迁理论:竞争与竞争结果的制度化的辩证性互动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31)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徐峰、巨桐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7、29、30页。一言以蔽之,立足于中国国家形构的独特历史经验,《儒法国家》在尝试新的研究进路的同时,不仅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资源,更展现了将中国置于比较历史分析的中心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对日本武士名誉文化与国家形构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还是对中国大一统政治秩序背后历史逻辑的探究,《收刀入鞘》和《儒法国家》均强调国家构建过程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脉络的联系。更难为可贵的是,两位作者有意识地与西方主流理论保持距离,立足于东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从广泛的比较视野出发,不仅发展出独特的分析路径和理论资源,更展现了国家形构的多元路径。当然,从非西方视角反思西方国家形成模式的研究者还有他人,土耳其裔美国学者凯伦·巴基(Karen Barkey)就把社会网络分析充分运用到奥斯曼帝国研究,并收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手史料来分析帝国的政权构建与社会抗争。(32)Karen Barkey,Empire of Difference:The Ottom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面向当代社会,在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的背景下,这些试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关注非西方国家历史经验、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的比较历史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国家形构之间的关联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文化偏至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