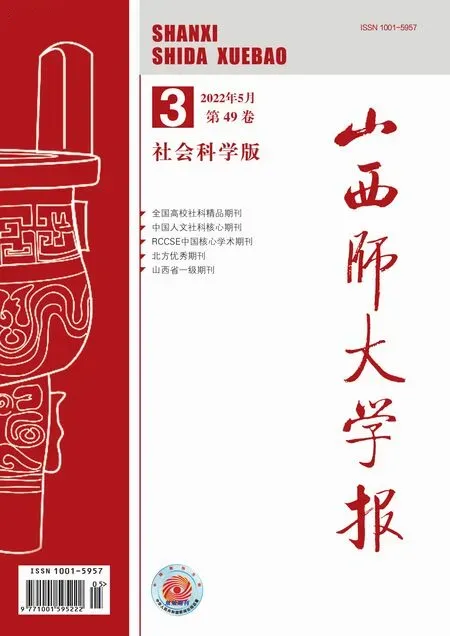文学阐释学的基本形态
傅 其 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207)
文学阐释学作为阐释学的重要分支,历史悠久,纷繁复杂,形态多样。它作为对文本理解与解释的艺术,对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演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参与到文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影响到文学批评的进程,涉及文学史的书写。其基本形态可以区别为文学注释学、普遍阐释学、现象学阐释学、批判阐释学、后现代阐释学等类型,透视出文学阐释学的多元性。这些形态既具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也具有共时存在的当代性。梳理这些基本形态,可以探测文学阐释学的已有基础与未来新的可能性。
一、文学注释学
文学注释学是文学阐释学的原初形态,也是文学阐释学的基础性形态,可以称之为语文学或者语义学模式。它作为文史哲的经典性阐释学形态,在当代仍然具有生机与活力。它主要关注文本的注解与注疏,是集中于语义学的阐释学。塔尔斯基指出:“语义学是一门严肃而谦逊的学科,它没有那种要成为专治人类一切想象的或真实的疾病的万能良药的抱负。在语义学中你不能为蛀牙或者壮丽的梦幻或者阶级斗争找到任何药方,语义学也不是一种要证明除你和你的朋友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说胡话的装置。”(1)[美]A·塔尔斯基:《语义性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载[美]A·P·马蒂尼奇编:《语言哲学》,牟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7页。这门严肃而谦虚的学科奠定了文学注释学的基础。阐释学在中西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得名于传递神的信息的神使赫尔墨斯(Hermes)。阐释者对信息加以解释并进行传达,这种解释与传达实质上是对语言文本的注解。在中国,文学注释学体现为对经典神圣符号信息的注释,其历史亦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传说中伏羲对河图洛书的符号理解是中国文学阐释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文学注释学所阐释的对象是具有神秘性的符号信息,主要是经典性的语言符号。保罗·利科指出,阐释学企图研究的第一个领域无疑“是语言,尤其是文字语言”(2)[法]保罗·利科尔:《诠释学的任务》,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10页。。在他看来,这种特殊阐释学包括关于经典文本(主要是希腊-拉丁古代经典)的古典语文学和关于圣经文本的注释学。文学注释学不仅仅涉及西方的传统,而且关注非西方的经典语言文本对象,尤其关注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实践成果的中国文学注释学。日常语言作为人类生活与社会交流的媒介,在人们之间能够被理解,而且能够进行信息传递,在某种意义上不需要阐释。但是在人类社会早期,随着文字符号的出现,语言与符号的结合超越了时间的当下性,文字符号化的语言获得了其存在的独立性、超越历史性与现实性。原初语言信息的意义日益变得陌生,难以理解,阐释成为必然。譬如《周易》中由阴爻与阳爻交相叠加的符号以及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些符号代表何物,传递何种意义,人们难以准确地把握。在人类文明史上,我们不难找到不同民族类似的早期经典符号文本。这些文本语言符号数量有限,时间久远,内涵丰富,譬如“元亨利贞”之类的语词。
文学注释学的目标是解释文本语言的意义。注释者通过音形义与语法规则、历史文化语境的辨析弄清楚词语的内涵、句子的意义、语篇的意图,因此主要涉及语言学的能指与所指。也就是说,要把文本的原初意义弄清楚,表达明白,即敞开隐蔽的或者不理解的意义。范文澜对《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注释如下:“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故篇后承以《征圣》《宗经》二篇,意旨甚明,与空言文以载道者殊途。”(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页。这种从文本语词到语篇意旨的阐明,是文学注释学的根本任务,也是文学阐释学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语义学的阐释基础,文学理解与解释是不可能进行的。在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中,对原义的追求是根本旨趣,这包含着阐释者对文本意义的遵从与顺应,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是由文本决定的。这是对传统、圣贤意旨的言说与传达,阐释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阐释者的一切能力、理性智慧与方法路径都聚焦于经典原义的显明与内在连贯。
二、普遍阐释学
文学注释学主要依附于语言文本的阐明,重在文学注释实践,较少在理论本身上加以建构。这主要是因为它较为原初,也较为基础,似乎是文学阐释学的自明之事。但是这种形态奠定了所有文学阐释学的基础,可以说,现代的文学阐释学形态都与之联系。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注释学属于特殊阐释学或者局部阐释学,而以阿斯特(Friedrich Ast)、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阐释学属于普遍阐释学。我认为把注释学作为特殊阐释学是不确切的,因为它本身在文学阐释学的范围之内。之所以提出普遍阐释学,是针对更为普遍的知识学尤其是精神科学或者哲学而言的。如果用赫勒(Agnes Heller)的历史意识概念来理解,文学的普遍阐释学是基于现代普遍性的历史意识的阐释学,具有鲜明的宏大叙事的现代性特征。
19世纪是普遍阐释学的黄金时代。德国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提出阐释学的普遍性诉求与普遍性原则,我们可以将其归属为浪漫主义阐释学。阿斯特在1808年出版了《语法学、阐释学和批评学基础》(Grundlinie der Grammatik, Hermeneutik und Kritik)一书,此书提出以精神、生命等概念奠定阐释学的普遍性基础,建立阐释学的艺术系统规则。他认为:“一切行动都有从其自己本质而来的它自己的方式和方法;每一生命行动都有它自己的原则,如果没有原则的指导,它将使自己失落在不定的方向之中。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而在这世界中,没有熟悉的精神(Genius)在指导我们的不确切的步骤或给予我们不定的努力以方向时,这些原则将成为最迫切需要的。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构造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将——虽然只是逐渐地和困难地——领悟陌生现象,理解陌生精神的世界和推测它们的深层意义。”(6)[德]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页。这表明,阿斯特试图构造基本原则,以通达对人类行动与深层意义的理解,领悟陌生精神世界及其意义。这不再囿于语言文本与母语文本,而是涉及人类普遍的行为与现象及其深层意义的理解。为了确立这种有效性原则,阿斯特构建了精神的统一性与普遍性,因为精神建立“更高的无限的统一,一切生命的核心,这不是为任何边缘所束缚的”,“所有生命都是精神,没有精神就没有生命,没有存在,甚至没有感官世界”(7)[德]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页。。作为语文学的文学阐释学就不再属于特殊阐释学的领域,而是建立了语文学与精神、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意义。语文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使精神脱离短暂的偶然的和主观的东西,并授予那种对于更高的和纯粹的人类,对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是本质的原始性和普遍性,以致他可以理解真、善、美的一切形式和表现,即使那是陌生的,通过转换使它进入自己的本性,而与原始的纯粹的精神再度统一,这种精神只是由于他的时代、教育和环境的限制他才离开了的”(8)[德]弗里德里希·阿斯特:《诠释学》,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这种关于文学阐释学的表述无疑是激动人心的,对纯粹性、普遍性与统一性的凸显包含着浪漫主义想象的无限性与人类精神的包容性。语言成为精神的表现,对语言的理解具体化为对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的理解。阿斯特认为,对古代作者的理解有三种:一是历史的理解,涉及作品的内容;二是语法的理解,关涉作品的形式或语言和讲话方式;三是精神的理解,涉及个别作者和古代整体的精神。只有精神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因为它把历史的理解和语法的理解融合为一种核心的生命,把内容与形式融合为精神性的生命。譬如,品达的作品在内容、形式和精神层面体现出一位真正的古代诗人向我们揭示了一切古代的精神。他歌颂的体育竞赛和纯洁的表现形式、韵律,在我们心中唤起了真正古典世界的光荣形象,揭示出人不仅可以在内心培养高贵的情感和值得赞美的情感,而且能够乐于为祖国及其神灵做出伟大的英雄业绩。品达的诗歌以独特的方式与整个古典精神建立了普遍的联系。阿斯特探索了文学阐释学的具体程序,不仅确立了整体与个别的循环关系,而且明确提出解释的三要素即文字、意义、精神。在他看来,文字的阐释学就是对个别的语词和内容的解释,意义的阐释学是对段落关系中意味性的介绍,精神的阐释学是对文本整体性的更高关系的解释,也就是对于处于和谐统一之中的文字和意义的完美无缺的内涵的解释,对作品的真正生命的解释。如果说文学注释学主要集中于文字和意义层面,那么阿斯特的普遍阐释学则是基于精神生命的文学阐释学,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文学阐释学。
施莱尔马赫对普遍阐释学的贡献在于更为系统地确立普遍阐释学的方法论与规范性原则,创建了基于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上的文学阐释学,有意识地超越特殊阐释学。他明确提出普遍阐释学的诸原理,强调理解的精确性的东西才属于阐释学,阐释学必须立足于正确使用注释。对他来说,历史诠释学的任务是严格的理解,就是基于文本原义的整体性理解,因此解释的普遍性原则是关注的焦点,这些原则力图避免误解或肤浅的理解,也避免读者的附加性理解。在一系列避免理解困境的普遍阐释学原则中,施莱尔马赫强调语言用法原则,要培养对比喻理解的能力,要重视词汇学历史,要求阐释者努力成为文本所期待的直接读者。这些原则的建立确立了作为普遍阐释学的艺术:“诠释学的艺术就是知道在何处一个应当给另一个让路。”(9)[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页。这表明,施莱尔马赫试图建构作为语言艺术的普遍阐释学。他把阐释学与修辞学、辩证法密切联系起来,因为言语是思想共同性的媒介,所以“修辞学和阐释学融于一体,且与辩证法有着相同的关系”。(10)Schleiermacher,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Andrew Bowie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7.他通过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的程序性规则的系统建立,提出领会作品统一性以及写作结构主要特征的普遍视野(general overview),这无疑是作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普遍阐释学的重要推进。语言解释基于两种规范:第一,在既定表达中的一切东西只能通过语言域(language area)加以确定,这种语言域对于作者和他最初的接受者是相同的,因而语境对于表达的确定极为重要;第二,每一个在既定点的词语意义必须根据其所属的整体加以确定。这些规范确保了语法解释的确定性意义。心理解释是确定文本与作者的个体性、人格、环境的复杂关系从而理解文本的风格、观念和思想的原则。对施莱尔马赫来说,心理解释的整个程序始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两种方法:猜测与比较,“猜测法就是把自己转变成他人,尽力直接地去理解个体性元素。比较法先是把要理解的人设想为世界性的对象,然后通过与其他相同世界中的对象的权衡比较,从而找到个体性维度。就对人的识别来说,前者是女人的优势,后者是男人的优势”(11)Schleiermacher, 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Andrew Bowie 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92—93.。通过语法解释原则和心理解释原则,一个文本的“精确理解”得以可能。
可以说,施莱尔马赫达到了比阿斯特更为普遍的阐释学的科学高度,这也是哲学与精神的高度。他的目标是建立普遍阐释学的科学原则。在他看来,人们对话语与文本的兴趣可以区别为历史兴趣、艺术兴趣或鉴赏兴趣和思辨兴趣。第三种兴趣即思辨兴趣才是普遍阐释学的任务,因为这源自人的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涉及科学兴趣和宗教兴趣。他认为:“从最高级的科学兴趣出发,我们可以认识人是怎样在教化中和使用语言中而得到发展的。同样,从最高级的科学兴趣,我们可以理解人是作为理念的人性而来的现象。这两者最紧密地被联系在一起,因为语言在人的发展中一直指导着人和伴随着人。——如果说鉴赏兴趣深化了任务,那么这一任务只有通过科学兴趣才能被彻底完成。”(12)[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阐释学演讲》,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69—70页。可以看出,施莱尔马赫把语文学提升到科学阐释学或者宗教阐释学的层面,也提升到哲学人类学或者普遍人性层面,这种普遍性特征与阿斯特具有同样的目的,使文学阐释学获得了哲学的普遍性的意义。按照狄尔泰的理解,施莱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是以文学阐释学为对象取得的:“在对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创作过程的生动直观中,施莱尔马赫认识到了一种过程的条件,这另一过程是由文字符号理解一部整体作品并由此进而理解其作者的目的和精神气质。”(13)[德]威尔海姆·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7页。但是,这种普遍阐释学仍然有限度,施莱尔马赫清晰地认识到阐释规则适用于抒情诗的困难,“抒情诗人的思想运动是完全自由的,而读者始终不是抒情诗性的读者,因而他不能从诗人自己的意识来重建抒情诗。这里建立的阐释学规范立足于思想连续链条的设想,因而不能直接运用于抒情诗,因为在抒情诗这里无限制性是主导的”(14)Schleiermacher,Hermeneutics and Criticism,Andrew Bowie 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64.。
狄尔泰进一步在包括文学、诗学、音乐、历史、哲学等人类精神科学意义上展开普遍阐释学的理论建构,这是立足于人的本性、历史理性以及“存在的总体性”(15)[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童奇志、王海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7页。,继而从认识论角度奠定精神科学这棵知识之树的可靠性根基。在狄尔泰看来,理解是精神科学的内在合法性基础,因为只有通过理解过程,生命才得到深刻的说明。他指出:“人类之所以变成了精神科学研究的主题,完全是因为存在着这种介入经验、表达和理解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精神科学就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了,而这种关系则为它们提供它们所特有的标准。只有当一个学科的主题,变成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建立在生命、表达和理解之间的联系之上的程序而加以理解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学科才会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16)[德]威廉·狄尔泰:《历史的意义》,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7页。就阐释学而言,狄尔泰所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个别文本的理解如何获得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有效性或者客观性,而这种普遍有效性是生命的意义概念。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总是以他人的理解为前提,语文学与历史科学就是把对个别事物的重新理解提升到客观性高度。这种历史意识使现代人有可能重新把握人类的整个过去:“他们超出自己时代的一切界限而极目于已经过去了的文化;他们吸取了这种过去文化的力量并追享着它们的魅力;极大的幸福增长就这样对他们产生出来。如果系统的精神科学由这种对个别物的客观把握中推出普遍的合规则的关系和包罗万象的联系,那么理解(verstaendnis)和阐释(Auslegung)的过程对于这种精神科学就是总基础。”(17)[德]威尔海姆·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75页。在阐释学的普遍有效性原则中,文学注释学或者语文学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狄尔泰认为,文学对理解精神生活意义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语言中,人的内在性才找到其完全的、无所不包的和客观可理解的表达,所以他认为阐释学的核心在于对著作中的人类此在留存物的阐释。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探讨生命最大奥秘的方式。狄尔泰需要奠定整个精神科学的普遍有效性,而理解与解释就是其基本方法。理解和解释作为普遍有效性方法汇聚了各种功能,包含了所有精神科学的真理,切入生命本身,为人们打开了世界。狄尔泰把普遍有效性命题融入其生命哲学之中,也包括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与阐释的有效性。在他看来,作品成为精神性生命的表达,理解伟大作品就成为可能:“由于在伟大的作品中,一种精神性东西脱离了其创作者——诗人、艺术家和作家,于是,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这里欺骗停止了。……作品自身是真实的、稳定的、可见的和持续的,所以,对它的艺术上有效的和确定的理解将成为可能。……生命似乎在一个观察、反省和理论上无法进入的深处袒露自身。”(18)[德]威尔海姆·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95页。狄尔泰虽然洞察到体验与理解的不确定性,但是借助于普遍有效性与客体精神的把握,在充分吸取施莱尔马赫的普遍阐释学的基础上,把阐释学定位于共同性与确定性的理解与阐释,赋予了普遍阐释学更宽广的历史时代性和社会交往性:“从我们呱呱坠地,我们就从这个客观精神世界获取营养。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中介,通过它我们才得以理解他人及其生命表现。”(19)[德]威尔海姆·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97页。因此,虽然文学艺术作品是想象力的精神构建,显示出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奇迹,但是这种奇迹是心理活力的强有力的构想,“这种强有力的构想过程通过经过整合的形式和功能的统一体,展示人类的精神生活及其各种普遍法则”。(20)[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童奇志、王海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审美感受力也是按照精神的普遍法则发挥作用的。因此,对文学原义的理解与阐释是可能的,意义与生命的交往是可能的,阐释共同体是可以确立的,“理解过程可以达到最高程度的确定性”。(21)威廉·狄尔泰:《历史的意义》,艾彦、逸飞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44页。
狄尔泰通过对莱辛、歌德、诺瓦利斯、荷尔德林的文学创作的阐释,进一步奠定了基于生命哲学的文学阐释学的基础。在他看来,诗艺是生命的理解与表达,是作家借助于语言、想象和形式,建构在对生命的理解中的从日常生活状态提升到普遍有效性的自律整体性王国,从而为作品的生命意义的理解与解释提供了可能性。文学创作与接受都是基于对生命的理解。狄尔泰指出,诗艺作品把理解者置于自由境地,提高他的生存感,“它使他经历他本人所不能实现的渴望和生活的可能性从而使他得到满足。它让他打开眼界看到更高更强的世界。它在这种二次经历中让他的整个本质在一个与他相适应的、诸心理事件的过程中活动,从乐音、节奏、感官直观性所引起的喜悦直至按照诸事件同生活的整个宽度的关系对诸事件的最深刻的理解”。(22)[德]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4页。狄尔泰对生命理解的交往之可能性的把握,与其对莱辛的生命理想的理解是一致的。在他看来,莱辛的杰作《智者纳旦》表达了生命的最显著特征,就是自由的人形成共同体的可能性,个人相互接近“是通过思考——提问,答复,辩证地寻找相互理解,随后从相互理解中产生意见一致和友好这种持久的感情”。(23)[德]威廉·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9页。显然,尽管狄尔泰始终挑战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这种心灵共同体的设想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特征。事实上,狄尔泰也深刻地认识到,对于文学经验感受的非规则性,不可加以理性把握和语言阐释,“自从关于自然界的机械论观念崛起以来,文学一直保存着对自然界生命的伟大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神秘的,因而是无法加以说明的”。(24)[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童奇志、王海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254—255页。
当年在祖屋里玩耍的孩童们早已长大成人,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购置新居、结婚生子,有些人已有数年未回祖屋相聚了。如今,人去楼空的祖屋再不加以修缮,过几年也许就真的全塌了。俗语有云:树长千丈落叶归根,人行万里涅槃回乡。祖屋留在故乡,我们这一代的根才能继续留在故乡,才能给在外拼搏的游子留一个回乡的念想。
可见,普遍阐释学不同于文学注释学,它基于人的普遍本性,体现了哲学的普遍性追求与客观真理性。正如狄尔泰为精神科学所确定的科学内涵之一,“它们在囊括一切的逻辑体系内部都是普遍有效的”(25)[德]威廉·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童奇志、王海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6页。。也就是说,对文本的理解涉及对精神本质与生命本质的理解,归根结底是人的科学。普遍阐释学是基于现代哲学认识论、逻辑学与理性原则的阐释学形态,体现了普遍人性,具有浪漫主义和宏大叙事特征,形成了文学阐释的普遍价值维度。这种形态在当代阐释学及其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譬如美国学者赫什的《解释的有效性》,从意大利阐释学家贝蒂那里汲取普遍规则的思想养分,其中的“固定文本”“原义意义”“有效性”等概念仍然延续着普遍阐释学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模式,正如他本人所言,解释的关键在于“真正的知识”(26)E.D. 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205.,目的是挽救绝对真理。
三、现象学阐释学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在1983年的著作《文学理论导论》中把“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作为一章,这表明了文学阐释学在20世纪主要体现为现象学阐释学形态。事实上,现象学阐释学主要是在胡塞尔现象学基础上发展演变的阐释学,在德国与法国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等现象学哲学家为代表。现象学阐释学形成了不同于文学注释学、普遍阐释学的阐释学思想。如果说文学注释学主要局限于语文学领域,普遍阐释学建基于现代启蒙理性或者认识论、方法论,那么现象学阐释学则是提出本体论(ontology)或者存在论转向,以本体论阐释学为旨趣的文学阐释学形态。
海德格尔1927年的代表性著作《存在与时间》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探索存在与此在的阐释学命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境缘性是生存论结构之一,而它与理解本源性地关联着,这形成了境缘性与理解的意向性结构。这种结构构成了存在的基本样式:“境缘性向来就有其理解,即使境缘性抑制理解。理解总是带有境缘性的理解。既然我们把带有境缘性的理解解释为基本的生存论环节,那么这也表明这种现象被理解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样式。”(27)[德]马丁·海德格尔:《理解和解释》,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此在的存在状况从本体论来说就是理解的命题,所谓理解就是此在的展开状态,涉及整个在世存在。就生存论来说,理解包含着此在之能在的存在方式。这种对此在的能在性或者可能性的展开与筹划就是理解。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此在展开状态的理解是此在的日常存在方式。基于此,解释获得了新的含义。解释根植于此在的理解,成为理解的造就自身的活动,它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加以整理。海德格尔指出:“解释并非把某种‘含义’(Bedeutung)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东西上,并不是给它贴上某种价值,而是与那种世内照面的东西一起已经具有某种在世理解中展开的因缘关系,解释(Auslegung)无非是把这种因缘关系释放(herausgelegt)而已。”(28)[德]马丁·海德格尔:《理解和解释》,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在这种意义上,因缘整体性是解释的本质基础,这涉及解释的三种结构性条件:一是解释奠基在先有之中,作为理解的占有,解释活动有所理解地向着已经被理解了的因缘整体性去存在;二是解释奠基于先见之中,这种先见对先有的东西进行选择切割;三是解释奠基于先把握之中,解释包含着对某种把握方式的赞同或者认可。因此任何解释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29)[德]马丁·海德格尔:《理解和解释》,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同样,意义概念也不再是文本的含义或者作者的意图,而是具有存在论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此在才具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当世内在者随着此在之在一切被揭示即被理解,这个在者就具有意义。意义根植于此在的存在论状态,根植于解释者的理解。它是理解者的展开活动中可以明确说出的东西,是此在的一种生存论性质,而不是一种依附于在者、躲在在者后面或者作为中间领域漂浮在什么地方的属性。海德格尔对理解、解释与意义以及阐释学循环进行了新的理解,将其融入此在与存在的展开的结构之中,有意识地超越认识论,建构了存在阐释学的基础。尽管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嬗变,但是其对阐释学的基本设想,对此在的时间性、语言存在的把握,仍然是现象学存在论的。他的路径是利科所说的“阐释学嫁接于现象学”的捷路:“捷路是理解存在论(ontology of understanding)所取的路,它沿着海德格尔的方法进行。我之所以把这种理解存在论称之为捷路,是因为它与方法论的讨论截断关系,它直接把自身带到有限存在的存在论层次,以便在那里重新恢复理解,使之不再作为一种认识方式,而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30)[法]保罗·利科尔:《存在与诠释学》,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伽达默尔作为海德格尔的继承者,把阐释现象学置于当代哲学的核心地位,从而更新了传统文学阐释学或者经典阐释学,系统地建构了文学现象学阐释学,也称之为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不再是建立理解的艺术,不是提出一套规则体系或者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而是探究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也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他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Dasein)的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3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版序言》,[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页。他在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代阐释学的历史视野中讨论阐释学的诸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现象学阐释理论。
伽达默尔的代表性著作《真理与方法》首先对现代美学核心概念即审美经验、审美主体性进行批判,在批判中提出新的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这是具有阐释学意义的理解,也是本体论意义的理解。伽达默尔从现象学角度理解艺术,不注重康德、席勒视野中的审美经验,而是关注真理命题。这种真理不是一致性符合论的含义,而是海德格尔的作为去蔽的真理概念。同样,艺术作品不是形式主义者所主张的一个客观的自律对象,而是具有游戏性、表演性,是具有开放性的存在。这种艺术作品的本体论把游戏视为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这不是从创作者的立场也不是从接受者的立场获得的,它摆脱了康德和席勒的游戏的审美维度,因为游戏的本质不在游戏者而是在于游戏本身,是游戏的自我显现,这是潜在地为某人的自我显现,因此向他者显现这种方向性是艺术存在的构成性元素。这种向他者的开放性具有重要的阐释学意义。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是重建原文的作者意图,而是形成阐释者与阐释对象的对话,理解是面对传统对象进行的新的建构,是对存在的敞开,是此在历史性的创造性运动。他追溯海德格尔开拓的新领域,认为解释是此在现实的原初性形式,“理解是人类生活本身存在的原初性特征”。(32)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Continuum, 2004),250.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伽达默尔对阐释经验理论元素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涉及阐释学循环、作为理解条件的偏见、时间距离、效果历史原则等,提出了“效果历史意识”“视域融合”“问答逻辑”等重要概念。在他看来,理解与解释是基于效果历史意识的对话,其结构机制则是视域的构建与融合。阐释现象的逻辑就是提问与回答的结构:“一个历史文本成为解释的对象,这意味着它向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因此解释总是关涉向解释者提出的问题。理解一个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阐明的,这要通过我们获得阐释视域才能进行。我们现在把它视为问题视域,在这种问题视域之中,文本的意义才能得到确定。”(33)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 Continuum, 2004),363.人文科学的逻辑正在于此。
理解中的视域融合最终要依赖语言。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中,语言命题是关键点。虽然传统阐释学都论及语言的重要性,但是伽达默尔把语言提升到新的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实现阐释学从认识论、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型。从路径来看,伽达默尔如海德格尔一样试图回到日常生活领域,但是他的不同之处,在于看到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交往对话性对于阐释学中的语言观的重要性。他把日常言语的理解作为阐释的基础,分析语言的机制,重建本体论阐释学的关键点。伽达默尔欣赏施莱尔马赫的论断“阐释学的一切前提不过只是语言”,据此,他认为语言是阐释学经验的媒介,它使谈话得以最终发生,使某种存在的东西涌现出来。理解与语言是内在联系的,理解并不在于使某人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34)[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8页。,因此,在人们常常把理解的艺术归属于语法学和修辞学的领域,“语言是人们之间进行理解和认同的媒介”。(35)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London: Continuum, 2004),386.外语翻译具有启发性,它必须把要理解的意义置入另一个说话人所处的语境之中,因此翻译本身就是解释,就是翻译者对词语的解释。虽然这种理解的语言中介在谈话中不是一种规范,但是它要求在谈话中放弃各自独立的权威性,“谈话是达成理解的过程。因而每一次真正的谈话就是每个人向对方敞开,真正把对方的视角视为有效的视角,设身处地,以至于他理解的不是特殊的个人,而是其所说的东西”(36)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London:Continuum,2004),387.。因此,如同翻译外语文本一样,我们对文本的解释不是复现原文的本义,而是我们基于文本内容的再创造。对读者而言,文本接受了来自另一种语言的光,从而获得新的世界与新的理解,因而忠实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基于作者意图的解释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共同的基础是语言媒介所奠定的,没有语言的普遍性媒介,理解和解释都不可能发生。解释如同谈话,是由一问一答的辩证法所建立起来的循环。因此,理解本身是具有语言性的,理解的语言性深入到效果历史意识本身之中,形成了语言与思维意识、生命、历史的融合。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是阐释对象的决定性因素,作为解释对象的流传物(tradition)具有语言特性,不论就语言文本而言还是就造型艺术而言。伽达默尔充分利用对文字书写的流传物对象的分析,来建构本体论阐释学的基础。在他看来,文字书写的流传物是语言性,这对阐释学而言十分重要。这里,语言脱离了言说,化作了文字符号。通过文字书写,所有的流传物成为陌生的,在历史过程中遭遇不同的读者,不断地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就是克服文字符号的陌生性,建立起现在与过去的交往或者对话。不仅阐释对象具有语言性,而且阐释行为本身的决定因素也是语言。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就是解释,解释意味着使解释者的前概念起作用,从而使文本的意义真正对我们言说。解释过程的语言性在于我们通过解释使文本说话。因此,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阐释本体论的视域。语言作为我和世界相遇的媒介,体现了人和世界的融合,它是世界的经验,是世界的视角,一种语言观就是一种世界观。如洪堡所说,一个人学习一门外语,就获得了世界观的新立场。而且,语言媒介具有思辨特征,体现了人类有限构成与历史构成,是在无限概念中的有限定位。诗歌的语言媒介与日常言语一样,也是如此:“文学人物所说的词语如同日常生活的言语,均是思辨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说话人通过言语表达了与存在的关系。……诗性陈述本身是思辨的,因为诗性词语的语言事件表达了与存在的独特关系。”在伽达默尔看来,这是荷尔德林所称的“诗歌精神的演进模式”。(37)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Continuum,2004),465.
可以看到,伽达默尔的阐释本体论是对海德格尔阐释学的系统化与深入推进,但是核心概念如存在、本体论、语言等范畴仍来自海德格尔。现象学阐释学在当代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在法国,利科是重要代表。1974年,利科在德国现象学学会上宣读了论文《现象学和阐释学》,提出“阐释现象学”。他在批判胡塞尔的唯心主义现象学基础上又回到胡塞尔的意义与意向性原点,这个原点超越了自我意识,语言符号的秩序也关乎经验结构。如果说任何阐释学关涉意义,那么“任何涉及‘存在’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存在’的意义的问题”。(38)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ohn B.Thompson ed.and Tra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14.这正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所涉及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利科把海德格尔视为阐释学嫁接现象学的捷径方式,他自己则选择漫游的方式。他从胡塞尔《逻辑研究》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发展路线的终点,创新思考存在论阐释学,用理解存在论取代理解认识论:“理解不再是认识方式,而是存在方式,是那个通过理解而存在的存在方式。”(39)[法]保罗·利科尔:《存在与诠释学》,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利科深刻地认识到存在阐释学所带来的革命意义,因为找到了更为根本的本体基础。在先于数学化自然构造之前存在着一个意义领域,这个意义领域对一个认知主体来说是先于客体性的,在客体性之前存在着世界视域,从而将理解问题和真理问题带到了彻底性程度:理解变成此在“筹划”,是此在向存在的开放;真理不再是方法问题,而是显现理解性存在的问题。利科不同于海德格尔的路径就是通过语义学层次取代此在分析,通过语义分析或者说文本阐释学进入反思领域,从而达到存在领域。在他看来,语义学是对具有意指结构的象征符号的意义的分析。解释是思想的工作,它透视明显意义中的隐蔽意义,阐明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正是通过解释,意义的多样性被表现出来。在《活的隐喻》中,我们不难看到利科在语义学方面所探测的深度与复杂性。他在该书中指出他的路径就是“始于修辞学,经过符号学和语义学,最后到达诠释学”。(40)[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页。隐喻的分析既体现了对修辞学的理解,也体现了对符号学和语义学的把握,但是隐喻阐释学还需要实现转换,就像从语句层次向语篇层次转换一样,在隐喻中奠定更普遍的哲学意义和现实根据:“由语义学向诠释学的这种过渡在意义和指称通过全部话语而进行的联系中找到了最基本的根据,这里说的意义乃是话语的内部组织结构,而指称是涉及语言之外的现实的能力。”(41)[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页。他把隐喻的理解作为阐释学的核心问题,作为对更长文本理解的指导基础,从文本话语内在意义的解说延伸到对涉及世界的能力的解释:“我们的工作设想因而使我们从隐喻到‘意义’及其解说的文本,然后从文本到作品涉及世界和自我的隐喻,即严格解释层面的隐喻。”(42)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ohn B.Thompson ed. and Tra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71.在语义层次基础上,他实现与海德格尔的会合,通过反思实现符号理解与自我理解的桥梁,从而达到存在领域的理解。利科不仅立足于语义学,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伽达默尔所忽视的叙事命题。在三卷本《叙事与时间》中,他通过融合叙事与时间意识现象,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阐释学”(43)John Arthos,Hermeneutics after Ricoeur,(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9),95,从而对阐释现象学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他认为,“叙事的统一性是对阐释学循环的诗性解决办法”(44)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II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248.,通过作为中介的叙事的结构机制分析,我们可以领会存在的基本意义。可以说,利科的存在阐释学是一种他称之为迂回的复杂化的阐释学,更注重对理解与解释的复杂意义机制的探索。
现象学阐释学作为20世纪文学阐释学最重要的形态之一,体现出知识话语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它把语言符号的意义机制与存在的本体理解以及此在的创造性建构结合起来,实现了文学阐释学的革命,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影响深远。其中,解释作为解释者与文本的交往对话的观点,激发了姚斯、伊瑟尔的阅读现象学、接受美学的产生。
四、批判阐释学
上述三种阐释学是从文本理论到精神科学再到存在意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尽管伽达默尔提出解释是一种实践,其阐释学也称之为实践哲学,但是这种实践哲学主要是话语实践,停留在语言事件层面,不能有效地进入社会现实的领域。正如有学者指出,当代阐释学先驱所提出的“实践阐释学”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劳动相去甚远。(45)Domencio Jervolino,“Gadamer and Ricoeur on the Hermeneutics of Praxis”,in Richard Kearney ed.,Paul Riccoeur:The Hermeneutics of Ac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63.批判阐释学则是对这种缺陷的弥补,从而丰富了当代文学阐释学的形态。这种形态主要以哈贝马斯、赫勒、鲍曼、詹姆逊等学者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社会批判阐释学为代表,形成了阐释学与社会理论、伦理政治的结合。在这种形态中,理解与解释不仅是意义的发现或者创造,而且本身具有社会批判的意义。批判阐释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发生的阐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论争,即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之争,也就是利科所说的“阐释学与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冲突”。(46)Paul Ricoeur,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ohn B.Thompson ed. and Tra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63.利科认为,伽达默尔代表了传统阐释学一方,而哈贝马斯代表了意识形态批判一方。事实上,阐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能够相互渗透,形成一种利科所说的“批判阐释学”形态或者詹姆逊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利科看来,“对虚假意识的批判能够成为阐释学的有机组成部分”(47)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John B. Thompson ed. and Tra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94.。参与阐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论争的德国学者布博纳尔(Rüdiger Bubner)认为,批判理论与阐释学在反思的形式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如果批判的态度是在自我和反思的对象之间形成根本的区分,那么阐释学主要立足于与对象的调和和认同。”但是这种区分和调和的反思态度不是不相容的,而是并存的,“批判从来不是完全没有调和的元素,阐释理解并没有压抑所有的批判性判断”。(48)Rüdiger Bubner , Essays in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Trans. Eric Matthew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45.这为批判阐释学或者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奠定了基础。
无疑,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视为批判阐释学的奠基者。他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出版不久,针对存在阐释学或者现象学阐释学进行批判,在批判中把阐释学纳入批判理论的视域,从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阐释学的新形态。起点是他1965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就职演讲的文章《认识与旨趣》。这篇文章蕴含着哈贝马斯后来系统地建构交往对话理论的诸多思想元素。在他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以批判客观主义为目标,但是最终陷入客观主义的泥潭,从而脱离了认识与旨趣的有机联系的基础,陷入他自己所批判的传统理论。如果说胡塞尔现象学犯了客观主义错误,那么伽达默尔的历史—阐释学也同样如此。哈贝马斯看到,历史—阐释学研究变化不定的领域,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传统流传物,但是这种研究如同经验—分析科学,具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特征:“尽管精神科学(历史—阐释学的科学)通过理解去把握它的事实,尽管精神科学对于发现普通的规律并不怎么关心,然而精神科学和经验—分析的科学却有着共同的方法意识(das Methodenbewusstsein):用理论观点去描述结构化的现实。”(49)[德]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在批判现象学阐释学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掌握对象的三种认识旨趣:技术、实践和解放。在此,他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的一些阐释学思想。如果说技术的认识旨趣是从技术把握对象化的过程,有效控制活动以达到信息维护与扩大,解放的认识旨趣在于以批判为导向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虚假意识形态,那么实践的认识旨趣就包含在历史—阐释学的视域之中。哈贝马斯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即阐释学的规则规定着精神科学陈述的可能的内涵和意义,阐释学的知识总是以解释者的前理解为媒介。哈贝马斯指出,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只有随着解释者自身的世界同时清晰可见时,才向解释者敞开,理解者在两个世界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他把传统流传物运用于自己和自身的状况时,他就抓住了流传物的真实内涵。显然,这是《真理与方法》的基本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诠释学研究的主要旨趣是维护和扩大可能的、指明行为方式的谅解的主体通性,并以这种旨趣来揭示现实。对内涵的理解按其结构来说,目标是行动者在流传下来的自我认识的框架内的可能的共识。”(50)[德]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6—237页。这就是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实践的认识旨趣。哈贝马斯把这种旨趣融入他的知识系统的探究之中,定位于更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过程之中。属于阐释学的认识旨趣作为人类的利益关系,受到社会化媒介的制约,融于劳动、语言和统治一体的生活世界:“人类首先是在社会的劳动的和强制性的自我保护的系统中保障自身生存;其次是通过以日常语言为交往(手段),以传统为中介的共同生活,最终是借助于自我同一性来保障自身的生存;这个自我同一性在个性化的每一个阶段上,参照群体规范,重新巩固个人的意识。”(51)[德]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40页。自我反思的批判与独立判断都与语言联系在一起,因为随着语言结构的形成,我们进入了独立判断,随着第一个句子的形成,一种普遍的和非强制的共识的意象明确地说了出来。这是交往对话或者说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得以实现的条件,但是这不仅是语言的条件,还存在着对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民主自由的确立:“只有在一个其成员的独立判断已经成为现实的、解放了的社会里,交往才能发展成一切人同一切人的摆脱了统治的自由的对话;我们从自由的对话中获得了相互都有教养的自我同一性的模式以及真正一致的观念。因此,陈述的真理,建立在成功的生活的预见中。”(52)[德]哈贝马斯:《认识与旨趣》,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41—242页。可以说,这些精彩的论述透视出伽达默尔对自由的独立判断的漠视以及对生活本身的漠视,也透视出现象学阐释学的保守主义,突出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特征,即突破物化的价值规则和不明智的信仰力量,为人的自由解放建立可能性。他重新在语言与规则之间确立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基础,批判社会生活中的被扭曲的公共领域与交往,去发现破坏人们真正对话与自由对话的暴力踪迹,从而推进合法化进程。
哈贝马斯的这些批判阐释学思想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得到更为系统的论述,此书是批判阐释学的经典代表。交往行动理论是基于阐释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交往行动是以一种合作化的意义过程为基础的,在这种意义过程中,参与者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关系……在这里,发言者和听众把三种世界的关系体系运用作为解释的范围,在这种解释范围内,他们制定了他们行动状况的共同规定……理解意味着交往参与者对一种表达的适用性的赞同;意见一致意味着主体内部的发言者对一种表达的适用性提出的运用要求的认可。”(53)[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这种普遍意义的交往行动理论也包括对文学的理解与阐释。他充分挖掘了米德对文艺的理解。米德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在于发现情感可以在不同地方可以同样表达的表达方式。抒情诗人具有与一种感情激动联系在一起的美的经验,并且作为艺术家可以运用词汇,他寻找适合他的激情的词汇,以及在其他情况下能够引起自己态度的词汇。对米德来说,“决定性的是交往的词汇,就是说,象征在一种个人那里,本身是引起与在其他个人那里相同的情况。应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相同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应该在相同的情况下出现”(54)[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1页。。米德对语言象征符号的普遍性的认识对哈贝马斯来说具有启发性,可以深化对文学创新的理解,“一个寻求新的阐述的诗人,在适合的意义惯例的资料创造了他的新的作品。他必须直观地实现相应的发言者预计的态度,从而不能把他的态度作为简单的冒犯而加以拒绝,以对付惯常的语言运用”。(55)[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1页。但是米德的认识还不够,哈贝马斯在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规则概念、皮尔斯的普遍语用学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于语言规则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一旦交往的活动采取了文法语言的形式,象征性结构就渗透了内部活动的所有组成部分,就是说,不仅实在的认识的工具性的观点,而且不同内部活动参与者相互决定的行动的控制机制,以及行动者连同他们的处理方法,都与语言交往相联系,并象征性地完全结构化了。”(56)[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83页。这种语言性的结构化就如伽达默尔的语言的普遍性认识一样,构成了谈话理解的规则,从而执行人们行动合作和社会化的职能。语言的理解与交往不仅使得意义达成一致,获得普遍共识的基础,而且成为社会形态的内在基础。因此,借助于阐释学的路径,哈贝马斯认为,通过话语交往,可以形成普遍的理想化的交往共同体。从根本上说,这种基础来自生活世界,从逻辑上有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基础,但是获得了批判理论的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形成了当代文学阐释学的重要形态之一,这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文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因为它关注文学阐释的命题,而且他的批判阐释学也适用于文学阐释。当然,这种文学阐释学在批判阐释学内部也受到不少质疑,赫勒与鲍曼在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的同时,批评了他话语理解的普遍主义模式,认为话语理解体现出多元的有限性。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是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深入研究的问题。他在宏大的知识视域与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提出“政治阐释学”“辩证阐释学”等理论,并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他立足于黑格尔现象学和历史哲学传统,深入探讨批判理论,钻研法国现象学文本以及语言命题,对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扭转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脆弱无力的印象。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概念,并把本雅明、马尔库塞和布洛赫的文学辩证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变体”。在他看来,理解与解释的问题不仅仅是语义学和结构主义的意义阐释,而且深深地融入政治与历史之中。詹姆逊引述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的宣言:“只有自由这个字眼仍然使我感到鼓舞”,基于此进行了政治阐释学的创建之路:“有多少观念,我们可以说在理性上理解了,却忘记了它们在所有本原意义上的含义。”(57)[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5页。在他看来,阐释学就是复活掩盖在死亡语言层面之下的活的观念。这种复活是本原过去和我们解释者的文化和阶级中的比较与衡量,因此过去的意象与其说发挥了过去历史的功能,不如说发挥了阐释的功能。从传统意义看,阐释学尤其是宗教阐释学是宗教用以复原抵抗它们的文化文本和精神活动的技巧,但是它也是政治学,“提供在停滞时代革命活动的源泉和保持接触的手段,在压抑的地质年代隐蔽地保持自由概念本身的手段。确实,只是自由的概念,同爱或者正义、幸福或工作等那些其他可能的概念加以比较,才证明是政治阐释学的特殊的工具,而且反过来,这个概念本身也许最宜理解成释义手段,而不是哲学的本质或观念”(58)[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76页。。因此,阐释学涉及自由,自由促进了政治阐释学的形成。詹姆逊认为,利科做出否定阐释学和肯定阐释学的区分,前者是利科所认可的唯一正确的阐释学,也就是宗教阐释学。它试图恢复被忘却的意义,抵达生命本质之源,作为怀疑与否定,具有非神秘性和觉醒的意义,这是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意识形态和幻觉意识的批判一致的。事实上,詹姆逊试图扭转声名狼藉的阐释、解释、评论概念,面对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所提出的批评阐释的形式主义困境,提出了阐释学的新路径,也就是元评论(metacommentary)之路径,这带有鲜明的批判理论或者利科所提出的否定阐释的特征。这种阐释不注重正确解释一部作品,而是关注为什么要进行解释,涉及解释本身的合法性,“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59)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对詹姆逊来说,布洛赫的阐释使命就是把世界看作形象的巨大贮存库,试图揭开每一个生存瞬间的匿名状态,破译语言和作品、经验和客体下面隐约不定的意义。因此詹姆逊认为,布洛赫与马尔库塞、本雅明体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试图恢复文本的真实政治维度,把文本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冲动理解为无法遏制的革命愿望的比喻。这些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詹姆逊看来透视出辩证思维的逻辑,从而能够对对象进行深切而本真性的理解。他把洪堡提出的具有阐释学意义的“内部形式”纳入辩证批评之中,通过文本探测社会和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的深度。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大贡献体现在1981年出版的《政治无意识》之中,提出了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解释的理论。詹姆逊认为,这种政治解释是所有阅读与解释的“绝对性视域”。他在狭义阐释学的批判性视域中扩大了文学阐释学的话语空间,把20世纪重要的文学流派都纳入文学阐释学的领域加以辨析,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对话性与知识话语的丰富性。按照他本人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相对于伦理、心理分析、神话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神学解释,就语义丰富性而言显示出优先性与不可取代性,只有马克思主义解释才能解决历史主义的困惑,挖掘过去文化的根本秘密,实现文学理论与文学历史的统一。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或者政治阐释以辩证批评和元评论为基础,深入整合弗洛伊德阐释学、结构主义意义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分析,形成了其追求的强误读(strong misreading)阐释学。詹姆逊认为,“解释不是一种独立性行为,它发生于荷马笔下的战场之中,在这样的战场上,众多选择或明或暗地相互冲突。倘若实证主义关于语文学正确概念是唯一选择,那么我情愿认可目前欢呼的强误读而不是弱误读。正如中国经典所言,执柯以伐柯:在我们的语境中,其他更强的解释能够颠覆或事实上拒绝已有的解释。”(60)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ondon:Routledge, 2002),xiii.马克思主义解释以与其他阐释学不同的目的与方式,实现阐释学的嬗变,它使人们最终认识到,“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的确,一切‘最终’是政治的”。(61)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ondon:Routledge, 2002),5.詹姆逊的政治解释在于穿过文化产品的表象,深入暴露作为社会象征符号行为的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此,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观念是极有启发的,因为在他的结构主义中,结构概念本身作为各种在场元素的关系是不在场的,同时中介也是更为结构化和隐蔽的,而不是表面上的同构。这种结构概念与弗洛伊德阐释学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在詹姆逊看来,心理分析是目前最有影响力和最精细的阐释系统,是真正新的原创性阐释学,其无意识、欲望、愿望满足等概念无疑促成了政治无意识概念的形成,欲望意识形态成为政治阐释学的内在基础,但政治阐释超越了弗洛伊德的个体欲望,而是如弗莱的原型批评所启发的,进入集体的社会政治层面。这样,研究的个体作品对象即文本就不是作为文学注释的有限对象,而在本质上是一种象征符号的行为,而且语言视域被延伸到社会秩序的层面,解释的对象被辩证地扩展,并以集体和阶级的话语形式加以重构。最后,当达到整体历史的终极视域时,文本和意识形态元素转变为形式的意识形态,象征符号信息本身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某些痕迹或者期盼。詹姆逊具体阐释了三种解释视域或者解释阶段及其辩证发展的动力机制。第一种视域是象征符号本身,是狭义的政治或历史视域,这里意识形态不是注入象征符号生产之中的某种东西,“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审美或者叙述形式的生产本身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对没有解决的社会矛盾寻找想象的或者形式的‘解决办法’”(62)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London:Routledge,2002),64.。第二种视域是社会视域,涉及阶级话语的视域或者意识形态元素的视域。第三种则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视域,文本成为形式的意识形态,文本被转变为社会生产方式彼此角逐的力量场域。这里,历史本身成为我们人类普遍理解的限度和我们具体的文体解释的限度。有学者把詹姆逊的阐释学系统理解为政治、社会和历史三种元素。(63)Christopher Wise,The Marxian Hermeneutics of Fredric Jameson,(New York:Peter Lang,1995),51.我认为,通过对象征符号到意识形态元素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辩证发展,政治阐释学的内在解释逻辑与程序得到了具体而合理的论证。
可以看到,詹姆逊的政治阐释学与哈贝马斯的交往阐释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征,在解释中实现政治的愿望,表达了人类的总体性的把握权力的合法性命题。但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哈贝马斯关注重建公共领域与实现共同体的理想价值,而詹姆逊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革命的政治想象,带有更多的政治乌托邦色彩。不过,他们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促进了文学阐释学的重要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与批判创造性,因为它关注现实社会中人的命运及其改变。这可以用马克思的经典语句来表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五、后现代阐释学
在现象学阐释学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兴盛的同时,后现代阐释学针对普遍哲学阐释学的批判应运而生,在当代文学阐释学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形态,形成了“幽灵阐释学”“超越阐释学的阐释学”“阐释学考古学”等不同的表达。这种阐释学以差异性、去中心化、解构的姿态颠覆了以往的阐释学形态。德里达、布鲁姆、罗蒂是后现代主义阐释学的重要代表。现象学阐释学的一些理论家如胡塞尔、梅洛-庞蒂也包含了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和偶然性观念和思想,1988年出版的《后现代阐释学》(G.B.Madison)、1992年出版的《梅洛-庞蒂、阐释学与后现代主义》(Thomas W. Busch and Shaun Gallagher)就是代表。我们主要以德里达和罗蒂为代表探讨后现代主义阐释学的差异性理论追求与解构性话语特征。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德里达否定日常交往领域,“贬低对应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表达的交往表达”(65)[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这是对“规范话语和诗性话语的本质特征的双重否定”。(66)[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德里达的阐释学以对语言本身的质疑为核心,提出文字学基础上的延异概念,从而对文本原义和普遍共识进行了解构或者摧毁。这种正如活人与死者对话的阐释学被学者称为“幽灵阐释学”,“唤起多样而充满冲突的阐释、话语的涌动、众多诗性的、宗教的和哲学的话语”。(67)John D. Caputo,“Haunt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Faith”, in Kevin J. Vanhoozer, James K. A. Smith & Bruce Ellis Benson eds. Hermeneutics at the Crossroads,(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100.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基于逻各斯基础的语音中心主义把语音与概念结合起来,这种语音特权构成了普遍性规范及其对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听—说’系统,通过语音成分——表现为非外在的、非世俗的、非经验的或非偶然的能指——必定支配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甚至产生了世界概念、世界起源概念,而这一概念源于世界与非世界、内与外、理想性与非理想性、普遍与非普遍、先验与经验的区分等等”(68)[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9页。。语音作为逻各斯与意义内在联系在一起,包括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表示意义、“收集”意义。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所表达的言语是心境的符号观念,就是表明言语作为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联系,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的符号关系。德里达认为,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音中心主义主张“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69)[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5页。可以说,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以语言作为理解基础的阐释学事实上是立足于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不论是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存在之家,还是伽达默尔对日常言语的看重,还是哈贝马斯对言语行为的依赖,他们都试图为理解与对话寻找共同性的根据。但是,德里达试图解构这种语言普遍性,其颠覆的武器就是诉诸文字所蕴含的阐释学意义的延异范畴。这里,他从尼采的文字观即超越逻各斯和理性的文字观看到了解构的力量,又看到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探索所提出超越形而上学观念对存在的沉默特性或者能指性的洞见,从而建立了延异的本体论:延异是最本源性的,而这是与文字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字是语言游戏,处于痕迹的无目的的生成过程之中,这不是一种既定的结构,而是一种不断运动的活动,差异本身就凸显出来了,因而纯粹的痕迹就是延异:“它并不取决于任何感性的丰富性,不管这种丰富性是声音还是可见物,是语言还是文字。恰恰相反,痕迹是感性丰富性的条件。虽然它并不存在,虽然它不是在所有丰富性之外的此在,但它的可能性先于我们称之为符号的一切(所指/能指,内容/表达,等等),不管它是概念还是操作,不管它是动机还是感觉。”(70)[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89页。它无法感知,也不可理解,也没有透明的意义,也非连续性的时间之流与空间之维,不是在场的显现与确定。
基于对文字现象学的痕迹延异的考察,德里达对理解与解释的把握就突破了已有阐释学的框架,理解和解释本身就是差异性的延伸。这样,解释的文本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确定性对象,而是具有意义的开放性与可能性的网络。德里达认为,文本不是基于因果关系和层层积累的直线性的东西,而是超越规范性和逻辑性的复杂文字系统网络:“人们不断将各种根须混合在一起,让它们盘根错节,重复穿梭,加强粘连,在它们的差别中循环往复,层层盘绕或者纵横交错。”(71)[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文本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也导致阅读与解释差异的无限可能。德里达提出的“批判性阅读”虽然尊重注释文本原义的传统批评,因为没有这种尊重,批判性阅读将成为盲目而任意的活动,但是批判性阅读不同于复制性注释,而是要处理在场与缺陷的关系,关注作者可以用语言支配的东西和他不能支配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样,解释则是无限的不确定的替补过程,摧毁在场的确定性,因此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就如他对卢梭作品的解释意义。德里达认为,卢梭的著作是复杂的多层次结构,“我们可以审慎地进行自由阅读”:“卢梭说A, 由于我们必须确定的一些原因,他将A解释成B。此后,在不脱离卢梭原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A与‘把A解释成B’分离开来,并且发现各种可能性。”(72)[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46页。文学阐释无疑就成为差异性和创造性的文字游戏。德里达追随海德格尔的存在阐释学而最终以海德格尔的方式解构了总体性与宏大叙事,为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阐释提供了典范。
同样,罗蒂不满意于当代阐释学对认识论的隔离,认为阐释学和认识论可以相互补充。而他更不满意的是阐释学对共同规则的建构和公度性的理论设想。的确,阐释学的主要旨趣在于解释规则的建构,从文学注释学对语法规则的肯定,再到普通阐释学对精神规范的设定,再到现象学阐释学对语言普遍性以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语言交往理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阐释学总是在建构普遍的规则体系。意大利著名阐释学家贝蒂还专门研究阐释的规则体系,提出解释的指导原则是阐释学对象自主性的规则:“我们把这第一个规则称之为诠释学的对象自主性规则或者诠释学标准的内在性规则,以此我意味着,富有意义的形式必须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并且必须按照它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们所具有的联系,并在它们的必然性、融贯性和结论性里被理解。”(73)[意]埃米里奥·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这里的“规则”“标准”“逻辑”再加上“必须”的语态,透视出阐释学的严格性与真理性的确定性追求,主要是宏大叙事的价值追求。罗蒂虽然认可认识论的意义,但是不认同普遍性的确定性真理的阐释界定,这事实上颠覆了现代意义的认识论。阐释学取代了认识论,不是用阐释学来填补这个空白。如果对知识论的愿望就是对限制的愿望,即找到可资依赖的基础的愿望,找到不应游离其外的框架,那么罗蒂的阐释学就是突破这些基础、限制与框架:“诠释学是这样一种希望的表达,即由认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再被填充,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成为这样一种状况,在其中不再感觉到对限制和对照的要求。”(74)[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77页。因此,罗蒂从认识论到阐释学的转向不是重建精神科学的认识论,而是突破认识论框架走向后现代阐释学。他的阐释学就是对可公度性的挑战。
在罗蒂看来,认识论的假设是某一话语的一切参与活动都是可公度的(commensurable),因此要去寻找与他人共同基础的最大值和共同基础,达成一致的希望可以说是共同基础的征象,表明解释的共同的合理性的存在。而阐释学是对这种假设的斗争,不可公度性成为关键点。在罗蒂看来,库恩对阐释的不可公度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库恩在探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著名的范式理论,这被不少人视为公共阐释的重要论据,因为范式确立一个科学家群体的共识。但是正是在这里,范式是一个科学家的革命性创建,一种传统规范的突破,对已有共识的瓦解。科学的革命或者创新是建立不同于已有范式的新范式,这种革命的范式最初根本不成为科学家共同体的规则,也就不被认可。库恩表达了传统与革新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意味着真正科学进步的元素是打破可公度性。罗蒂极为欣赏库恩的如下关于理解的差异性的论述:“当阅读一位重要思想家的著述时,首先寻找文中明显荒谬之处,然后自问,一位聪明的人怎能这样写呢。我继续阅读,当你找到一个答案时,当你完全理解这些段落时,你会发现,你以为你先前理解的那些核心段落,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75)Thomas S.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xii.库恩对学生所表达的肺腑之言,说明了理解的过程性与变化性。如果用于范式理论,这意味着范式的不稳定性和在创新中的形成规则,在规则中突破规则,从传统与更新的张力中推动科学的革命与进步。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尚且如此,精神科学更难以获得可公度性,文学阐释无疑更艰难。罗蒂认为:“库恩断言,在具有不同的成功说明范式、或不具有相同的约束模式、或二者兼有的科学家集团之间,不存在可公度性。”(76)[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84页。罗蒂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以及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认识论传统追求自然之境的准确表象,不同于实践或美学的事物的一致性的方法。虽然实践或美学中存在一致性方法或者共识,但却不是认识论的可公度性。虽然科学与艺术具有相互的影响与联系,但是库恩强调了两者的差异性,范式概念主要在科学领域运用,对艺术领域的范式使用持怀疑态度。虽然科学与艺术都看重革新,但是库恩指出:“科学家和艺术家对革新本身而言定位于极为迥异的价值。”(77)Thomas S. Kuhn, The Essential Tens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350.这涉及对认识性与非认识性或者规则系统与非规则系统的理解。认识论明确地区分两者的界限,或者把非认识性的东西归结为认识性的东西,把非规则归结为规则系统。而库恩所选择的就是把认识性的东西归结为非认识性的东西,因为像历史与文学一样的东西在于创造而不是发现。罗蒂认为,作为精神科学的阐释学重视不可公度性,“解释学只在不可公度的话语中才为人需要”。(78)[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44页。人的精神不能够加以精确预测,这正如社会学家泰勒所表达的观点,因为人是自我规定的动物,自我规定改变了,人是什么也随之改变,其理解的词语也就不同,这在人类历史形成了“不可公度的概念网”。(79)[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03页。
语言的共识以及语言翻译的等同性对罗蒂来说都是值得怀疑的,伟大诗歌当然是可以翻译的,“问题在于,翻译作品本身并不是伟大的诗歌”。(80)[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12页。人的精神是如此之不为人熟悉和不可操纵,以至于我们疑惑语言是否能够适合于精神的表达。中国古代的言语之辨无疑为解释的不可公度性提供充分的阐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成为公度阐释学的困境。如果说认识论是在我们自身的镜式本质中准确地反映周围的世界,建立系统哲学,以本质的知识建立一切话语的公度性,那么阐释学则是解构传统,怀疑普遍公度性的整个设想,强调对话持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因而哈贝马斯的普通语言学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认识论是立足于正常话语,那么阐释学则是属于反常话语。罗蒂的阐释学蕴含着对人的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探索,因而他认为把一切话语变成正常话语是把知识变为物而不再成为人,这是恐怖的,因为这消除了新事物的可能性,消除了诗意的而非仅是思考的人类生活的可能。相反,阐释学作为基于谈话的文化哲学“想为诗人可能产生的惊异感敞开地盘,这种惊异感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存在的某种新东西,它不是已然存在物的准确再现,人们(至少暂时)既不能说明它,也很难描述它”(81)[美]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境》,李幼蒸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22页。。可以把罗蒂的后现代主义文学阐释学视为具有创造性的“无镜的哲学”。这种无镜性循着尼采的现代精神和解构学派的摧毁精神,瓦解了语言的交往性与再现性的真理观,向偶然性与自由创造打开了大门,文学解释不再追求普遍性的目的,而是成为基于偶然性的无限的过程。他认为对拉金的诗歌的解释永远是未完成的,“其所以不可能完成,乃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必须要我们完成:事实上,只有一张关系的网——一张在时间中天天延长的网,必须不断重新编织”。(82)[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2页。在这种阐释学中,交往与公共阐释也随之失去了合法性基础。
综上所述,文学阐释学体现出多元的丰富的形态,显示出不同的哲学基础、解释目的、文学观念与价值选择。文学注释学以意义的原义为旨趣,普遍阐释学追求浪漫主义的精神生命与认识论的普遍规则性,现象学阐释学关注本体论与语言本体论,批判阐释学强调解释的伦理政治,后现代主义阐释学则张扬话语的激情式延异游戏。这些阐释形态构成了当代文学阐释学的“家族相似”话语网络。它们面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具体文学文本提出的问题是不同的,所做出的回答也是不一致的。虽然“阐释学”“理解”“解释”等术语被共同地挪用,但是它们在五种主要的阐释学形态中具有不同的所指意义,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系统与价值体系,构建了各自的阐释学合法性基础,同时形成了阐释的冲突与张力,因而多元性是文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倘若“真理”或者“意义”是阐释学的核心目标,那么它在不同形态的理解中是有差异的,它指客观性或是本真性,是普遍性抑或精确性或者偶然性,不一而足。它们对于“规则”“语言”“文本”的理解,亦是如此。虽然这五种阐释学形态存在理论的缺陷与实践的困惑,但是对文学阐释理论的发展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视域。特别是它们关于阐释规则、解释合法性、复杂机制、哲学意义、现实关怀等方面做出的探索,为中国阐释学的进一步建构奠定了理论反思的重要基础。
——意象阐释学的观念与方法》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