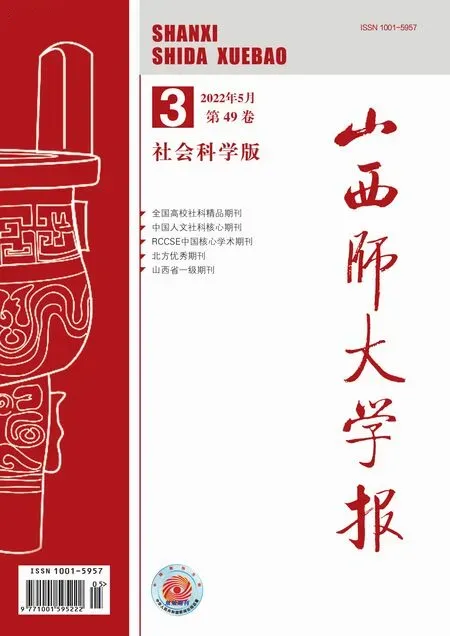中西文学瘟疫叙事比较
曹顺庆,王熙靓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一、中西文学瘟疫叙事流变比较
瘟疫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文学作为历史的重要表征,对此有充分反映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这也使得瘟疫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然而由于文化的异质性,中西文学中瘟疫母题的叙事流变呈现出较大差异,本部分将分别梳理中西文学中瘟疫母题叙事的历史流变。
“天灾流行,国家代有”(1)《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僖公十三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03页。,中国自古便疫病频发,史料中关于瘟疫的记载卷帙浩繁。殷商甲骨文中就已有“疫”字,《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2)(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56页。。而“瘟疫”一词,由于汉晋时期并无“瘟”字,因此最初写作“温疫”,“温”即发热的意思。中国文学中瘟疫母题的叙事流变可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明代以前,这个阶段关于瘟疫的记载多见于史书、方志、档案等文献,这些文献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文学价值不高。这一阶段文学中的瘟疫叙事散见于诗文中,其中以瘟疫为主题的诗歌充分展示了“诗可以怨”的功能。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文学的瘟疫叙事深受中国古代哲学“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多将瘟疫发生的原因与上天及君王的德行相联系,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思想观念,作者在叙事中多刺怨当时君王的失政之举并劝诫统治者施行“仁政”,暗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不乏对当时自然灾异进行描写的诗歌,而以瘟疫为主题的诗歌亦有不少。《小雅·节南山》曾言:“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3)《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40页。郑玄注曰:“天气方今又重以疾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4)《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40页。《大雅·召旻》亦有“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5)《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79页。。这两首诗中所说的“瘥”“降丧”即指瘟疫。从“天方荐瘥”“天笃降丧”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古人将瘟疫与上天相联系的倾向,认为“灾异天谴”。同时,这两首诗歌都以瘟疫为由怨刺当时朝廷的失政行为,《毛诗序》指出《召旻》一诗是“凡伯刺幽王大坏也”(6)《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79页。,亦称《节南山》是家父刺幽王。这反映出中国古人朴素的“天人感应”观念,将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与君王的德行相联系,认为“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7)(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54页。
汉末魏晋时期瘟疫盛行,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从171至185年,短短十五年间就爆发了五次瘟疫,因此丧命者不知凡几。曹植的《说疫气》曾言:“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8)《太平御览》卷第七百四十二“疾病部五”,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4383页。从曹植的记载可以窥见当时瘟疫盛行,民不聊生的凄惨境况。同时,从“鬼神作疫”“悬符”的描述也可以看出百姓仍将瘟疫与鬼神相联系的观念。虽然曹植在文中对此做出了批评,但他“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9)《太平御览》卷第七百四十二“疾病部五”,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4383页。的看法,反映出他对瘟疫的认知依然秉持着“阴阳和谐”“应天顺时”的朴素理念。
更为重要的是,这五次瘟疫的爆发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创作风格及其思想倾向。鲁迅先生在谈及魏晋风度时提到,建安七子的文章悲凉、激昂和慷慨。魏晋时期文人的创作风格多弥漫悲怆之感,与当时瘟疫盛行世人多夭折短寿不无关联。生命的无常与短暂使得文人一方面生发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及时享乐之念,另一方面又滋生出渴望通过立言以求不朽的矛盾之情。如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就提及“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10)(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78页。,这种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使得曹丕转向文学,试图通过著书立说以求不朽于后世,因此发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11)(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87页。的感叹。
及至宋朝,瘟疫爆发更为频繁,据统计“两宋时期中国境内约发生了311次较为严重的疫病”(12)韩毅:《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页。,因而宋朝曾将疫灾与旱灾、水灾、畜灾并列,共称为民之四患。宋朝的统治阶级对于瘟疫的防范和治理给予了充分重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疫体系。在医学措施方面,政府重视医学方书的编纂,并建立了隔离病人的“安济坊”及医疗救助机构“施药局”等;在政治措施方面,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疫情上报体制,并“对参与疫病救治的官员,按其政绩和救活人数,予以升迁和奖赏”(13)韩毅:《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6页。等。然而宋朝的统治者仍然秉承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观念,“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撤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衿,形于诏旨”(14)(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996页。。“罪己诏”的颁布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积极实施仁政,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一方面亦是“君权神授”观念的鲜明表现,将灾变与君王的德行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者,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也”。(15)(汉)戴德辑,(清)孔广森注:《大戴礼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年,第535页。
第二个阶段为明清之际,由于小说这一体裁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瘟疫叙事逐渐从诗文转移到小说。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几乎很少纯粹以瘟疫为主题,而多将其作为背景或者支线情节推动主要故事发展。如《水浒传》《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小说都涉及瘟疫叙事,瘟疫在其中或作为背景铺垫故事情节,或作为次要情节出现推动故事发展。这一阶段的瘟疫在叙事中逐渐表现出其隐喻意义,瘟疫不仅仅单纯作为一种自然疾病呈现,其中更隐含着作者自身的价值取向。然而瘟疫的这种隐喻意义,依然是立足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
这里以《水浒传》为例进行分析。《水浒传》的引言即交代了故事发展的背景,“谁想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上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16)(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3页。从引言的这一段就可看出,瘟疫是造成这一百零八好汉下临凡世的原因。同时,《水浒传》的第一回名为“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即以朝廷试图消除瘟疫作为《水浒传》全文的开篇。需要指出的是,瘟疫在《水浒传》中并非只有简单提示背景这样无足轻重的作用。相反,瘟疫为《水浒传》整个情节的发展确立了合理性,为这次农民起义举起了正义的旗帜,同时也为起义的失败蒙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如上文中笔者指出的,瘟疫在中国古代社会多与君王的德行相联系,人们多认为瘟疫是一种天谴,是对君王失德行为的惩戒和警示,因此这一百零八好汉就是这场天谴的具象化身。这也可与第一回宋仁宗采取的消除瘟疫的措施相关联,宋仁宗在听闻瘟疫愈演愈烈后,“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17)(明)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页。这些消除瘟疫的措施,从另一层面佐证了中国古代“灾异天谴”的观念,同时也为梁山好汉揭竿起义确立了充足缘由。因此,这场愈演愈烈的瘟疫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当时宋朝昏庸腐败、奸臣当道的专制统治的批判与讽刺。瘟疫在《水浒传》中实际上为这次农民起义确立了合理性,它是对官逼民反的宋朝专制统治的有力批判,同时也使得这场起义的失败更具悲剧和宿命色彩。
第三个阶段是现当代文学中的瘟疫叙事。随着科学和医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瘟疫的认知祛除了迷信和神秘色彩,将瘟疫与上天及君王的关联进行了切割,瘟疫开始言说自身。同时,现当代小说中开始出现了纯粹以瘟疫为主题的作品,瘟疫不再作为背景出现而是走上舞台中央成了主角。
现代的瘟疫小说,叙事视角多聚焦底层人民,着眼于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沈从文的小说《泥涂》为例,这部小说聚焦瘟疫横行下某市的北区即底层难民区,瘟疫像是一场局地暴风雨,小范围地集中爆发在此处,居住在这里的穷苦人民饱受折磨。贫富像是一条天然的隔离带,市南的繁盛区丝毫未受影响。沈从文在文中多次写到北区是被抛弃的区域,并将这场瘟疫冠以“下贱龌浊病症”的名称。小说以一场大火和张师爷的死亡为结尾,天灾与人祸并行,小说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不见丝毫亮光。
而经历过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当代小说的瘟疫叙事扩展了视角,作家们更深刻地意识到瘟疫是一场无差别的席卷全体人类的灾难。“从‘苦难’到‘灾难’,当代文学对瘟疫采取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认知和处理,将瘟疫理解为国家的灾难,而非仅仅是个体的苦难,是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瘟疫叙事的重要区别。”(18)赵普光、姜溪海:《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转型及其机制》,《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因此相较于现代瘟疫文学将视角聚焦于底层人民,当代的瘟疫文学叙事则将不同阶层的人民都纳入了叙事范围,全面突出地强调瘟疫的灾难属性。同时,当代瘟疫文学不再沉湎于瘟疫所致的暗无边界的苦难,而是在其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播撒出希望的种子,这就是当代瘟疫文学叙事中“抗疫者”形象的出场。如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小说中的这场鼠疫对于贫富人民一视同仁,丧命的不止有傅家甸里的贫苦百姓,连红极一时的女演员谢尼科娃也未能幸免于难。这场鼠疫从俄国经满洲里再蔓延至哈尔滨,成为一场席卷全人类的灾难。而小说中伍连德这一人物在故事的后半程出场,成为这场鼠疫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他的带领下,疫情得到了控制,傅家甸得以起死回生。小说的最后一章名为《回春》,在经历了漫长苦难的冬天之后,春天带着生机重新回到了这里。
西方文学中瘟疫母题的叙事流变也可大致区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古代至中世纪,这一阶段瘟疫叙事中神学因素突出,瘟疫被认为是神对个人或者群体道德败坏的惩戒,消除瘟疫的办法唯有虔诚祭祀。
古希腊神话作为民间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其中就已蕴含瘟疫叙事元素。古希腊神话是古人对于他们所身处其中世界的理解,马克思曾指出神话是古人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背景中,借助想象以征服、支配自然力并将其形象化的结果。霍克海默以及阿多诺也从存在的本体论来阐述神话,他们认为神话的诞生是为了“摆脱恐惧,树立自主”(19)[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瘟疫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威胁,因此古人对于瘟疫的恐惧可想而知。为了征服和支配这种超越自身认知能力的自然力,古希腊人在神话中将其进行了形象化的塑造。如冥王哈迪斯不仅是冥界之神,同时也掌管瘟疫,神话中他曾使忒拜城邦染上瘟疫,直到两个少女自愿献祭,瘟疫才最终停止。除此之外,太阳神阿波罗的姐姐阿尔忒弥斯也是掌管疾病与死亡的女神,她一方面拥有养育万物的母神之能,一方面却又拥有带给人类瘟疫和疾病的能力。而太阳神阿波罗作为人类的守护神,与阿尔忒弥斯类似,一方面他具有医治和消灾弥难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散播瘟疫以惩戒人类。古希腊神话中的这些瘟疫叙事,体现了当时的西方人民试图理解这些超越自身认知能力的外界事物的努力。
《荷马史诗》作为集古希腊口头文学的大成之作,瘟疫叙事在其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伊利亚特》的开篇即记载了阿波罗由于不满国王阿伽门农的傲慢而在其军队中降下瘟疫以示惩罚,这场瘟疫使得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不得不开会进行商讨。阿喀琉斯说:“阿特柔斯之子,战争和瘟疫将毁灭阿开奥斯人……不过让我们首先询问先知或祭司,或者圆梦人,因为梦幻来源于宙斯,他或许能解释福波斯·阿波罗为何动怒,是责备我们疏于祈求或者未奉献百牲祭吗?但愿他接受绵羊或者纯色山羊的香气,有心为我们阻挡这一场凶恶的瘟疫。”(20)[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王焕生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从阿喀琉斯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瘟疫的可怖,以及古希腊人将瘟疫与神的惩戒牢牢挂钩的观念。瘟疫来源于太阳神阿波罗的愤怒,而阿喀琉斯所设想的阻止瘟疫的方法是向阿波罗祭祀,请求他的宽恕。这场瘟疫是一个楔子,它引出了后续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纷争,对于故事情节的推进有重要作用。
十四世纪黑死病在欧洲的爆发,促进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出现,从某种程度而言改变了欧洲文明的进程,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近现代文学时期。这一阶段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深受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影响,神学因素逐渐淡去,作品中焕发出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光辉,这里以薄伽丘的《十日谈》和笛福的《瘟疫年纪事》为例进行分析。
薄伽丘的《十日谈》消解了早期瘟疫叙事中的神学信仰,同时以各类故事作为依托对教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十日谈》的创作背景就是十四世纪时盛行在欧洲的黑死病。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此时的人们已经不像古希腊时一样完全寄希望于虔诚祭祀渴望得到神的救赎,而是采取了一些科学的手段进行防治,比如对感染者进行隔离、焚烧感染者接触过的一切物品等等。与此同时,在黑死病爆发的早期,人们仍然会向宗教寻求帮助。然而事实却是疫情变得愈发严重,甚至神父和执法人员都不能幸免于难,教会变成了一个空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个男青年和小姐聚在了一起,开始讲些故事以解闷。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不难理解薄伽丘在小说中对教会进行大胆嘲弄和讽刺的原因。黑死病势不可挡的趋势以及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死亡人数,动摇了人们心中对于宗教的信仰。将一切诉诸神的宗教,在一视同仁的瘟疫面前褪去了神性的光环,走下了真理的神坛。人类自身的意识和存在开始萌芽,要求得到确证和重视。瘟疫揭开了教会伪善、愚昧的面纱,神性消退之后,人自身的诉求被旗帜鲜明地提倡和要求。因此,薄伽丘在文中无情嘲讽了教会所倡导的禁欲主义等违反人性的主张。
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进展,随之而来的17至18世纪的启蒙主义则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更进一步要求祛除宗教的愚昧主义,提倡自由和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对1665年发生于伦敦的鼠疫进行了纪实性的书写。在这部小说中,笛福“把这场鼠疫的发生、传播,它所引起的恐怖和人心惶惶,以及死亡数字、逃疫的景况写得如身临其境。当时法国马赛鼠疫流行,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笛福的作品满足了市民对鼠疫的好奇心”(21)《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 258 页。。在小说的导言部分,辛西娅·沃尔写道:“《纪事》部分是纪实——大半生里是个新闻记者的笛福,从当下能弄到手的档案和小册子,获取许多资料和统计数字。”(22)[英]丹尼尔·笛福:《瘟疫年纪事》,许志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3页。因此,这部小说的结构模式也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其情节是非线性的,笛福在小说中经常进行叙事跳跃。但正如辛西娅·沃尔所言,这种叙事方式反而可以“反映瘟疫本身的运动,兴起和衰落,侵略和退却”,(23)[英]丹尼尔·笛福:《瘟疫年纪事》,许志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8页。使得读者得以倾听“《纪事》‘史诗的宏伟,还有令人心碎的熟识亲近’”,(24)[英]丹尼尔·笛福:《瘟疫年纪事》,许志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8页。同时使文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得以凸显。
西方文学瘟疫叙事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至今,西方的瘟疫写作逐渐脱离具体的事件与医学范畴,并与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相联系。瘟疫成为一个现代社会隐喻的寓言符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瘟疫文学当属加缪的《鼠疫》。加缪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鼠疫》中倾注了自己哲学观念,瘟疫在小说中不再仅仅指向一种具象化的疾病,而隐喻着病态的社会现实。瘟疫在这里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呈现,它被还原成世界的荒诞本质,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中西文学瘟疫母题的叙事流变具有各自的文化特点,这些差异背后隐含着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如在文化的早期阶段,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中西方对于瘟疫的认知多带有神秘色彩和神学因素。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方与中国文学中第一阶段的瘟疫叙事都有将瘟疫与神及上天相联系的倾向,但其背后蕴含的意旨却有绝大差异。
首先,中国神话中虽然也有掌管瘟疫之神,但这种神话传说很少进入文学创作之中,这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书写传统有关。尤其在第一阶段,中国文学的瘟疫叙事以诗歌为主,作为托物言志的诗歌自然不欲言说鬼神之事,这同时也与中国古代贬黜玄想的思维观念相关。其次,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有突出的“神人同形同性”特点,神统摄掌管万物的书写实际上是人类借助想象征服世界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据此认为,神话即是启蒙,古希腊神话中蕴含的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古希腊人试图借助系统的神话体系的构建以确立自身存在的努力。而中国文学瘟疫叙事中“天人感应”观念中的“天”,则是全然神性化、超然物外的存在,其中蕴含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差异。
二、中西文学瘟疫叙事模式比较
经过第一部分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历史悠久,叙事流变在各个阶段都呈现出较大差异。本部分主要探讨的是20世纪以降西方文学中以瘟疫为背景的生存困境隐喻叙事,与中国当代文学中以瘟疫为主旨的英雄主义宏大叙事,并将二者进行比较。
中国当代文学的瘟疫叙事通常将瘟疫作为主旨并由此展开史诗性的宏大叙述,追求瘟疫叙事的完整性,“瘟疫成为被‘克服’或‘终将过去’的事件”(25)赵普光、姜溪海:《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转型及其机制》,《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并善于塑造潜在的英雄人物形象。
首先,中国当代文学的瘟疫叙事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在叙事中突出强调了“抗疫者”的视角。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以女作者罗玮芝在王府抗疫总指挥部的视角作为切口对这次瘟疫进行了讲述,小说的叙述主线在于“抗疫”,因此《花冠病毒》几乎全程聚焦于“抗疫者”的视角。这部小说更像是从宏观的角度描绘了一场战争,战争的双方是总指挥部和花冠病毒。总指挥部对于病毒的恐惧,“因其主体的集体性与英雄性而最终被崇高化,崇高化的结果是取消了恐惧本身”。(26)赵普光、姜溪海:《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转型及其机制》,《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因此这种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从某种角度而言,使得个体的人的苦难和重量被削弱了,抗争取代了人成了叙事的主体。
其次,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从社会整体性角度和治理者角度叙述了一场瘟疫被克服的完整过程”。(27)赵普光、姜溪海:《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转型及其机制》,《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在伍连德的带领下,疫情得到了控制,傅家甸得以起死回生。小说的最后一章名为《回春》,“昏睡了半年的冬天,到了清明的日子,终于打了个长长的呵欠,醒来了”。(28)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 236 页。傅家甸也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复又起死回生,人们在坟场哀哭过逝去的亲人后继续开始生活,而伍连德由于抗疫有功成为英雄。可以看出,《白雪乌鸦》的整个故事情节是非常完整的,从瘟疫开始到最后被消灭结束,每个人的结局都有交代,这个结局与《失明症漫记》中没有缘由的荒诞结尾显然具有明显差异。
最后,善于塑造一些潜在的英雄人物形象。《白雪乌鸦》中的英雄人物除了伍连德之外,还有傅家甸里一些普通的百姓。如傅百川,瘟疫发生后各类商铺都开始抬高价钱,只有傅百川联合商会身体力行地抵制这波涨价风潮,力图稳定物价。在口罩奇缺的情况下,傅百川利用自己的绸缎庄,在原有缝纫机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两台,并且还高价雇用了几个缝纫手艺好的女人,大批量加工口罩。封城后,也是他动员中医参与防疫。除傅百川外,周耀祖一家老少志愿为隔离在火车上的人们做饭,周家三代都因此而命丧于这场鼠疫;以及拉马车的王春申志愿加入了感染风险最高的埋尸队,等等。这些疫情下的小人物用自己朴实无华的善意点亮了这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都是迟子建笔下潜在的英雄人物,是灾难里透出的最后一点温热之光。这场鼠疫之战的胜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这群潜在的英雄人物共同抗争的结果。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的瘟疫叙事多将瘟疫作为背景进行隐喻叙事,瘟疫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通常是一种寓言符号,用来隐喻人类的某种生存困境。同时,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瘟疫作为指向人类生存困境的隐喻,是一层笼罩在人类生存空间上的阴影,不可能被克服,如加缪在《鼠疫》的结尾所说的,“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藏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29)[法]加缪:《鼠疫》,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
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即是一部以瘟疫作为寓言符号进行隐喻叙事的小说,小说从情节、人物形象到思想内涵等方面都传递着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自身体验,即一种深刻的荒诞性,这种荒诞性通过人性在极端情况下所展现的姿态而表达得淋漓尽致。
从故事的情节来看,小说虚构了一场具有传染性质的“失明症”。这场“失明症”从一个等待红绿灯的司机开始,并迅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蔓延全城。由于瘟疫失控,当局采取了强制隔离的措施,将所有患上失明症的人进行关押看管。然而,在选择隔离场所时,管理层的人出于经济方面的衡量,最终将这群感染者关进了环境恶劣的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内除了看管的士兵,没有任何医护人员,这群被感染的盲人无法照料自己的生活起居,因此精神病院内的卫生环境开始急剧恶化,大家甚至随地大小便,失去了为人的耻感。在失序的精神病院里,一群盲人靠一把手枪取得了称霸地位,他们控制了所有的食物,要求其余盲人用财物甚至身体进行交换。人类的文明在这一刻彻底消失殆尽,精神病院回到了弱肉强食的原始社会,盲人们逐渐向兽人转变,他们所有的欲求围绕着最底层的生存物资展开,人性的恶劣得到了极致的书写和呈现。在整个社会沦为地狱后,故事突兀地结尾了,盲人们开始逐渐恢复视力,而唯一伪装成盲人的医生的妻子却“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30)[葡]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第326页。故事以毫无缘由的“失明症”开始,又毫无缘由地结束,荒诞感弥漫始终,引人深思。
从人物形象来看,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名字,作者采用一些简单的信息对其进行指代,如医生、医生的妻子、军官、士兵、带眼罩的老人等等。这样抽象化的描写使得人与人之间模糊了个性特征,小说中的人成了一个符号,象征着现代社会里的每一个我们。这是一场可能发生在全人类身上的灾难,自诩文明的我们在极端的环境下,都有可能撕破体面的外衣,化身成为丑陋肮脏的兽。
从这场瘟疫的特殊病症来看,“失明”在这部小说中具有非常明显的隐喻特征。在正文前,萨拉马戈引用了《旧约·箴言》中的一句话:“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这句话可以看作小说的题眼。很明显,“失明症”是作者虚构的一个病症,患上“失明症”的人眼睛没有任何病变,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了,好像在浓雾里,好像掉进了牛奶海里”(31)[葡]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第3页。。白色眼疾在这里隐喻着理性的丧失,肉体的盲目隐喻着精神上的盲目。失序的精神病院回归到弱肉强食的原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代社会引以为傲的文明和理性崩坏失落,“失明”这个肉体的疾病撕扯开人类最后一块遮羞布,兽欲取代一切成了主宰,人性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暴露出最丑陋的一面。
在小说中,所有人都是“失明”的,这里的“失明”既包括真实感染了“失明症”而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中的人,同时也包括没有被感染却导致并无视一切发生的当局管理者以及看管的士兵们,“失明”在这里指代的是真正意义上精神上的盲目,他们打着隔离的幌子彻底抛弃了这群感染者。士兵们对这群感染者毫无同情心理,他们抱着“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32)[葡]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第58页。的心理,甚至随意对感染者进行射杀。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群健康人才是真正的“失明人”,他们也是导致精神病院最后沦为人间地狱的凶手。在小说的结尾,一场大雨后,失明的人逐渐开始恢复视力,医生在与妻子交谈时说道:“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33)[葡]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第325—326页。对一切袖手旁观的当局管理者以及那群冷漠的士兵就是这样一群“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虽然“失明症”的瘟疫突兀地结束了,但这只是肉体“失明”的结束,对于精神上“失明”的人而言,这场瘟疫远未结束。小说最后以这座精神病院里唯一看得见的医生妻子的视角写道:“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着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她抬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34)[葡]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第326页。城市还在那里,在这场劫难后变成垃圾场、沦为人间地狱的城市还在那里,这场精神的失明仍在蔓延,它仍然笼罩在城市上空,蒙蔽在每一个人类精神之上,只等着下次“瘟疫”的降临。
通过对比中西方这两种不同的瘟疫叙事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学更关注瘟疫的隐喻意义,作家们以瘟疫为触角探索人类更为本质的生存困境,并通过笔下人物在这种困境中所作出的不同选择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中国文学的瘟疫叙事模式则更多地体现作家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儒家精神,儒家提出的“三纲八目”即儒家责任伦理的核心内容。“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5)《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73页。,“八目”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这种责任伦理首先体现在个人品性的修养之上,其次在于“齐家”,最后生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伦理观念。梁漱溟先生曾言:“中国人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3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页。“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3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页。这样心怀天下的责任伦理观念深深烙印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独特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瘟疫叙事模式中对于史诗性、英雄性的追求,以及对于潜在英雄人物的塑造就是儒家责任伦理观念的体现,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与众不同的民族特性。
三、中西文学瘟疫叙事伦理机制比较
“所谓伦理其实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38)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4页。中国文学的瘟疫叙事伦理机制更多地表达为瘟疫与集体的关系,作家们虽然也会聚焦于个体,但集体通常不会缺席。同时,这个集体也表现为对国家这一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上。然而西方文学瘟疫叙事伦理机制更通常表达为瘟疫与个人的关系,集体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与个人的关系表现为冲突甚至是对立。因此本部分将通过具体的文本探究中西文学叙事中不同的伦理机制,并试图从东西方哲学的异质性中寻根溯源,对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阐释分析。
以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为例。虽然迟子建在后记中写道,“然而我在小说中,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39)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 254—255 页。,不可否认的是,伍连德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后半程出场,成为这次鼠疫的关键转折点。伍连德并不是一个孤立出现的人物,在他的背后是整个朝廷,可以说伍连德是集体的化身。在介绍伍连德这一人物时,作者写道:“一九○七年,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他从南洋归来,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袁世凯选中伍连德,除了外务部施肇基大人的举荐,还因为他听海军处的程璧光介绍说,林国祥是伍连德的舅舅,而林国祥是甲午战争的英雄。”(40)迟子建:《白雪乌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28页。从这个介绍就可以看出,伍连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人物,他背后牵扯的是当时整个朝廷的高级官员,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集体。同时,伍连德之所以能够带领傅家甸的人战胜此次鼠疫,集体的出场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境地,俄国控制了西伯利亚至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日本控制了大连至奉天的南满铁路。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瘟疫,在这场瘟疫背后是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日俄两国都想借插手这次瘟疫的机会,图谋更大的利益。因此,如果傅家甸的瘟疫得不到控制,日俄双方就会悉数撤出华医,彻底控制这里。伍连德身上背负的已经不仅是一场瘟疫,更是一场国家防卫战。最初,伍连德发现傅家甸的瘟疫是通过人与人进行传染的肺鼠疫时,他的观点并不被俄国医生哈夫肯接纳。与此同时,法国使馆要求自己国家的医生迈尼斯取代伍连德,出任东北三省防疫总医官。面对这样棘手的难题,是外务部施肇基顶住了莫大的压力,坚持任命伍连德主持东北防疫事务。在防疫陷入僵局时,伍连德能顺利实施焚尸的举措,也是施肇基与摄政王协同努力的结果。
因此,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虽然着力展示鼠疫来临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但是集体在小说的出场是非常鲜明的,它在小说整体中所占比例不大,然而每一次集体的出场都决定了抗疫结果的走向,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小说对于集体的描写也与其创作背景紧密关联,《白雪乌鸦》以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为写作素材,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小说对于集体的描摹具有一定的历史现实特征。
与中国文学瘟疫叙事伦理中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相反,在西方的瘟疫文学中,集体通常是缺席的,即便偶尔出场也大多呈现出负面的姿态,这在《失明症漫记》中有鲜明体现。
首先,《失明症漫记》中的管理层并非是出于方便治疗的目的而采取隔离措施,部长对于要将病人关闭四个月还是四十年完全不在乎,只需要确保他们不得从隔离区离开便可。因此,出于资金的考量,管理层下令将这群感染者关进了环境恶劣的精神病院,当局除了命令一些士兵进行把守外,没有配备任何医护人员,就这么让这些盲人在这座环境糟糕的精神病院里自生自灭。
其次,管理层在小说中没有具体的人物形象,它以扩音器的方式出场,对这群感染者进行残酷的管教,甚至制定了十五条毫无人性的规定。比如,如若发生火灾,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在未获得允许的情况下试图离开就可以被立即击毙;如果内部发生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任何外界介入,等等。从这些残酷严苛的条例可以看出,这群感染者已经被社会完全抛弃了,一场瘟疫彻底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权利。负责看守他们的士兵更是将他们视为草芥,可以随意开枪射杀。正是集体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使得这座精神病院最后沦为了人间地狱,一杆枪就能让西方人引以为豪的理性社会堕落为原始丛林。
最后,作者在小说中借管理层之口,对其宣称的集体主义以及爱国主义等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讽刺。在将感染者关押进环境恶劣的精神病院后,政府通过扩音器以响亮生硬、惯于发号施令的声音对这群人进行了训话。在训话中,政府反复强调了“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负担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为”(41)[葡]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范维信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第43—44页。。在这一段冠冕堂皇的讲话后,政府立即宣布了那十五条完全违反人性的规定,而这样讽刺的训话每天都要循环播放。作者在小说中多次用“生硬”来描述扩音器里的声音,这里的生硬不止是一种物理属性,也是一种精神向度,是对这群管理者冷血虚伪的强烈谴责,同时也是对这群管理者用来粉饰自身的所谓“责任”“爱国之心”“支援全国”等话语的无情讽刺。
中西方这两种不同的叙事伦理机制内含着东西方哲学的异质性。中国儒家文化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三纲八目”中的“八目”就是“家—国—天下”的集体秩序的建构过程。而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主要建立于“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之上,牟宗三先生曾说道:“主体和天可以通在一起,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最特殊、最特别的地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42)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2页。“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孔孟这里表述为“天人合德”,“天道”是超验性的存在,是一切伦理秩序的起源,“人道”需遵循“天道”以达到“天人合契”的境界。这也生发出了儒家的责任伦理观,“人作为 ‘天地之心’,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使人心与天道秩序相感通而连为一体,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对万物负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道义上的责任感”(43)任亚辉:《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探究》,《心理学报》2008年第11期。。因而使得“家—国—天下”这种集体主义的建构深入中国儒家文化肌理,成为熔铸在知识分子血液中的文化养分,促使历代仁人志士不断生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慨。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始终是其核心价值观。虽然按照哈耶克对于“个人主义”一词的考察,这一术语最早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并被广泛使用,但是这一精神却一直贯穿在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之中。就西方文化的发展源头两希文化而言,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还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都蕴含着个人自由、自主独立等文化因素。宇文所安曾使用“盾牌阵”这一术语对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首诗作进行解读。在阿尔基洛科斯的诗中,他将象征着公民荣誉的盾牌随意丢弃。“宇文所安‘盾牌阵’所指称的,就是把我们每个个体绑在一起的诸如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价值。”(44)邱晓林:《向上抑或向下:西方现代性思想及前卫艺术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9页。宇文所安认为阿尔基洛科斯的这首诗歌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和宣扬,它“宣布将个人和个体生命凌驾于城邦的意识形态之上”(45)[美]宇文所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程章灿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19页。,弥补了某种空白。而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进一步张扬和显现,也出现了一系列与其相关的学说,“个人自主、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和个人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西方社会中已逐渐成了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文化信念’”(46)韦森:《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东西方社会秩序历史演进路径差异的文化原因》,《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西方的这种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念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迥异,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寻求的是集体的和谐,甚至愿意为集体的利益而自我牺牲,因此“儒家的自我在诸种社会角色所构成的等级结构背景中不可避免地会淹没于集体之中了”(47)[美]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曹幼华、单丁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页。。中西方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反映在瘟疫文学中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伦理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中西文学的瘟疫叙事不论是母题的叙事流变、瘟疫叙事模式,还是瘟疫叙事伦理机制,都具有较大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中内含着中西方哲学的异质性以及中西不同的文化机制和文化肌理。因此在看待中西文学不同的瘟疫叙事时,需要将文本放置于其所处的文化意义网络和文化视野中,这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新冠疫情以来中西方不同的应对机制及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