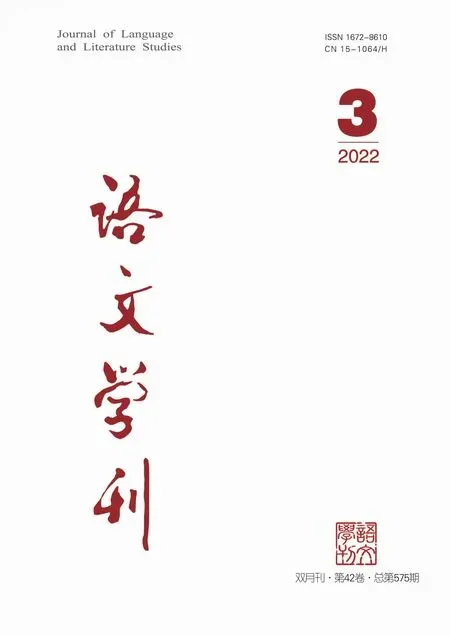论多尔小说中的社会生态学思想——以《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为例
○ 赵莹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一、引 言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AlltheLightWeCannotSee以下简称《所有》)是美国小说家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该小说2014年一经出版便收获大量好评,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并于2015年获得普利策奖。莫林格(J. R. Moehringer)评价多尔“用科学家般的眼睛观察,却如诗人般感受这个世界”[1]。斯特德曼(M. L. Stedman)认为这本书“温柔地探索了这个世界的悖论:自然法则之美以及被战争颠覆的可怕结局、人类心灵的脆弱和复原力,以及瞬间的不变性和时间的治愈能力”[1]。在故事中,一名叫做玛丽-洛尔·勒布朗(Marie-Laure Leblanc)的法国盲人小女孩和一名叫做维尔纳·普芬宁(Werner Pfennig)的德国孤儿小男孩的命运,通过收音机电磁波的牵引交织在一起。在战争中,他们相互传递力量和关怀,寻找内心的安宁与救赎。
该小说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论述,主要观点有:《所有》中蕴含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生态关怀和女性意识[2];从新历史主义角度来看,《所有》在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出文本的历史性以及历史的文本性[3];《所有》中战争主题对成长在和平时代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教化作用,同时拓宽了成长小说的研究领域[4];《所有》中体现出人性中的两大关键要素,即“同情心”和“宽恕”,彰显了人性光辉的主题[5];“光”在《所有》中作为符号所承载内涵丰富,通过其传递、接收和接受过程,传达了主人公在战争中表达出的人类共同情感[6];多尔在《所有》中以熵为隐喻,揭示出战争带来的无序状态给人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个人身份的丧失[7]。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对这一作品进行解读,本文拟做一些尝试。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理论始于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他是该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生命结束,他一直致力于书写该理论方面的著作。1970年,布克钦在其著作《生态与改革思想》(EcologyandRevolutionaryThought)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社会生态学的概念。社会生态学家认为当前生态问题根源于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源自等级制的支配结构。“人类必须主宰自然的观念直接源自人对人的支配。”[8]85社会生态学家相信,在20世纪和21世纪,除了那些由自然因素导致的灾难外,最严重的生态问题均是由于经济、种族、文化、性别等各个领域内部的冲突造成的。如果社会内部的问题得不到恰当处理的话,当今时代的生态问题便不能被人们所理解,更不用说被人们所解决。等级制度是基于命令和服从的人际关系,促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统治,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等级制的概念都普遍存在。由于等级制植根于人类的心理结构中,因此“在‘无阶级’或‘无国籍’的社会中,等级和统治仍可以很轻易地继续存在”[9]4。布克钦认为等级制是极其危险的,并驳斥了其存在的意义:“因为等级制威胁着今天社会生活的存在…… 威胁到有机自然的完整性,因此它不能继续这样支配下去。”[9]37
在《所有》中,等级制观念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令人关注:在国家政治教育学院中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两次世界大战中强者对弱者的在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双重摧残,人类对非人类自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的掠夺和利用,以及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导致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多尔通过列举等级制观念给人类社会和非人类自然所带来诸多伤痛的事实说明,只有逐步消除这样的观念,人支配人和人支配非人类自然的行为才会逐步消失,从而有助于人类走出现今生态问题频发的困境。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对作品中表现出的生态社会观、生态自然观和生态科技观进行阐释,具有很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二、多尔的生态社会观:反对支配他人
布克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而且是相对稳定的整体,即彼此需要的关系。在土著文明中,没有人支配人或试图使自身享有特权的观念,这种文明具有三个特征——“不分年龄或性别地尊重个人;惊人的社会和政治一体化程度;超越所有政府形式和所有部落和群体利益与冲突的个人安全概念的存在”[10]106。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血统、性别分布和年龄差异之类的生物学事实,将不同人类群体团结在一起,进而转变为社会机构,并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逐步被改组为等级结构[11],人类社会的等级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像命令、剥削和等级这样的词语,实际上是描述人们彼此间如何相互联系的社交称谓。”[12]216在《所有》中,多尔通过对二战前夕德国舒尔普塔的国家政治教育学院、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前线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描述,揭示出社会中上级对下级以及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形式的存在,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些等级和统治关系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在国家政治教育学院,军官和学员之间基于命令和服从关系普遍存在,“为统治而统治的制度形式很明显”[9]127。军官是上级的代表,他们向下级学员下达命令。维尔纳(Werner)作为学员之一,一直处于被命令状态。在进入该学院之前,维尔纳参加了入学考试,入学考试的选拔标准由军官们规定:“我们只会选择最纯正、最强大的人。”[1]112为了通过选拔,学员们首先要证明自己体内流动的血液是“纯净的”,即没有犹太人的血统。学员们被军官要求填写一份有关自身血统的一百多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并参加了生理学测试。在证明自身血统纯正性之后,他们还要证明自己是最强壮的,其中最残酷的一项测试是从25英尺高的顶部跳下来。患有恐高症的学员在晕倒的瞬间从高处摔下来,“胳膊先落地,伴随着柴火折断般清脆的声音”[1]115。巴斯蒂安(Bastian)是学院的一名军官,他试图训练学员践踏他人生命。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命令所有的学员将冷水泼到一个偷了牛奶充饥的囚犯身上,“囚犯的脚上锁着脚镣,从手腕到前臂都被绳子捆着,单薄的衬衫从接缝处崩开,他已经冻僵了,目光呆滞地注视着前方”[1]227,直至他被折磨致死。在国家政治教育学院中上级的统治下,下属逐渐成为没有感情的执行命令的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冷漠。
除了上级对下级的统治外,多尔向我们展示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公元前9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中总结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发起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强者总是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强大,弱者会做一些事情来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揭示出那个时代战争的逻辑——强者希望变得更强大,而弱者则不得不面对强者可能在任何时候发起的战争,以及思考如何击败强者并改变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这是人类历史的自然选择。在《所有》中,多尔通过埃蒂安(Etienne)和维尔纳的视角为我们展示战争中这种心理结构给人类身体和精神所带来的灾难。埃第安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在战场上,他目睹自己兄弟亨利(Henry)被炮弹击中并失去生命,然而在他向玛丽-洛尔的讲述中,战争夺取的不仅是自己亲人的生命:“杀死你祖父的战争导致1600万人死亡。其中有150万法国男孩,大多数比我年轻。德国一方死亡人数达200万。如果将死者排成一列纵队行进,他们走上11天11夜才能从我们的门口经过。”[1]360维尔纳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士兵。在来到前线的第一天,他看到一辆运载着囚犯的火车从他面前驶过,成百上千的男人像稻草人一样挤在车厢里,一堆尸体为他们组成一面防护墙,而那些活着的人只剩下“凹陷的脸颊、肩膀和发光的眼睛”[1]319。在强者压迫弱者的战场上,人类的生命被视如草芥,这种支配关系也进一步使人类精神蒙上阴影。经历过一战的埃蒂安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由于在战场目睹了一母同胞的兄弟在自己面前倒下,他在战后患上恐旷症(agoraphobia),患上这种病症的人在诸如公共交通工具上(如公交车、火车、飞机等)、开阔的空间(如停车场、大桥或超市等)、封闭的地方(如商店、剧院或者电影院等)、排队或在人群中以及独自一人外出等其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况下,会感到害怕或焦虑。在患者心理作用下,在这样的情形下如若产生类似恐慌或令人尴尬的症状时,自己不能够轻易逃脱或不能得到帮助[13]217-218。 在这种精神疾病的折磨下,他自参与一战之后便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强者支配弱者的战争对人类的摧残可见一斑。
三、多尔的生态自然观:尊重非人类自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人类来说,生活就像一场斗争,“但这场斗争不在于人与人之间,而在于人与自然之间;每个人都有责任承担它”[14]46。在社会生态学中,人类控制非人类自然的思想史几乎和导致支配的等级制度的历史一样古老。“随着等级制度和人类支配的兴起,人类开始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自然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存在,而且是分等级地组织起来,并且是可以被支配的。”[11]在人类观念中,非人类自然一直以来都是“低等的”,人类从非人类自然中“掠夺了许多生物世界中美丽的、有创造力的和充满活力的事物”[11]。多尔在《所有》中表现出人类对非人类自然的支配,同时思考如何重建两者之间的和谐。
在《所有》中,人类自认为“优于”非人类自然,将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看成是满足自身私欲的工具,并对它们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掠夺。一方面,多尔通过揭露人类对待海螺的残酷方式,反对人类对非人类自然中生物的支配权。热内法博士(Dr. Geffard)是一位年长的软体动物专家,将这类生物视为实现自己毕生梦想的“无生命”客体。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实验室中,他保存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数不清的贝壳,“博物馆拥有超过一万个标本,超过世界上已知物种的一半……”[1]30。虽然他对海螺很着迷,但它们对他来说只不过是研究标本,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收集大量贝壳而不是活着的海螺的原因。另一方面,多尔以煤矿的开采和掠夺为例,反对人类通过支配非人类自然中的非生物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对于人类来说,煤炭是一种提供燃料的矿藏。“地球上的巨大区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特定的工业目的或沦为原材料的堆场。”[15]60在《所有》中,多尔所刻画的德国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方圆四千英亩”[1]24,那里的人们从这样巨大的“原材料的堆场”中掠夺煤炭资源。由于煤炭的工业开采,当地环境变得肮脏不堪,由煤车、活塞和皮带形成的平稳而疯狂的生产过程随处可见。然而,在发动疯狂战争的德国人看来,挖掘矿产资源所引发的污染并不算什么,利用能源赢得战争才是一切,这便是人类掠夺非人类自然中非生物的缩影。
“从人类从中获取生存所需简单物品的生物环境这个广义层面上来看,‘自然’往往对于文字出现以前的民族没有意义。”[11]对于那时的人类来说,自然正是他们沉浸其中的宇宙。在布克钦看来,非人类自然的进化和人类一样,同样“具有自主性和灵活性不断提高的特点,以及不断提高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使有机体更加适应新环境中的挑战和机遇,并且使生物更有能力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来满足自身需求”[11],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目的论的有机体”[16]91。在《所有》中,多尔肯定了非人类自然的主体性,并消解人类和非人类自然之间的等级差别,这都有助于重建二者之间的和谐。多尔从弗雷德里克的视角出发,通过对飞鸟的描述,显示出非人类自然中生物的主体性。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是一名痴迷于飞鸟的孩子,他热衷于观察自由翱翔的鸟类,将它们视为和人类一样具有能动性的生物。在他看来,冠小嘴乌鸦比大多数哺乳动物更聪明,北极燕鸥是地球上真正的航海家,灰鹡鸰依靠自身的信念从美洲飞到非洲。非人类自然中的非生物的主体性同样也需要受到尊重。在《所有》中,“海之焰”(Sea of Flames)是一块稀有的钻石,被人类视为无价之宝,法国和德国在战争中争相追踪它的下落,但玛丽-洛尔却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将这块梨形钻石扔进大海。在多尔的描述中,“它从世界炙热的底层,两百英里深的地下走来。它是一块纯净的碳,每个原子有四个距离相等的邻居,完美地构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正四面体”[1]520。多尔尊重“海之焰”来自非人类自然的事实,并且通过玛丽-洛尔这个人物,将它的最终归宿安排在大海之中。
四、多尔的生态科技观:批判科技滥用
科技在当代人类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18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科技革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大多数人对科技创新抱着一种自相矛盾的感受,他们一方面对核灭绝充满恐惧,另一方面又向往充盈的物质、休闲和安全。”[8]107如何合理地看待和利用科技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所有》创作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在此期间,电磁波的应用是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那么,多尔是如何通过电磁波的利用,向我们展示科技的双重效果,以及他所主张的合理利用科技的途径呢?
多尔通过描述战场中人类对电磁波的使用,向我们展示科技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利弊两面。首先,电磁波的传输给人类带来精神满足和慰藉。维尔纳是受电磁波影响最大的人,他通过收音机接收的电磁波接触到自己热衷的科普类节目。长久以来,他对于煤炭的认知一直停留在充斥着繁重劳动的煤矿区以及机器作业这些层面,而收音机中的科普节目改变了维尔纳一直以来对煤炭的看法:“那块煤曾经是一株绿色植物,或许是蕨类或许是芦苇,生活在一百万年前,也许两百万年前,甚至一亿年前……”[1]48类似的广播节目中对各种事物百科全书式的讲解,使他对科学知识越发好奇和着迷,也越发渴望亲眼看到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他甚至梦想自己成为一名穿着白大褂走在实验室的高大工程师。电磁波不仅扩展了维尔纳的视野,也照亮了他的梦想。然而,电磁波也成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帮凶”。德国人对电磁波最残酷的使用莫过于在战场上,即通过“敌人”释放电磁波的位置对其进行定位,进而将他们杀害。“这是一场更干净、更讲究的空中之战,前沿阵地无处不在却又隐形不见。”[1]343维尔纳经过在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的训练走向战场,并成为德国军队通过电磁波对“敌人”进行追踪的关键人物之一。当维尔纳被派往前线时,他服务的是一个特殊技术部门,所承担的任务是搜集一切不被德国政府允许的电磁波信号。维尔纳利用他从豪普特曼博士那里学来的知识,在团队其他成员的配合下,精确定位“敌人”的具体位置,一旦发现目标,便将“敌人”击毙。电磁波在战场上成为杀人工具。
对于现代人来说,科技只是原材料、工具、机器和生产可用物体所需要的相关设备的集合[9]221。然而,科技、装备和原材料在不同程度上与巩固社会的理性、道德和制度互相联系;就这个程度而言,科技所涉及的一切都被视为一个整体[9]223。我们不能忽视科技所产生的社会矩阵,即相应的政治、管理和官僚制度以及与此保持一致的信仰体系。在《所有》中,等级制观念作用下的支配关系,是导致科技滥用的罪魁祸首。维尔纳和埃蒂安在使用电磁波方面都很有天赋,但是作为分别服务于德国和法国政府的下属,他们在使用电磁波时必须遵守命令,完全没有自主权。对于维尔纳来说,在战争之前,电磁波使孤儿院儿童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在战争期间,他逐渐意识到电磁波应用所带来的邪恶和毁灭性。但是作为下属之一,他无法自由决定是继续利用电磁波杀人还是放弃对其使用。埃蒂安对电磁波的使用与维尔纳的经历类似。他强烈渴望通过电磁波传递的收音机节目使人们的生活获益,维尔纳在孤儿院时所痴迷的便是他的节目。但是在二战期间,由于法国受到德国侵占,作为法国人,埃蒂安开始利用电磁波传递情报,致使许多德国士兵失去生命。同维尔纳一样,他无法自主决定如何利用电磁波。除了认识到等级制观念在科技滥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外,多尔还认为,现代人应当意识到“忽视技术当然不是解决方案”[8]156,并时刻谨记,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捷越多,可能带来的灾难也会越多。
五、结 语
从社会生态学视角下的三个维度,即生态社会观、生态自然观和生态科技观,对《所有》进行阐释具有很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从生态社会观角度来看,多尔反对人与人之间相互支配的关系。在国家政治教育学院中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强者对弱者的支配,使人类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遭受双重摧残。生态自然观要求人类尊重非人类自然。在《所有》中,人类对非人类自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进行肆意践踏和掠夺,海螺和煤炭等均被视为满足人类需求的“低等的”客体。为了重建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要承认诸如飞鸟和钻石等非人类自然的主体性。生态科技观批判人类对科技的滥用。在《所有》中,电磁波的传播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维尔纳便从中得到心灵慰藉,但是在战场上,它则被用来定位以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成为战争的帮凶。等级制观念直接导致电磁波的滥用。维尔纳和埃蒂安在战争期间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利用电磁波帮助自己的国家打击和摧毁“敌人”。21世纪,电磁波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更是无孔不入,这值得引起人类的注意和思考。人类对科技的态度应该是理性的,不应该忽视其对当代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快速渗透。总的来说,多尔在他的小说中传达了丰富的生态内涵,其中包括人类对社会、自然和科技的生态意识,并倡导我们要努力更加接近生态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管理世界的未来,但这种管理不仅像是象棋游戏,更像是在驾驶船只。”[17]216社会生态学希望教给我们的是找到小溪的涌流并了解其方向[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