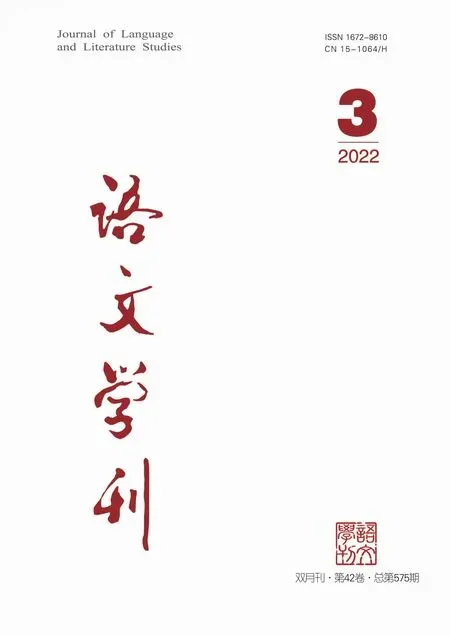汉语量词语法化补议——兼与李建平、张显成先生商榷
○ 向贤文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李建平、张显成先生在《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以下简称《动因研究》)一文中,依据出土文献统计数据提出关于汉语量词语法化的一些看法,尤其强调“双音化”才是量词语法化的根本动因。作者所做的统计对于研究量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动因研究》一文中也有一些问题,我们对此提出几点商榷意见,以请教二位学者,并对量词的产生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一点我们自己的初步看法。
一、关于《动因研究》一文的几点商榷意见
(一)关于双音化的相关问题
《动因研究》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条双音化路径:
双音化进程早在甲骨文时代便已萌芽,春秋战国至秦获得初步发展,两汉时代加快步伐,魏晋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逐渐取得绝对优势地位。
与传统研究相比,作者把双音化的萌芽时代推早到了甲骨文。为了证明这一推论,作者先引用了《甲骨文字典》的统计数据,然后总结说:
按殷代复音词的内容,大致可分八类:神祇名称、宗庙和神主名称、宫室名称、方国名称、地名、职官名、人名、时间名称。这八类复音结构大多是专有名词,而且几乎全是偏正结构,可见卜辞时代是双音词的萌芽时代。
后一部分又紧接着说:
与双音化萌芽相适应,殷代甲骨卜辞中量词也已萌芽,……
我们认为,作者的论述尚不能证明双音词和双音化都萌芽于殷代。首先,从作者提供的内容来看,殷代的复音结构具有很大的局限,因为“大多是专有名词”,所以其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宫室、地名、方国名最为典型。再从这八类结构本身看,不一定都是殷代才产生的,像神祇一类,很可能在殷代以前就已经产生,这源于古人的神灵崇拜。因此这些词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正是作者所述“几乎全是偏正结构”的一个原因。与此相反,殷代时间名称则不是很稳定,天干与地支是配合着使用的,用于记日,因其在一定范围内每天都会变,所以两者组合而成的时间名称是否是词还值得讨论。要想证明殷商时代确实是双音词的萌芽时代,就要证明在常用词系统中存在双音词,且词性不能单一,但从作者提供的资料来看,殷商时代常用词系统中的双音词是极其罕见的,这也就不能证明双音词萌芽于殷代。
其次,作者在论述中混用了两个重要概念:双音词和双音化。双音词是一种语法单位,而双音化是一种语言发展的趋势,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两者是“量”与“质”的关系。既然是趋势,就必然会对语言系统产生影响,但其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语言系统中已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双音词。双音词本身不会影响语言系统,只有双音词达到一定的数量,才会在语言系统中形成一股推力,这便是双音化趋势的产生。其外在表现是新的双音词较前代显著增加。然而从作者提供的资料来看,殷代双音词非常罕见,更谈不上双音化趋势的产生,作者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不太准确。
那么双音化趋势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董秀芳在总结了相关研究后认为,“研究表明,殷商时代语言的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的,复音化的各种构词法萌芽于西周早期”[1]9-10,我们基本赞同董先生的观点。同时我们还认为,从语法化的角度来说,类推是有方向的,即:多数→少数。因此,一种趋势在形成之初对语言的影响很小,只有等其构成基础在语言中继续发展并基本取得优势地位时,其影响力才会大大增强。双音词萌芽于西周,但是包括《动因研究》的作者自己也认为春秋时代双音词的地位才“稳固确立”,两汉时代双音化才“加快步伐”。我们认为其原因是:经过西周双音词的积累,春秋战国时期双音化趋势初步形成,促进了双音词的第一次增长,使得双音节标准音步初步建立,开始影响语言系统。直至两汉,双音词的数量已经趋近总词汇量的一半,双音节标准音步此时完全确立,对语言系统的影响大大增强,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新的双音词产生。我们的这一结论可以得到如下验证:冯胜利根据相关研究数据认为,双音短语分为“自然形成的双音短语”和“应韵律要求而形成的双音短语”,前者是双音化早期的“潜意识趋双”,后者是韵律要求变强之后的“有意识求双”。而复合词中的两大最能产的结构:偏正结构和并列结构,因为语义特点的差异,双音节偏正结构更适合前者,因此早期多于双音节并列结构,双音节并列结构则更适应后者,因此在韵律要求强化以后会反超双音节偏正结构。因为“韵律要求越强,自然短语就越不足以满足韵律要求,而能为韵律‘造双’的并列结构就越占据统治地位”[2]47-49。相关数据证实了冯先生的结论,在《论语》中,偏正式占优势,《孟子》中,两者趋同,而到了《论衡》中,并列式占据了绝对优势[2]49。同时,从词汇总量上看,“汉代复合词有了翻倍的增长”[2]33。我们认为,这正反映了双音化趋势在战国初步形成时,对语言系统的影响不强,因而表现出的是“潜意识”被动操作,而到了两汉双音节音步占据统治地位之后,这种影响表现为主动性操作和复合词数量猛增,说明此时双音化取得了语法化中类推源动力的资格。如果按《动因研究》作者所说,双音词的这两大快速增长期就不好解释了。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动因研究》的作者在文中认为“双音词在汉语中不是先在的”[3]154,并人为把殷代定为萌芽期,也就是说,殷代以前的汉语中不存在双音词。可是殷代汉语并不是最原始的汉语,而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语言,这一点学界多有论述。殷代以前的汉语面貌,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也就不能证明作者的观点,而且作者的观点似乎过于绝对化。作者在文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似乎暗含这样的观点:双音词不是先在的,而是在殷代受双音化趋势的影响而产生的。作者甚至认为,“双音节标准音步”也在殷代建立了(见后文)。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双音化在殷代形成一股趋势呢?既然双音化已然形成一股趋势,而且殷代就是“双音节标准音步”,为何殷代乃至西周,单音节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且殷代复音结构绝大多数都是偏正结构的“专有名词”?这一设想显然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古汉语的大环境是单音节为主导,外在表现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上古汉语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3]150。从这点上看,《动因研究》中作为动因的双音化趋势并不存在,这点下文还要讨论。
(二)双音化与量词
《动因研究》一文的核心论点是“双音化趋势才是诱发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3]149,但作者的论证本身就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况,下面具体分析。
1.双音节标准音步建立的时间问题。《动因研究》第二部分的第一段是本文的核心,既叙述了本文的理论基础,即“音步”理论[4]161-176,也给出了本文的核心论点和结论。为论述方便,现转录如下:
双音化是汉语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王力把双音化列为汉语语法史最重要的五个变化之一,石毓智认为双音化趋势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构词法范围,对促进整个语法系统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双音化进程早在甲骨文时代便已萌芽,春秋战国至秦获得初步发展,两汉时代加快步伐,魏晋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逐渐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随着双音化的发展,双音节音步逐渐成为汉语的标准音步。冯胜利认为由于标准音步具有绝对优先的实现权,汉语中的“标准韵律词”只能是两个音节。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在《普通话3000常用字表》中,双音词占75%以上。双音词在句法上也更为自由,单音词则受到很多限制。由于数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数词从一至十都是单音节,在双音节音步占据主导地位后,单音节数词构成的“蜕化”音步并不具备优先实现权。要适应双音化趋势,数词必须和其他成分组成双音节韵律词才能自由使用,于是量词开始了由名词等其他词类的语法化历程。考察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量词发展史与双音化趋势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双音化趋势构成了汉语量词系统起源的动因,并在漫长的历时演变中推动了量词系统的建立、发展与成熟。
作者余下的部分均是围绕此论点展开。这段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只有在“双音节标准音步”建立以后,作者所说的种种变化才能展开,不然便不存在“优先实现权”和“主导地位”,也不存在作者所述的量词“组成双音节韵律词”,即作者在后文所说“组成标准音步”(见后文引文)的功能,量词也就不会开始语法化。然而汉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双音节标准音步”,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单到双的过程,这点作者自己也承认(见上引文)。那么按作者的论述,“双音节标准音步”建立的时间即是量词开始语法化的时间点,那么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是什么?作者在下面论述殷代至魏晋双音化和量词的发展部分中并未直接说出,而是在殷代部分中这样说道:
在“Num+N”结构中,数词和名词的结合非常紧密,共同充当句子成分,但在“N+Num”结构中当数词单独充当谓语时,数词单音节的不和谐性便突显出来,如现代汉语可以说“三人”,也可以说成“三个人”,但“人三”却不符合语言习惯,必须说成“人三个”。因此,量词首先出现在“N+Num”结构之后构成“N+Num+Cl”结构,这符合汉语双音化的趋势。……虽然其语法化程度还很低,却显示了量词语法化的趋势,量词正是在这一特定语法结构中开始其语法化进程的。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的不和谐性在殷代汉语中也同样存在。(2)量词的语法化开始于殷代。作者在说明“不和谐性”时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例子,说明了结论(1),而(2)是作者直接说出的。通过(1)(2)再结合上引作者第一段,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殷商时代的标准音步就是“双音节音步”,否则根据作者自己所说,单音节数词便不会产生“不和谐性”,量词也就不会因要和数词“组成标准音步”而开始语法化。上述结论和推论正确与否,我们先来看看作者自己的描述。作者在文章的第四部分第二节这样说道:
两汉时代,随着双音词在词汇中优势地位的初步确立,双音节作为标准音步也基本确立,单音节数词的使用逐渐不再自由,需同量词组成双音节标准音步才能更为自由地充当句子成分。但量词的发展相对滞后,绝大多数名词还没有专属量词,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方式:一是采用拷贝的方式,但拷贝量词有很大的局限,一个名词使用一种量词很不经济,大量同形同音现象模糊了名、量两类词的界限。另一种方式是采用泛指量词。
这一段的论述与前文明显不统一,表现在:(1)前文论述表现的是双音节标准音步在殷代已经建立,因而殷代单音节数词“不和谐”,量词才“开始语法化进程”。而这里却明确说明双音节标准音步在汉代才确立,单音节数词此时才“不再自由”,也就是说,两汉以前单音节数词使用自由,不存在“不和谐性”。(2)前文说量词在殷代开始语法化进程,与词汇的双音化“保持了很强的一致性”[3]148,这里却说“相对滞后”,这个“相对滞后”的主体明显是指“词汇的双音化”,因此又产生了另一个矛盾。其实上文的结论(1)与推论明显有疑问,这点在(一)中已经说过了。此外,作者在文章中以“书面语相对于口语总是趋简”[3]151,153推测口语中的双音词多于书面语,这个观点似乎靠不住。口语重交际,以简洁、明了为原则,书面语重描述,以详细、精确为原则,正因为如此,口语中多短句、独词句和省略,而书面语正好相反。
综上所述,《动因研究》一文中,作者对“双音节标准音步”的建立等问题,存在前后不一的描述,我们认为其根源可能在于作者未能充分认识到(一)中所说的双音词的产生是双音化趋势形成的基础,二者是“量”与“质”的关系这一点。语言系统中的双音词如果是少数,便无法形成影响其他语言成分的力量,也就无法形成双音化趋势,更不用说“双音节标准音步”的确立和“占据主导地位”了,《动因研究》的作者显然将三者混同了。双音词萌芽的同时,双音化趋势也萌芽,“双音节标准音步”也建立,此时量词就要与“双音化萌芽”相适应。那么是什么原因一定要使量词在殷代与一个自身都是极少数的双音词相适应?同时,量词的发展和双音词的发展是两种语言现象,即使真如作者所说具有“高度一致性”,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一定是前者去适应后者而不是相反,也不能排除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这种情况。因此,《动因研究》中的种种设想缺乏理据性。
2.拷贝量词与泛指量词的相关问题。上节已经谈到了《动因研究》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冲突。单就第四部分来看,也有一些前后不一的情况。这一部分是讲拷贝量词与泛指量词的产生原因及功能的,我们先将作者的主要观点转录如下:
(1)二者(指拷贝量词和泛指量词)表量、分类、修饰等功能都很弱,只有同数词补足为双音节的标准音步才是这两类量词的根本语法功能,其发展历程正可以充分证明双音化趋势是量词系统建立的根本动因。
(2)从汉语来看,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与甲金文时代就开始的双音化趋势是矛盾的,而这种不适宜性构成了变化产生的动机,不适宜的形式有必要做出调整,即用音节进行调剂。改变基数词单音节形式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重复前面的名词,组成数名结构共同修饰前面的名词,即“N+(Num+N)”结构。
(3)两汉时代,随着双音词在词汇中优势地位的初步确立,双音节作为标准音步也基本确立,单音节数词的使用逐渐不再自由,需同量词组成双音节标准音步才能更为自由地充当句子成分。但量词的发展相对滞后,绝大多数名词还没有专属量词,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方式:一是采用拷贝的方式,但拷贝量词有很大的局限,一个名词使用一种量词很不经济,大量同形同音现象模糊了名、量两类词的界限。另一种方式是采用泛指量词。量词“枚”由于其特殊的语义基础迅速崛起,解决了双音化趋势与个体量词缺乏的矛盾。
同时,作者引用李宇明先生的观点,认为拷贝量词的另一个功能也是解决“个体量词”匮乏的矛盾[3]156。从以上作者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拷贝量词与泛指量词的出现均是为了调节单音节数词与双音化和个体量词缺乏两者的矛盾,而根据作者自己的论述,拷贝量词出现于殷代,而第一个泛指量词“枚”出现于汉代。那么一个问题是,既然这两个矛盾在殷商时代就有,为何在经历了拷贝量词和作者自己所述春秋战国量词系统的初步建立之后,在两汉又再次产生?此外,既然拷贝量词的方法存在作者所说的种种缺陷,为何在殷商时代采用此法解决两大矛盾而不直接采用泛指量词解决?且拷贝量词的存在时间从殷商一直持续到西周,而且,作者所举补足音节的例子为《小盂鼎》:“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很明显,此例并不能证明拷贝量词的功能是为了补足音节,因为被拷贝的量词“人”“牛”“羊”前均是一个多音节“系位组合”[5]46,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双音节,无需再补。
此外,根据作者自己的论述,殷代“N+Num”结构中数词单独做谓语时因单音节而产生不和谐性,从而加上量词组成双音节标准音步,即“N+Num+Cl”,而后“Num+Cl”被重新分析为“前面名词的修饰语”,后来移前[3]156。也就是说,“Num+Cl+N”中“Num+Cl”是后面名词的修饰语,重新分析前是谓语。但是“修饰语+名词”的计数结构先秦以“数+名”结构为主流,此结构大多本身就是双音节的,而且作者自己也认为,“在‘Num+N’结构中,数词和名词的结合非常紧密,共同充当句子成分”[3]156,然而,“Num+N”结构最终消失了,被“Num+Cl+N”结构所取代。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既然补上量词是为了形成标准音步,那么当“N+Num+Cl”成立之时,它与“Num+N”结构分工明确,即“名词+谓语”和“修饰语+名词”,而且一个计数一个计量,又都符合双音节标准音步,何以后来“Num+Cl”部分由谓语变成了修饰语而移前?且移动后的“Num+Cl+N”较之“Num+N”反而不符合“双音节标准音步”了。其实,“数+量”之所以移动不是因为双音化,而是因为句末普通重音。
最后,我们认为,冯胜利提出的相关原则对上古汉语韵律研究十分重要。主要有:(1)上古汉语的最大音节结构为CCCMVCCC,最小为CVC(C=辅音,M=韵头/介音,V=元音),属于结构复杂的重音节,可以独立构成音步,因此上古汉语是由单音节中的两个韵素构成的双韵素音步[2]38。(2)由于复辅音和韵尾辅音的丢失,上古汉语重音节结构消失,使得中古汉语单音节无法独立构成音步,因此,双音节音步取代双韵素音步以弥补其失,“这就是双音化的历史来源”[2]39-40。(3)“到了战国,单音节词语已经无法独立,凡需音步者,均需双音节。”[2]40,132(4)“双音节音步的建立和韵律构词法的完成,当在两汉前后。”[2]50从以上规则我们可以得知,汉语音步经历了由单音节到双音节的转变,战国越往前,单音节越占优势,单音节词独立充当句法成分就越自由;而到了战国自两汉,双音节音步逐步建立,单音节词不再自由。因此,《动因研究》一文的相关结论要想成立,必须证明甲骨文时代,汉语“重音节”已经不存在,汉语的双韵素音步已经解体,单音节词不再能自由充当句法成分,需要凑足双音节,然而根据前文所述,这是违背汉语发展史的。因此,双音化并不是量词产生的根本原因。
以上我们总结了《动因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而分析了由这些问题带来的种种矛盾。下面我们将简要讨论我们对量词发展的一点看法。
二、量词的产生与双音化
量词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我们认为,不同种类的量词产生的情况不同,有必要对量词进行分类研究。量词大致可以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前者比后者的产生早很多。殷代汉语中的名量词大致有三类:容器量词、集体量词和“拷贝量词”。对于三者的产生,姚振武认为:
集体量词,容器量词的产生与人类的基本活动密切相关,例如液体,如果要计数,仅仅用数词与个体名词直接结合的方式是不行的,非得通过称量的方式才行。例如“鬯十卣”这个“卣”就非有不可。群体,如果要计数计量,也同容器量词一样。如“贝十朋”这个“朋”也非有不可。当一个语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度量衡量词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唯独计数天然个体,一般数词与名词直接结合就能完成,并不一定要个体量词。个体量词只是汉语以及其他汉藏语系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6]122。
从这个角度来说,容器量词与集体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是人类计量活动的需要,与双音化趋势无关。在殷代,液体计量和集体计量的主要格式是“名+数+量”,如“鬯十卣”“贝十朋”等,这必然会影响到天然个体的计量。因此姚振武先生认为,“拷贝量词”的产生是受类似上述格式的类推,在“名+数”结构后补上一个量词[6]124-125。我们赞同姚先生的观点。同时,我们还想补充一点,拷贝量词中有的词使用得更加频繁,因而词义容易泛化,如“人”,既可以用于“人十人”,又可以用于“羌十人”,此类拷贝量词的量词性更强,可视为个体量词的雏形。此外,与其他词类相比,量词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其丰富、兴替和完善,除了语言系统本身的原因以外,社会原因也必须考虑。量词的两个大发展时期是春秋战国和两汉,而前者更是量词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裘锡圭认为,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的逐渐动荡、战乱频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字逐渐散落到民间”[7]51-52,这正是春秋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社会动因,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此种社会环境同样会推动语言加速发展。在此社会背景下,计量需求自然会增加,其直接后果便是量词数量的快速增长。根据姚振武的研究,个体量词在春秋战国时期获得大发展,数量大增[6],同时,产生了类似动量词的“终”“发”等[6]168-170。因此我们认为,量词产生的外因是人类的计量需求,因为对不同物体的计量需求大小不一,不同种类的量词产生也就有早有晚。容器量词、集体量词产生最早,而个体量词因为有“名+数”格式的存在而产生稍晚,是受由容器量词和集体量词形成的“名+数+量”格式的类推而产生的,这也是个体量词产生的内因。且个体量词经历了逐渐成熟的过程。同时我们认为,双音化趋势的作用只在于促进“名+数+量”结构中数词和量词结合得更紧。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说过,春秋战国时期双音化趋势才初步产生并开始影响语言系统,而此时个体量词早已产生。史存直[8]89、张玉金[9]19都认为,殷代已有专用的个体量词“丙”,如“车十丙”“马十丙”,西周又产生了“匹”[8]89“辆”[8]89“伯”“田”“夫”等[6]127-128新的个体量词。同时,从殷商到春秋战国再到两汉,新旧量词也处在不断兴替中。此外,西周容器量词的使用已经非常严格,出现大量的“名+数+量”结构[3]150。因为语义上“数”与“量”更近,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双音化趋势的推动下,“数”与“量”开始融合,并最终前移。
最后,想对“数+量”移位作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初步设想。以往对此问题的论述多是从句法和语义的层面展开,我们认为,韵律层面同样要考虑。上古“名+数+量”结构中,“数+量”充当谓语,当有动词出现形成“动+名+数+量”时,形成连谓结构。而根据冯胜利“古汉语的基本词序是SVO”[2]126,这和现代汉语一样。而汉语的普通重音在句末,是由核心动词指派到其右边的论元成分上的[2]82,89-91,且动词后不允许有两个非轻读成分[2]89。因此,在“动+名+数+量”中,普通重音由动词指派到名词上,但是“数+量”结构一般不能弱读,由此造成“轻+重+重”的情况。按韵律规则,“数+量”必须被“删除”,然而语义上不允许,因此,一个两全的办法是作为修饰语移动到动词之后、名词之前的位置,因为普通重音只对句子的基本成分即“主、谓、宾、补”起作用,不对修饰成分即定语、状语起作用[2]91。“数+量”结构因为具有类似形容词的性质,因此前移做名词修饰语不至于影响语义。我们认为,这是“数+量”前移的韵律动因。姚振武根据出土金文材料,认为“数+量+名”结构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战国大为丰富[6]161-163,从其所举例子来看,大部分为“动+数+量+名”结构[6]161-163。“数+量+名”结构的完全确立当在魏晋南北朝,而西周至魏晋正是句末普通重音逐渐强化直至完全确立的时期[2]129-137,因此在时间上也吻合。
综上所述,量词产生和丰富的真正动因是社会发展所引起的计量需求,这也是不同时代大批新旧量词不断兴替的内在动因。双音化趋势在春秋战国时代才开始形成并逐渐影响语言系统,其作用只在于加速“名+数+量”中数词与量词的融合,与量词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
三、结 语
本文针对《动因研究》一文中相关问题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商榷意见,简单概括如下:(1)双音词、双音化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双音化趋势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其作用只在于促进数词与量词融合成一个整体,与量词的产生没有直接关系。(2)量词产生的外因是社会发展产生的计量需求,这也是新旧量词兴替的动因。个体量词产生的内因是容器量词与集体量词的类推。不同种类的量词因计量需求的不同产生的时间也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3)普通重音是“数+量”移前的重要动因。限于水平,我们的文中不免有错误和疏漏,还请两位作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