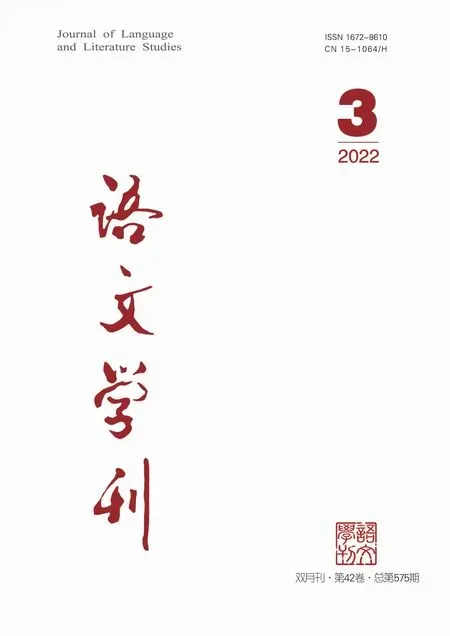《文心雕龙》生态论之时空意识探究
○ 徐超 胡红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0)
《文心雕龙》是研究文学创作规律的一部理论专著,而文学创作必然会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细读《文心雕龙》中的许多章节都有涉及这一问题,而《物色》篇更是就此进行专题探讨。针对“物色”一词的解释,学术界众说不一。曹虹先生认为,“物色”一词“不仅意味着有关物象的空间形态,而且还必定包含季节性或时间性的特质”[1]1。其不仅是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是自然景物在时空中活泼的样貌,是时空流变中生展的自然景物。“时空观是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观点。时空观念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43刘勰生态观中的时空意识在以《物色》篇为代表的一系列篇目中得到生动呈现,其并非静止,而是与主体生命共融并处于动态发展中,呈现出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
一、生命审美与生态化的融通
魏晋是继汉代“儒学治天下”后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朝代。汉朝的灭亡打破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格局,汉末动荡的时局以及司马氏一族黑暗的统治,使一大批失意士人群体渴望在精神上寻求超脱。此时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的道家思想开始复兴,佛教开始兴盛,玄学清谈流行,人们开始以气性和才情去品评人物,充分发掘人性之美。这种风气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突出性表征,是作家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3]152-158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站在作家角度,对主体生命价值进行思考。《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4]1,刘勰认为,文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体现,而对文章的创作主体,则以“惟人参之,性灵所钟”赞美之,其中“性灵”一词将作家这一创作主体提升至天地本体的崇高地位。
刘勰的主体生命意识具体展现在对于文学与作家之间关系的探寻中。《养气》篇,刘勰从作家的生命维度对“气”进行观照。《情采》篇,刘勰强调作品中的情感表达,重视人的情感。《才略》篇,刘勰集中论述从虞、夏、商、周一直到两晋时期九十多位重要作家的才华,并注意到每位作家身上的独特个性。《知音》篇则从文学鉴赏与批评角度,对鉴赏者因自身喜好偏爱某一类作品而摒弃其他作品的现象,提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4]517,需以博观的眼光去品评。“魏晋人的价值观已由汉代以用人重道德实用价值追求向精神价值追求方面转变,性情、才智、美感构成了魏晋人对个体人格肯定和追求。”[5]117-122刘勰对诸如“气”“情”“才”等与作家自身密切相关的范畴进行深入阐释,是其主体思想意识觉醒在文学评论领域的反映。刘勰所具有的主体生命意识使其注意到文学艺术的形式与生命机体的相通性,这与苏珊·朗格所提出的“艺术是一种生命形式”在价值旨归上有着一致性。“如果要想使得某种创造出来的符号(一个艺术品)激发人们的美感,它就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6]43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同样认同并重视人的生命性和人类所具有的真实情感,并肯定人类情感表达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魏晋时代风气使人在体认自身生命之美的同时,亦开始注意到自然山水所体现出来的生生之美。魏晋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时人独特的山水审美意识。魏晋士人钟爱山水,这种亲近自然的转向,外在表现为地理空间的逐步扩大,内化为士人胸怀的进一步开阔。从最初封闭性的宫廷走向七人小型聚会的竹林,再到社会群体性的兰亭赋诗,至陶渊明开始真正生活于自然之中。“自南朝始,中国士人对于山水的接受,逐渐由理入情,以情之所需,情之所好,来体貌山川。”[7]224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士人普遍将自然融入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形成自觉的创作意识。此时大量涌现的山水题材的文学作品,“以玄对山水”的色彩逐渐减退,取而代之的是以审美的眼光对山水。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刘勰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1,吸纳道家“道法自然”之论,认为“自然”是“道”之根本特性,并肯定主体“自为”之性情与“自然”的内化关系。刘勰的生态观中将主体生命意识与自然进行了有机融合,并在其文论中得到诗意化呈现。
二、刘勰生态观的时间意识
时间,是人们感受自然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中国古代,‘时’或时间并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只是作为时间概念的工具性表达,而同时包括了对时间变化的文化认知、价值评判和感性经验。”[8]74这种对时间变化的认知,就是所谓的“时间意识”。刘勰生态观中的时间变化,有以下两种形态。
(一)春夏秋冬的流转
早在先秦思想中,“时”就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生态学意义的范畴,而四季变化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们感受到的时间现象。《诗经》中的农事诗,就反映了当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诗经·风·七月》就有“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句,体现出当时庄稼人对于季节变化特有的敏感。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非常注重时令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早期农耕文明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朝代更迭的不断演化,到了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诗作中,人不再依附自然而存在,并显露出独立的主体意识。《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屈原在季节“代序”的书写中,流露出“美人迟暮”的惶恐与感伤。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大多还停留于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状态,汉代《乐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就已注意到自然之物对于人心的感召作用。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主体思想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于自然与人心的交感互动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西晋陆机《文赋》“悲落叶之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就注意到季节变化与人的心情的对应关系。随四时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属于物候学所讲的“物候”。所谓“物候”,如竺可桢先生所言,“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9]14。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直承陆机的“四季言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4]493谈及物候在每一季,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姿容,这些变化往往能被作家的机体敏锐察觉。作家的生命情感,也会随着自然的变换和时间的推移,时而忧郁时而喜悦,时而肃穆时而欢快,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情韵。钟嵘《诗品》中“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以及唐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四季更替,春华秋实,斗转星移”之论,皆与刘勰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写景语词的发展
作家对于景物的感知,如何在创作中得到生动呈现,就涉及文辞运用的问题。刘勰《物色》篇谈到作家如何描写自然之景,就体现其文艺生态观。“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点明文章创作的要领。刘勰列举了《诗经》中描写景物的例子,“‘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4]493。诸如“灼灼”“依依”为双声叠韵词,虽然简洁,却能够“瞻言而见貌”,形象展现景物之特征。刘勰的生态观强调自然是文学创作的内在核心,更是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方式,作家在创作中应自然而为,不可过分追求语言的雕饰。《诗经》所具备的写作风格则契合刘勰所推崇“以少总多,情貌无遗”[4]494的宗旨,即虽然外在自然之景纷繁复杂,但作家需要以简要的文辞最大限度展现事物的情貌。此外,刘勰认为作家受自然感召而萌发创作冲动时需处于“入兴贵闲”[4]494的状态,这种心境具有“审美主体性”特征,即非功利的价值取向,往往能够使作家文思泉涌,而不是陷入一种闭门觅句的桎梏中。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目中,如《文心雕龙·养气》“从容率情,优柔适会”[4]456、《文心雕龙·通变》“长辔远驭,从容按节”[4]331,刘勰多次对这种悠闲从容的心境进行论述。由此可见,刘勰生态观承续了中国传统艺术人生精神,反映出对自由及纯粹化审美体验的向往与追求。
刘勰关于写景语词的论述,是针对当时文坛风气所发。齐梁文坛相继出现了永明体、宫体诗等一系列崭新的文学形式,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过分追求文辞的华艳,忽略事物的本真内涵。刘勰举出司马相如创作汉大赋的例子“及长卿之徒,诡势瑰生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4]493,暗喻那些刻意描摹山水之貌,而导致文章徒有其表之人。实际上,刘勰对于刘宋时期作品重视自然、写景真切的优点是肯定的。对于山水诗集大成者谢灵运,史书中有“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赞美(《南史·颜延之传》)。但谢灵运之后涌现的模仿者,刘勰认为他们只是把精力放在单纯的描摹上,难以创作出有深度的文章。因此,刘勰站在文学时代发展的高度,主张作家具有创新意识,对于像《诗经》《楚辞》等写景模范之作,要善于抓住描写之精髓,达到推陈出新的境界。刘勰的创新理念建立于“通变”意识的基础之上,“变则堪久,通则不乏”[4]331,他认为作家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长处并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进行融会贯通,以达到新的境界。后世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黄庭坚所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无不和刘勰文艺生态观所引申的内涵相契合。
三、刘勰生态观的空间意识
空间意识原本是一个建筑学、设计学方面的概念,后来被引入到文学、影视等艺术领域。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认为,“中国诗人、画家确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而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游心太玄’”,因此,中国诗画里所表现出的空间意识,是“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10]249-250。刘勰生态观继承诗意化传统,其节奏化与音乐化特征突出表现为主客体的交互体验以及“江山之助”地理功能论。
(一)主客体交互体验
刘勰所追求的是一种具有审美特性的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这种思想契合于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畅想。而在中华传统美学中,可溯源至庄子美学。庄子美学把人与自然等同起来,通过人的自然化提升了自然的地位,自然成为与人平等的主体,二者处于一种融合不分的境界,类似于艺术琴弦上“谐振”的理想状态。刘勰从主体实践层面将这种主客体关系具体形象化,《物色》篇中所描绘的“目既往还,心亦吐纳”[4]494,在主客体的交互体验中,自然中的景物所传达的讯息被主体捕捉到,随之产生强烈的心灵体验,并进而产生创作冲动。
在刘勰的生态观中,自然不仅仅只是满足人的生存之需,而是成为人类所欣赏的对象。刘勰的自然观中蕴含着一种生态主体间性思想,它融合了道家的“自然之道”、禅宗的“无我”“无物”的观念,而走向极致化。“主体间性哲学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定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通过二者的交往、对话、沟通、融合而达到审美的境界。”[6]81-84在这种体验中,主客体之间产生“情以物迁,辞以情发”[4]493式的审美移情,即主体受到外物感召,并将情感投射于外物,进而主体的生命内涵也随之衍射到了自然万物。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说道:“在聚精会神的观照中,我的情趣与物的情趣往复回流。有时物的情趣随我的情趣而定……有时我的情趣也随物的姿态而定……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回环震荡。”[11]163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人们超越现实功利世界对人精神的束缚,实现由生活层向审美层的跃进与升华。主体在这种忘我的境界中,积极地体验生命本真的含义。这种审美的生存方式虽然带有乌托邦性质,但却是一种最自由、最与生态契合的生存方式。
刘勰生态观中,人与自然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对于《情采》篇中言及的主体情性之自然,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及情、物、采三者关系:“故采之为物,虽以状物写象为职,而其用乃在明情表思。且其至者,虽似纯状物象,亦及表达情思。”[12]106文采要通过状物写象来表达感情色彩。《物色》篇中,刘勰则将“物”具体化,认为文学创作的过程与作家发现自然之景、探寻自然之境密不可分,主观之情思须与客观世界实现和谐统一。对于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的距离问题,刘勰在《神思》中提到“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4]295,追求的是一种主客不分的状态。以刘勰为代表的生态思维认为自然万物各具情性,作家只有打破物我界限之鸿沟,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意蕴,才能够创作出佳作。这种思想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光是在文学领域,在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同样也适用。苏轼结合自身绘画创作实践,提出“身与竹化”命题,“化”意为创作主体将自己的感情、精神、生命完全对象化,是主体对审美对象展开的最透彻的审美体验下,身入化境忘我的超越性再现。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融合,才能实现艺术上的浑然天成,而中国历代文人所拥有的根源于内心深处的蓬勃的生命精神,才是真正沟通人与自然的根本所在。
(二)“江山之助”地理功能论
在刘勰的生态观中蕴含着对自然作用于人的思考。“山水所展现的自然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所展现的自然万物的和谐的整体感,常常引起关于宇宙万物、关于生命的种种思考。”[7]181在活动区域不断扩大的演变中,文人的思想在与自然的共处中得到沉淀。刘勰在对文人与自然的不解之缘进行深刻体悟后,创造性提出“江山之助”这一论断。
“江山之助”的首要之义是肯定自然对文学之助益。“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4]493刘勰认为屈原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具有生命情韵的诗篇,得益于楚国独特的自然地理风光。关于自然的具体价值,刘勰将其称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4]494。自然中的山林原野,是为文构思的丰富宝库。由此可见,刘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倡导作家要走进自然,在亲历性的生命体验中进行文学创作。“江山之助”论本身所营造的极具空间艺术的空旷感,主体以开阔的胸襟与气度接纳自然中的万物,徜徉于其中,尽情受用自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并应用于创作中。“艺术的境界,既使心灵和宇宙净化,又使心灵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脱的胸襟里体味到宇宙的深境,一呼一吸,微笑相伴,悦怿风神,悠然自足。”[13]97纵观历代文人作家的创作实践,他们往往能够在自然中获得创作灵感。“物色之动,心亦摇焉”[4]493,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作家心灵受到摇曳与启发,如清代厉志所论“须山水灵秀之气沦涣肌骨,始能穷尽诗人之真趣”(《白华山人诗说》),作家的人格性情得到净化,才能成为得山水之趣的“真诗人”。
“江山之助”承载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情韵。“物色尽而情有余,晓会通也。”[4]494自然所具有的地理环境特征会随时间更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但其所具有的生命形态却是在循环往复的轮回中不断重生。正如同“一切景语皆情语”,历代作家虽处不同的时代环境,其受自然感召而在作品中呈现的情态各异,但若通晓情变便可以创作出好文章,这是刘勰生态观中“通”的意识体现。这种融会贯通的精神同时还体现在不同文风的交融上,与刘勰处同一时代的庾信,前期在南朝度过安定的生活,此时他所创作的以宫体诗为代表的诗文作品,多有供君王娱乐的性质。而梁朝因侯景之乱濒临灭亡,庾信受梁元帝之托出使长安,却因江陵沦陷而不得南归。“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周书·庾信传》),地理环境的变迁使得庾信的诗文融合了南北文风的长处,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褪去前期的浮华迷艳,而呈现出一种劲健苍凉的笔调,艺术上臻入成熟之境。
刘勰的“江山之助”论在后世也得到了深化。特别是在唐宋旅游之风兴盛后,为文人站在新的高度认识江山与作家的关系创造了条件。陆游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丏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翁方纲《诗境篇题放翁书石本后》亦云:“江山信为诗境开,我酪江山酒一杯。吁暖放翁一代才,江山气尚泄不尽,吁磋诗境易有穷止哉!”由此可见,“江山之助”论具有深远的辐射性影响,在后人不断的阐释生发中,将其中蕴含的传统“天人合一”的意识推向高峰。
四、时空融合的生态化思辨
刘勰生态观中的时空融合特性具体表现为“神用象通”的意象性思维,即在论述一个文学道理或文学现象时,经常会用自然中被时序赋予动态化生命表征的物候来阐释一个较为抽象的理论。“神用象通”的产生机制为“感物”,即主体神思与物象接触而感通,这与传统中以“象”喻“意”的思维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意象”,始见于《周易·系辞传上》中的“立象以尽意”,意为以“象”暗喻某种天地运转、生命变迁之“意”。而“神用象通”的意象性思维在刘勰生态观中则体现为以“自然之道”求解“人文之理”的探索与尝试。
刘勰以自然之物阐述文学的具体例子,可分为作家创作、文体特征、文学道理三类:
作家创作。《神思》“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4]295,将作家在大自然中所获体验来解释作家在创作过中的构思状态。
《事类》“皓如江海,郁若昆邓”[4]413,刘勰以“江海”“昆邓”喻经书典籍中丰富的文辞义理,意在要求作家自身需具备较好的文学素养,对古往今来的著述无所不知,能够在创作中旁征博引。
文体特征。《议对》“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4]267,刘勰以“风”的广阔致远和“水”的浩荡而不泛滥来比附对策的特征。《诠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4]80一句,则是刘勰所提出关于赋的创作要求,若作赋之人只追求文采,则会使赋丧失其勉励鉴戒的功能。
文学道理。《定势》“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4]339,以湍急的水流不泛涟漪,枯死的树木不成浓阴这一自然规律来说明各种文体都有着确定的态势,并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
《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4]346一句,形象地论述了文采与文质之间的关系:文章需要文采,但需建立在情理之上,而作家需要把握文章的本质。有关文采更为细致的论述,是《丽辞》中“炳烁联华,镜静含态”[4]385。“联华”意为并蒂之花,刘勰以花的光彩鲜明来喻文章的均衡相称之美,若作家恰当运用对偶,会使文章增色不少。
刘勰在《通变》篇中论述了文章所呈现的面貌,并提出:“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4]330以草木不同的生长情况来譬喻文章经由不同创作主体而风格各异的现象,并认为诗、赋、书、记等各种体裁有着特定的体制和规格要求,但诸如文章的文辞气力等外在因素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程式,可以进行变化创新。
这种生态化思辨脱胎于儒家“比德”思维,具有“中庸之道”的中和内涵。《镕裁》“辞如川流,溢则泛滥”[4]356,认为写文章不能只是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是需要认真衡量如何增减,使文章免受其累。这种观念根源于儒家所倡导的文质观,刘勰所追求的是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之文”,即“文质并重”,是事物发展的协调状态。《声律》“声得盐梅,响滑榆槿”[4]365,刘勰以自然之物来比喻文辞声律上所具有的美感。“盐梅”指一种咸酸调和之感,而“榆槿”意为两种皮有滑液的植物,用以调味可使食物滑润可口。人的口味各异,有人喜咸,有人喜酸,声律上的咸酸柔滑之感是一种“中和”的理想状态。刘勰之后,钟嵘《诗品》中提出“滋味说”;唐末司空图集前人之大成,创造性提出“以味论诗”的系统性理论,主张诗歌追求“味外之旨”,进一步深化该理论谱系。“《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文化选择是道(玄)、儒、佛的三栖相会,是亦儒亦道亦佛又非儒非道非佛,鲜明地呈现出复杂宏博的精神面貌与人文内涵。”[14]48刘勰的生态化思维,继承儒家文学社会价值观,但并没有只望一山之隅,而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去接纳具有进步性意义的理论精华。例如《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48,刘勰将道家思想中崇尚自然的主张融合进文论体系中,肯定文学与个人情志、自然三者的关联。由此可见,儒道思想的有机融合使刘勰的生态文论观摆脱了传统思维的厚重单一,使其内蕴深广且具清新脱俗之感。
刘勰“神用象通”的生态化思辨实现了自然与文学之间的生态关联。自然万物代代不穷,生命轮回永不停止,意与象、物与创作主体融合为一,生生不息。这种感性体悟的意象思维不逊色于西方严密推理式的思辨,从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律得到启发和熏陶,更深刻探寻到文学创作的生命理路。刘勰以“自然之道”求解“人文之理”,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世界因此成为人文的世界。在这两重世界的生态融合里,自然之物经由人的主观情思构造,实现与文的异质同构。
综而言之,在刘勰的生态观中,其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往往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时空交错的美感。正如杜维明所说:“人与自然是声息相通的,他们永远相依为伴。”[15]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自然与人深情勾连起来,展现了主体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其生态观中蕴藏的无限蓬勃生机,给当下的生态文艺学建设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