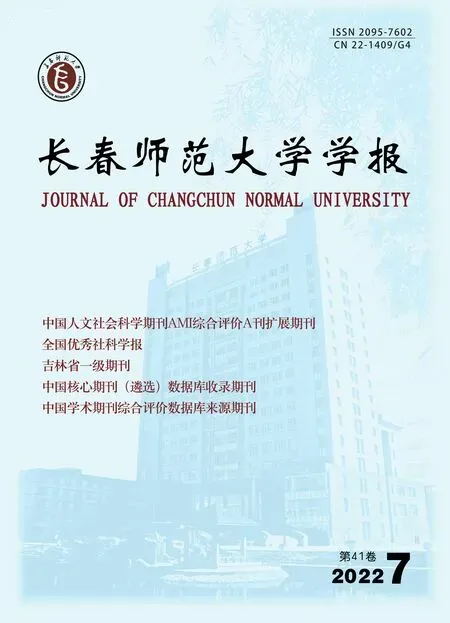“黄祸”语境下的傅满洲角色塑造:一个关于刻板印象与陈规定型的迷思
黄琼慧,陈 矿
(1.广州华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1399;2.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20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家萨克斯·洛默(Sax Rohmer)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虚构的华裔反派人物——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近百年以来,这个角色在电影、电视、广播、连环画中都有广泛的亮相,并已然成为邪恶的科学怪人与犯罪天才的角色原型,甚至连他的标志性胡须也成为一个别致的能指。
傅满洲的形象在小说及其后各种媒介形式的改编作品中都有鲜明体现。他最具代表性的外貌特征在于狭长细窄、末端逐渐变尖并一直下垂到下巴的胡须,甚至牛津词典都将“Fu Manchu mustache”一词收录在内,足以见得这一特征强烈的标出性。《阴险的傅满洲博士》(TheInsidiousDr.FuManchu)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想象有这样的一个人吧:身形高挑瘦削,束肩敛息,宛若一只饥肠辘辘的老猫;撒旦般的脸庞上有着莎翁式的眉宇……他神机妙算,坐拥着空前绝后的技术资源……想象一下这个可怕的存在,你脑海中便会浮现出傅满洲博士的形象,‘黄祸’的概念便也化身为一个具象的人物。”[1]
本文致力于探讨傅满洲的角色塑造背后存在的社会性根源,即由刻板印象催生出的“黄祸”观念;通过梳理“黄祸”这一隐喻的思想脉络,进一步审视傅满洲及其他西方文艺作品中的华人形象创作由此受到的影响;并指出“黄祸”的种族主义恐慌在当下并未消散,呼吁文艺创作应避免陈规定型的负面倾向。
一、概观“黄祸”:从色彩隐喻到种族主义论调
“黄祸”(Yellow Peril),常常也被称为“黄色恐怖”(Yellow Terror)或“黄色幽灵”(Yellow Spectre),是一个充斥着种族主义思想的色彩隐喻,也是殖民主义仇外心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黄皮肤的东亚人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的生存威胁。罗斯洛普·斯托达德(Lothrop Stoddard)在其论著《反对白人世界霸权的颜色浪潮》(TheRisingTideofColorAgainstWhiteWorld-Supremacy)中指出,作为一种对威胁的心理文化感知,作为仇外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基于臆想的东方“黄祸”恐惧是模糊的,它更多针对的是种族而非国家,是来源于对西方世界对岸的一群无名的黄种人的不祥恐惧;“黄祸”的意识形态将东亚人与“类人猿、矮子、原始人、疯子和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等意象并置。[2]
据学者考证,这种偏见起源于公元前499年古希腊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出现了对东方有色人种的文化表征。几个世纪以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地理扩张进一步将东亚纳入“黄祸”的范畴。[3]从词源看,在19世纪末,来自沙皇俄国的社会学家雅克·诺维科夫(Jacques Novikow)在其论文《黄祸》(LePérilJaune)中首创了这个术语。从社会动员实践来看,德意志皇帝凯撒·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利用“黄祸”这样的种族主义论调鼓励欧洲各帝国入侵、征服与殖民当时的清朝。他甚至将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亚洲取得的胜利描述为对白人社会的种族主义威胁,并将清朝和日本的关系误判为征服与奴役西方世界的联盟。[4]
基于“黄祸”的各种政治实践,种族主义政治家不断呼吁白人之间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种族团结。为了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当代社会不同领域爆发的突出问题,他们号召白人团结起来,以对抗来自亚洲的威胁。尽管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在军事上击溃了反殖民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但是在西方世界,白人对当时东亚国家产生的民族主义的恐惧逐步上升为一种文化性恐惧,即黄种人试图侵略和征服表征着西方世界的基督教文明。
汉学家梁永辉(Wing-Fai Leung)认为,“黄祸”这一概念及由此衍生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融合了西方文明对性的焦虑、对异族威胁的恐惧,以及某种斯宾格勒式的信念,即所谓‘西方的没落’,其终将被东方超越并奴役。”[5]吉娜·马切蒂(Gina Marchetti)则认为,“‘黄祸’结合了对外来文化的种族主义恐惧、性焦虑,以及对西方将被东方不可抗拒的黑暗神秘力量压倒和包围的深信不疑”[6]。从国际形势来看,鉴于日本日益崛起的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倾向,西方将日本人纳入“黄祸”的指涉范围当中。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作家们开始将所谓“黄祸文学”发展成为一种以种族主义为主题的叙事小说,并在故事中引入了殖民冒险、种族战争和科幻等元素。
西方文明存在的性焦虑是探讨“黄祸”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奥地利哲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厄棱费尔(Christian von Ehrenfels)认为,西方与东方正处在达尔文式的种族斗争中,双方争夺世界霸权,而黄种人正越来越接近于获胜。他甚至指出,一夫一妻制在法律上阻碍了白人至上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因为它将基因优越的白人男性限制为只有一名女性的孩子的父亲;而在当时东亚社会风行的一夫多妻制中,黄种人似乎具有更大的生育优势,因为他们允许一个基因优越的东亚男性与许多女性繁殖后代。
历史学家克劳斯·特威里特(Klaus Theweleit)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厄棱费尔将他对性的不安全感投射到“黄祸”的种族主义当中,而不像通常所谓“反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神话那般,后者是一种在德国社会中更为常见的偏见。同样,特威里特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右翼雇佣军组织“自由兵团”(Freikorps)的宣传中也常常出现致命的水意象,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对右翼欧洲人的世界观构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威胁。“自由兵团”在心理上缺乏安全感,痴迷于男子气概,并且急着想证明坚强的男性气质。他们使用水的负面意象反映出其对女性身体柔软、情欲、爱、亲密关系和人类依赖感的恐惧——这些元素在心理上威胁着他们,使他们显得不那么男性沙文主义化。[7]
二、演绎“黄祸”:傅满洲角色塑造背后的现实错觉关联
在西方殖民冒险小说中,“黄祸”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反派人物是由萨克斯·洛默创作的傅满洲博士。傅满洲是一个邪恶的华裔黑帮分子,他想征服世界,尽管他的计划不断地被英国警察和绅士间谍丹尼斯·内兰·史密斯爵士(Sir Denis Nayland Smith)及其助手佩特里博士(Dr. Petrie)挫败。傅满洲通常被描述为一个诡秘莫测的恶棍,因为他其实很少出现在舞台上,而总是派他的爪牙为他犯罪。例如在《阴险的傅满洲博士》里,傅满洲往往派遣一位曼妙的女郎到案发现场帮他确认受害者是否已经毙命。
在虚构的故事当中,傅满洲是“四藩集团”(Si-Fan)的头目。这是一个国际犯罪组织,是一个从“东方最黑暗的地方”招募党羽的泛亚谋杀团伙,有无数来自中国、缅甸、马来亚和印度的暴徒愿意执行傅满洲的任何命令。小说中反复出现傅满洲派遣刺客(通常是华人或印度人)去谋杀的情节。在冒险过程中,内兰·史密斯和佩特里博士往往被意图伤害他们的有色外国人包围。这无疑是对斯宾格勒式文化形态史观,或者说是“东方侵入西方”的比喻。傅满洲的出现,使得华人被描绘成西方文化语境下的肇事者和威胁者。正因如此,“傅满洲”这一角色在一些人看来成为“黄祸”的典型代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傅满洲成为西方对华人的看法里最臭名昭著的化身,也成了当代“黄祸”题材创作中其他反面角色的标杆:这些反面角色身上往往具有与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对东亚人群的仇外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特征。
在社会心理学中,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对某一特定类别的人的过度概括的信念。[8]有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可以建立在一种认知机制的基础上,这种认知机制被称为“错觉关联”(illusory correlation),是对两个事件之间关系的一种错误推断。如果两个统计上罕见的事件同时发生,观察者会高估这些事件同时发生的频率;罕见的、不频繁的事件是独特和突出的,当它们成对出现时,会变得更加明显;显著性的提高导致更多的关注和更有效的编码,这加强了事件相关的信念。在谈到如何开始创作“傅满洲”这一角色时,萨克斯·洛默声称自己对中国文化其实并没有任何先入之见;据说当他对着占卜板求卦“对白种人而言,危机在何处”的时候,占卜板给出的答案是“C-H-I-N-A-M-A-N”——这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心理暗示指引的下意识动作,他由此开始创作傅满洲系列。然而巧合的是,在他创作这一角色的时候,正是“黄祸”观念在北美社会传播开来的时期。西方人曾担心华人会通过埋头苦干以更快的速度从大学毕业,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争夺资源;与此同时他们也极易沾染毒瘾,让社会陷入歇斯底里的境地。[9]洛默在与妻子合著的传记《邪恶大师》(MasterofVillainy)中,对其被指将亚裔人妖魔化作出了回应:“当然,并非所有居住在莱姆豪斯的华人都是罪犯,但其中确实有许多人是因为最为紧迫的原因离开时自己的国家。这些人除了违法犯罪以外,并不知道如何谋生,于是乎,他们从中国带来了他们的罪行。”洛默的论点是,他将傅满洲和其他对“黄祸”的解读,建立在他担任莱姆豪斯当地记者时接触到的与华人有关系的犯罪案例的基础之上。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和肯尼斯·布拉里(Kenneth Braly)认为,当人们对一个群体产生情感反应,并将现实特征归于该群体的成员,然后评估这些特征时,陈规定型会导致种族偏见。[10]有学者认为,作为反映“黄祸”的典型反派人物,傅满洲这一角色的塑造来自洛默自身对异族扩张和侵犯的非理性恐惧。
即使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行为或特征所占比例相同,错觉关联也会导致人们将罕见的行为或特征错误地归为少数群体成员,而非多数群体。在傅满洲系列作品里,我们看到创作者将威权主义、犯罪和性焦虑等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强加在华裔角色身上。在洛默去世以后,他的传记作者及前助理凯·范·阿什(Cay Van Ash)成为接手创作该系列的作家。据他的描述,“傅满洲”其实是一个荣誉称号,指的是“好战的满族人”(the warlike Manchu)。范·阿什推测,傅满洲是满清皇室的一员,在义和团运动中站错了队,支持了失败的一方。在系列早期作品中,“四藩”是一个针对西方帝国主义进行暗杀行动的同盟组织,而傅满洲是这个组织的一个特工。在后来的作品里,傅满洲逐渐获得了对“四藩”的控制权,在他的领导下,“四藩”也从一个纯粹扎根于华人的同盟会日益跃升为一个国际组织。除了试图接管世界和恢复中华民族的古老荣耀之外,它还试图击溃法西斯独裁者并组织共产主义的传播。傅满洲深知,这两者会是他统治世界计划的主要障碍。“四藩”这个名称让人容易想起中国古代的“四方”概念,即对中国边区文化较低各族之泛称。《礼记·王制》记载:“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四境极远之地,本来就充满一种对异族的神秘想象。“四藩”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各种犯罪活动,尤其是毒品贸易和对“白奴”的人口贩运业务。傅满洲通过服用长生不老药,使自己已经相当长的寿命继续获得延长,他甚至花了数十载的实践不断调配和完善这一配方。《奇怪的死亡之王:萨克斯·洛默的恶魔世界》(LordofStrangeDeaths:theFiendishWorldofSaxRohmer)一书批评洛默公然将傅满洲塑造成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书中提到:“这些极其荒谬的作品,散发着疯狂的异国情调,实际上远没有它们最初看起来的那么两极,那么黑白分明,甚至是‘黑黄分明’。”[11]1932年上映的电影《傅满洲的面具》(TheMaskofFuManchu)反映出白人在“黄祸”意识形态面前折射出的性焦虑,例如傅满洲在率领他的亚裔团伙时发号施令:“杀死白人,并掳走他们的女人!”在《傅满洲的面具》中,父女之间的乱伦关系也是电影叙事反复出现的主题,尤其是傅满洲和女儿之间的暧昧关系,这样的情节设置被指影射黄种人社会里的恋童癖等非自然性欲。
刻板印象常常被认为是共享的(shared)。一个解释是,它们是一个“共同环境”(common environment)的结果,这个环境刺激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12]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描述不同的种族和民族群体时彼此非常相似,尽管这些人对他们所描述的群体没有个人经验。[10]作为一个虚构的民族主义者和犯罪首脑,傅满洲引发了无数关于种族和“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争议。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在1932年发行了改编自《傅满洲的面具》的电影,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馆便对这部电影提出了抗议。在这部电影里,傅满洲以一个恶棍的姿态吩咐他身边聚集在一起的亚洲人(包括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必须“杀死白人并掳走他们的女人”。由共和电影公司(Republic Pictures)出品的改编电影《傅满洲的鼓》(DrumsofFuManchu)在1940年上映之后,美国国务院要求该公司停止拍摄以傅满洲为主角的电影,因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的盟友。在美国参战之后,与洛默合作的双日出版社(Doubleday)拒绝出版傅满洲系列小说的新作品。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百老汇的投资者也取消了对傅满洲系列的广播剧与舞台剧的创作提议。1972年,有电影院宣布重映《傅满洲的面具》,但这一举动遭到了日裔美国公民联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的抗议,该联盟称这部电影“是对亚裔美国人的冒犯与贬低”[13]。有鉴于这场抗议活动带来的波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决定取消对《傅满洲复仇记》(TheVengeanceofFuManchu)的播送。洛杉矶的KTLA电视台最初也有这样的考量,然而最终还是决定播放《傅满洲的新娘》(TheBridesofFuManchu),并在“声明”中说:“这部电影作为虚构的娱乐类节目,无意对任何种族、信仰或民族血统进行负面的反映。”[1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受傅满洲启发的邪恶刻板角色又一次日益成为挖苦讽刺的对象。“著名的中国竹萨克斯演奏家”弗雷德·傅满洲(Fred Fu Manchu),是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广播喜剧《呆子秀》(TheGoonShow)中多次出演的角色。1955年,他甚至有了专属剧集《弗莱德·傅满洲的可怕复仇》(TheTerribleRevengeofFredFuManchu),还在《中国故事》(ChinaStory)、《黑夜堡垒的围攻》(TheSiegeofFortNight)和《失落的皇帝》(TheLostEmperor)等剧集中客串出演“东方纹身师弗莱德·傅满洲博士”一角。
由“黄祸”推导的种族刻板印象,是20世纪初俗文学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傅满洲系列作品出现后,又诞生了一些借鉴前者对“黄祸”的隐喻而创作的作品,例如由H·欧文·汉考克(H. Irving Hancock)创作的反派人物李朔(Li Shoon)于1916年第一次出现在《侦探故事》(DetectiveStory)杂志的《李朔的禁令》(UnderTheBanofLiShoon)和《李朔的致命任务》(LiShoon’sMission)这两篇连载小说上。从肢体来看,李朔是一个又高又胖的男人,有着“浑圆的、满月一般的黄脸蛋”,在“凹陷的眼睛”上方长着“鼓鼓的眉毛”;而就人格来说,李朔是“邪恶与智慧的惊人结合”,这让他“对所有邪恶的事物都感到惊奇”,并有着“撒旦般狡猾的神奇”。基于对李朔的创作,1937年DC漫画出版公司(DC Comics)又创作了《青龙》(ChingLung)这个作品。又如《闪电戈登》(FlashGordon)里的“无情的大明帝”(Emperor Ming the Merciless),也被认为是对傅满洲系列作品的模仿。有学者称之为“未来的黄祸”,将这位邪恶的虚构帝王描述为“泛光的秃顶下是一对斜眼,长着弯弯的眉毛,留着尖尖的指甲,穿着奇特的东方华服”[15]。另一部漫画《巴克·罗杰斯》(BuckRogers)描述了蒙古红军(Mongol Reds)在未来的25世纪征服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晚期,阿特拉斯漫画公司(tlas Comics),也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漫威公司,创作了《黄爪》(YellowClaw),这被认为是对傅满洲系列作品的仿制。不过这也是一个以亚裔对抗亚裔的作品,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最终被其中的英雄人物——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亚裔特工吉米·吴(Jimmy Woo)击败。这对外界可能存在的种族主义怀疑而言是一种抵消,也是一种平衡。
三、反刍“黄祸”:对刻板印象引发文化症候的省视与提防
无可否认,“黄祸”是一个典型的种族主义隐喻。在19世纪,极端种族主义者声称,黄色人种是对白色人种的威胁,并将吞噬欧“西方文明社会”(Western civilized society)。当时,“黄祸”是一种普遍的焦虑和恐惧,也是一些统治者用来攻击东方的一个理由。20世纪初,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利用这一点鼓吹欧洲帝国对中国的入侵、征服和殖民化。人们被社会化后会接受同样的刻板印象。一些学者认为,刻板印象通常是幼儿时期在父母、老师、同龄人和媒体的影响下形成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公众舆论》(PublicOpinion)中反映了刻板印象的内容依赖社会价值观的观点,即如果刻板印象是由社会价值观定义的,那么刻板印象只会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16]
19世纪70年代,“黄祸”引起了美国社会的焦虑。由于害怕在经济衰退期间失业,加州工人将亚洲移民归入“肮脏的黄色群体”。一些美国人认为,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勤劳的亚洲工人的出现对他们的生计构成了威胁。这种厌恶导致了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ExclusionAct),该法案不仅禁止华人成为美国公民,还牵涉到一些已经拥有合法居留权的人。当时,著名记者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说过,“华人不文明、不洁、肮脏”,具有“淫荡、肉欲的个性”[17]。这些负面特征也成为当时一些美国人心目中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平权运动逐渐削弱了美国人对亚洲人赤裸裸的歧视,取而代之的是对亚洲人(尤其是华人)正在侵蚀白人或西方文明霸权的更深恐惧,这可以被美国高等教育界证实。在1933年出版的小说《傅满洲的新娘》中,傅满洲声称自己拥有四所西方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在1959年出版的小说《皇帝傅满洲》(EmperorFuManchu)里,他透露自己曾就读于海德堡大学、索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而在《傅满洲的面具》这部电影中,傅满洲自豪地夸耀道:“我是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基督学院的法学博士和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我的朋友们出于礼貌,直接称呼我为‘博士’。”在作品中,佩特里博士与傅满洲博士第一次相遇是在1911年,那时佩特里博士认为傅满洲已经年过古稀,因此可以推断,傅满洲在19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开始在西方攻读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无论如今亚裔身上装点的是时尚领域还是学术领域的头衔,抑或其他彰显成功的标识,他们仍然很难成为所谓主体性的“自我”,而被视为西方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the other)。2019年6月,有报道指出,哈佛大学在积极性、善意、勇气和受尊重程度等人格特质方面一直对亚裔申请人打出低于其他族裔申请人的评分。[18]这表明即使亚洲精英有能力进入美国常春藤盟校,他们的“优秀”反而会成为对既得利益白人的威胁,从而遭到拒绝。“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一词既否定了个人付出的努力,又贬低了其他种族。这个词乍听之下像是恭维,实则不然,因为对成功的期望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认为亚洲人有优势的想法源于白人社会对其将“被接管”的恐惧:这是一个被重新包装的新“黄祸”。
刻板印象的观念是我们社会中的严重问题,它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包括:越来越多毫无根据的偏见使得人们不愿重新思考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某些被陈规定型的人会被阻止在其活动领域中取得成功。不同的学科对刻板印象形成的原因给出了不同解释:心理学家可能关注个体与群体的经历,以及群体的沟通模式和群体间的冲突;社会学家可能关注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刻板印象本身是冲突且糟糕的,它是人们精神和情感发展不足的体现。一旦刻板印象形成,有两个主要因素可以解释它们的持久性。第一,图式(schema)加工处理的认知效应,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如人们期望的那样行动时,这种行动证实甚至强化了现有的刻板印象;第二,偏见使得反对刻板印象的逻辑论据在对抗情感反应的力量时无效。[19]由于种族、性别或性取向限制了人们的行为方式,陈规定型观念的负面形象会让人憎恨少数群体,甚至导致仇恨犯罪。
从社会现实再回过头来看傅满洲引发的文化症候,我们发现文艺创作一方面观照着时代与社会,另一方面对现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幸的是,许多文艺创作将现实扭曲,提供了一种将世界浅显地分为好与坏、善与恶、忠与奸的呈现方式。20世纪至今,以欧美为强势主导的文化产业中的亚洲人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刻板印象和代表性不足的困扰。从历史上看,假若亚洲人不曾被塑造成刻板化形象,那么他们似乎像是从未被赋予任何角色,也更容易被相应文化产业的受众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忽视。亚洲人在文化产业中的边缘化角色,对他们在社会中被如何看待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文艺创作及承载它们的媒介对叙事题材和形式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完全透明的,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傅满洲这样的“系列人物”的制作中。在这种背景下,媒介不仅充当叙事平台,而且凭借自身的力量成为自我反思的对象,体现出不断变化的叙事功能。从傅满洲的案例出发,在亚洲人尤其是华人的媒介形象呈现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