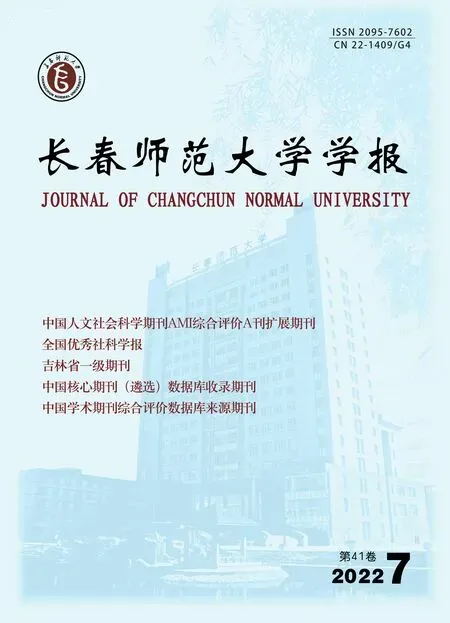先秦《诗》教管窥
——兼论对青年网络道德异化问题的纠治
于 涛,张 元
(江苏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以《诗》为载体、以道德情感培育为旨归的社会教化模式,可简称为《诗》教。古人把《诗》作为五经之首,并探索出一整套通过学诗、写诗、吟诗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和人才能力训练的卓有成效的方法。然而由于诸多复杂原因,《诗》教在中国教育中,特别是道德教育中的地位被大大削弱,青年的道德情感培养失去了有力的抓手,道德教育变成了道德规范的机械灌输。缺失道德情感的青年成为盛满“知识容器”的“空心人”,缺失道德情感的社会易变成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精神荒漠。因此,须对《诗》教做进一步研究。
一、《诗》教内容的层次性
我国有着悠久的《诗》教传统。《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131直到周代,《诗》教的教育地位才得以完全确立,《诗》教成为古代社会教化的重要手段。
(一)《诗》教是国家邦交人才辞令教育的重要内容
《诗经》中的诗歌在先秦时期的邦国交往中常被用作外交辞令,对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鄘风·载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2]320在“联齐抗狄”的表述中,许穆夫人用八个“不”字简洁有力地陈述了利害关系,这为先秦时期的邦交辞令教育奠定了基础。《左传·闵公元年》讲狄人将伐邢,管仲向齐侯明“请救邢以从简书”之重要,遂有“齐人救邢”之事。其中“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出自《小雅·出车》。管仲引此《诗》以谏桓公的用意主要有:其一,向邢国展示齐桓公良好的邦交信誉;其二,向玁狁等其它周边部族显示齐国的民心集聚和综合国力不容侵犯;其三,向齐桓公细明“宴安鸩毒,不可怀也”的利害,希望齐桓公予以警惕。可见,善学《诗》教以活用邦交辞令,可在处理国家邦交政事的过程中带来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诗》教是贵族子弟品行教育的主要内容
西周以来,《诗》教率先被用来培养贵族子弟。《春官·宗伯》有太师教六诗的明确记载,以风、赋、比、兴、雅、诵为教之本,以“六律”为教之音。其中“瞽矇”的职责是讽诵诗,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这表明大司徒、大司乐、太师这些职能官员不仅要教会贵族子弟诗乐舞方面的技能,更要借《诗》教培养万民的“六德”(义、忠、智、信、圣、仁)与“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从“皆选有道德之人”和“皆学歌九德”可以看出,德品高低是衡量《诗》教之师能否胜任的重要道德标准。虽然天子听士大夫公卿的献诗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但天子还是需要对献诗之义理进行合理反思,以达自我教化之功效。[4]016与此同时,贵族子弟的妻室同样需要《诗》教。如《周南·葛覃》中归宁女子“言告师氏”之“师氏”,即“女师”。据《地官·师氏》对“师氏掌以微诏王”的记载可知,师氏也要以“三德”“三教”教国子。“女师”必须具备品仪端庄、贤淑善良等德行,才能在贵族子弟妻室面前做好表率。
(三)《诗》教是古代家庭人伦教育的基本内容
《诗》虽简而意繁。《左传·隐公三年》中的“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指出,“兄爱弟敬”乃理想的家庭伦理状态。《大学》中以“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对“兄爱弟敬”加以补充。《诗》教如何做到“兄友弟恭”?以“燕兄弟也”(《小雅·常棣》)为例,毛序认为正因“闵管、蔡之失道”,召公才作《常棣》以鉴之。郑笺认为,这是在说周公吊二叔(管叔蔡叔联殷后裔武庚叛周)之不咸,才使兄弟异心;召公作《常棣》正是想以歌明“兄友弟恭”之道,《常棣》内容确实也以花萼、花蒂暗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2]408,以“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咏叹”[2]408等诗句呼应“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中心思想。可见,兄弟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影响家庭的和睦。
二、《诗》教形式的多样性
《礼记·经解》将“温柔敦厚”作为对《诗》教功用的概括。如“终温且惠”(《邶风·燕燕》)之“温”有“温柔”“温和”之意,“柔远能迩”(《大雅·民劳》)之“柔”有“柔软”“怀柔”之意,“有敦瓜苦”(《豳风·东山》)之“敦”有“团团”“聚集”之意,“则笃其性”(《大雅·皇矣》)之“厚”有“多”之意。“温、柔、敦、厚”是理想人格的《诗》教结果。
(一)《诗》教是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是《诗》教的重要内容。情感教育强调君子在具有德行、才干的同时拥有健康的情志、情趣。如《关雎》中的“坚贞不渝”“婚恋以时”等朴实之思都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这些感情往往可引申出更深刻的德育理念,教人通过对诗歌感情的体认进行自我教育。我们从而不难理解孔子为何用“思无邪”总结《诗》三百。“思无邪”源于“思无邪,思马斯徂”[2]610(《鲁颂·駉》)一句,当时是诗人用来赞美鲁侯专心致志的,孔子把鲁侯的谋略与成就放入“思无邪”中进一步升华。孔子认为“思无邪”不仅有怡情之作用,而且有对修身的指引。此外,如《小雅·正月》之“忧”、《豳风·东山》之“畏”等都是《诗》教培育情感的例证。这些质朴情感跨越时空,为人所感同身受,根本在于情感共鸣。朱熹也认为《诗》是人心之感的产物。自古诗乐难分家,《诗》教正是通过刺激“人心”让人产生种种情愫,最终让情感依附于“人心”生成声乐。
(二)《诗》教是道德教育
崇礼是《诗》教的重要内容。《鄘风·相鼠》云:“相鼠有齿,人而无耻”[2]319。《相鼠》不同于其他诗歌的地方在于启发君子对“礼”的反省。《相鼠》对无礼者的痛恨与拥护礼法者的感情相一致,《相鼠》已被士大夫阶层视为用于维护礼法的权威,“君子”与礼关系密切。再如季札在鲁观乐时曾对“二南”作出“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也”[3]2006的评论。《论语·阳货》载:“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5]258尔后的毛诗、三家诗都继承了此种观点并有所发挥,且都肯定了“二南”的重要性。再结合朱熹对“二南”之“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的解释,可充分得知婚礼是家庭和立国的根本。“二南”既充分体现出文王、周公、召公的德行,又完全符合周代礼乐标准,难免不被世人遵奉。
(三)《诗》教是价值观教育
《尚书》云:“诗言志”。《诗》教之“志”在广义层面体现为培育人的远大理想和志向,在狭义层面更突出人的情绪抒发。“诗言志”中的“志”有显志和隐志之分。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2]328这表达诗人想把未能实现且不便明说的情感,通过“投桃报李”的形式换得宝贵之物,“琼琚”(宝贵之物)是隐藏在诗人心中的那份永结同好的情意。《鄘风·柏舟》中的“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辱不少”[2]313让人直接感受到诗人身陷忧谗畏讥却又难离困境的苦楚。《诗》教教人知道欲望其实并不是社会祸乱的重要诱因,愚蔽之情与暴戾之气才是引发人祸的主要来源。人之情感本身就包含物质身体的欲望和血气的冲动,但人性中拥有的情欲、冲动并非都是恶,《诗》教让人们懂得顺循情欲、冲动以达中正才是正确树立价值观的关键。
三、《诗》教对青年网络道德异化问题的启示
《诗》教对解决青年网络道德异化问题有积极的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育本真之性情、修感恩之道以及成乐善有为之己三个方面。
(一)育本真之性情
互联网的出现给人际情感带来巨大冲击。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青年聊天交友方式愈发多元化,但面对面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网络具有的虚拟特质使得青年人的情感宣泄具有隐蔽性,不乏以假情博真心的闹剧出现。长此以往,人与人之间会出现严重的情感危机,不利于个人的情感建设,也不利于社会发展。《诗》教重点在于培育性情之正,重视人的自主性。《诗》教既包含个人生活与情感,又包含社会性内容与情感。[6]50诗与人性发生直接接触,但“在讨论‘个性’时不能把‘事物’和‘环境’分割开来”[7]168,因为人的天性(欲望)往往具有隐藏性,难以发掘和抑制。人有时虽可以克制欲望,却不能完全消灭它[7]174;而网络道德异化是在彻底否定和消解个人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以及网络社会生活的意向和能力。《诗》教是要让人的自我个性的张扬处于“中和”状态下,让人明白想要战胜自身的天性,必须量力而行[7]174;而网络道德异化让人逐步沦为被操控的客体。可见,育本真之性情是一个人德育发展的前提,绝不可忽视。
(二)修感恩之道
网络道德异化促使青年沉迷虚拟世界,已然忘却社会责任,更忘却父母的养育之恩。《诗》教认为孝德既是一种传统美德,又是一种社会责任。孝德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涉及伦理角色的转换。如父慈子才能在爱中产生孝敬,但父对子的慈爱需要适度,否则父越溺爱子越乖戾。《小雅·蓼莪》中“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一句就是在教人要知父母之恩,懂得感恩与报恩。安乐哲对“道”的释义非常深刻:“‘道’在人中,并由人传递下去。而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吸收‘道’和体现‘道’。”[7]183修道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要在“学而知之”的同时既保留个性又为他人着想,《小雅·小旻》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2]443一句或许能为这种状态之“度”的把握提供参考。《诗》教强调不断培养一个人的感恩意识,强调反躬内省。一个人如果一心只是向外贪婪索取,不注重自己对他人的回报,这种“感恩之情”仅是流于形式而已。[8]31因此,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既知道感恩他人,也知道充实自己。现实中绝大多数人还不可能自诩为这样的极致者,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修自己的感恩之道。
(三)成乐善有为之己
网络道德异化易吞噬青年的社会伦理角色。一心只讲个性不讲价值观念,盲目自大且目中无人,虚幻地将自己在网络世界中的自我“现实化”,认为做好“双面人”就是成功人设。殊不知,乐善有为在情感的运作中注入了诸多道德元素,让有为去做“体验式”检验。《诗》教强调乐善有为的主客双向互动关系,如《小雅·鹿鸣》全诗看似是在描写贵族大宴宾客之情景,但其实此诗以“鹿鸣”为起兴就折射出“和”的意蕴,再伴以乐奏而出,进而达到“崇和”的氛围。“崇和”就是让人们在礼乐秩序中尽享其乐,成就自我。《诗》教注重引导和建立与人为善、和谐共处的生存环境,自觉树立健康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教育人把握成己之“和”的度。成乐善有为之己是对育本真之性情和修感恩之道长期坚持的结果性检验,成效如何会直接影响一个人与否还会继续秉持。人的影响都具有两面性,即既影响他人,又被他人影响。[7]89一个人达到自身目的的同时,自己又是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成乐善有为之己的良果就是己他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