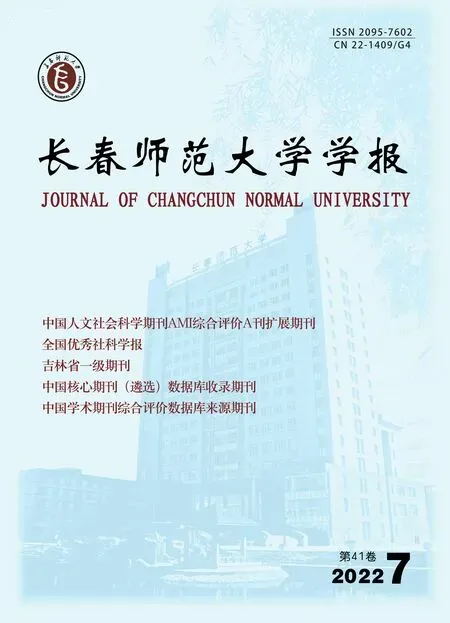《浮生六记》英文译介研究
——基于翻译动机视角
许宗瑞,胡小兵
(1.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1620;2.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浮生六记》是我国清代文人沈复所著的一部自传体笔记,自清嘉庆年间问世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堪称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珍品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据考证,该书著于1808年左右,于1877年刊行,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俞平伯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开始受到关注,并被译成外文。目前,全球已有上千家图书馆收藏《浮生六计》英译本。“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无论是在文学批评上,还是在翻译研究上,都有特别的价值。”[1]
一、《浮生六记》及其英文译介研究
自《浮生六记》被发现以来,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围绕作者沈复的生平事迹、与其他文学经典的比较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持续、广泛、深入的探讨。《浮生六记》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作品本身达到的艺术高度和蕴含的文学价值。俞平伯在《重刊〈浮生六记〉序》中对其评论道:“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2]98陈寅恪则将《浮生六记》概括为“例外创作”:“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3]99诚如两位学者所言,《浮生六记》以浑然天成的特质和注重表现日常生活和真情实感的细腻描摹,开创了第一人称抒情小说的美学范式,树立了一种新的中国文学文体类型。因此,它不仅感染了一大批中国读者,也吸引了不少海外人士。
《浮生六记》的首部译本出自林语堂。该译本为英译本,于1935年推出。此后,这部作品陆续被译成日语、捷克语、意大利语、马来语、瑞典语、法语、韩语、俄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丹麦语、荷兰语、德语等十余个语种,译著多达二十多部。其中,译介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英译。除1935年林语堂译本之外,英译本还有1960年英国译者Shirley M. Black译本,1983年美国译者Leonard Pratt和我国台湾译者Chiang Su-hui的合译本,以及2011年加拿大译者Graham Sanders译本,共计四部。
文军、邓春在评述国内《浮生六记》英译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时指出,相关研究可分为总括性述评、译者研究、翻译策略研究、译本对比研究、文化视角的研究、文学视角的研究、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七大方面[4]。但是,翻译动机研究一直未得到充分关注。翻译动机研究虽然在译者研究中有所涉及,但基本针对林语堂一人。梁林歆、许明武在回顾和展望国内外《浮生六记》英译研究时也指出,过往研究存在切入视角有待开拓、研究对象比较单一等问题[5]。许钧曾强调,在影响翻译具体活动的所有因素中,最活跃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翻译的主体因素,尤其是翻译动机和翻译观念6]。鉴于此,本研究将聚焦《浮生六记》四英译本译者不同的翻译动机或翻译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翻译影响。
二、林语堂:为“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树碑立传
1935年《天下》月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上,林语堂发表了《浮生六记》第一章“闺房记乐”的英文译文,译文中还附有他用英文撰写的译者序。之后,该刊第2、3、4期继续推出了第二至第四章的译文。1936年林语堂又将《浮生六记》以英汉对照的形式在《西风》月刊创刊号第1期连载,连载至1939年第29期完成,且同年该英汉对照版由上海西风社出版。1938年美国纽约庄台出版公司出版了林语堂的TheImportanceofLiving(《生活的艺术》),其中以四页篇幅展现了《浮生六记》中的女主人公陈芸对自然的热爱。193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林语堂的MyCountryandMyPeople(《吾国与吾民》)一书,其中以三页篇幅引用《浮生六记》中的片段,展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人的生活。1942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英译本汇编入TheWisdomofChinaandIndia一书,由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1962年香港华文出版社推出《浮生六记》中英对照译本注释版,此后我国两岸三地陆续推出了近十个版本的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
近百年来《浮生六记》之所以屡屡获得译介,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林语堂可谓功不可没,尤其是他对这部作品的推崇,对女主人公陈芸的赞美。他在译者序中写下的第一句,一直被很多学者广为引用:“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one of the loveliest women in Chinese literature)”[7]17。在这篇序言中,林语堂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赞美陈芸,赞美她贤达、驯良、天真、痴情,为她树碑立传。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译笔,让世人知道她的故事,“以流传她的芳名”。林语堂坦言,在主人公陈芸和沈复的简朴生活中他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7]17。尽管他们遭遇接二连三的不幸和悲剧,但他们胸怀旷达、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深深感染了林语堂。这种强烈的翻译动机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海内外读者,如1938年将《浮生六记》译介到日本的伊藤春夫。除译介工作外,伊藤春夫还于1943年在《江苏日报》上分五期发表“谈浮生六记:中国文学中最可爱之女性”一文。这是日本人较早发表的关于《浮生六记》的研究文章[8]92,仅根据文章题目就不难判断伊藤春夫深受林语堂的影响。再如澳大利亚当代作家Nicholas Jose(尼古拉斯·周思),他以《浮生六记》为基础,利用作品提供的想象空间创作了爱情小说TheRedThread(《红线》)。小说使沈复和陈芸转生,让这对前世恩爱夫妻历经磨难和坎坷后再续前缘,演绎出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Jose坦言,其改编完全基于自己对原文的翻译和林语堂1935至1936年间的译本[9]。此外,我国学者关于《浮生六记》的讨论还衍生出了专门的“陈芸形象研究”。陈芸形象所凝聚的文化底蕴,使得《浮生六计》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10]。所有这些,都以林语堂为起点。
三、Shirley M. Black:再现“一段至悲的悲剧人生”
继林语堂后,Shirley M. Black翻译的ChaptersfromaFloatingLife:TheAutobiographyofaChinesePainter是《浮生六记》的第二个英译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Shirley是英国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翻译家,中文名马士李,出版有RainbowSkirtsandFeatherJackets:TwentyChinesePoems(《霓裳羽衣:中国古诗英译20首》)等译著。与林语堂为陈芸树碑立传不同,Shirley译介《浮生六记》的主要动机是再现“一段至悲的悲剧人生”(a life essentially tragic)[11]xii。在译文前的作品简介中,她虽然也提及小说蕴含的浪漫、怀旧、温馨等情调与特质,但反复强调沈复、陈芸夫妇的“悲剧”和“不幸”,使用了诸如“out of place”“pressures”“destroyed”“misfortune”“miserable”“poverty”“failed”“died”“cheated”等词语。正是出于这一翻译动机,Shirley在翻译时将与作品悲剧主题无关的一些章节进行删减,对原文中一些让读者在叙事顺序方面感到困惑的部分进行重组。对此她这样解释道:“在翻译这部传记时,我首先尽我所能再现作品的细腻情感,以及其中的悲伤、激情、快乐,这在我看来就是沈复原著中的最突出的特质……第四记中很多部分我省去未译,比如游览庙宇名胜等处,它们基本大同小异,而且对于这些庙宇名胜不太熟悉的读者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同时,也省略了原文中与文学评论、养花种草有关的一些部分,因为涉及专业知识,对读者吸取力不大。再者,我还对一些章节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重组,以减少读者的困惑。”[11]xiii
针对这种翻译理念和处理方式,国内外学者褒贬不一。国内翻译家刘士聪认为,“(Shirley)超出了语言层面的形式‘对应’,她实际是‘翻译’加‘创作’。所谓‘翻译’,指她的翻译以原文内容为依据,这当然是生产译文的基础;所谓“创作”,因为她要把原文‘微妙情感氛围’和‘汉字的确切意思’译出来,就需摆脱原文句法和行文方式的束缚,因而常有增译,常有变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遵从英语表达习惯和行文方式进行的独立创作。”[12]美国汉学家Cyril Birch(白之)在1972年编撰出版的AnthologyofChineseLiterature(《中国文学选集》)中选用了Shirley《浮生六记》译本,并在一篇针对该译本的书评中对Shirley的“省译”行为表示理解[13]。不过,也有学者明确反对,认为“Shirley女士的译笔可谓专横,不仅任意删减,还任意调整。硬是将李白(第13页)和杜甫(第14页)的诗歌插入至一段文学讨论中;第12页中的一段似乎纯粹是捏造……如果这是《浮生六记》首译倒还情有可原,具有一定价值,但实际上林语堂之前已译出了全本。”[14]总体而言,Shirley译本是几部英译本中争议最多、最大的一部。
四、Leonard Pratt 和Chiang Su-hui:奉上“一份有价值的中国社会档案”
《浮生六记》第三个英译本由美国人Leonard Pratt(白伦)和我国台湾学者Chiang Su-hui(江素惠)合译。该译本作为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之一,由企鹅出版社1983年出版,后来又入选我国《大中华文库》(LibraryofChineseClassics),由译林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关于翻译该书的缘起,译林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许冬平这样描述道:Pratt指出,当初在阅读台湾版林译双语本时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有些地方翻译不够准确,没有完全反映中文原意;二是许多需要加注的地方,林译本注解阙如;三是有几处可能因为中文原文较难翻译,结果并未译出;四是译文语言风格不太一致,文中有些文字像莎士比亚时代英语,有的如19世纪美国小说或20世纪20年代的俚语[15]。从Pratt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他们之所以翻译《浮生六记》,主要由于林语堂译本语言的准确性和地道性问题。但如果细读Pratt和Chiang译本前的作品简介,则会发现两人译介的目的主要是为西方读者奉上“一份珍贵的中国社会档案”(a valuable social document)[16]9。在他们看来,这份档案比较“别具一格”(unique):“尽管《浮生六记》是围绕沈复和妻子芸的爱情故事,但是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段爱情故事——夫妻之爱与丈夫狎妓、妻子替夫寻妾等共存并生,相互交织。”[16]9
因此,在译文前的作品简介中,“社会”是Pratt和Chiang笔下的关键词,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当时中国妓女、衙门、幕友(俗称师爷)的大段介绍。将作品的文学性置于次要位置,凸显其历史档案价值或文献价值,是两位译者的用力所在。这也是一直以来不少海外汉学家、翻译家译介中国文学时的普遍做法。很多海外读者原本就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译者如果偏离轨道,广大读者容易随之误入歧途,作品也最终沦落为社会历史档案或文献资料,与文学无关或者关联较少。美国作家Celeste Heiter在评论Pratt和Chiang译本时,较为认同《浮生六记》的文学魅力,但同时也指出,书中有些章节令读者困惑,如“闲情记趣”一章开始十页的叙述完全围绕盆栽、插花、居家装饰等琐事[17]。再如Carlos Ottery的评论:该作品结构不同寻常,各记之间常有重叠,一些关键事情反复提及,但又切换视角,这种分层叙事让人雾里看花,故事发展的关键转折又经常从天而降……另一让人费解之处在于,作者沈复叙事的可靠性问题,他并不意在将自己描绘成一成功人士或者孝子良夫,也不希望谋求读者的同情。[18]虽然Pratt和Chiang译本是四译本中唯一入选企鹅经典丛书和我国《大中华文库》的译本,但产生的影响可谓喜忧参半,这与两人的翻译追求不无关联。
五、Graham Sanders:擦亮“这块中国叙事文学的瑰宝”
《浮生六记》第四个英译本为加拿大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汉学家Graham Sanders(中文名孙广仁)所译,书名译为SixRecordsofaLifeAdrift,由美国Hackett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与林语堂译本、Shirley译本、Pratt和Chiang译本相比,Sanders译本的作品简介部分最长。Sanders译本最鲜明的地方在于,希望擦亮(“擦亮”为笔者所加)“这块中国叙事文学的瑰宝”(this gem of Chinese narrative)[19]viii。显然,在重视和追求译本的文学价值方面,Sanders可比肩林语堂。Sanders认为,《浮生六记》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存在,虽然各章节间时间有所重叠,但展现了不同主题[19]viii。他还指出,沈复以诗歌、散记、官史所采用的简洁的文学语言进行书写,而非明清时期流行的长篇小说、戏剧惯用的冗长的口语叙事,能较快进入诗性、抒情的叙事模式,描摹自我内心感受、与他人的爱恨情仇以及自然世界之美[19]viii。不仅如此,Sanders在简介中还提醒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容易产生误解之处。譬如,陈芸喜爱憨园很可能是为取悦丈夫,作品的多层拼贴结构与人类记忆本身的样态极为相似,表现出选择性、前后矛盾、循环往复、情绪化等特点。
Sanders在一次访谈中曾坦言,翻译这部作品时自己一直努力保留沈复原文中流畅、抒情、率真的特质[20]。他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对其价值底蕴的执着追求和深入阐释,令《浮生六记》在海外获得了较好反响。美国汉学家Michael Gibbs Hill(韩嵩文)对Sanders译本大为褒奖,认为Sanders为学生、教师和学者奉上了一部全新且权威的译本,再现了沈复古雅飘逸的文笔,让人领略到作者的书写风格和古文散记的意蕴[21]。加拿大中国文学研究专家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指出,这部让中国读者痴迷一个多世纪的经典,最终在Sanders的努力下才以应有的英文样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其翻译融入了对原著语言、风格、结构的深刻理解[22]。美国英语文学研究学者Joe Sample认为,与其他三个译本相比,Sanders译本最为丰富、最为全面,完全可以作为性别研究、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以及创意写作等课程读本[23]。
六、结语
许钧认为:“翻译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确实,它可以是政治的,文化的,也可以是艺术的。它可以是强大而明确的,也可以是微弱而隐约的。应该承认,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受到一定的动机所驱动,都为着一定的目的去进行。”[6]《浮生六记》四英译本译者不同的翻译动机或翻译追求,不仅体现了译者本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对自己译介活动的不同期待,还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英语世界广大读者甚至专家学者对《浮生六记》的阅读实践,影响了他们的阅读感受和对作品的接受。展望未来,关于翻译动机与翻译影响间关系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考察作品及相应译本、译者的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如此可为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整体在海外的译介传播梳理出更为清晰的路径,为今后深入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工作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