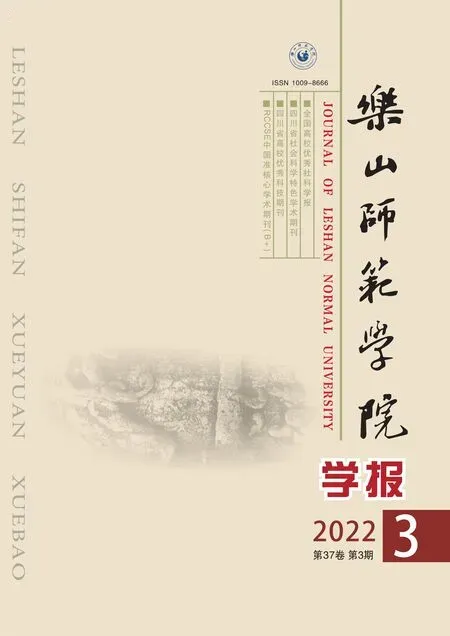“心具众理”与“心皆具是理”:朱陆“心”义之同异
郑义成
(四川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朱陆之辨由来已久,从南宋到当下一直存在学者争辨。例如,清代陆门学者李绂作《朱子晚年全论》,对朱陆之辨概括道:“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同异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也。”[1]对此,清代朱门学者夏炘作《述朱质疑》,回应云:“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2]从而,夏氏主张朱陆早晚均异。民国时期,对于朱陆之辨,冯友兰先生认为:“若以一两语以表示此二派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3]305与冯先生不同,钱穆先生认为:“后人言朱陆同异,率谓朱子乃理学,象山乃心学,其说之误,已辨在前。其实两人异见,亦正在心学上。”[4]。当今学者乐爱国教授则认为,朱陆之学的差别在于“气禀”说[5]。
事实上,朱陆之辨的关键在于朱陆“心”义之同异。诚然,朱熹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但同时,朱熹也重视“心”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朱熹说:“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6]528朱熹认为,从为学的角度来讲,“心”与“理”同等重要。关于朱熹论心,张岱年先生说,秦以后的哲学家中,论心最详者是朱熹,朱熹成立了一个比较精密周详之心说[7]。然而,面对程朱“性即理”命题,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命题,强调“本心”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陆氏多次强调孟子的“求放心”为学问之重点。对此,崔大华先生评述道:“陆九渊心学的方法和其哲学基础在性质、特色上都是一致的:一切从‘心’出发。”[8]
既然如此,朱陆之辨就应当从朱陆“心”义之同异的视角切入分析。
一、朱陆“心”义之同
理学家论心,通常包含知觉思虑的意义。张载说:“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9]程颐说:“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10]168-169同张载、程颐一样,朱陆“心”义也指知觉思虑,并且在此基础上,朱陆皆认为,此知觉思虑之心兼有善恶的意义。
(一)心之知觉思虑与虚灵
朱熹“心”义通常指知觉,此知觉有狭、广两种意义。狭义指人的知觉能力,广义指人的知觉能力和具体知觉。关于狭义的知觉,朱熹说:“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11]2590。“有知觉谓之心”[12]3606,“心者,人之神明”[13]310。朱熹所谓的“神明”指精神,即人的知觉能力。关于广义的知觉,朱熹说,“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14]1419,“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15]3180。概言之,朱熹认为,心不仅指人的知觉能力,而且可以通过心的具体知觉活动去认识事物。
与此同时,朱熹“心”义还指思虑的功能。朱熹说:“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于物”[12]1515,“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16]298“心中思虑才起,便须是见得那个是是,那个是非”[12]827。朱熹认为,因为心具有思虑的功能,所以心不仅能够认识事物之理,不为外物所蔽,而且还能够判断认识的是是非非。
为何“心”能知觉思虑?朱熹说:“心之知觉,又是那气之虚灵底。聪明视听,作为运用,皆是有这知觉。”[12]1531“知觉正是气之虚灵处,与形器渣滓正作对也”[15]2944。除此之外,朱熹又说:“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12]93。质言之,朱熹认为,心能知觉思虑的原因在于,心是由知觉之性和虚灵之气所构成。
与朱熹相似,陆九渊“心”义也指知觉思虑。陆九渊说:“人非木石,安得无心?心于五官最尊大。《洪范》曰:‘思则睿,睿作圣。’《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16]149陆氏认为,人不同于木石的依据在于人有知觉之心,而且心相比于人的其他四官,独具思虑的功能,故“心于五官最尊大”。
为何“心”能知觉思虑?陆九渊认为,原因在于人心之“灵”。对此,陆氏常说“此心之灵”“人心之灵”。陆氏进一步认为,由于“此心之灵”,故心能够认识外在事物。他说:“谓心至灵,可通百圣,谓物虽繁,在我能镜”[16]514。
由此可见,朱陆皆认为,由于心之虚灵,故心能知觉思虑。对此,黄宗羲评述道:“先儒以灵明知觉为心,盖本之乾知”[17]。
(二)道心、人心与正心、邪心
朱熹认为,根据心之知觉方向的不同,可将知觉之心分为“人心”“道心”。他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12]2157朱熹认为,心之知觉方向指向道德原则的是道心,心之知觉方向指向个人情欲的是人心。
为何心会有人心、道心两种不同的知觉方向?朱熹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13]14根据朱熹的理气观可知,人是由天命之性与气质“凝合”而成。为此,在人心、道心问题上,朱熹认为人心根源于人之气质,道心根源于人之天命之性。
需要注意,朱熹并不认为道心、人心等同于天理、人欲。他说:“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12]2158朱熹认为:一方面,如若说道心等同于天理,人心等同于人欲,那就相当于说人存在两个心,而实际上人只有一个心;另一方面,从心之知觉方向而言,天理是道心的知觉方向,情欲是人心的知觉方向。申言之,人心与人欲在善恶问题上是存在分别的。朱熹认为,“虽圣人不能无人心”[12]2159,故“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12]2157,而“可为善,可为不善”[12]2161。与人心不同,朱熹认为人欲全是私欲,应当“革尽人欲,复尽天理”[12]240。于是,对于道心和人心的关系,朱熹认为应当以道心支配人心。他说:“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13]14
陆九渊认为“心”的本来状态为“至灵”,但心“有所蒙蔽,有所移夺,有所陷溺,则此心为之不灵”[16]149,“故心当论邪正,不可无也”[16]149。陆氏所谓的“邪正”即指是非善恶。他说:“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岂可安于所惑,恬于所溺,而缓于适正也哉?”[16]76“善恶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气类相从盖如此”[16]43。陆氏认为,既然心有邪正,那么就应当“必也正人心乎”[16]425,“亦粗见于惟其以正人心为本”[16]532。
与此同时,对于当时学者饶有兴趣讨论的人心、道心话题,陆九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圣’,非危乎?‘无声无臭’,无形无体,非微乎?”[16]395-396陆氏首先对当时学者将人心、道心等同于人欲、天理的看法,表示否定。其次认为人只存在一心,只是从“人”和“道”的不同角度来看,存在“危”和“微”的特点。
由此可见,朱陆皆认为知觉思虑之心兼有善恶的意义,只是朱熹体现在人心、道心问题上,陆九渊体现在正心、邪心问题上。进一步而言,在人心、道心话题上,朱陆皆认为人只存在一心,并且人心、道心不等同于人欲、天理。
总而言之,朱陆“心”义的相同点在于:第一,朱陆皆认为由于心之虚灵,故心能知觉思虑,心属于认识论范畴;第二,此知觉思虑之心兼有善恶的意义,心具有伦理学意义。
二、朱陆“心”义之异
朱陆“心”义的根本差异在于:朱熹主张“心具众理”,陆九渊主张“心皆具是理”。“众”与“是”虽一字之差,实则代表朱陆“心”义的根本差异。
(一)朱熹主张“心具众理”
朱熹哲学的心相比于其他万事万物有一特性,即“心具众理”。朱熹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也。”[13]310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心具众理”命题强调的不是“心与理之关系”,而是强调“心之定义”。因为从语法角度而言,“……者,……也”是典型的文言判断句,表示用“也”字前的谓语对“者”字前的主语进行判断。朱熹又说:“心具众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谓之易。”[14]1395从语义角度而言,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指“心与理之关系”,而是指“具众理之心”,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所以称为易。与此同时,朱熹也用“心具万理”来表达和“心具众理”相同的思想。他说:“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12]167。“一心具万理”[12]167。
当然,朱熹“心具众理”命题中的“众理”指的是万事万物的殊别之理,而不是指同一共同之理的太极。朱熹说:“盖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18]根据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朱熹认为,人与物本应皆具有太极之道,但最终只有人因“其心为最灵”,从而保全了心中性之全体。需要注意,此处的“性”指的是殊别之理,而不是指共同之理的太极。关于太极与性的差异,《朱子语类》记载:“问:‘先生说太极“有是性则有阴阳五行”云云,此说性是如何?’曰:‘想是某旧说,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为禀于天者言。若太极,只当说理,自是移易不得。”[12]254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殊别之理可以称为性,而共同之理的太极只能称作理,而不能称作性。
除此之外,朱熹还曾多次将“心具众理”与“万事”“万物”对举。朱熹说:“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19]。“能存得自家个虚灵不昧之心,足以具众理,可以应万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12]282“心惟虚灵,所以方寸之内体无不包,用无不通,能具众理而应万事。”[11]805概言之,朱熹“心具众理”命题中的“众理”指的是万事万物的殊别之理,而不是指共同之理的太极。
(二)陆九渊主张“心皆具是理”
陆九渊认为每个人“心皆具是理”。他说:“‘天之所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芻豢之悦我口’。”[16]149“此理甚明,具在人心”[16]7,“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16]273。由此可见,陆氏是从“心皆具是理”的意义上谈“心即理”。
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心皆具是理”命题中的“心”指的是“本心”,而不是指知觉思虑之心。陆氏说:“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烁我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16]5简言之,本心指每个人先天具有的道德理性。与此同时,陆氏认为,作为道德理性的本心是道德法则的根源,提供道德法则,发动道德情感。陆氏说:“仁义者,人之本心也。”[16]9《年谱》记载:“问:‘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16]487
既然每个人先天地具有本心,本心又具有“是理”,那么陆九渊所谓的“是理”有何内涵?陆九渊哲学的理首先指宇宙普遍规律。陆氏说:“人为学甚难,天覆地载,春生夏长,秋敛冬肃,俱此理。”[16]450其次,陆九渊哲学的理具有客观性。陆氏说:“此理在宇宙间,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损”[16]26。“此理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16]461最后,陆九渊哲学的理指道德法则。陆氏说:“塞宇宙一理耳……乾坤同一理也……尧舜同一理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16]161关于宇宙普遍之理与道德法则之理的关系,陆氏同其他大多理学家一样,认为内心的道德法则之理与宇宙普遍之理具有同一性。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16]423。“是极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16]269
更为重要的是,陆九渊“心皆具是理”命题的“是理”指的是同一共同之理。陆氏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16]273,“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16]196,“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16]4-5,“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无有二理”[16]453。由陆氏以上种种说法可知,陆氏认为本心如宇宙一般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而本心所具有的“是理”指的是同一共同之理,而不是指万事万物的殊别之理,千万世之前与千万世之后只存在“一理”。
总而言之,朱陆“心”义的根本差异在于:朱熹“心具众理”命题强调心所具有的是万事万物的殊别之理,而陆九渊“心皆具是理”命题强调本心所具有的是同一共同之理。如若用朱熹“理一分殊”命题来解释的话,那么朱熹“心”义强调“分殊”之理,而陆九渊“心”义强调“理一”之理。
三、朱陆之辨再辨与朱陆明理之方
朱陆之辨的根本差异在于“心”义之根本差异,即“心具众理”与“心皆具是理”,而不在于朱熹主张“性即理”,陆九渊主张“心即理”。由于朱陆“心”义之根本差异,导致朱陆不同的明“理”之方,尤其是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存在巨大差异。
(一)朱陆“性即理”与“心即理”再辨
关于朱陆之辨,许多学者认为“性即理”与“心即理”是朱陆哲学的根本差异。事实上,明代罗钦顺早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安可不明辨之?”[20]
冯友兰先生在罗钦顺的观点上提出:“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但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3]305-306冯先生认为,朱熹哲学的心与理是不同的,心是“具体物”,理是“抽象物”,所以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冯先生又说:“盖朱子所见之实在,有二世界,一不在时空,一在时空。而象山所见之实在,则只有一世界,即在时空者。只有一世界,而此世界即与心为一体,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故心学之名,可以专指象山一派之道学。”[3]306冯先生又从实存世界和潜存世界的角度来分析朱陆之辨,认为朱熹所见的世界有实存与潜存两个世界,朱熹哲学的心与理分别属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同时,冯先生认为,陆九渊所见的世界只有一个实存世界,此实存世界与陆九渊哲学的心为一体。
然而,冯先生的见解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冯先生认为朱熹不能讲“心即理”,事实上,朱熹也讲“心即理”。朱熹认可学生的“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也”[12]438,他又说“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来,便有一理以应之,所以无忧”[12]1056。其次,冯先生认为朱熹哲学的心是形而下的具体物。关于心属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朱熹说:“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12]95由此可见,朱熹哲学的心既不同于形而上的性理,也不同于形而下的气,而是“操则存,舍则亡”的神妙不测。
事实上,朱熹“性即理”命题与陆九渊“心即理”命题并不具有对应关系。关于朱熹的“性即理”命题,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13]16对此,向世陵教授概括道:“‘性即理’就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性在质上等同于理,即从本体论说性就是理;二是从生成序列说性来源于理,或曰天理变形为人性。”[21]可见,朱熹“性即理”命题完全与心无关,但陆九渊“心即理”命题的重点却在于心,故朱熹“性即理”命题与陆九渊“心即理”命题不具有对应关系。
由上文分析可知,陆九渊“心即理”命题的意义在于“心皆具是理”,因此,从朱陆“心”义出发,朱熹“心具众理”命题与陆九渊“心皆具是理”命题才具有对应关系。要言之,朱陆之辨的根本差异不在于“性即理”与“心即理”,而在于“心具众理”与“心皆具是理”。
(二)穷“众理”与明“一理”
由于朱熹主张“心具众理”,陆九渊主张“心皆具是理”,于是,对于明“理”的目的,朱陆表现出不同的明“理”之方。尤其表现在,朱陆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截然不同。
朱熹格外重视《大学》的“格物致知”一章,并以极大的魄力作了《格物致知补传》。但朱熹既然讲“心具众理”,为何不直接探究心所具之“众理”而倡导“格物致知”呢?朱熹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3]4事实上,所谓的“明德”即指“许多道理”或“众理”。对此,朱熹说:“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许多道理在这里。本是个明底物事,初无暗昧,人得之则为德。……缘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镜本明,被外物点汙,则不明了。少间磨起,则其明又能照物。”[12]280质言之,朱熹认为虽然“心具众理”,但心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不明,因此,朱熹倡导“格物致知”而明心所具之“众理”。
朱熹所谓的“格物致知”是与“穷理”不相离的。朱熹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13]7关于“格物穷理”,朱熹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13]7当然,朱熹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在于“致知”。朱熹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3]7所谓“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指心所具之“众理”无不明,因此,朱熹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在于“致知”,在于使心所具之“众理”无不明。由此可见,朱熹倡导“格物致知”的原理在于:“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6]528简言之,心所具之“众理”与万事万物之理在内容上、本质上是同一的,故可以通过“格物穷理”而明心所具之“众理”。
陆九渊“心皆具是理”命题强调本心所具有的是同一共同之理,既然如此,陆氏认为就完全没必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而强调直接“明此理”。他说:“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事”[16]182,“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间,诚能得其端绪,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6]173。陆氏所谓的“诚能得其端绪”即指“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16]469。因为在陆氏看来,万事万物之理只是“一理”,因此,得其端绪自然能得其全体。
对此,为了明得此同一共同之理,陆九渊主张直接“格此物致此知”和“发明本心”。同朱熹一样,陆氏也重视《大学》,但陆氏在注解《大学》“格物致知”时,完全围绕“此心此理”而解释。他说:“所谓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于天下。《易》之穷理,穷此理也,故能尽性至命。《孟子》之尽心,尽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16]238为何陆氏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格致此心此理?原因就在于,陆氏认为万物之理皆备于我心。当学生问道:“天下之物不胜其繁,如何尽研究得?”[16]440陆九渊回答说:“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16]440陆氏认为,既然万物之一理皆备于我心,那么就只须明得此心之“一理”即可。于是,他又说:“此理本天之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16]4所谓“此理本天之所以与我”中的“我”即指“我心”。
当然,在陆九渊看来,既然“心即理”,那么只要发明本心,自然明得此同一共同之理。陆氏所谓的发明本心即指“存心”“养心”“求放心”。陆氏说:“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16]64
总而言之,朱陆之辨的根本差异不在于“性即理”与“心即理”,而在于“心具众理”与“心皆具是理”。基于此,对于明“理”的目的,朱熹从“心具众理”出发,主张通过“格物穷理”而复“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从“心皆具是理”出发,主张通过“格此物致此知”和“发明本心”以明得此同一共同之理。
四、朱陆对于程颐的思想的不同态度
朱陆之辨的根本差异在于“心”义之根本差异,即朱熹主张“心具众理”,陆九渊主张“心皆具是理”。为何朱陆“心”义有此差异?或许缘于朱陆对于程颐的思想的不同态度。
朱熹主张“心具众理”无疑是其“理一分殊”命题的逻辑发展,而“理一分殊”四字最初是由程颐所提出。程颐在解答其弟子杨时对《西铭》的疑惑时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10]609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程颐“理一分殊”四字的本义在于,说明基本的道德原则如何表现为不同的具体规范。
然而,朱熹在程颐“理一分殊”四字的伦理学意义基础上,重点发展了“一理”和“万理”的关系,所谓“一理”即指共同之理的太极,所谓“万理”即指万事万物的殊别之理。对此,朱熹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12]730由此可见,相比于“理一”,朱熹更加注重“万殊”。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何朱熹主张“心具众理”和倡导“格物致知”了。
与朱熹盛赞程颐的思想不同,陆九渊明确表示:“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16]388所以陆九渊从未谈论过程颐“理一分殊”四字。他又说:“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16]388陆氏认为程颐有许多言论与孔子、孟子的言论不相类似,而且有许多不当之处。关于孔子、孟子言论的主旨,陆氏说:“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16]4根据陆氏所引用的种种孔子、孟子的言论可知,陆氏认为孔孟之道“一以贯之”,主旨就在于“易简”。既然孔孟之道本来易简,那么陆氏对于程颐和朱熹所主张的“理一分殊”自然兴致索然,从而陆氏根本不谈“理一分殊”,只是强调“心皆具是理”中的“一理”。
总而言之,由于朱陆对于程颐的思想的不同态度,以及陆九渊更倾心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易简,故朱熹主张“心具众理”,陆九渊主张“心皆具是理”。
五、结语
朱陆之辨不仅是南宋学术思想史的一次盛会,而且是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课题,因此,对朱陆之辨的相同点和根本差异的分析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以往学者关于朱陆之辨的论述,多关注于“性即理”与“心即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抑或朱陆“气禀”说,罕有人从朱陆“心”义的视角分析朱陆之辨。即使有学者从朱陆“心”义的视角分析朱陆之辨,也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到朱熹主张“心具众理”,陆九渊主张“心皆具是理”,“众”与“是”虽一字之差,实则代表朱陆“心”义的根本差异。明乎此,也就可以对朱陆之辨这一重要学术课题有一个透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