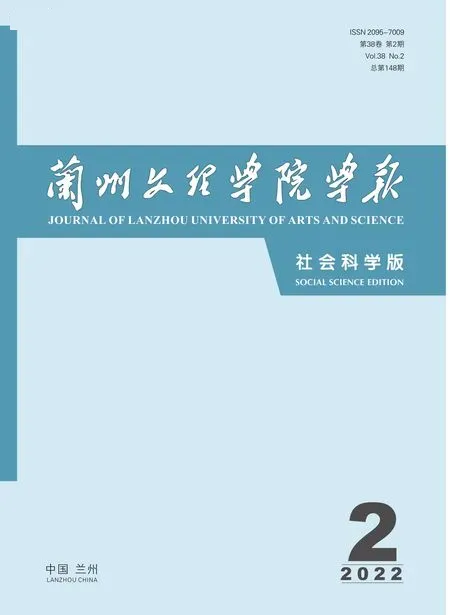略论晚唐小说《灵应传》的思想主题及价值
周 承 铭
(长春社会主义学院 长春中华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41)
《灵应传》作为晚唐小说仅有的几个单篇之一,近年来渐受学界重视,也取得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对文本内容的探究,特别是思想内涵的挖掘仍然不够深透。此文也尚不足即称深透,唯愿所陈浅见对人们做进一步研究略有裨益。
一、文本解读的几个问题
小说究竟作于何时?程毅中主张作于乾符五年后[1],石昌渝、李剑国等则认为作于广明以后僖宗、昭宗时期[2~3]。仅就能够掌握的佐证材料,要确认具体的写作时间无疑具有较大难度,这使得划定出一个大致时间范围成为目前最切实可行的选项,但依据小说文本内容,把写作时间仅是笼统定为广明以后的僖宗、昭宗时期既过于宽泛,也缺少实际利用意义。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泾原节度使周宝在文本中先后五次被称为“相公”,其中,九娘子4次,九娘子部下“青衣者”1次。这一特殊称谓为我们推定小说的成文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周宝是晚唐时期有一定影响的政治人物,《新唐书》辟有本传,《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亦对其行迹有零星记载。宝早年因“善击球”而获补军将以及武宗的超拔[4],并“以球丧一目”。小说对此在叙述中也间接涉及:“是月三日晚衙,于后球场沥酒焚香,牒请九娘子收管。”小说特别拈出“球场”作为人神互动的重要场所,与其“善击球”的专长与爱好不能说绝无关系,也说明作者对周宝其人情况还是比较熟悉了解。其任泾原节度使未详始自何年,但在故事发生时亦即乾符五年正在任上无疑,及至乾符六年(879)十一月乃调任镇海军节度使,“又制以神策大将军周宝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旧唐书·僖宗本纪》)中和元年(881)十一月又以镇海军节度使复加宰相衔,“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同平章事”[5]。“相公”在唐代是对具有宰相身份官员的尊称,使用限定十分严格,能被称为“相公”的只有“真相”或“使相”两种人[5]3177,“真相”是指中书令、门下侍中以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在朝廷实际担任宰相的官员,“使相”则指在镇节度使加带宰相虚衔,有其名位而无其实权者,此外,任何人都不能妄称“相公”。据史载,周宝镇泾原时加带的官衔仅为“检校工部尚书”[4],即使后来又有加衔“神策大将军”以及“检校尚书左仆射”等都不足以尊称“相公”。要之,乾符五年泾原节度使确系周宝,但此时尚非“相公”,中和元年虽系“相公”,然已非泾原节度使,说明故事虽属虚构,但所借用的“周宝”这个历史人物又可能确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相对确切的写作时间应是僖宗中和元年(881)十一月后。
小说究竟是几个人的故事?一部分学者认为小说所写仅是关于一个人物的故事,亦即善女湫龙女九娘子的故事,具体言之是“把龙女离婚再嫁的故事改造为龙女守节拒婚的故事。”[1]237“讲述了一个龙女拒婚的故事。”[6]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小说所写是关于两个人物的故事,即九娘子与制胜关使郑承符的故事,具体言之是“传在记龙女之贞淑,郑承符之智勇”。或谓:“铺陈九娘子之贞洁,郑承符之智勇,振奇可喜。”[7]由于秉持“二人说”者主要是鲁迅与汪辟疆先生,遂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成为当今学界的主流意见。主张一个主要人物与一个叙事核心的“一人说”和主张两个主要人物与两个叙事核心的“二人说”共同之处在于,一致认为泾原节度使周宝不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更不足以构成叙事核心。周宝能不能算作主要人物,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同时也直接关乎对小说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周宝比起九娘子与郑承符,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程度固然远逊前者,但有两点决定了他也应该而且必然是主要人物之一,而非一般陪衬性人物,更不属于可有可无的多余人物。首先周宝是作为故事前半部分的叙事立场与核心而出现在小说中的。在郑承符未登场的前半部分内容,亦即关于周宝与九娘子反复商量沟通如何实施援助的这段故事,小说主要是以周宝为视点,从周宝的立场出发,以周宝为叙事核心来构置人物和展开情节,故事主要矛盾冲突在于周宝能否施以援手和如何施以援手,“愿闻其说”“宝遂许诺”“遂差制胜关使郑承符以代孟远”等周宝的言行与态度,特别是他“君子杀身以成仁,狥其毅烈,蹈赴汤火,旁雪不平,乃宝之志也”。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成为这一部分乃至全文赖以成篇的关键因素和决定性环节。在这一部分,九娘子所着笔墨之多和刻画之细固然都远胜周宝,但在矛盾冲突中却始终不是具有主导作用的矛盾主要方面,真正决定整个故事走向与结局以及引发后面情节发生和人物出场的,显然不在她,而在周宝。其次小说讲述的是三个人的故事,而并非一个人或两个人的故事。小说中确乎凸显了一个人“守节拒婚”或九娘子与郑承符两个人物的德行与品格这样一些内容,但却不能据此判定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故事,依据小说陈述的全部事实,是三个人共同完成了一个人心愿的故事,周宝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或缺。“若非相公之殊恩,将军之勇武,则息国不言之妇,又为朝那之囚耳。永言期惠,终天不忘。”九娘子认识和评价自己最终能够守住“终天之誓”,关键是有相公周宝和将军郑承符的倾力相助,尤其是周宝“悯其孤惸,继发师徒,拯其患难”的“非常之惠”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九娘子“守节拒婚”而言是如此,对郑承符的施展平生“智勇”又何尝不是!郑生时仅为周宝治下一关使,“平生志气,郁而未申”,死后魂赴龙池,遂因战功而被龙女“寻备礼拜平难大将军,食朔方一万三千户。别赐第宅,舆马,宝器,衣服,婢仆,园林,邸第,旌幢,铠甲”。所获荣宠之高,放在有唐一代的真实历史中可谓无人可及,连号称再造社稷,位列三公,被皇帝尊为“尚父”的郭子仪,其食封总计也不过二千户而已(《旧唐书·德宗本纪》)。尽管郑承符是以牺牲阳寿博取这场荣华富贵,所付代价不谓不惨重,但在他本人看来这不仅不是人生悲剧,反而是实现了其“扇长风,摧巨浪”之“大丈夫”理想的人生喜剧,特别是在前呼后拥中得以找到了人生感觉,由是“气概洋洋然”。这样结局,悲也罢喜也罢,其始作俑者无疑是周宝。对郑承符而言,建功立业的平台是九娘子的,而建功立业的机会却来自周宝,如果周宝最后“牒请九娘子收管”的另有其人,那么他有纵天大本事与抱负也是徒然。
人物对话引经据典究竟意欲何为?当代学界普遍认为九娘子自述身世时大段的引经据典,完全出于作者炫耀才华的目的,对刻画人物和表达主题没有什么帮助和作用,是小说的败笔。“九娘子自述引经据典,剌剌不休,良多赘词。要之,作者逞才之迹过露,而失自然之韵,此其病也。”[8]“作者有意卖弄才学,引经据典,虽词采华茂,骈章俪句,却显得繁冗空泛,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9]对话之中引经据典过于冗长繁复,不能简明扼要、直奔主题,言赡而意寡的是文病,如若从另一方面看“年可十七八”的年轻女子之言谈竟然出经入史,言必有宗,浑身散发着与其年龄性别外貌都极不匹配的教师爷说教般的酸腐味道,这就构成了一个值得充分注意的特点了。至若谓作者“有意显示才学”[1]237,则更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以今人的思维臆测古人,特别是比照今人普遍的教育经历和知识构成而得出的结论。考察文本所引用的经史内容,概不超出唐人所谓“五经”“三史”以及“三礼”“三传”范围,如《诗经》之《鄘风·柏舟》、《召南·行露》,以及《毛诗序》之邵伯听讼,“春秋三传”与《史记》之伍子胥鞭尸、申包胥乞秦师等。而这些经文内容与史典故事,对唐代读书人而言不过是尽人皆知的常文熟典而已,引证这些当时文人应知应会的内容在当时不可能被认为是有才学的体现,更不必说会博得广泛称道。这一点作者比我们要清楚。自高宗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奉敕修订孔颖达《五经义疏》为《五经正义》毕,“五经”遂为唐代文士必读之书,必考之题,“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10]虽进士科,亦莫能外,考试形式一般为贴经、墨义、策论等。“五经”者,《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也,《五经正义》作为官修教科书,内容不仅涵盖了“五经”文本,还包括“春秋三传”“毛诗”“郑笺”等历代相关的传注疏等。长庆二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文云:“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10]1199据此可知,唐以“三史”为科举考试科目由来已久。合而言之,“五经”“三史”实乃当时生徒之必读、科举之必试书目,熟悉了解和掌握其中内容,乃彼时文人士子的一项基本功与寻常事。回归历史,认为作者欲以当时众人尽知或者至少是本应知晓的一些经文典故去炫耀学识,这样的认识就显得甚是不合逻辑。至于《梁四公记》与《柳毅传》更是出自本朝文人的手笔,且晚唐之世小说数量几倍从前,写作、传阅、编纂小说殊为时尚,小说中所引有关内容虽然在当时未必家喻户晓,但对读书人而言也绝对算不得冷文僻典,对炫耀才学同样不会有太大帮助。既然这些经典起不到炫才的作用,那么作者是基于何种目的加以引用,而且还是大段大段的引用,难道就是由冗长文风所导致的一种累赘之病吗?会否还有更深的思想涵义?这就必须要等到我们真正把握和理解了这篇小说时,才有可能做出回答。
九娘子在他人帮助下究竟战胜了谁?一些学者认为《灵应传》是 “一部颇为诡谲热闹的妖神大战的长篇传奇”[11]。“神人在人间的支持下战胜邪恶。”[12]“既保全了龙女九娘子的贞节,又惩罚了恶势力,伸张了正义。”[13]“小说宣扬九娘子不事二夫的妇德,同时也赞美她不屈从于恶势力的抗争精神和郑承符为人间雪不平的侠士心肠。”[14]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做出了明确的道德评价与价值判断。那么在这些学者眼中谁人是神谁人是妖?何者为正义何者又是邪恶?不言而喻,神当然是指誓死不二嫁的龙女九娘子,妖也当然是指强迫九娘子改嫁的朝那小龙;支持九娘子不嫁是正义,逼迫九娘子再嫁就是邪恶。这样的道德评价与价值判断未免过于简单和武断,而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有违小说本意,也不会被唐人普遍认同。朝那被龙女及其同党称为“贼”,盖因其以武力逼婚有害龙女从一之志也,然在作者笔下则不仅与龙女享有同样的神格,并且其神通功德竟还在龙女之上,“朝那镇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蚃灵应,则居善女之右矣”。这段文字说明,朝那非但也是神,而且还是一位泽被乡里有求必应的善神。求聘寡妇为妻之事,新旧《唐书》多有载录,在唐代从上层贵族官僚到底层庶民百姓皆视之为寻常事,绝少有人以为不妥,甚至连皇帝也不厌弃再醮之妇。以小说为例,《谢小娥传》中谢小娥的“誓心不嫁”与“里中豪族争求聘”同时受到作者充分肯定并非出自偶然。朝那小龙为未婚之季弟“潜行礼聘”,尽兄长应尽之责任本无可厚非,错只错在未以礼数而竟以武力胁迫龙女就范,但小说于此则特别强调指出朝那之“纵兵相逼”不是自作主张的率意而为,而是遵照“我王”“家君”之“令”,换言之,是老龙王普济欲假朝那之手对叛逆的女儿行允婚与教训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替其父教其女,故而当朝那兵败就擒时普济王即亟命人传语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轻吾过。”要求女儿不得怪罪朝那。龙女与朝那围绕能否再婚的斗争只是一种表象,其本质乃是父女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与对抗,“罪魁”是普济王,最后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的也是普济王,这在小说中均有明明白白的交代,没有什么模糊与歧义。父亲从亲子之爱角度出发要求女儿放弃腐朽道德束缚,重启幸福人生之旅,在唐代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乏其例,两唐书《列女传》有所反映,现今存世和考古发现的唐代妇女墓志碑铭尤有一定体现,置于现代道德与价值体系加以衡量,无疑是应予肯定的历史进步与文明。小说中真正矛盾冲突的焦点是,父亲有父亲的主张,女儿有女儿的意志,父亲出于爱女之心而命其夺情改嫁,父亲的主张和做法,本质是疼女爱女而非坑女害女,结果女儿非但不理解不领情,还予以强烈反抗与抵制;朝那支持父亲的主张和做法失败了,周宝与郑承符支持女儿的选择胜利了,如此而已。以此论之,在朝那与龙女之间根本谈不上有所谓孰善孰恶,孰是孰非,以及谁代表正义谁又代表非正义的问题,朝那逼婚不对,但为弟求婚没错,而逼婚之举事出有因,不可简单否定;龙女有权利拒绝再嫁,而单纯为着某种信念或抽象的价值观而甘愿葬送青春年华和终生幸福则不值得肯定。把女子夫死是否应该再嫁的分歧归属为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两个阵营及其对立与斗争,在小说研究上脱离了文本实际,作为理论观点更是不应有的历史倒退。
二、不同寻常的思想内容
作为以龙女为核心的故事,她与各方面错综复杂关系构成塑造人物与展开情节的特定环境和背景。除了与周宝、郑承符、朝那小龙这几个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负载着一定的思想内涵,还有一些没有实际登场,甚至没有具体指向的一类人物关系,如与父命、夫家以及众生的关系也同样负载着不容忽视的思想内涵与意义。
在孝亲与守节的矛盾冲突中凸显贞节地位优先。龙女夫死还家,作为返室女再次置身于父权的监管之下,父亲令其再嫁,而龙女竟抗命不遵,坚决抵制。“父母抑遣再行”“父母怒其刚烈,遂遣屏居于兹土之别邑,音问不通,于今三纪”,甚至“乃令朝那纵兵相逼。”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对于父母之严命置若罔闻,“妾终违命”;对于父母的恩情无动于衷,因不恭顺而与严父慈母长期隔绝,甚至不通音讯,“慈颜未复,温靖久违”,却从无愧疚自责之意,相反还十分心安理得,“甚为得志”;对于父亲一手策划的逼婚闹剧,更是针锋相对,直面还击,毫无顾忌,“亦率家僮五十余人,付以兵仗,逆战郊原”。种种举动,都表明此实逆子,绝非孝女。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龙女看来女子守节乃是“天赋”使命,一切纲常伦理都不足以与守节相比拟,“天赋孤贞,不从严父之命”。守节既是天经地义,为守节就该无视孝道、亲情;“贵主以父母再通音问,喜不自胜”“昔吾违命,乃贞节也。今若又违,是不祥也”。贞节的崇高地位与价值是绝对的,而孝道与亲情只有以不妨碍贞节为前提,才能成为重要的人伦道德与价值,不妨碍守节的父命即乐从之,有害于守节的父命则怒争之,孝亲和父女情、母女情与守节发生矛盾冲突时,必须无条件让位于守节。
在守义与守节的矛盾冲突中凸显贞节价值独立。象郡石龙一家招致天谴,惨遭灭门,“覆宗绝嗣,削迹除名”,家破、财散、人亡、名灭,唯龙女因外姓之身而“仅以获免”。夫死族灭后重回娘家,又以“公主”身份再现于家庭和社会,在观念上并不认同夫家为本家,或曰从未把自己当做石龙家族的成员,在经济上不依靠夫家生活,在责任义务上没有管理家产与抚育后代的任务,而尤为重要的是与其夫石龙少子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二人共同生活时间原本就很短暂,“未及期年”,而少子品德极差,生性凶残暴虐,非礼坏法,并非佳偶良配,“良人以世袭猛烈,血气方刚,宪法不拘,严父不禁,残虐视事,礼教蔑闻”。夫妻之间既缺少你敬我爱的情分,龙女也从未尽劝夫从善的妻子之责,表面上看似门当户对,旗鼓相当,而实则是一桩冷漠而不幸的婚姻。《礼记·昏义》于夫妻关系强调“男女有别”的同时,也强调“夫妇有义”,关于这个“义”古今解说纷纭,且多有分歧,然概括起来大体无外两端,即恪守夫妇道德与珍重夫妇情义。龙女之守节,与夫妇之义无关,其抗拒父命,坚守从一而终的“终天之誓”,一不因其家,二不为其夫,也非出于主妇应有之责任与使命,而只为身是“孀妇”这样一个事实和“笄年配于象郡石龙之少子”身为人妻这样一个名分。在龙女看来,夫死守节是五经(如《诗经》)之大义,先圣(如召公)之遗教,具有独立于其他人伦道德之外的意义与价值,不应设前提,无需有条件,更不要拷问应不应该、值不值得,无论夫族之存与亡,“良人”之贤与愚,以及夫妻情义之深与浅,甚至有与无,都必须一体遵行。
在仁爱与守节的矛盾冲突中凸显贞节选项优越。龙女守节除了涉及到与本家以及夫族的关系,还间接地涉及到与包括人在内的众生灵之间的关系,在众生性命与女子贞节二者必选其一时,小说的设计与安排是毫不犹豫地牺牲前者,而保全后者。九娘子曾明确表示,如周宝不能借兵助战,她就组织发动内外昆季、八水鹰扬“扇巨风,翻暴浪”,不惜“伤生害稼,怀山襄陵”“泾城千里,坐变污潴”,并且特别强调为守住贞节她会不顾一切的决战到底,即便遭受天谴也不会畏惧退却:“君若不悉城款,终以多事为词,则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责也。”如果这还仅是一时的愤激之辞,那么在此前后发生的激烈争斗给无数生灵造成的灭顶之灾则是血淋淋的现实。先是“伤人害稼,其数甚多”,然后又是 “血肉染草木,脂膏润原野,腥秽荡空”“死者如麻”“所经之处,但闻鸡犬”,人的生命、财富以及其他众生的性命都无可选择地成了贞节的祭品,而更可怕的是连久经沙场的郑承符见此情景都未免“颇甚酸辛”,肇事者龙女却毫无罪恶感,不仅从未为此流露过愧疚不安,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理直气壮—连古人最敬畏的“上帝之责”竟也都不在她的话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爱人,不在爱我。”(《春秋繁露·仁义法》)“爱人”是封建时代的核心价值“仁”之内涵的最本质性规定,是全社会始终不渝的价值崇尚和追求。在“仁”与“贞节”、“爱我”与“泛爱众”之间,九娘子的选择与作为,显然是将“贞节”凌驾于“仁”“爱我”凌驾于“泛爱众”之上。
贞节高于孝,优于仁,重于天,不为“三从四德”所制约,具有至高和绝对独立的地位与价值,在贞节面前其他一切社会人伦道德都变得微不足道。守护贞节可以无所顾忌,不必畏天,不必敬父,也不必考虑会伤害无辜,甚至摧残和牺牲自己的身体和性命也要在所不惜。渗透在小说故事中的这些思想,不用说唐及唐以前闻所未闻,就是后来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宋儒,也仅仅是把贞节凌驾在个体生命之上而已,而不敢这样大胆又公然地表达如此离经叛道的主张。有如此不寻常的思想内容,就使这篇小说在唐代小说史以及整个古代小说史,甚至中国思想史上都显得极具个性,不容忽视。
三、特定背景与思想主题
女子守节何以竟被小说强调到这般极致?考察二十四史《列女传》可以发现,其中许多节妇烈女都是产生在兵戈四起,王朝动摇,社会动荡的乱世。凡遭逢这样的时代,广大妇女除了要与夫家或父族一同承受生存和生命威胁的苦难,还要独自面对来自各种恶势力的强抢、强占和强暴,于是有人选择了逆来顺受,有人则选择了誓不从贼,拼死顽抗,宁做玉碎不为瓦存,从而演绎出一幕幕悲壮而凄厉的历史故事。返观《灵应传》,应该就是这样的社会土壤催生了隐含其中的那些荒唐而奇怪的思想。以小说问世于僖宗中和元年十一月后这个时间点论之,在其前后的几十年间先有裘甫在浙东起义,庞勋在淮西起义,后有王仙芝、黄巢在山东起义,中间还经历了沙陀部落叛乱等事件,这段时期的历史面貌大体上可用“烧”“杀”“淫”“掠”几个字来概括。仅摭拾史家记述数条以证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又分兵掠明州。”“贼又遣兵掠台州。”“甫自将万余人掠上虞,焚之。”“所过俘其少壮,余老弱者蹂践杀之。”[5]3104“与勋同举兵桂州者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5]3123“(黄巢)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5]3139“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5]3143“沙陀焚唐林、崞县。”[5]3147“黄巢寇掠蕲、黄。”[5]3145“贼转掠湖南。”[5]3146“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5]3158“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5]3161其中,黄巢军对生民之残害和社会破坏之剧烈可称史无前例,尤其是僖宗广明元年十二占据长安称帝后更是极尽凶残与狼戾,“乃下令洗城,丈夫丁壮,杀戮殆尽,流血成渠”[15]5394。“巢复入京师,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4]6460“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春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15]5397财帛、妇女尤是暴徒所爱:“甫数日,因大掠,缚箠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4]6458不止叛军如此,本该平叛治乱的各路官军也乘势纵暴作恶,“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5]3176。“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5]3161“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5]3148在“夺人货财,掠人妇女”方面,官军之害比之叛军有过之无不及。从广明元年十二月两京陷落僖宗仓皇出逃兴元、成都,至光启元年(885)正月平定黄巢起义僖宗还京,唐代社会完全陷入强强争斗、弱肉强食、四分五裂和杀人如麻的混乱血腥状态,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民的安定生活被彻底剥夺,生命和财产没有保证,广大妇女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更是面临着宰割和摧残的命运,无数人因战争、动乱而失去家庭、亲人、贞洁以至生命。这是唐代历史上最悲哀的时代,而其中广大妇女又是那个时代最可悲哀的人。更为悲哀的是,面对“王业于是荡然”的空前危机,朝野上下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却无人做出应有的深刻反省与反思。中和二年淮南节度使兼侍中高骈上书朝廷公开指斥僖宗昏庸,甚至直截了当地将之称为“亡国之君”:“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僖宗不仅拒不承认过错,还命郑畋草诏切责之,略云:“宗庙焚烧,园陵开毁,龟玉毁椟,谁之过欤!”“‘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5]3169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比起王室与社稷安危、宗庙焚毁、园陵开掘以及黎民百姓的空前劫难等国家和苍生大事,唐代的统治者似乎更关心和关注女子的守节这些细枝末节问题。中和四年(884)黄巢及其余党被诛,七月献俘于成都:“秋,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5]3182皇帝亲自审问罪囚,从总结为政教训的角度出发,当时可问和该问的问题何止千万,可放着所有军国大事不问,却只单单对女子为何失身于贼颇有兴趣,一方面说明在战乱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中,女子失贞丧节也成为一个相对突出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说明咎责女子失贞已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社会思潮。《灵应传》正是这样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土壤孕育与产生的一篇小说和演绎出的一个荒诞故事。
守节不嫁完全出自孀妇九娘子的个人意志和选择,是她的道德自觉和自愿,没有任何主客观因素强迫她去这样做,但最终完成守节愿望却又不是凭她一个人力量办到的,而是在各方面支持和帮助下才实现的结果。由此,夫死守节也就由女子的个人私事,而顺理成章地上升为地方官府的一桩公事以及一些英雄豪杰藉以建功扬名的一件大事。孀妇九娘子有守节不嫁的意愿,地方军政长官泾原节度使周宝赞同并倾力支持九娘子的意愿,怀有“奋其鹰犬之心,为人雪不平之事”抱负且智勇双全的军将制胜关使郑承符统兵指挥帮助九娘子最终实现了意愿,这就是小说的主要故事梗概和脉络。没有九娘子矢志守节,就没有故事的赖以发生因由和叙事核心;没有周宝的三次派兵遣将,就没有故事的层层展开和步步深入;没有郑承符挂帅迎战,就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高潮和耐人寻味的故事结局。以人物刻画与审美需要为视角,固然是九娘子以及郑承符显得比较生动与突出,以表达思想与演绎主题为视角,则可见是三个人物各有分担,各有侧重,共同完成了孀妇守节不嫁的故事,每个人物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不同人物为立场和出发点,必然会概括出彼此不同的思想内容和得出不尽一致的结论,但若从三个人物共同演绎一个故事,即同一事件由不同相关人承担不同的责任而最终完成的角度出发,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就是“龙女之贞淑,郑承符之智勇”或“龙女守节拒婚”等这样一些观点所涵盖不了的,更勿论完全撇开女子守节这一叙事核心和主线的所谓“异类相通和拯人患难的主题”[16]。纵观全篇,小说虽然是以女子守节为叙事核心和叙事线索,但小说的叙事重点却又进而集中在女子如何才能守得住节,而非女子要不要守节以及为什么守节等问题上。分别以三个人物为核心的三组故事,是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具体回答。首先,当事女子真心和一心守节是有志守节女子能够守得住贞节的根本。具体言之,即能够顶得住来自家庭内的情感纠缠、伦理困扰以及家庭外的暴力胁迫,能够始终把贞节视为高于孝道、高于生死、高于一切的最高人生价值来对待。龙女作为丧夫还家的返室女,其地位、生活、权利、责任和义务均等同于在室女,公主身份是娘家赋予,生活用度全靠娘家提供,权力来自娘家,城池为父王别邑,身边侍从尽是父王臣民,掌握支配的财物也莫非父王之所有,并且她在观念上也有着极其强烈的家庭归属感和自豪感,不仅对娘家的宗族历史深感荣耀,与周宝对话历数先祖之辉煌,尤其是沾沾自喜于父亲普济王“阴灵普济,功德及民”“威德临人,为世所重”,而且凡指事言物皆习惯以“娘家人”身份自居,言必称“妾家”“先人”“先宗”,以及“我王”“家君”。这样的一种境况,意味着龙女在夫死再嫁问题上服从父母之命改醮他门原本是顺理成章,况且出嫁女听从父祖之命而再行改嫁在唐代现实中向来也不乏其例,两唐书以及存世的唐代墓志碑铭均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另外,唐代《户婚律》等法律条文也明确规定父母或祖父母等嫡系血亲享有责令出嫁女或孙女再嫁的绝对权力(《唐律疏议》),同时,唐人思想观念中早就有视女子再嫁为人伦常事的一面,如贞观初年楚王李灵龟薨,妃上官氏寡居,诸兄姊力劝其再嫁时即云:“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妃可思之。”[15]5143但是,龙女九娘子面对贞节与孝道、亲情、仁义以及个人生命等价值选择时,却能够超越现实羁绊,超越传统影响,超越血脉亲情与伦理道德束缚,为了贞女不二嫁的信念和追求,不惜逆孝道、悖人伦、弃仁义而一往无前,严父不足以撼其意志,慈母不足以动其感情,涂炭生灵、殃及无辜不足以感其良心,大军压境、三战三北不足以怯其英勇,内心从无矛盾,选择一贯分明,斗争始终坚定无比,女子守节能做到不顾一切、坚决果断,达到无不安、无纠结、无牵绊、无顾忌、无畏惧,如此干脆决绝之境界者在古代小说史中再无第二人。其次,地方主官高度重视并给予实质性的支持,是有志守节的女子能够守得住贞节的关键。周宝作为位同古代诸侯的一方军政长官,其在封境内所推行教化可与史上亲自听讼、支持女子守节的古之大贤召公相媲美,“今则公之教可以精通幽显,贻范古今。贞信之教,故不为姬奭之下者”。就周宝本人而言,不仅久有“蹈赴汤火,旁雪不平”的救世济人之志,而且在听了九娘子遭遇后即“心许”其夫死不嫁的选择和决定,不惜纡尊降贵,三番五次为九娘子挑选兵马,给与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以最坚定有力的支持和帮助。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支持不仅体现在派出对他已没有实际意义的阴兵,更体现在毫不犹豫地抽调出对他注定要有一定影响的守军一千五百人(对于当时一般只拥有几万人马的节度使而言上千人马绝不是小数目)“戍于湫庙之侧”以听龙女调遣,尤其是在藩镇割据斗争加剧的晚唐之际抽调拱卫封境安全的边关大将去为他人统兵更属冒险之举;而且他为之选派兵马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先后三次,而如果没有这关键的最后一次,就恰恰未必能有九娘子的如愿以偿。第三,具有庇护能力的人物实际出手加以庇护是有志守节女子能够守得住贞节的保证。九娘子守节拒婚主要体现为决心和意志,而非誓死相搏的行动,是郑承符替她战胜了朝那小龙的武力凌逼;郑承符的真正出彩处不在于帮助龙女战胜了朝那,而在于他具有足以战胜朝那的非凡指挥才能,亦即为鲁迅与汪辟疆等交口称道的“智勇”,郑挂帅龙潭非其主动请缨,而是受遣而行,要不要帮助固然取决于上司周宝,是不是帮助得了,亦即有没有实施帮助的能力则在于给与帮助者本人的禀赋,如郑承符所具备的“素谙其山川地里,形势孤虚”“分布要害”“设三伏以待之”“明悬赏罚,号令三军”“千里转战,四面夹攻”等带兵、筹划和作战指挥能力。如果周宝不选派郑承符,或派了郑承符而他并不具备战胜朝那的那些“智勇”,即如同先前的都虞候孟远那般无能,九娘子即使再刚毅再贞烈,也终将难逃被强暴的结局,故九娘子最后有总结概括之语曰:“若非相公之殊恩,将军之雄武,则息国不言之妇,又为朝那之囚耳。”要之,小说实则是要告诉人们,女子守节并非一人之事,既要有九娘子这样的“贞女”以守志不移为“终天之誓”,也要有周宝这样政教不逊于姬奭的“相公”以推行“贞信之教”为己任,还要有郑承符这样擅于统兵的“权谋之将”藉庇护“孤惸”以立身扬名、伸展“平生志气”;女子守节也不单纯是个人之事,必需个人、官府和社会几个方面各尽其责,共同努力,协同行动,个人要做的是下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官府要做的是推行教化和给与支持,家庭与社会要做的是赞成而不阻止、庇护而不旁观。在僖宗中和元年后,在战事连年,兵匪相继,无数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时代背景下,针对上至皇帝下到庶民百姓普遍关心的因战乱造成的当时众多妇女贞节不保,提出一套应对方案和办法以期解决妇女难于守节的问题。这才是小说的思想主题所在。
这个故事和这个主题的进步意义在于,在女子守节问题上表达了贞女之“志诚”与“相公之殊恩”“将军之雄武”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主张,指出了想不想守节与能不能强有力地支持及庇护守节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在强调个人的决心与意志的同时,也强调了国家与社会的责任与作用,而没有片面地将失贞丧节全部归罪于当事女子本人。中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动荡不安形势的日趋加剧,特别是经历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后,迫使许多妇女不得不选择以牺牲贞节与人格尊严以保留性命的苟且求生之路,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选择主要是基于身处乱世的无助和无奈,在无助和无奈的背后折射出的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缺失了责任。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骨肉分散,无所依托”,时有凤翔李姓少女孤身一人逃难,路途上为求有人庇护,主动对同行者董生以身相许,及至蜀则提出分手,并语董生曰:“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携,以至于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17]由此可见,乱世之中为求活命,迫使许多女子看淡贞操,甚至还有个别女子会主动出卖贞操。当事者不认为是个人的“不幸”,那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大不幸。女子贞节是涉及并影响两性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来都受到男性世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而且越是在动乱时期往往越是不能接受和容忍、体谅女性失贞。晚唐时期,在诸多社会问题中,女子守节所以会成为当时被广泛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完全是由男人的立场、男人的利益和男人的价值观决定的,而且必然要主张女子失节的责任完全在女子个人意志不坚,没有真心与决心守节,即女子能不能守节主要是能不能放下心中的贪恋和羁绊。也正是缘于此,才会有皇帝出面指斥女子背弃国恩,如僖宗在成都审讯罪囚之发问;官员断言“女子之性,尤昧义方”[15]5152,如大中五年兖州节度使萧俶的奏议;道学家从夫家立场出发对女子守节提出严格要求,如《女论语》等女教书的问世;诗人对贞女烈妇的倾心赞美,如白居易《蜀路石妇》“夫行二十载,妇独守孤茕”。孟郊《琴曲歌辞列女操》“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等;小说家把众多红杏出墙,主动投怀送抱的妇女形象形诸笔端,如《李章武传》之王氏子妇、《飞烟传》之步飞烟、《郭翰》(《太平广记》卷六十八)之织女等等。这些现象背后,既反映了对女子守节问题的认识,也反映了对女子守节责任的确定与态度以及解决问题的立场与办法。相比之下,《灵应传》强调女子个人责任,也强调国家与社会责任,主张的是“邵伯听讼,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也”。态度公允,方法也比较可行。邵伯是辅弼大臣,也是地方长官,贞信之教的兴与衰,主导权也是在朝廷与官府,而不是在社会与民间。如果强暴之男的强暴行径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则贞女之贞节自然可保无虞。这样的主张就等于是把矛头指向了朝廷和各级官府,具有封堵朝廷、官府与官员推卸和逃避责任之借口与退路的意义。这一思想使它在唐代同类小说中显得十分突出。
另外,小说把周宝塑造成一个“贞信之教”的推行者和维护者形象,与史上真实周宝的所作所为形成反差,也可能别有寓意。《北梦琐言》卷四《崔氏女失身为周宝妻》即载,乾符中崔姓宰相有姊妹寡而幽居,周宝竟“逾垣而窃之”,致使“相国不得已而容之”[17]1836。把一个破坏女子守节者美化为帮助女子守节者,反话正说,是否寓有对当政者的嘲讽之意,也很值得重视。
这个故事和这个主题暴露出的问题,一是把贞节强调到极端程度,不顾仁义,特别是公然否定被《孝经》称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被玄宗称为“德之至,道之要”(《孝经注疏·开宗明义章第一》)被奉为“天经地义”之至高无上价值核心的“孝”和“孝道”,无视作为“天性”的“父子之道”,擅改人伦道德规范,撼动封建宗法统治制度的思想基础和根本,扰乱封建思想体系,借卫道之名,行逆道乱常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唐时期在社会政治大混乱的同时,思想观念的大混乱也同样十分突出,二者相互鼓噪的结果必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大崩溃。孔子云:“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孝经》)所言正是此意。有论者认为小说的用意是在维护腐朽的封建礼教,显然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二是以女子守节和帮助女子守节为救时济世的良策反映了唐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肤浅与狭隘。小说不顾“宝玉迁徙,宗社凌夷,万乘之灵,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这种天下大乱,王室如毁的社会现实,看不到强暴之男所以能够肆意侵凌贞女的根本症结在于封建统治的全面崩溃,许多妇女丧贞失节不过是天下大乱的诸多后果之一,责任在封建王朝及其统治的失德和无能,是腐朽政治的深重灾难在广大妇女身上的体现,不着眼根本问题,回避主要社会矛盾,而侈谈什么“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希图以“贞信之教”来解决包括社会道德沦丧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大失控和大混乱,未免浅薄幼稚。尤为可笑的是,小说让龙女九娘子把向周宝借兵自比历史上的申包胥乞秦师,与“复楚退吴,仅存亡国”的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女子守节视为救济国家危亡的大计,反映出封建文人思想深处对妇女之偏见和歧视的根深蒂固。小说在女子守节的责任上虽然主张三分论定,不惟一方之罪,但骨子里坚持的依然是中唐以后主流社会意识一贯主张的女人祸水和女人祸国论思想,这一点与谴责妇女失贞丧节的大多数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若不然也不会将当时男人们都不肯担当也担当不起的那么沉重政治和社会责任一股脑地都压在女子和女子守节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