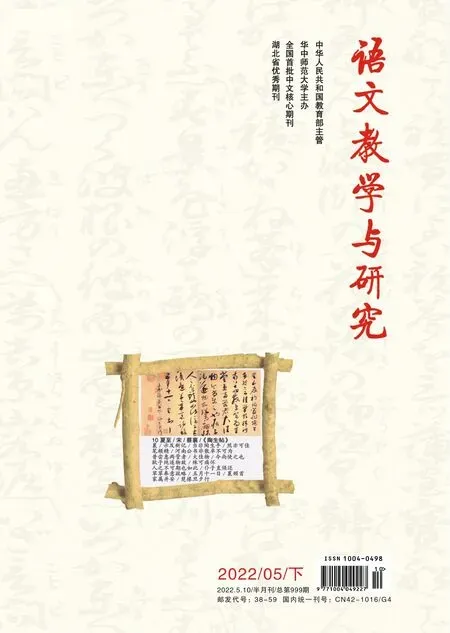冯至《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路的隐喻
◎蔡文婧
写“路”的文章不少,其中也有值得认真琢磨的名篇。但是对于冯至散文《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而言,这一入选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的文本,主题不是写路,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篇意境含蓄、韵味隽永的美文精品,极能体现冯至散文诗意和理趣结合于一体的特点。[1]但是在笔者看来,路依然是文中的一个重要的对象,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路,那这篇文章的意境就体现不出来,甚至逻辑都有可能是不通的,因为如果没有路,那这个消逝了的山村就不可能为人所知。当然这只是客观逻辑,认识路的价值,更需要从人文角度去认识其隐喻,这才是其中的精髓所在。
所谓隐喻,一般是指在类似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隐喻是相对于明喻而言的,巧妙的隐喻运用,虽然给文本的理解增加了难度,但是一旦解读出隐喻的价值,往往可以更好地窥得作者行文的用心。《一个消逝了的山村》显然也是如此,如果说“消逝了的山村”是作者的明示的话,那路之隐喻就是“消逝了的山村”背后更加值得琢磨的对象。
从宏观角度来看,作者写“消逝了的山村”更多的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对话,体现着人在自然当中完成审美感悟与哲学思考的心路历程。文章借助于对一个已经消逝了的自然山村的写实,与自身想象及意象建构基础上的写意,让一个已经消逝了的自然山村成为内心意象建构的基础,从而在作者自己的心中,在读者的心中展现出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随后,将文本解读的视线进一步射向文本的内部,射向作者的内心,则可以发现在诸多描述当中,“路”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对象,解读其隐喻也成为本文的另一个重点。
一、路,展现着时空
“一条窄窄的石路的残迹泄露了一些秘密”,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从人文视角并将解读之触角伸向作者的内心以及文中的意向,然后通过初步的解读就可以发现,消逝的山村与遗留的石路,恰恰是一对矛盾体,同时又是一对依存体。在文中,作者说了两个景致与感想:一是“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的“浓绿浅绿”。二就是路,这个路在作者心中是分开的,一条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另一条路是“用石块砌成,从距谷口还有四五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山谷这边引来,先是断断续续,随后就隐隐约约地消失了”的“旧路”。在作者的意象中,“好像是走着两条道路,一条路引我走近山居,另一条路是引我走到过去”。很显然,这个时候冯至在时间和空间元素中灵活穿越,其借助时空特质,展现了个性化抒情方式。[2]
这一跨越时空的对“路”的认知,奠定了本文的一个基调:路不仅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也存在于作者的心中;在自然环境中出现的“两条道路”,正是来自或通往新旧的道路,在作者的心中,这“两条道路”分别代表着过去与现在。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意味着什么?从过去到现在,跨越的是时空,时空跨越又意味着什么?
可以说,无论是谁,当眼里具有了时空意识之后,即使是面对同一事物,也会有不同的人生态度与感悟,这种感悟当中既有时光如水的感慨,也有斗转星移的冥想。对于冯至而言,在跨越时空的过程中,展现的是对人生的认知:原来的山居里,树林、草原、溪水……这些存在于大自然中的景物,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冯至认为是“曾经和人生过关系,都隐藏着一小段兴衰的历史”。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其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探究这样的历史价值,就可以让探究者(即读者)徜徉在历史时空当中,这也就是“路”的隐喻之一。
二、路,衔接着历史
在文中,路与历史关系极为密切。路的延伸实际上就是历史的延伸,历史的延伸就是生命的演绎,从这个角度来看,文章正是借助于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实现了对时空的跨越,通过对一个消逝了的山村的怀想,表现了大自然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文化、审美和艺术启迪,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珍爱、对生命的珍爱。[3]因此,当认为路衔接着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对路的隐喻的探究中,寻找历史与生命的生长点的时候。
我不能研究这个山村的历史,也不愿用想象来装饰它。它像是一个民族在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我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
这段话在笔者看来,有着非常大的解读空间,其中的意味之足,足以令读者对历史与生命的探究获得一个新的高度。“山村的历史”之所以“不能研究”,之所以“不愿用想象来装饰”,正是因为想将一段最为真实的历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即使这段历史像消亡在世界里的民族一样,即使其像自身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湮灭一样,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能是消亡的历史所存下的无限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指向生命的,因为人们可以“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
草木有枯荣,草木的余韵彰显着生命的存在,在这种生命延续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生命许多滋养”;村庄虽然消逝了,但曾经的“风物,好像至今还在述说它的运命”。于是,“风物”成为衔接历史的最佳载体。什么是风物啊?风物不就是生命在演绎的过程中形成的那最为朴素、朴实的民风历史吗?不就是在历史延续的过程中形成的那最为真实的一个个生命之物吗?这些延续的载体是什么呢?在文中,不就是那“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的一条路吗?
路,其所面向历史与生命的隐喻,于是又成为解读课文时可触摸的脉搏。
三、路,承载着众生
无论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还是在文人的笔下,路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事物,关于路的意蕴或者说赋予的路的意义,也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路承载着芸芸众生生活中的一切希望,只要路在往前延伸,那么希望就在心中绽放。在文中,路的若隐若现,路与山居的相互依存又相互支撑,体现的是一种极为辩证的关系。
无独有偶的是,这样的依存与辩证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冯至的原创,宋朝陆游在其《游山西村》诗中,留下了经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句中,“路”与“村”正是依存辩证的关系,在这里,路依然是希望,当在“柳暗花明”中看到“又一村”时,即使面对着“山重水复”而心生“疑无路”之感,心中也坚信希望是存在的。
同样,冯至的笔下,山村消逝了,这又怎么样呢?即使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依然可以)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而走向“生命的深处”,依然可以去探寻那“意味不尽的关连”……路,正隐喻着这种关连!
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认为,虽然冯至在四十年代只有《十四行集》和《山水》两小本著作,但是“在诗和散文两方面,他都站在‘一览众山小’的高峰”。包括《一个消逝了的山村》在内的(另外的是《山水》中的《一棵老树》)最为精纯。[4]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既准确又恰到好处,当作为读者在探究路的隐喻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寻求人与自然之间、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大千世界与人的内心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而路所隐喻的这种关系,应当是跨越时空与历史并承载起众生之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