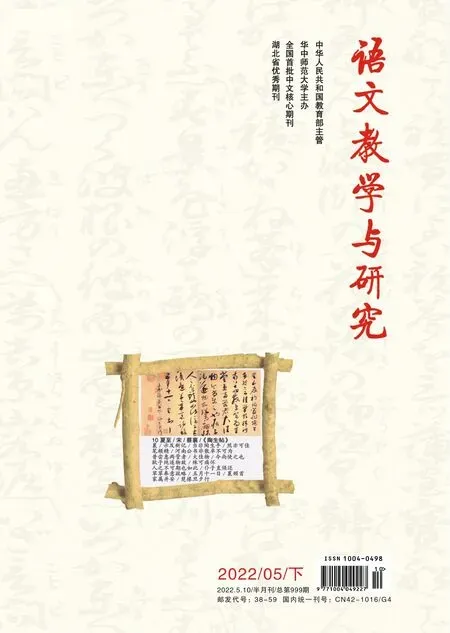透视细节描写,把握文本人物关系
◎冯慧丽
文章中人物关系的构建需要依托细节描写进行具体的展示,在进行文章阅读时,可以对文章中人物性格特征进行单个分析,寻找人物之间关系的产生,再结合细节描写,找出人物性格后的时代背景与情感动机,再围绕人物的核心关系分析叙事的必然性。细节描写可以让抽象的人物关系具体化,再运用精湛的写作技巧使得人物关系与故事发展形成系统的闭环,并呈现在书面上。
一般而言,作者为加强文章的可读性,在构建人物关系时会将细节描写融入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为动作对人物关系的精准运用,准确且具有特殊含义的动作语言能够在微妙的人物关系变化上作出细致的表现;第二,配合情境对人物关系进行处理,不同的相处交流情境会造成不同的人物关系,其中涵括视线交流、直接接触及间接接触等等,利用情境的不同可以表述人物关系的转变,以此推动情节、矛盾的产生;第三,虚实重组对人物关系的解读,通过空间、时间等抽象维度进行实向虚或虚向实的调度叙事,能够阐明人物间的关系,向读者传达作者的思想;第四,物件对人物关系的情感影响,依靠物件的意义能够传递人物的身份信息,并将人物的内核精神与物件相联系;作者逻辑技巧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不同的逻辑处理技巧可以表述出不同的情感维度。
一、动作细节对人物关系的描述
文章中人物的肢体动作承担着一定的艺术重量,有着传递情感与表现艺术的作用,从单个动作向多个动作的组合,能够输出一定的信息,让人理解。人物的肢体语言是携带着身体语义向语言交际进入的语言。具体的动作外部能够传达人物的身体语义,而其内蕴含的思想便是在一组或多组的动作间的语义交际,从而便能够让读者很清楚分辨出人物之间的关系。以礼仪行为为例,如同等身份者相互作揖,而地位低下者则低头、行跪拜礼等等。
而作者在设计人物动作时,需要确定动作与表达语义上的准确性。在进行单个造型时,作者应确定人物应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再结合几组动作,传输人物的思想,并形成对其的刻画。
如鲁迅在《故乡》中对杨二嫂的第一印象的刻画,杨二嫂先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而“我”的反应是“吃了一吓”,然后抬头观察杨二嫂“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此时的杨二嫂已经饱经这破落的时代影响,作为底层的人民,杨二嫂兼有着市井妇人的尖酸浮夸虚伪等特征,因此她的动作整体以一种荒诞夸张扭曲为基调,“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鲁迅运用了精致的动作细节表现出杨二嫂的一种病态的特征,当其与“我”产生交际之初,先是大叫,浮夸且虚伪,一副自来熟的面孔,并摆出圆规状。这与中国传统的美人形象是不同,中国传统的美人形象应是举止文雅,姿态亭亭玉立,说话细声细语,在与人交际时识礼数,欲遮还羞。在这浮夸的动作语义下与“我”记忆中的“豆腐西施”更是格格不入,使得“圆规”的形象更加深入读者的心灵。而面对杨二嫂的“咄咄逼人”,“我”的动作语言,先惊吓抬头,随之愕然,然后惶恐站起,最后摸摸站着。由此一连串的动作语言表达,使得“我”与“杨二嫂”间的关系水落石出,在作者准确的语言表达及姿态调整下,进一步的用语言阐述了“我”与“杨二嫂”间“不容”属性,从而由内及外的唤醒了读者对人物的理解。
此外,每一段人际关系间,都蕴含着不同的人物情感。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世界,人际交往间都很难维持平等关系,每一段人际关系都注定是亲疏有别的,而建立人际关系的双方,也势必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而不同情感下也势必造成不同的行为。如母子关系,母亲对儿子的关系多呈现保护、宽容、理解等,这是一种以“上”看“下”的视角,而儿子则对母亲多是顺从、叛逆、索取等。因此这段关系中的两人在进行动作表示时,有着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式。如史铁生《我与地坛》中,对母亲与“我”的关系进行了书写:“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我”心情不好,仿佛中了魔,而母亲却明知而不敢问。可知,在这段人物关系中“我”是属于主体地位的,而母亲是附属于“我”的。
二、焦点转变对人物关系的影响
文章中的人物存在着一定的相互,而这关系又由一定的行为关系支撑。作者为使得言语交际场面中人物关系显示出来,需要以点带面,在行为搭配下不断转变焦点以此形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而这焦点转变可以依靠两个以上的人物视线配合,构成线性关系,从而达到焦点转移的效果。根据人物所作出行为,如人物视线的发出构成一个抽象的放射状的线性,再通过“线”的指向转移判断画面的聚焦点。例如,人物A 看人物B,B 不看A,此时B 是焦点。这在司马迁《鸿门宴》中的宴饮中有所呈现,范增几次示意项羽动手发难宰杀刘邦,此时整个宴会上人物关系的焦点变聚集于范增与项羽两人身上,并由其行为在两人间转变方向。一般而言,人物关系有三种:及物之看、不及物之看、参半之看。当处于及物之看时,代表两个人都能够看见;而处于不及物之看时,代表两个人都有着一定的视线,但相互间看不见。参半之看:则是指一方能够看到另外一方,但另一方却没有视线看过来,即构成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之景。这种视线配合下的不断变化,便会造成焦点转移的效果。而要抓住视线配合便要通过细节描写来传达单个个体发生动作到多个个体的动作配合,并产生语义交流,形成人物之间的情感对话。
通常这类线性的细节关系形式又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将人物间的接触磨合形成动作语汇,从而展示人物关系,营造情感气氛等。但是这接触磨合并不代表其是直接性的接触,还有可能是间接性的接触。此时,细节描写在构建人物情感间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两个熟知的好友相会,握手言谈,相谈甚欢”此句为例,这属于宏观上的描写,不采用具体到个人的语言、神态、表情的文字进行刻画。而细节描写便是将这接触磨合时的细节进行放大,如“A 抬头,远远望去,那片野地上有个熟悉的白点向自己走来,他内心不由着一酸,眼角泛出了星点。近了,是老友!A 按捺着心情,快步走去。更近了!他一把抓住老友的手,嘴里嘟囔不清,夹着笑意:‘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此句,通过细节描写将人物关系中的“点”扩大,然后结合语言、神态、动作等细节描写,进行“面”的表述。这种关系不一定依靠两个人接触而产生,如诗词中“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中便运用了大量的事物进行转移情感,文中的焦点从现在转到过去,最终在情境的铺设下,将两人的关系表达出来。
三、虚实重组对人物关系的阐述
虚实重组是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表现方式,其中“实”是客观的理性存在,包括自然规律、存在事物等,而“虚”多体现于人的主观感受,包括情感、思想等。文学创作是依据空间或者时间为线索发生的事件、展示的事物进行艺术呈现的,但其在精神表达上又是凌驾于时间、空间之上的。因此,如何从现实的“实”走向精神世界的“虚”,需要作者在创作时把握好虚实结合的艺术呈现手段,借助细节描写形成有意义的叙事,并阐明人物间的关系,以此传递作者的思想,让读者更容易感悟文学中艺术思想。
(一)虚述实的空间叙事
对于人物行为而言,特定的行为需要特定的场合才能够发挥出预计效果。因此,作者需要仔细的了解场景空间以后再思考如何运用此空间构建人物关系,推动故事情节。
在文学作品中空间不仅是指现实空间还包括想象空间、思维空间等,通过细节的刻画还能够延伸到人物的内心活动空间。人物在以现实生活为叙事的过程中,多处于同时空内的物质空间,而在进行虚构性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动作语义时,则处于虚幻空间。
虚述实的表现是通过空间内的虚实转化所呈现的,在双重的空间构建中融合人物的动作细节从而构成现实的叙事发生。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便是以虚为实进行构建。一方面,作者在创作时将叙事的空间划为两个虚拟空间,让人物在其分配的空间里完成现实动作,离社会黑暗越近的人物实化,离社会现实越远的则人物虚化,在书中作者以大量的细节描写阐述了主角变昆虫的过程,并通过其对家人对亲属的表现,勾勒出了主角性格特征与其人际交往关系。在书中,变形的过程是能够被主人公感知到,并逐步以一种真实的过程所呈现出来,在这个虚构的空间中主人公的命运发展是真实的,但是他这种变化又是不被别人所察觉的,在作者笔下,除主人公在外其他人逐渐虚化,他们依旧保存着金钱交易,亲情交流等人际交往条件,但是他们却无从察觉主人公的身体变化,在作者的笔下依旧维持着以前的关系。而通过这种近距离观察与误差式的人物调配,作者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构建,完成了人物关系变化的信息。
另一方面,虚述实的过程中,虚拟空间也逐步与现实空间相融合,形成一种更深的情感构建。例如,作者为丰富人物形象会虚构出一种过去与现在所不同的人格并形成新的人物关系。在虚化的空间下,可能人物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充满和谐但在现实空间下则正好相反,人物关系充满了仇恨,嫉妒等负面因素。而在这种虚化与现实的交替中,作者会以细腻的笔法将人物间的内心猜想进行转述,从而产生新的艺术效果。
(二)实呈虚的调度叙事
文学作品中空间调度是有效的细节处理手段之一,通过有效性的调度手段处理人物的空间位置,能够达到突出人物形象特征,揭示人物内心,以及反应人物关系的效果,借助空间调度能够引导观众视线的转移,创造意境等等。
一般而言,人物在叙事中的行为动作是事实存在,但其心理上的想象活动则则为虚。实呈虚的表现即通过现实舞台构建虚幻交错的时空。这种艺术的表现打破了时空顺序的界限,借助有限的空间展现更广阔的生活内容与复杂的人物精神世界,从而调动读者在审美观察中的艺术想象力。以朱自清《背影》中“我”回首与父亲相处时的家庭关系为例,其中关于父亲呈现的人物关系是虚幻的,是“我”的记忆回顾,唯独真实的只有“我”的情感变化,根据故事倒叙的时间,作者将父子关系间的亲疏划分开来,在回忆的带动下,将现实空间融合到心理空间中,而在这心境路程中,父亲的形象与行为动作逐渐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大量的细节刻画充实了这段人物关系的动作关联,从而表达出作者对父亲的深层思念,但这种深刻羁绊又是以送别而告终,因此最后只剩下“我”的心灵独白,从记忆空间又重新回到现实空间,在送别场景的细致描绘下,以空间的调度推动了故事以及人物关系的发展。
为了加强人物关系的感情联系,作品中还加入“橘子”这一道具,如果仅仅是依靠人物的肢体语言来进行传达情感可能会让人无法带入,但是通过道具与一些微小的事物,则可以将抽象的肢体语言变成具象的信息。并且能够将这种情感的虚幻转化为实际的人物关系内容,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在文中,父亲买橘子的场面,作者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写: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
而“我”作为观察的人是在火车这一空间上,因此“我”的观察是一种全面的角度,在这一角度下,焦点便集中于父亲的身上,父亲的行为表现巨细无遗,从中“我”与父亲的关系通过“买橘”进行了具象。同时在“望”与“走”这一角度上,与文章题目《背影》相衔接,使得文章的情感层层叠加。并且,由于“我”是作为现实空间所存在的,因此,明明是父亲与“我”送别,最终却是“我”目送了父亲的背影,使得父子间的情感更加令人动容。
在文本鉴赏中,我们可以从人物关系的构建角度出发,在文学创作中细节描写与人物之间构建的复杂关系中,去分析动作、焦点以及虚实建构在细节描写中的作用,并延伸到人物关系的分析上,以此剖析文本中真实、相互纠缠的人物关系,把握人物间情感,实现对文本的深度解读与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