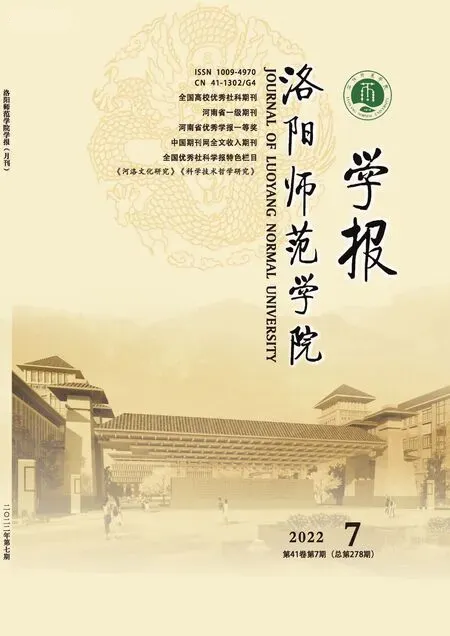孔子弟子研究辩误四题
王 峥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历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太史公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2347近年来,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孔子弟子逐渐成为关注热点并取得可喜的成就。笔者发现以往学界对部分孔子弟子的思想、身份认知有误。笔者拟对其中四种说法加以详考。
一、驳“子羔行为有缺”说
高柴,字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以孝闻名,注重“恕”道。他热衷于政治,在从政过程中能够努力施行仁政,做好分内之事。据文献记载,在卫国发生内乱之后,一同供职的子羔、子路抉择不同,子羔选择逃离卫国,而子路却捍卫道义,最终战死,从对比来看子羔的行为似乎有缺。《盐铁论·殊路》谓子羔“不能死其难,食人之重禄不能更,处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于己而薄于君哉”[2]271,学界也多认为子羔的行为是“明哲保身”,不符合儒家思想[3]。
《左传·哀公十五年》载:
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子路)。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太子闻之,惧……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4]2175
卫国内乱,卫国太子蒯聩欲杀其嫡母南子,被发现后出逃,其子成为卫国国君(卫出公)。之后蒯聩回国,当时的卫国大夫孔悝受迫发动内乱,打算废掉卫出公,但此时担任孔悝家臣的子路愤怒不已,干预了这场纷争,最终战死。在内乱发生之初,子羔曾告诫子路不要参与纷争,但子路却说“食焉,不辟其难”“利其禄,必救其患”,毅然捍卫卫出公,而子羔“明哲保身”,选择逃离卫国。这则记载表现了子路忠义、刚勇的气魄,子路之死充满英雄悲剧主义色彩,得到后人的诸多赞扬。但是作为衬托,子羔“明哲保身”的选择能被定性为“行为有缺”吗?我们认为不能。
第一,看孔子对这件事的态度。孔子在知道卫国内乱后曾有一句预言:“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1]1936这显然是根据两位弟子性格做出的判断,但在这句预言之外,孔子没有发表过任何批判子羔的言论,可见在孔子看来,子羔的行为没有问题。由文献记载可知,孔子本人倡导和秉持的从政理念是“用行舍藏”,他十分强调君子的“全身免祸”,《孔子家语·颜回》篇载:
颜回问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贤?”孔子曰:“武仲贤哉。”……孔子曰:“……武仲在齐,齐将有祸,不受其田,以避其难,是智之难也。……”[5]225-226
颜回在问孔子臧文仲和臧武仲谁更贤明的时候,孔子认为臧武仲更为贤明,原因是他能够避免齐国的祸患从而保全自身。可见在孔子看来,全身免祸、保全自己的生命是首要的,而子羔的行为恰好符合这一要求。
第二,在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逐渐兴起,“士”与“士”之间在思想和行为上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虽同属于儒家弟子,但在面对一件事时,子羔与子路的选择不必完全相同。这并非道德层面的判断,而是一种自我价值的选择。从史料记载来看,子羔并非食君之禄不干实事的伪君子,恰恰相反,子羔在从政当中表现出的思想、行为完全配得上一个合格君子,因此前人仅凭子羔出逃这一件事批判子羔,明显有失公允。
第三,子羔的“明哲保身”也并非纯粹的“明哲保身”。在对比颜回等弟子的言行时可以发现,同样是注重自我,子羔与他们的选择并不相同。面对乱世,颜回所代表的内化者群体(1)“内化者群体”的具体内涵参见拙作《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七十子”思想的传承与分化》,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不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他们完全远离政治,对社会丧失信心。但子羔不同,他没有对社会失去信心,还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践行儒家政治理想,只是身处乱世,遭遇危险时,子羔将自身性命看作第一位,选择暂时躲避,远非“明哲保身”就能盖棺论定。子羔虽然注重自我生命的安危,但他仍然愿意冒险去为拯救乱世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这一角度来说,子羔的行为不应受到苛责。我们认为,子羔在自我与外界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他的做法符合自己的思想,言行也完全配得上“君子”二字。
二、驳“樊迟背离孔子思想”说
樊须,字子迟,亦称樊迟,孔子弟子。樊迟曾向孔子请教过学农问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其思想与孔子有背离之处。《论语·子路》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6]2506
这是文献对樊迟个人兴趣的直接且唯一的记载。材料中孔子批评了樊迟,甚至谓其“小人”,可见孔子对樊迟的提问十分不满。
但是,学者们似乎都不大注意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史载樊迟的出生时间有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其“少孔子三十六岁”[1]2690,即生于公元前515年,《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则谓其“少孔子四十六岁”[5]438,即生于公元前505年。李启谦认为《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可靠,因为《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冉有和樊迟御齐之事,季氏本不同意樊迟参加,因为樊迟“弱”,“弱”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恰好与《孔子家语》的说法相符[7]198。李零则认为这段材料的发生时间应当在公元前495年之后[8]212,但他未考虑到《孔子家语》的记载情况而仅以《史记》为论。
樊迟究竟何时拜到孔子门下,文献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可稍作推论。樊迟生于公元前505年,据匡亚明考证,公元前501—前497年(鲁定公九年至十三年),孔子在鲁国短暂出仕[9]48,此时樊迟尚幼,不大可能拜入孔门学习;公元前497—前484年,孔子在周游列国[9]67-72,据《左传》的记载可知,此时樊迟在季氏手下工作,因此不大可能跟随孔子周游,但在这段时间,他应当已经成为孔子弟子(《孔子家语·正论解》)(2)据《孔子家语·正论解》载,在冉求和樊迟战胜之后,季氏曾问冉求跟谁学的,冉求说孔子,樊迟将这段话转告给了孔子,当然樊迟的转告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之后,但从材料的记载可知,樊迟当时已经成为孔子弟子。;在孔子返鲁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84年之后,樊迟才有可能真正跟随孔子学习儒家礼义[9]75。此时樊迟正值“弱冠”,对儒家学说了解不深,因此笔者认为,这段对话的记载极可能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只有先搞清楚樊迟学农发生的时间,我们才能对这段材料进行合理的分析。笔者认为,樊迟向孔子请教“农”的问题发生在他初入孔门时期,那时樊迟并不了解儒家思想,他只是就自己的兴趣来对孔子进行提问。樊迟确实对“农”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贸然向孔子进行请教,没想到遭到孔子的批评。其实不仅樊迟,其他弟子在初入孔门时也都受到过孔子的批评,最典型的就是子路。子路在初入孔门时经常被孔子批评,甚至得到过“野哉由也”的评价[6]2506。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子路由最初的“野人”慢慢蜕变为知耻尚德的君子,因此我们不能仅据孔子最初的负面评价来对樊迟进行定性,认为他背离了孔子思想。
由文献可知,樊迟对儒家学说是虚心求教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6]2462
樊迟问知,子曰……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6]2479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6]2504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6]2504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6]2507
从记载来看,樊迟对礼、知、仁都进行过询问,尤其是“仁”,樊迟曾多次提问,可见樊迟希望了解并掌握儒家思想,这非但不能认为他与孔子思想产生了背离,反而能证明他对孔门学说充满了渴望。
此外从孔子对樊迟的解答中,我们也能得出一些结论。当樊迟向孔子询问“仁”时,孔子这样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先事后得”,都强调了先付出再获得的原则。李启谦认为,孔子这样回答反映出樊迟急于求成的思想[7]199。但笔者认为,孔子的回答体现的是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前文已述,樊迟对“学农”抱有浓厚的兴趣,当樊迟向孔子请教“仁”的时候,孔子在面对一个初入儒门的学生时,会从他擅长且熟知的角度进行解说。孔子认为,“仁者先难而后获”“先事后得”,正是从付出与回报的角度来对樊迟进行的解答,这与“做农活”的核心思想一致。孔子这样解说自己的“仁学”,是希望樊迟能够从熟悉的事物入手,尽早熟悉儒家学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樊迟与孔子的思想并未发生背离,“学农”只是樊迟的个人兴趣而已。
三、驳“公伯寮非孔子弟子”说
公伯寮,字子周,亦称公伯缭。对于公伯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将其列为弟子,名列24位,但《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却没有将其纳入。公伯寮最有名的事件是诽谤子路,因此前人对其身份多有怀疑。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李启谦《公伯缭非孔子弟子辩》认为公伯寮并非孔子弟子:
第一,……从前后文看,公伯缭攻击子路,实际上就是攻击的孔子……背后攻击老师,在孔门弟子中是没有先例的。
文奇的“奇点”理论提出后,并没有立即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只是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如库兹韦尔。库兹韦尔于1990年出版《智能机器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一书,认为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升,未来经过足够多的时间,人类将会创造比他自身更聪明的实体[27]。库兹威尔的推断是基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及技术的加速循环规则。
第二,孔子和他的学生有着相互支持互相保护的关系,如果公伯缭真是孔子的弟子,子服景伯就不会在孔子面前表示愿派人把公伯缭杀死示众。
第三,孔子对他的学生的不规言行,都是进行教育批评的,甚至对冉求还说出“非吾之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的话来。而公伯缭做出这样的事情后,孔子既不教也不责,只是表示了个不怕的态度,可见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师生关系。[7]194
李启谦列出三条证据说明公伯寮并非孔子弟子,然而这三条证据有疏误。
在第一条证据中,李启谦认为背后攻击老师的情况在孔门中没有先例,公伯寮攻击了孔子,因此他不是孔子弟子。诚然,从文献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中没有直接攻击孔子的先例,但在现实当中,师徒反目,师生相互攻击的现象屡见不鲜。公伯寮攻击孔子,不能仅据此认为他并非孔子弟子,这只能说明公伯寮和孔子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再者,公伯寮并没有直接攻击孔子,他攻击的是子路,公伯寮攻击子路的行为,很可能是他碍于师生之间的面子而作的妥协,这恰好能够说明公伯寮与孔子之间存在着师生关系。我们认为,从攻击孔子的角度来否定公伯寮孔门弟子的身份,这样的推论不能成立。
在第二条证据中,李启谦说孔门弟子之间是互相保护的关系,如果公伯寮真是孔子弟子,那子服景伯就不会有杀了他的想法。然而,无论是《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还是《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子服景伯”都未被列入孔门弟子之列,虽然清代的朱彝尊据汉代鲁峻石壁画像认为子服景伯可能是孔子弟子[10],但这至少说明他的身份是不确定的。我们认为,与公伯寮相比,子服景伯的“七十子”身份更应存疑。李零认为,“子服景伯对孔子这么好,杀人的事都敢干,前人宁愿相信,他才是孔子的弟子”[8]237,可见“子服景伯”的身份反倒更像后人加上去的。以此看来,子服景伯要杀掉公伯寮,完全不用顾忌什么师门间相互保护的原则,因为他们之间可能并没有实质性的同门关系。
在第二证据条中,李启谦认为,孔子对公伯寮的诽谤没有采取教育行为,而是表达了“无惧”,这不像老师对学生做的事情,因此公伯寮不是孔子弟子。但笔者为,正是由于公伯寮诽谤了子路和孔子,触犯了师生之间的大忌,所以孔子才会对公伯寮完全失望。在孔子心中或许已经产生将其逐出师门的想法,因此他才不再对其说教,这与孔子呵斥冉有、樊迟、子路、宰我等情况完全不同。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学界认为公伯寮言行有缺,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是孔门的“犹大”[8]236,但这些说法都不能否认他曾是孔门弟子的身份。他的诽谤师门,只能说明他和孔子之间产生了较大分歧。笔者认为,这种分歧的最大可能是在思想层面。
四、驳“两个司马牛”说
司马耕,字子牛,亦称司马牛,孔子弟子,其言行事迹主要见载于《论语》。除《论语》以外,《左传·哀公十四年》也记载了一个司马牛,他是宋国桓魋的弟弟。历代评注家皆认为这两个司马牛是同一个人,然而杨伯峻却予以质疑:
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和宋国桓魋的弟弟司马牛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难于混为一谈。第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既不说这一个司马牛是宋人,更没有把《左传》上司马牛的事情记载上去,太史公如果看到了这类史料而不采取,可见他是把两个司马牛作不同的人看待的。
第二,说《论语》的司马牛就是《左传》的司马牛者始于孔安国。孔安国又说司马牛名犁,又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司马牛名耕的不同。如果孔安国之言有所本,那么,原本就有两个司马牛,一个名耕,孔子弟子;一个名犁,桓魋之弟。但自孔安国以后的若干人却误把名犁的也当作孔子学生了。姑识于此,以供参考。[11]
杨伯峻认为《论语》与《左传》所载的“司马牛”为两人,对此,笔者认为,杨伯峻的论据有可商榷之处。首先,杨伯峻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不载司马牛之兄造反一事而认为二者不是一人,但从事实来看,《史记》所载的内容并非全部,其遗漏的史料并不在少数。此外,《史记》的叙述特点有“互文见义”之处,所以在《仲尼弟子列传·司马牛》中不载《左传》一事虽有可疑,但不能完全证明这个“司马牛”另为他人。其次,杨伯峻以二者名称不同而发起怀疑,但二者名称虽异,却仍为相关,“犁”“耕”二字语义相类,这恰恰代表两个司马牛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这一推论不乏先例,如“漆雕开”,“开”是名,然《汉书·艺文志》载《漆雕子》一书注谓:“孔子弟子漆雕启后”[12]。郭沫若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中认为,“启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13],可见“漆雕启”“漆雕开”二者同一。再如“高柴”,“柴”为其名,然上博简《子羔》篇其名却为“钤”,马承源注谓:“‘钤’字与今本文献对应者,只能是子羔之名……‘钤’从金、今得声,古从今声字有不少音变,此字音读当与‘柴’音相近……但简本早于后世传本,或子羔名本作‘钤’。”[14]可见仅以姓名不同而断定二人身份有异也不能成立。
今人文俊威在杨伯峻的基础上又提出一些论据。《论语·颜渊》篇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6]2503对于司马牛忧心的理由,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认为:“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忧其为乱而将死也。”[15]而宋人陈祥道在《论语全解》中认为:“司马牛忧无兄弟,非无兄弟也,无令兄弟(即无好兄弟)也。”文氏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成立,因为依据史料,“宋公是没有打算把向魋(按:即桓魋)一家人都斩尽杀绝的。所以司马牛‘忧其为乱而将死也’是没有必要的。当然,司马牛更不是‘无令兄弟’了,除了向巢外,他的另一个兄弟子车在向魋谋反时也说:‘不能事君,而又伐国,民不与也,只取死焉。’说明子车也是反对向魋谋反的,因此陈祥道的观点也不成立,所以《左传》的司马牛与《论语》的司马牛是两个人”[16]。
笔者认为,司马牛的“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主要抒发了一种孤独寂寞的感受,但在这种孤独寂寞之外,其实还有他对兄弟的埋怨,这个埋怨主要针对的是桓魋。如《左传》所载,司马牛的兄弟桓巢和子车并未同桓魋一同作乱,甚至还进行了劝阻,但这不能否认桓魋作乱的事实,更不能认为司马牛此时抒发孤苦寂寞之感是虚假的。司马牛的感叹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这只是一种情感的抒发,而情感的抒发带有主观性,它不全是客观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因此从对这句话的理解当中我们也不能断定《左传》中的司马牛必非《论语》中的司马牛。
当然,文俊威所提供的另一证据值得我们思考。文俊威认为:“向魋作乱是在哀公十四年,然后向魋之弟司马牛先后去了齐国、吴国,然后回到宋国。后面‘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与‘卒于鲁郭门之外’应该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即司马牛想去投奔赵简子或陈成子,却半路上死在了鲁国的城门前,也就是说司马牛并没有真正到过鲁国,和孔子的对话也无从谈起了。”[16]据《左传》的记载,事实似乎确实如此,司马牛最后没有踏入鲁国的大门,但《左传》载“阬氏葬诸丘舆”,杜预注谓“阬氏,鲁人”[4]2174,可见司马牛是由鲁人最后埋葬的。如果司马牛之前未曾踏入过鲁地,或者与鲁人没有任何交情,那为何最后埋葬他的会是鲁人?这其实也存在矛盾。
笔者认为,《左传》载录的内容应当隐藏了一些信息没有全部表达出来,这是史书记述的一种缺失。史书对历史内容的记载通常会保持一定的完整性,其突出某一主题而对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加以节省,这就造成了史料之间的矛盾和抵牾。针对司马牛这个例子而言,我们更倾向认为《左传》和《论语》所载为同一人,这个司马牛在一个于史无载的时间向孔子求学,并在鲁国活动过,他的一些言论应当是发生在鲁国无疑。司马牛的“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很有可能是他对桓魋之乱的一种预见,这个时间应当在他最后逃亡之前。在桓魋发动内乱期间,他预见了桓魋的结果,于是曾短暂地住在鲁国并发表了一些感慨。在这之后,司马牛又回到宋国,在桓魋之乱发生后他开始逃亡。司马牛最后应当是死在重回鲁国的路上,由于其人际关系,鲁国的阬氏最后埋葬了他,并将他葬在了丘舆。
总之,从现存文献来看,笔者无法断定当时存在着两个“司马牛”。在将《左传》和《论语》结合分析之后,笔者反而发现了二者身上存在许多思想和言论的共通性。因此笔者仍然赞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将《左传》和《论语》中的司马牛看作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