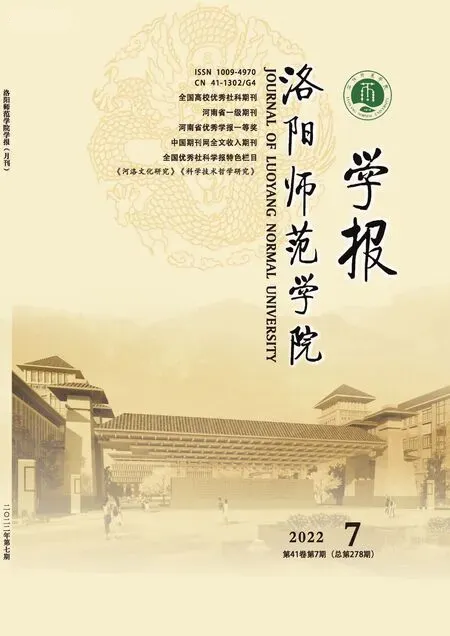事实与撕扯的“事实”
全林强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撕扯”一词来自陈波《“以事实为根据”还是“以证据为根据”》一文,用来形象地描述具有主观性的“事实”的形成。“撕扯”包含了撕扯的主体和受体。陈波认为:“‘事实’是认知主体带着特定的意图和目标,利用特定的认知手段,对外部世界中的状况和事实所做的有意识的剪裁、提取和搜集,因而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混合物。用一种更形象的说法,‘事实’是认知主体从世界的母体上一片片‘撕扯’下来的;认知主体最后撕扯下来一些什么,取决于他们‘想’撕扯什么、‘能’撕扯什么,以及‘怎么’撕扯。”(1)参见陈波:《“以事实为根据”还是“以证据为根据”——科学研究和司法审判中的哲学考量》,《南国学术》2017年第1期,第22—38页;《客观事实抑或认知建构:罗素和金岳霖论事实》,《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第17—29页。撕扯的“事实”实际上是陈波放弃以事实为基础的实在论,提出新符合论的前提。“事实”包含了主观意志,导致事实有可能“撒谎”,无法为“真”概念提供实质性的作用,而致力于“塑述一种不使用‘事实’概念的新符合论”。(陈波:《没有“事实”概念的新符合论(上)》,《江淮论坛》2019年第5期,第5—12页;《没有“事实”概念的新符合论(下)》,《江淮论坛》2019年第6期,第120—126页。)尽管陈波不支持“事实”观作为真命题的基础,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种事实观,因此,本文把陈波作为这种事实观的代表,而并不是针对他的新符合论。也就是说,“事实”并不是纯粹的客观实在,而是被主观所决定的,而“撕扯”是塑造这种“事实”的过程。当我们说“鲁迅在写作”时,这种“事实”观所提示的不仅是鲁迅在写作这个特定的事实,而且是“鲁迅”作为一个与众多鲁迅相关的事实的载体——陈波引用的金岳霖的“东西”。我们之所以没有从“鲁迅”身上发现其他的事实,而仅仅聚焦于“在写作”,这里体现了我们对于鲁迅作为一个“作家”的职业的期望,或者我们想用这个事实体现鲁迅是个作家的意图。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说“鲁迅在写作”这个语句时,我们需要关注鲁迅作为一个众多事实的载体的地位,而不是仅仅关注鲁迅在写作这个事实呢?当我们说“陈波在北大上课”时,我们是否必然联想到“陈波是北大的著名教授”“陈波是著名哲学家”等等?
当我们说“鲁迅在写作”“陈波在北大上课”时,所陈述的是一个事实,它确实包含了一个承载这个事实的行为主体,但是,我们是否真的要把这个行为主体作为我们的关注对象,而不仅仅是这个事实呢?我们从对一个事件的关注转移到对一个载体“东西”的关注,是否具有合理性?这种“撕扯”包含了一种整体论的视角,使得我们所关注的事实“鲁迅在写作”依附于“鲁迅”这样一个整体论概念。这种整体论消解了事实的“使真者”知识论功能,转移到了选择性的意志功能;从事实作为语句为真的保证,转移到了该语句为什么会从语句集中被挑选出来,比如“鲁迅在写作”“陈波在北大上课”为什么会从“鲁迅”“陈波”所具有的众多属性中被挑选出来。这种转化,就不得不关注说话者在做出这个选择时的意图,因此,“事实”被说话者的意图所介入,转化为说话者的“想”“能”“怎么”。
我们用引用“撕扯”来代表一种主观主义,这种主义认为事实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是由意志塑造的,并且这种理论包含了整体论框架,即把事实视为一个拥有众多属性的载体的其中一个属性,而意志决定了为什么我们提取的是这个事实,而不是那个事实。这种“撕扯”的整体论框架包含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故意的陷阱”困难,以及我们将放弃这种主观性的“证据”,而回归到不同于陈波所理解的“金岳霖”的金岳霖的实在论立场。
一
从知识论的视角,我们承认人类的认知能力的限制,即没有人具有整全性的视角,每个人都可能由于认知的有限性而对事实的判断产生错误的结果,这点是没有疑问的。承认事实认知的可错性是我们与陈波所共享的立场。区别在于,我们无法容纳为错误的判断所提供的合法性证明。我们承认事实的判断是可错的,目的在于修正这种错误,而“撕扯”是试图为错误提供合法性证明。甚至,陈波从现代司法制度层面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从司法效率等方面讲,我们也赞同司法取证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但是,把这种局限性建构在主体意志之上,而不是主体的客观有限性之上,这点让人无法接受。因为一旦这种理论承认了主体意志介入“取证”的合法性,那么就意味着按照意志剪裁有利的证据将是合法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而是说,“撕扯”已经显著地使之合法化。如果我们不赞同这种主张,那么我们就要指出这种“撕扯”整体论包含了某种困难,而这里我们称之为“故意的陷阱”。
在平常的事例中,“鲁迅在写作”“陈波在北大上课”,“撕扯”并不会导致什么恶果,反而会加深我们对于“鲁迅”“陈波”等对象的理解。当我们把上述两个事实纳入“鲁迅”“陈波”整体论范畴中时,可以关联我们对于“鲁迅”“陈波”的信息,获得更深刻的认知,如“鲁迅如何创作一篇深刻的短篇小说”“陈波如何上一堂精深的逻辑学课程”。至少“撕扯”在这些事例中是无害的,尽管我们不明白“鲁迅在写作”“陈波在北大上课”为什么必须纳入“鲁迅”“陈波”的整体论中而得到理解。
但是,我们描述这样一个日常可见的场景:有某人Q正走在大街上,当他走到一个街道口时,发现有一个小孩在街道中间玩耍,不远处有一辆汽车直撞向这个小孩,小孩浑然不知。我们假设汽车司机没有发现这个小孩,也没有刹车。如果Q不救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必受重伤,甚至死亡。假如救这个小孩,那么Q必须抱起这个小孩往旁边的街道里躲闪。此时,躲闪的街道是通向其他地方的,并且没有人。
这是一个“好人好事”的日常场景,Q救了这个小孩本身是一件好事,或者“有良知”的事,也是值得赞扬的。我们也认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应该做的,并且,假设Q也是这样认为的。按照常识,小孩身处危险这个事实给予了Q施救的理由,以及Q救了小孩的事实使得“Q救了小孩”命题为真。这种论断符合我们“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直观,即“Q救了小孩”为真,是以所直接观察到的事实(而不是“事实”)为根据的,不包含事实背后的观察者的意志。
对于“撕扯”而言,“Q救了小孩”包含了众多事实的载体“Q”,当我们说“Q如此这般”时,本质上包含了我们这么说的原因,即我们为什么会在面对Q这样一个整体论的实体而选择说“Q如此这般”而不是“Q如此那般”。此处在“Q救了小孩”与Q之间插入了“间隙”:说话者的意志。此处,“Q救了小孩”并不能直接由Q救了小孩而使真,而由说话者的意图、目的来决定。虽然陈波称“事实”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混合物”,但是“撕扯”本身就说明了主观性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假设我们与Q不认识,我们会赞赏Q的所作所为。但是,假如我们知道Q曾经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如上所述,要救小孩就必须抱起小孩往一条无人的街道跑去。那么,依据“撕扯”的整体论,我们对Q的认知包含了“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并且我们也把“是个坏人”这一评价归属于Q。当我们发现一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抱起一个小孩往一条无人的、幽深的街道跑去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将是:“Q在抢小孩”。即使小孩处于险境时,我们仍然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撕扯”的整体论赋予了我们利用所拥有的知识背景的权利,对于Q,我们可能更关注“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在这个事例中,Q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救这个小孩,没有产生任何歹念。但是我们仍然会认为Q是在抢小孩,或者借着险境的掩饰来抢小孩。“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这种认知所产生的负面评价的期望,介入了事实与事实之为真之间。在这个事例中,意志掩盖了事实,或者取消了事实。因此,当意志介入到事实与真之间时,实际上无法保证“撕扯”的另一面“客观性”是成立的。Q被我们期望他之所是的形象定义“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而Q救小孩脱离险境的事实没有在我们的期望中获得考虑。因为一旦我们拥有“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期望,“Q救小孩”的事实就被扭曲了,成为我们对于Q的期望的定位一个示例:Q是一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他正在抢小孩,或者他正在利用小孩的险境来掩饰抢小孩的行径。甚至,Q能够懂得利用任何突发事件来进行他的违法的勾当,他是一个“高明的”,且“极度危险的”人贩子。我们把这种例子称为“故意的陷阱”。即当某个事实被当成整体论意义上的载体的属性而进行联想时,事实被联想者的意志所消解,或者所包裹,事实转变为联想者的“故意”的意志表达。这个“陷阱”对载体而言,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这个比喻要表明的是,事实的客观性和真的本性的丧失。
事实并非不可错的,比如在后期的调查中,Q的行为被证明是“有良知”的行为,那么我们面对这个证据时,就需要修改我们的描述及评价。这点,我们相信陈波也是如此。我们这里的分析指出的是,这种“撕扯”的整体论,使得假事实的信念合法化,这点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的主张是,我们之所以相信“Q救了小孩”,因为事实直接使之为真。
二
事实与真之间没有嵌入主体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实在论主张。Q救了小孩的事实是真的保证,而说话者意志构成了对于真的干扰。意图、期望等等这类主观意志的介入与认知的有限性是有本质区别的。比如说,在我面前有一块广告牌,恰好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到Q抱着小孩往无人的街道里跑去,那么我就会做出“Q在抢小孩”陈述。但是,与“撕扯”不同的是,承认认知的有限性并不会授予“Q在抢小孩”以一种合法性证明的权利。“Q在抢小孩”是一个受到错误的认知所导致的错误陈述,它是客观的、是真的,但它可能是错误的。“撕扯”的“事实”无论正确与否,都是主观意志的表达,不是客观的、真的,是依赖于主体意志的。
陈波论证“事实”的主、客观性的混合性时引用了金岳霖的事实的观点,认为金岳霖关于事实的说明中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紧张。实际上,这是误解。金岳霖虽然认为“事实有知识者的接受和安排”[1]780,“化所与为事实”[1]741,但是“所与”在金岳霖的知识论中是纯粹客观性的。“所与”与“呈现”二者是有差别的,“呈现”是有主观的或者客观的,但是“所与”却是纯客观的。当金岳霖说“化所与为事实”时,它指事实是由纯客观的“所与”来构成的,“事实总是客观的,它底材料总是所与”[1]739。金岳霖虽然认为事实是混合的,但是他指的是“意念”与“所与”的混合,“事实是一种混合物,它是意念与所与底混合物,我们既可以说它是套上意念的所与,也可以说是填入所与的意念……事实确实是混合物”[1]741。“意念”不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心理状态,而是共相,“意念是抽象的、普遍的,它所表示的是共相或共相底关联”[1]586。因此,当金岳霖说“事实确实是混合物”时,并不引起主观意志的介入,也不会导致事实的主观化。
“这朵花是红的”,由“所与”和“意念”所组成,是纯客观的,是共相的关联,本质上无法包含主体意志。但是,按照“撕扯”的整体论,“花”作为众多属性的载体,是一个整体论的概念,而当我们说“这朵花是红的”时,包含了我们为什么要在众多属性中挑选出颜色“红”,而不是形状“圆的”、味道“香的”等等。之所以选择颜色“红”必须涉及我们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所隐藏的意志性或者意向性,是这种意志性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说“这朵花是红的”,而不是“圆的”“香的”。这种主张凸显出陈波的“事实”与金岳霖的事实的根本性差异。金岳霖在分析主、属性问题时也曾经指出,观察者的意向性会造成观察侧重点的不同,“在我们当前的呈现或所与之中,有一呈现或一所与是可以引用‘白’‘纸’‘长方’……去接受的。这一呈现就是那样,没有所谓主性与属性,我们可以说它是白的,或者它是纸,或者它是长方的,这要看我们底兴趣所在。如果我们底兴趣是颜色,我们会说‘这白如何如何’,如果我们底兴趣在写字,我们会说‘这纸如何如何’”,但是,他却坚持认为这不属于知识论的范畴,“从这一方面着想,主属性底分别有用处。这分别虽有用处,然而本书亦不必利用,本书只承认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法而已”[1]582。知识论所要求的是共相的客观性理论,而不是主观意志的表达,“主观的世界在别的方面也许重要,也许在艺术方面重要,这颇难说。无论如何,在知识方面不重要。知识总是客观的。知识底根据总是客观的呈现”[1]489。
单纯从知识论来讲,金岳霖所谓的“事实有知识者的接受和安排”实际上排除了主体意志的介入,纯粹是包含“理”的事实,“所谓事实本来就是以意念去接受了的所与,而以意念去接受了的所与,假如我们没有错的话,就是以理去接受了的所与。事实本来是有理的”[1]661。但是,如果我们要问,观察者是否可能排除主观意志而得到纯客观的事实,那么只能回答说,对于金岳霖而言,尤其是在知识论层面,他并没有准备给予关注,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注重客观性的知识理论,而意图、期望、目的等意志性要素被排除在了知识论范畴之外。因此,这里我们无法赞同陈波对于金岳霖的解读,因为他把金岳霖所排除出去的要素又抛了回来。
事实是一种客观性,是真的,并不是说是不可错的。比如广告牌对我的视线的遮蔽,即使所做出的事实判断是错误的,它仍然是客观的、真的。如果Q在抢小孩不是事实,那么“Q在抢小孩”就不是真的,是完全由这一事实所决定的。而对于“撕扯”的整体论而言,“Q在抢小孩”不是由Q在抢小孩的事实所保证的,而是由我的意图、期望所保证的。假如我仍然坚信Q是“死性不改”的,那么我就不可能说“‘Q在抢小孩’是假的”是真的。“‘Q在抢小孩’是假的”无法动摇我对Q的根深蒂固的印象,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有一系列整体性的、相互辩护的、融贯的信念证明“Q在抢小孩”。
我们的主张是前者,“就事论事”,认为事实本身保证了真,或者事实本身即是真,当我们说“这是事实”时,实际上是指“这是事实,这是真的”。实际上,金岳霖是也这样主张的,他认为“真命题不一定是事实”[1]750,但是事实必定是真命题所描述的[1]755。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在于客观性的“意念”“所与”组成的描述自然项目与类之间的共相的关联,即事实表现在类“有观”中自然的共相的关联。
自然是有规律的,但自然是没有判断的,只有在“所与”和“意念”把自然的规律客观地组建为时空中的事实,以命题来表达,才具有判断性。比如说,地球绕太阳公转,这一自然项目不包含判断,而把“地球”“绕”“太阳”“公转”等“所与”组建成“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命题时,它描述的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共相的关联,“地球绕太阳公转”就是事实。金岳霖所强调的事实的客观性、真理性的共相的关联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当我们说一个事实命题为真时,甚至我们并不是指称一个世界中的真实存在的实体,而是指称这样一种共相的关联,比如我们说某个类似于太阳与地球的质量、距离比例的系统,那颗类似于地球的行星必然绕太阳公转。假如我们在宇宙中无法找出我们所设置的具体的、特定的质量、距离数据的类似于太阳和地球的实体,我们仍然能够说这是一个事实,是真的。
金岳霖的“事实”与“自然项目”的区分,在知识论上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立场。当我们面对一些简单的陈述“桌子上有一个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时,我们要判断这些语句为真时,如果不想步入融贯论的立场,可能就会选择符合论,也就是确实桌子上有一个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金岳霖实际上不能赞同这种方案,事实是所与和意念组建的,因此它也必然是命题式的,因此事实与命题之真是一回事,因此不能用符合论。事实是共相的关联,是“固然的理”的体现,“遵守固然的理的命题的只是事实”,而“固然的理”属于自然的范畴,不受我们的意志所更改(2)金岳霖描述了“固然的理”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它不是我们所创作的。寒暑表虽是我们所创作的,然而水银和温度的关系不是我们所创作的。第二,它是非遵守不可的。不遵守它,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结果。第三,它不是随我们的便(见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94页)。。也就是说,凡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都是事实。
三
符合自然项目的规律都是事实,这种主张带来了一个问题:在“桌子上有一部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事例中,如何判断这个命题为真。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水杯”“手机”都有可能在“桌子”上出现,而这些“所与”:“桌子”“上”“有”“一”“个”“水杯”“部”“手机”所组成的命题“桌子上有一个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当我们接触到上述场景时,就会产生一种“客观感”(3)“客观感”“实在感”是指精确的测量“度量”所带来的“靠得住”的感觉,金岳霖主要是在“量”这个范畴中使用的,认为精确的“量”比传统的“质”的办法更具有可靠性,用“量”化“质”更具客观感。金岳霖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我们认为“客观感”这个概念在不那么需要高精确度的事例中,也可以使用,至少金岳霖也认为在传统上,知识尚未发达之时,也有“质”的客观感。而在我们上述事例“桌子上有一个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中,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客观感、实在感,这种感觉验证了事实。(参见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2—703页。)。由于“客观感”的出现,我们自然而然地验证了“桌子上有一个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的事实。“客观感”实际上在事实命题和自然项目之间进行了沟通。事实是共相的关联,“水杯”“手机”与“桌子”的共相“上”关联并不违反自然项目的规律,是“固然的理”的事实,而我的视线所及之处使我产生了“客观感”,意味着事实得到验证。在自然项目和命题的真之间获得了验证。
当“所与”是正确的运用时,就能够保证“桌子上有一个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的客观性,因此就为真。但是,这里我们要重申的是,客观的、真的,并不等于不可错的。实际上“水杯”是一块木头,“手机”是一个机模的时候,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说“桌子上有一个水杯”“桌子上有一部手机”就是错的,但仍然是客观的,因为这两个语句的运用并没有包含任何的主观性纠缠。
与陈波要求的事实的判断需要主体意志的介入不同,金岳霖强调纯粹的客观性的判断。金岳霖的理论,尤其是“客观感”提供了反驳陈波“撕扯”的整体论一个很好的工具。当我们有这些“所与”时,我们在面对水杯、手机能够在“所与”中映射的自然项目时,我们会产生“客观感”。比如,当我看到右手边的保温杯时,我产生一种实在感,或者客观感,也就是它能够映射在我的“所与”中,并且这是真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的右边或者桌面上没有水杯,而有人对我说,“你的右边有一个水杯”,那么,当我的视线所及之处我没有发现与“所与”的映射物,就无法产生客观感。
客观感是纯客观的、受动的感觉,当其所指向的事物缺位时,这种感觉就无法产生。如果我的右边没有水杯,或者有的不是水杯,当你说“你的右边有一个水杯”时,那么我的客观感不会出现,或许我所产生的是疑问:“为什么你会说有一个水杯?”此时,我不会怀疑我的视线所及而得到的结果。
在Q的事例中,如果Q抢在孩子被汽车撞上之前抱起孩子往无人的街道里跑去,在我的“所与”中“汽车即将撞上孩子”“Q抱起孩子跑开”“进入无人的街道里”都得到事实“Q抱起孩子往无人的街道里跑”的映射,产生客观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Q确实救了这个孩子。我不可能因为看到Q抱起孩子迎着汽车撞上去而产生Q救了这个孩子的客观感。因为按照自然项目的规律,我们都知道被汽车撞上会死或者严重受伤的。因此,事实充实了我的客观感,验证了“Q救了孩子”的判断。
这种主张不需要主体意志的介入或者纠缠,因此保持了判断的客观性。我们并不否定Q也有可能是在借机拐卖小孩,但也不肯定,因为这个事例并没有进入对于Q拐卖小孩的客观感的充实之中。如果Q抱起小孩跑了好几公里,而孩子的父母一直在后面直追,Q就是不归还,那么此时Q拐卖小孩的事实就充实了我们的客观感,我们将作出“Q在拐卖儿童”的判断,但是,至少在上述事例中,是无法得出这个判断的。
我们的主张是“就事论事”,事实本身给予了判断的根据,不需要主观意志的介入。观察者的介入并不一定会引起主观化,这是金岳霖的事实观给予我们的启示。强调事实与完全受动性质的“客观感”,可以有效地阻止主观意志的介入。这点建立在承认自然项目只有规律但没有判断的观点,把判断设置在所组建事实之上。这点与杨国荣区分自然和“事”二分有所不同。杨国荣把“事”看成人的意义的生成的过程,尽管意义的生成是与自然属性相关的,“表现为事实界和价值界的统一”[2],但是“事”过多地强调人的意志性及意义主体性创造。金岳霖的事实则相反,“所与”“意念”是客观的,由“所与”“意念”所组建的事实是被动地接受的,尽管金岳霖也说“安排”,但是,这是根据自然规律而进行的客观性的安排,因此,“它是接受了的,安排了的,所与,也就是接受了的,或安排了的,自然项目”[1]767。在自然项目与事实之间没有空隙,主观意志无法介入,因此无法产生人的意图、期望、意义等主观主义色彩的理论。
我们之所以批判“撕扯的事实”,是因为他给予了主观性对于客观性的绝对优先性。我们所作出的判断不是出于事实自身,而是出于我们所理解的“事实”。“事实”是我们自身规范性的产物,是我们对我们自身理解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对事实理解的结果。因此,事实被忽略了,这将导致“以事实为根据”的常识受到伤害。我们要承认的是,我们的实在论没有给予主观心理足够的关注,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个体的隐秘性的、任意性的心理过分的信任,使得我们陷入上文所讲的“故意的陷阱”之中,这种陷阱类似于我们日常所讲的“一厢情愿”。我们并不否定这种“一厢情愿”是有意义的,至少对当事者而言是有意义的,比如我曾因我的孩子被拐卖而痛苦,导致我对于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深恶痛绝,凡是人贩子或者曾经是人贩子的人对于我而言都是这世界上最大的恶,那么对于一个人贩子的任何行为,即使他已经改邪归正,如Q,都会得到我“一厢情愿”的“恶”的定义。即使这种“一厢情愿”的结果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仍然说它不是客观的、真的。这种“撕扯”本质上是以主观意志为依据的,因此它所得出的“事实”不是客观的。“事实”无法作为判断的根据。
四
由于我们所关注的是事实,而没有把事实与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关联起来,给人的印象是过于浅薄。比如在Q事例中,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Q实际上是在抢小孩,而该事实并没有把这些证据显示出来,我们是在做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判断。这种批评,假如有的话,那么我们也不会赞同。因为“就事论事”所反对的是主观意志对于事实的介入,确保事实的客观性,而无法确保事实是正确的。事实作为举证,最重要的是客观性,如果Q在之前一刻还在干着拐卖小孩的非法勾当,并且被我所见,那么Q现在抱起小孩向无人的街道跑去就坐实了“Q在抢小孩”的事实。这里并不包含我对于Q的“故意”,Q在之前一刻还干着拐卖小孩的非法勾当,依据这个事实做出“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判断是真的,符合自然项目Q的本质规律。而Q现在抱起小孩向无人的街道跑去充实了客观感,由此我做出“Q在抢小孩”的判断。“Q在抢小孩”是客观的,是真的,并不是说它是不可错的,而是在符合自然项目Q的本质规律下,我的客观感的充实性验证了Q在抢小孩的事实。但它可能是错的,因为Q的行为可能是“有良知的”。如果我所观察到的是Q抱起小孩向无人的街道跑去,待脱离了风险后,Q放下小孩自己走了,那么我所观察到的就无法充实“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客观感,“Q在抢小孩”的事实就无法成立。“就事论事”的实在论不要求“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信念的结构化,而是伴随事实而动。
与“就事论事”的实在论相反,融贯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整体论的结构的稳定性。即使存在着能够推翻这种结构的事实,但是由于这种稳定性,也可能对接受新的事实产生抗拒力。比如Q已经痛改前非,并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基于我所形成的Q是人贩子的整体观念而言,即使Q确实是真心救了小孩,我也仍会相信他的行为是在“抢小孩”。这种类似的事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如在2021年的疫情期间,相信政府隐瞒疫情的人,尽管在政府部门公布的权威的、准确的疫情数据后,仍然会相信数据造假,而宁愿相信道听途说的东西。这种反常现象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故意的陷阱”。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其内构成了一整套稳定的、融贯的辩护机制。当外在事实构成了对这种信念的挑战时,这种结构会排斥无法容纳的事实,而选择与其兼容的其他信息,比如说各种离奇的谣言。
融贯主义恰好为这种“故意的陷阱”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在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的协调样式的理论中,比如苏珊·哈克(Susan Haack)的“基础融贯论”,要求感觉证据和内省信念的相互支持,虽然她并不认为这种相互支持的“循环”是困境,但是她所谓的二者“被部分地证成”[3]中的“部分”是什么意思,这点我们是可以提出疑问的。比如在Q事例中,“Q救了小孩”的事实如果无法推翻我的“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整体信念,那么即使Q救了小孩是真的,对于这一事实的感知仍然无法得到证成。苏珊·哈克没有讨论如果感觉证据与内省信念相冲突,我们该如何抉择。是放弃感觉证据,还是放弃内省信念的连贯性?如果融贯论或者整体论要求的是结构的稳定性,像吉拉·谢尔(Gila Sher)的基础整体主义“高度结构化”,那么我们无法理解“基础”一词是如何在理论中发挥作用的。对于结构内的纠正,像纽拉特之船,拥有一个坚固的内部结构足可以支撑谢尔所说的“立足点”[4],那么,我们说它根本不需要联系与世界相关联的事实,仅从其内部就可以消化掉。
异常的外部事实是无法介入融贯的、整体的结构中发挥作用的,比如我对于Q是个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坚决的信念。陈波过分夸大了“广义的反思平衡”在纠正、调整等层面的作用,毕竟这种反思本身没有可见的操作性。从知识论的角度上看,对于内在结构特征的反思是有利于对于真理的发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真理的认知是以我们的意志结构为前提的,由于这种反思本身受到意志性的介入,对于真理的探究可能会转化为我们的意志的表达。宋代哲学家朱熹在与湖湘学者往来谈论“中和问题”“性善恶”问题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湖湘学者不能平心静气地面对与自身传统相反的理论,最后导致双方的讨论转化为一种意气之争。这就丧失了探寻真理的本意。
融贯论产生的一个困难是:如果赞同外在事实的输入,那么它就不能赞同内在的结构性,或者至少不能坚持一种强的结构性。内部知识结构应该松散化,甚至不要求逻辑的一致性,如既可以相信Q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又可以相信Q是真心悔过,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Q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或者Q是真心悔过的话。“就事论事”要求:如果Q的事实没有出现,那么我就无法对Q做出明确的判断,而不是以意志的手段去决定Q。
我们赞成的内部知识是一种弱的结构性关联,一个“例外”的出现足以引起我们重组内部知识结构。我们仍用Q的事例“Q救了小孩”,这一事实是真的。这个事实牵引观察者关于Q的内部知识结构的变化,从而重组内部知识结构。一开始我们可能知道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Q救了小孩”的事实得到验证后,“Q是一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Q是真心悔过”等相关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Q是真心悔过”转化为显著性信念,反之亦然。
事实“牵引”内部知识结构的变化,而不是诉诸主体的意志,这点坚持了金岳霖的客观性的传统。在面对事实时,进行客观的、真的反映,以及依据事实而调整内在知识结构。尤其是在科学研究中,一种“例外”(黑天鹅)的出现有可能导致旧的理论体系信念的崩溃,如物理学史中的“电子的发现”“放射性的发现”“以太漂移”“黑体辐射”,如果固守旧的理论结构,那么就有可能在维护旧的结构的意志行为中故意忽略这种“例外”,或者以一种扭曲的理论来解释“例外”。虽然融贯论强调了对于已有知识结构的尊重,但是它忽略了旧有结构的解释力量的有限性和可突破性。而“就事论事”的实在论表达了对于事实的尊重,强调事实对于知识结构的检验,客观的事实对应于客观的知识结构。如果事实本身对原有结构构成了挑战,那么坚持事实所提供的真理而放弃原有知识结构,或者重建知识结构,像物理学史上从经典物理学转化到现代物理学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