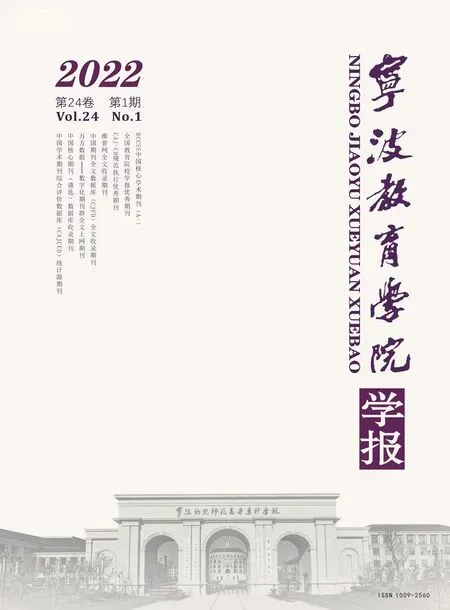“工匠精神”融入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
王雁茹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鹤琴学前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336)
一、“工匠精神”的溯源与解析
(一)“工匠精神”的生成溯源
“工匠”一词扎根于世界文明的土壤中,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是全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有诸多的典籍言及“工”“匠”,如《说文解字》曰“工,巧饰也”。《说文解字·匚部》曰:“匠,木工也。”《辞海》中将其释义为:“工,匠也。凡执艺事成器物以利用者,皆谓之工。”[1]在中国古代“工匠”一词主要是指拥有手艺的劳动者,“工匠精神”的内涵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重技”,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艺;二是“致善”,追求完美,达到完满的境界;三是“悟道”,一方面指尊师重道,尊敬师傅;另一方面指依循做人做事的规律。在西方文化中,“工匠”一词来自拉丁语,由最初的“Ars”逐渐演变为“Artisan”,由最初的靠出卖体力换取报酬的劳动属性逐渐演绎为工匠或手艺人的意思。西方世界的“工匠精神”一直从古代延续至今,一以贯之的在社会中发挥着精神引领作用。希腊哲学的职业化促进了希腊民族思辨精神的发展,使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2]。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至善,正确的思维是正确的行动所不可缺少的。美德对人有利,一切诚实和有用的行动的趋向会使生活无痛苦而快乐[3]。柏拉图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非利唯艺的纯粹精神,工匠集中毕生精力钻研一门工艺,精益求精,追求作品自身的完美是工匠制作产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亚里士多德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至善尽美的目的追求,是工匠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古希腊“理智、思辨、实践”的哲学精神始终对西方社会不同时代的“工匠精神”产生着浓厚的影响。
(二)“工匠精神”的构成解析
“工匠精神”首先是一种精神范畴,它是从业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追求,是一定人生观影响下的职业态度、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职业理想,是一种职业精神。同时,“工匠精神”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环境造就了“工匠精神”不同的价值意蕴,时代的更迭变迁赋予“工匠精神”相应的时代内涵[5]。国外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工作内在价值的精神追求、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创新性思维三方面[6]。中国古代的“工匠精神”主要表现为尊师重道、知行合一、德艺双馨等精神特质。要使“工匠精神”能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必须赋予“工匠精神”丰富的时代内涵与本真的社会价值。与时代变化和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工匠精神”表现为:精益求精、细致严谨的专业精神,专注执着、爱岗敬业的职业态度,乐于奉献、勇于创新的人文素养[6]。“工匠精神”所强调的职业能力与素质远远超越“实用与够用”的范畴,爱岗敬业是大国工匠们的共同特征。从感性层面,爱岗敬业表现为热爱自身岗位;从理性层面,爱岗敬业表现为对职业价值的认同[1]。
二、“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的结构与内涵
“核心素养”这一概念舶来于西方,指一系列可迁移的、多功能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集合,是每个人发展自己、融入社会和胜任工作所必备的21 世纪的关键素养,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素养,其产生的背景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了应对21 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7]。高职大学生作为准职业人,其核心素养应具有社会人和职业人的双重属性,具体包括专业基础、自主发展、社会适应三个层面。专业基础具体体现为专业底蕴与敬业精神;自主发展具体表现在学会学习与健康生活;社会适应表现在责任担当与实践创新[8]。“工匠精神”表现为精益求精、细致严谨的专业精神,专注执着、爱岗敬业的职业态度,乐于奉献、勇于创新的人文素养。“工匠精神”作为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体系中指向职业素养的核心要素,其所强调的专业精神、职业态度与人文素养融合在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各要素之中。
三、“工匠精神”融入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的价值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说:“职业教育是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者也。施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联络,受教育者对于职业应有极端的信仰。”[9]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具有高尚的职业精神、精湛的职业能力、虔诚的职业态度的学生,引导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将“工匠精神”融入核心素养教育,既能够丰富核心素养教育的内容,也有利于“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一)“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与深度融合,要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而职业教育内涵发展一靠以产教融合为依托不断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治理体系,二靠构建现代化教学体系来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10]。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作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追求的目标,其对人才培养的专业基础、自主发展、社会适应做出明确界定。“工匠精神”融入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是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培养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战略需要。
(二)“工匠精神”是职业素质涵养的核心与抓手
在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中,职业素养教育因教育内容的不明确而沦落于边缘地带。而职业素养又是高职生必备的核心素养,课程作为承载职业素养教育的载体,其具体内容散落于思政课、社团活动、就业指导课、心理健康课等课程中,这必然导致目前高职大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的目标不清晰、课程无定式、教育无体系的尴尬局面。“工匠精神”作为一种职业精神,作为职业素质教育的核心与抓手,这种精神的培养与养成可为陷于困境中的职业素质教育提供一个“阿基米德支点”。用“工匠精神”的培育作为高职大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的切入点,以“工匠精神”的内涵为核心来组织实施高职院校的职业素质教育,由此可以解决职业素质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最终通过“工匠精神”的培养这个支点逐步完善高职院校的学生职业素质教育体系[11]。
(三)“工匠精神”是社会价值的指向与回归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但我国制造业要想在工业4.0 时代迎头赶上欧洲发达国家,亟需高校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毕业生,亟需企业发扬“工匠精神”,由人口红利专向人才红利。“工匠精神”本质上是职业诉求与产品诉求的统一,是职业技术技能与职业理想信念的结合,是“做人”与“做事”的有机融合,是“德”与“才”的完满结合。所以,“工匠精神”融入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社会价值的一种回归。
四、“工匠精神”融入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的路径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对系统内各要素的不断优化。对教育系统进行优化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对于融合“工匠精神”的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而言就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入手,发挥合力。
(一)政府推动:政策引领核心素养教育
近年来“工匠精神”由于国家的重视与提倡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工匠精神”的内涵、构成要素、实践路径等仍不明确。核心素养作为目前世界改革的潮流与风向,培养具备核心素养的高职大学生自然是高职教育的目标与追求,但符合高职大学生特征的核心素养是什么、如何培养等问题仍是困扰教育界的难题。既然“工匠精神”与高职大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那么政府主导制定系列政策制度来规范指向“工匠精神”的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的体系与标准,将会为职业院校指明努力的方向与追求的目标,使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成为可追求、可衡量、可检验的知识、技能与态度的集合。
(二)教育支撑:重点推进核心素养教育
1.构建指向核心素养的课程体系。高职院校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首先,是开发系统的核心素养课程。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包括不同纬度多个要素,高校教务处可以通过对各要素各指标的分析与提炼,形成系列课程,由专职或兼职教师讲授,如企业优秀工匠的系列授课来强化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其次,将核心素养相应内容融合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当中。如团结合作精神、执着坚守的品质等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课作为载体来培养。再次,在专业课程中渗透核心素养的相应内容。核心素养区别于普通素养对高职生有共性要求,这些要求可以通过一些专业课程来渗透,通过恰当的方式渗透相应的核心素养内容不仅可以达到熏陶学生优良精神品质的目的,也可以使单调的专业课程更为丰富生动。
2.培养合格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教育者作为教育要素中重要的一环决定着教育目的的达成度。教育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的一方面表现为教师本身是教育的手段,教师的言行举止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因此教师队伍是否品德高尚、是否为双师型教师、是否具有“工匠精神”、是否能够以自身表现生动诠释“工匠精神”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认知与态度,最终影响学生的行为。
(三)文化浸润:情感体验浸润核心素养教育
文化的作用在于潜移默化地熏陶人,使处于这种氛围中的人无形中接受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人是社会性动物,人在社交活动中被别人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别人。政府倡导什么品德、社会颂扬什么品德、民众拥护什么品德就会自然影响个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由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中,我国人民受“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的影响,社会大众对工匠的接纳度较低,工匠成为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工匠精神也一度失落。因此,要倡导“工匠精神”首先就要引领尊重“工匠精神”的社会文化的形成,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人都有被认可、被尊重的需要,在被尊重、被认可的氛围重拾失落已久的“工匠精神”才会成为可能。
(四)校企合作:实现核心素养的知行合一
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是使学生在校期间所掌握的知识升华为情感、落实到行动中的重要手段。核心素养是知识、能力、态度的集合,单纯拥有丰富的知识,而没有实践能力、敬业精神、探求品质的学生依然没有达到核心素养所要求的素质,而后者需要在一线锻炼中才能得以形成。因此,加强校企合作深度融合的力度,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机制成为指向“工匠精神”的高职大学生核心素养践行的前提。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可以为学生搭建核心素养历练与检验的平台,在企业实践一方面可以继续完善核心素养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在检验学校核心素养培养当中有无缺失,并进行弥补。